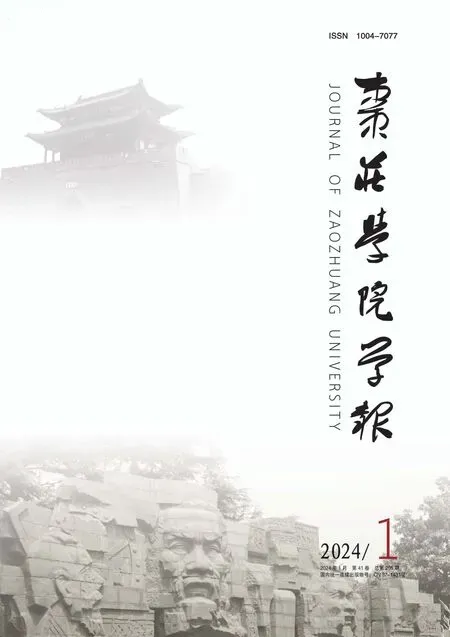由創作地與賦作中心地的離合論漢賦的頌諷怨娛功能
鄧 穩
(四川師范大學 文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8)
孔子認為士人應“謀道”不“謀食”,所謂“學也,祿在其中”[1](P346),即強調通過學習而得“道”,為此還總結出多條仕宦干祿的技巧。創作地與籍貫地分離的現象,即為賦家以學習所得之“道”尋求干祿途徑的反映。然而,孔子亦言“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1](P143)“君子憂道不憂貧”[1](P346),這里的“義”“道”實為士人在學習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對國家政治、個人倫理、社會準則等一系列自我理想化的認識。馬斯洛理論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愛和歸屬感(Love and belonging)、自尊(Esteem)和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五類,并依次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排列。[2](P18~29)賦家以作賦而出仕或者升遷,當然屬于滿足基本物質需求甚或個人價值自我實現的范圍。但中國士人與現代西方以個體為基石或核心的價值觀畢竟不同,他們除了實現自我價值之外,還有對國家、君主應當如何的教導責任。當賦家用這樣一種觀念來作賦,頌美與諷諫自然成為賦篇的應有之義。清人程廷祚《詩論》即認為:“漢人言詩,不過美刺二端。”[3]卷二這里的“刺”不是今天常用的“諷刺”義,而是“諫正”“諷喻”的意思,故本文把“美、刺”稱作“頌、諷”。漢賦頌美、諷喻的功能是賦家對幕府主、皇帝乃至國家充滿希望時采取的積極行動。當這些改造性的積極建議未被采納,賦家通常仕宦受阻、情緒低落,由此產生一種憤激現實或自怨自艾的情緒。發之于賦,則使賦具有疏導情緒的怨的功能。由失望走向絕望,賦家由政治中心走向個人世界,仲長統《樂志論》所構建的“仲長園”式生活成為士人新的生活模式①,賦體文學自娛自樂的功能逐漸得到體現。概而言之,賦體美刺功能多使用在賦家居于或趨近政治中心之際,而怨娛功能則多使用在偏離政治中心或打算偏離之際,兩者皆可以由賦篇創作地及賦作中心地窺探一二。如果仔細梳理賦體流變的歷史,也會發現漢代大賦、言志賦、行旅賦、抒情小賦的流變與漢賦創作地、賦作中心地以及賦體頌、諷、怨、娛功能也有一定關聯。
一
中國歷代社會的政治中心多在京師,中國疆域版圖的政治表現即為以京師為中心的內聚模式。如果把京師及其附屬區域看作一個整體稱為京畿,則西漢、東漢、建安三個時期賦家賦篇的創作地、作品中心地呈現相應的變遷,以此可以考察漢賦美刺功能的具體內容、實施過程。
武帝之前的賦作,岡村繁《周漢文學史考》據史實歸納為:“其間首先是由附從于漢高祖的北楚出生的陸賈、朱建等,將一種與中原歌謠形式相混合的變形了的北楚系辭賦帶入了長安宮廷。這種辭賦所形成的風格在長安似乎一直持續到文景時代。另一方面,相對于北楚系辭賦的、可稱為辭賦文學策源地的江淮地區,則基本上直接繼承了楚國歷來的辭賦傳統。”[4](P133)在長安的北楚系辭賦家由于漢初皇帝需要休養生息并未以賦篇上奏,所以不能作為賦篇美刺功能的考察對象。江淮地區由吳王劉濞集團、梁孝王劉武集團、淮南王劉安集團組成,留下賦篇創作史料較多的僅限于梁孝王劉武集團,今以此略加分析。
漢賦由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創作的楚國宮廷文學漸次演化而來,如以《西京雜記》所載諸賦而言,梁孝王時這種供貴族娛樂性質的文學集中在以日常生活中的器物頌美主人,尚未境界遼闊。如枚乘《柳賦》頌梁孝王“君王淵穆其度,御群英而玩之”,而表自己忠心為“小臣莫效于鴻毛,空銜鮮而嗽醪”[5](P174)。甘心被“玩”還自卑為“鴻毛”之效,可見這時賦家還未有較為強烈的個人意識。鄒陽《酒賦》“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5](P181~182)之頌也僅停留在對諸侯王個人的逢迎,鄒陽代韓安國所作《幾賦》亦以“君王憑之,圣德日躋”[5](P190)草草結尾。路喬如《鶴賦》“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5](P178)、公孫詭《文鹿賦》“嘆丘山之比歲,逢梁王于一時”[5](P179)、公孫乘《月賦》“月出皦兮,君子之光”[5](P187)、羊勝《屏風賦》“藩后宜之,壽考無疆”[5](P189)皆是一個套路。這時期的賦篇集中創作于主人的宴會,賦篇雖沒有明確的中心地,但指向皆是供給自己生活的恩主。
枚乘《七發》較為特殊,張銑論《七發》主旨:“梁孝王時,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諫之。”[6](P524)是知,《七發》創作地在梁國,賦篇中心地亦為梁國,不過其創作意圖與鄒陽、枚乘幾次上吳王書相仿,意在諷喻梁孝王保持諸侯王國的本分。不過,筆者認為:“枚乘《七發》設‘楚太子’與‘吳客’以戒‘膏梁之子’,實為對諸侯驕奢的譎諫,其時諸賦家雖對東方諸侯僭擬天子有所批評,但囿于(‘封建迷夢’),對天下一統、天子獨尊尚未有清晰認識。”[7]
漢武帝大力推廣漢賦創作,曾要求各地奏獻賦作,《漢書·藝文志》“賦略”中帶有官職的賦家賦作創作地基本上系其居官所在地,因為“奏御”的關系,賦文本的描寫中心似也應多集中在漢皇所在地長安。據筆者統計,漢武帝至西漢末期有司馬相如、枚皋等賦家36人比較明確地在京師長安有作賦行為,占同期賦家總數52人的69%。像莊助、朱買臣等雖被征召到長安,但沒有明確史料證明其在長安有過賦作,未列入36人的行列;陽丘侯劉隁、陽城侯劉德、廣川惠王劉越等諸侯王既可能在長安獻賦亦可能于封國奏賦,也未列入36人的行列。因此,該時期于長安作賦的賦家占總數的比例應該略高于69%。這時期賦作中心地可以明確系在京畿長安或賦文反映長安京畿人物、事件(如搗素、蓼蟲等普遍性事、物不計入其中)的賦家賦作有: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哀秦二世賦》《大人賦》《長門賦》、枚皋《平樂館賦》《皇太子生賦》、莊蔥奇《茂陵賦》、劉徹《李夫人賦》、孔臧《諫格虎賦》、東方朔《皇太子生賦》《平樂館賦獵》、王褒《洞簫賦》《甘泉宮賦》、劉向《請雨華山賦》、揚雄《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劉歆《甘泉宮賦》、桓譚《仙賦》共計11人20篇。此一時期賦作中心地較為確定不在長安的賦家賦作有:司馬相如《美人賦》《黎賦》《魚菹賦》《玉如意賦》《梓桐山賦》、劉勝《文木賦》、揚雄《蜀都賦》、劉歆《遂初賦》共計4人8篇。其中,司馬相如、揚雄、劉歆三人皆曾在京畿及其他地方創作以各自地方為題材的賦作,因此在賦作中心地比較明確的此時期賦家賦作中,只有中山靖王劉勝一人在魯國創作《文木賦》。據這些殘缺信息統計出來的數據,可以推論這一時期在長安作賦描寫或頌揚京畿長安事、物的賦家約占總數的92%,賦作中心地在京畿長安或反映京畿附近人物、事件的賦作約占總篇數的71%。賦家于長安創作大量有關京畿事物的賦篇行為,反映出這一時期的賦體文學仍然帶有較為濃厚的宮廷文學特色。
司馬遷認為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8](P3073),又評《子虛上林賦》“其卒章歸之于節儉,因以風諫”[8](P3002);自荀悅《孝武皇帝紀》再次認定“《子虛》《上林》皆言苑囿之美,卒歸之于節儉,因托以諷焉”[9](P163)后,歷代士人皆以戒諫武帝節儉為該賦主旨,且認同揚雄對諷諫效果的批評:“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10](P2609)筆者認為《子虛上林賦》的創作主旨是頌揚漢朝正在逐漸加深的大一統政治局面,且頌揚角度與梁王集團的個人主義頌揚角度不同,已經提升到國家統一的層面:
《子虛上林賦》“奏之天子,天子大說”既是君臣間的契合,亦是“非常之人”對中華民族統一的把握與塑造。以此觀之,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封禪文》對華夏民族統一精神的頌歌與完型作用尚有待重新闡釋。[7]
司馬相如賦的頌美常常具有前瞻性,即以一個政治家、戰略家的眼光看待漢朝統一的發展趨勢以及應采用的形式。漢武帝欲開西南夷,巴蜀士民多有苦其勞累而抱怨逃脫者。司馬相如為漢朝兩次出使蜀郡,分別撰有《喻巴蜀檄》《難蜀父老》二文。《漢紀》[9](P183~185)《資治通鑒》[11](P587~596)把唐蒙、司馬相如通“西南夷”的所有行動都系在元光五年(前130),《劍橋中國秦漢史》則將其系在建元六年(前135)[12](P436~437)。《難蜀父老》開篇云“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集解》引徐廣注云:“元光六年也。”[8](P3049)熊偉業《司馬相如研究》以為“漢興七十有八載”的意思“不當是紀年,而應是計年,應該按周年計算”,因此認為司馬相如第二次出使西夷的時間應在“元光六年春到元朔元年”[13](P109)。即以最遲的時間元朔元年(前128)定《難蜀父老》文的寫作時間,則司馬相如第一次出使所作《喻巴蜀檄》必早于元朔元年。今觀其文:“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后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8](P3044)考漢武帝朝首次向匈奴挑戰始于元光二年(前133),此次未斬匈奴一將,遂把首謀者王恢下獄,使其自殺,可見未有任何戰功。而首次大敗匈奴的戰役應為元朔二年(前127)的河南之戰,打通河西要道的戰役則是元狩二年(前121)的河西之戰。因此,《喻巴蜀檄》言匈奴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皆想象之辭,在當日并無事實。但這也并不是司馬相如信口雌黃,其實應該是司馬相如或者說漢武帝與大臣、謀士日夜策劃反擊匈奴的戰略方針。事實證明,漢武帝一朝最終確實完成了匈奴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的宏偉目標。《難蜀父老》云:“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乃臻厥成,天下晏如也。”[8](P3050)以司馬相如為代表的賦家正是那個激情昂揚時代產生的富有勇氣而偉大的國家理想政治模式的構想者。
司馬相如在賦中不僅大力頌揚漢朝“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始”[8](P3041)的空前盛況,還虛擬“游乎《六藝》之囿,鶩乎仁義之途”[8](P3041)“德隆乎三皇,功羨于五帝”[8](P3042)的儒家理想治世模式。這些狀態在司馬相如作賦的時候根本沒有達到,但《子虛上林賦》如此歌頌實有相當的根據。早在漢文帝之時,賦家賈誼即倡導改制度、易服色:“誼以為漢興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10](P2222)賈誼的建議曾得到漢文帝的認可,只是因“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8](P2492)才沒有及時施行。司馬相如在該賦中再次頌揚漢廷改制的盛況,不能僅看成是迎合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其實也正是時代潮流的必然需要。錢穆曾論及這一潮流:
(武帝一朝之政治)首當及其對于郊祀、封禪、巡狩種種典禮之興復。當時政治上實際問題,最大者厥為社會貧富之不均。而武帝政治措施,于此全不理會,最先即及郊祀、封禪、巡狩種種典禮之興得者;此由其時學者間共同信仰,太平景象之特征,定有一種天人交感之符兆。故遂于無形中造成一種觀念,即努力于促現此種天人交感之符兆,亦即為造成太平之階梯。[14](P94)
“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始”乃與倡導封禪為一體兩面的事件。武帝封禪之達成與司馬相如有莫大關系,錢穆亦認為:“是武帝之慕神仙,行封禪,其意亦由辭賦之家助成之。”[14](P99)至于《子虛上林賦》倡導以《六藝》使天下“向風而聽,隨流而化”更是與董仲舒三策之主旨相吻合: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0](P2523)
兩相校閱,是知司馬相如與董仲舒等皆主張以《六藝》統一思想并以其為治國之理想。這些措施雖有鉗制思想的弊端,但當日在提升國民文化素質、塑造中國士大夫階層上自有其不可磨滅的意義。
誠然,揚雄批評“靡麗之賦,勸百諷一”,或為事實,但也要看賦家所勸為何。司馬相如勸漢武帝封禪、改制,漢武帝以此勵精圖治,在綏撫閩越、教化西夷、橫掃匈奴、溝通西域之后,始行封禪、改制,就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勢而言,豈能說沒有絲毫的意義?然而,任何“非常之功”皆“始于憂勤”[15](P417上欄),是以《子虛上林賦》從假設“天子茫然而思”的悔悟角度來頌揚漢武帝“與天下為始”的德教武功。當我們把宋玉賦家群體、梁孝王賦家群體與以司馬相如為代表的漢武帝賦家群體放在同一個歷史維度觀看,三者雖同近于宮廷文人,但所頌大小、層次不可相提并論。司馬相如之賦頌美、諷喻合而為一,不但融入了賦家個人對國家政治、民族發展的理想,而且其本身也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趨勢,這實際上已經完成把賦作為弄臣的宮廷文學地位提升為有益社稷的廟堂文學地位的轉變。
二
司馬相如之后,西漢唯揚雄《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比較鮮明地體現頌諷精神。據《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明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10](P3522)“初,雄年四十余,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吏,薦雄待詔,歲余,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并”[10](P3582)知,揚雄在京師至少閑居一年以上才因奏《羽獵賦》獲得“除為郎,給事黃門”的身份。這一年應該給了他很多關于漢朝政局及皇宮的重要信息,因此當他獲得侍從漢成帝游而作賦的機會,便文思泉涌,一口氣寫下四篇賦作表達自己對漢皇及國家政治的意見。《漢書·成帝紀》載:
(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宮,賜從官。[10](P326~327)
《漢書》揚雄本傳“上方郊祠甘泉泰畤”的“方”字既可理解為“剛剛”,又可理解為“將要”②。據《漢書·揚雄傳》載隨漢成帝郊祠甘泉宮的趙昭儀“是時趙昭儀方大幸”[10](P3535)以“方”字為“剛剛”義,同傳載揚雄《校獵賦》“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以“方將”合稱為“將要”義。故本文暫定“方”字為“剛剛”的完成義,則據四賦前的介紹文字可定其創作時間為:《甘泉賦》元延二年春正月、《河東賦》元延二年春三月、《羽獵賦》元延二年冬十二月、《長楊賦》元延三年。據《成帝紀》元延二年冬十二月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而《長楊賦》主要論述胡人與校獵之關系,《揚雄傳》卻言“明年,上將大夸胡人以多禽獸”,兩者之間頗有矛盾。但《羽獵賦》《長楊賦》賦作中心地皆為長楊宮,只不過一從漢成帝角度寫校獵,一從胡人與校獵關系立論,雖然時間上或有短暫的先后關系,但其實是一項較長校獵活動的不同部分。這四篇文章雖通篇不離頌美,但皆有明顯的諷喻成分:
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且為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眾,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10](P3534)
顏師古注云:“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10](P3583)以此觀之,揚雄自以為《甘泉賦》有兩主題:一是諷喻甘泉宮的奢泰過甚;二是諷喻漢成帝寵幸趙昭儀而破壞齋肅之事。第二個主題應該是漢成帝的癥結所在,《漢書·成帝紀》載元延元年,即揚雄扈從行幸甘泉的前一年,“昭儀趙氏害后宮皇子”[10](P326)。因此,揚雄以此諷喻漢成帝算是對癥下藥。第一點,筆者則認為揚雄是以自己所理解的儒家君王的理想道德模范來責全漢成帝。社會在不斷發展,揚雄卻在諷喻甘泉宮非“木摩而不彫,墻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棌椽三等之制”,難道真要漢皇和漢代臣民回到“小國寡民”的時代去么?《漢書》本傳所載,或者說揚雄自選的另兩篇賦,皆意在諷喻漢皇回到遠古時代的節儉風氣:《校獵賦》借漢成帝校獵“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后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10](P3541),《長楊賦》諷漢成帝縱胡人校獵使“農民不得收斂”[10](P3557)。其實,這一諷喻或許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是漢成帝之世的癥結所在。當時社會莫大于兩病:一為漢朝社會的貧富分化問題,一為漢皇及宗室權力旁移外戚。錢穆論曰:
蓋漢自昭、宣以來,休養生息,元氣漸復。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不啻武帝之全盛。元、成因之,未能有所制限。社會財富,一任其自然為發展,自易走入鉅富、極貧之境。時雖中朝一統,外無強國,而外戚淫放,則較往者封王亦不殊。于是前朝賈、晁、董生扼腕嘆息之現象,乃一一重見。[14](P283~284)
如果考慮到揚雄四大賦問世后不到二十年時間,王莽已篡漢自為,揚雄所諷之小大自然不言而喻。然而對于揚雄又是情有可原的。蓋自武帝朝始,“更化復古之聲,一時而起”[14](P85),“自宣帝以下,儒者漸當路。至于元、成、哀三朝,為相者皆一時大儒”[14](P187)。在儒者一統的大背景下,士人乃至皇帝皆深受其熏染。以成帝而言,亦有幾種言行屬于儒家君王范式。
一為鼓勵直諫、善于自責,《漢書·成帝紀》載有如下幾條:
(建始三年)冬十二月申朔,日有蝕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曰:“……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乃戊申日蝕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后言。’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10](P307)
(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蝕之,既。詔曰:“朕獲保宗廟,戰戰栗栗,未能奉稱。傳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為之蝕。’天著厥異,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輔不逮。百寮各修其職,惇任仁人,退遠殘賊。陳朕過失,無有所諱。”[10](P309)
(鴻嘉二年三月)詔曰:“古之選賢,傅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無廢事……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余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數困于饑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乃招賢選士之路郁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10](P317)
(元延元年秋七月)詔曰:“乃者,日蝕星隕,謫見于天,大異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與內郡國舉方正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10](P326)
上述幾條漢成帝詔皆一方面謙讓自責,另一方面不僅敦促在位公卿大臣、博士、議郎還要求共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陳朕過失,無有所諱”。
一為時有節儉之行為:
(建始元年)秋,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10](P304)
(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10](P304)
(永始元年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10](P320)
成帝盡力保持自我節儉以為天下先,實際是針對當時社會奢侈之風甚囂塵上而發,其永始四年(前13)六月詔即云:
又曰:“圣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新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列侯近臣,各自省改。也隸校尉察不變者。”[10](P324~325)
這種奢侈逾制的行為不僅威脅到皇室的權威,更讓大多數百姓失去土地、流離失所,造成社會的極度動蕩。因此,“一時不者,如王吉、貢禹之徒,乃復盛唱‘制節謹度’之議”[14](P284)。
現在我們來看揚雄四賦的頌與諷。第一,因為創作地、賦作中心地皆在長安,甚至就在宮廷左右,揚雄四賦對大漢的基調是頌美。第二,由于儒家諷諫精神進一步內化為士人的自覺行動,賦家也更加自覺地利用賦體表達自己對國家乃至君王理想模式的認知,諷喻是其中的一種重要方式。第三,面對新的社會矛盾,上至漢皇、公卿大臣,下至賦家及一般士人,并沒有有效的解決方案,大家不約而同地拾起復古的道德模式化的救治方案,換言之,賦家在賦中的諷喻在“直言極諫”上往往還沒有漢皇詔書來得直接,這種微弱的諷諫行為往往成為對漢皇納諫的頌揚,所以揚雄首奏《甘泉賦》,“天子異焉”;后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第四,漢賦頌、諷功能合二為一,皆是賦家在對漢皇、國家有信心時積極參政治改革的表現。第五,西漢成、哀之際,漢朝積弊深重,已不可能挽大廈于將傾,此時的賦家必然會對漢賦頌、諷功能產生懷疑、指責。揚雄后來即認為:“以為賦者,將以諷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于正,然覽者已過矣。……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10](P3575)揚雄的心態可能是司馬相如完全不能理解的。時已至此,豈獨賦勸而不止呢?
東漢京師定于洛陽,賦篇創造地、賦作中心地迅速集中在洛陽及其附近。其作明確在洛陽有過創作的賦家有馮衍、杜篤、傅毅、崔骃、班固、班昭、李尤、李勝、葛龔、張衡、馬融、王逸、崔琦、崔寔、高彪、韓說、鄧耽,共計17人,約占東漢賦家總數52人的33%,約占至少有一個創作地可以確定的東漢賦家總數27人的63%。賦作中心地在洛陽或賦文反映洛陽事件、事物的賦有:杜篤《祓禊賦》、傅毅《洛都賦》《反都賦》《神雀賦》、崔骃《反都賦》《大將軍臨洛觀賦》、班固《兩都賦》、班昭《大雀賦》、李尤《函谷關賦》《辟雍賦》《德陽殿賦》《平樂觀賦》《東觀賦》、張衡《二京賦》《羽獵賦》、崔寔《大赦賦》、鄧耽《郊祀賦》,共計9人17篇;賦作中心地明顯未在洛陽的有:班彪《覽海賦》《北征賦》《冀州賦》、杜篤《論都賦》《首陽山賦》、崔骃《武都賦》、班固《終南山賦》《覽海賦》、班昭《東征賦》、張衡《溫泉賦》《南都賦》、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邊讓《章華臺賦》、蔡邕《述行賦》《漢津賦》,共計9人15篇,則東漢時期現存可以判定以洛陽為賦作中心的賦作約占賦作中心可以確定的賦篇總數32篇的53%。同時以長安及附近為賦作中心地的賦篇急劇減少,唯有杜篤《論都賦》、班固《終南山賦》、張衡《溫泉賦》三篇,其中杜篤《論都賦》雖以頌美長安為主,但卻于洛陽上奏東漢皇帝,其他兩篇賦也不再以天子禮儀頌美長安。因此,隨著政治中心的轉移,賦家賦作的中心地或者說象征皇權的漢賦景觀發生了變化。關于論都等大賦前人論述已多,其諷頌方式也與西漢略相仿佛,暫不討論。拙文《由京都賦看王城居中的觀念》已對賦家如何在一篇賦文中將京畿附近乃至整個天下版圖內聚在京都的方式作過簡略探討[16],亦無需贅言。
盡管在實際的昆曲唱調(以下簡稱“昆唱”)中,三節以上的多節型過腔已屬少見,但形式多樣的過腔結構及其架構,讓我們看到了“昆唱”繁復的變幻和廣闊的發展空間。實踐證明,過腔的功能是發展和結構“昆唱”,豐富、提高、拓展“昆唱”的表現力,保障昆曲既唱又嘆基本特色永不衰敗的內動力和基石。
漢賦頌美的功能往往還以一系列賦作完成對京畿附近景觀的王權重塑來實現。李尤《函谷關賦》《辟雍賦》《德陽殿賦》《平樂觀賦》《東觀賦》是一個典型。李尤,巴蜀文化區廣漢郡人,不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其賦有司馬相如、揚雄之賦,召至東觀受詔作賦,以此拜為蘭臺令史。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劉珍等俱撰《漢紀》。順帝立,遷為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李尤五賦可能作于召至東觀受詔作賦時期,因為正當壯年,又值仕途光明之際,這五篇賦作皆為頌圣之制。與《子虛上林賦》等精心構思的宏大體制不同,李尤五賦雖皆為殘篇,但由殘文亦可看出每篇賦皆聚焦在京畿的某一個重要地點,全篇結構簡單清晰。函谷關本秦關,為東西方的鎖鑰,但當洛陽為京師,函谷關又肩負護衛京師洛陽西邊的重要職責。《函谷關賦》“惟皇漢之休烈兮,包八極以據中”[17](P376)先以“王城居中”的地理空間描寫方式把函谷關放置在以京師洛陽為中心的王朝地理版圖之中,后文即在此王朝地理版圖中頌揚函谷關的重要意義:“永平承緒,欽明奉循,上羅三關,下列九門。會萬國之玉帛,徠百蠻之貢琛。”[17](P376)《辟雍賦》《德陽殿賦》《平樂觀賦》《東觀賦》皆不是簡單地對某個地方景觀的鋪寫,而是把這些地方景觀置于以洛陽為中心的王朝地理版圖中予以頌揚。因此,李尤將京畿附近的景觀逐一頌揚,實則是想通過一篇篇單獨的賦作構建出一個巨大且神圣的空間來完成對大漢的歌頌。如果把同時代賦作中涉及的相應景觀鉤沉出來,我們就可以借此構建一系列的王朝地理景觀,漢代賦家頌美漢朝的方式也將得到更為全面的認識。
建安時期,戰亂頻繁,雖然形式上有統一的大漢共主,但實際上已漸趨三國鼎立。由于魏武好文,曹操集團產生大量賦作,但該集團的中心不在漢獻帝所都的許昌,而集中在曹操集團的鄴城,因為曹操魏國曾在此短暫定都,姑稱為鄴都。鄴都之上存在著名義上為共主漢獻帝所都的許昌,因此曹氏集團的賦作并沒有以王朝地理的空間形式頌揚鄴都或曹操。曹植《洛陽賦》篇名不僅去掉班固、張衡的“京”字,其殘句“狐貉穴于紫闥兮,茅羲生于禁闈。本至尊之攸居,□于今之可悲”[18](P26)更顯示出其失去政治中心地位備受兵火摧殘的破敗景象。因為鄴都只是權力、軍事中心,并不能算作名正言順的政治中心,其賦多為娛樂性質,這和梁孝王集團的賦作頗為相似。此時真正的賦頌作品,主要集中在撰征賦中。這些撰征賦無一例外地頌美軍隊出征的威武強盛,至于戰爭給賦家及社會帶來的痛苦要由賦家行軍途中的其他賦作來表現。
由于受賦體文學緣起時的性質、功用的影響,頌美甚至逢迎是漢賦一個不可回避的特點,但隨著士人自我意識的覺醒、賦體自身的發展,賦體不僅發展出諷喻的功能,而且也改變單純逢迎的頌為以自己的主觀理想進行選擇性地頌美,這樣就使得頌、諷合二為一,皆成為賦家在仕途光明時以積極樂觀的心態影響、改變漢皇或國家政治的重要手段。賦家創作地點與賦作中心地隨著政治中心的變遷迅速地發生改變,這為探討賦體的流變、性質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三
“學而優則仕”是每個士人求生存、求發展的必由之路,但是“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1](P388)?因此,大批賦家在積極入仕的時候創作飽含頌、諷精神的賦作,而在失意之際寫下深含怨情的賦篇。賦體文學形式的濫觴者屈原即已具有這一特點。屈原早年,“王甚任之”[8](P2481),所作《橘頌》以頌揚橘樹“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19](P125)來表達昂揚向上的入世情懷;后來被讒被疏,則作《離騷》《懷沙》等抒發憤懣之情。司馬遷對屈原這種心情的產生有精彩的論述: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8](P2482)
由“王甚任之”到因“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而作賦,幾乎也成為漢代賦家創作幽怨之賦的全部心路歷程。由于“王甚任之”多發生在國都或京畿,被疏被放則遠離京畿,“至于江濱,被發行吟澤畔”[8](P2486),漢代賦家創作幽怨之賦也大致遵循這樣的創作旅程。賈誼被司馬遷放在屈原傳之后,合稱《屈原賈生列傳》,其人生經歷及作賦經歷與屈原也頗多相似之處,可為漢代幽怨之賦創作面貌的代表。賈誼因廷尉吳公推薦由洛陽遷至長安,“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于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8](P2492)。后為絳、灌、東陽侯等讒間,“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8](P2492)。賈誼于是遠離京都長安,來到南方偏遠卑濕的長沙而作幽怨之賦《吊屈原賦》《鳥賦》,本傳敘其作賦地點與過程如下:
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8](P2492)(《吊屈原賦》)
賈誼遠離政治中心長安,創作地遷至南方長沙,賦作中心亦隨之變成長沙附近令人傷感的人、物,以此可見文學地理要素與幽怨之賦對應的一種典型關系。
董仲舒(前179~前104),廣川(今河北棗強)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武帝時拜江都相,中廢為中大夫,以言災異幾下獄死,后為膠西相。《漢書·董仲舒傳》高度評價董仲舒對漢武帝一朝政治的積極影響:“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10](P2525)劉向也稱其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10](P2526)。其《士不遇賦》通篇皆為怨世、怨己之言。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云:“公孫用世,同學懷妒。出相膠西,謝病自免。怨哉董生,向賦不遇,今其然耶?”[20](P9)萬光治《漢賦通論》引賦文“屈從人意,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不出戶庭,庶無逼矣”認為:“是知作于晚年家居時,張溥所言不確。”[21](P433)以此,該賦的創作時地亦在董仲舒退出仕途于老家閑居之際。
劉歆《遂初賦》亦為幽怨之賦,但與此前同類作品相比又有了新的發展,即形成以行旅途中的歷史古跡作為抒發幽怨之情的媒介。劉歆《遂初賦》創作于外放五原太守途中的故晉之域,《藝文類聚》卷二七載其序云:“(歆)為朝廷大臣所非,求出補吏。后徙五原太守,志意不得。經歷故晉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22](P490)因為遠離政治中心,“志意不得”是劉歆與其他賦家在此情況下共同的感情基調,但其以行旅地名抒發怨情的方式卻很特別。該賦先以象征性的地名敘寫自己入仕之初的顯達:“昔遂初之顯祿兮,遭閶闔之開通。蹠三臺而上征兮,入北辰之紫宮。備列宿于鉤陳兮,擁太常之樞極。總六龍于駟房兮,奉華蓋于帝側。”[17](P231)“遂初之顯祿”展現出士人為求生存出仕的基本目的。“閶闔”一詞借自《離騷》“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19](P25),在賦中代指西漢長安宮門。“三臺”,本系星名,喻指三公,即指劉歆與其父劉向曾領校皇家圖書秘籍一職。“北辰”以星名借指漢皇,“紫宮”以星名喻指長安未央宮正殿。故賦文開篇多以天上諸物喻指自己在西漢長安朝廷中入仕之順遂。賦文以“惟太階之侈闊兮,機衡為之難運。懼魁杓之前后兮,遂隆集于河濱。……行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17](P231)數語,揭示自己受大臣誹謗遠徙五原的背景。后文即鋪敘自己貶徙五原沿途的見聞,因為作者熟知歷史,又欲以歷史諷喻、怨嘆自己的遭遇,遂形成以歷史遺跡抒發怨情的特殊結構。如“劇強秦之暴虐兮,吊趙括于長平。好周文之嘉德兮,躬尊賢而下士。……過下虒而嘆息兮,悲平公之作臺”[17](P231),即以長平(今山西高平)哀悼趙括的覆軍殺身之禍,又以行旅所過之下虒聯想到晉平公因奢侈宮室建筑而帶來晉國的衰敗。賦家一邊行游,一邊聯想此地發生的歷史悲劇,但最終卻把情感聚焦于君臣之不相得、賢士之不得志:“何叔子之好直兮,為群邪之所惡。賴祁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美不必為偶兮,時有差而不相及。雖韞寶而求賈兮,嗟千載其焉合。昔仲尼之淑圣兮,竟隘窮乎陳蔡。彼屈原之貞專兮,卒放沉于湘淵。何方直之難容兮,柳下黜而三辱。……揚蛾眉而見妬兮,固丑女之情也。曲木惡直繩兮,亦小人之誠也。”[17](P232)賦文最后又由歷史地理轉向蕭瑟的自然地理:“山蕭瑟以鹍鳴兮,樹木壞而哇吟。地坼裂而憤忽急兮,石捌破之嵓嵓。天烈烈以厲高兮,廖窗以梟窂。雁邕邕以遲遲兮,野鸛鳴而嘈嘈。望亭隧之皦皦兮,飛旗幟之翩翩。回百里之無家兮,路修遠之綿綿。”[17](P232)因此,《遂初賦》綜合運用象征性地理、歷史地理、自然地理構建由政治中心地遷往貶謫地的整個地理空間體系以抒發賦家不得志的幽怨之情,開啟了一種新的抒情模式。《兩漢賦評注》指出這篇賦在賦史中的地位:“此賦《歷代賦匯》編入‘言志’類,自然是不錯的;但如果我們把它移入‘行旅’類,似乎更合適。……我們可以把它視為行旅賦的首唱。屈原的《離騷》、司馬相如的《大人賦》寫的是神游,此賦則寫人游。隨后班彪的《北征賦》、班昭的《東征賦》、蔡邕的《述行賦》等等,就是在它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23](P300)《遂初賦》列入“言志”類,或列入“行旅”類,皆有一定道理,就其創作地、賦作中心地及綰合賦家創作心態來看,亦可歸入抒發仕宦不得志的幽怨賦之列。東漢特別是建安時期,因仕宦不得志、逃避戰亂等各種原因,賦家于流離遷徙途中所作賦往往皆有這一特點。班彪《北征賦》、班昭《東征賦》、蔡邕《述行賦》、曹丕于行軍途中所作《感物賦》、曹植于行軍途中所作《感時賦》《愁霖賦》皆對賦體文學怨的功能有所表現。
賦體文學誕生于“試為寡人賦之”的過程之中,因此娛樂功能是其產生的原因之一。但仔細分析也會發現,在賦體文學早期的發展過程中,如梁孝王的賦家集團、漢武帝的宮廷賦家集團、漢宣帝的宮廷賦家集團等的賦家所作賦皆為娛樂諸侯王或漢皇,其娛樂功能可稱為娛人,而并非娛己。賦體文學娛己的功能一般不用于政治中心地的奏獻場合,而多體現在賦家遠離政治中心所作的作品之中。這種賦的代表首推馬融《長笛賦》。《后漢書》本傳載馬融“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24](P1972),其《長笛賦》序云:“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又性好音,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獨臥郿平陽鄔中,有洛舍逆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逾年,蹔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賦》。”[25](P249)由序文可知,馬融作《長笛賦》完全出于自己對音樂藝術的愛好,既不為政治而作,也不為他人命賦。馬融《樗蒲賦》《琴賦》《圍棋賦》皆有這一特點,可看作漢賦自娛現象的一個典型。曹丕、曹植與諸文士許多同題共作之賦,大多也具有這一特點。筆者以為,從漢代士人生存方式以及思想潮流的發展趨勢來看,正是士人包括賦家從出仕時的頌、諷漢皇,到不得志時的自怨自艾,才逐漸演變至士人包括賦家作文作賦以自娛的形式。這一歷程既可以看成士大夫階層包括賦家“士志于道”意識的碰壁、衰落,也可以看成士大夫階層包括賦家個體意識的自我覺醒。當然,伴隨這一過程成長起來的是士大夫階層經濟上的獨立,換言之,即漢末莊園經濟的興起。漢末士人仲長統《樂志論》是這一士大夫意識生成的重要標志,其文云: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筑前,果園樹后。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③
“居有良田廣宅”是保障士大夫獨立的經濟基礎,“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是士大夫對仕宦為奴的超越,“游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則是士大夫自我娛樂的形式,賦體文學自娛的功能即與此密切相關。
余 論
漢賦體式,前人多有研究,但分類卻不盡相同。《史記》載“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8](P2491),是可為辭、賦之區分。漢宣帝以漢賦功能分賦為大、小賦:“‘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10](P2829)此雖從意義大小而分,但后世亦有散體大賦、抒情小賦的區別。揚雄“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26](P49)乃從創作效果分類。后世分類,標準不一,所分類別多寡相差巨大。如從文體語言形式分類,則萬光治漢賦三體分類法較為合理,即以荀況賦為代表的四言賦,以賈誼《鳥賦》、淮南小山《招隱士》為代表的騷體賦,以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為代表的散體大賦。[21](P61~115)
如從文學地理學的角度考察漢賦體式流變的形式與原因,則會提供一種新穎的視角。第一,賦體文學在以“不歌而誦”的形式于“試為寡人賦之”的創作環境中真正脫胎出來,因此創作于政治中心地的頌體賦率先出現。這種頌體賦最先出現在楚國或諸侯王國,皆因娛樂因素過重,而體式短小,品格卑弱;進入大一統的政治中心以后,才出現《子虛上林賦》《兩都賦》等“潤色鴻業”的頌體大賦,這類賦氣象宏偉,與學界所分散體大賦相合。第二,隨著賦家個體意識的增強,他們走進政治中心,有著強烈的匡諫意識,諷體賦由是誕生,這種賦常頌中寓諷,故與頌體賦多有相通之處。第三,當諷、頌所要達到的政治理想未能實現,賦家或久不得遷,或遭貶謫,怨自內生,怨體賦由此產生,這類賦多用騷體句式,與學界所分騷體賦相仿。第四,當諷、頌不得,怨亦無助,賦家開始轉向個體的生活方式,自娛自樂的賦作大量出現,其中詠物小賦多屬此類。
雖然所有的賦體創作皆可分列在趨近政治中心或遠離政治中心的范圍之類,但因為漢賦體式形成的復雜性,也不能等而論之。不過,如能綰合賦篇的創作地、賦作展現的中心地來考察漢賦體式的演變,應當會對漢賦體式流變的問題作出一些新的解答。
綜上所述,漢代賦篇創作地、賦作中心地會隨著政治中心的更改而相應地發生巨大改變,但這一改變也往往伴隨著中華民族的大融合以及大一統進程的加深。“體國經野”“潤色鴻業”的漢大賦由此形成,賦這種文體也因此“蔚為大國”。由此似乎可以大膽設想:通過對賦家籍貫、賦篇創作地、賦作中心地合、同、離、異趨勢的考述,不僅可以發現漢賦諷、頌、怨、娛功能形成的原因及其形態特點,還可以突破既往漢賦史研究過于偏重時間敘述的限制,在漢賦發展、演變的時間經線上通過繪制賦家籍貫分布、創作地點圖表等方式織就空間緯線,最終在時空交織的經緯線上考察漢賦興起、傳播、流變的過程與原因,展現漢賦發展的另一個面貌,形成一種嶄新的漢賦史書寫方式。
注釋
①漢末仲長統《樂志論》以其對現實生活與精神生活的理想構建,被后世士大夫尊稱為“仲長園”。“仲長園”是古代士大夫精神生活、現實生活的詩意化理想,故成為多數士大夫的畢生追求。詳參筆者碩士學位論文《“仲長園”現象研究》,四川師范大學,2011年.
②熊良智《揚雄“四賦”時年考》(《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以“將要”義定《甘泉賦》作于永始四年漢成帝第一次郊祀甘泉宮之際,可參.
③嚴可均《全后漢文》認為仲長統這段文字“疑在《自敘篇》,或當以‘卜居’名篇。胡維新《兩京遺篇》題為《樂志論》,而出之《昌言》外,非也”。詳參(清)嚴可均輯,許振生審訂《全后漢文》,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904頁。筆者以為自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廣為傳播,后世文人如王充、王符等著書多有敘傳,今所題《樂志論》極有可能是《昌言》《自敘篇》的一部分,如是則更可證明仲長統在撰《昌言》時即已把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和道家逍遙隱遁的思想完美地結合起來。由于文獻不足,姑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