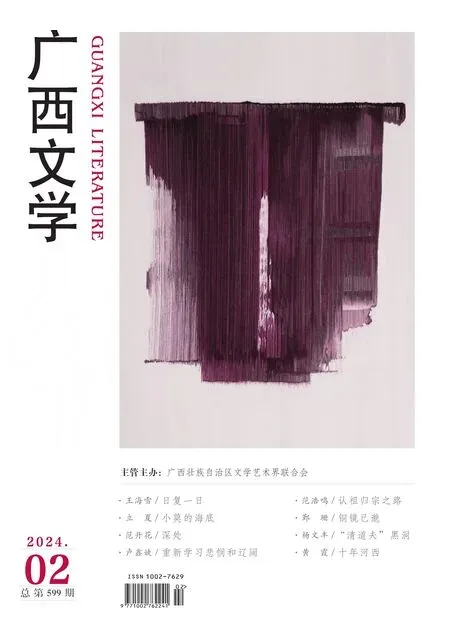心跳,才是一首詩(shī)最好的節(jié)奏
大 衛(wèi)
不敢想象現(xiàn)實(shí)中一個(gè)叫余春紅的人,一轉(zhuǎn)身,會(huì)變成詩(shī)人羽微微。據(jù)不可靠消息,余春紅是一個(gè)數(shù)據(jù)工作者;而羽微微是一個(gè)信手拈來(lái),撥動(dòng)文字像撥動(dòng)算盤珠子的人,三下五除二就把生活給加加減減了。我覺(jué)得羽微微比余春紅更高級(jí)的地方,是把俗世過(guò)出了詩(shī)意,如果余春紅是一朵花,那么羽微微無(wú)疑就是她的最高級(jí)。
我無(wú)意于把財(cái)務(wù)工作者羽微微與土地測(cè)量員卡夫卡和保險(xiǎn)公司高管史蒂文斯相比,我想說(shuō)的是,在這金色的秋日,再次集中閱讀羽微微,是一件特別有意思的事。
在魚龍混雜的當(dāng)下,作為詩(shī)人的羽微微的辨識(shí)度特別高。甚至,可以自信地在羽微微這三個(gè)字之前省去“著名”的。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一提到羽微微這三個(gè)字,會(huì)下意識(shí)地想到那首《約等于藍(lán)》。
不可能一開始,就是藍(lán)。
要若無(wú)其事地泡泡茶,想想別的
打幾個(gè)電話。或者把屋子里的書收拾好
如果外面不是陰天,就站在陽(yáng)光下
假裝是一株薔薇,正在微笑
你知道,美好的事物都是慢慢開始的
不可能一開始,就是藍(lán)。
這首只有七行的短詩(shī),從標(biāo)題到內(nèi)容,都讓人感覺(jué)新鮮。換種說(shuō)法,就是陌生化。文字帶“藍(lán)”的詩(shī)歌標(biāo)題車載斗量,但只有羽微微的這個(gè),給我觸目的印象。“約等于”這三個(gè)字與“藍(lán)”結(jié)合,新鮮感一下出來(lái)了。哲學(xué)家說(shuō),世間唯一的確定就是不確定,作為詩(shī)人的羽微微,她用一首言簡(jiǎn)意賅的詩(shī)告訴我們,約等于藍(lán)才是藍(lán)。
這首詩(shī)的敘述也是得心應(yīng)手,從容不迫,層層推進(jìn),又在結(jié)尾抽絲剝繭。這首詩(shī)還妙在開頭與結(jié)尾都是同樣的一句“不可能一開始,就是藍(lán)”。這種修辭的妙用,實(shí)在非高手不可為也,全詩(shī)才七句,竟然有兩句重復(fù),但你又根本感覺(jué)不到有任何饒舌之處。
這無(wú)形中與帕斯那個(gè)說(shuō)法不謀而合:“可在一首詩(shī)中,第一行詩(shī)包含著最后一行詩(shī),而最后一行詩(shī)又喚起著第一行詩(shī)。詩(shī)是我們反抗直線的時(shí)間——反抗發(fā)展的唯一手段。”實(shí)話實(shí)說(shuō),讀到羽微微這首詩(shī),再對(duì)照帕斯這段話,我是非常吃驚了。同樣作為一個(gè)文字分行工作者,我深知詩(shī)人創(chuàng)作的時(shí)候,是不需要理論的。甚至可以說(shuō),在靈感來(lái)臨時(shí),理論是一種干擾。你看到哪一棵樹是按照植物學(xué)的教材生長(zhǎng)的?這方面歌德看得最為透徹,他在《浮士德》中,借靡非斯特菲勒司之口說(shuō):“一切理論都是灰色的,唯有生活之樹是長(zhǎng)青。”
我注意到羽微微特別擅長(zhǎng)于節(jié)奏的應(yīng)用,她甚至大膽地拋棄了韻律,通過(guò)句子的遞進(jìn)或者反復(fù),來(lái)創(chuàng)造——對(duì),是創(chuàng)造——一種節(jié)奏,這種寫法太有意思了。一般以為詩(shī)歌要押韻,甚至有人以為,韻律是詩(shī)歌的標(biāo)配,如果不押韻就不是詩(shī)。但我以為,這是對(duì)詩(shī)歌的誤解,衡量一首詩(shī)的標(biāo)準(zhǔn)不是押韻與否,而是有沒(méi)有詩(shī)意。相較于韻律,我更喜歡那種節(jié)奏感。
比如這首《聲聲慢》——
什么慢?光陰慢。枝上的雨
從去年的天空來(lái),滴在今年的檐角
什么慢?傷心慢。
慢如霜降。慢如葉落。
什么慢?風(fēng)慢。它吹啊吹——
但風(fēng)只吹人間
天堂寂靜。
什么慢?相聚時(shí)慢。見你來(lái)
又見你來(lái)。又推門,又坐下
又來(lái)和我,沉默了一會(huì)。
全詩(shī)通過(guò)“什么慢……慢”的反復(fù)出現(xiàn),讓詩(shī)歌獲得一種節(jié)奏感,同樣的還有這首《離開》——
開始不是這樣的
開始是人間小。時(shí)間慢。
開始是美好的東西簡(jiǎn)單地美好。不深刻。
開始是青草,玩笑和黃昏
唉朋友,我為貪戀你們的氣息和溫暖
好幾次忍住了憂傷的淚水
開始不是這樣的
開始是,我哭得理直氣壯
哭得受盡委屈
和“開始是……”一樣,接下來(lái)的這一首,多次出現(xiàn)的“仿佛”也讓全詩(shī)產(chǎn)生了獨(dú)特的節(jié)奏:“草那么深,不能再往前行/但時(shí)有引路的蟲鳴/仿佛是在呼喚,逝去者歸來(lái)/仿佛是我,也在這人間,伏著,鳴叫/仿佛也有蟲鳴,呼喚我——/而我沉默。而天色慢慢暗了下來(lái)/仿佛是人間收攏了巨大的翅膀”(《清明》)。讀這樣的詩(shī),你完全感覺(jué)不到技巧什么的,你只能感覺(jué)到真實(shí)的心跳,一首詩(shī)最好的節(jié)奏應(yīng)該是心跳,或者說(shuō),心跳,才是一首詩(shī)最好的節(jié)奏。作為一個(gè)動(dòng)不動(dòng)就押韻的人,我特別欣賞羽微微這種只需一個(gè)詞就能領(lǐng)跑世界的手法。她只讓一束花反復(fù)出現(xiàn),就能獲得春意盎然的春天。
羽微微的這種寫法,讓其詩(shī)歌自然產(chǎn)生音樂(lè)性——哪怕說(shuō)的是“哲理”,她也特別擅長(zhǎng)用深沉的“低音”,這樣讀者就更容易接受。她還有一首流傳甚廣的詩(shī),叫《墓志銘》——
這是我的最后簡(jiǎn)介,我希望更簡(jiǎn)短一些,潔白的
大理石碑上,除了名字、性別、時(shí)間
還應(yīng)該有一句什么?
如果你沒(méi)有其他的想法
我建議就寫上:
她曾深深愛(ài)過(guò)及被深深愛(ài)著
其中的“深深”
不要省略相信任何一個(gè)人都能看懂這首詩(shī),但要真正地理解,可能還需生活的淬煉。這首詩(shī)讀來(lái)非常“松散”——但這種松散是一種自信,是藝高人膽大,是風(fēng)打敗了時(shí)間。我甚至想表達(dá)這樣一個(gè)觀點(diǎn):一首詩(shī)內(nèi)在有多凝練,外在就有多松散。艾青先生對(duì)于那種寫得太緊、太像詩(shī)的詩(shī),不惜提倡“散文化”——我明白艾青先生是想說(shuō),詩(shī)歌要大氣,要放松,要拋棄一切束縛它的東西,詩(shī)歌的“散文化”絕不是把詩(shī)歌寫成散文,而是無(wú)限接近于“大象無(wú)形”“大音希聲”。這讓我想到沈從文先生的散文,充滿了詩(shī)意,是可以當(dāng)作詩(shī)來(lái)讀的。昌耀后期的許多詩(shī)作,甚至直接都是散文的形式。羽微微的詩(shī)歌,在當(dāng)下千人一面的詩(shī)壇,有著鮮明的辨識(shí)度。哪怕把她放在古代,我也能看出,瞧,這就是那個(gè)寫出了《約等于藍(lán)》的人。
寫到這里,突發(fā)奇想,如果放在古代,羽微微是誰(shuí)呢? 這是不好假設(shè)的,哪怕假設(shè)成功了,也是出力不討好的事情。我隨便想了一下,如果放在宋朝,羽微微可能約等于李清照,但李清照酒量很大,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有十六次大醉全記錄,那么羽微微,這個(gè)一笑就有酒窩的人,不知酒量如何?不知她醉過(guò)是否有胡適先生的感慨:醉過(guò)才知酒濃,愛(ài)過(guò)才知情重。
繼續(xù)假設(shè)下去,如果把羽微微放在國(guó)外,不知她是否愿意與辛波斯卡來(lái)個(gè)“約等于”。辛波斯卡有幾首詩(shī)深得當(dāng)下文青與白領(lǐng)的喜歡,比如那首《在一顆小行星下》那著名的幾句——
我為把偶然稱為必然而向它道歉。
萬(wàn)一我錯(cuò)了,我就向必然道歉。
請(qǐng)別生氣,幸福,如果我將你占為己有。
死者,但愿你容忍這一切,我的記憶正在枯萎。
每一秒鐘我都忽視了整個(gè)世界,于是,我向時(shí)間道歉。
我為將新歡當(dāng)成初戀而向舊愛(ài)道歉。
…………
我為桌子的四條腿而向被砍倒的樹木道歉。
我為小回答而向大問(wèn)題道歉。
我想,在李清照與辛波斯卡之間,羽微微只想做余春紅,或者,余春紅只想做羽微微。不管在詩(shī)歌中還是在生活里,她都是特立獨(dú)行的那個(gè)。
如果我把羽微微稱為天才詩(shī)人,估計(jì)余春紅會(huì)第一個(gè)反對(duì),那么,我只能假裝是裁判地嘟囔一句:反對(duì)無(wú)效。特別是當(dāng)我讀到這樣的佳制——
天堂鳥開了,勿忘我開了
紫色薰衣草開了,金色百合開了
美麗的名字都開了
只是不要留意我
我要慢慢想,想好一瓣
才開一瓣
——《花房姑娘》
好一個(gè)“我要慢慢想,想好一瓣/才開一瓣”,這樣的句子,讀之入心而又出神。如果讀出訝異與恍惚也不意外。這種句子,是直擊天靈蓋的。當(dāng)下,讓人記住一首整詩(shī)是很難的,著名如海子者,我們脫口而出的也是那八個(gè)字: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我喜歡的曼德爾施塔姆,也是那句:黃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再諸如木心的:我是一個(gè)在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啊,你再不來(lái),我要下雪了。
比這些句子略長(zhǎng)一些的,是短詩(shī)(也可以理解成加長(zhǎng)版的句子),比如阿米亥的《愛(ài)與痛之歌》:
我們?cè)谝黄鸬臅r(shí)候
我們像一把有用的剪刀。
分手后我們重又
變成兩把利刃,
插入世界的肉里,
各在各的位置。
羽微微不僅僅有出其不意、讓人過(guò)目不忘的句子,整體來(lái)看,她的詩(shī)還透露出某種哲學(xué)意識(shí)。詩(shī)歌就是她的血壓計(jì),生活的收縮壓與感情的舒張壓,她都擅于測(cè)量并告訴我們心跳與脈搏的真相——
輕盈的事物總在拖動(dòng)沉重的
正如靈魂拖著肉體
白云拖著群山
人要穩(wěn)住腳步,才能不被回憶拖走
兒童笑著
小小的身子
裹著時(shí)間的蜜糖
光令萬(wàn)物生長(zhǎng)啊
但光是如此地輕
令樹木長(zhǎng)出重重陰影
也長(zhǎng)出累累果實(shí)
這首名為《萬(wàn)物生》的詩(shī),可以讀出千般滋味。這首詩(shī)的風(fēng)格更舒緩、博大。我很喜歡這種壓低了嗓音的娓娓道來(lái)的抒情,深刻而又節(jié)制。
我曾在北京天橋劇場(chǎng)看過(guò)皮娜·鮑什精彩絕倫的舞蹈,好些年過(guò)去了,舞蹈動(dòng)作模糊了,但皮娜·鮑什那句話卻穿越了時(shí)間,歷久彌新:我跳舞,是因?yàn)槲冶瘋?/p>
對(duì)于詩(shī)人來(lái)說(shuō),寫詩(shī)何嘗不是靈魂在跳舞呢?這兒的跳舞有兩個(gè)意思,一是在塵俗之中,讓自己的靈魂起舞,而且是任何時(shí)候都可以“起舞弄清影”,任何時(shí)候都能以詩(shī)的舞蹈對(duì)自己進(jìn)行靈魂的救贖;二是詩(shī)歌是一種非常講究的藝術(shù),得有基本功,詩(shī)歌不是誰(shuí)都能跳的廣場(chǎng)舞,而是芭蕾舞,看似不經(jīng)意,其實(shí)一招一式皆是千山萬(wàn)水。
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著名詩(shī)人與評(píng)論家T.S.艾略特,曾在《四個(gè)四重奏·小吉丁》一文中,非常形象地將詩(shī)歌中文字的排列組合比喻為“舞蹈”——“每一個(gè)詞都恰到好處、各就其位、相互銜接、相互襯托,既不晦澀也不炫耀,新的和舊的毫不費(fèi)力地交易。普通的詞,精確而不俗氣;正規(guī)的詞,確鑿但不迂腐,一出完整的語(yǔ)音的舞蹈。”
毫不猶豫地說(shuō),羽微微就是一個(gè)優(yōu)秀的舞者,不論境界還是技巧,她都有自己的“高標(biāo)”。她用詩(shī)歌在眾聲喧嘩的時(shí)代,發(fā)出自己的獨(dú)唱。她應(yīng)該是一個(gè)安靜的人,一個(gè)看透生活本質(zhì)而又裝作若無(wú)其事的人,穿過(guò)世俗依然不失純真的人。帕斯有一句話,曾讓我找到寫作的理由,今天集中讀一次羽微微,再次讓我覺(jué)得,帕斯這種先知般的話語(yǔ),著實(shí)是一種預(yù)言與啟示:詩(shī)人傾心于沉默,卻又只能求助于話語(yǔ)。
當(dāng)然,帕斯的另一句話,似乎也可以解決一些當(dāng)下的困惑,他認(rèn)為“詩(shī)是無(wú)法解釋的,但并非不可理解”。這就提醒我們,任何一個(gè)詩(shī)人,都不要裝神弄鬼,對(duì)于詩(shī)歌必須保持最基本的尊重。在這方面,羽微微做得特別到位,她的詩(shī),句句可解,句句簡(jiǎn)潔,你想在她的文字里找到晦澀,注定是徒勞的。但那些簡(jiǎn)潔的句子一旦被她合成,就會(huì)產(chǎn)生幾何級(jí)別的魔幻。用文字跳舞的羽微微,一旦把自己拋進(jìn)舞池——不管是生活的、親情的、愛(ài)情的,還是命運(yùn)的——著實(shí)讓我感受到一個(gè)清澈而迷離的畫面:“我泛起了漣漪/就像泛起了很多的自己/然后我將她們輕輕地推遠(yuǎn)了。”(《漣漪》)
讀她的詩(shī),屢屢讓我動(dòng)容,在平靜的文字下,她呈現(xiàn)給我的,是陡峭、顫栗與凜冽——“跑很快,但飛翔更接近自由/我懷有一顆柔軟之心/立于懸崖之上”(《飛翔》)、“當(dāng)我不再愛(ài)你/世間萬(wàn)物,符合邏輯/一一各歸其位/消失了神奇”(《當(dāng)我不再愛(ài)你》)。
有一首詩(shī),名曰《打結(jié)》,用形象的語(yǔ)言,直逼內(nèi)心——
我總喜歡雙手交叉
抱在胸前
年輕的時(shí)候
就像摹擬一個(gè)喜歡的人
在擁抱自己
現(xiàn)在像是一個(gè)
正在打結(jié)的人
雙臂再抱緊點(diǎn),把結(jié)打好
就可以
隨便拎起自己
丟到別的地方去
這首只有十一行的小詩(shī),意象鮮明、準(zhǔn)確,我真的感覺(jué)到,命運(yùn)之繩,可以把任何一個(gè)人捆成粽子。羽微微的詩(shī),讓我覺(jué)得生活中的各種結(jié),放大了看,何嘗不是成長(zhǎng)過(guò)程中放大的傷疤。幸好,生活哪怕有各種不堪,對(duì)于詩(shī)人來(lái)說(shuō),還有詩(shī)歌,作為藝術(shù)的最高形式,詩(shī)歌也許不能拯救個(gè)人與世界,但至少可以抵抗,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布羅茨基說(shuō)得太刻骨了:藝術(shù)是抗拒不完美現(xiàn)實(shí)的一種方式。
羽微微的詩(shī),讀多了,發(fā)現(xiàn)在“藝術(shù)”之外還有一股狠勁,與其說(shuō)她寫詩(shī)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抵抗,不如說(shuō)她寫詩(shī)是與生活和解,消解一切意義,只有把花朵看成傷口的人,才能寫下這樣豪邁而又揪心的句子:“風(fēng)吹過(guò)/我沒(méi)有悲傷/我渾身空空蕩蕩。”(《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