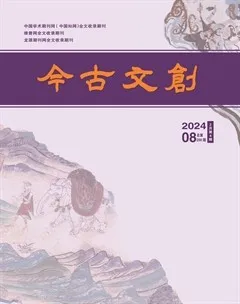論《女勇士》中女性文化身份追尋困境
王盈鑫
【摘要】在《女勇士》中,作者湯婷婷刻畫了不同類型的女性形象:真實的抑或是虛構的。本文借助法國女性主義理論,分析中國傳統女性“無名女人”、月蘭、美籍華人女性“我”和母親英蘭等在父權制文化以及中西文化沖突影響下的生存困境。通過剖析,本文旨在探究被不同文化和社會觀念影響的女性在追尋自我身份認同時所面臨的困境以及為突破困境所做的努力。
【關鍵詞】女性文化身份;性別沖突;中西文化沖突
【中圖分類號】I712?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08-002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8.008
一、引言
《女勇士》是美籍華裔作家湯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撰寫的一本書,于1976年出版,曾獲得過美國國家書評獎,并被《時代》雜志評為20世紀70年代優秀非小說類書籍。湯婷婷的短篇小說集深受英語讀者和學者的好評,奠定了華裔美國文學在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作者采用碎片式拼貼的后現代手法,反映了關于“性別、種族、階級、文化和歷史等多重但卻相互關聯的身份網絡”。[9] 湯亭亭作品在國內傳播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并于21世紀初研究達到高潮。國內研究主要側重對《女勇士》中人物身份建構、女性成長主題、人物形象、小說敘事策略、記憶書寫等。
《女勇士》共分為五個部分:“無名女人”“白虎山學道”“鄉村醫生”“西宮門外”“羌笛野曲”。第一章講述無名女人在丈夫外出賺錢時意外懷孕被逼致死;第二章改編自花木蘭從軍的故事,想象自己上白虎山學道;第三章講述母親英蘭出國前后截然不同的文化體驗和生存困境;第四章講述的是月蘭前往美國尋夫卻慘遭被拋棄而發瘋致死;第五章講述敘述者“我”在中西文化價值沖突情況下對自我身份的探索。盡管這五個故事的內容不同,但它們有共同的特點,即每個故事都以女性成長歷程和自我意識覺醒為主題,小說著力刻畫游離在中西文明兩個世界中的女性面臨的生存困境。
法國精神分析女性主義者之一朱麗婭·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認為,女性之所以成為女性,男性之所以成為男性,是出于社會差異,而不僅僅是生理上的差異。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生來具有女性的生理特征,那么她同男性相比在社會交往中往往被賦予較少的權力。歸根結底,“正是賦予性別差異的社會意義使女性在追尋自我的過程中面臨難以擺脫的生存困境”。[2]當談到文化身份時,湯亭亭講道:“我們小的時候常常覺得自己的內心世界是由幾種不同色塊構成的;長大后,我們把不同的文化元素經過核查后合成,變成了一個有機體,我們創造出了一種新的文化。”[6]小說中,作者根據自己的移民生活經歷刻畫了中國傳統女性“無名女人”、月蘭、美籍華人女性“我”和母親英蘭在不同的成長背景和文化夾縫中尋求自我身份及生存意義。
二、性別沖突
海倫·西克斯(Helene Cixous)認為,女性本身就是力量和能量的源泉。如果一個女人不知道她需要被解放,她就不能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獲得解放。因此,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女性語言來消除壓迫女性的父權制二元思想。
同樣,盧斯·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認為,在父權制文化中,大部分女性通過男性語言媒介被征服。她認為,在父權制社會中,女性只有兩個選擇:1.保持沉默(因為女性說任何不符合父權制邏輯的話語都會被視為不可理解、毫無意義);2.模仿父權制社會賦予她的低人一等的角色。超越父權制的方法是通過“消解父權制社會為女性設定的工具即語言”。[2]父權文化是一種典型的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這意味著一切都圍繞著男性,女性被完全忽視。男人被認為是社會的典范,而女人則被視為異端,即“他者”。
在中國傳統封建制度下,男人主宰著整個社會,女人完全從屬于男人,沒有任何話語權。她們是被排除在社會主流之外的邊緣化群體。她們必須遵守三從四德,三從即“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即“婦德、婦言、婦容、婦功”。[3]
無名女人是作者勾勒出的第一個試圖推翻傳統父權統治的勇敢女性形象。無名女人在丈夫還在國外時懷孕了,這個消息立即在村里傳播開來。村民們在嬰兒出生的那天晚上突襲了她們的房子。村民對非法懷孕這一事件感到憤怒:“人們在我們的土地上蜿蜒而行。起初,他們向房子扔泥土和石頭。然后他們扔雞蛋,然后開始宰殺我們的牲畜。”[1]除了村民們態度嚴厲外,就連她自己的家人也對她不屑一顧,對村民的暴行無動于衷。他們并不關心非法懷孕背后的原因,即被男人強奸。在父權制社會中,女性生活在一個無權為自己辯護的社會中,即使奮力維護自己的身份,也不會得到周圍人的理解與同情。出于羞辱,無名女人抱著孩子跳進井里,以表明她的反抗。她去世后,她的家人不想向別人談論她,也不允許別人談論她的名字。他們認為她是“從未出生過的”。[1]在這個故事中,無名女人的悲劇與她所處的社會息息相關。重男輕女觀念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只有死去,才能表達出她對社會男女不平等的不滿。
波伏娃認為,在父權制社會中,男性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主體(具有自由意志的獨立自我),而女性則被認為是連續的存在(受周圍環境控制而存在)。在第四個故事“西宮門外”中,湯婷婷刻畫月蘭為傳統的好女人形象,即女人留在家里照顧孩子和父母,而男人則離家賺錢,養家糊口。月蘭姨媽“一生都在等待丈夫的指令,沒有自我愿望”,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樣,一直圍繞其他球體運轉。[3]三十年來,月蘭一直從美國丈夫那里收錢。但她從未告訴過他她想來美國。她等著他提出建議,但他從來沒有這樣做。在父權社會的文化影響下,她不認為自己被丈夫拋棄了,她對丈夫給她的生活感到滿意:金錢、房子、仆人等等。甚至她對丈夫感到虧欠,因為他支持他們的女兒讀完大學。在她看來,男人可以對世界采取行動,改變它,賦予它意義,而女人只有在與男人的關系中才有意義。
然而,三十年后,在姐姐的幫助下,她來到了美國,找到了她的丈夫。但不幸的是,他又結婚了,不承認她是自己的妻子,因為美國法律不允許一個男人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妻子。在傳統的中國婚姻中,大家認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然而,現在一切都變了。女人不是男人的財產,她們有自己的發言權。另一方面,由于語言障礙,她的丈夫告訴她,她甚至不適合做女傭。被丈夫拋棄后,她感到孤獨,無法找到自己的精神歸宿。最后,她逐漸發瘋并死在精神病院。
無名女人和月蘭同樣被困在專制社會的固有秩序中,無法按照自己的意志掌握命運,但她們并沒有妥協,而是以悲壯的方式挑戰父權制社會——跳井自殺或者抑郁致死。無名女人和月蘭的悲劇表明,中國傳統女性意識正在覺醒,開始尋求自己的身份,而不僅僅是將自己視為男人的私有財產。
三、中西文化價值沖突
處于社會底層的華裔婦女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總是作為被剝削的勞動力,她們不僅像商品一樣被交換和剝削,而且也被剝奪了話語權。華裔女性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遭受多重傷害。湯亭亭在一次訪談中講道:“語言對我們的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你必須要講出你的故事,甚至有時你要去杜撰你的故事,否則你會發瘋。”[5]早期移民的華裔女性在父權制和種族主義的雙重壓迫下,陷入生存困境與失語狀態,但隨著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她們逐漸打破沉默,積極主動地追尋自我價值。
美國的《排華法案》從1882年一直持續到1943年,在美華人早期從事淘金、筑路和各種農活,生活極為艱苦。1882年美國政府通過《排華法案》,并在1902年將其變為永久性條款,對華裔移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其中重點限制華裔女性進入美國,以致唐人街成為“單身漢社會”。[6]大部分居住在城市的華裔主要從事下層服務業如餐飲業、洗衣業等。這些底層職業或卑微或神秘,奠定了西方白人對華裔的刻板印象。1910年至1940年,美國移民局在舊金山灣的天使島設立移民檢查站,專對入境華人進行無端檢查、隔離審問。華裔女性與丈夫、孩子被隔離,等待漫長的審問,對未來感到迷惘和不知所措。
英蘭作為第一代美籍華人移民,深受種族主義的壓迫,但她不輕易屈從命運,勇敢堅強且自立,努力追求自我價值。在封建專制社會下,即使女性在考試中取得優異的成績或者在戰場上表現突出,社會對于女扮男裝的女性絕不容忍。但是英蘭突破封建思想,即使在三十七歲時,她仍到廣州哈克特女子醫學專科學校與年輕的女孩一起學習,并獲得了醫師證。與同齡的傳統中國女性不同,她不僅像同齡女性一樣撫養孩子,而且還去學校尋求自我教育。她認為畢竟父親是能背誦整首詩的人,而自己不夠聰明是因為自己不夠努力。她為了不被嘲笑而努力學習。經過兩年的努力學習,她如愿回到家鄉當醫生,幫助村民。她反對女人留在家里,男人出去賺錢的傳統觀念,所以自己湊錢去美國與丈夫團聚。
在中國,英蘭是令人尊重的醫生,而到了美國她沒有了事業。在美國,母親發現到處都是“各種各樣的鬼——的士鬼、公車鬼、警察鬼、開槍鬼、查電表鬼、剪樹鬼、賣雜貨鬼”。[1]由于種族歧視,英蘭和大多華裔移民一樣,只能在洗衣房、農場這些底層的場所工作。繁重的體力勞動使她心力交瘁,健康狀況遠不如從前:風濕病,靜脈曲張,長年咳嗽……在美國種族主義政策影響下,她承受了身體和心理的雙重折磨,長期忍受白人主流社會對華裔的歧視與壓迫。
英蘭無法改變這種生存現狀,只能在中西方文化沖突中尋求被動的妥協與調解。但是她不希望女兒繼續過她這樣無法擺脫的生活,并試圖通過給女兒講花木蘭的勵志故事來寄托自己的希望,即用花木蘭的勇氣反抗美國華人生活中的不平等。作者通過改寫花木蘭的故事,彰顯了“強烈的女性主體意識”。[8]
這部小說中的“我”作為敘述者,是處在兩個世界夾縫中的第二代美籍華人,內心充滿困惑,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美國的價值觀都持懷疑態度。從小接受西方教育的“我”在學校經常受到白人同學的嘲笑,老師有意把她和其他同學區別對待。她期待從家庭獲得安慰和支持,但是中國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使她時刻對自己的存在產生懷疑。主人公在雙重文化身份中痛苦掙扎,試圖探索自己的文化身份。
男孩和女孩的區別在他們出生時就存在,當一個男孩出生時,父母非常高興,并舉行諸如出生時在他臉上滾雞蛋、舉辦百日宴等儀式。在極其貧窮的年代,女孩兒甚至作為交易的對象,以此來維持一個家庭的生計。當她聽到父母或移民的村民說“養女孩就像養鵝”,她就會“踹地板、放聲大哭,哭到沒辦法說話”。[5]當她聽到這句話時,她感到羞愧。因為在中國傳統中,女性生活在一個幾乎所有意義都由父權制語言定義的世界里。但作為受美國文化影響的第二代美籍華人,她無法忍受這種辱罵。因此,她通過肢體語言而不是口頭語言來反擊他們。她覺得唐人街的生活令人失望,為了找到在社會上的一席之地,她嘗試逃離唐人街,積極認同西方文化并渴望融入美國社會,“正常華人婦女的聲音粗壯有威。我們華裔美國女孩只好細聲細氣,顯示出我們的美國女性氣”。[5]她把美國的拉拉隊隊長視作自己的人生偶像,討厭母親英蘭所講的關于中國的故事。
此外,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女性解放運動思潮背景下,她努力地考上了伯克利大學,想要改變世界,但卻發現女性想要在社會上有所作為,受到太多阻力,甚至還在抱怨為什么自己不是一個男孩呢。
除了性別歧視帶來的困擾外,種族歧視使華裔女性在追求自我的道路上更加困難。在童年的時候,“我”在英語學校和唐人街外的其他地方因為被歧視低看而無法流暢地講話,總是磕磕絆絆,但是在中文學校和唐人街可以順其自然地交流。當她離開唐人街后,經歷太多的種族歧視的現象,使她對自我身份產生了懷疑。一方面,唐人街上步履維艱的生活與欣欣向榮的美國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同情自己出生的社區人民。隨著美國經濟的發展,想要建更多的停車場滿足社會的需求,唐人街上的中國店鋪如洗衣房等被要求騰空,而這些店鋪卻是移民生活收入的大部分來源。另一方面,當她長大找到工作后,她的老板使用具有種族歧視的語言使她難堪,而無法真正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在無法理解中國傳統文化與不被美國主流社會認可的夾縫困境中,“我”試圖尋求自我的整合,重構自己的身份。
“我”和母親英蘭作為早期移民的美國華裔女性,承受著美國對華人的一系列歧視性法律,在種族壓迫中依然過著艱難的日子,同男人共同承擔家庭重擔及社會責任。這使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改善,也改變了女性對丈夫的絕對依賴。女性再也不是男性的附屬品,而是作為家庭的支柱,積極主動地尋求自身發展和家庭發展。
四、結論
臺灣著名學者馮品佳認為湯婷婷“塑造亞裔身份的作品對成長小說研究、美國文學史”做出了重大的貢獻。[4]在《女勇士》中,作者結合自身游離在唐人街和美國社會之間的移民生活經歷,呈現了處在不同歷史時期華裔女性在發現自我、追求自我、構建自我身份時所面臨的性別沖突與中西文化沖突的雙重困境,以及為擺脫這種困境所做的嘗試與努力。她們抑或沉默,抑或吶喊,但都在試圖打破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的壓迫過程中,重新構建了自我身份。
參考文獻:
[1]Kingston M H.The 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6.
[2]Lois Tyson.Critical Theory Today:A User-Friendly Guide(Second Edition)[M].Routledge,2006.
[3]Smith,Paul.A Cultural Production[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3.
[4]馮品佳.再造華美女性文學傳統:任碧蓮的《莫娜在希望之鄉》[J].歐美研究,1991,(23).
[5]付明端.從傷痛到彌合[D].上海外國語大學,2010.
[6]令狐萍.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7]衛景宜.全球化寫作與世界華人文學——美國華裔作家湯亭亭、裘小龍談話述評[J].國外文學,2004,(03):46-49.
[8]趙小琪.論歐美華人女作家自傳性作品的不可靠性敘述[J].中國比較文學,2021,(03):151-164.
[9]鄭慶慶.站在邊緣的女勇士——對湯婷婷《女勇士》的跨文化觀讀解[J].外國語言文學,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