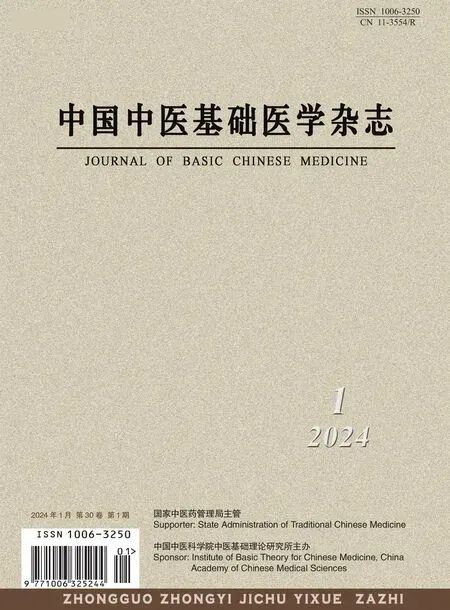404 Not Found
404 Not Found
從對中藥毒性的認識與處理看本草學的反思與嬗變?
陳仁壽
(南京中醫(yī)藥大學中醫(yī)藥文獻研究所,南京 210023)
本草學是研究傳統(tǒng)中藥學的一門學問,其內涵十分豐富,包含中藥的品種資源、炮制加工、藥性理論、臨床使用等多個方面。毒性,是中藥藥性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歷代醫(yī)藥學家在發(fā)現中藥、認識中藥、研究中藥、利用中藥過程中,總結出的一種藥物特性。從開始認識到藥物具有“毒”的性質,并發(fā)現“毒”的利用價值,再到使用一定的方法與技術對藥物進行控毒或減毒,甚至解除人體因使用毒藥后的身體危害,可以概括為“識毒、用毒、控毒、解毒”四個不同過程和階段,體現了本草學的不斷反思、調整與嬗變。這一過程使得本草學的內容更加充實,認識愈加深入,體系不斷清晰與完備,學術價值得以進一步體現,并成為中藥從資源發(fā)現到臨床運用過程多個環(huán)節(jié)的重要影響因素,至今對有效、安全使用中藥仍有指導意義。歷代對中藥的識毒、用毒、減毒與解毒相關理論認知的發(fā)展,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tǒng)本草學的起源、形成、充實與完備的不同階段。因此,全面認識中藥毒性,可以了解本草學發(fā)展過程中的重要節(jié)點與關鍵知識[1]。
1 識毒:對中藥毒性的發(fā)現與了解——本草學的起源與肇始
本草學的起源可以說是從“識毒”開始的,這里所謂的“毒”,是指區(qū)別于普通食物的藥物,通常認為是自然界物質的偏性。此即有關中藥毒性概念的一種:毒即是藥[2]。
人類為了生存,首先從大自然界尋找食物以充饑,慢慢地發(fā)現有些食物除了充饑,還可以改善或減輕人體的不適,或者能夠增強體質,這就具備了“藥”的性質。自然界的物質對人體無論是正或反兩個方面的作用均有其偶然性,或可有益于機體生長和生活,或能減輕人體的不適癥狀,或可引起人體的不適,或帶來危害,從而確定某些物質食用后對人體所產生的不同反應。
對自然界物質偏性或毒性的認識,從開始少數人的偶然發(fā)現,逐漸轉向更多人的關注與研究,從而為本草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因此通常認為,本草學是人類在長期的生活實踐或與疾病斗爭之中,不斷積累經驗并逐漸總結而來的。中藥的發(fā)現與農業(yè)的發(fā)展是同步的,《淮南子·修務訓》中有云“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谷,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3]。播種五谷、土地施肥同時嘗食草木、飲用水泉,在這過程中遇到具有偏性(毒性)作用的草與泉水,可以調治人體的偏差與不適,甚至有的引起中毒。《靈樞·五味論》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4]371,即指出五味之飲食各有偏性,使用失當則對健康不利,變生疾病,如“高(膏)粱之變,足生大丁(疔)”[5]23。很多有毒礦物藥如水銀、石鐘乳、硫黃、砒石等,早在戰(zhàn)國時期就被用于多種外科疾病,如瘢、癰、痂等,但因其有毒,醫(yī)者認為使用須慎。《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6],五石即五石散(石鐘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這些有關食物與藥物的偏性和毒性以及用毒與避毒知識,為本草學說形成積累了基本知識。
“識毒”是對自然物質具有藥性本質的最原始的認識,也是對中藥能夠調治人體的根本性質的最初認知。這一了解與發(fā)現在本草學的發(fā)展中十分重要,如果離開了對自然物質具有藥性作用的認識,則談不上此后本草學說的全面發(fā)展。在此基礎上,順著這樣的思路尋求,不僅越來越多的自然物質被認識到具有藥性作用,而且人們更懂得了一些自然物質通過加工制作產生新的物品,亦成為一種具有藥性的物質。如通過谷類糧食釀造而成的酒,通常被認為是中藥起源的重要佐證,人們可以用此御寒,但過多飲用則又會引起醉狀,甚至昏迷,這也是既認識到它藥性作用,也了解到有可能產生對人體不利的方面,關鍵是如何正確使用它。因此,對食物與藥物偏性和毒性以及具有治病作用的認識,是本草學起源與開端的重要標志。
2 用毒:對中藥毒性的認識與利用——本草學的形成與充實
本草學的形成從“識毒”開始,人們發(fā)現并認識到中藥之所以成為中藥,是因為這些自然物質具有一定的毒性(即可以調整人體的偏性)。接下來就是如何使用這些毒性,認識是使用的基礎,使用是認識的延伸。還是以食物為例,最初人們只認識到食物可以充饑,然后逐漸發(fā)現不同種類的食物在人體充饑過程中,還在不同方面對機體起到有益的作用。如《素問·藏氣法時論篇》曰“五谷為養(yǎng),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闡述了谷物、果實、動物、蔬菜對人體的不同作用,并言“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5]199,即這些食物應當共同配合食用,對人體產生補精調氣的作用。這里明確指出食物也即藥物,食物用對了對人體也有調養(yǎng)和治療作用,關鍵是用好用對它們的特殊偏性。
總的來說,食物對人體起著有益的作用,然而人們又逐漸認識到,不同的食物也存在不同的偏性和不同的作用,既有對人體有益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對食物的特性(藥性)與效用的認識不斷深化、豐富與總結,在本草學中形成了一門專科本草學說,即食物本草。早在漢代就有《神農食經》《神農食禁》一類的書籍出現,專門論述食物的特性與藥性、功效與主治以及使用宜忌。漢代的食物本草著作原書基本已亡佚,僅在《漢書·藝文志》中保留其書名,其中內容大多已看不到全貌。而唐代的《食療本草》原書雖亦已佚,但其內容基本比較完整地保存于后世的本草文獻如宋代的《證類本草》和明代的《本草綱目》之中。唐代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亦有專門篇章介紹食物的藥性、功效、主治與使用禁忌。這些系統(tǒng)知識的出現,均是對于食物偏性(毒性)認識的整理與總結。食物的毒性主要是指偏性而已,所謂食物的毒性(偏性)相對來說是比較緩和的。對于食物毒性(偏性)的利用是本草學中藥物“用毒”的最初開始,也是中國傳統(tǒng)藥學形成的重要標志。
至于偏性較大或毒性猛烈的自然物質,古代也很早就對其有了全面認識,并大量記載于本草文獻之中。如我國現存第一部本草學著作——漢代的《神農本草經》,載藥365種,書中按照藥物的屬性,按有毒與無毒者分為上、中、下三品,分別是上品無毒、中品無毒或有毒、下品有毒。這種分類主要是根據毒性的程度和大小來進行的,無毒主要是指具有偏性的藥物,而標明有毒的藥物屬于偏性較重和藥性猛烈者,這里的毒性與現代藥學上的毒性已十分接近,這些藥物大多數在現代藥理學上又具有急毒或慢毒特性。《神農本草經》將偏性較猛烈的藥物都歸為有毒一類,并沒有區(qū)別是大毒還是小毒。但從其所歸納的類別看,還是有大小區(qū)分的。中品中的有毒藥物,一般為小毒;而歸于下品的有毒藥物,通常為大毒。這些不同程度的有毒藥物其療效也有明顯的區(qū)別,書中謂中品“無毒有毒,斟酌其宜”[7]75,主要用于“遏病”,而下品“多毒,不可久服”[7]126,主要用于“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7]126。從其功用和使用注意來看,毒性的程度是有區(qū)別的,毒性小的可遏病(普通疾病),而毒性大的可治重疾(寒熱邪氣和積聚)。《神農本草經》開創(chuàng)性地將使用毒性中藥與其功效主治明確關聯(lián)起來,后世則不斷豐富其內涵,將“用毒”作為認識和利用中藥的重要思路,填補臨床藥學知識,為治療疾病提供方向性思維,提醒用藥過程中的注意事項,提出中藥臨床使用禁忌,從而提高中藥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素問·五常政大論篇》云“帝曰:有毒無毒,服有約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5]584。這里明確指出了有毒與無毒藥物在使用上是要限制的,要根據病的新久輕重,確定是用無毒還是有毒藥物;還要根據毒性的輕重,從大毒、常毒,到小毒、無毒,藥物的使用量上要不斷減少,亦即毒性越大,藥量越小,毒性越小,藥量越大。從《神農本草經》提出不同的有毒藥物適合于不同的臨床病證,到《黃帝內經》規(guī)定在使用有毒中藥上應當根據病情的輕重緩急,用量上應當區(qū)別對待,表明自代漢代起,對如何“用毒”的認識已非常深入和全面,指明有毒藥物的臨床使用價值,還提出了有毒藥物使用注意,反映了對本草學術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表明了本草學的基本形成及其內涵的不斷充實。
3 控毒:對中藥毒性的消解與減控——本草學的修正與完善
本草學的形成與藥物學知識的充實,離不開對毒性的深入認識。然而僅僅認識到毒性的作用與效用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毒性具有兩重性質,既能治病,亦能對人體產各種不同副作用。于是在本草學的認識與發(fā)展過程中,與認識毒性的效用同步而來的是,各種消解與減輕毒性的方法與措施被發(fā)現和利用。
對自然物質毒性或偏性的消除或減輕,也是從食物開始的。《呂氏春秋》記載商初伊尹曰“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膻,必以其勝,無失其理”[8],表明商初就認識到食物有偏性,使用必須去除如腥、臊、膻這樣的偏性,以免過食引起人體不適。不同偏性的食物對不同的體質存在宜和忌兩個方面,《素問·宣明五氣論篇》曰“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咸走血,血病無多食咸;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令多食”[5]202。一方面說明食物之五味適合于不同的體質,同時不同的疾病應當避免與之相對應的五味食物攝入,即所謂“五禁”。選取適當的食物,也是一種減輕或控制偏性對人體傷害的重要手段。
在對藥物毒性或偏性認識不斷深入的同時,相關消減藥物毒性的方法亦同時出現。前面提及的《素問·五常政大論篇》中所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其八”[5]584,即是從減輕藥量來減控藥物毒性。《神農本草經》提出藥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7]1等配伍關系,其中相畏、相殺即是毒性藥物通過配伍其他藥物達到減輕毒性的作用。具體的解毒藥物在此后魏晉時期的《名醫(yī)別錄》中有許多記載,如生大豆“殺烏頭毒”[9]166,葵根“解蜀椒毒”[9]77,薺苨“解百藥毒”[9]126等。而“十八反”與“十九畏”理論,則是從相反的方面提出了應當避免一些藥物在一起同時配伍,否則會引起毒性增加,這也屬于控毒的一個方面。關于“十八反”與“十九畏”中的藥物,至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中也是不建議同時配伍使用的,如甘草與海藻、附子與半夏等,目前在中醫(yī)院中也是禁止在處方中同時出現的。
在中藥的使用時間上,古人也常常提倡“中病即止”,這也是避免產生藥物毒性的一種手段。在古代醫(yī)藥文獻中記載了很多藥物“不可久服”,或記述久服容易產生毒副作用,如南北朝《本草經集注》中一些藥物雖未記載其“有毒”,但由于其具有明顯的氣味偏性,在使用上要注意其服用方法,認為不可長期服用或過食,否則對人體不利,如麻黃、葶藶子“久服令人虛”[10]330,知母“多食令人泄”[10]272,白堊“不可久服,傷五臟,令人羸瘦”[10]176。
在本草學發(fā)展過程中,對食物與藥物的加工炮制始終是消解與控制毒性的主要手段。各種為了減毒的加工炮制方法最先記載于醫(yī)籍方書之中,如半夏屬有毒之品,《靈樞·邪客》[4]417中有“治半夏”的記載,即是加工炮制后的半夏;東漢張仲景《金匱玉函經》方藥炮制篇中記載“半夏湯洗十數度,令水清滑盡,洗不熟有毒也”[11],即用水洗的方法對半夏進行減毒。通常方書中在記錄處方用藥時,常于藥名旁加下腳注,標明炮制方法,如附子(炮去皮)、巴豆(去心皮,熬黑)、王不留行(燒存性)等。此后,關于藥物的加工炮制減毒方法越來越豐富,南北朝劉宋時期雷敩全面總結藥物加工炮制方法而著《雷公炮炙論》一書,幾乎囊括了我國5世紀前的所有炮制技術,為后世中藥的減毒控毒提供了有效的藥物加工炮制措施。自《雷公炮炙論》之后,藥物的炮制技術越來越豐富和成熟,很多藥物針對不同的臨床病證出現了不同的炮制品。如半夏,唐代之前主要是湯洗為主,宋之后增加了姜半夏、法半夏、清半夏等。除此而外,一些特殊的劑型和服法也是減輕藥物毒性的重要方法,如有毒中藥牽牛子,多制成“糊丸”用;有毒中藥白附子、牽牛子等多強調用“米飲下”。部分有毒藥物使用外用法如外敷、塞肛、鼻吸等,以減輕毒性的攝入[12]。
中藥毒性的消解與減控方法,概括起來包括了減量、配伍、禁忌、炮炙、制型等多個方面。本草學的發(fā)展過程中,醫(yī)藥先賢們不斷通過各種方法減輕藥物毒性對人體的影響與傷害,使藥物的毒副作用降低到最低。這種對藥物的不斷調整和改良措施,能夠充分發(fā)揮中藥毒性的臨床效應,避免中藥毒性對人體的有害影響,從而大大充實了本草學的內容,促進了本草學的發(fā)展。
4 解毒:對中藥毒性的清除與治療——本草學的反思與完備
盡管在本草學的發(fā)展過程中,發(fā)現并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以減輕毒性藥物對人體的傷害,但或因藥物本身的毒性程度,或因使用不當,導致人體中毒或產生副作用的情況依然會產生。因此排毒除毒和治療毒副反應亦成為醫(yī)藥過程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更是本草學中主要內涵之一。
中藥中毒后的解毒方法,與直接對中藥本身進行減毒和控毒是有區(qū)別的。解毒方法主要針對的是中毒后的人體,通過采取催吐、服藥等方法,將體內毒性排除出去,或治療因中毒引起的毒副癥狀。本草學發(fā)展過程中,一直在探討中藥毒性的解毒方法,這也是臨床醫(yī)生在使用中藥過程中不得回避的問題。
對有毒中藥進入人體后引起毒副反應的解毒方法,也是很早就已經開始出現了,如《傷寒雜病論》中方劑在使用半夏時,大多加入生姜或干姜一起煎煮,其目的一方面是在煎煮過程中以姜解半夏之毒,同時人體服用姜后,在體內也可以化解半夏對人體的毒害作用。可見,古代很早就懂得毒藥使用的必須性,但同時又想方設法尋找解毒的方法,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知識。南北朝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序錄專列“解百藥及金石等毒例”篇,詳細記錄了“百病藥毒”的解毒方法[10]11,羅列了解除中藥中毒的通用藥,如甘草、薺苨、大小豆汁、竹瀝、大麻子汁、六畜血、貝齒屑、葍根屑;另外記載了射罔、野葛、斑竹貓、蕪菁、狼毒、蜘蛛毒、蜂毒、狗毒、巴豆、藜蘆、雄黃、甘遂、蜀椒、半夏等30余種有毒中藥食用后中毒的不同解毒方法,大多是“以藥解毒藥”。此后這些內容被收載于歷代的本草、方書等醫(yī)籍之中,后世越來越多的解毒方法既有繼承,也有發(fā)揮。
除了古代醫(yī)書記載,民間還有很多的藥物中毒的解毒處方,如附子中毒,可服用干姜甘草湯,或用蘿卜、綠豆、生姜汁共同服用。現代隨著藥理毒理研究的深入,很多毒性藥物的中毒機理得到了進一步明確,了解了藥物中的主要有毒成分。如附子毒性,主要因為含有烏頭類生物堿,對心血管系統(tǒng)、中樞神經系統(tǒng)和消化系統(tǒng)均可造成一定損害,解毒的方法主要是對癥處理,根據各個部分的損傷而進行相應的治療。如有報道3例附子中毒,使用中西醫(yī)結合方法,給予溫水催吐、洗胃、導瀉、補液、利尿,同時抗心律失常治療,用阿托品、利多卡因、維生素 C、維生素 B1、ATP、輔酶A等,同時予中藥處方:金銀花 30 g,綠豆 100 g,生甘草 60 g,水煎內服,或蜂蜜內服,每次 120 g,必要時可服至 500 g[13]。
近年來關于有毒中藥的毒性成分、毒性靶器官、毒性作用機理、毒性的分級、毒性控制與減少等方面均有創(chuàng)新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成果,加深了對有毒中藥和中藥毒性的認識,為更有效的解毒方法提供了理論依據[14]。然而,由于中藥毒性成分與毒性機理的復雜性,加上各種自然和人為的因素干擾,控毒與減毒方法有時不甚理想,導致中毒事件時有發(fā)生,甚至因服中藥導致的死亡也時有出現,因使用中藥引起的醫(yī)療糾紛不斷產生,因此解毒方法還有待深入研究,以彌補因使用中藥引起的嚴重后果。
對中藥中毒后的解毒處理,是本草學用藥中的一種深刻反思以及對其不良后果的彌補,從而使本草學術盡量趨于完備。在使用藥物過程中,不僅僅應充分認識藥物的毒性,而且對中毒后的救治應有必要的知識儲備與有效方法。在具體的解毒方法上,既有傳統(tǒng)的以中藥解中藥之毒,又有引入現代藥理毒理知識,利用西藥進行解毒,體現了古今結合、中西藥并用的綜合解毒思路,將本草學術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總之,本草學發(fā)展中涉及的理論與知識頗多,而以毒性為綱的學術思路,從識毒、用毒到減毒、解毒,不同的切入點,不同的認識層面,體現了本草學形成與發(fā)展過程中從初級發(fā)現到高層認知,從單一結構到多維度的遞進認識,從而使本草學內涵越來越豐滿,并更加科學與實用。同時,毒性是本草學藥性理論的重要內涵之一[15],對毒性的認識和運用過程,反映了本草學說不斷探索、充實、改良和完備的一系列反思與變化的過程。因此中藥毒性并不可怕,它是本草學內在的要素,不僅不能排斥,還要合理和正確地使用[16]。反過來也可以說,要全面認識本草學的發(fā)展歷史與進程,可以從系統(tǒng)梳理中藥毒性的認識、運用、減輕、消除等方面為視角進行分析研究,從而一方面可以客觀看待中藥毒性的利與弊,另一方面可以正確對待并利用好中藥毒性的內在價值,為臨床安全使用毒性中藥提供必要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