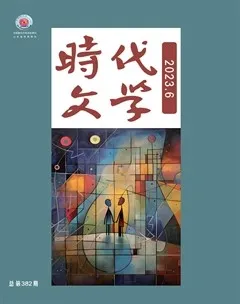一路走來(lái)
王紹德
這里群山懷抱,圍成一座不大的山鄉(xiāng)——官田鄉(xiāng)。南面那條坎坷的石子路,是鄉(xiāng)里與外界溝通的主要通道。勤勞、憨厚是山民的本色,犁耙式的水稻種植是他們的主要生計(jì)。坐落在東南丘陵上的官田中學(xué),便是山娃成才的搖籃。在丘陵之下,有一座很小的山村——新屋場(chǎng)村。七百多年前,祖宗遷徙至此時(shí)取此名,現(xiàn)在實(shí)在不新了。我家就世代居住在這個(gè)村莊。
我排行老五,與兩個(gè)哥哥、兩個(gè)姐姐和父母,一家七口擠住在一間小房子里。房子分兩層,上層堆放干稻草,也是我、二哥和爸爸的床鋪,下層勉強(qiáng)容納兩張床。
幼時(shí)的我,是父母和哥哥、姐姐的寵兒。父親是個(gè)篾匠,常去別人家做工,偶爾帶點(diǎn)零食回來(lái),藏在我們的草鋪里,然后偷偷地告訴我,并再三囑咐我別告訴媽媽。可我每每津津有味地吃完,總免不了告知母親,父親又得挨一頓訓(xùn)。有一次,我玩耍歸來(lái),看到父親和大哥各拿一把鐵鍬,圍著村子你追我趕。父親厲聲地罵著大哥,嚇得我哭嚷著問母親:“大哥怎么了?”母親說(shuō):“你大哥有點(diǎn)不對(duì)勁。”此后,我每次都是怯怯地看著大哥。
七歲時(shí),母親領(lǐng)著我走進(jìn)了紅磚平房的學(xué)校——官田鄉(xiāng)中心小學(xué)。雖然大哥、大姐為了弟妹上學(xué)相繼輟學(xué),但家里還有三只書包。于是母親帶著大姐,操起扁擔(dān),拿起柴刀,去離家十五公里的深山砍柴,賣些錢供養(yǎng)我們?nèi)齻€(gè),并攢些錢買藥,醫(yī)治父親多年的胃病。雖然父親做篾匠能掙點(diǎn)錢,但愛吃零食、愛喝酒的他總是留不住錢,他的胃病也就一直未能得到根治。每年春耕時(shí),母親總是到銀行貸款買化肥,秋收后賣了谷子還貸款。當(dāng)時(shí),水稻品種不好,產(chǎn)量低、米質(zhì)差,價(jià)格總在每百斤三十幾元。即使家里種了十五畝責(zé)任田,每年也只能勉強(qiáng)填飽肚皮,再添件粗布新衣,草草地過個(gè)年。于是,從我讀書起,就知道學(xué)費(fèi)來(lái)之不易。有書讀,便成了我童年的一大奢侈。
當(dāng)我走進(jìn)教室,捧起嶄新的課本時(shí),我知道只有好好讀書,才對(duì)得起辛勞的父母,于是我學(xué)習(xí)格外用功,成績(jī)也名列前茅。每個(gè)學(xué)期末領(lǐng)成績(jī)單時(shí),是我最快樂的時(shí)候。那天,母親總是拿出“最新”的衣服,其實(shí)是哥哥穿不得的半新衣服,并從瓷缸里摸出一個(gè)雞蛋,煎給我吃。當(dāng)然,我也不負(fù)眾望,每次都能帶上一張“三好學(xué)生”的獎(jiǎng)狀獻(xiàn)給母親。母親總是笑瞇瞇地把它貼在廳堂條案后面的板壁上,初中畢業(yè)時(shí)板壁幾乎貼滿了。
每天放學(xué)回家,母親交代我:“先做完作業(yè)再去玩。”我一到家,就搬出一條板凳當(dāng)桌子,坐在一塊石頭上認(rèn)真寫作業(yè)。每到節(jié)假日,我常常獨(dú)自一人,挑著擔(dān)箕上山砍柴。有一次,我發(fā)現(xiàn)一叢荊棘中有許多筆直的灌木,便揮起柴刀劈開一個(gè)小洞,爬進(jìn)荊棘叢中,坐在地上吃力地砍。可直徑一寸左右的野柴,竟要砍上幾十刀。有些灌木富有彈性,每砍一刀只能砍入一毫米,柴刀彈出老遠(yuǎn),等到砍斷時(shí),手震得發(fā)麻、腫起血泡。后來(lái)血泡腫得實(shí)在大了,我就戳破血泡讓血水流出,強(qiáng)忍著疼痛把剩下的幾根灌木砍斷。等鉆出荊棘叢,才發(fā)現(xiàn)太陽(yáng)已經(jīng)偏西了。
砍斷只是第一步,還得想辦法把它們拉出來(lái)。于是,我又和荊棘、樹藤展開拔河比賽。有的樹條被野藤纏得緊緊的,我就鉆進(jìn)去把藤劈斷,實(shí)在劈不斷,就爬上荊棘叢,把細(xì)枝末梢砍斷,再拔出來(lái)。等把灌木都拔出砍成一段段的,并裝進(jìn)擔(dān)箕時(shí),太陽(yáng)已經(jīng)落山了。看著滿滿一擔(dān)箕的木材,我高興地把扁擔(dān)往肩上一撂。“完了!”太重,挑不起,但又舍不得扔掉一些。于是,我弓起背,咬緊牙,一步一步地挪回家。每走十幾步休息一下,走了不到一里路,肩膀磨得通紅,腰板快直不起來(lái)了。等天天黑時(shí),才遇到二哥來(lái)接我回家。
夏收是農(nóng)民最忙最累的時(shí)節(jié)。每到這時(shí),我就和大人們一起,卷起褲腿蹚進(jìn)水田插秧,操起鐮刀鉆入稻田收割。六歲時(shí),我就開始學(xué)干農(nóng)活。剛學(xué)插秧時(shí),母親總是教我:“左手拇指和食指分秧,右手五指捏緊,筆直插入,早稻粘泥起,晚稻插到底。”我插的秧筆直像標(biāo)兵,可速度太慢,常被哥哥、姐姐“鎖”在秧苗里,腳也被他們打得通紅。速度是練出來(lái)的。為了趕超哥哥姐姐,我憋上一口氣,認(rèn)真、使勁地插,腰疼也無(wú)暇顧及。后來(lái),一天也能插完一畝田。
晚稻插下后,灌溉便成了令人頭疼的大事。記得有一年,接連幾十天沒下雨,村里的兩個(gè)小水庫(kù)幾乎都干了。家家戶戶掄起一把鐵鍬,二十四小時(shí)守候,爭(zhēng)著把溪水分流進(jìn)自家田里,往往分到自家稻田時(shí)猶如茶壺嘴倒水。一天晌午,我扛起鐵鍬來(lái)到后山的稻田,先把水路引進(jìn)自家田里,再沿水溝到上游引水。如果遇見人,就商量著把水流一分為二,再逆流而上引水。當(dāng)我返回查看水路時(shí),發(fā)現(xiàn)王悍站在那里,把我的水路全堵死了。我嚷著:“我從上面一直分下來(lái)的,你為什么堵住我的?難道我就不能分水?”“不準(zhǔn)分,你動(dòng)一下就把你的鍬丟掉。”他厲聲喝道。“做人要公平,憑什么我就不能分水?”我一邊嚷著,一邊蹲下去分了一點(diǎn),僅僅是他的四分之一。可王悍二話不說(shuō),抓住我的鍬扔進(jìn)田里。我哭著說(shuō):“憑什么我就不能分水?憑什么欺負(fù)人?”他怒目喝道:“你家又不是這里人,做崽的,還想分水?”
父親是上門女婿,所以村里人大都叫我們是“做崽的”,再加上家里窮,我們常遭欺凌。村里的小孩也常嘲笑我是“做崽的”,聯(lián)合起來(lái)不跟我玩,并慫恿學(xué)校的同學(xué)也不跟我玩。我只好時(shí)常找?guī)讉€(gè)老實(shí)、淳樸的同學(xué)下軍棋、看書,并暗暗地用功,以優(yōu)異的成績(jī)?nèi)セ負(fù)羲麄儭?杉幢闳绱耍陋?dú)、自卑早已在我幼小的心靈埋下了種子。有一次,比我小兩三歲的少安罵我“做崽的”,我就用拳頭回?fù)袅怂M砩戏艑W(xué)回家,他爸爸氣勢(shì)洶洶地來(lái)到我家,見我就一巴掌。我也不甘示弱,用幼小的雙手推他一下,并嚷著叫他的外號(hào)“毛狗仔”。從那刻起,我意識(shí)到要自尊、自立、自強(qiáng)。
人生無(wú)常。1989年夏天一個(gè)周六中午,太陽(yáng)火辣辣地烤著大地。我中午放學(xué)回家,吃過午飯就和二哥一起去放鴨子。此時(shí),母親還在稻田里噴灑農(nóng)藥。忽然,稻田里隱約傳來(lái)母親呼喚二哥的喊聲,一聲高過一聲。二哥拔腿就往回跑。等我挽起鴨籠回到家時(shí),母親已住進(jìn)鄉(xiāng)里的衛(wèi)生院。醫(yī)生診斷,母親是因晌午打農(nóng)藥中暑引起中風(fēng)。從此,母親再也沒有健康地站起來(lái)。為了省錢,母親不久就出院,父親到處尋訪赤腳醫(yī)生。每次醫(yī)生的到來(lái),都給我們帶來(lái)一點(diǎn)希望,可每次都是失望大于希望。直到后來(lái),經(jīng)浬田鄉(xiāng)的王醫(yī)生治療幾個(gè)月,母親才能不用拐杖獨(dú)立行走,但左腳只能拖著向前邁,左手耷拉著前后擺動(dòng),甚至不能把碗端至嘴邊。這一年秋季,二哥、二姐都輟學(xué)了,父親母親卻堅(jiān)持借錢送我上學(xué)。命運(yùn)的天平又一次向我傾斜,我還有書讀。
父母得病,大哥弱智,生活的擔(dān)子誰(shuí)來(lái)扛?剛二十出頭的大姐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fù)?dān),帶領(lǐng)我們姐弟四人開荒種花生、種紅薯,進(jìn)山砍柴、買柴,挑大糞、下牛糞,把十五畝責(zé)任田種得好好的。我在學(xué)校學(xué)習(xí)更加刻苦,以全校最好的成績(jī)考入鄉(xiāng)里中學(xué)。
讀初中時(shí),我走讀。每天凌晨四點(diǎn),母親就強(qiáng)撐著身子起床做飯。五點(diǎn)半,我一起床就往學(xué)校跑。上完早自習(xí),再跑回家吃早飯。學(xué)校離家有一里路,來(lái)回需要二十分鐘,只有十分鐘的吃飯時(shí)間。每次我一到家,不管鍋里是熟飯還是生米,盛上滿滿的一碗就狼吞虎咽。有時(shí)菜還沒炒,又無(wú)前一天的剩菜時(shí),就舀碗米湯澆上飯,草就一頓。下午一下課,我就往家里跑。一到家,就洗碗、喂豬,趕雞鴨進(jìn)籠,洗豬草,再炒菜。等爸爸媽媽和哥哥姐姐回家時(shí),菜已炒好。我匆匆吃上幾口飯,撒開腿就往學(xué)校跑,常常腳步聲和著晚自習(xí)鈴聲一起走進(jìn)教室。
待到初二,二哥和大姐相繼去廣東省打工,家里的重?fù)?dān)就落在我和二姐肩上。平常我除了幫母親做家務(wù),還要幫二姐管理稻田。春耕時(shí),每天下午課外活動(dòng)時(shí),我都扛把鐵鍬去田畦上除草,下水田鋪岸,進(jìn)秧田查看水位。節(jié)假日,我挑著尿桶,和母親一起去菜園里翻土、下種、鋤草、澆菜。母親邊干活邊教我種菜。如春天種辣椒時(shí),土要壘高、碾細(xì),均勻地撒上辣椒籽,再鋪一層草木灰,然后插上幾根竹片,拱成半圈,再在竹片上蓋一層油紙以保溫。栽包菜時(shí),先挖一個(gè)盤子大的小坑,兩坑之間隔一尺,再把包菜筆直地栽入坑內(nèi),然后澆水,并在坑邊撒上石灰以驅(qū)蟲。
1993年2月,二十四歲的大姐要出嫁了。爆竹聲聲送新娘,我卻躲進(jìn)小巷子偷偷地哭了。我舍不得大姐離開,她為了我們一家勤勤懇懇,自小聰明的她只讀了兩年書就輟學(xué),二十歲如花的姑娘挑起了一家的重?fù)?dān),出嫁時(shí)只有一個(gè)衣柜、一只箱子、一臺(tái)黑白電視機(jī)、一張小方桌。大姐出嫁后,二哥接過大姐的擔(dān)子,每天天剛亮,就挑起糞桶到中學(xué)廁所挑大糞。別人挑一擔(dān),他可以挑兩擔(dān)。他使出全身力氣,挑起糞飛奔向稻田。插秧、砍柴、割禾、打谷,二哥樣樣在行。鄉(xiāng)鄰都夸二哥“插秧就如插秧機(jī),割禾勝過收割機(jī),打谷快如柴油機(jī),好像有使不完的力”。
借遍遠(yuǎn)親近鄰,總算湊齊三千元。二哥帶父親到縣醫(yī)院看病,經(jīng)化驗(yàn),確認(rèn)為胃癌晚期,醫(yī)生說(shuō)最多還能活六個(gè)月。我們得知父親的病情后,心如死灰,耗盡全部家財(cái),換來(lái)的卻是噩耗。我背負(fù)著沉重的悲痛走進(jìn)課堂,模糊的雙眼看不清老師寫了什么,嗡嗡的腦子總想著家里,想著全家如何生活下去。我內(nèi)心開始動(dòng)搖,真不想再拖累家人。二哥、二姐都無(wú)奈地說(shuō):“下半年的初三,你就不要讀了,家里實(shí)在沒錢。”我含淚點(diǎn)頭。可母親卻堅(jiān)持說(shuō):“賣了房子也要供你去讀書。”我渴望讀書,卻又深知家里的赤貧。我不怕困難,寧愿去替別人挑大糞、做小工掙錢,卻害怕有一天沒辦法再讀書。哥哥、姐姐拗不過母親和我,就說(shuō):“初二期末如果沒考到全年級(jí)前四名,你就別讀了。因?yàn)橹挥星八拿庞锌赡芸忌蠋煼叮瑤煼秾W(xué)費(fèi)便宜。如果考上高中或其他中專,也供不起。”于是我憋著一口氣,更加刻苦地學(xué)習(xí),成績(jī)也確有長(zhǎng)進(jìn)。期末領(lǐng)成績(jī)單時(shí),我驚喜地發(fā)現(xiàn)自己的成績(jī)剛好是全年級(jí)第四名,并得了一張“三好學(xué)生”獎(jiǎng)狀和6元獎(jiǎng)學(xué)金。我欣喜若狂地跑回家,一進(jìn)門就氣喘吁吁地喊道:“姆媽,姆媽,我得了獎(jiǎng),我考了全年級(jí)第四名,我得了6塊錢獎(jiǎng)學(xué)金。”母親笑了,額頭上折疊的皺紋也舒展開來(lái)。父親輕聲喚著我的乳名:“蠢公崽,還要努力。”吃過午飯,母親要我送擔(dān)豬草到五里外的姨奶奶家。我挑起豬草,哼著小曲,晃悠悠地出門去。雖然肩膀磨得通紅,可一想到剛才領(lǐng)了獎(jiǎng)學(xué)金,有書讀,我又“嘻嘻”地笑起來(lái),兩腳生風(fēng)般地往前奔跑,兩簍豬草也蕩起秋千。
初三,如期開學(xué)。醫(yī)生預(yù)測(cè)的期限早已過了,雖然父親安在,可一天比一天消瘦,兩只腳如打火棍,只剩皮、骨頭和干癟的血管,整個(gè)身體如被掏空的軀殼。我每天扶父親起床,幫他穿衣。他總是說(shuō):“蠢公崽,要爭(zhēng)口氣,好好讀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早晨,和往常一樣,颼颼的寒風(fēng)穿透屋里墻上的每個(gè)縫隙,我們的心隨著寒風(fēng)一起冷卻。姐夫又來(lái)看望父親,給原本壓抑的家中增添了些許生氣。中午放學(xué)回來(lái),母親要我去喊父親起來(lái)吃午飯。她說(shuō),父親早晨打著呼嚕睡著了,沒吃早飯,現(xiàn)在應(yīng)該醒了。我走進(jìn)房間喊父親,他沒應(yīng)聲,再喊,還是沒回應(yīng)。我伸手一摸,冰涼的感覺觸電般地迅速傳遍全身。我默默地走出房間,對(duì)母親說(shuō):“您去看看……”我知道,那個(gè)時(shí)刻還是來(lái)了。那年春節(jié),是在一片沉默中度過的。
債務(wù)逐年累加,生活越來(lái)越難。拖了半年的400元學(xué)費(fèi),到了不得不繳的時(shí)候。春節(jié)一過,二哥、二姐就都出去打工,剩下我、大哥和母親。初三下學(xué)期緊張的學(xué)習(xí)任務(wù)壓得我喘不過氣,為了抓緊時(shí)間學(xué)習(xí),我把床從家里搬到了教室的課桌上。這樣,晚上可以多點(diǎn)時(shí)間溫習(xí)功課。每天晚上十點(diǎn),學(xué)校熄燈后,我就從抽屜里摸出煤油燈,小心地點(diǎn)燃。在豆大的燈火下,我捧著書繼續(xù)復(fù)習(xí)。此時(shí),伴著窗外蟋蟀的輕吟,教室里豆大的燈火在風(fēng)中搖曳。當(dāng)上下眼皮打架時(shí),我就把床板架在課桌上,攤開棉被,和衣而睡。早晨,起床的鈴聲還沒響,習(xí)慣早起的我已疊好被子,堆放在教室的角落,用床板擋住,再來(lái)到校園外的草地上,背課文、記單詞。
學(xué)習(xí)和農(nóng)活,兩手都要抓。春播在即,培種育秧苗便成了頭等大事。在母親的指導(dǎo)下,我把稻種從樓上背下來(lái),按品種分裝在不同的蛇皮袋里,并扎上不同的結(jié),放進(jìn)池塘浸泡,用磚塊壓實(shí),避免與別人家的混淆。兩天后,再把稻種提上岸,倒進(jìn)可以滲水的籮筐里。每天早晨和晚上,燒一鍋熱水,再摻點(diǎn)涼水,調(diào)至溫?zé)幔瑵姙⒃诘痉N上,滲干水后提到屋檐下,這樣保持溫度可以催芽。當(dāng)?shù)痉N的根長(zhǎng)長(zhǎng)了但芽還短時(shí),就適當(dāng)灑些冷水,待芽長(zhǎng)到兩毫米便可播種了。看著稻種圓圓的身子上長(zhǎng)著長(zhǎng)長(zhǎng)的腿、白白的芽,甭提多高興。
一整個(gè)春天,我都奔波在學(xué)校和田間。繁忙的農(nóng)活和繁重的學(xué)習(xí),使原本體弱的我有點(diǎn)支撐不住。我臉上蠟黃,每次蹲下去就很難起身,只好扶著東西吃力地站起來(lái),感覺天旋地轉(zhuǎn),頭腦渾渾噩噩,把眼睛閉上好一陣子,才能看清事物。有一天晚上,我實(shí)在支撐不住了,學(xué)校熄燈鈴響起,我就架起床鋪睡了。第二天早上,起床鈴響了,我一醒來(lái),就感覺渾身疼痛,額頭燙得厲害。我收拾好床被,坐在凳子上,想硬撐,但頭痛無(wú)力,只好向老師請(qǐng)了半天假。一回家里,我就告訴母親我發(fā)燒了。母親摸了摸我的額頭說(shuō):“好崽,怎么發(fā)高燒了。”她忙找來(lái)姜、蔥和米飯一起煮,要我趁熱吃下去。可燒依舊沒退。早飯后,母親連忙帶我去醫(yī)院。經(jīng)檢查,高燒40度,過度貧血,這下可急壞了母親。我說(shuō):“沒關(guān)系,打幾針,吃點(diǎn)藥,就會(huì)好的。”醫(yī)生開了二十幾元錢的藥,并打了退燒針。母親堅(jiān)持要買一瓶補(bǔ)腦汁給我,我不同意,但拗不過她,最后還是花4元錢買了一瓶。下午,我又走進(jìn)教室。
由于干農(nóng)活擠占了不少學(xué)習(xí)時(shí)間,我的成績(jī)受到影響。畢業(yè)會(huì)考,我的成績(jī)從全班第三名退到第九名。班主任彭老師找我談話,我一股腦兒把實(shí)情向他哭訴出來(lái)。他鼓勵(lì)我說(shuō):“別灰心,離升學(xué)考試還有一個(gè)月。我相信,逆境出人才。”我點(diǎn)了點(diǎn)頭。我知道,如果以這樣的成績(jī)參加升學(xué)考試,肯定考不上師范,即使考上高中,也必將告別讀書生涯。經(jīng)過彭老師的開導(dǎo),又想起父親“要爭(zhēng)一口氣”的囑托,我重新鼓起勇氣。5月底,二哥打工回來(lái),我便全力撲在最后一個(gè)月的沖刺中。
也許是天無(wú)絕人之路,或是多吃一份苦就多一分收獲。中考后一進(jìn)校園,就有同學(xué)告訴我我考上了師范。我半信半疑地走向班主任的辦公室。彭老師早早站在門口張望,一看見我就說(shuō):“紹德,紹德,你過來(lái)。你考上了師范。總分523分,物理98分,數(shù)學(xué)89分,語(yǔ)文……”他一口氣說(shuō)完我所有科目的成績(jī)。當(dāng)別的老師問我的分?jǐn)?shù)時(shí),他都搶著一一回答。我考上師范的消息迅速傳遍村鄰鄉(xiāng)舍,好像比考上北大、清華還激動(dòng)人心,一時(shí)成為鄉(xiāng)里的焦點(diǎn)。村民們看到母親,都說(shuō):“你的崽可爭(zhēng)了一口氣,考上師范了。”母親更是笑得合不攏嘴。原本絕無(wú)閑人串的家門,不時(shí)也有人進(jìn)來(lái)坐坐,道聲喜。我獨(dú)自走進(jìn)山里,來(lái)到父親的墳前,告訴他:我爭(zhēng)了氣,考上師范了。
錄取通知書是9月5日收到的。可一看到950元的學(xué)費(fèi),全家都陷入沉默,不知如何是好。雖然哥哥姐姐打工掙了點(diǎn)錢,但大多數(shù)用來(lái)還債了,只剩兩三百元的生活費(fèi)。母親忙叫二哥拖谷子去賣,1500斤稻谷只賣得500元。剩下的只夠全家口糧,不能再賣了。實(shí)在沒辦法,我只能厚著臉皮去向親戚借錢。每個(gè)親戚都了解我的家境,今年借不知何年才能還。與其說(shuō)是借,倒不如說(shuō)是乞求更貼切。
晚上,我兩手空空地來(lái)到姨媽家里。出門時(shí),母親就囑咐我:“你二表哥匯了2000元給你姨媽,你去向她借,肯定借得到。”我真不好意思再向姨媽借錢了,前些年欠的幾千元還沒還。姨媽最疼我,一到她村口,我老遠(yuǎn)就喊:“姨媽!姨媽!”“誒!好崽!你怎么這么晚才來(lái)?吃飯了嗎?”姨媽摸著我的腦袋說(shuō)。“我到鄧家請(qǐng)客。”我答道。“請(qǐng)客?”姨媽疑惑地說(shuō)。我接過話茬:“我考上師范了,九號(hào)做酒。”“真的?”姨媽問道。“嗯!收到了錄取通知書,錄到永新師范統(tǒng)招生,學(xué)費(fèi)950元。”姨媽笑瞇瞇地說(shuō):“太好了!太好了!總算爭(zhēng)了口氣。”“可我……”我哭著說(shuō),“可我還沒湊夠?qū)W費(fèi)。” 姨媽說(shuō):“別哭,別哭,還差多少?”“還差四五百。”我哽咽著答道。“唉,”姨媽嘆了口氣又說(shuō),“明天,我借給你五百,別哭了,別哭了啊!”姨媽為我煎了三個(gè)雞蛋。我吃完就去睡覺,躺在床上翻來(lái)覆去,我不覺想起初中三年來(lái)的學(xué)習(xí)與生活,淚如泉涌。第二天早上醒來(lái),枕頭都被淚水浸濕了。
九月九日的小山村,沐浴在一片喜洋洋的氛圍中,到的客人不多,收到的禮金也不多。那天,班上還有幾個(gè)同學(xué)做升學(xué)宴,但班主任跟全部科任老師都來(lái)到我家,并贈(zèng)送我一本筆記本和一支鋼筆,筆記上面寫著: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十日早晨,噼里啪啦的爆竹聲喚醒了山村的黎明,金秋的朝陽(yáng)把希望灑向大地,溫柔的山風(fēng)輕拂著衣角,在山路拐彎處,我回望老屋,斜立門口的銀鬢母親正拭淚眺望,不停地?fù)]手,她身旁是踮腳遠(yuǎn)望的二姐、屹立風(fēng)中目送我的二哥。再見了,我親愛的故鄉(xiāng);再見了,這辛酸的故土。帶著親人的寄托,帶著自己的理想,帶著沾滿淚水的學(xué)費(fèi),我獨(dú)自踏上了求學(xué)之路。
來(lái)到朝思暮想的永新師范,我立刻陶醉在它迷人的景色里。學(xué)校坐落在東華嶺上,潺潺的禾河傍山而過,錯(cuò)落有致的教室、宿舍隱蔽在樹蔭中,如蓋的樹木庇護(hù)著這座教師的搖籃。我在師兄的幫助下,報(bào)名、繳費(fèi)、找宿舍。晚飯后,彼此不相識(shí)的同學(xué)操著方言各自找老鄉(xiāng)。我獨(dú)自徘徊在環(huán)山路上,想起家務(wù)誰(shuí)來(lái)做,剛栽的白菜誰(shuí)去澆水、施肥,晚稻長(zhǎng)勢(shì)如何,推算今年的收成,想起母親的辛勞,不覺潸然淚下。我開始盤算每天的生活開支。饅頭一角錢一個(gè),吃5個(gè)就飽了,飯菜最低一元一份。于是,我決定每天花兩元,早晨、中午吃饅頭,晚上吃飯。只身在外,我不愿在學(xué)費(fèi)之外再給家里多添負(fù)擔(dān)。我下定決心,日子雖然清苦,但我一定要學(xué)出成績(jī)來(lái)。
學(xué)習(xí)步入正軌,矮個(gè)子的我坐在第三排,讀書依舊如初三時(shí)一樣認(rèn)真。平時(shí)寡言少語(yǔ)的我總是默默地學(xué)習(xí),心中放不下的還是家里的事務(wù)。我平常交往的同學(xué)不多,周仁清便是其一。在草坪上一次偶然交談后,我們相識(shí)了。他說(shuō):“人窮一點(diǎn)沒關(guān)系,但要窮得有志氣。”我也說(shuō):“人活著就是要不懈地奮斗,不斷地向困難挑戰(zhàn)。其實(shí),每一個(gè)困難,對(duì)我們來(lái)說(shuō)都是一次機(jī)遇,要么倒下,要么崛起。”月明星稀時(shí),我倆挑燈夜讀,爭(zhēng)論不同的觀點(diǎn)。后來(lái),我擔(dān)任班里的團(tuán)支部書記,忙于學(xué)校的事務(wù),而他潛心美術(shù),沉醉于線條色彩里,我倆便踏上了不同的學(xué)習(xí)軌道,但信念是相通的。
十月一日快到了,聽說(shuō)學(xué)校放假3天,加上雙休日,共5天。同學(xué)們奔相告知,個(gè)個(gè)扳著指頭倒計(jì)時(shí)。好不容易盼到9月30日,晚自習(xí)后,大家急匆匆地趕往寢室,拾掇衣物和書籍,裝進(jìn)旅行包里。第二天一早,同學(xué)們就三五成群地走向車站,踏上回家的客車。
歸心似箭,景物飛逝。雖然客車時(shí)速達(dá)70公里,但總覺得像一只慢慢向前爬的蝸牛。
客車駛進(jìn)家鄉(xiāng)的車站了,焦灼如焚的心終于平靜。一剎車,我抓起包跳下車就往家趕。金秋的風(fēng)蕩起層層稻浪,山中麻雀的歌聲在風(fēng)中飄過。馭風(fēng)的雙腳一踏進(jìn)村莊,一股鄉(xiāng)情涌滿心頭。
老屋的木門依然如舊,我推門而進(jìn),張口就喊:“姆媽,我回來(lái)了!”久久未有人應(yīng)聲,我忙丟下包去尋找。半山腰的菜地上,一位銀發(fā)老婦正單手鋤地,我忙跑上去喊姆媽。母親猛回頭,抖落掛在額頭的汗珠,放下鋤頭,撫摸著我的頭說(shuō):“乖崽呀,這么早就回來(lái)了,累了嗎?”我忙說(shuō):“不累,不累。姆媽,我來(lái)。”說(shuō)著就掄起鋤頭,邊鋤地邊跟母親講學(xué)校里發(fā)生的雞毛蒜皮的事。母親總是面帶微笑地傾聽著。
午飯過后,我扛起一把鐵鍬走向田間,瞧瞧稻谷的長(zhǎng)勢(shì),估算每畝的收成,下到田里踩踩,看看田泥是否過干。走遍每畝稻田,才放心地回家。
在家的這幾天,我每天都忙著菜園、稻田和家務(wù),好像要把在校幾個(gè)月欠下的勞作全補(bǔ)回來(lái)。時(shí)間匆匆,返校的日期到了。母親炒了一大兜花生和一把缸蘿卜干炒肉,塞得我的包快炸了。我背著沉甸甸的包,背上沉甸甸的母愛,含著兩眶淚水,再次離開了故土。
返校后,每位同學(xué)都帶來(lái)了家鄉(xiāng)的特產(chǎn),大家分享著、談?wù)撝瑐€(gè)個(gè)喜氣洋洋,而我正算計(jì)著這把缸菜可以省下一個(gè)星期的菜錢。一切又歸于正軌。第一個(gè)學(xué)期,在靜靜的學(xué)習(xí)中悄悄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