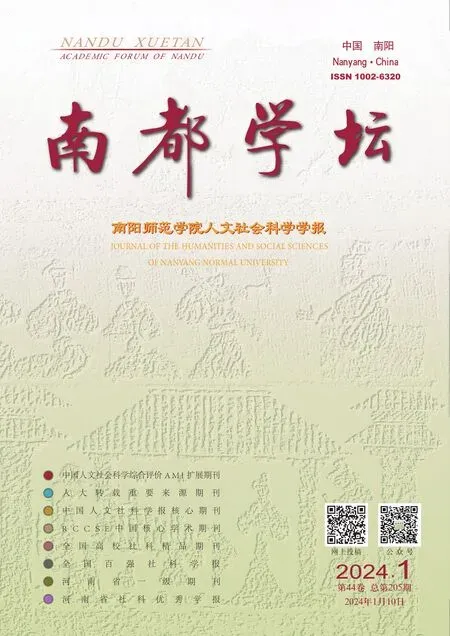數字貿易、產業結構升級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基于長三角樣本的分析
劉 偉, 未良莉
(合肥師范學院 經濟與管理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問題提出與相關研究
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促進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數字經濟形勢下,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成為實體經濟的重要驅動力。利用智能技術、數字技術對傳統制造業進行改造,賦能制造業轉型升級。作為數字經濟延伸與應用的數字貿易,研究其與產業結構升級、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邏輯關系很有必要。
長三角地區是我國經濟發展最為活躍、開放程度最為廣泛、創新能力最為強勁的區域之一,肩負著“一體化”與“高質量”協同發展的重要使命[1]。《長三角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顯示,長三角以數字經濟帶動整體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態勢已經形成。2021年浙江省、江蘇省、安徽省和上海市的數字經濟規模總量達到12.7萬億元,以移動支付、線上交易平臺、跨境電商為代表的數字貿易新模式、新業態,正在長三角地區高速發展。長三角地區如何通過發展數字貿易這一方式來優化產業結構、提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
關于數字貿易、產業結構升級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相關文獻可歸納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是關于數字貿易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研究。王瑞榮認為,數字貿易驅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系,其賦能創新和發展需要政策要素、資金要素、技術要素等多方面要素支撐[2]。謝會強、雷一鳴提出,要通過技術知識的溢出和學習效應,充分釋放數字貿易對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共同前進的跨區域貢獻,實現產業高質量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3]。徐世騰、金翎等指出,隨著數字服務貿易壁壘的增加,我國制造業出口產品的質量升級受到了明顯的抑制,設施與連接、支付體系等領域限制性措施增加的負面效應尤為顯著[4]。黃永興、沈紫君提出,需要健全現代金融體系,加快構建數字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機制體制[5]。
第二類是關于數字貿易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研究。韓民春、張霄研究發現,數字貿易的發展不僅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金融服務效率,還促進了技術創新與制造業出口技術復雜度的提升,進而推動出口產品升級[6]。羅晶認為,數字貿易發展能夠通過技術賦能效應和“倒逼”效應促進產業結構升級[7]。方昊煒認為,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傳統產業的運營等環節,通過優化內部生產結構,靈活改進生產過程,成功實現了產業鏈上的上游遷移,從而推動了產業發展基礎的轉型升級,加速了組織業態的變革和創新,同時也對產業布局產生了重要影響[8]。黨琳等指出,被數字技術強化的市場競爭機制會倒逼企業加速創新研發,加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9]。
第三類是關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研究。王婷偉,蘇梽芳等采用NCA與fsQCA相結合的方法,得出單個條件變量并非是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但優化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具有普適的作用[10]。梁小甜,文宗瑜通過驗證表明,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等均有助于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11]。童磊、榮亞飛為廓清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外部性(專業化外部性、多樣化外部性)與產業升級之間的關系,基于2006—2019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運用PVAR模型,對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探究[12]。
研究長三角數字貿易發展的文獻較少。金澤虎、蔣婷婷分析發現,數字貿易水平的提高顯著促進了長三角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中介作用不顯著[13]。傅為忠、劉瑤指出,2011—2019年長三角區域產業數字化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呈現上升態勢,但整體水平不高且空間差異較大,與良性協調仍存在一定差距[14]。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多基于數字貿易的作用路徑進行理論分析,較少有學者開展實證研究;另外,研究長三角地區數字貿易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文獻很少。本文立足于長三角地區,將數字貿易、產業結構升級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歸入同一范疇,研究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構建模型進行實證驗證。
二、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貿易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
數字貿易在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方面具有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創新發展新動能的作用。秦鑄清等研究發現,數字經濟通過提升經濟效益、促進綠色共享、引致技術創新以及增加社會效益等途徑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15]。產業的數字化促進了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創新,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技術基礎;貿易方式的數字化打破了貿易空間和時間的局限,擴大了市場空間,推動了制造業向高質量發展邁進;貿易對象的數字化加強了貿易主體的聯系,實現買賣雙方信息的有效對接,為制造業企業提供信息交互,形成了更高效的分工和關系協調,提高資源配置和貿易市場效率,優化了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數字貿易對長三角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產生促進作用。
(二)數字貿易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機制
數字貿易的快速發展加速了貿易方式的轉變,推動了制造業的高端化、智能化進程。姚戰琪研究發現,數字貿易通過 R&D 強度對中國產業結構的作用主要通過人力資本、R&D 強度進行傳導[16]。其一,從數字產業化視角來看,數字技術改變了傳統要素的投入方式,優化了要素資源配置效率;通過挖掘數據、制定精準營銷策略、定制個性化需求,滿足消費者不同偏好,數字貿易在此情境下重塑消費者需求,推動產業升級重構。其二,從產業數字化視角來看,數字技術賦能制造業產業鏈上的生產、研發、服務等環節,推動制造業產業鏈的智能化升級和重塑。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數字貿易對于促進長三角地區制造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具有積極作用。
(三)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
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能直接和間接推動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方昊煒認為,隨著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新技術、新動能、新產業的持續涌現,尤其是制造技術和智能技術的融合,為上下游關聯部門的協調運轉提供了便捷,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8]。BRANDT L, THUN E提出,產業結構升級通過新技術形成產業的先發優勢和創新生態系統,可以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17]。伴隨著萬物互聯、智能化的發展,工業結構向智能化、高端化發展,產業結構升級致力于將傳統資源轉化為新產品和新服務,高技術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的快速成長優化了服務業結構。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互為促進,實現產業由量變到質變,促使制造業的高級化和合理化,進而推動制造業實現高質量發展。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在數字貿易助推動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中介效應。
三、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研究設計
(一)評價體系
學者們對于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觀點不一。黃順春、張書齊認為,應從經濟效率、科技創新、資源環境、質量品牌、社會服務、保障和支撐程度等方面評價制造業高質量發展[18]。鄭耀群從創新驅動、效率變革、質量提升、綠色發展和產業融合5個維度,構建了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19]。本文借鑒黃順春、鄭耀群、唐曉華[20]等學者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的選取,結合長三角地區制造業發展現狀,構建以技術創新、經濟效益、綠色發展和社會效益為一級指標的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具體的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長三角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二)測度方法
1.熵權法計算
熵權法以熵作為信息量的度量,通過計算某個指標的信息熵,來反映該指標提供的信息量的多少,以確定該指標在綜合評價中的作用大小[21]。信息熵的大小與該指標的變異程度呈反比,變異程度的大小又反映出提供的信息量的多少,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則其權重越大。熵權法計算各指標的步驟如下:
(1)數據的無量綱化處理。
對正向指標標準化處理:
對負向指標標準化處理:
上式中Xij表示第i年第j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指標數據。
(2)計算評價指標的貢獻度:
(3)計算熵值:
(4)計算差異性系數:
gj=1-ej
(5)計算評價指標的權重:
其數值越大,說明該指標越重要。
(6)計算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
2.指標變化趨勢
長三角地區2012—2021年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指數及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分析下圖的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指數,我們發現該區域各省市指數表現各異。浙江省2012—2021年的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指數一直處于上升趨勢,安徽省2012—2021年的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指數處于波動上升趨勢;江蘇省和上海市2012—2021年的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指數處于先上升、后下降趨勢。總體來看,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呈上升趨勢。

圖1 2012—2021年長三角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指數及變化趨勢
四、實證檢驗
(一)相關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
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Y)。具體測算方法見本文第三部分。
2.解釋變量
數字貿易發展水平(X)。學者對數字貿易的評價指標不統一,借鑒任同蓮[22]、金澤虎[13]等學者的研究,選取互聯網環境、物流環境、貿易潛力和政策環境四個一級指標評價數字貿易。互聯網環境包括互聯網寬帶用戶數、電話普及率(部/百人)兩個二級指標;物流環境包括貨運量、物流相關活動從業人員兩個二級指標;貿易潛力GDP、進出口貿易總額、貿易開放度三個三級指標;政策環境包括R&D經費支出,具體評價指標體系見表2。根據以上數字貿易評價指標體系,利用熵值法計算長三角地區2012—2021年期間數字貿易發展水平的指標權重。

表2 長三角地區數字貿易評價指標體系
根據上述測度方法計算出長三角地區各省市的數字貿易水平,并繪制2012—2021年長三角地區的數字貿易發展指數及變化趨勢,如圖2所示。分析圖2,我們發現長三角地區2012—2021年的數字貿易水平是逐漸遞增的,其中遞增趨勢比較明顯的是江蘇省和浙江省,平穩遞增的是安徽省,緩慢遞增的是上海市。從數字貿易的平均發展水平來看,最高的是江蘇省,其次是安徽省。總體來看,長三角地區數字貿易發展指數呈上升趨勢。
3.控制變量
(1)政府調控(K1):借鑒金澤虎和蔣婷婷的計算方法,按財政支出占GDP比例來進行量化[13]。
(2)對外開放度(K2):以進出口貿易額占GDP比例來進行衡量。
4.中介變量
產業結構升級(M):借鑒方昊煒等學者利用產業結構層次系數法來計算產業結構升級指數[8]。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qi是第i產業產值占三大產業總值的比重。M值越大,產業結構升級水平越高;M值越小,產業結構升級水平越低。
(二)模型設定
1.基準回歸模型
構建驗證數字貿易對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影響的模型如下:
Yij=α0+α1Xij+α2K1ij+α3K2ij+ε
i=1,2,3,4;j=2012,2013,……2021
2.中介效應回歸模型
Yij=α0+α1Xij+α2Kij+ε
Mij=β0+β1Xij+β2Kij+σ
Yij=γ0+γ1Xij+γ2Mij+γ3Kij+μ
其中:Yij,Xij,Mij分別表示長三角地區第i個省市,第j年的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數字貿易發展水平,以及產業結構升級水平;K代表控制變量,本文的控制變量有政府控制和μ代表隨機擾動項。
(三)實證結果分析
1.描述性統計
本文針對2012—2021年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所得結果見表3。其中,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Y)的最大值為0.5470,最小值為0.3532,說明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在不同的時期區分明顯。可以看出數字貿易發展水平(X)統計中,均值為0.3673,最大值為0.6673,最小值為0.1798,具有明顯的差異。控制變量產業結構升級(M)、政府調控(K1)、對外開放度(K2)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同樣也具有明顯的差異。
2.基準回歸分析
模型(1)為數字貿易對長三角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結果,數字貿易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在顯著性水平為1%的情況下通過了檢驗,表明數字貿易對長三角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呈現積極的促進效用。隨后逐步向模型(1)中添加政府調控和地區開放程度兩個控制變量,得到模型(2)和模型(3),從回歸結果可得出,即使加入了控制變量,數字貿易對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依舊在1%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進而可驗證假設1成立。

表4 基準回歸分析
3.中介效應回歸分析
本文考慮廣義最小二乘法來驗證數字貿易、產業結構升級及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所得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中介效應回歸分析
模型(4)的回歸結果顯示數字貿易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表明數字貿易對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具有促進作用。模型(5)驗證了數字貿易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其回歸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表明數字貿易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促進作用,可驗證假設2成立。模型(6)驗證了數字貿易與產業結構升級同時對長三角制地區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在10%顯著性水平下回歸系數為正,表明數字貿易能作用于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進而推動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可驗證假設3成立。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在全球數字經濟飛速發展時期,數字貿易作為數字經濟外向延伸與應用的重要媒介,已成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驅動力量。作者在綜合分析數字貿易、產業結構升級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三者理論影響機制基礎上,提出了三個假設,并利用長三角地區四個省市的經濟、社會以及環境變量通過熵權法分別構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數字貿易發展水平數據,利用中介效應模型測算數字貿易發展水平對制造業發展水平的促進作用,以及產業結構升級的中介效應。
結果表明數字貿易水平的提高對長三角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數字貿易水平的提高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進而能推動長三角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即數字貿易在推動長三角制造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發揮了一定的中介作用。而且,政府調控和地區開放程度對長三角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也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
(二)建議
立足長三角地區實際情況,加快數字貿易發展,充分發揮其在推動長三角地區制造業實現高質量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加快推進數字設施建設,賦能數字化技術,提升數字化使用效能,搭建數字貿易平臺,構建數字貿易發展評估數據庫,增強制造業國際競爭力,有效推動長三角地區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
要以開放引領數字貿易發展,帶動長三角地區產業數字化水平與數字產業化水平的提升,加快制造業產業結構高端化、智能化進程,發揮數字貿易在資源配置和要素流動中的作用,提升企業研發創新水平,優化數字產業布局,加快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相互融合、共同發展,間接促進長三角地區制造業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