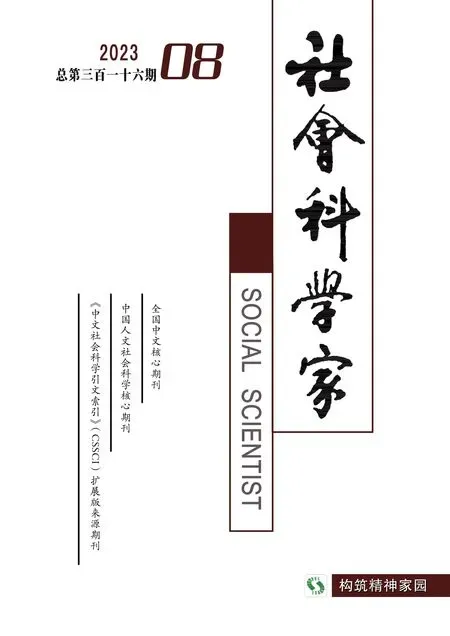小兒科有大學問:推動中國特色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發展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姚建龍教授訪談
姚建龍,柳 簫
姚建龍(1977-),江西永豐人,法學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政治與法律》主編,兼任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會長、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會長等,受聘為國務院婦兒工委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共青團中央等在相關領域咨詢專家以及上海市重大行政決策咨詢論證專家、市政府立法專家、市教委法律顧問、浦東新區區委區政府法律咨詢專家等。主要從事刑事法學、青少年法學、教育法學研究,近年來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等國家級、省部級課題10 余項,在《中國法學》等核心刊物發表論文近200 篇,出版個人專著9 部。曾獲全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先進工作者、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上海市十大優秀中青年法學家、上海市杰出青年崗位能手、上海市禁毒工作先進工作者、上海市曙光學者、第八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首屆“全國刑法學優秀學術著作獎(1984-2014)”專著類一等獎等榮譽。
柳簫(以下簡稱“柳”):姚教授,您好!很榮幸您能夠接受此次訪談。我們都知道您深耕法學領域二十余載,始終將法學作為一種志業,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刑事法學、青少年法學、教育法學。不知能否與我們分享一下您走上學術道路的心路歷程?
姚建龍(以下簡稱“姚”):仔細想來,我成為一名法律人也是出于偶然。1995年,我考入大學。起初我的第一志愿并非法學,而是其他專業,最后調劑到商學院的法學專業。不過,雖然是法學專業的本科生,但當時我們更多精力是在學習一些經濟類課程。盡管我十分努力地學習,可還是產生了許多迷茫和困惑,不過也搞清楚了一件事,即我對刑事法學更感興趣。大學畢業那年,我正處于一個非常迷茫的階段,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前景何在。但我并沒有深陷其中無法自拔,而是依然努力學習為碩士研究生考試做準備。后來,機緣巧合下我暫時選擇了重慶市勞教戒毒所民警作為我的第一份職業。也正是在戒毒所工作期間,一次特殊的經歷為我日后堅定從事青少年犯罪與保護研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這段從警生涯也對我的學術研究和觀點產生了較大影響。2000年,我考上了華東政法學院刑法學(青少年犯罪)專業研究生,也是這個專業方向唯一的研究生。然而在當時,這個專業方向在很多人看來是沒有前途的。如此境況一度對我打擊非常大,于是我用了8個月的時間思考這個專業的意義是什么、自己未來要做什么。最終我意識到,人生很多時候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成本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當下所處的位置和所經歷的事情也許就是最好的安排,危機也可能是機遇,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做到最好。于是,青少年犯罪與青少年保護便成了我一直堅持研究的核心領域之一。2003年,研究生畢業后我選擇了留校并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主要從事比較少年司法的研究,博士畢業后又在北京師范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可以說,學生時代的我,最大的收獲是清楚了自己的目標,堅定了自己追求學術的道路和方向,我將其稱為理智化的過程。法律學習本身是一種理智化的過程,這種理智化并不在于讀書的多少,而在于考慮清楚自己需要成為什么樣的人。
柳:您一直致力于我國兒童福利與未成年人保護事業,積極為維護兒童利益發聲。在您看來,2020年我國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以下簡稱“《未保法》”)實現了“福利法”的基本轉向,形成了未成年人“六大保護”體系,同時確立了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新體制。那么,在此背景下,您認為我國當前在未成年人保護領域還存在哪些不足?
姚:首先,我認為最為重要的一點是目前中國還缺乏一個兒童權利啟蒙的過程。兒童史的研究發現,現代兒童觀念的產生不過是近兩百年來的事情。在此之前,雖然經歷了從認為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幾乎沒有區別到認為孩子是“縮小的成人”的改變,但未成年人始終未被看作是區別于成年人的獨立群體。直到17世紀,啟蒙思想家們開始關注孩子被忽視的問題,并認為他們需要保護和培養。18世紀至19世紀,隨著家庭的日漸解體與學校教育制度的形成,同時受到啟蒙運動、反對兒童虐待以及拯救兒童運動等社會改革運動的影響,現代兒童觀念正式誕生,未成年人才真正開始從成人社會中脫離出來。可見,現代兒童觀念的基本特征是認為未成年人與成年人本質上是不同的,是需要特殊撫育和保護的群體。現代社會的未成年人保護制度便是建立在此現代兒童觀念基礎之上。客觀上說,現代兒童觀在我國的確立還任重道遠。近年來,輿論過度渲染一些低齡未成年人極端惡性犯罪案件,兒童的形象出現了被解構并逐漸污名化的傾向,其負面影響正在顯現。
進一步而言,雖然新修訂的《未保法》實現了“福利法”的基本轉向,正式確立了國家親權原則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并完善了包括建立未成年人保護協調機制、明確民政部門作為國家監護人的角色和地位等在內的未成年人保護體制機制,同時將“四大保護”拓展為“六大保護”,強化和嚴密了未成年人保護的法網。但是其中一個重大的問題在于,該法仍然在總體上將未成年人視為被保護的對象,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主體地位。因此,我一直強調要將“福利權”作為未成年人的一項基本權利,即在法律上賦予未成年人以獨立的法律主體地位,從而避免陷入“無微不至的保護等于無微不至的控制”的悖論。這樣一種缺乏對未成年人權利主體地位尊重的具體表現是,一方面強調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但另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未成年人保障性權利(如普惠性兒童津貼)并未能在法律上得以確認。再如,國家對于未成年人受教育權的保障還不完善,特別是義務教育范圍仍未能涵蓋未成年人的完整成長階段。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國還處于適度普惠型兒童福利階段,且“適度普惠”的提法都十分謹慎。然而我認為,對于未成年人“福利權”的保障不應當被忽視,這雖然與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相關,但更關乎的是觀念。
此外,我國當前在未成年人保護領域的不足之處還包括缺乏一支從事相關領域研究的專業隊伍。未成年人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無法像婦女、老年人、殘疾人等特殊群體一樣為自己的權利發聲。在此種情形下,對未成年人及未成年人法學的研究便顯得尤為重要。但是,目前在我國從事這一相關領域研究的專業隊伍還十分匱乏,同時未成年人法學的邊緣學科地位也極大地限制了未成年人保護領域研究的發展。
柳:《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簡稱“《預防法》”)已實施兩年有余,您曾受托起草了《預防法》修訂草案建議稿。能否和我們分享一下您的心得,以及對該部新修訂的法律的進步、局限與其實施過程中的重大問題稍加點評?
姚: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專家建議稿》(以下簡稱“《建議稿》”)的起草工作,我主要有以下兩點心得:第一,目前我國學界對于未成年人法的理論研究極為薄弱。例如,在《預防法》修訂的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十一)》”)居然采取了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做法,實在令人無法理解。因為《預防法》的修改原本便已經能夠阻止未成年人罪錯行為的刑法化,從而貫徹“以教代罰”。但最后我們會發現,低齡未成年人犯罪依然還是要通過刑法進行規制。那么在兩部法律同步修訂過程中,為何不直接通過完善《預防法》來回應此類問題卻要依靠刑法呢?此情形的出現,實則反映出未成年人法背后的理論準備嚴重不足以及未成年人法學學科地位的相對弱勢。第二,立法機關應當保持理性,不能僅僅根據個案而簡單地對輿情進行回應。要始終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高立法的專業化水平。
當然,新修訂的《預防法》還是有進步的:第一,與《未保法》同步修改,“兩法”的關系更加合理、清晰;第二,進一步完善了“不良行為”與“嚴重不良行為”的內涵與外延,對未成年人罪錯行為的分級相對更加科學;第三,盡可能地細化和完善了對未成年人罪錯行為的保護處分措施。當然,相較于舊法,該部法律雖然具有許多進步之處,但我們在肯定這種重大進步的同時,還應當看到在如此重要的“兩法”修訂契機下,仍然留下了諸多遺憾。其中主要體現為:第一,將違警行為與觸刑行為這兩種法律性質截然不同的行為混同為嚴重不良行為,進而造成了相對應的保護處分措施配置的混亂與爭議;第二,《預防法》未能進一步“少年法化”,即未能將未成年人罪錯行為的干預從《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中分離出來,代之以專門的保護處分措施——即仍然未能實現“寬容而不縱容”。總之,《預防法》本應系統規定罪錯未成年人處置的組織、實體和程序,從而解決我國獨立少年法缺位的問題。因此,我認為,本次《預防法》的“少年法化”雖得到關注,但遠遠沒有完成。
對于《預防法》實施過程中的重大問題,我認為當前主要存在的不足在于:一方面,《預防法》第七條指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門應當由專門機構或者經過專業培訓、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專門人員負責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同時在實務中也強調對相關工作設置專門評價體系。然而,在實際責任落實過程中卻存在對法律規定的變形、走樣和加工。另一方面,相關實務部門對于新修訂的《預防法》缺乏必要且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導致在實踐中法律執行效果不佳。例如,《預防法》規定公安機關可以對有嚴重不良行為未成年人采取矯治教育措施,原本這一新規定可以有效彌補對有嚴重不良行為未成年人干預措施不足的問題,但實踐中公安機關對這一規定基本上并未啟用。再如,對于專門學校的建設出現兩個“極端”,有的地方專門學校閑置,而有的地方全省卻沒有一所專門學校。
柳:近年來,低齡未成年人惡性犯罪案件屢見報端并掀起了巨大的輿論反響,網友們出于道德義憤主張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刑法修正案(十一)》也將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下調至十二周歲。但我知道您一直立場鮮明地反對刑事責任年齡的降低,請問您是基于怎樣的考量?
姚:在我看來,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將刑事責任年齡下調至十二周歲的規定并不是一次創新,與清末《大清新刑律》所采用的“刑事成年(丁年)”年齡標準一致。其實,最初沈家本在主持起草《大清刑律草案》時,本將刑事責任起點年齡規定為十六周歲,但因當時反對之聲過于強烈,才最終確定為十二周歲。此后歷經百余年,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變化呈現出不斷升高而非降低的趨勢。但本次《刑法修正案(十一)》卻“逆升反降”,對這一涉及刑法根基的問題作出重大調整,且刑法學界對此竟然少有人反對,實在令人“費解”。
正如沈家本所言,“丁年以內乃教育之主體非刑罰之主體”。我國刑事立法經過百年變遷,逐漸確定了將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作為未成年人承擔刑事責任的例外規定,并且設定了十四周歲這一法定最低年齡以約束此例外。換句話說,確立刑事責任年齡過渡階段即將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承擔刑事責任年齡的范圍限定于八類犯罪本身就已經是對十六周歲刑事成年年齡的例外,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又設置了在特定情形下能夠突破十四周歲的底線將下至十二周歲的兒童納入刑罰處罰范圍內,可謂是例外之外的“再例外”。然而,我們需要清楚的是,刑事責任年齡的確立實際上只是相對公平、合理的法律擬制,這既是科學問題,更是觀念問題。因此,在本質上,刑事責任年齡是“有跟無”的關系,而非“多跟少”的關系。
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爭議,實則關乎童年觀、罪錯觀、保護觀三個觀念性的分歧。其一,童年觀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判斷未成年人與成年人的界限;其二,罪錯觀的分歧主要在于對未成年人罪錯行為應側重報應主義還是保護主義;其三,保護觀的分歧主要在于未成年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沖突時應如何取舍。在我看來,對于童年觀的分歧,我們不能僅將生理標準作為判斷是否成年的依據,還應結合心理、社會、法律等多元角度進行分析;對于罪錯觀的分歧,我認為面對未成年人罪錯行為應堅決摒棄報應主義而采用保護主義;對于保護觀的分歧,其實只有優先保護未成年人才會最終達到與保護社會利益的二元價值統一。
如果立法機關不從頂層設計角度系統地考慮我國獨立少年司法制度的構建問題,那么,《刑法修正案(十一)》只不過是打開了“飲鴆止渴”的“潘多拉魔盒”,立法機關遲早將再次面對刑事責任年齡是否應繼續降低——甚至恢復未成年人死刑的“呼吁”。
柳:您一直認為未成年人犯罪不是“惡”,而是“錯”,并強調解決“逗鼠困局”和“養豬困局”的關鍵在于對罪錯未成年人進行“以教代罰”,呼吁在“一放了之”和“一罰了之”之間構建第三條道路即建立以保護處分為核心的獨立少年司法制度,形成少年司法與刑事司法二元結構體系。那么,請問您認為目前在我國建立獨立的少年司法制度所面臨的困難與障礙主要來自哪些方面?
姚:少年司法制度是社會發展的穩壓器,也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目前,我國已經初步探索了少年司法制度,但遠遠未建立完全獨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其中最為關鍵、需要突破的難題是制定一部系統性、綜合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少年法。該部法律的核心是未成年人罪錯行為的預防、干預和處置,旨在將其從成人刑事司法體系中完全分離出來,同時具有司法法的法律屬性。該法的主要特征表現為:一是不將未成年人犯罪看作是“罪”而是“錯”,并將“未成年人罪錯行為”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概念;二是強調“提前干預、以教代罰”,即構建完善的保護處分措施,以“行為人”而非“行為”為中心,著眼于改善、解決罪錯未成年人背后所涉及的成長環境和社會問題,幫助罪錯未成年人重新回歸社會,通過“辦理一案”進而“治理一片”。其次,建立完全獨立的少年司法制度還需要設置專門的少年司法機構。目前,從整體而言,由于我國缺乏少年司法專門立法,因此在對于獨立少年司法機制運行過程中各個環節不同職能部門的專門職責、部門間的互相協作以及所形成的工作合力、專門程序和人員等方面均缺乏頂層設計。從局部來看,我國未成年人審判組織的運行還有待完善,未成年人警務機構依然缺位,同時專門針對少年司法改革工作的評價考核體系也尚未形成。此外,我國保護處分體系還不健全。新修訂的《預防法》對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分級并不科學,也造成了保護處分措施體系性不足。針對此問題,我曾在《建議稿》中提出設置“教育處分、觀護處分、禁閉處分、教養處分”四種保護處分類型,較為全面地涵蓋了社區性保護處分、中間性保護處分以及拘禁性保護處分,以更好厘清保護處分與治安處罰和刑罰的關系,完善我國保護處分措施體系。可惜,立法機關并未完全接受。
柳:近來您承擔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未成年人司法先議權研究”,可以說此項研究在國內尚屬空白,請問您是否能和我們分享一下最新的研究成果?
姚:其實對于“先議權”的研究我已關注多年,只是近年來才將研究慢慢聚焦于該領域。其中一個主要背景是,我在關注《預防法》的修訂過程中,對于一些保護處分措施的設計提出了很大質疑。例如,專門矯治教育并未予以司法化改革,而是通過雙行政機關管轄模式的程序設計決定專門矯治教育措施的適用。很多人批評其未能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我認為這是站在成人法立場的判斷,有一定道理。但從少年法的視角看,我們沒能解決一個核心問題即各種保護處分措施的決定權應當歸屬于誰。根據《預防法》的規定,管理教育、矯治教育、專門教育的決定主體分別為學校、公安機關、教育行政部門。看似分工明確,但是一旦涉及具體個案,由于在對未成年人罪錯行為的干預過程中缺乏一個基于貫徹“以教代罰”的保護主義理念而對未成年人罪錯行為作出實質判斷并統一協調少年司法體系中各個機構合作運行的主責部門,難以形成少年司法的最佳合力,結果往往會造成“當一個孩子出現不良行為時,學校、教育行政機關、公安機關等責任主體所實施的教育、管理或矯治措施均未能產生良好的效果,直至進入刑事訴訟程序時,孩子已經生了‘重病’”的尷尬局面。于是,在此背景下,我們提出未成年人罪錯行為是否需要統一由專門的未成年人司法機構享有先議權(優先審查及實質決定的權力)這一涉及未成年人司法的根基性問題,以解決“養大了再打”“養肥了再殺”的“養豬困局”。
柳:我關注到您撰寫的童話《呼嚕嚕與獨角獸的幸福生活》于2021年再版,國內很少有法學家像您一樣愿意花費大力氣做普法類讀物,更何況還是面向孩子的,這令人十分欽佩。請問能否和我們分享一下您出版兒童法學科普讀物的初衷和關切?
姚:關于我出版兒童法學科普讀物的初衷和關切,我曾經在接受《上海法治報》采訪時進行過專門論述,這里再簡要闡釋一下。當時我兒子很小,晚上經常拉著我講童話故事。但在念書的過程中,我發現一些童話并不適合低年齡段的孩子。例如經典童話《小紅帽》中會描述“大灰狼被開膛破肚”的場景,而這樣的畫面對于年齡較小的孩子太過血腥。又如白雪公主吃下毒蘋果后經王子的親吻才得以蘇醒,但公主與王子第一次相見便親吻的行為從法律人的角度來看是十分不恰當的。于是,我開始為兒子編故事,后來陸續編了“獨角獸系列”“超級大卡車系列”“小南鼻冒險系列”“小魚飛噓系列”等許多童話故事,《呼嚕嚕與獨角獸的幸福生活》是形成文字的一個系列。
其實,在《呼嚕嚕與獨角獸的幸福生活》一書中,每一個故事、場景或是人物都能在生活中找出原型。可以說,這本法律童話帶有一定的“自傳性”。令我欣慰的是,這本書一度成為法律出版社的暢銷書,很多孩子對其愛不釋手。回首這本法律童話的寫作歷程,歷時一年之久,當時我暫停了手上幾乎所有科研工作,最終完成的這本書還不能算科研成果,這在他人看來無疑是一次“性價比”極低的嘗試。不過,我覺得很值得,而這也是我唯一會拿出來“吹牛”的書。
柳:多年來,您為我國未成年人法律體系的完善及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貢獻了諸多具有開創性的理論與實踐成果,且在研究過程中始終保持著謙遜嚴謹的治學態度與實事求是的學術作風。作為前輩,能否和年輕學者分享一下您多年來的治學心得和經驗?
姚:結合我自身的治學經驗與體會,我想向年輕學者分享以下幾點:第一,多努力,少抱怨。首先,在如今“內卷”嚴重的時代背景下,我非常能夠體諒當代學生抑或“青椒”的不易,也十分理解他們傾向去“躺平”“擺爛”的“反內卷”心態。但是,其實每個時代都一樣,不同的時代會面臨不同的壓力和困難。年輕人應該多努力、少抱怨,不要總是為自己的懶惰與平庸找借口。第二,做學問要專注、執著,不要斤斤計較。我常常與我的學生講“散墨原理”——一滴墨水滴落宣紙之上,墨水慢慢滲開,在邊緣逐漸模糊,直至紙墨渾然一體。也就是當你選擇了一件事就要努力把它做到極致,而后由專到博。同樣,人生決不能太精細、太功利,我認為這也是當代年輕人最缺乏的,當你選擇了一條道路,就只需要埋頭專注做好自己手中的事情,憑著一股“傻勁”甚至是“蠻勁”,機會自然會來到你的身邊,許多事情會水到渠成。第三,以寫促讀,即帶著問題去讀書、去思考。一直以來,我給自己的研究生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每月寫一萬字的論文,為什么會這樣要求呢?因為我們總是會發現,當完整閱讀一本書時,往往讀著后面忘了前面,知識也無法形成體系。然而如果就某一問題去寫作,在此過程中會翻閱許多書籍、參閱很多資料,寫到最后你會發現,自己不僅閱讀了很多書,同時對某一領域的某些問題也有了深入了解。當然,這也是我多年寫作的經驗和體會。第四,培養廣泛的學術興趣。首先我們需要明確自己的學術興趣,在此基礎上持續拓展自己的專業領域,不斷地為自己創造成就感。第五,鍛煉身體、規律作息,開發自身潛能。習近平總書記曾在接受采訪時提到,鍛煉身體是“磨刀不誤砍柴工”。健康的身體、良好的生活規律以及穩定的情緒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和保障,每天強化自己保持某一種生活規律,久而久之這種生活規律就會融入你的生活中,成為你的一種習慣。當然,在規律作息的同時,你的時間管理能力也會提升,從而逐漸做到“一心多用”。到那時你會真正意識到,“不努力一把,你永遠不知道自己的潛力有多大”。第六,學術要做在田野里和祖國大地之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把論文寫在田野大地上”。學術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書齋里,學者一定要關注實踐、與實踐融入一體,要在祖國大地上做學問。第七,要做有用的學問。我們所做的研究一定要能夠解決實際問題,并且要讓別人看得懂,即在學術語言規范的基礎上也要接地氣、讓人容易親近。第八,辯證看待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總免不了會面對他人的評判,我經常會以“鏡中自我理論”來回應這一問題。該理論認為,每個人對自我的認識其實都是在與他人的社會互動中形成的,他人就是一面“鏡子”,你可以從他人這面“鏡子”中了解自己。當然,“鏡子”雖然重要,但如何照、怎么看也很重要。換言之,“鏡中我”并非真的“我”,而是被原有“自我”解讀過的“我”。因此,我常勸誡我的學生不能生活在別人的期待和看法之中甚至過度地精神內耗,但也要多聽他人的意見提升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