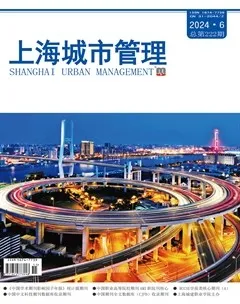功能區何以實現治理層次的躍遷
摘要:功能區已從城市規劃概念上升至服務國家部署的層面,實現了治理層次向上躍遷。作為常見治理工具的功能區何以保持長期活力、實現多元化發展,并逐漸具備戰略意義?基于“驅動—約束”框架,從整體層面審視功能區發展軌跡可知:功能區的演變由自上而下的目標引領和自下而上的需求反饋雙軌驅動,經價值定位、權力配置、空間屬性三重約束形塑,對應產生變動空間邊界、調整權力結構和優化管理模式等發展路徑。作為縱向政府談判而生的“中間板塊”,功能區的戰略型演變是權力部門進一步優化賦權增能方式的體現。從各自為政到戰略性協同,功能區要在全國一盤棋式統籌中兼顧治理靈活性,達成空間功能適配國家布局的發展主旨。
關鍵詞:功能區;治理單元;“驅動—約束”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4.06.006
功能區一詞的起源可追溯至《雅典憲章》中提出的為土地劃分用途的“功能主義”思想。[1]國內外城市規劃與建設都遵循著按照不同功能分區展開的基本理念。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治理使用功能區的范圍得到拓展。以1980年設立深圳特區為發端,中國涌現出一大批跨尺度的功能區。功能區開始從規劃學領域的一項專業術語,演變為政策新區的代名詞,并持續服務于改革開放大局。伴隨著我國改革進程的深入與空間策略的漸進調整,各類政策新區的屬性同樣經歷了“梯度發展”的過程。[2]功能區從原本僅用于推動經濟增長的單一領域治理手段,轉變為承載諸多重大發展使命的戰略型手段。星羅棋布的功能區蘊含著多元化的功能,從各自為政向區域協調,乃至全國一盤棋的戰略協同方向發展。時至今日,功能區的覆蓋范圍越發廣泛,實踐形態也越發豐富,在運作中表現為經濟特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國家級新區、先行示范區等多種類型。
一、問題的提出
從政策新區的意義上講,中國最先使用且使用最廣泛的功能區是經濟功能區,隨后根據治理需要拓展到其他領域。在持續的空間政策和相關的政策效應共同作用下,功能區呈現出多元性、選擇性和層次性特征。[3]各級政府通過放權賦能設立的功能區,逐漸成為推動經濟增長、[4]進行體制機制創新試驗、[5]打造示范樣板的重要手段。[6]功能區承擔起超越增長型任務的發展目標,意味著其內涵從刺激經濟的單一價值向承擔各類戰略使命的綜合價值演變。自此,蓬勃發展的功能區對行政區搭建的四梁八柱型治理架構形成了有效補充。
行政權力的引導貫穿功能區發展始終。為此,實務界認為,在權力部門的引領下“常變常新”是功能區治理手段取得豐碩成效的關鍵。然而“常變常新”是一個模糊化、頗具主觀性的要求,那么該如何從學理層面解釋?理論界系統探討了各類功能區的治理實踐,關注影響某類或具體功能區設立、發展的各種因素。其研究內容豐富、領域寬泛,為進一步理解功能區的演進提供了基礎,但少有學者立足宏、中觀層面提煉各類功能區發展背后的共性內容。既有研究只能解釋特定功能區具備何種設立價值以及如何維持自身活力,卻無法回答功能區為何能在發展中實現作用功能的拓展和治理層次的提升,并逐步走向戰略協同。
四十余年的治理實踐表明,功能區的發展包含解決自身面臨問題、承載價值使命持續疊加、在整體層面趨于有序演進三重內涵。既有研究只關注其中的經驗事實,理論貢獻較為有限,更未能從整體層面對功能區的歷史演變進行系統性回看,無法就功能區何以實現治理層次的提升這一核心命題做出有效回應。為探討功能區從一項單一領域的基礎性治理手段向綜合領域的戰略型治理手段轉型背后的作用機制,并就此提出一個具有一定普遍指導意義的分析框架。本文試圖通過對功能區發展驅動力與約束性因素的探討,勾勒功能區既有活動圖譜,歸納未來走向,解構其價值機理的擴充,并進行學理層面的提升。
二、文獻述評和研究框架
(一)文獻述評
功能區是權力部門將“空間中的生產”轉向“生產空間”的表現,[7]是權力重構空間的產物。功能區的空間屬性構成既有研究的出發點,權力創設本質則已成為理論界的共識。[8]當前對功能區發展在整體層面的研究并不多見,研究者主要圍繞功能區性質、種類展開探討。從研究內容和進路看,對功能區發展的研究可歸為兩類。
一是關注功能區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功能,尤其是發展中的功能區的新形態、新動向的戰略價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功能區的治理層次、覆蓋領域不斷豐富,多區疊合現象日漸普遍。[9]理論界集中分析了國家級新區、[10]示范區、[11]全域功能區等帶有綜合性質的新型功能區在國家治理中的特殊權力結構和獨特治理意涵。[12]大量研究還依據功能區外延和內涵的持續拓展,從體制機制創新、法治保障、[13]政策投入等維度解釋了功能區演變的基本緣由。[14]
二是在高質量發展主題下,采取“問題—對策”思路,分析如何解決特定功能區的發展困境,推動功能區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實現新突破。相關研究論證了功能區如何通過調整產業結構、改革管理體制等方式提升影響力,[15]如何規避與行政區的摩擦等。[16]相應對策集中于進一步完善功能區評價體系、加強考核監督、創新管理模式等方式提升功能區質量,優化發展路徑。[17]這些研究主要立足于功能區所處地域的區位因素、資源容量、權力配置狀況等客觀條件限制,[18]探討如何推動功能區與自身發展命題相匹配。
在“工具主義”取向下,理論界對功能區的既有發展軌跡和未來演進走向展開了全面探討,這些研究已深入到每一類功能區的任一發展環節。從總體上看,這類研究雖然能夠捕捉特定功能區的治理地位和戰略價值,但碎片化特征明顯。聚焦式研究更切中功能區具體發展需要,卻常面臨“精度有余、高度不夠”問題,缺乏對功能區整體演進規律的發掘,更沒有關注到其背后的作用機制。相關觀點難以串聯成片,既有結論容易顧此失彼,甚至會出現矛盾現象,看待功能區發展的視角需要進一步拓寬。
(二)整體層面的“驅動—約束”框架
國家治理要樹立大局觀和整體觀。權力在重塑、劃分空間后,還必須在全局層面整合空間功能。即使關注微觀層面功能區演變的研究,也有必要樹立整體意識。這是確保各類功能區發揮自身積極性的同時,還能凝聚成彼此配合的戰略手段,共同服務于國家部署的關鍵。
梳理總結相關文獻可知,理論界對功能區發展問題的探討,雖然在切入點和側重點上有所差異,但均涉及“驅動”和“約束”兩個共性因素。前者是推進功能區發展的內外生動力;后者負責規制、限定,防止出現功能區發展偏離預設目標的情形。作為縱向政府間博弈的結果,功能區的發展由自上而下的目標引領和自下而上的需求反饋雙軌驅動。進入新時代以來,高質量發展要求對功能區提出了更為嚴格的約束性條件。功能區需嚴格遵循國土空間規劃所規定的空間基礎屬性,根據自身權力配置發揮先行者價值。
理論上功能區屬于“約束性條件在前,方向性驅動在后”的演進模式,但實踐中功能區都是在摸索中發展的。早期功能區的發展基本呈現出發展導向,尤其表現為經濟功能區以增長為導向,而約束相對缺失的問題,中國功能區的發展事實上遵循著“先生長,再規制”的一般性規律。基于此,本研究構建“驅動—約束”框架,嘗試從整體層面解析功能區演進背后的依據,并展望未來走向。文章結構安排如下:一是從功能區設立、發展的驅動維度入手,分析功能區發展的動因;二是立足功能區的約束性要件,從設立價值、權力結構、空間屬性三個維度出發,尋找功能區變革的限制條件;三是解析功能區出現當前變革形態的緣由,并作出展望。
三、雙軌驅動:“目標—需求”導向指引功能區發展
功能區是縱向政府間博弈的產物,尤其是承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功能區,一般都由中央設立,代表促進頂層設計與地方落實相結合的一種創新舉措。功能區在運行中要遵循自上而下的目標引領和自下而上的需求反饋。在這“雙軌導向”中,頂層設計為功能區提供引領性目標,是發展的指揮棒;而滿足差異化發展需求的底層反饋,則是功能區長盛不衰的助推器。目標和需求導向疊加形成雙重驅動,共同演化出種類繁多的功能區,最終實現功能區治理層次的提升。
(一)自上而下的目標引領
引領功能區發展的目標導向可分為單兵突進型和綜合試點型兩類。前者通過聚焦層級政府注意力,將有限資源集中于亟須解決的問題上,推動重點領域獲得優先發展。后者傾向于通過設立承擔綜合改革使命的功能區,實現高質量和協調發展。單兵突進的目標導向對應著特殊政策支持下握有特殊發展權,負責局部突破的功能區;綜合試點的目標導向設立的功能區是立足地方特色展開的政策試驗,力求得出可復制、可推廣的創新經驗。在單兵突進彌補治理體系短板的基礎上,綜合試點用于實現經驗推廣后的全局推進,二者是從局部到整體的關系。
1.單兵突進的目標導向
單兵突進的目標導向是黨和政府為突破傳統體制機制束縛,在落后治理領域集中推進的常見手段,可以理解為舉國體制在特定情境下的牛刀小試。受長期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基本路線的影響,單兵突進的治理目標主要催生了經濟功能區,中國最早設立的功能區就是經濟特區。在經濟社會相對落后的背景下,黨和政府不遺余力地支持經濟特區,通過開放權限、賦予優惠政策等方式鼓勵其先行先試,以保證先發優勢。例如,深圳特區成立初期,鄧小平就提出:“給你們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深圳在全國率先開展經濟政治體制改革,通過開放特定區域,批準開放口岸,試水金融業開放等方式,打開了對外開放的窗口。[19]
在經濟領域設立單兵突進型功能區,推動中國形成了以特區為起點的非均衡發展路徑。“特區模式”獲得極大成功,[20]帶動權力部門進一步設立了經濟開發區、自由貿易試驗區、保稅區等多種經濟功能區,這些功能區成為中國經濟騰飛的重要驅動力。黨和政府在經濟領域設立戰略功能區,順應要素流動的一般規律,突破了行政區的空間約束;更重要的是,通過疊加優惠政策打造政策洼地,實現了窗口式發展。秉持單兵突進目標導向的經濟功能區充分利用政策紅利,成為刺激經濟增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手段。
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看,單兵突進目標導向下設立的經濟功能區又可細分為增長導向和改革導向兩類,或用于直接推進增長目標,或用于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這兩類功能區共同作用,成為當時發展水平較低、各項制度體系尚不健全的中國實現趕超式現代化的前提。隨著治理重心的轉移,當前單兵突進型功能區已從經濟增長拓展到生態環保等諸多新領域,直接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
2.綜合試點的目標導向
相較單兵突進型功能區的突破性,綜合試點目標所設立的功能區更重試驗性與推廣性。改革開放早期的經濟功能區屬于低市場化、低開放度“雙低時代”的過渡品。[21]隨著改革向深層推進,各領域的聯動性持續增強,各類矛盾交織出現,單兵突進型功能區逐漸難以回避來自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等維度的復雜問題。同時,改革也不可能再以經濟為“單軸”推進,黨和政府必須根據發展需要、民生訴求進行結構性調整,這一調整將首先以功能區為試驗田展開。
一方面,為解決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深層問題,在政策高地之外追求全面發展和系統改革的重要性越發突出;[22]另一方面,改革必須把有效治理、風險規避和成本控制結合起來,穩步推進。[23]根據各地特色,設立肩負綜合使命的功能區進行普遍試點成為必然。帶有“獨角戲”意味的功能區內部改革不會影響其他地區,避免了在全國范圍推行未經論證的改革后,一旦失敗可能付出的沉重代價。在試點范圍內不斷調適,總結出可推廣經驗后再輻射全國,符合中國穩健發展的基本要求。以綜合試點型功能區帶動全局改革的深化,實現“小齒輪”對“大體制”的撬動,體現分散燒鍋爐的政治智慧。[24]綜合試點型功能區覆蓋多維度、多層面,呈現“多點開花”格局,助力改革成果的全面豐收。
綜合試點型功能區是對單兵突進型功能區的遞進補充,國家級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相應的,在綜合試點目標導向下,我國功能區的內涵也實現了從單一功能向綜合功能的發展,推動改革從重點突破向兼顧整體創新的發展。單兵突進和綜合試點兩類目標的使用情境不同,但二者并無優劣之分,更不是取代關系。不同目標導向下產生的功能區相互疊加、各盡其責,構成功能區的發展圖景。
(二)自下而上的需求反饋
從基本治理手段到戰略性手段,功能區的演進是“摸著石頭過河”的體現,側面反映出功能區在發展過程中并沒有成熟可借鑒的經驗。目標導向為功能區預設了發展方向,而根據現實需求適時調整,是推進功能區平穩發展的有力保障。需求導向下功能區的發展包括改革內部管理體制、控制質量和協同發展三個維度。
1.管理體制改革需求
改革管理體制需求是伴隨功能區發展出現的過程性需求。很多功能區設立初期采用的管理體制不夠成熟,需經實踐檢視后逐步更迭。作為先行先試典范的功能區不存在統一管理體制,而自身權力對行政權力的依附性,又使其容易出現權力難以理順、管理不夠規范、法律地位尷尬等問題。功能區適用何種管理體制要依靠地方自我調適,通過逐步改革達成現實條件與管理體制相匹配。
部分在發展中逐漸“膨脹”的功能區,在不同階段適用不同管理體制,突出體現的是經濟功能區和一些帶有綜合發展任務的功能區。這類功能區每一階段的發展主題不同,治理任務的差異性決定了管理體制的動態性。在發展早期,功能區人口不多、產業也不密集,因此匹配了較為輕便的管理體制。隨著功能區發育成熟,自身變成具有復合功能的綜合性區域。既有管理體制會因授權不夠、不堪重負等問題產生革新管理體制的需求,[25]要求整合過渡性管理體制與層級制政府體系。[26]功能區是在原有的特定功能外,繼續承擔起新的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一般職能?抑或是緊急減負,以保持輕便優勢?總之,這些功能區都需要變革原有管理體制。
2.質量控制需求
控制質量是推動功能區提升競爭力、保持活力的基本要求。功能區是縱向政府“共意”產生的政策空間,[27]部分地方為謀求更多上級授權,常出現濫設、亂擴功能區的現象。一些缺乏合理論證的功能區淪為地方要優惠、套補貼的手段,不僅在目標定位、產業結構上存在嚴重的同質問題,還會阻礙資源整合,成為一種內耗。以經濟開發區為例,從1984年至2003年短短的二十年間,我國各級經濟開發區從14個激增至6866個。經濟開發區野蠻生長的背后是地方政府間的惡性競爭和企業的投機性遷移。為了招商引資,地方政府不惜為功能區賦予超出自身承受力的“自殺性”優惠政策,一再降低土地價格、水電資源費用和其他標準,造成嚴重資源浪費。一些企業為逐利在相鄰園區持續遷移,同樣嚴重違背功能區設立初衷。
控制功能區質量的關鍵是為之制定合適的質量標準,并清理不合格功能區。我國正逐漸完善由對口部委領銜、地方政府負責的功能區考核方法。功能區考核要“賞罰分明”,甚至要做到“優勝劣汰”。截至當前,我國已連續三次清理不合格、不合法的經濟開發區。[28]控制功能區質量的核心不在于減量,而在于為功能區施加發展壓力,進一步追求質量。剔除不合格功能區不是壓制各地新設功能區的積極性,而在于要求各級政府新設、變動功能區要在謹慎考慮和系統規劃后展開,以充分發揮每一類功能區的治理功效。
3.協同發展需求
協同發展是功能區在任何階段都需要重視的需求邏輯。功能區協同發展有兩方面內涵:
一是功能區與行政區保持協同。設立功能區會分走行政區部分權力,部分行政區不滿這種“奪食”,矛盾由此而生。功能區是疊加在行政區上的,還會出現跨行政區現象。受管轄界限存在交叉的影響,功能區和行政區在一些職能上常存在機構重復、權責不清現象,治權重疊、職責同構會引發管理沖突。功能區的發展涉及縱向政府間博弈,管委會與行政區政府沒有管轄關系,功能區一般還具備高配權限,兩方逐利爭奪、扯皮推諉屢見不鮮。即使學界始終強調功能區與行政區空間上的互補,職能上的分工合作是主要的,[16]但隨著功能區逐漸具備戰略意義,行政區的削弱不可避免,[29]協同發展的意義越發突出。
二是功能區之間以及功能區與國家重大部署之間的協同。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為實現各種重大布局設立了諸多功能區,但幾十年的發展中,功能區各自為政的現象突出,這變相削弱了功能區的整體競爭力。功能區具有靈活性,但靈活不代表隨意,各級政府要在科學考察、嚴密論證的基礎上審批、設立功能區。功能區的設立和發展要追求全國一盤棋的運作,要考慮到區域協同、全國協同、與國家重大部署相協調,這是充分發揮功能區競爭優勢,推動功能區從治國的基礎手段向戰略手段轉型的必然要求。
四、多重約束:功能區的先行者定位、權力配置與空間屬性
隨著各類治理體系的完善和高質量發展要求的提升,功能區的發展不僅要依靠“目標—需求”導向驅動,還越發受到多重限制性條件約束。功能區發展中面臨的約束一般表現為三個維度:先行者的價值定位約束是基礎,功能區必須以創新性與引領性作為存在前提;權力配置的結構性約束是本質,決定功能區的自主程度,也影響著功能區管理體制的形態;空間屬性的稟賦約束是核心,確立功能區的核心功能和空間開發強度。
(一)先行者的價值性約束
覆蓋不同治理領域、擁有差異化核心功能的功能區,是中國改革開放和體制機制創新試驗的先鋒隊。但無論是身處政策高地,能夠匯集優惠政策實現局部突破;抑或是負責綜合改革,力求通過圈地試點獲得全方位推進,所有功能區的基礎價值都在于其先行者身份。功能區在使用中常出現的新設、撤銷、優化管理體制和變動空間范圍等操作,源于自身靈活性優勢。但從本質上講,諸多發展變動始終受到先行者的價值定位約束。能否保持這一特征,甚至決定功能區的“存亡”。在國家治理中充分發揮先行優勢、積極完成所承擔使命的功能區會得到權力部門重視,進而被推動發揮更大作用;反之則會被邊緣化,甚至面臨取締風險。
功能區先行者的價值定位可分為“示范先行”和“一般先行”兩類。“示范先行”側重示范性,要求通過打造治理樣板,為其他地區提供標桿。部分擁有示范定位的功能區直接為貫徹某一理念而生。例如,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生態文明示范區等,都代表國家層面的部署方向和發展理念,相應功能區的發展不能偏離這些預定價值的約束。示范價值并不局限于單一功能,也存在追求綜合示范的功能區。例如,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上海浦東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以及各個具有引領性、負責推動區域協調的國家級新區,都身受綜合示范的價值定位約束。上級對特定功能區賦予示范定位,是肯定其發展成績的表現。這也有助于調動地方積極性,刺激其他功能區向“榜樣”看齊。
功能區的“一般先行”價值要求作為試點的功能區得出可推廣經驗。黨和政府早期設立功能區的目標是集中優勢資源取得點狀突破,但隨著改革向縱深發展,集聚政策優勢的功能區向普通試點轉變成為必然。試驗只有在同樣政策環境下展開,才能保證改革成果與一般地區的適配度。一般試點身份的功能區往往不擁有政策優惠,上級僅會賦予其先行先試權。這類功能區在一般試點的價值約束下不再是政策高地,只作為特定問題上具備典型性的一般政策區域。例如,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按照四大板塊戰略,兼顧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地區的改革需求,在試點內容上涵蓋我國改革發展需要解決的體制性重點難點問題。[30]每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都面臨著典型性任務和一般性政策相結合的背景。
(二)權力配置的結構性約束
作為縱向政府談判的“中間板塊”,功能區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控制性賦權基礎上。功能區突破了常見的條塊關系,通過打破行政壁壘,重塑事權配置構造出“條—塊—塊”的混合治理架構。[31]高位政府根據功能區的性質不同,在不同時機、環境決定對功能區授權的內容、程度和方式,進而形成新的權力關系,塑造出差異化的功能區管理模式。
功能區權力配置產生的結構性約束可歸為權力重塑型與疊加型兩類。大部分功能區都由高級別政府指定,通過權力重塑承擔特定使命。這種權力的大小并非固定,其容量由高位政府釋放的權力量決定。上級政府重塑空間意味著對特定治理功能的重視,一般功能區都能獲得上級讓渡的更多權力。權力配置的高度、廣度代表功能區“放開手干”的程度,決定了功能區自主性的范圍、深度及效果。[32]例如,自2007年上海發布《關于完善市區兩級管理體制,賦予浦東新區更大發展自主權的意見》,明文指出“凡法律沒有限制的、屬于本市的權限,原則上下放給浦東新區政府”后,[33]浦東新區闊步改革,獲得了快速發展。
隨著功能區設立邏輯復雜化,在既有功能區上疊加新的職能權力,由多元“條條”插入功能區“塊塊”,可以“增生”承載更精細化目標的新功能區。這種功能區權力結構更加簡單,無法獨立承擔發展使命,要依附原有功能區發揮作用。例如,國家級高新區是通過實施高新技術產業的優惠政策和各項改革措施,最大限度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區域。[34]而隨著為高新區注入示范引領功能,中央又設立了國家級自主創新示范區。在管理上,國家級自主創新示范區僅擁有國家層面的部際領導小組和個體層面的市級領導小組,其日常履職仍然要依賴高新區管委會。
歷經四十余年的發展,功能區已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但部分功能區的發展中尚未形成頂層設計和基層先行先試創新的良性互動。[35]功能區的發展必須立足自身權力配置展開,進一步厘清與行政區的權力關系,徹底解決權能模糊、權能失衡等問題。這是功能區在承擔戰略使命的過程中,獲得應有權限配置,達成與行政區的互嵌式協同。[36]
(三)空間屬性的稟賦約束
功能區是在特定空間內展開的治理活動,其所有發展都必須考慮到所處空間的地理位置、發展潛力等客觀條件。權力機構為功能區預設的核心功能必須與區域發展定位、空間功能結構和開發政策的強度限制保持高度一致。[37]國土空間規劃是我國的空間總體規劃,確立了全部國土的空間屬性。功能區的核心功能必須在國土空間規劃體系所設定的空間屬性約束下,根據自然稟賦,滿足“宜工則工,宜農則農,宜開發則開發,宜保護則保護”的基本要求。[38]
主體功能區規劃是國土空間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注不同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主體功能區規劃為權力生產空間提供了稟賦約束,按照開發強度和開發內容將國土劃分為不同類型地區,[39]功能區的一切發展都必須按照主體功能區規劃及其配套政策的約束展開。在運行中,主體功能區戰略逐漸形成了覆蓋全局的法律法規、體制機制、規劃政策,[40]有針對性地確立了區域政策和績效考核評價體系,推動了空間管理的精準化。這也為功能區的設立、發展找準了方向,避免了權力對空間的濫用。
新時代以來,中國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視程度顯著提高,當前空間屬性對功能區的稟賦約束也集中體現在如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格局上。[41]主體功能區戰略為功能區在內的一切空間發展確立起最基礎的發展安全保障線、生存安全保障線和生態安全保障線,以限制性身份促進功能區合理發展。兩種稟賦約束不僅體現為限制功能區的開發強度,也會直接催生相關功能區。自2013年以來,為建立資源循環利用體系,中國根據主體功能區定位的開發格局設立了大量生態文明示范區,[42]已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生態文明建設模式。
五、對功能區主要發展路徑的理論解析
功能區的設立和發展是在“目標—需求”的雙軌驅動下,根據功能區承擔的價值使命、權力配置和空間屬性展開的。差異化的驅動邏輯和約束性要素決定了各類功能區的發展路徑,這些發展路徑主要包括變動空間邊界、調整權力結構和優化管理模式三類。
(一)變動空間邊界
通過變動空間邊界進行自我優化是功能區發展的最常見路徑。綜合試點型功能區承擔試驗任務,要將改革內容嚴控在特定范圍內,防止風險外溢。因此,空間邊界變動多發生于單兵突進型功能區。從需求導向看,功能區空間邊界的變動與功能區控制質量、追求協同發展密切相關。空間變動對功能區定位并無限制,但處于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的功能區變動空間范圍的可能性更大,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區的功能區邊界相對固定。在縱向博弈中,地方政府一直擁有擴權欲望,除非遭遇裁撤,否則很難主動上交“分得的蛋糕”,功能區空間邊界的變動一般也表現為擴容而非縮小。示范區主要用于高質量發展的探索,變動空間邊界的可能性小,難度也較高;一般試點區更傾向于將改革成效盡快推廣,變動可能性更大。功能區擴容意味著管轄范圍增加,必然要以高位政府對既有發展成果的認可為前提。功能區擴容主要體現為功能區直接向周邊擴張、功能區通過空間跳躍向外設立飛地兩類。
1.直接向周邊擴張
功能區直接擴容可以將自身優惠政策、先發經驗擴散到周邊地區,這是功能區疏解功能、帶動區域發展的重要手段。功能區空間邊界的變動最常見于經濟開發區,隨著經濟增長,產業聚集,功能區輻射范圍逐漸增加,變動空間的可能性也更大。例如,北京經濟開發區至今經歷了三輪擴張,從3.8平方公里擴展到225平方公里的規劃面積。[43]在“好成績”的支撐下,開發區建設持續加快,上級政府一度主動推動了功能區擴容。
一方面,向周邊擴容解決了功能區面臨的臃腫化問題。北京經濟開發區在擴容中形成了核心區、配套區、多組團相協調的發展格局,這對保持核心功能、維持治理優勢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功能區擴容是將發展優勢向周邊輻射的體現,原本3.8平方公里的“小齒輪”帶動了如今200多平方公里區域的快速發展。
2.在外設立飛地
設立飛地是跨區域合作的一種創新模式,可以實現飛入地與飛出地在產業、資源等方面的有效互補。功能區向外設立飛地實現空間跳躍,是一種較特殊的擴容方式。這種擴容分為兩類:一是功能區為實現自身優勢的跨地域輻射,在土地、建設成本較低的地區設立飛地,實現產業、政策的復制移植。例如,深圳特區在汕尾設立“深汕合作區”。遷入合作區的企業繼續享有深圳特區的各類優惠,合作區黨工委和管委會由深圳市委、市政府派出,[44]這有力推動了汕尾發展。
二是新生功能區為更好地承擔使命,在發達地區設立飛地,向更具優勢的地方學習。例如,為深入實施“科創興城”戰略,浙江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在上海浦東新區租賃場地,設立蕭山經開區上海創新中心。該中心譜寫了“研發、創新在上海,生產制造在本地”的區域合作新樣本。科創飛地借助上海作為中國科技創新前沿的重要地位,以“借船出海”的方式鏈接了優勢地區的稀缺資源。
(二)調整權力結構
功能區權力結構的變動普遍發生于每一類功能區當中,根據不同驅動和約束產生差異化表現。權力結構的變化主要由治理實踐產生的需求導向,自下而上反饋到高位政府,引發功能區權力配置、權力關系的變化,最終表現為功能區管理體制的調整。
1.體制合一
功能區與行政區體制合一是指為推動功能區更好地承擔使命,解決功能區發展的系列問題,將功能區原有管理體制與當地行政區政府合并設立的變革。這種權力結構的調整通常發生在“易膨脹”的經濟功能區或綜合試點型功能區,對應著產業發展、社會事務日益繁重后,功能區面臨的體制改革需求驅動。在約束性要素上,體制合一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探索,需要高位政府的首肯。在行政區上疊加功能區,可以借助高位政府勢能,凝聚當地資源,避免行政區與功能區體制沖突,調動“兩個積極性”。
體制合一的副產物是功能區和行政區的重疊,原本占據行政區一隅的功能區會擴容到行政區全域,這能有效解決發展臃腫問題。功能區與行政區體制合一并不是改革走回頭路,而是針對實際需求的應勢變革。體制合一也不意味著行政區取代功能區,一般會兼取二者優勢,形成一種介于傳統行政區和功能區管理體制中間形態的特殊模式。例如,青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在與黃島區體制合一后,面積得到極大擴展,發展空間不足問題得以緩解。體制合一后的行政區兼具了功能區的治理內涵,也延續了“小政府大社會,小機關大服務”的機構設立原則。目前青島經濟開發區的機構設置依然較為精簡,管委會(區政府)下屬機構20個,對應著青島市32個政府序列部門。[45]
2.功能區統攝行政區
功能區統攝行政區是指某功能區在發展中居于主導地位,由承載戰略使命的大功能區協調小功能區和行政區發展的現象。功能區統攝行政區的演變同樣發生于承擔綜合試點任務的功能區內,其核心需求是實現區域協同。就約束性要素來看,負責統攝行政區的“超級功能區”必須立足所處區域空間性質展開。功能區統攝行政區意味著高級別政府在設立功能區時,顛倒了行政區與功能區之間在行政體系中的一貫位置。為確保功能區有效達成治理目標,高級別政府必須為該功能區給予高配權限和足夠的資源支撐。能夠統攝行政區和小功能區的“超級功能區”承擔的必然不是一般試點任務,而是發揮著立足地方發展需要,引領示范區域發展等具備戰略意義的作用功能。
功能區統攝行政區的典型案例是國家級新區。國家級新區體量龐大,肩負著國家重大戰略使命,并要求立足特定使命推進區域協同發展。國家級新區打通了既有功能區與行政區的界限,呈現出“多區疊合”的特征。例如,重慶兩江新區內部不僅包括兩路寸灘保稅港區、兩江新區工業開發區等功能區,還包括江北區、渝北區、北碚區等行政區。國家級新區通過特殊政策的集中賦予與治理權限的“高配”等權力重塑手段,為解決既有治理難題提供了新平臺。
3.去行政化改革
秉持單兵突進目標的功能區在設立初期,一般會采取輕裝簡行的管委會體制,以擺脫行政區冗雜、繁瑣的治理手段和審批事項。當這類功能區逐漸發育成熟,尤其是所處地域從簡單的園區發展成為新城區后,其治理過程會不可避免地增加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職能。功能區管委會在“膨脹”中不堪重負,逐漸淪為地方政府的“行政替身”,喪失其原本進行體制創新的功能。為保持突破性治理的優勢,部分功能區有必要進行去行政化改革。去行政化改革基本都發生在優化開發或重點開發等城市化建設已取得一定進展的區域,最常見的依然是經濟功能區。功能區去行政化改革需要上級政府大力支持,也需要當地政府重新接管功能區的部分事宜。只要管理事務日漸冗雜,功能區就需“刪繁就簡”。
不同于初設之際功能區只需要考慮如何完成單兵突進目標,當前功能區去行政化改革,還需注重滿足發展帶來的復雜治理需求。功能區去行政化有多種手段,如設立法定機構、采取“管委會+聯席會議”“領導小組+管委會”等體制,這些都有助于保持功能區運行機制上的公開性和組織架構上的非行政性。[46]例如,深圳于2011年1月成立前海管理局作為法定機構,該機構在經濟、金融等核心功能領域享有副省級城市管理權限,而類似于治安、環保等其他社會管理職能則依然由深圳市負責。
(三)優化管理模式
權力部門持續優化功能區管理模式并完善考核評價體系,是促進功能區從一種治理現象發展為戰略性治理手段的重要保障。功能區的評價考核工作主要由對口部委負責,在運作中表現為自上而下的“發包—執行—考核”一般流程。為防止部分地區出現只重視短期“拿帽子”“充政績”,不重視功能區長期發展的問題,各部委應立足自身職能專長,逐漸構建起系列覆蓋功能區發展全階段的考核指標和評價體系。隨著功能區在國家治理中重要性的提升,進一步規范化、科學化、嚴格化考核體系將是必然趨勢。
以國家經濟技術開發區為例,其設立初衷是為了解決我國審批手續復雜,機構疊床架屋等制約經濟發展的問題,經過數十年發展,經濟技術開發區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排頭兵。為防止經濟技術開發區出現質量下降問題,從2016年開始,國務院、商務部出臺了系列考核評價辦法,并持續進行更新。權力部門通過激勵創新、倒逼發展、分地區排名等方式,形成了一套科學合理、有進有退的動態管理模式。
在控制質量的需求導向下,國家部委針對特定功能區的各類考核越發常見。例如,生態環境部為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范區印發管理規程及相應指標;科學技術部針對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和國家級高新區出臺考核要點等。在國家級新區等其他重要的功能區,雖然暫不存在退出機制,但相關部委也在為優化管理而持續努力。國家部委對功能區管理考核的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嚴格,是維持功能區發展活力、助推功能區承擔使命的能力逐漸強化的重要保障。
六、結論與討論
區別于一般政策手段的漸進式發展,功能區在演進中不僅解決了自身發展問題,還實現了治理層次的向上躍遷。作為高位政府打破既有權力結構,靈活調整權責配置、集中治理資源的一種有益探索,功能區轉向承擔戰略性使命,實則是將這種探索推向了新的高度。種類繁多的功能區展現出的差異化發展路徑看似雜亂,但探尋其整體發展可知,多樣化演進路徑的背后依然有跡可循。本研究的理論特色在于,通過闡釋功能區整體發展的關鍵性要素,提煉出“驅動—約束”包容性框架。這一框架不僅可以理清功能區既有演化脈絡,亦可用于預測未來功能區走向,從而推動理論界和實務界對功能區發展中一些必要點、薄弱點的關注。
從發展的視角看,功能區演進也是黨和政府在改革深水區持續攻堅的寫照。面對改革中的“硬骨頭”,新時代功能區必將承載更復雜、更深刻的治理使命,其蘊含內容也將更加豐富。這一現實映射于治理實踐,則意味著已然縱橫交錯的功能區會在行政區治理單元的基礎上進一步疊加,形成更加細密的治理網絡。因此,在繁復的發展軌跡中理順功能區的發展邏輯尤為重要。功能區如何在權力重構中充分發揮其功能,這不僅關系到功能區自身的發展,也與功能區與行政區、功能區與國家戰略的協同息息相關。探討功能區如何實現治理層次的躍遷,不僅在于解析以往,更在于推動每個功能區在國家戰略體系布局中找準定位。
說明:本文系高等學校中央基本科研業務費(63242129)部分成果。
參考文獻:
張京祥.西方城市規劃思想史綱[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5.
于棋,毛啟元.我國城市戰略功能區的建構策略與尺度邏輯[J].東岳論叢,2021(5):97-105.
Neil B.New state spaces: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rescaling of statehood[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劉君德.中國轉型期“行政區經濟”現象透視——兼論中國特色人文—經濟地理學的發展[J].經濟地理,2006(6):897-901.
蔡玉勝.經濟功能區社會管理創新的探索[J].理論探索,2011(3):84-87+99.
郁建興,黃飚,江亞洲.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的目標定位與路徑選擇——基于浙江省11市《實施方案》的文本研究[J].治理研究,2022(4):4-17+123.
亨利·列斐伏爾.空間與政治[M].李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趙吉.權力創設空間:我國戰略功能區發展的政治邏輯[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6):48-54+72.
王興平,韓靜.國家級新區內“多區疊合”現象及其效應分析[J].城市發展研究,2022(6):43-52.
吳曉林.模糊行政:國家級新區管理體制的一種解釋[J].公共管理學報,2017(4):16-26+63+153-154.
林仁鎮,文宏.目標設定、資源整合與中國特色政策試點機制——基于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分析[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4):129-140.
汪云,鄭金,夏巍,等.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下市級全域功能區體系研究——以武漢市為例[J].規劃師,2022(6):101-108.
徐燕飛,秦鵬.國家級新區賦權增能的理論邏輯、實踐樣態與規范進路[J].中國行政管理,2023(2):12-21.
汪濤,李祎,汪樟發.國家高新區政策的歷史演進及協調狀況研究[J].科研管理,2011(6):108-115.
馮烽.國家級新區高質量發展面臨的困境與對策[J].當代經濟管理,2021(11):65-72.
陳浩,張京祥.功能區與行政區“雙軌制”:城市政府空間管理與創新——以南京市區為例[J].經濟地理,2017(10):59-67.
杜春麗,杜子杰.高質量發展視域下省級經開區評價體系探析[J].學習與實踐,2019(7):51-57.
羅清和,曾婧.關于經濟特區模式若干問題的思考[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1):94-99.
孫長學.深圳經濟特區的體制改革探索及其示范價值[J].改革,2018(5):18-26.
袁易明.中國經濟特區建立與發展的三大制度貢獻[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4):31-36.
胡彬.開發區管理體制的過渡性與變革問題研究——以管委會模式為例[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4(4):72-80.
陳振明,李德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實踐探索與發展趨勢[J].中國行政管理2008(11):78.
姚尚建,劉銘秋.從政策試點到制度示范——發展型國家的治理轉向[J].學術界,2020(8):25-32.
曹正漢.中國上下分治的治理體制及其穩定機制[J].社會學研究,2011(1):1-40+243.
倪星,梁劍輝.中國經濟功能區在走向體制復歸嗎——基于發展型國家和城鎮化兩種視角的分析[J].學術研究,2019(8):42-48+177.
高恩新.事權分化、尺度重構與權威嵌入:開發區管理體制變遷的三重邏輯[J].行政論壇,2021(3):51-58.
高恩新,李佳麗.張力治理:特殊經濟功能區空間治理的一個闡釋性概念——基于4個國家級經濟開發區的分析[J].復旦城市治理評論,2022(2):28-56.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清理整頓各類開發區加強建設用地管理的通知[EB/OL].(2003-07-30)[2024-07-15].https://code.fabao365.com/law_23104.html.
楊龍,王朦.經濟功能區的體制困境與轉型模式選擇[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4(5):89-9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12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重點改革任務發布[EB/OL].(2019-05-11)[2024-09-13].https://www.gov.cn/xinwen/2019-05/11/content_5390613.htm.
高恩新.城市開發區治權沖突與關系調適:以S開發區為例[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20(4):46-56+126.
Ci Q M,Zhi L L.Experiment-based policy making or conscious policy design?The case of urban housing reform in China[J].Policy Sciences,2014(3):321-337.
湯蘊懿.政府職能轉型:從政府管理到公共服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人民網.科學技術部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中心常務副主任張志宏做主旨發言[EB/OL].(2012-12-07)[2024-08-18].http://energy.people.com.cn/n/2012/1207/c353109-19830227.html.
薄文廣,殷廣衛.國家級新區發展困境分析與可持續發展思考[J].南京社會科學,2017(11):9-16.
張桂蓉,曹子璇.跨界環境治理中國家級新區與行政區互嵌式合作機制的生成邏輯——基于Z流域黑臭水體治理的案例研究[J].行政論壇,2022(5):118-126.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并監督實施的若干意見[EB/OL].(2019-05-23)[2024-9-10]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5/23/content_5394187.htm.
習近平.之江新語[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構建高效、協調、可持續的國土空間開發格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解釋材料[M].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16.
靳利飛,劉天科,劉芮琳.空間秩序的尺度選擇:基于國家級國土空間規劃視角的剖析[J].城市發展研究,2022(7):30-37.
生態環境部.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范區管理規程(試行)[EB/OL].(2016-01-12)[2024-03-13].https://www.mee.gov.cn/gkml/hbb/bwj/201601/W020160128368938015540.pdf.
北京市統計局.改革開放40年北京市開發區發展回顧[EB/OL].(2018-11-02)[2023-07-26].https://tjj.beijing.gov.cn/zt/dgsdzxp/cxfz/201811/t20181105_146338.html.
蔣明華.城際合作空間的構建策略——基于特別合作區案例的比較研究[J].區域經濟評論,2022(1):92-98.
青島經濟技術開發區網.青島經濟技術開發區概況[EB/OL].(2022-08-21)[2024-08-17].http://qda.qingdao.gov.cn/qqjs/qdkfqjj/202208/t20220821_6318114.shtml.
傅小隨.法定機構及其在公共服務體系中的特殊作用[J].行政論壇,2009(2):8-11.
How to Achieve the Transition of Governance Levels in Functional Areas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Driver Constraint\" Framework
Wu Hanbo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Functional zones have risen from the concept of urban planning to the level of serving national deployment, achieving an upward transition in governance levels. How can functional areas, as common governance tools, maintain long-term vitality, achiev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and gradually acquir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drive constraint\" framework,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that the evolution of functional areas is driven by a dual track approach of top-down goal guidance and bottom-up demand feedback. Through the triple constraints of value positioning, power allocation, and spatial attributes,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paths such as changing spatial boundaries, adjusting power structures, and optimizing management models are generated. The strategic evolution of functional zones, as a \"middle plate\" born from vertical government negotiations,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power departments further optimizing their empowerment and empowerment methods. From individual governance to strategic coordination, functional zones need to balance governance flexibility in a unified national plan, achieving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adapting spatial functions to the national layout.
Key words: functional zones; governance unit; drive constraint
■責任編輯:王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