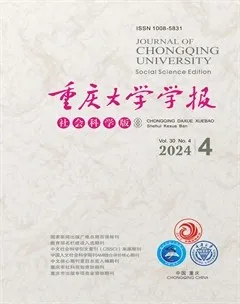碳中和時間表在應對氣候變化基本法中的規范表達
摘要:我國當前的碳中和工作主要在政策道路上推進,相關立法還不完善,特別是缺乏明確的碳中和時間表使得有些地方在推進碳中和工作時出現了“碳沖鋒”“運動式減碳”現象,既不利于積極穩妥推進碳中和目標實現,也帶來了生產生活上的不確定性。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間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和碳達峰碳中和立法的研究與論證工作。碳中和時間表是管理碳中和工作進程、確保碳中和目標實現的有效方法,大部分國家的碳中和立法都對其進行了規定。在我國“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時間框架下,研究制定切實可行的碳中和時間表法律規范,有利于推進應對氣候變化和碳達峰碳中和立法工作進程,更有利于提升碳中和相關立法的指向性和可實施性,穩定社會生產生活預期,提升我國在國際氣候合作治理中的話語權。碳中和時間表法律規范的制定應立足我國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等基本國情,結合國際氣候合作治理需要,以科學性與政策性相結合、國際性與國別性相結合、現時性與將來性相結合為設計基準,通過《應對氣候變化法》立法目的條款、碳中和時間表專項條款將我國碳中和工作進程納入法治軌道,充分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作用,保障當下及將來世代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與自由。具言之,《應對氣候變化法》立法目的條款中,碳中和時間表內容建議表述為“推動國家碳中和戰略決策實現,促進國際氣候治理合作”。專項條款設置上,一方面應規定具體明確的相對近期碳中和時間表,另一方面就中長期碳中和時間進程應確定特殊時間節點設計階段性目標,并授權國務院負責階段性期間內碳中和時間表的“細化”與“調高”。
關鍵詞:碳中和;應對氣候變化法;時間表;立法目的
中圖分類號:D922.6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24)04-0225-12
我國政府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的自主貢獻承諾,明確了我國實現碳中和的時間框架,即“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1]。碳達峰、碳中和的實現并非一個單年度時點,而在一個多年度時區[2]。碳中和時間表是在實現碳中和的多年度時區內,以凈零排放為目標,按照年度設置減碳目標的時間進程安排。碳中和時間表是實現碳中和的一種有效管理方式,不少國家的碳中和政策法規均以碳中和時間表為核心內容。“堅持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3],法治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保障,亦是氣候治理的必由之路,將碳中和時間表轉化為法律條文是確保氣候立法發揮法律規范預測、指引、評價、強制作用的關鍵,對于穩定社會生產生活預期和提升我國在國際氣候合作治理中的話語權具有重要意義[4]。我國不少地方立法都對碳中和進行了規定,但在碳中和時間進程上普遍采取了較為模糊的處理,未明確具體的碳中和時間進程。理論研究中,除少數學者基于嚴肅性和規范性考量,認為不宜在立法中直接規定“雙碳”目標的具體時間節點外[5],較多學者提出應對氣候變化法應設置碳中和時間進程條款[6],以達成《〈巴黎協定〉第13條所述行動和支助透明度框架的模式、程序和指南》要求[7],提升政府減排行動力[8],確保“雙碳”領域各項改革于法有據[9]。但就碳中和時間表條款的具體設計,除有學者提出應在立法目的條款中融入時間進程內容[10]、以相對靈活的調整機制確保碳中和時間進程條款科學合理外[11],關于其條款具體設計尚無專門研究。有鑒于此,本文從應對氣候變化法律體系的“氣候憲法—氣候基本法—氣候單行法”三階形式構造出發,著重探討碳中和時間表在應對氣候變化基本法中的規范表達。
一、應對氣候變化基本法應規定碳中和時間表
(一)應對氣候變化法的三階構造
碳中和已成為我國當前重要的政策話語。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在國際國內重要場合提及“雙碳”目標,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行業組織、大型企業紛紛推出了相應的碳中和政策、行動方案,初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的“雙碳”目標“1+N”政策體系。雖然相較于法律,政策更加靈活,更能適應科學不確定、國際氣候治理角力下國家碳中和工作的推進,但也存在著穩定性差、強制性弱、政策內容沖突等缺陷[12]。碳中和應盡快實現由“事理向法理”的轉變,將國家的碳中和政策話語轉化為法律的規范表達。但與碳匯、碳排放交易等“傳統”氣候法學概念有別,碳中和不僅是碎片化的概念集合,也是國家新時期經濟社會政策的概括表達,涉及對社會多元利益的重新分化與組合,因此必須立足于系統論視角,依次經由“雙重轉譯”實現碳中和政策的有序法律化、碳中和立法的有序體系化。第一重轉譯系對憲法中國家環境保護義務和憲法序言中生態文明建設國家根本任務的詮釋與細化,第二重轉譯則是在前次轉譯的基礎上,將碳中和政策的各項措施落實到單行法中,通過“構成要件+法律后果”的規范結構將碳中和政策內容轉化為法律語言,進一步規制個人、企業、國家機關的行為模式。雙重轉譯的結果便是形成“氣候憲法—氣候基本法—氣候單行法”三階形式構造的應對氣候變化法律體系,其中氣候基本法即《應對氣候變化法》[13]。
(二)《應對氣候變化法》應規定碳中和時間表
《應對氣候變化法》是碳中和從“事理向法理”轉變的橋梁,統領應對氣候變化專項立法,不僅可填補現有應對氣候變化專項法律體系中的制度空白,還可以從法律層面彰顯我國氣候行動的決心和動力。作為綜合性、框架性立法,《應對氣候變化法》應對碳減排過程中涉及的有關權力、權利、義務配置,以及碳中和政策的核心內容等進行規定,使其能夠初步達成法律規范的結構功能。這其中,碳中和時間表便屬于碳中和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我國當前公布的碳中和政策性文件中,已經有了碳中和時間表的雛形,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分別以2025、2030和2060年為時間節點,設置了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實現碳中和的目標。碳中和時間表是實現碳中和的一種有效管理方式,不少國家或地區出臺的碳中和相關法律文本均對碳中和時間表作出了規定,如歐盟《歐洲氣候法》、法國《能源和氣候法》、德國《聯邦氣候保護法》、加拿大《凈零排放問責法》、日本《全球變暖對策推進法》、韓國《碳中和與綠色發展基本法》。《應對氣候變化法》作為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法,亦應對碳中和時間表作出系統性規定,以切實推動碳中和目標實現,同時保護公民基本權利,提升我國在國際氣候治理中的話語權。
首先,將碳中和時間表轉化為法律條文是碳中和相關立法指向性和可實施性的前提。除已實現碳中和的國家,其他各國設置的碳中和目標達成時間短則20、30年,長則50、60年。若不設置具體的時間表,寄希望于幾十年后順利實現碳中和目標是不現實的。德國《聯邦氣候保護法》第3條對德國碳中和目標設立了2030年、2040年、2045年、2050年4個時間節點,在第3a條、第4條又分別對不同行業的年度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作出規定,形成了具體、詳細、明確的碳中和時間表,對德國低碳改革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缺失碳中和時間表的《應對氣候變化法》將減損指引和強制作用,有可能成為回應公眾期待的象征性立法,難以發揮保障氣候有效治理的作用。《應對氣候變化法》規定明確的碳中和時間進程將有效倒逼國家機關、各行各業、社會公眾進行低碳改革、調整生活方式。
其次,將碳中和時間表轉化為法律條文是立法穩定社會生產生活預期功能的要求。法治有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14],將政府碳中和工作納入法治軌道,接受社會公眾監督,可以有效避免政府減碳不作為或運動式減碳給經濟生產和社會生活帶來的不確定性。立法規定具體且向將來延伸一段時間的碳中和時間進程,并輔以相應的激勵引導措施,可以在全社會形成一個能夠產生壓力和激勵的低碳生產生活預期[15],為相應的技術開發提供政策指引。企業、個人可以依據這一預期適時啟動必要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長期且持久的大規模生產技術開發、生活方式調整,并在法治框架下確保這種調整免受來自國家的突然、徹底、別無選擇的限制。缺乏具體碳中和時間表,有可能引發運動式碳中和執法現象,不僅不利于碳中和目標實現,而且會引發社會生產生活的不安定,非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之義。
最后,將碳中和時間表轉化為法律條文是提升國家在國際氣候合作治理中話語權的需要。《巴黎協定》采取由各國自主承諾國家減排目標的氣候治理方式,各國按照提交的自主貢獻承諾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減排目標。從比較法上看,不少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將碳中和時間表寫入法律條文作為落實《巴黎協定》的主要方式,以獲得國際社會認可[16]。近年來,我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是《巴黎協定》得以達成的關鍵一環[17],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上向國際社會作出碳達峰、碳中和的鄭重承諾,我國政府也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了具體方案。將碳中和時間表轉化為法律條文可以彰顯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提升我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話語權,鞏固我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地位。
二、碳中和時間表法律規范的設計基準
(一)科學性與政策性相結合
碳中和工作是一項高度依賴科技的工作,碳中和時間表法律規范的設計應以氣候科學認知為出發點,有關全球氣候變暖的進展、后果及治理的新的充分證實的調查結果都應納入考量。自1990年開始,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已連續34年發布年度氣候變化報告,并每隔6至7年發布一份綜合科學評估報告,這些報告已成為各國、國際組織制定應對氣候變化法律的關鍵參考,如《巴黎協定》的主要科學依據便是2014年編制的第五次評估報告。
但氣候科學的不確定性令碳中和時間表法律規范設計亦有隱憂。當前,關于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導致全球氣候變暖的說法,科學界幾已不存在分歧,但關于氣候系統內的復雜交互作用、氣候變暖導致的確切后果目前只是抽象的預測[18],即便是《巴黎協定》強調的1.5℃升溫閾值所導致的生態后果也只是基于一定科學知識的粗略預測,并無確定的科學依據[19]。此外,是否有必要將地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和溫度上升限制在特定水平以及限制在何種水平屬于價值判斷,系一國氣候政策選擇范疇,是科學和技術無法回答的。法律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并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統治階級意志的規范體系。碳中和立法是立法者對國家關于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的法律化,而國家碳中和政策的制定是一個政治決策過程,一國在設計碳中和戰略決策時,必然會涉及多方利益權衡、優先次序分配問題,科學知識僅僅是決策的重要參考,而非唯一決定要素。因此,碳中和時間表法律規范的設計應立足國家的碳中和戰略決策,在科學技術與國家碳中和政策間建立足夠靈活的聯系,堅持科學性與政策性相結合,避免將碳中和偽裝成純粹的科學問題[20]。
(二)國際性與國別性相結合
氣候治理需要全球各國在信賴的基礎上開展一致行動,《巴黎協定》國家自主貢獻的實現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各國間的相互信任,建立和培養各方實現目標的信任成為《巴黎協定》氣候保護制度總體有效性的關鍵。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義務不能局限于一國內部,而應包含參與國際合作,碳中和時間表法律規范的設計必須考慮氣候治理“全球共同體”的基本結構[21]。近年來,全球范圍內氣候訴訟大量增加,其中有關國家的碳中和時間進程立法無法滿足《巴黎協定》規定的1.5℃控溫目標、應就跨境環境損害承擔立法及賠償責任等問題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也將進一步推動氣候治理的國際參與。
借鑒國際氣候保護制度中的已有規則制定本國碳中和時間表法律規范不失為一條捷徑,也體現了國家履行國際氣候治理責任的決心。但借鑒國際氣候保護制度中的相關規則并不等于照搬,我國碳中和時間表立法設計還應考慮經濟社會發展實際以及國家形象的建設。首先,碳中和時間表法律規范將深度影響我國的社會生產與居民生活,雖然我國對外承諾2060年實現碳中和,但實現這一承諾的時間節奏、具體路徑、方式方法等都屬于我國內政。碳中和時間表立法應立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按照法律規范性要求進行設計。實際上,其他國家在碳中和時間表設計上同樣將本國情況擺在了重要位置,如英國要求國務卿制定碳預算時必須將經濟情況、財政情況、社會環境、能源政策,甚至是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和北愛爾蘭之間的環境差異納入考量。其次,諸如《巴黎協定》中的目標條款僅是締約國關于氣候治理目標的最小公分母[20],直接將其轉化為國內法會削弱我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的影響力,不利于提升我國氣候治理負責任大國國際形象,也正因此,我國對外宣布的碳中和實現時間要早于印度等不少發展中國家。碳中和時間表法律規范的設計應在立足維護我國發展權益的同時,體現我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與態度[10]。
(三)現時性與將來性相結合
2021年德國《聯邦氣候保護法》憲法訴訟中,年輕世代訴愿人提出,《聯邦氣候保護法》規定的碳中和時間表給2030年后世代造成了過大減碳負擔,侵害了其依據憲法將來享有的符合人類尊嚴生活以及職業自由的基本權利。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就此創造性適用比例原則,支持了年輕世代的訴求,認為《聯邦氣候保護法》第3(1)條第2句、第4(1)條第3句以及附件2違憲,因為它們給未來世代的基本權利造成了不成比例的風險。聯邦憲法法院指出,根據德國《基本法》第20a條,國家負有為將來世代保護生命自然基礎的義務,義務內容包括保護后代免于因同樣履行此類保護義務(后代為其后代履行保護生命自然基礎義務)而不得不徹底“禁欲”。比例原則系從禁止侵害過度的維度來保護基本權利,其并不要求對基本權利的損害已然發生,只要有損害發生之虞即可,即對現世代的未來基本權利、未來世代的未來基本權利的保護并非只有在侵害達到絕對不合理程度后才開始提供保護,而是要求在這之前便啟動保護機制。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以比例原則審查碳中和時間表是否符合代際正義有其政治體制原因。多黨選舉制下,受選舉期影響,未來或長期利益在民主進程中的代表性很低,立法對將來世代的保護明顯不足[22]。當前氣候狀況要求必須立即采取限制當代人相關活動的減碳行動,但減碳與經濟發展緊密相連,這很可能令執政黨因擔心失去部分選票而將巨大的減碳負擔單方面轉移給子孫后代。我國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國家,立法者負有將憲法的科學精神和客觀規律滲透到立法過程的義務[23],在碳中和時間表法律規范的設計上不會出現為選票而置代際正義于不顧的問題,已有相關環境立法均將可持續發展作為立法目的并貫穿法律條文始終即為有力證明。但立法是利益博弈的過程,多元化的發展訴求不可避免地帶來日趨激烈的沖突,特別是在資源約束趨緊背景下進行的碳中和立法,難免有為了部門利益而逃避減碳責任的現象發生[24],故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以比例原則審查碳中和時間表的代際正義以及圍繞其構造的碳中和時間表設計理念與技術路徑值得借鑒。特別是,為確保碳中和時間表的科學性必然涉及對政府的授權立法,更應要求政府部門在具體設計碳中和時間表時打破部門利益,充分考慮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之間的辯證關系,沿襲已有環境立法理念,將可持續發展作為根本要求,兼顧現時性與將來性,在碳中和時間表規范設計中充分體現代際正義。
三、碳中和時間表在立法目的條款中的規范表達
立法目的是法律規范的內在靈魂和精神實質[25],但并非所有法律文本均須設置立法目的條款。一般而言,作為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備規范的“秩序法”可設可不設立法目的條款,而具有高度政策性的“政策法”原則上應設立法目的條款,以發揮區隔與自我正當化作用[26]。《應對氣候變化法》是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達成碳中和目標的基礎性立法,政策目的鮮明,屬于典型的政策法。為確保法律條文不偏離政策目標,應設置立法目的條款,將游離渙散的立法目光聚焦于應對氣候變化之上[27]。在立法目的條款的具體設計上,法律條文繁簡疏密適度要求下,不宜通過簡單枚舉將所有目的一概囊入,只能規定最主要的立法目的,通常將直接目的或較為貼近的間接目的納入[26]。實現碳中和目標是應對氣候變化專項立法的直接動因,碳中和實現的時間進程安排是碳中和目標的核心,將碳中和時間表寫入立法目的條款符合立法目的條款設計要求,當前已進行碳中和立法的國家也多將碳中和時間進程寫入立法目的條款。但與制定專門的直接以實現碳中和為目的的“碳中和法”不同,《應對氣候變化法》以應對氣候變化為直接目標,基于此直接目標還可以派生出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等間接目標,如墨西哥《氣候變化法》便規定了保護健康環境權,促進向有競爭力、可持續和低碳經濟過渡等7項立法目的。將碳中和時間表在諸多立法目的中按照法律條文繁簡疏密適度要求寫入《應對氣候變化法》立法目的條款,需符合科學性與政策性相結合、國際性與國別性相結合設計基準。
一是根據科學性與政策性相結合設計基準,立法目的條款中的碳中和時間表內容應保持相對開放。一方面,立法目的條款中的碳中和時間表內容表達應相對明確,以服務于后續條文設計,為碳中和執法和司法提供指引。當前國際上有關碳中和立法,大多在立法目的條款規定較明確的碳中和時間表內容,如德國《聯邦氣候保護法》、丹麥《氣候法》等。第75屆聯合國大會之后,我國有14部地方性法規、2部部門規章將碳中和寫入了立法目的條款,但絕大部分(15部)籠統表述為“推動碳中和”,并未涉及碳中和時間表相關內容,僅《延安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規定“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的戰略決策”,與碳中和時間表內容有間接關聯,因為碳中和戰略決策必然涵蓋實現碳中和的時間安排,“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的戰略決策”意含以戰略決策中的時間安排為依據推進工作。另一方面,科技不確定性要求立法目的條款中的碳中和時間表內容表達應適度明確。當前不少國家或地區在應對氣候變化專門立法的目的條款中對碳中和目標實現進行了精準時間定位,如丹麥《氣候法條例》第1條規定,該法之目的是使丹麥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1990年減少70%,并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積極實現《巴黎協定》將全球氣溫上升限制在1.5℃的目標。我國也有學者建議直接在立法目的條款中規定“實現2030年碳達峰目標和2060年碳中和愿景”[10],但碳中和高度依賴科技,科技又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碳中和時間表可能會隨著科技發展而調整,立法目的條款系抽象模糊的愿景式表達,具有高度概括及彈性特征,其中的碳中和時間表內容應保持一定的開放性,以適應科技的發展變化。此外,碳中和的政策性要求立法目的條款與政策同向。碳中和政策會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變遷而調整,如我國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對外承諾,可能會隨著國內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和公眾生活方式的轉變而提前。
二是根據國際性與國別性相結合設計基準,立法目的條款中的碳中和時間表內容應立足國際協定并體現國家意志。不少國家直接將國際協定中的有關內容作為本國專項立法目的條款中的碳中和時間表內容,如德國將《歐洲氣候法》及《巴黎協定》寫入立法目的條款,墨西哥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寫入立法目的條款。應當注意的是,在當前的國際氣候治理中,“共同但有區別責任”仍是核心原則,發展中國家不能將本國碳中和政策和國際氣候治理“快車”完全綁定,制定碳中和政策必須考慮國內經濟發展實際,特別是要考慮公民的生存、發展權利。作為人口和經濟大國,我國制定碳中和政策時尤要立足國情實際,不能簡單加入減碳競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我們承諾的‘雙碳’目標是確定不移的,但達到這一目標的路徑和方式、節奏和力度則應該而且必須由我們自己做主,決不受他人左右”[13]。當然,立足本土實際并不意味著在立法目的條款中排斥國際約定,為體現我國的氣候治理決心和提升國際氣候治理話語權,立法目的條款對國際條約應有所體現,這也是當前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法立法目的條款的通行做法。
基于以上兩方面考量,本文認為在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法》的立法目的條款中,碳中和時間表的規范表達可參酌《延安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中規定“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的戰略決策”的方式。首先,戰略決策有相對開放性,以“戰略決策”取代具體的時間規定,既體現了《應對氣候變化法》的政策法屬性,也使得目的條款有關碳中和時間表的規定可以適應科技與經濟發展變化需要。其次,“戰略決策”的作出本身便是兼顧國際氣候治理要求和本國國情的,體現了國際性與國別性的結合。但“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的戰略決策”表述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沒有明確戰略決策的制定主體,戰略決策可以是國際戰略,也可以是一國戰略,甚至是一省一市戰略,需要在條文中明確制定主體;二是法律并不能保證目的“落實”,立法目的是立法者賦予法律的價值目標[28],價值目標的實現需要法治系統的整體聯動,立法對目的的實現只是發揮保障和推動作用;三是對國際協定的體現不夠直接,雖然碳中和戰略決策意含國際協定要求,但鑒于語言習慣,難以被國際社會直觀理解,應在立法目的條款中直接點明。因此,建議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法》立法目的條款對碳中和時間表的規定表述為“推動國家碳中和戰略決策實現,促進國際氣候治理合作”。
四、碳中和時間表專項條款的規范表達
(一)碳中和時間表專項條款的規范模式
妥適的碳中和時間表專項條款設計有助于推進碳中和目標循序漸進實現[29]。但碳中和目標的實現高度依賴科技,既需要對現有氣候系統的準確評估,也需要預測科技發展引發的碳中和技術變革。而氣候系統內在混沌、復雜多變,且伴有多種時間尺度的非線性反饋[30],以現有科技無法準確繪制出具體明確的碳中和時間表,如何設計妥適的碳中和時間表專項條款成為各國立法的難題。不少國家采取授權立法模式,在應對氣候變化基本法中僅規定碳中和時間表的制定原則,而將制定具體碳中和時間表的權力授予行政機關。英國、丹麥等不少國家都采取了此種模式,如丹麥《氣候法》,在主要規定碳中和時間表內容的第一章,先是通過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則條款對實現碳中和進程進行了規定,而在具體的碳中和時間表制定上則是采取了完全授權政府部門的立法模式,授權氣候、能源和供應部長至少每5年制定一個10年期的國家氣候目標。最后則是對政府部門的碳中和時間表制定權限進行了限制,要求制定的碳中和時間表應比立法目的條款中的碳中和目標達成時間更積極。
雖然授權行政機關制定碳中和時間表更契合碳中和工作實際,但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涉及對社會多元利益的重新分化,授權政府部門制定碳中和時間表是否合憲在實踐中仍存在一定爭議。特別是在大陸法系的成文憲法國家,授權政府部門制定碳中和時間表涉及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的問題。如在德國,憲法訴訟前的《聯邦氣候保護法》不僅對2030年之前各年度減排目標進行了詳細規定,還細分了各行業領域的年度減排目標,而對2030年之后的年度減排目標則采取了授權立法方式,“聯邦政府有權通過法規命令
“法規命令”(Rechtsverordnung),在德國指由行政機關根據法律授權制定的規范性文件。詳見趙宏《實質理性下的形式理性〈德國基本法〉中基本權的規范模式》(《比較法研究》,2007年第2期16-29頁)。修訂附錄2所列行業的年度排放限額,而無需經聯邦參議院同意”,“聯邦政府通過法規命令確定各個部門的年度排放限額”。這一授權立法方式在憲法訴訟中成為了爭議焦點,訴愿人認為,授權政府制定(調整)碳中和時間表違反了重要性理論。重要性理論是德國理論與實務界普遍認可的判斷立法者是否遵循法律保留原則的基準[31],要求立法者授權立法時,“基本的法律領域,特別是基本權利行使領域內的所有重要決定……都應自己作出規定”[32]。德國《聯邦氣候保護法》憲法訴訟中,聯邦憲法法院認為,實質影響公民基本自由和平等權利的決定必須經由正式的議會立法予以明確,但這并不排斥授權行政機關參與決定的執行與監管,即實現碳中和的決定必須經由議會立法,但碳中和時間表屬于對決定的執行,可以授權政府制定。與此同時,為了避免行政機關的參與不當影響公民的基本自由和平等權利,議會立法必須對授權的內容、目的和范圍作出詳細規定,《聯邦氣候保護法》授權聯邦政府通過法規命令確定各個部門的年度排放限額未能滿足這一要求,因其對聯邦政府制定年度目標的授權不夠具體詳細。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后,立法機構隨即對授權條款進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法律條文從多個方面構建了授權約束機制:一是以附表的形式明確了2031—2040年間的年度減碳目標,并要求聯邦政府至遲于2032年提交一份設定2041—2045年間年度減碳目標的立法提案;二是要求聯邦政府分別于2024年、2034年以法規命令的形式確定2031—2040年、2041—2045年各部門的年度減碳目標;三是要求年度目標應有利于實現《聯邦氣候保護法》規定的碳中和目標,能夠切實保障每個部門大幅減少碳排放。修改后的《聯邦氣候保護法》在碳中和時間表專項條款設計上形成了有別于英國、丹麥等國家單純的授權立法模式,而是通過職權與授權相結合的模式使碳中和時間表規范既滿足合憲性要求,也更加契合碳中和工作實際。
在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以下簡稱《立法法》)第11條只是對立法權限的劃分,與奧托·邁耶所主張的“法律保留”原則存在較大區別[33],我國實踐中也未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通過合憲性審查發展出諸如重要性理論等法律保留原則適用的判斷基準。但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和《立法法》的相關規定中亦可窺見我國碳中和時間表規范的立法權限劃分以及授權政府制定碳中和時間表的規范依據。首先,碳中和是一項系統性改革,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特別是在經濟領域,會引發稅收、財政、金融等基本制度的變革,因此根據《立法法》第11條第(六)、(九)項等規定,實現碳中和的決定只能以法律形式作出。其次,根據《憲法》第89條,國務院在經濟發展、城鄉建設、生態建設、教科文衛體、對外事務等領域享有管理職權,是否以及何時實現碳中和系國家政治決定,只能由全國人大制定法律予以規定,但實現碳中和的具體時間進程則屬于管理性事務,可以由國務院予以明確。再次,根據《憲法》第89條第(一)項的規定,國務院在管理方式上可以根據憲法和法律,采取規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規、發布決定和命令等方式,即可以經由《應對氣候變化法》授權國務院制定(調整)具體的碳中和時間表。由此觀之,授權國務院制定碳中和時間表并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礙。
(二)授權國務院制定(調整)碳中和時間表條款的設計
雖然授權國務院制定(調整)碳中和時間表符合憲法規定,但考慮到碳中和時間表對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可能造成的較大影響,應對氣候變化基本法在授權時應對以下三個方面內容予以特別規定。
一是明確授權范圍。對國務院制定碳中和時間表的授權不應采取概括授權方式,而應將其明確在“細化”和“調高”兩個方面,“調低”的權力則保留給全國人大。首先,國務院負責細化階段性碳中和時間表。《應對氣候變化法》對相對近期的碳中和目標應按年度予以規定,對中長期碳中和目標則應采取確定特殊時間節點設計階段性碳中和目標的方式,國務院僅負責階段性期間內碳中和時間表的年度細化工作。具體而言,考慮到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將應對氣候變化和碳達峰碳中和歸為“立法條件尚不完全具備、需要繼續研究論證的立法項目”,以及我國作出的2030年碳達峰承諾,建議在2030年左右通過《應對氣候變化法》,并以2030年碳排放量為基數,設計碳中和時間表,對于中長期的2036—2060年,以5年為期,分別規定2040、2045、2050、2055年的階段性碳中和目標,階段性期間內的年度目標則授權國務院制定。其次,國務院僅享有“調高”階段性碳中和目標的權力。當代風險社會,傳統上立法者在授權時根據相對確定的預測作出具體安排的情況已然不復存在,立法者只能根據高度不確定的知識和預測授權行政機關采取規制措施,行政機關在未來不確定性的范圍內作出的任何預測和判斷原則上都具有形式合法性。[34]國務院在制定碳中和時間表的過程中,因科技認知變化、低碳技術發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等需要調整階段性碳中和目標的,可以調整,但基于現實性與將來性結合考量,其僅能調高而不能調低階段性碳中和目標,以防將減碳責任過多轉移給將來世代。如因特殊情勢確需調低階段性目標的,只能向全國人大提交調整議案,由全國人大通過修法的方式進行。
二是督促國務院主動承擔提高階段性碳中和目標責任。國務院制定碳中和時間表并非完全限于對《應對氣候變化法》中階段性目標的細化,其還負有主動提高階段性目標以推動國家盡快實現碳中和目標的責任。為督促國務院履責,要求其在公布下一階段碳中和時間表時必須對上一階段碳中和進展情況作出報告,對于超額完成階段性碳中和目標的,超額部分不納入下一階段基數;對于未完成階段性碳中和目標的,必須作情況說明以及下一階段改進提升的方案,且未完成部分應在下一階段消解,不能推遲至再下一階段。如規定到2040年碳排放量減至2030年的60%,2045年為50%,若2040年完成至58%,則2045年順調為48%,若2040年僅完成62%,則2045年仍應為50%。
三是保障公眾知情權。國務院在細化或調整碳中和時間表時,必須以適當的方式向各省級人民政府、專家學者、社會公眾征求意見,特別是考慮到代際正義,要向年輕世代征求意見,以防因短視片面地分配自由、減輕現世代負擔、損害未來世代利益。同時,為使社會公眾知悉國家減碳計劃,提前作好生產生活規劃,應要求國務院提前2年公布下一階段的年度減碳目標,即應分別在2033、2038、2043、2048、2053年公布2036—2040、2041—2045、2046—2050、2051—2055、2056—2060年各時間段的具體年度減碳目標。經提前公布也可引發公眾討論,便于在其實施前根據公眾意見建議、上一階段目標實現情況及時調整年度目標。
(三)相對近期碳中和時間表條款的設計
對于相對近期(2031—2035年)的碳中和時間表,建議采德國立法例,即在應對氣候變化基本法中以盡可能具體明確的條文予以規定,具體原因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設置具體明確的相對近期碳中和時間表條款堅持了現時性與將來性相結合設計基準。向凈零排放社會轉型是一個長期且伴隨巨大負擔的過程,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條文不僅關系當前世代的基本權利與自由,也關系到將來世代的基本權利與自由。基于代際正義要求,立法者必須以尊重將來世代基本權利的方式制定轉型負擔代際分配的規范性保障措施,制定具體明確的相對近期碳中和時間表規范便是對這一要求的回應。因為具體明確的相對近期碳中和時間表規范一方面可直觀回應尊重未來基本權利與自由須立即開始向碳中和過渡,而不是將巨大轉型負擔單方面轉移給后代子孫的要求,即根據比例原則在當前世代和將來世代間公平分配減碳負擔;另一方面也可傳達足夠程度的發展緊迫性和規劃確定性,以確定哪些生產生活活動在最廣泛的意義上需要立即進行重大重塑,并輔之以適當的監管、知識創造措施促進創新,加快經濟社會的必要結構轉型進程。
二是設置具體明確的相對近期碳中和時間表條款堅持了國際性與國別性相結合設計基準。當前不同國家關于碳中和時間表內容的立法表達雖有差異,但大部分國家都以2030年為界,其中2030年之前的條文內容較為具體明確,而2030年之后的條文內容則相對模糊或是通過授權條款的方式制定[29]。雖然我國實現碳中和的路徑和方式、節奏和力度自主決策,不受他人左右,但黨的二十大報告已經提出,我國碳中和“逐步轉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制定具體明確的相對近期碳中和時間表條款并不是單純緊隨國際趨勢,而是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要求,立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的主動作為。
三是設置具體明確的相對近期碳中和時間表條款與科學的不確定性并不矛盾。不確定性是科學的常態,但在特定場域或相對較短的時間維度,科學仍然具有相對確定性,正如在量子力學高速發展的今天,牛頓經典力學于日常生活中仍然有其廣袤的適用空間。根據當前相對確定的氣候治理科學認知制定相對較近一段時期的碳中和時間表與科學的不確定性并不矛盾。更為重要的是,氣候科學的不確定性并非導向氣候治理的不可知論,不應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滋生消極被動觀念[35]。預防原則是環境部門法最為重要的原則之一,“事實不確定、價值有爭議、政策影響大、決策時間緊”是“后常規科學”階段公共決策的共同特征[36]。面對氣候科學的不確定性,立法機關更應積極作為,在現有氣候科學認知基礎上,將價值、政治、環境、傳統等社會因素納入決策考量基準,并基于更開放的平臺和更廣闊的認知論框架以知識協同生產的方式設計碳中和時間表專項條款。
結論
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應對氣候變化和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立法規劃,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了能耗“雙控”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轉變的新要求。應對氣候變化基本法應設計碳中和時間表條款,在落實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要求的同時,保護當前世代和未來世代公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本文基于國外立法例和我國碳中和工作實際,分析了應對氣候變化基本法中碳中和時間表條款的設計基準,并基于此基準就應對氣候變化基本法中的立法目的條款如何融入碳中和時間表、碳中和時間表專項條款如何設計提出了建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不僅與科技發展緊密相關,也與國家社會經濟政策勾連甚深,既涉及國家的國際戰略,也涉及國家內部的央地協同與部門聯動。本文從應對氣候變化基本法維度提出的碳中和時間表立法建議相對較為中觀,還需經由授權條款交國務院及其相關職能部門予以具體細化,關注如何制定地方碳中和時間表、行業碳中和時間表等。
參考文獻:
[1] 中國落實國家自主貢獻成效和新目標新舉措[EB/OL].(2021-11-10).http://www.ncsc.org.cn/zt/2021_COP/202111/P020211110590484647110.pdf.
[2] 薛進軍,郭琳.科學認識氣候變化,合理制定碳達峰碳中和的路線圖和時間表[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5):38-45.
[3] 習近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需要處理好幾個重大關系[J].求是,2023(22):4-7.
[4] 柳華文.“雙碳”目標及其實施的國際法解讀[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13-22.
[5] 王操.碳中和立法:何以可能與何以可為[J].東方法學,2022(6):185-198.
[6] 余耀軍.“雙碳”目標下中國氣候變化立法的雙階體系構造[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2(1):89-96.
[7] 陳貽健.《巴黎協定》下國家自主貢獻的雙重義務模式[J].法學研究,2023(5):206-224.
[8] 王江.論碳達峰碳中和行動的法制框架[J].東方法學,2021(5):122-134.
[9] 田時雨.以系統觀念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法治化[J].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3(3):69-78.
[10] 常紀文,田丹宇.應對氣候變化法的立法探究[J].中國環境管理,2021(2):16-19.
[11] 李猛.“雙碳”目標背景下完善我國碳中和立法的理論基礎與實現路徑[J].社會科學研究,2021(6):90-101.
[12] 劉志仁.論“雙碳”背景下中國碳排放管理的法治化路徑[J].法律科學,2022(3):94-104.
[13] 曹明德.社會系統論視角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法律對策[J].中國法學,2023(5):128-148.
[14] 熊選國.論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地位和作用[J].中國法學,2023(2):5-24.
[15] 馬吉.工商業與人權的氣候變化之維:形成中的“氣候盡責”概念[J].李卓倫,譯.人權,2022(4):138-166.
[16] 鄭軍,劉婷.主要發達國家碳達峰碳中和的實踐經驗及對中國的啟示[J].中國環境管理,2023(4):18-25,43.
[17] 古特雷斯:中國是《巴黎協定》中重要一環[EB/OL].(2020-12-12).https://m.news.cctv.com/2020/12/12/ARTI0tHdu2N4GiJeomaKJ1sd201212.shtml.
[18]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Climate change 2021: The physicalscience basi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
[19]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Global warming of 1.5°C. An IPCC special report on the impacts of global warming of 1.5°C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and related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pathways, in the context of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response to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fforts to eradicate poverty[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20] EIFERT M, VON LANDENBERG-ROBERG M.Climate change challenges constitutional law: Contextualising the German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s climate jurisprudence within climate constitutionalism[G]//BAUMLER J, BINDER C, BUNGENBERG M, et al. Europe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22.Cham:Springer,2022.
[21] EDENHOFER O, FLACHSLAND C, JAKOB M, et al.The atmosphere as a global commons[M]//BERNARD L, SEMMLER W.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macroeconomics of global warm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22] FRANZIUS C. Die Rolle von Gerichten im Klimaschutzrecht[M]//RODI M. Handbuch Klimaschutzrecht. München: C.H.Beck,2021.
[23] 韓大元.民法典編纂要體現憲法精神[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6(6):3-10,169.
[24] 呂忠梅.尋找長江流域立法的新法理[J].政法論叢,2018(6):67-80.
[25] 孔祥俊.法律解釋與適用方法[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
[26] 劉風景.立法目的條款之法理基礎及表述技術[J].法商研究,2013(3):48-57.
[27] 秦天寶.整體系統觀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法治保障[J].法律科學,2022(2):101-112.
[28] 楊銅銅.論立法起草者的角色定位與塑造[J].河北法學,2020(6):34-50.
[29] 田聿申.全球典型國家碳中和目標實現路徑對我國的啟示[J].中國能源,2021(9):80-88.
[30] 秦大河.氣候變化科學概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
[31] 黃衛.作為司法審查方法的法律保留原則[J].法律方法,2019(1):254-262.
[32] 趙宏.限制的限制:德國基本權利限制模式的內在機理[J].法學家,2011(2):152-166,180.
[33] 莫紀宏.新立法法視角下憲法保留原則的特征及其規范功能[J].政法論壇,2023(5):63-72.
[34] 金自寧.風險規制與行政法治[J].法制與社會發展,2012(4):60-71.
[35] 顧小峰.環境訴訟“科學上的不確定性因素”[J].法學,1991(6):40-41.
[36] RAVETZ J.Three types of risk assess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post-normal science[J].Social Theories of Risk,1992:251-273.
Normative expression of carbon neutrality
schedule in climate change basic law
MA Jing
(School of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P. R.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carbon neutrality work in China is mainly promoted on a policy path, and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is not yet perfect, especially that the lack of a clear carbon neutrality schedule may lead to carbon charging and campaign style carbon reduction in some places. It is not conducive to actively and steadily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and may also bring uncertainty to production and life.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research on climate change and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legislation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Carbon neutrality schedule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managing the progress of carbon neutrality and ensuring the achievement of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which is provided in most countries’ carbon neutrality legislation. Under the schedule for “striving to achieve carbon peak before 2030 and carbon neutrality before 2060” of China, studying and formulating practical and feasible carbon neutrality schedule legal norm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advancing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climate change and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but also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feasibility of carbon neutrality legislation, stabilizing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expectations, and enhancing China’s voice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The carbon neutrality schedule legal norms should be based on China’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such a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ergy structure, combined with needs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nd designed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and policy nature,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ature, and current and future nature. Through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clause and special clauses on carbon neutrality schedule of the Climate Change Law, the process of China’s carbon neutrality work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track of the rule of la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rule of law in solidifying foundation, stabilizing expectations, and promoting long-term benefits, and safeguarding the basic rights and freedoms of the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of the people. Specifically, in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clause, the content of carbon neutrality schedule is suggested to state a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carbon neutrality strategy and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limate governance cooperation”. In the special clauses, a specific and clear relative short-term carbon neutrality schedule should be provided, phase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for medium and long-term carbon neutrality schedule should be designed, and the State Council should be authorized to refine and advance the carbon neutrality schedule during the phased period.
Key words:
carbon neutrality; climate change law; schedule; legislative purpose(責任編輯 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