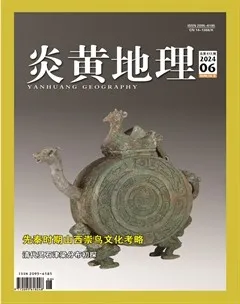嚴復與侯官文化



“侯官文化”是福建一種獨特的地域文化,在中國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為“侯官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嚴復是中國近代極具影響力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教育家和翻譯家。他的八大譯著,尤其是《天演論》,對中國近代社會思潮起到了巨大影響,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西學東漸”這股洪流中不可撼動的地位。他曾將自己的學術思想題為“侯官嚴復學”,并在譯著和文章署名時皆在名字前加上“侯官”二字,使得“侯官”這個遠離政治文化中心的縣名從19世紀末起就成為文化的代名詞。
2023年4月8日,福建省委宣傳部部長張彥在《瞭望》雜志上發表論文《推動“閩派”特色文藝蓬勃發展》,這是“侯官文化”首次作為福建地域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被提出來,并上升到福建省規劃綱要的地位。
侯官文化
侯官原為漢代冶縣之地,從東漢到晚清,在福建地域文化之中,形成了一個具有其鮮明的時代特征與地方特色的侯官文化。作為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歷經宋明以來閩文化的發展變遷,在晚清福州地區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中,形成了一支具有福建文化標識意義的地域文化。
“侯官文化”,指的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曾出現過一個奇異現象:地處東南之隅,遠離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彈丸之地侯官,在極短的時間內崛起了包括林則徐、沈葆楨、嚴復、林紓、林覺民、薩鎮冰這些特殊時空的人物群體。更為令人驚嘆的是這些杰出人物門類齊全,有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文學家、外交家、思想家、翻譯家,幾乎囊括了各個領域。這么多著名人物集中出現在一個不大的區域,“晚清風流數侯官”,體現了所謂“地靈人杰”,或謂“天時、地利、人和”。正是這些風流人物,在各自的領域對中國近代史起到或大或小的推動作用。
早在19世紀末開始至20世紀上半葉,“侯官”雖然只是一個縣域地名,卻頻繁出現在《申報》《新民叢報》等各大全國發行的報刊版面,且一度成為知識分子交談和筆墨觸及的“熱詞”。這一現象的出現同“侯官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嚴復及其譯作《天演論》的流行密不可分。
求學之路
嚴復(1854—1921),福建侯官縣人,是近代極具影響力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他出生于中醫世家,從七歲起上私塾,從小便打下了堅實的文字功底。1866年,是嚴復人生最重要的轉折點。這年春天,14歲的嚴復成婚,6月,福州瘟疫,家中經濟的頂梁柱父親在救治病人時不幸染病過世。這徹底改變了嚴復的命運,中斷了嚴復的科舉之路。家道中落,全家不得不搬回城郊的陽崎老家。不要說繼續讀書,就是家中生計都要靠母親和妻子做針線活來艱難維系。就在嚴復急于尋找出路、謀求擺脫困境時,恰好年末福州船政學堂開始招收第一屆學生,不僅食宿、學費和醫藥費全免,而且每月還有四兩銀子補貼。巧的是,那年的考題是與父母孝道有關的“為大孝終身慕父母論”。剛經歷了喪父之痛的嚴復,觸題生情,揮筆成章。聲情并茂的文章打動了也剛經歷了喪母之痛的主考官沈葆楨,因此嚴復最終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
在晚清海軍人才的搖籃——福州馬尾船政學堂,嚴復上的是以英文教學為主的后學堂,并接受了幾何、代數、光學、天文學、航海術等現代科學課程。因此,嚴復從14歲到18歲期間,不但接受了系統的英文教育,還接受了遠遠先進于同時代國人的基礎科學教育,這兩者都為嚴復日后的“嚴譯名著”打下了堅實的語言基礎和知識基礎。
1877年,23歲的嚴復作為清政府派遣赴歐的第一批留學生,前往英國留學。他先是就讀于普茨茅斯海軍學院,后考入倫敦的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即現在的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繼續深造。1879年,26歲的嚴復回到母校馬尾船政學堂任教習。從此,教育成了他畢生的事業。
教育事業
嚴復作為近代中國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不僅提出了豐富的教育理論,而且在多所名校主持教育。1880年,他于馬尾船政學堂任教一年后,經陳寶琛舉薦,被召去北洋水師學堂任總教習(教務長)。十年后,被提升為水師學堂會辦(副校長);第二年又被提升為總辦(校長),并在此執教二十年。
除了北洋水師學堂,嚴復還先后擔任過安慶高等師范學堂和上海復旦公學校長。1912年5月,他出任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他執掌北大之際,北大正處于艱苦創業的階段。為創建、保全和發展北京大學,他經歷了一生辦學實踐中最艱難的階段,為此傾注了無數心血。無論是為籌措北大辦學經費嘔心瀝血,或是兩上“說帖”請求保留北大,拯救將遭停辦厄運的新生學府:還是改良教學,提出“兼收并蓄、廣納眾流,以成其大”的辦學主張,使之成為后來北大辦學思想的主流和傳統。嚴復為北大,為這所中國最高學府,為艱難前行的中國現代教育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作家李志偉在《北大百年(1898-1998)》一書中稱贊嚴復為“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北大校長”,感嘆嚴復留下了一個“具備了一流精神底蘊和辦學思路的北大”。在一百多年前的民國元年,在一個動蕩不安、官僚軍閥們都忙著爭權奪利的社會大環境下,竟還有這樣一個頭腦在思考著中國高等教育制度的未來,這不僅是北大之幸事,中國現代教育之幸事,更是中國之幸事!
翻譯事業
從1898年維新變法運動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的十余年間,是嚴復一生中精力最旺盛、學問造詣最深厚、思想認識最成熟的時期。他主要致力于翻譯西方十八、十九世紀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邏輯學、哲學、法學等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向中國知識分子系統介紹了“西學”的精華。他的譯作,不僅使當時的中國人耳目為之一新;而且為中國學術的更新,為中國近代社會科學的創建奠定了重要理論基礎。
嚴復于西學的接觸始于福州馬尾船政學堂,發展于英倫留學期間,真正讓他從教育事業跨界到翻譯事業的導火索是1894年的中國甲午海戰的慘敗。他為了喚醒國人、救亡圖存,開始選擇用筆和文字作為戰斗工具。甲午戰爭前,人們普遍關注西方的“堅固的船只和猛烈的大炮”,而洋務運動也主要是學習西方精巧的機器,以達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的。嚴復批評這些膚淺的認識,認為學習“技藝器物”等有形文化只是學習西方的皮毛;主張更需要學習的是西方的思想、觀念等無形文化。為了讓中國知識分子全面、系統地認識西學的精髓,他從1896年到1905年的十年間,慧眼獨具地選擇翻譯了一批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原著,后來史稱八部“嚴譯名著”。這八部“嚴譯名著”,詳見表1。
八部“嚴譯名著”中最重要、影響力最大最深遠的當屬1896年翻譯出版的赫胥黎的《天演論》。嚴復成為第一個將達爾文進化論全面系統介紹到中國來的學者。在《天演論》自序中,嚴復明確表示,他翻譯此書的目的,是因為此書的主題是闡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可以號召國人在民族存亡的關頭要發憤圖強,急起直追,而不應坐以待斃。這不但與嚴復“維新圖治、救亡保種”的思想非常合拍,而且與當時中國救亡圖存的社會思想主流是十分吻合的。嚴復在翻譯此書時,并非字字直譯,全盤照搬,而是在翻譯過程中,加了大量按語、解釋或評價,在闡述自己的社會政治見解的同時,引導讀者的思路。他甚至在文本翻譯中,也根據自己的思想觀點對原文進行了改造和發揮。
這部譯作不但使他成為“向中國介紹西方先進思想的第一人”,而且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詞成為人們的口頭禪。時至今日,哪怕這本譯作面世已百余年,現代人一提起嚴復,除了《天演論》,下一個脫口而出的關鍵詞必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該書190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后,到1921年就印行了20版。該書對社會影響之廣,由此可見一斑。正是因為嚴復翻譯《天演論》,康有為稱贊他是“精通西學第一人”,梁啟超稱贊他為“于中學西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魯迅熱情地稱道他“是一個19世紀末年中國感覺敏銳的人”,胡適稱贊“嚴復是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綜觀嚴復的譯著,涉及政治學、經濟學、哲學,邏輯學、法學等眾多學科,形成了相對完整的西學體系。具體而言,《天演論》為近代中國敲響了亡國滅種的警鐘,為救亡運動作了總動員,并且為人們提供了新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社會通詮》向人們展示了一幅由圖騰社會到宗法社會,再到軍國社會階段的完整社會進化過程;《原富》為中國人民自強求富貢獻了“自由平通”的方略;《群學肄言》則強調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對國家政治的指導作用;《穆勒名學》與《名學淺說》介紹了近代西方格物窮理的治學方法;《法意》宣傳自由民權學說、三權分立學說及君主立憲的好處。嚴復以一己之力,率先獨立翻譯出橫跨如此眾多學科的西學名著,在中國近代史上絕無僅有。
更為重要的是,嚴復的譯著在介紹西方學術思想時,不是一味吹捧、盲從或是全盤接受。而是結合中國國情,或借用原著闡發自己的觀點,或介紹對中國人可資利用的新思想、新方法、新知識,或對原著加以評析。嚴復在每本譯作中都針對性地加上按語和序言,鮮明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他不是以西學排斥中學,而是融中學和西學為一體,既傳播了西學,又能切中時弊。他的翻譯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化移植過程,而是一個文化再創造的過程,因而產生了較強的社會效果,因此每次譯書出版之際,便得到社會各界讀書之人的爭相購買,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
嚴復對中國近現代的影響除了“嚴譯名著”外,他還在自己的翻譯實踐中結合翻譯的心得體會,首次在《lt;天演論gt;譯例言》中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并指出這三個標準是翻譯中最難達到的三件事。嚴復所說的“信”就是盡可能地忠于原文,使譯文意義不違背原文;“達”就是在“信”的基礎上準確充分地表達出原文的內涵,當“信”和“達”發生沖突時,“信”是第一位的。嚴復主張,為了做到“達”,在具體翻譯過程中不能硬譯死譯,只要能準確表達出原文意旨,不必斤斤計較文字和句次。嚴復提出的“雅”,本意是強調譯文必須正確規范,符合正道與正統。所以“雅”泛指譯文的文字水平,而非單純指譯文的文學價值,也不是要求譯文要一味追求所謂的“高雅”。近代中國首次提出將“信、達、雅”作為翻譯標準,并論述三者之間的有機聯系,使之成為一種較為完整的理論,則始自嚴復。“信、達、雅”是中國近代翻譯理論的起點,在中國翻譯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我國翻譯理論中至今仍占據主流地位。
侯官嚴復學
嚴復和侯官文化之間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嚴復曾將自己的學術思想題為“侯官嚴復學”,而當代學者汪征魯教授則稱之為“侯官新學”,并認為“侯官新學”的內涵主要表現在:以社會進化論為核心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社會歷史觀與以“三民論”(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為核心的救國方略。“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的價值取向。嚴復學術思想的最大特色還在于,他是立足于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思維、以儒家傳統中的基本價值理念為基點來介紹和宣傳西方的價值觀,努力尋求中西思想的一致性。因此,嚴復的“侯官新學”無疑是侯官文化的核心。“嚴譯名著”是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的產物,嚴復對外來文化的包容吸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自信及對構建中國近代新型的文化體系的不懈努力,堪稱“侯官文化”最具代表性人物。
另一方面,縱觀當時各個版本的《天演論》,嚴復的署名都冠以“侯官嚴復”。在《天演論》成名之后,嚴復經常在當時流傳甚廣的報紙,諸如《申報》《大公報》《東方雜志》等撰文發表政見,皆署名“侯官嚴復”。《天演論》發表之后,嚴復陸續翻譯的其他西方名著都引發了社會的關注。當時影響力較大的報刊——《新民叢報》《東方雜志》《教育雜志》《鷺江報》等,都以“侯官嚴復”譯或譯著為名進行了宣傳報道。這樣一來,“侯官”也就和“天演”一樣成為嚴復的標簽。
值得一提的是,嚴復因《天演論》獲得了一大批粉絲,他們也都喜歡用侯官嚴復來稱呼他。比如他重量級的粉絲之一梁啟超就常以“嚴君”“侯官嚴復幾道”等稱呼嚴復。而當時極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如蔡元培、錢穆、魯迅等盛贊《天演論》時都冠以“侯官嚴復”的標簽。“侯官”本僅為一縣名,跟隨著當時社會的“嚴復熱”和嚴復粉絲的二次傳播再度成為當時中國報刊及文人爭相傳播的“熱詞”。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林尚立教授認為,“侯官文化”雖然是地域文化,卻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是中華優秀文化在華夏大地開枝散葉結出的果實。“侯官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受人敬仰的文化現象,最重要的不在于孕育了一批歷史名人,而在于所蘊含的精神特質體現了中華文化精髓。其中最鮮明的一點就是將個人之小我同國家、民族之大我統一起來,時時處處以國家為大、以民族為重。
中央黨校許耀桐教授認為,以林則徐、嚴復為代表的侯官先賢愛國主義精神中,蘊涵有崇高的理念宗旨,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層面。“侯官文化作為地域性文化,能夠如此集中、全方位地體現出愛國主義的偉大精神,這是非常獨特和難能可貴的現象”。“嚴復八大譯著”蘊藏著同一個指向:如何讓中國人凝聚并團結起來。
概言之,侯官文化具有愛國自強、開放包容、敦厚務實的精神特質,在中國近代史乃至中華民族復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此,侯官文化有著鮮明的現實意義。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