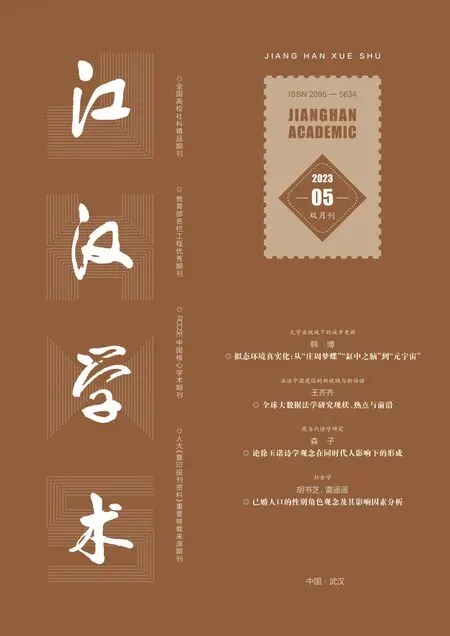“詩歌形式史”與林庚新詩觀念的演進
熊 威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048)
在林庚詩歌觀念的發展中,“形式”無疑占據一個重要位置。這一點,不僅體現于他關涉新詩問題的思考,更見于他對古典詩、新詩這樣一種整體歷史的敘述。不過,與胡適儕輩所依傍的進化論文學史模式不同,林庚通過溝通、比較新舊文學,提出了文學形式不斷承續環復的假設,其背后折射的歷史相對主義態度實際上可以看作是對胡適們的反撥。林庚敏覺于1930 年代新詩主要面臨來自“散文的壓力”[1]19,因此如何化用古典詩歌遺產,調適新詩的“尖銳”“偏激”,進而修復“詩的本色”,就成為林庚展開思考和實踐的現實前提。
學界以往的觀點,多將林庚窄化為一個“格律”論者,放在“格律與自由”或“古典與現代”的二元框架中辨析,而鮮從林庚初始持有的詩歌史視野出發,去考衡其新詩形式觀念的演遞邏輯。誠然,在林庚后期的詩學探索中,具有明顯的朝向“格律”偏至的色彩,但也應留意到,林庚后期所呈現的詩歌觀念,與其早期的詩歌觀念始終內在地連通著,并未脫節。
一、形式的詩歌史觀:以循環為模式
1946 年,林庚撰成文學史第四編《黑夜時代》,次年5 月,與前三編《啟蒙時代》《黃金時代》《白銀時代》總成一部《中國文學史》,交由廈門大學出版。根據書中自序,其“計劃寫一部文學史”的構想可追溯至十二年前[2]。在這本“拿詩為核心”[3]的林著《中國文學史》中,著者揭橥了中國文學史主潮的起伏,即從“詩的散文化”到“詩的形式”這樣一種循環圖式,如:
《九歌》的成功,使得詩的散文化又回到詩化來。《詩經》原是一種較平穩的形式,經過一次散文化后,雖然打破了詩的形式,卻獲得更多新奇的表現;如今再回到詩的形式上,便成詩的詩了。[4]63
駢文到了唐代,本已是強弩之末,散文的再起,原也是意中的事。[4]216
不難看出,林庚認為在中國文學史的發展中,存在“詩的散文化”和“詩的形式”兩種力量或趨勢的消長。每當“詩的形式”臻于完善而封閉時,就需要接受“散文化”洗禮,從而容納更多的時代感性,激發詩的活力;而當“散文化”湮滅詩的本色時,形式的回歸就顯得迫切而必然。以《詩經》為例,它的“四言詩”形式在其時代占據了主導性地位,同時也由于這種主導地位的要求被規范化,久而久之則變得空乏,不足以表達“百家爭鳴中戰國時期的思想感情”[5],因此,諸子散文和楚辭的興起相對于穩固的“四言詩”形式來說,擴展了表現力,構成了形式的“刺點”(punctum)[6],是文學發展上的關鍵一步。
作為一種理想化的“理論假設”,林庚所提供的這種“形式的循環圖式”,含有較大的對歷史簡化的成分和某些想象的樣態,這本不足怪,但了解這一圖式對于我們解析林庚詩歌觀念的進路卻十分必要。事實上,就在林庚計劃構想寫一部文學史的同年(1934 年),他的第一篇重要的新詩論文《詩與自由詩》也發表于《現代》第6 卷第1 期,文中表達了如下立場:
自由詩也許有一天會命運終結,那便是它完全宣告成功的時候。類乎傳統的詩也許會重又生長起來,那便也得要等到這一天的到來!以后呢?是又是一個自由詩的時代嗎?又是一個傳統詩的時代嗎?[7]10
自由詩、傳統詩構成了一對彼此消長的趨勢和力量,詩歌發展的歷史似乎就在自由詩、傳統詩兩種形態之間循環運動,既不可離分,也表現出變化之中隱約可預判的性質。
林庚認為,西方19 世紀后半葉浪漫主義高潮過去之后,“象征派等自由詩體在法國接踵而出”,繼而“自由詩便以其代表了一個新方向的追求,影響于全世界的詩壇”[7]7。而從自由詩逐漸取替傳統詩、繼而占據主導地位的過程來看,傳統詩由于“一切可說的話都概念化了,一切的動詞形容詞副詞在詩中也都定型了”而失去表達的新意和活力,所以自由詩“應運而生”,通過開拓利用語言上所有的可能性,使得一些新鮮的語辭和語法得到無限變化,“追求到了從前所不易抓到的一些感覺與情調”[7]9。由此可見,林庚對自由詩的“新意”“新鮮”和“感覺”“情調”的關注,是切入文學活力生長消衰這一層內因上,其中隱含了對詩歌本質、詩歌形態、詩歌功能的認知。換言之,無論是在古典文學史階段還是在新文學史階段,傳統詩和自由詩都同時存在,它們各自代表了一種風格和姿態,二者循環轉遞,缺一不可,區別僅僅體現在某一時期誰占主導地位[8]。
不得不說,林庚的這種整體、變通的歷史眼光使他出離了“新”“舊”規則的支配,而確立了他自步入新詩研究之初便一以貫之的立場:即以形式的循環史觀為預設,將文學的重述放在文學形式與文學活力的消長變動上。其之后的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基本可視作在此“詩歌形式史”觀念的根株上散葉開花。對此,冷霜也早有覺察,認為“林庚有關詩的認識重點從一開始就放在形式問題上面”[9],“他(林庚)從寫格律詩之初就有一個詩歌史或者說詩歌形式史的觀念框架在支撐他”[10]。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形式”在林庚這兒,并不只是一個勻停在文本表層的形而上學概念,而是具有形式與內容融合傾向的歷史性概念:除了指代歷史上的“四言”“五言”這樣的定型言數體式和一般的韻律因素之外,還包括語言的詩化、模仿和創造,風格的興起、衰敗和復興等等。
五四以降,隨著西方史學觀念的輸入及近代教育制度的遷變,有關文學史的撰著不絕如縷。其中,新史學對文學史的一個重要影響是產生了如胡適的《白話文學史》(1928 年)和《中國新文學大系》(1935 年)這樣的集中體現了“進化論”文學史觀的著作。但是林著《中國文學史》里邊鋪設的思路顯然有別于胡適:一概淡化了社會外部條件如朝代紀年、人物生平等基本史實,轉而注重文學系統自身的自律性和文學形式的審美判斷。職是之故,林著《中國文學史》在出版后引起了一些微辭,如“這本書的精神和觀點都是‘詩’的,而不是‘史’的”、“用文學史來注釋他自己的文藝觀”[11]。不過,在筆者看來,林庚的這種強調文學形式在文學內部循環遞轉的闡釋框架,自有其恰切和特色之處。
陳國球曾經引述維柯的觀點,認為林庚的《中國文學史》的論述模式是“一種以‘詩性智慧’或者‘詩性邏輯’進行的書寫”,類似初民認識自然一樣,以“生之驚異”和“宇宙的驚異”來追寫文學史和作出聯想。[12]實際上,把循環看作構造世界、歷史的認知圖式,原本即是中國思想早期塑形的基本思維之一,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周易·復·彖傳》)、“反者道之動”(《老子》第四十章)、“一陰一陽之謂道”(《周易·系辭上》)、“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不勝枚舉。林庚的文學史特色即在于化用了“循環”思維,這分別體現在“一元復始”和“二元循環”兩個方面:前者,近似于西方神話中文明的循環往復,中國文學史總體上被林庚表述為“啟蒙時代—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黑夜時代—文藝曙光”①的終點即起點的圖式;后者,則是在具體的文學形式和風格上,被林庚表述為“古典”與“浪漫”的交替、詩的形式與散文化的交替、“新鮮”與“成熟”的交替、“質”與“文”的交替等等。
可以說,正是依借于“循環”的詩性思維邏輯,林庚“否定了關于文學形式一次性興亡的假設,提出了文學史是一個不斷承續、回復和沉淀的過程”[13]。因而我們了解了林庚的這種循壞結構模式的形式史觀念,對于我們從新文學史的段落上理解林庚的新詩創作和詩學思路的演進,是一個起點和幫助。
二、從自由到韻律:“自然”的調適
1934 年秋,繼第二部自由詩集《春野與窗》出版后,林庚的新詩創作開始了由“自由詩”向“韻律詩”轉變。造成這一轉向的動機,與其說是出于對自身既往寫作“甘苦”的一次調校,不如說是表達對邇時彌漫詩壇的散文化風向的“不滿”。縱觀自胡適啟曙以來的白話新詩的發展,“散文化”一直處在新詩輿論中心,縈繞未去。若根據朱自清對新詩第一個十年粗略勾勒的圖貌來看,似乎存在一條從“散文化”(自由詩派)到注重“形式”(格律詩派、象征詩派)的軌轍。[14]但實際上,以聞一多、徐志摩為代表的格律詩派,嘗試通過假借外國詩體改造中國詩、使之“勻稱”“均齊”的同時,也引起頗多疵議,最終僅僅作為與自由詩并行的一體而存在,而稍后的象征詩派更是傾力在詞語的聲色和感覺的自由聯想上。于是一時之間,新詩的“規律運動卻暫時像衰竭了似的”[15]。這其中的原因,除了新詩自由、逐新的天生結構外,還受制于急切變動的現實的吁求,尤其迨至九一八事變之后,新詩為了訴諸大眾,配合政治和宣傳的需要,不可避免又沖擊、反抗“新月派”和“現代派”,“散文化的傾向很重”[16]。因此,如何祛除來自“散文”影響的焦慮和另辟爐灶、摸索一套建設“新詩陣地”的行之有效方案,自然就成了林庚的思慮重心。
依林庚看來,自由詩“對于傳統的文言詩壇也正如同一場革命”,但是由于缺乏相應的建設,詩壇出現了分化,要么“愈來愈不自然”,要么“失去詩的本色”,新詩陷入了“除了分行之外別無陣地”的困境。[1]19不言而喻,對于新詩這一困境的辨識顯示了林庚清晰的問題意識。恰如俞平伯早在林庚的第一本自由詩《夜》(1933 年)中指出的:“他不贊成詞曲歌謠的老調,他不贊成削足適履去學西洋詩,于是他在詩的意境上,音律上,有過種種嘗試。”[17]與發軔于1930 年代的新詩寫作實踐近乎同步,林庚對于新詩的檢討和理解,立足于一個較為穩固的“形式循環”觀念的支撐,故他對自由詩和韻律詩的理解,既沒有陷入“新”“舊”之爭的窠臼中,也跳脫了自由和格律二元對立的思路陷阱②:
自由詩的重要并非形式上的問題,乃在他一方面使我們擺脫了典型的舊詩的拘束,一方面又能建設一個較深入的活潑的通路……警句與天然永遠是兩個方面——當然我們不能說哪一種比較更好——若可以說自由詩代表的是前者的性質,則韻律的詩當是近于后者了;這二種詩體中無論哪一種,其單獨的發展結果則前者必流于“狹”,后者必流于“空”,都是衰亡的思路。故自由詩在今日縱是如何的重要,韻律的詩也必有須要起來的一天。[18]11
在林庚看來,自由詩和韻律詩各自只能代表詩歌發展的一個方面,各有優點,如果偏執一端極度發展下去,勢必形成前者的“狹”和后者的“空”,因而枯竭了自身。這實際就是對詩壇已產生分化的困境的變相表述。有意思的是,林庚在此處撦挦出自由詩和韻律詩的兩種性質,或者說,兩種維度:“警句”和“天然”。
表面上看,“警句”和“天然”似乎是林庚有些“率爾”地將古典文學的審美風格和新詩的詩體牽引到一起,因為和詩體比起來,文學風格更多跟作者的人格修養和語言表現相關。但這種貌似“率爾”實則表現了林庚詩學話語構造的特點,由于他將新詩和舊詩放在一個水平上,更由于他對古典文學運用裕如,所以很多時候,他討論新詩時的例證幾乎全從古詩文取得,或者干脆移植古典文論中的術語闡說新詩。在一定意義上,林庚這種援古證今的詩學表達,可能會將他推到一個關于普遍的詩的觀念上,但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他“以古律今”,時有保守、開倒車的嫌疑。③不過真實的情況始終還在于我們閱讀林庚的原意。至少,在《詩的韻律》中,林庚論證的重心是自由詩向韻律詩轉變的依據,包括歷史鏈條的合理性和韻律詩自身的優勢。之所以用“警句”和“天然”區分自由詩和韻律詩,大概是采取一種相對簡化和好接受的方式來為韻律說項:
……為什么既有了自由詩又仍不能忘懷于韻律呢?
自由詩好比沖鋒陷陣的戰士,一面沖開了舊詩的約束,一面則抓到一些新的進展;然而在這新進展中一切是尖銳的,一切是深入但是偏激的;故自由詩所代表的永遠是這警絕的一方面……于是人們乃需要把許多深入的進展連貫起來,使它向全面發展,成為一種廣漠的自然的詩體。[18]15
“尖銳”“偏激”“警絕”,幾個與“警句”家族相似的詞匯反復標出了自由詩迥異于韻律詩的特性的強度。與其說,這些詞匯的拈取來自林庚對自由詩的自覺證悟,不如說,這些詞匯是出于詩學策略的一次“站位”,它們并不是孤零零的,而是本著與“天然”對質的使命為韻律詩“勾兌”和“計劃”出來的。林庚的關切點即在于利用“警句”和“天然”之間的反差效果放大韻律詩的長處,所謂“廣漠的自然的詩體”,也作為一種方案上的調和被納入到韻律詩的詩學框架中:
這種“詩體”,姑名之曰“自然詩”;如宇宙無言而含有了一切,也便如宇宙之均勻的,從容的,有一個自然的,諧和的形體;于是詩乃漸漸的在其間自己產生了一個普遍的形式。[18]15
這是“自然詩”首次以概念命名的方式出場,在此之前,林庚發表于1935 年2 月《國聞周報》上的《極端的詩》一文,可以視作“自然詩”的先引。
在《極端的詩》中,林庚指出,無論小說、戲劇、散文如何與詩分不清,卻不會混進極端的詩里,“極端的詩指那支持了詩而使它仍與其他作品有別的特質”[19]。可見,“極端的詩”的樞要在詩的特質上。林庚通過釋說不同文學體裁對于生活反映的不同姿態,得出比較:小說、戲劇是以人生中特殊的事情或想象吸引讀者,讀者雖然入迷,但也清醒自己并不在里邊;散文作品中的作者往往即是主角,主角和讀者的距離仍是拉開的;因此,只有在詩中,作者、主角和讀者之間不存在距離,是“三位一體的成功”,是能與生活合二為一的,是“如春風之與草原,在不知不覺間,自然的綠色千里了”[19]。“極端的詩”的“自然”特質正是在這個意義層面被提點出,它既具備充足的詩質,又無聲無息,使人易于接受,不留下教化的痕跡。而且我們可以從林庚為“極端的詩”和“自然詩”同樣從詩與宇宙的關系立論的角度,理解它們的共通性:
宇宙永遠是無言的,宇宙卻又在無言中啟示了人們,詩是宇宙的回聲,而詩的彌漫乃也正像宇宙是在每一個人心頭……詩是宇宙的代言人,它不討論什么,不解決什么;它只如宇宙之有著一切……[19]
林庚認為,宇宙的無言、無邊與渾然的性狀,是可以同構于詩的諧和和自然上。宇宙含納萬物,雖有若無,詩歌則以宇宙、生活本來的面目言說,“好像這首詩不是從外邊來的,乃是早已藏在我們的心中”[18]16。林庚這種詩與宇宙同構的觀念,可以說,是取法于中國古代哲學以“道”為本源、“道法自然”的宇宙論,宇宙循環變化,詩的存在“與宇宙氣數相關”,“合乎天地自然之節”。[20]
除了運用與“自由詩”對質的風格(如從容、自然、諧和)對“自然詩”進行描述外,林庚還從自然詩的外形、葉韻的角度進行說明。他認為:“自然詩的價值是自然,故其外形亦必自然,外形的自然則自由不如韻律。”[18]15換言之,自然詩由于韻律的存在,比起驚警緊張的自由詩在形式上更具“自然性”;隨后他又以民歌中的起興為例,認為諧韻能夠祛除所詠事物之間的跨度,如“梔子花開心里黃”與“三縣一府捉流氓”,本來毫無干系,一葉韻便讀得十分自然。值得注意的是,林庚雖強調“韻”的自然性和重要性,但并不等于認可只要葉韻的詩就一定是自然詩,而是葉韻要和詩的內質及外形、風格全部統一起來。誠如張桃洲指出的:“林庚所說的‘自然詩’,是一種超越了自由和格律表面對立、囊括了多種因素的詩體,而作為‘自然詩’之核心的‘韻律’,則是一個既包含外形、同時更具內質的范疇。”[21]
鑒于“自然”概念在傳統詩學中的多異性、變易性和整體性的特點,以及在早期新詩詩論中,“自然”之說已廣為流布的事實,這里,有必要簡單回溯一下新詩的“自然”論說:1919 年,在《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中,胡適以“詩體大解放”為目的,闡說了新詩的“自然的音節”,其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句子節奏按照意義、文法自然區分;二是詩的聲調平仄、用韻要自然。[22]此后,“自然的音節”迅速得到其他擁躉者的展敘,一方面,將“自然”與“自由”對標、為自由詩編織合法的文體依據是他們的共同立場,另一方面,在“自然”內部的細讀上,又各自不盡旁逸。如康白情認為,“情發于聲”自成文采,即為自然的節奏,實是肯定了“情感”對于“自然音節”的重要[23];俞平伯則認為“作詩,只須順著動機,很熱速自然的把它寫出來”[24],明顯使“自然”帶有自發性色彩。與此同時,身受西方浪漫主義感召的郭沫若,主張“自然即自我”,提出了“詩之精神在其內在的韻律”、“內在的韻律便是‘情緒的自然消漲’”[25]的主情主義觀點,“自然”的落實同樣質押在情感上。因此,總觀早期的“自然”觀念并未助益于新詩更為謹嚴的“形”與“質”的探求。
筆者以為,林庚的“自然詩”的提出,一方面顯出了其敏銳洞察新詩之“狹”與“空”的危機,通過征用“自然”這一傳統美學中的元范疇,以自然無為、“詩法自然”的辯證統一思維將自由詩和韻律詩引入到一種能夠對話的共同體上,避免了各執一端的體力消耗,無論是對寫作者還是讀者而言,都意味著必須要有更耐心、更從容的心智,來涵育和理解新詩的這一變化。同時,就另一方面來說,由于“自然”本身可闡釋的空間巨大,林庚依其表達自己的觀念時,把“自然詩”當作全部歷史中“詩的理想”境界,不僅宗附著一層神秘的、詩意的和懸想的色彩,而且經常與一些本應區別的其他概念糾纏互滲,導致了它一旦觸及形式具體邊界的討論時,或者說,當以它作為寫作方法時,常有前后不鑿枘、名實不符的地方。故而,自1937 年過后,“自然詩”已不知不覺在林庚的詩學表達中“退場”,林庚轉而從較為科學、理性的層面分析形式要素的組合。但如果從林庚勾畫的新詩發展邏輯上看,“自然詩”實應屬于“自由詩—韻律詩”之后的更完熟階段,所以更大的可能是,林庚在遭遇到“理想和現實”的頓挫后,反思了自己的“躍進”而有意先回到建立“韻律詩”的“普遍形式”這一階段。因此,對于林庚而言,自然詩并未破產,而是完成了它準備性的任務,其形式的內核也將以另外的線索表達出來。
三、形式的中心環節:建行與詩化
在1936—1937 年為國立北平師范大學編寫的教學講義中,林庚以當事人的身份檢視了新文學史脈絡,指出“新月派形式的嘗試已經失敗,詩壇上正缺少一種形式”,新詩的發展“關鍵在于形式的生成”[26]30。如果以林庚同期創作出版的兩部詩集——《北平情歌》和《冬眠曲及其他》——作為觀照的話,其中形式的統一性(如最突出的特征是采用四行、言數整齊、葉韻)幾乎可以看作他詩學追求的主題,并且在具體每一行的言數上,他分別進行了“八字詩”“十字詩”“十五字詩”“十八字詩”等嘗試,得出了較為真切的體悟:
四行不過是起碼數,長了八行,十二行也無不可……之后我又搜集了許多別人的詩,才發現凡念得上口的多是五個字與三個字,而三個字則往往要附在五個字前后。[27]
這些由理論和創作互動延伸出來無論是行數、還是言數的觀念,它最終標的即為林庚汲汲營營的“普遍形式”,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林庚往后探索“詩行”構造的前提。
不同于將“詩行”看作詩的一句或一行的一般認識,在林庚看來,“詩行”就是“普遍形式”,是“在一切語言形式上獲取最普遍的形式”[28],其它要素諸如韻和平仄,只是形式的附加特征,而非詩歌形式的基本規律。林庚通過考察中國古詩的普遍形式發展成型的歷史,認為五七言詩作為“詩行”的問題,過去一直被行與行的問題遮蔽:比如中國近體詩中的律詩規定一首詩要八行,中間的四行要求對仗,同時行與行之間平仄必須相襯;而在新詩里邊,既有五行一段的,也有三行一段的,還有長行和短行相互之間調配的,“總之所注意的都是行與行的問題”[29]。基于此,林庚提出回到五七言詩的形式問題上來,把目光集束于詩歌語言節奏內部,從建立詩行的基本工作開始做起。
反觀既往的新詩形式運動,如饒孟侃、聞一多等,在關于新詩語言節奏的問題上,均有試圖將西方的“音步”或“頓”概念移植中國詩行的嘗試。不過,這些嘗試似乎由于“駕馭文字的力量不足”[15]763,路徑偏窄,或者用林庚的話說,沒有抓住“真正的形式的命意”,不可避免流于失敗。為此,在1948 年8 月刊出的《再論新詩的形式》中,林庚首次用“逗”的概念闡說自己對于詩歌節奏的理解,他從歷史中的《楚辭》尋求例證,認為“兮”字類似于“逗”(pause)的作用,使楚辭取得了詩行的節奏,故而“一個詩行在中央如果能有一個‘逗’,便可以產生節奏”[28]41。林庚通過把四言詩、五言詩、七言詩從整行中依“逗”劃分為“二·二”“二·三”“四·三”,指出“逗”是中國詩歌形式上的普遍現象,并且“逗”的位置標出了不同詩體之間的音組變化。
1957 年,林庚進一步完善了先前關于節奏“逗”的認識:
事實上中國詩歌形式從來都遵循著一條規律,那就是讓每個詩行的半中腰都具有一個近于“逗”的作用,我們姑且稱這個為“半逗律”,這樣自然就把每一個詩行分為近于均勻的兩半。不論詩行的長短如何,這上下兩半相差總不出一個字,或者完全相等。[30]
通過“半逗律”,詩行近于均勻地分割,其中,“逗”的位置就是“節奏點”的絕對位置,不可移動,如五言必須是“二·三”而不能是“三·二”,七言必須是“四·三”而不能是“三·四”;至于“節奏音組”,它始終“作為‘半逗律’劃分的下半行”[31],決定著詩行成為幾言的形式。這樣,圍繞著建行問題實際化歸出兩條定律:一是“半逗律”的普遍性,二是“節奏音組”的決定性。
毫無疑問,“半逗律”和“節奏音組”標志著林庚建行理論的成熟。林庚的目的也正在于模仿古詩,在新詩系統內部中創設一種或幾種具有穩定性和生產性的范式。由于它對于鮮明節奏的嚴格規定性,也形成了林庚詩行的特色:行式均齊、內部節奏一致。對照起來,它與陸志韋的“五拍詩”以及聞一多的“字數整齊方見出節奏”在建立定型詩行的目的和外形呈現上似乎大同小異。
縱觀百年新詩史,林庚焦思苦慮的“建行”理論,不啻獨步一時,但在歷史效力的驗校中,基本共享了以往新詩形式運動的困境。在這背后,新詩形式的建設是否應該僅僅被還原在節奏問題上,抑或形式在新詩中的定位是功能性還是本體性的,以及語言現代化、語言思維和形式到底是什么關系等話題,都值得我們深入去思考。不過,我們也應當注意到,在林庚所探照的“普遍形式”圖景中,“建行”固然重要,但與此相關的“詩化”命題,則使詩行回到語言的肉身上來,為其形式觀念敞開了更為豐富的面向。
在林庚看來,詩化就是詩歌語言突破生活語言的邏輯性和概念的過程,包括詩的句式、語法和詞匯的詩化。[32]如前所述,不論是歷史上的五、七言詩,抑或新詩中的定型詩行,它們都是從散文化的時代逐步建設起來的,所謂“建行”,也就是詩的句式,它的成熟僅是“語言詩化的最表面的一個標志”[33],如果沒有語法和詞匯兩個方面配合——前者使“語句更精練、更自然、更解放”,后者表現為對新鮮事物的敏感、吸收和創造——那么,一整個的詩化也就不可能完成。林庚通過對建安時代到唐代約近四百年詩化歷程的考察,厘清了語言詩化的兩個主要標志:一、在一般語言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特殊語言,如齊梁五言詩一律省掉了散文語言中必不可缺的虛字、唐詩中省掉了動詞,這樣的精減法對于語言來說,既自然,也使語言更精練、靈活;二、從《詩經》的起興到山水詩的活躍,語言的形象性和豐富性獲得加深。
盡管林庚尋繹的對象是古詩,但他所展開的一種把詩歌發展的深沉歷史感和語言的藝術性糅合一起、同時將新詩與古詩“其內里最核心的”[34]“詩化”機制交互證詮的思路,無疑具有啟示新詩的意義。林庚認為,詩之所以成為一種特殊的文體,就在于“它有它獨特的形式——獨特的語言形式”[35]31。顯然,結合1930—1940 年代林庚意欲為新詩“建立陣地”的現實觀眺來看,林庚對詩歌語言形式特殊性的強調,與散文化的詩壇風氣對新詩語言形式的籠罩、逐斥有關。在林庚看來,詩歌語言和散文語言的區別主要體現在“詩的跳躍作用”上,因為憑借“跳躍”,“詩的文字比散文更不受邏輯的束縛”,“不但打破了邏輯的束縛,同時卻還建立一個更解放的語言”。[35]34
詩的“跳躍”在后來又被林庚表述為“語言的飛躍性”,即通過形式的節奏,從日常語言中萌發出特殊的語言,捕捉到日常語言中難以捕捉的新鮮感受,“使語言中感性的因素得以自由浮現”:
若沒有感性潛在的交織性,語言上的飛躍就無所憑借,沒有飛躍性的語言突破,感性也就無由交織。詩人的創造性正是從捕捉新鮮的感受中鍛煉語言的飛躍能力,從語言的飛躍中加深自己的感受能力,總之,一切都統一在新鮮感受的飛躍交織之中。[36]122-123
可見,語言的飛躍性和感性是語言的一體兩面,不可分割。由于散文注重行文的邏輯性和連續性,不覺間制約了語言中蘊含的感性因素,而詩恰恰是需要鮮明的感性的,所以詩歌的藝術性在于它能夠充分地發揮語言的飛躍性來恢復原有的敏感,“這敏感正是藝術的質素”[36]119。新詩的之難,注定要在處理現代經驗的向度上,使語言從沒有感覺(或自動化、無意識化的感覺)的“物的死亡”中,走向復活。從這個角度上看,詩化就是突破概念性和邏輯性的窒礙,通過豐富感受的交織,使詩歌結晶成“立體的語言形式”。
事實上,與詩化相關的對于“新鮮的認識感”的推重,早在林庚初始創作新詩時即顯蹤跡。林庚的同時代好友李長之在評論《夜》與《春野與窗》時,曾十分驚醒地點出林庚的詩作特質:“林庚之看重感覺,從而看清詩人的貢獻和天職”[37];“所謂靈感,所謂跳,就是林庚所自己意識到的‘感覺’”[38]。作為1930 年代生活在北平的“邊城”知識分子,林庚在“氣氛異常壓抑”的生存處境中,沒有陷入“沒落”或“絕望的毀滅感”[39],反而以充沛的精神狀態呈現出“一個新的蓬勃和崛起”[40]。由此想來,林庚的詩學觀念恐是其向上執求的生命意識的一種寫照,或者說,他的人生追逐中始終續存著清潔的詩歌精神的溉濟。
四、結語
新詩歷史已屆百年,如何妥善地從傳統中尋繹對話性經驗、進行創造性轉化,始終是新詩繞不過去的一個嚴峻課題。林庚的詩學意義在于,以宏通辯證的詩歌史視野,重新體認、回接漢語傳統,展開新詩形式、語言的本體建構。由本文的論析可知,“形式”作為林庚一以貫之的核心主張,不僅表現為形式的循環這一歷史認知圖式,還包括建行、詩化、風格和語言的創造等面向的設計及討論。回溯胡適及其擁躉在新詩語言革命時期散播的“形式以自由詩為主體”的白話詩理念,林庚在1930 年代意圖對新詩展開的本體建構,表面上看是形式革命的進一步深化,實際上是在縱深的文學史視野中,改革人們對于新詩“功能”和本質的認識。但遺憾的是,林庚的詩學構想雖富于創見,卻無法從一種被限定的歷史條件中解放出更活泛的動能。由此延伸出的一個問題是,在中國新詩形式探索的過程中,對于不同文化資源、經驗的征引,是否在塑造了新詩內景和評判尺度的同時,還依然伏藏著更深層次的問題?也許詩作為“人類的母語”,在本性上,注定要同人類的歷史境況一起,繼續“學習新語言”“尋找新世界”。盡管如此,林庚等前輩學人將文學的審美歸之于語言形式的真實有效的驅力,確已深刻影響到我們對于新詩活力的遷移和樣態創造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