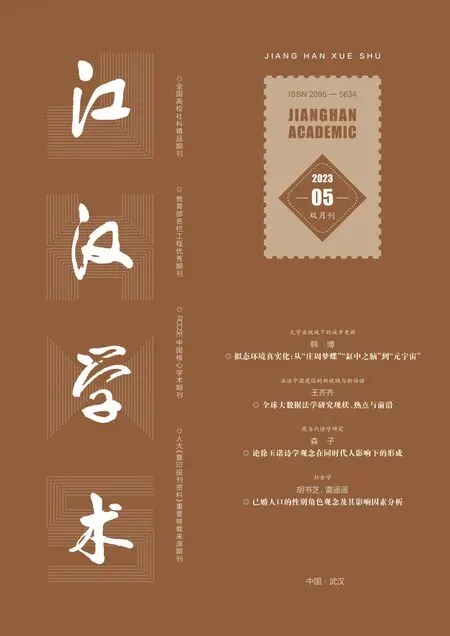擬態環境真實化:從“莊周夢蝶”“缸中之腦”到“元宇宙”
韓 博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北京 100021)
一、問題提出:萬物皆“元”視域下的紛爭與媒介進化視角
一個幽靈,元宇宙的幽靈,在人類世界游蕩[1]。
近年來,幾乎所有大型互聯網公司、科技公司都進行了平臺建設投資。在國外,2021 年3月,“元宇宙第一股”Roblox 上市,取得了優異的股票市場表現,“元宇宙”概念開始引人關注。2021 年10 月,Facebook 更名為“Meta”,打造元宇宙平臺,帶動了資本風向。在國內,幾乎所有知名的互聯網公司都參與到元宇宙“爭奪戰”之中。字節跳動收購虛擬現實設備公司Pico,網易建立了“瑤臺”,百度推出了“希壤”,阿里成立了XR 實驗室,騰訊參與了Roblox 的1.5 億美元G 輪融資。隨著大量資本的涌入,各行各業進軍元宇宙的大幕徐徐拉開,各種“亂象”也隨之出現。有防水公司提出“元防水”概念[2],有商業公司建立“元未來家族”,其核心產品為單價9.9 元的所謂“元宇宙令牌”[3]。雖然元宇宙離最終形成還相距甚遠,但“炒房”概念已經在虛擬空間中悄然流行,一款名為“虹宇宙”的社交元宇宙產品所發布的虛擬房產被掛在閑魚上“銷售”,價格最高的一套達到99.99 萬元[4]。
回歸傳播學研究,不少學者圍繞元宇宙進行了大量討論。方凌智[5]從技術變遷的視角探索了元宇宙的概念,認為元宇宙是未來互聯網發展的“終局”,應該從技術與人文兩方面構建元宇宙。杜駿飛[6]提出“數字交往”論,聚焦未來人類在元宇宙中的生存方式:跨體系、變維、多重分身的生存模式(MDSs)。胡泳[7]聚焦未來的傳播形式問題,認為未來的傳播是“元傳播”,即“傳播的傳播”,并設想了基于語境、聲音、化身、環境的未來傳播形式。
一時間,看天下,萬物皆“元”。從業界到學界,都在暢想元宇宙的未來發展模式,但針對元宇宙本身的探討卻依舊不夠[8]。這出于以下幾點原因。首先,誰都沒見過元宇宙,目前的所有理論都只是對未來元宇宙的“想象”。不論對元宇宙有多大的肯定,絕大多數研究者都意識到,不管是受技術限制還是人的觀念局限,現階段元宇宙并未真正實現。因此,研究者只能從多種方向進行探索,以期描繪其未來形態。其次,許多研究者引用《頭號玩家》《失控玩家》等影視作品作為重點案例進行研究,這是人類目前能想象到的較為符合元宇宙概念的影視化描述,Facebook 的虛擬元宇宙平臺所使用的用戶VR 平臺“綠洲(OASIS)”就與《頭號玩家》中的游戲世界同名。從案例展示的元宇宙實現過程來看,這是一種線上身份登錄的設定,因此“具身”“化身”受到了格外關注,作為人在虛擬空間的延伸,麥克盧漢的“媒介是人的延伸”更是必選理論。麥氏的理論充滿了作為人的“驕傲”,符合人類的“尊嚴”選擇。從屬關系上,媒介從屬于人;控制論上,人是媒介的使用者。如果3D 互聯網就是元宇宙的終極形態,人類能清晰感知媒介作為“物品”的存在,那么麥氏理論仍能完美適用。但隨著腦機接口等技術的逐漸成熟,“可聽、可看、可感”的元宇宙形態并不是不可期待,那時,誰是誰的延伸呢?“具身”“化身”等概念還有意義嗎?
面對一個未曾出現的新鮮事物,早期的“盲人摸象”是發展的必然階段,基于現有理論進行充分想象并提出新理論是必然路徑。面向元宇宙,有三點是清晰的:一、元宇宙是人創造出來的虛擬環境。二、元宇宙是目前的主流媒介——互聯網的下一步發展目標,與媒介發展有連貫性,傳承有序。三、元宇宙的“元(Meta)”是“超越”之意,既然要超越,首先要一致,“真實化”應是元宇宙未來的必備屬性。基于以上三點,本文認為,立足于“虛擬—現實”關系的擬態環境理論更加適用于未來的元宇宙研究,從該視角出發,結合媒介發展歷程與技術特點,可以探討擬態環境的未來發展趨勢與面臨的挑戰,為拓展擬態環境理論、未來元宇宙治理提供借鑒。
二、“現實—虛擬”環境的映射:擬態環境理論的立場與發展
在今年回顧擬態環境理論有不同尋常的意義。一方面,2022 年是擬態環境理論提出的100周年,經歷百年歷史,探討人為構建信息環境的擬態環境理論已經演變為傳播學的基礎理論之一,其廣泛的適用性與分析的實用性受到了廣大研究者的認可,從報紙、廣播電視研究到微博、微信、客戶端等新媒體研究,其影響力無處不在;另一方面,元宇宙以高技術含量、智能化為特色,為擬態環境理論提供新研究對象的同時也提出了新問題:針對未來的媒介環境,擬態環境理論應以何種視角繼續拓展以適應不斷發展的媒介?回顧百年,展望未來,本文將從擬態環境理論的基本立場出發,探討其核心要義與發展規律。
擬態環境理論學界有很多“前輩”,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擬態環境理論的前身,最著名的是柏拉圖的“洞穴隱喻”及其背后的“摹仿論”。該隱喻講述了一群背對洞口且渾身無法動彈的囚徒,通過身邊火炬映射出洞外的影子來認識外在世界,這些影子是受一群人操控的,他們讓洞穴人看到他們想展示的東西,最終洞穴人將影子代表的世界當作真實世界,并且不愿意相信還有其他更加真實的世界[9]。“洞穴隱喻”指向柏拉圖的“摹仿論”。“古希臘……經典作品的傳統,認為藝術即摹仿”[10],而這種摹仿在柏拉圖看來包含對自然的鏡像式復制、對自然的想象性再現,二者相結合,使摹仿行為本身具備了人造特性。模仿往往不是“按照真實的比例,而是按照看上去美的比例”[11]進行的,其得出的結果是一種“騙人耳目的視覺真實感,……與想象分不開”[12]。在柏拉圖看來,人的藝術產出是對理式的兩度離異而產生的影像,而非“真形”,朱光潛的《西方美學史》、繆朗山的《西方文藝理論史綱》等,都將它視為對現實的“臨摹”[13]。從摹仿論的角度來看,洞穴隱喻形象地提出了兩個核心觀點,首先是區分了虛擬世界與真實世界,提出了人認識世界的局限性。人們通過“投影”認識世界,“通過‘間接的方法’而達到觸及‘太陽’(對象)的認識,這種認識只是把握到‘太陽’的‘影響(或者相似)’而不是‘太陽(原像)’本身”[14]。這樣的世界是“虛假”的。其次,“影子(人們認識的世界)”是可以操縱的。既然影子的表現受一群人操控,那么人們對世界的印象也是可以人為“調整”的。從這兩個核心觀點來看,“洞穴隱喻”已經蘊含了擬態環境理論的基本思想。
1922 年,李普曼在《輿論學》一書中提出了擬態環境理論。與洞穴隱喻相類似的,李普曼認為:“回過頭來看,對于我們仍然生活在其中的環境,我們的認識是何等的間接。我們可以看到,報道現實環境的新聞傳給我們有時快、有時慢,但是,我們總是把我們自己認為是真實的情況當成現實環境本身。”[15]1-2在擬態環境理論中,“洞穴人”變成了大眾媒介的受眾,“火炬”變成了傳播媒介,媒介運營者變成了“影子”的操控人。“偶然的事實、創造性的想象、情不自禁地信以為真”[15]11-12構成了擬態環境的基本要素,形成了受眾在媒介影響下的行為模式——在經過媒體“加工”后的擬態現實中感受現實世界,并以此作為依據進行現實世界實踐。至此,擬態環境正式升級成為與現實環境相對應的虛擬環境,其以事實為基礎,但又展示的是經過人為選擇的事實,是一種介于現實與虛擬之間的“半現實”。
傳播學認為人與環境的關系主要有四個基本要素:一是客觀環境本身;二是人對環境的認知;三是人的行為;四是人的行為對客觀環境的反饋或影響[16]。李普曼的擬態環境理論主要對前三者進行了回應,1968 年日本學者藤竹曉在李普曼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擬態環境的環境化”的概念,重點對第四方面進行關注,探討擬態環境作用于人、改變現實的趨勢。“擬態環境的環境化”(另有別稱為“信息環境的環境化”)講述了這樣一個過程:雖然人們看到的是擬態環境,但該環境提供了人們實踐活動所需要的“信息指導”。其中擬態環境中流行的事件會在現實環境中也流行起來,“許多‘擬態事件’包括語言、觀念、價值、生活或行為方式等最初并不見得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進入大眾傳媒渠道,很快就會演化為社會流行現象,變成隨處可見的社會現實”[17]。這一過程使得現實具備了擬態的特點,擬態環境“環境化”了。
從以上兩個擬態環境的關鍵發展階段來看,擬態環境經歷了從媒介環境出發作用于人,進而改造世界的過程,雖然李普曼與藤竹曉研究的重點不同,但基本立場是一脈相承的,都強調媒介對人行為的影響,其核心都是在探討“現實—虛擬”環境的映射問題。擬態環境是人為構建的信息環境,對應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實質上是人們對“身—心”關系的探索。面對“心”中所想,面對印象當中的虛擬世界——人為創造出的擬態環境,人們的想象與認識在不斷發生變化。有時認為擬態環境代表了理想中的精神境界,有時又認為其只不過是人類的創造物,有時又要防止其過于強大以控制自身。
從“元宇宙”等概念出現以及媒介技術的現有發展趨勢來看,最為核心與明顯的變化是擬態環境本身從想象到現實的距離正變得越來越小,甚至在未來有“替代”現實的潛力。未來的擬態環境發展趨勢將超脫李普曼與藤竹曉的“現實—擬態”相互影響關系,構成擬態環境后來者居上的“擬態—現實”替代關系,我將這一發展趨勢稱為“擬態環境真實化”。擬態環境真實化包含兩個變化過程,其一,線性增長過程:由媒介技術、科技進步帶來的擬態環境真實性持續增強。其二,曲線波動過程:對“物質—精神”對應關系認識從漸進到分離的回環往復。
這里的“真實性”,主要指擬態環境與真實物理世界的相似程度。從哲學層面上來看,“真實”存在狹義的“符合論”與廣義的“融貫論”兩種定義[18]。符合論主要以客觀物理存在為基本依存,以可實證性為基礎判斷依據,是一種人類依據物理世界進行對比分析的常識性判斷。融貫論較之符合論更深一層,如羅素指出“‘真的’是一個比‘可證實的’范圍更廣的概念”[19],換言之,可證實是以物理世界為判斷基礎的,如果轉換其他標準為判斷基礎,其他世界亦可被定義為人們認識的真實。而判斷標準的變化是由技術發展帶來的,如物理學進入量子領域后,薛定諤提出,“主體和客體是同一個世界。它們間的屏障并沒有因物理學近來的實驗發現而坍塌,因為這個屏障實際根本不存在”[20]。綜合對真實性的兩種定義,有兩點非常清晰,第一,真實的判斷目前仍以物理世界為基礎。物理世界是人類目前賴以生存的基礎世界也是認識其他世界的基本參照。第二,技術進步能夠帶來真實的增強。隨著技術的發展,其他原本認定為虛擬的世界有可能隨判斷依據的變化轉變為人所認為的真實。在媒介研究領域,喻國明按照馬斯洛的人類需求五級模型提出,媒介功能從低到高應分為信息連接、技術連接、情感連接和價值連接四個發展階段,其中第四階段的媒介可以實現“第二世界”的全真模擬,真正實現元宇宙社會化的同步和映射,現實世界中的價值尺度也能與虛擬世界同步,使每個人都能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價值追求和目標[21],這種“全真模擬”將是擬態環境真實性的最高體現。因此,擬態環境的真實性指對物理世界的呈現程度,技術進步發展是推動擬態環境真實性增強的主要路徑,“可聽、可看、可感”程度是判斷其真實性高低的重要標準。
宏觀上,擬態環境作為與現實環境相對應的存在,其總體覆蓋范圍是“世界級”的,所以也只有考察“世界級的想象”——對于完整虛擬世界的暢想,才能探尋擬態環境的整體發展變化規律。縱觀中外歷史上著名的想象世界,“莊周夢蝶”“缸中之腦”和“元宇宙”可以說是最廣為人知的思想實驗。作為對擬態環境的想象,其思考對象是整個世界,其時間跨度覆蓋古代、現代和未來,從中我們可以探討擬態環境的基本認知變化過程,考察其是否存在真實化的發展變化趨勢。
三、擬態環境真實化:從“莊周夢蝶”“缸中之腦”到“元宇宙”
(一)“莊周夢蝶”:媒介技術匱乏時代的“物我合一”與“現實—擬態”漸進性
莊周夢蝶的故事家喻戶曉。“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爾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22]52簡而言之,莊周睡著了,做夢變成了蝴蝶,以蝴蝶的視角觀察世界,感受特別真實,以至于清醒后分不清自己是莊周還是蝴蝶。莊周夢蝶的故事從自身感知出發構建了龐大的擬態環境,這個擬態環境的名字叫宇宙,包含天地與世間的萬事萬物。
在莊周生活的“前大眾媒體”時代,媒介技術無疑是匱乏的。受科技水平限制,這是一個沒有微信、QQ、視頻通話,甚至連人際間通信都極為困難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擬態環境的構建主要靠兩件事來完成:想象與文字書寫。這是一個“雙重想象”的過程,想象構成了擬態環境的內容,文字書寫確定了擬態環境的最終展示形態。回到莊周夢蝶,想象構成了故事的基本內容。這個故事首先是莊子的想象,他想象了自己變身蝴蝶的過程,想象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其次,這個故事又可以說是后人對莊子的想象。莊周夢蝶出自《莊子·齊物論》,《莊子》一書本身就頗具爭議,學界普遍認為其內容并非一人所做。如顧頡剛認為《莊子》是戰國、秦漢間論道之人所作的單篇文章的總集[23]。書籍本身非一人所著,即使為一人所著,隨著文本在時間長河中的流傳,“編纂修訂”也不可避免。莊周有沒有夢過蝶,做夢的過程,做夢得出的結論,都是由后人所書寫的文字來決定的,甚至連“莊周夢蝶”這四個字都是后人總結出來的,我們現在看到的實際上是后人的“想象結果”。
以書籍為核心媒介的時代,擬態環境的實現是雙重想象的結果,“內容層面的想象+媒介想象”構成了最終的擬態環境,這樣的構成形式有兩方面特點:內容層面的自由性與媒介層面的局限性。內容層面的自由性指的是想象內容的豐富與天馬行空,雖然古代有倫理綱常等各種限制,但想象是自由的,什么都可以想。因此可以變成蝴蝶,可以為鯤鵬,可以變妖,也可以成仙。書中可以有顏如玉,亦可以有黃金屋。而作為媒介的書籍,其本身又有很強的局限性,其核心問題在于為形成擬態環境所提供信息的把關人僅局限于少數人,甚至可以說就是書籍作者本身。作為擬態環境的創建者,他可以修訂、改寫,讓莊周或者別的什么人夢蝶,甚至讓夢蝶的故事徹底消失。面對“骨感”的現實,“豐滿”的擬態環境明顯更有吸引力,精神世界追求(人文理想)高于現實局限有了擬態環境層面的基礎。從這62 個字構成的文本來看,莊周夢蝶的故事并未泯滅于歷史長河中,是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其蘊含的哲學思想是被人們廣泛參考的。“此之謂物化”是莊子對夢蝶故事的最終評價,講的就是人不要局限于人,要與萬物同化,忘掉了自己是自己,融入了宇宙,“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22]39,離“道”就近了。發展到道教,就有了“老子騎青牛而出函谷關,羽化成仙”的傳說——人要走出世俗,融入自然,才能羽化而登仙。
在莊周夢蝶構建的整個擬態環境中,人能夠分清現實和虛擬,現實生活與代表宇宙的“自然”有明顯區別。從擬態環境的視角來看,中國樸素哲學追求的“天人合一”是人向天(自然)靠近的過程,“現實—擬態”有接近性,并且虛擬世界更為豐富、更為本質,是“現實(人)”要靠近的目標。這個過程就是“物我合一”的過程。拓展到西方世界,笛卡爾發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論斷,也是將擬態環境置于真實環境之上。
(二)“缸中之腦”:媒介技術發展時代的“物我二分”與“現實—擬態”延伸性
1981 年,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他的《理性·真理與歷史》(Reason、Truth and History)一書中,闡述了“缸中之腦”的假想:一個邪惡科學家通過手術將某人的大腦保存下來,放到一個充滿培養液的大缸內。連接這個大腦的是一臺超級計算機,它擁有模仿人類一切感覺的能力,能夠讓人感受到他真實存在。邪惡科學家通過改變計算程序能夠使實驗品按照他的意志去“經歷”人生,甚至讓實驗體自身認為這是“自由意志”的選擇。他寫道:“實驗品甚至可以感到自己正坐在那里閱讀描述這個有趣但十分荒唐的假設的文字:有一個邪惡的科學家,他把人們的腦從身體上切下來,放進一個盛有維持腦存活的營養液的大缸里……”[24]這個實驗細細想來是極為恐怖的,您閱讀這篇文章的動作可能正是“程序”的操縱。在普特南看來,理想條件下,人無法分辨自己是在“缸中泡著”還是在“缸外看著”。
“缸中之腦”的思想實驗設置了幾個前提條件:1.意識是人腦的產物。2.人腦的活動可以被科學化,能夠通過高度的人工智能進行模擬。3.世界萬物可以通過數字化的形式得以保存與再現。對應的意識理論中,最為強勢的是生物主義還原論,即意識現象可以還原為構成神經元組織的每一個神經元的功能及性質的集合[25]。這里隱含了一種類似畢達哥拉斯主義的宇宙觀和生命觀:生命的意義在于其對外在表現形式的感受。形式可以被計算,計算可以再被設備重新表達,從而還原生命形式,以實現生命的意義。雖然“缸中之腦”的結論是人類無法區別擬態與現實,但就提出這個思想實驗行為本身,人不但能夠區分,并且在科技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還能主動創造逼真的擬態環境。因此,在這個思想實驗中,思想成了人腦的“造物”,擬態環境變成了現實的映射,“現實—擬態”的漸進性被徹底扭轉,“擬態”變成了現實物質條件的延伸。
回顧“缸中之腦”思想實驗的背景,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媒介技術的進步,相較于古代社會的“憑空想象”,“缸中之腦”所描繪的擬態環境是有現實技術支撐與未來實現可能性的。1955年,Morton Heilig 提出了“多感官劇院(Experience Theater)”概念①,想讓戲劇內容“可聽、可看、可感”。1962 年,最早的虛擬現實系統Sensorama 橫空出世,這是一種固定式機械設備,包括立體彩色顯示器、風扇、氣味發生器、立體聲系統和動感座椅[26]。它通過屏幕、風扇產生的風以及模擬的城市噪音和氣味,讓觀眾想象自己正坐在穿越紐約的摩托車上。隨著旅程繼續,各種人體可感知的元素在適當時間被觸發,例如當騎手接近公共汽車時排放模擬汽油味的化學物質[27]。這是人類首次在虛擬世界感受到“真實”,與如今的4D 電影院異曲同工,但遺憾的是并不能實現虛擬世界中的互動功能[28],人必須固定地坐在椅子上進行觀看。1968 年,虛擬現實技術邁出了移動化的第一步,第一款頭戴式增強現實系統“達摩克利斯之劍(The Sword of Damocles)”[29]由伊萬·薩瑟蘭(Ivan Sutherland)和他的學生共同創造而出,該系統通過懸掛在頭頂之上的多軸連桿實現了視覺跟蹤,用戶眼前是透明的鏡片,通過鏡片可以看見現實空間中出現了一個虛擬立方體[30],邁出了可移動虛擬空間構建的第一步。
更加真實的擬態環境隨著技術的進步一下子變得不再從屬于想象和神秘主義,變成了可以實際展望的現實。薩瑟蘭對于計算機技術所創造的“終極顯示(ultimate display)”進行了展望:“終極顯示的將是這樣一個房間,計算機可以在其中控制物質的存在。擺在這樣的房間里的椅子可以坐下,展示的手銬可以真的束縛住(人),出現的子彈會是致命的。通過適當的編程,這樣的展示實際上可以是愛麗絲走進的仙境。”[31]在這樣的擬態環境中,人類是可以“變換身形”的愛麗絲,走進了自己用規則(編程)創造的仙境,人類充分掌握著環境的構造規則,擬態是現實的延伸。
(三)“元宇宙”:媒介技術整合時代“現實-擬態”反轉中的“物我難分”
有人稱2021 年是元宇宙“元年”,其實是否是元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元宇宙作為一個概念確實承載了人們太多的想象與關注。看看近年來流行的概念: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每一個看起來都很厲害,元宇宙與他們有什么分別呢?會不會是曇花一現呢?相較于大數據等單一技術,元宇宙可以稱為“媒介技術的整合”,是一個高度復雜的數字技術復合體,由“六維乘六層”技術體形成。其中,由“BIGANT”組成的六維技術體系包含區塊鏈技術(B)、交互技術(I)、電子游戲技術(G)、人工智能技術(A)、網絡及運算技術(N)、物聯網技術(T)。六層架構體系,涵蓋底部硬科技層(包括5G、云計算、邊緣計算、AI、計算機視覺、智能交互、數字孿生等)、硬件計算平臺層(AR/VR/MR、腦機交互、全息影像、PC、CPU/GPU 等)、操作系統層、軟件層(3D 建模、實時渲染、AIGC、虛擬人等)、應用層(工業互聯網、智能工廠、社交、游戲、娛樂等)以及“元宇宙”經濟系統層(區塊鏈等)。因此,元宇宙是整合多種新技術產生的虛實相融的新型互聯網應用和社會形態[32],是人們構建未來擬態環境的發展方向。在未來,元宇宙可能不再叫這個名稱,但媒介技術整合的發展趨勢不會變,元宇宙在未來將要面對的問題是以何種形式存在的問題,而非是否會存在的問題。
目前看來,元宇宙離實現相距甚遠。區塊鏈等元宇宙底層技術仍處在初級階段,我們看到的元宇宙應用仍然非常“原始”。Meta 開發出的元宇宙Horizon Worlds 中,虛擬人沒有下半身。“希壤”等元宇宙空間看起來讓人想起多年前的3D 版網絡游戲,進入其中需要頭頂綁上VR 眼鏡用以顯示場景,手里握著兩個手柄控制人物走動與選擇[33]。僅以元宇宙中的“看”這一基本動作為例,提供視覺感受的計算全息三維顯示技術目前面臨缺乏低噪聲的全息圖生成方法、高精度波前畸變校正技術、三維內容嚴重不足等問題[34]。當人們手握遙控器,頭戴顯示器,面對卡通化的構圖與人物,應該能夠清醒地認識到身處擬態環境之中,也難怪有研究者稱元宇宙為“3D 互聯網”[35]。但元宇宙僅止于此嗎?3D互聯網就是元宇宙的最終形態嗎?未來的擬態環境就是如此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從字面意義上來講,“元(Meta)”是超越的意思,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宇宙可以簡單理解為我們的現實世界。合并起來,元宇宙是超越現實世界的世界。何謂超越?兼具現實的所有因素,并具有優于現實的特色才能符合人們對于超越的定義。要實現真正的元宇宙,人類必須擺脫外在設備的束縛,必須有能力“身臨其境”地進入其中。如此看來,目前所有的VR 頭盔、AR 眼鏡都只是元宇宙的初級階段,都是對現實的模仿,不是真正的“reality(現實)”。能夠幫助人類走向元宇宙的應該是腦機接口與人工智能技術,前者是數據通道,提供數據的上傳下載。后者是數據內容,提供真實化的擬態環境。二者相結合才能夠使人真正“感同身受”。2020 年,馬斯克的腦機接口公司(Neuralink)就已經實現了腦機接口實驗,成功接收到了實驗小豬的腦電波[36],但依舊需要植入電極,破壞頭部組織的完整性。如果有一天,人們可以通過非植入性設備,像戴發卡一樣佩戴腦機接口,元宇宙的實現就不遠了。到那時,由人自身與人工智能共同構筑的擬態環境——元宇宙,將具備目前現實世界的一切感官,視覺界面將擺脫卡通化,嗅覺、味覺的感觸將得以實現,并且將有可能實現飛行、自動學習等現實世界無法實現的能力,擬態環境將與現實環境“等量齊觀”,甚至超出現實。彼時,人類的肉體將變成類似于如今計算機一樣的“硬件設備”,為擬態環境存在而服務,也將面臨無法承載不斷進化的擬態環境與虛擬活動的問題。也許,人類也需要像如今不斷購買新型號手機一樣,不斷為身體升級以適應更好用的“軟件”。那時,人類是否還會將擬態環境稱為虛擬,將物質環境稱為現實?“物”與“我”的關系也許將從“物我難分”更進一步演變為走向“物我合一”的漸進過程。
四、主體性消逝、一般等價物的確立、契約的自由訂立:擬態環境真實化帶來的傳媒治理挑戰
在傳播學研究領域,媒介樂觀主義與媒介悲觀主義是兩種主流的媒介技術想象。前者以麥克盧漢、保羅·萊文森為代表,麥克盧漢肯定媒介的實用性,認為:“(媒介)是經驗的東西,是實用的手段,用來感知普通工具和服務的作用和特性。它們適用于一切人工制造物,無論是硬件還是軟件。”[37]萊文森更是肯定網絡的發展,認為“(網絡)成了分散的中心,不僅是閱讀、收聽和收看的中心,而且是生產和廣播的中心”,起到了分散權力的作用。后者以哈羅德·英尼斯、尼爾·波茲曼為代表,看到了媒介不光有良好的一面,更有對于社會的“毒害”,“每一種技術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賜,不是非此即彼的結果,而是利弊同在的產物”[38]。《童年的消逝》《娛樂至死》等著作是媒介悲觀主義的集中體現。
隨著擬態環境真實化的持續推進,不管是媒介樂觀還是悲觀主義都必須接受一個現實:計算理性完成了旨在占有和支配自然的計劃。但是我們作為自身的存在者,卻遠沒有借助技術的方法成為自然的主宰,相反,我們自己作為自然的一部分也服從技術的要求[39]。這一過程不可避免,是一個技術與人類雙向互動,甚至技術正逐漸超越人類的過程,它意味著人類必須要解決與擬態環境“和諧共生”的問題。美國學者艾倫·德倫森(Alan R Drengson)認為,技術無政府主義、技術樂觀主義、技術悲觀主義和技術控制主義是一般哲學觀念中對待技術的哲學傳統[40]。相較于前三者,技術控制主義不盲目反對技術,也不過分樂觀地贊頌技術。它認為技術是可以促進人類發展的,但要考慮技術的具體運用方式。如何充分考慮并提高人的個體的價值、生態的完整性及文化的健康性等以達成“人—社會—自然”之間關系的協調[41],是其探討的核心問題。從技術控制主義出發,重新審視擬態環境真實化,也許能夠進一步探析未來傳媒治理可能遇到的問題,讓擬態環境建設少走彎路。
技術控制主義有兩方面主要觀點:一方面,應該在技術價值中引進道德和生態價值,強調在技術、工具和人類以及道德之間追求一種正當的、巧妙的匹配;另一方面,強調應該按照生態系統的規則來打造協調、可持續的技術生態[42]。以此觀之,元宇宙帶來的擬態環境真實化也面臨兩方面問題:人類主體性的保存與開放性擬態環境構建。
人類主體性保存主要應防止技術超越人類自身,以致忘記自身的物質存在,防止馬克思所說的“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43]。這里最為核心的是,應意識到擬態環境真實化的危險性,認識到其對于人類主體性的挑戰,避免過度樂觀。有學者認為:“元宇宙中的虛擬文明并不是完全獨立于現實的文明系統,而是現實文明的附屬,為現實文明服務的文明系統。”[44]還有學者提出:“以算法為統領的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對社會中相對無權的個體和群體的賦權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正在更深刻地開發每個個體的主體性,帶來一場傳播權力的革命性回歸。”[45]“附屬論”“權力論”對元宇宙保持了樂觀的看法與心態,對于技術的早期發展是有利的,但隨著擬態環境真實化的推進,虛擬文明不一定就是現實文明的附屬,傳播權力一定會回歸,但不一定回歸到普通用戶手中。就現在的媒介環境來看,平臺越來越大,傳媒集團越來越多,用戶的選擇卻越來越少。在算法推薦機制下,用戶甚至逐漸喪失了搜索的欲望與能力。意識到人類精神與思想的脆弱性,才能有意識地在建設未來擬態環境中投入“人文”意識與關懷,這也是本文提出擬態環境真實化的初衷之一。
開放性擬態環境構建與人類能否在元宇宙中進一步實現自由息息相關。在現實社會,人的自由是通過自由交換的一般等價物與自由簽訂的契約來實現的。就目前的元宇宙構建狀況來看,這兩點在元宇宙中的實現面臨困難。一般等價物的出現使商業繁榮成為可能,也為人的自由選擇提供了機會,因為都認可“錢”,人們可以根據錢來判斷商品的價值,決定是否進行交換,如此價格能夠起到市場調節作用,經濟運行得以循環。基于區塊鏈技術的虛擬貨幣被人們寄予厚望,期望其能夠成為元宇宙中的一般等價物,但問題是虛擬貨幣本身就未實現統一,以目前主流的去中介化虛擬貨幣“通證”為例,就分為應用通證、權益通證和債權通證等不同的類型[46]。更進一步地,區塊鏈的產生以“挖礦”為源動力,虛擬貨幣的產生過程浪費大量能源的同時為違法犯罪提供了空間。國家發改委公開征求《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21 年版)意見時,將虛擬貨幣“挖礦”活動列入淘汰類,在中國境內所有與虛擬貨幣有關的活動都將被列為非法金融活動,全面取締或關閉[47]。未來各國都認可的元宇宙一般等價物還有待繼續探索。自由簽訂的契約更成問題,就目前看來,Facebook等美國科技企業所倡導的元宇宙更像是一種“科技向善”的意識形態神話。以馬斯克主義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總是夸大他們的使命:改變工作的未來、連接全人類、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拯救整個星球。打造種種意識形態幻象,都旨在讓人們相信眼花繚亂的虛擬世界代表了人類的未來。然而,資本實體本身卻無比清醒地借助于這種意識形態幻象攫取現實中的利益[48]。在2021 年的Connect 大會上,馬克·扎克伯格強調,“未來我們元宇宙將盡可能服務更多的人,包括普通人(People)、創作者(Creators)以及商業機構(Business)”,并推出了“Spark AR Curriculum”課程進行元宇宙技術的培訓和認證[49]。其實質是,平臺提供生產空間,同時又提供生產工具,最終也將收獲生產成果。這與互聯網的發展過程是何其相似,早期的技術賦能、自由民主,最終演變為國外的谷歌、蘋果、亞馬遜,中國的BAT,演變為手機APP 中的只能點擊同意的制式條款,演變為淘寶提出的讓商家作出淘寶和其他平臺間的“二選一”抉擇,演變為用戶的“選無可選”。如果按照現如今科技巨頭們進軍元宇宙的態勢,自由簽訂的契約恐有困難,未來的元宇宙只不過是擬態環境中對人類精神意志“蛋糕”的“再分配”。
五、討論:何以為媒介,何以為人?
探討至此,本篇想表達的觀點:擬態環境真實化,已經表述完畢。它包含媒介技術的不斷進步與人類“物質—精神”關系認識的回環往復。幸運的是,媒介技術正創造更加真實的擬態環境,為人類的想象插上了翅膀。不幸的是,真實化的擬態環境對人的主體性威脅正與日俱增,對未來的媒介環境構建提出了新挑戰。擬態環境是人創造的,越來越真實,“物我互換”仍然可以說只是眾多可能性中的一種,但“物我難分”的狀態至少是可以期待的,本文想留下一個討論問題來和各位評閱者一同探討:面對擬態環境真實化,何以為媒介,何以為人?
面對這個宏大的問題,在探索真實化這一過程中,我們已經看到了一個很明顯的現象:人在技術中不是被迫屈從于某種異己的東西,實際上遇到的是自己本身[50]。人類對于自身的存在有認識上的局限性,“我是誰”,如何定義自身存在,至今仍是哲學探討的終極話題之一。拋開這種“人類謎團”不談,擬態環境真實化提示我們的,應該是我們的未來選擇問題。構成擬態環境的技術是人創造的,擬態環境是人創造的,技術的集成化也是人創造的,最終的真實化擬態環境實質上是人們選擇的“孩子”。羅素提出“這個世界是我們的世界,要把它變成天堂或地獄都在于我們”[51],也許正是這些“選擇”代表了人,從而產生了媒介。為了阻止技術危險的波及,我們不應該把技術置于一旁,而是應該通過完全地揭示構成技術的特征的危險去正視它[52],這是本文探索擬態環境發展規律的根本目的。感謝李普曼先生在100 年前提出擬態環境理論,讓我們意識到虛擬環境中的控制問題,以此為基礎,我們可以在未來探討擬態環境真實化過程中如何實現真正的“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真正實現人在虛擬環境中的自由。或許技術控制論的思想:控制與自由的平衡發展是一條可選道路。人類也許會失敗,在擬態環境真實化中徹底轉變了自身的物質主體性,淪為《黑客帝國》中受AI 控制的“生物電池”;也許人類會成功,創造出新形態的文明,但“戰斗過,卻失敗,總比從未戰斗過好”[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