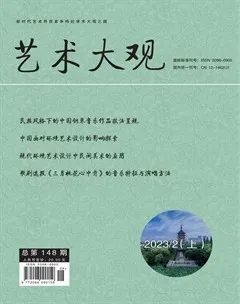論巴音樂的形態(tài)特征




摘 要:本文結(jié)合巴音樂歷史沿革、音調(diào)、旋法、節(jié)奏節(jié)拍、創(chuàng)腔方式綜合論證巴音樂的形態(tài)特征。結(jié)果表明,巴音樂具有與長江流域其他省份不一樣的形態(tài)風(fēng)格,其體現(xiàn)了古代巴人剛毅樸實(shí)的精神氣質(zhì)。由此證實(shí),巴音樂作為一種古老的地域音樂文化,直承該區(qū)域古老傳統(tǒng),是保留巴文化最頑強(qiáng)的因素。
關(guān)鍵詞:巴音樂;音樂形態(tài);審美風(fēng)格;文化背景
中圖分類號(hào):J609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2096-0905(2023)04-00-03
巴文化在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曾名噪一時(shí),與蜀文化并屹于西南地區(qū),后秦國南下剿滅巴國,使巴文化逐漸式微,西南地區(qū)逐漸統(tǒng)一于漢文化中,但巴文化至今仍保留其固有特色。
在巴文化中,音樂是最引人注目的要素之一。巴音樂歷史悠久,文化底蘊(yùn)豐富,涪陵小田溪巴人墓出土的編鐘乃巴人璀璨音樂之物證。除此之外,大量文獻(xiàn)亦記載著重慶音樂的燦爛歷史。商周時(shí)期巴人創(chuàng)造了豪邁粗獷的巴渝舞,據(jù)《華陽國志·巴志》中描述,“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這引起了春秋統(tǒng)治階級(jí)們的青睞;而春秋時(shí)期有巴人歌流行于楚的記載,“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shù)千人”;漢代《蜀都賦》記載的“謳歌,巴士人之歌也”,三國時(shí)期則有“巴人謳歌,相引牽手而跳歌也”,反映歷史上巴人唱歌的群眾基礎(chǔ)[1]。
一、巴音樂的發(fā)展
唐宋以來,巴音樂在民間以竹枝歌形式傳承下來并被廣泛傳唱。劉禹錫《竹枝序》中提道,“見聯(lián)歌竹枝,短笛擊鼓以赴節(jié),歌者揚(yáng)袂睢舞,以曲多為賢”,杜甫作記“萬里巴渝曲,二年實(shí)飽聞”;白居易在《竹枝詞》的記載“唱到竹枝聲咽處,寒猿晴鳥一時(shí)啼”;《寰宇記》所載“邪巫擊鼓以謠祀,男女皆唱竹枝歌”。不少文人亦在竹枝歌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小曲”,遂充實(shí)文人音樂。可見,竹枝歌在我國音樂史上的重要地位。至今重慶民歌多采用四字一襯詞,三句一襯詞的詞體結(jié)構(gòu),乃竹枝歌濫觴。
明清以來重慶的其他傳統(tǒng)音樂如川劇、清音等均不同程度地受巴民歌形態(tài)風(fēng)格的影響而形成特定形態(tài)要素,其中川劇以其高亢的音調(diào)、樸實(shí)性格而廣受百姓的青睞。近現(xiàn)代以來,川江號(hào)子、山歌等優(yōu)秀藝術(shù)紛紛被搬舞臺(tái),一些作曲家如金砂、郭文景等亦以巴音樂為創(chuàng)作素材,使巴音樂得以展示在更高的舞臺(tái)上。
既然巴音樂有著輝煌的歷史發(fā)展歷程,那其形態(tài)特征是什么呢?從文獻(xiàn)描述中客觀反映巴音樂的剛健質(zhì)樸特征,但這些多為感性認(rèn)識(shí),尚缺乏實(shí)證性。近年來,學(xué)術(shù)界也發(fā)現(xiàn)巴蜀音調(diào)的不同形式,即巴文化為代表的小羽曲折跳進(jìn)旋法和蜀文化為代表的窄羽級(jí)進(jìn)旋法[2],并認(rèn)為巴渝音樂有著剛健之風(fēng)格,但由于未對(duì)巴渝音樂做專門研究,且僅考慮了音調(diào)要素,尚未全面把握其風(fēng)格特征。另有論文通過對(duì)巴地編鐘構(gòu)造與特征的描述得出巴渝音樂的古拙摯樸風(fēng)格[3],此研究未涉足音樂分析,難以提供客觀的論據(jù)。
鑒于此,本文將以巴音樂最具代表的形態(tài)要素分析作為基礎(chǔ),將這些要素歸結(jié)為巴音樂的形態(tài)特質(zhì),并將其作為巴音樂的基本定義。
二、巴音樂的形態(tài)要素
音樂是文化中保存最頑強(qiáng)的因素,巴文化雖消亡許久,但巴音樂卻作為巴文化的重要物質(zhì)載體將其剛健質(zhì)樸的文化特性予以保留,而這些風(fēng)格主要由音調(diào)、旋法、節(jié)奏節(jié)拍以及曲式結(jié)構(gòu)、創(chuàng)腔方式等要素綜合體現(xiàn)。
(一)巴羽三聲腔及曲折跳進(jìn)旋法
巴羽三聲腔[3],即以羽音作為基音的小聲韻“La—Do—Mi”,另外有“Mi—SOL—Si”與“Re—Fa—La”兩種不同變體,因其主要分布在曾屬于巴國的重慶、宜賓等地,故得名焉[3]。
由于該三音列采用三度疊加作為基礎(chǔ)結(jié)構(gòu),奠定歌曲旋律跳蕩的基礎(chǔ),無論是單獨(dú)行腔或者混合行腔,均蘊(yùn)含著歡快或豪邁之感。單獨(dú)行腔者則將巴渝音樂的粗獷風(fēng)格發(fā)揮得恰到好處。這首涪陵的矮腔山歌《啰兒調(diào)》(見譜例1)就是其中例子,該歌曲頻繁使用六度、五度的跳進(jìn),加上其旋律與唱詞字調(diào)相貼近,遂產(chǎn)生激蕩風(fēng)趣、活潑的表現(xiàn)力。
(二)律動(dòng)而干練的節(jié)奏節(jié)拍
巴音樂的節(jié)奏節(jié)拍具有律動(dòng)而干練的特征,較少出現(xiàn)江南一帶回環(huán)繁復(fù)的節(jié)奏型,相反則常出現(xiàn)“前八后十六”“小切分”“小附點(diǎn)”“十六音符等分”等律動(dòng)性較強(qiáng)的節(jié)奏型,不同節(jié)奏型以不同形式進(jìn)行組合,使歌曲充滿激情且樸實(shí)。
這類節(jié)奏在民歌中普遍使用,《盤歌》(見譜例2)正是幾組律動(dòng)節(jié)奏的組合,其速度偏快,情緒高亢,頗有催人奮進(jìn)的情緒。
(三)三音列變奏為主的創(chuàng)腔模式
創(chuàng)腔指的是一首歌曲由其基礎(chǔ)結(jié)構(gòu)發(fā)展為具體曲調(diào)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原基礎(chǔ)結(jié)構(gòu)通過變形、鑲嵌、移位甚至是移調(diào)的形式產(chǎn)生不同的結(jié)構(gòu)體,而結(jié)構(gòu)體以不同節(jié)奏形成不同的具象形式,具象形式以豐富的有機(jī)組合形成完整的音樂作品[4]。音樂基礎(chǔ)結(jié)構(gòu)主要包括三音列、四音列或旋律片段。通常基礎(chǔ)結(jié)構(gòu)越簡單,所構(gòu)成的音樂旋律越簡潔。
巴音樂大多采用三音列變奏的創(chuàng)腔方式,其手法大致分為單一三音列創(chuàng)腔和同質(zhì)異構(gòu)的三音列創(chuàng)腔。
單一三音列創(chuàng)腔的歌曲多出現(xiàn)在一些初級(jí)民歌中,這些歌曲與方言字調(diào)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代表了巴渝民歌最核心的旋律。如譜例3所示的喪歌就是代表之一,其旋律單純建立在窄聲韻“La—Do—Re”基礎(chǔ)上,以單一樂句變奏反復(fù)進(jìn)行發(fā)展,每一句終止式均采用窄聲韻下行級(jí)進(jìn)的形式進(jìn)行,加上速度的徐緩,蘊(yùn)含著悲傷憂愁的情緒,與歌詞中“祭祀岳母”所表達(dá)的哀傷有機(jī)結(jié)合。
同質(zhì)異構(gòu)體的三音列創(chuàng)作在巴渝民歌中最常見,此類歌曲最顯著的特點(diǎn)是以窄聲韻“La—Do—Re”為基礎(chǔ),通過自由移位的形式演變出“Mi—SOL—La”“SOL—La—Do”“Re—Mi—SOL”三種不同變體,然后以這幾個(gè)不同的變體作為基礎(chǔ)行腔,如圖1所示。
從圖1中不難看出,3號(hào)腔乃2號(hào)腔的上五度位移,可簡寫成為2Y,而4號(hào)腔則是1號(hào)腔的上五度位移形式,可用1Y表示,故具有獨(dú)立結(jié)構(gòu)的音調(diào)只有1、2號(hào)兩腔,2號(hào)腔明顯是1號(hào)腔自由移位的產(chǎn)物,中聲韻“Do—Re—Mi”是連接性音調(diào),暫不考慮。幾種不同的窄聲韻或單獨(dú)行腔,或綜合行腔,不同音調(diào)以其窄小音程使民歌奠定了級(jí)進(jìn)為主的旋律。
重慶最負(fù)盛名的歌曲《太陽出來喜洋洋》(見譜例4),其采用上下句體形式。第一樂句第一短腔采用了中聲韻形式,第二短腔采用1號(hào)腔逆行下行形式。第二樂句分為兩個(gè)不同短腔,前短腔采用了2號(hào)腔級(jí)進(jìn)上行與1號(hào)腔級(jí)進(jìn)逆行的形式,后短腔采用1號(hào)腔的換序形式。從整首歌曲來看,1號(hào)腔不僅出現(xiàn)次數(shù)較多且多位于樂句結(jié)束處,起支配作用,2號(hào)腔乃其自由移位的產(chǎn)物,但兩個(gè)音調(diào)屬于同質(zhì)異構(gòu)體,所構(gòu)成旋律亦偏于級(jí)進(jìn)。
從上述例子不難看出,巴音樂主要采用三音列變奏為主的創(chuàng)腔手法,該創(chuàng)作手法雖不能形成華麗繁復(fù)的旋律型,但是其質(zhì)樸簡潔的旋律音型卻廣受群眾青睞,這也是春秋時(shí)期的《下里》《巴人》能引起千人共鳴,唐代竹枝歌“男女皆唱”的重要原因。
以上所分析的音調(diào)、旋法、節(jié)奏節(jié)拍、曲式結(jié)構(gòu)以及創(chuàng)腔方式顯然具有一定的同質(zhì)性特征。三度疊加的音調(diào)、曲折跳進(jìn)的旋法以及干練的節(jié)奏節(jié)拍共同體現(xiàn)出巴音樂的剛健風(fēng)格,而短小精悍的曲式結(jié)構(gòu)以及三音列變奏為主的創(chuàng)腔方式則體現(xiàn)出巴渝音樂的古拙質(zhì)樸的特性。
三、結(jié)束語
本文通過對(duì)最能夠體現(xiàn)巴音樂的形態(tài)要素進(jìn)行了剖析,初步認(rèn)為巴音樂以“La—Do—Mi”作為基礎(chǔ)的音調(diào)結(jié)構(gòu)奠定其跳進(jìn)旋法的基礎(chǔ),而常以曲折跳進(jìn)為主的旋律線條則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其激越跳蕩的氣質(zhì),簡潔干練的節(jié)奏節(jié)拍以及三音列為基礎(chǔ)的創(chuàng)腔手法又凸顯出巴音樂質(zhì)樸的風(fēng)格氣質(zhì),使巴音樂與長江流域音樂常見的典雅、陰柔之風(fēng)形成了對(duì)比。
而巴音樂的形態(tài)特征的形成正是巴人尚武氣質(zhì)的直接體現(xiàn),成為保留巴文化最為頑強(qiáng)的因素之一,正可謂“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因此當(dāng)代巴音樂很有可能保留原始巴音樂的諸多遺韻。
限于篇幅,本文只對(duì)巴渝音樂形態(tài)的一些代表特征進(jìn)行宏觀概述,在論證過程中筆者也發(fā)現(xiàn)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值得進(jìn)一步探討。
第一,既然巴音樂是巴文化最頑強(qiáng)的文化因子,因而可通過對(duì)巴音樂現(xiàn)狀分析的同時(shí)結(jié)合歷史文獻(xiàn)中描述的巴音樂現(xiàn)象對(duì)古代音樂進(jìn)行反推,由此初步推斷出古代巴音樂的一些旋律狀態(tài),這樣不僅可初步斷定巴渝竹枝歌可能常用的一種旋律結(jié)構(gòu)或者音樂旋律因素,甚至可斷定古代巴渝歌舞的一些因素,加上春秋統(tǒng)治階級(jí)推崇巴渝歌舞,可進(jìn)一步推測春秋宮廷雅樂可能具備的一些要素。
第二,外來的高腔、清音甚至宗教音樂等高層次的傳統(tǒng)音樂又是如何受到了巴音樂的旋律形態(tài)影響而發(fā)生區(qū)域性流變的呢?這些問題均值得深入鉆研,如此進(jìn)一步揭示巴地音樂的整體面貌以及相互之間的關(guān)系,從而有助于區(qū)域傳統(tǒng)音樂相互關(guān)系的研究。
第三,也是最核心問題,就是巴音樂當(dāng)代密集分布的區(qū)域很可能也是巴人歷史上遷徙的核心區(qū)域,而學(xué)術(shù)界至今對(duì)巴人源流亦未形成共識(shí)。通過對(duì)成渝地區(qū)“小聲韻三音列”的分布情況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并結(jié)合相關(guān)文獻(xiàn)關(guān)于巴人歷史的描述則有助于揭示巴人源流這一難題,為歷史學(xué)研究提供新的證據(jù),從而提升音樂研究的價(jià)值。
參考文獻(xiàn):
[1]彭貴華.中國歌謠集成(重慶市巴縣卷)[M].重慶:重慶市巴縣民間文學(xué)三套集成編輯委員會(huì),1988.
[2]蒲亨強(qiáng).巴蜀音調(diào)論[J].樂府新聲(沈陽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5(01):33-37.
[3]楊匡民,周耘.巴音、吳樂和楚聲——長江流域的傳統(tǒng)音樂文化[J].音樂探索.四川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1(01):7-11.
[4]蒲亨強(qiáng).苗族民歌研究[J].中國音樂學(xué),1988(01):6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