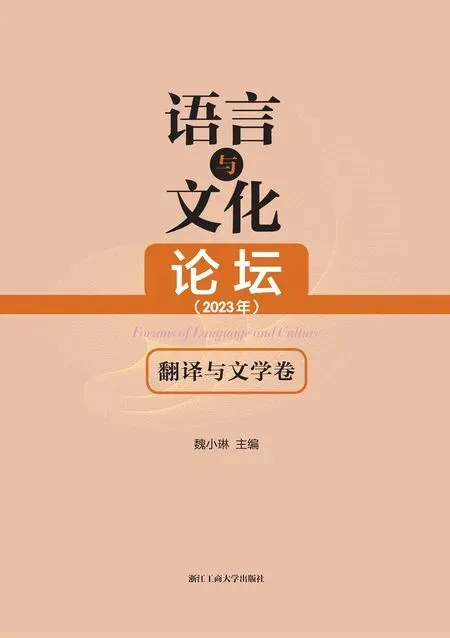中國科幻文學(xué)的海外傳播
——以《三體》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接受為例①
宋 菁 徐惟誠
1. 引言
2015年,劉慈欣憑借《三體》的英譯本TheThree-BodyProblem榮膺國際幻想文學(xué)界的諾貝爾獎(jiǎng)——雨果獎(jiǎng)最佳長篇小說的桂冠。多年來,《三體》在英語世界不斷深耕,積攢了大量粉絲群體,不但助力中國文學(xué)“走出去”,而且做到了“走進(jìn)去”,實(shí)現(xiàn)了中國科幻文學(xué)的實(shí)力崛起。中國教育圖書進(jìn)出口有限公司于2022年初宣布,已同美國麥克米倫出版公司旗下的權(quán)威科幻小說出版社托爾出版社完成了《三體》英文版版權(quán)的提前續(xù)約,續(xù)約金高達(dá)125萬美元,按當(dāng)時(shí)匯率折合人民幣近800萬元。這一數(shù)字“創(chuàng)造了中國文學(xué)作品海外版權(quán)輸出的新高,向世界證明了中國文學(xué)作品的國際市場價(jià)值”(佚名,2022)。但目前,我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的世界之路依然步履維艱,自莫言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以來,傳播到海外的本土文學(xué)作品數(shù)量雖有所提升,卻仍十分有限。中國作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吉狄馬加直言,雖然華文作家占世界文壇作家總數(shù)比例較大,但“就文學(xué)作品翻譯成不同國家的語言而論,中國的排名很靠后”(冉文娟,2016)。作為中國當(dāng)代科幻小說的現(xiàn)象級作品,《三體》的譯介,使劉慈欣在英語世界獲得了文學(xué)聲望,也讓我們可以從細(xì)節(jié)處發(fā)掘本土文學(xué)作品海外傳播的著力點(diǎn)。剖析《三體》在英語國家的譯介過程、譯本形態(tài)與接受情況,可以認(rèn)識(shí)到譯者和譯本在中國科幻文學(xué)走向世界的進(jìn)程中所發(fā)揮作用與影響,了解中國科幻作品中鮮明、獨(dú)特的地域與民族文化印記如何在異質(zhì)文化語境中獲得認(rèn)可,洞見海外讀者對中國科幻文學(xué)的理解面貌及中國科幻文學(xué)在異域的傳播和接受實(shí)績,從而為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對外譯介與海外傳播提供新的啟示。
2. 譯介過程:贊助人與譯者的多方合力
在以歐洲,尤其是法國文學(xué)為核心的世界文學(xué)體系中,亞洲與拉丁美洲等地區(qū)的文學(xué)因其異質(zhì)性長期處在邊緣地位,其文學(xué)資本與自治性都無法與歐洲抗衡(劉洪濤,2021),中國文學(xué)在海外傳播中自然也常遭冷遇。由于中西方思維和文化上的隔閡、海外傳播渠道的不暢、翻譯策略選擇的失當(dāng)、對中國文學(xué)閱讀認(rèn)同感的欠缺等多種因素交織,中國科幻文學(xué)在世界格局中更加面目模糊。盡管中國當(dāng)代科幻小說在英語世界的影響力偏低,仍有如韓松、王晉康、劉慈欣等作家的作品走進(jìn)英語世界,其中劉慈欣科幻小說《三體》的譯介在整個(gè)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文化的外譯中可謂一個(gè)具有典型意義的成功案例。
通常而言,原作者、譯者、出版機(jī)構(gòu)、讀者群體、批評家等多個(gè)行動(dòng)主體的合力方能促成一部文學(xué)作品的成功譯介與接受。具體到《三體》在英語世界傳播的成功,首先應(yīng)歸功于中方代理商——中國教育圖書進(jìn)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教圖”)團(tuán)隊(duì)、美國出版方托爾出版社的團(tuán)隊(duì)以及譯者劉宇昆,這三方的合力為譯作在英語世界的認(rèn)可和接受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資本是布爾迪厄(Bourdieu)從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中借用的概念,延伸至文化符號領(lǐng)域,成為文化社會(huì)學(xué)中“場域-慣習(xí)-資本”三位一體模型的核心概念。布爾迪厄(Bourdieu,1986)認(rèn)為:“資本是一種以物化、具體化或肉身化形式顯現(xiàn)出來的積累的勞動(dòng),當(dāng)這種勞動(dòng)在排他性的基礎(chǔ)上被個(gè)體或群體占有時(shí),就能使他們以具體的勞動(dòng)的形式占有社會(huì)資源。”資本又細(xì)分為經(jīng)濟(jì)資本、文化資本、社會(huì)資本和象征資本。在譯介過程中,經(jīng)濟(jì)資本、文化資本與社會(huì)資本對譯作的傳播和接受最為重要。經(jīng)濟(jì)資本是位于基礎(chǔ)位置的資本,以制度化的物質(zhì)財(cái)富轉(zhuǎn)化為商品與服務(wù)。文化資本是行動(dòng)者對上層階層的精致文化所掌握的程度,在所有資本中最為重要,主要表現(xiàn)為3種形態(tài):以行動(dòng)者慣習(xí)和性情傾向?yàn)轶w現(xiàn)的身體化文化資本,以文學(xué)、藝術(shù)等文化產(chǎn)品為體現(xiàn)的客觀化文化資本,以學(xué)歷、頭銜等能力資格證明為體現(xiàn)的制度化文化資本。社會(huì)資本是行動(dòng)者個(gè)人或群體通過加入穩(wěn)定且制度化的社交關(guān)系網(wǎng)而積累的實(shí)際或潛在資源總和。布爾迪厄社會(huì)實(shí)踐理論投射到翻譯活動(dòng)中,即各行動(dòng)主體攜帶自身資本,在權(quán)力場中一決高下,成為行動(dòng)者在特定的文化場域中獲取收益的重要砝碼。對《三體》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而言,譯者及知名出版社所積累的經(jīng)濟(jì)資本、社會(huì)資本和文化資本,是該作品成功傳播的重要基石。
在中國科幻文學(xué)的英譯過程中,以代理商和出版社為主體的贊助人之意愿至關(guān)重要。2012年7月,劉慈欣與中教圖、《科幻世界》雜志社簽署了《三體》的英文圖書版權(quán)合作協(xié)議,自此,中教圖著手開拓《三體》英文版版權(quán)輸出工作及面向歐美市場的主流銷售渠道工作。項(xiàng)目啟動(dòng)初期,以實(shí)體圖書進(jìn)出口為主要業(yè)務(wù)的中教圖公司與湖南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建立合作關(guān)系共同推進(jìn)版權(quán)輸出,并投入大量經(jīng)濟(jì)資本提供資金支持。美國版權(quán)交易市場要求出版商在選擇圖書時(shí)閱讀英文全文,因此,代理商必須要先要投入資金翻譯全文,方能明確國外合作伙伴(李明遠(yuǎn),2015)。在此過程中,湖南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也成功申報(bào)“經(jīng)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為版權(quán)輸出工作加注資金,支持《三體》翻譯工作。中方經(jīng)過漫長而艱苦的談判,說服美國麥克米倫出版公司旗下的權(quán)威科幻小說出版商托爾出版社主導(dǎo)出版,規(guī)避了大多數(shù)中國文學(xué)作品因由學(xué)術(shù)出版機(jī)構(gòu)出版致使無人問津的困境。美國托爾出版社主要出版科幻小說和幻想文學(xué),作為著名的科幻推手,它助力了一批世界頂級科幻作家如羅伯特·喬丹(Robert Jordan)、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等的成名之路。托爾出版社曾連續(xù)20年獲得盧卡斯最佳科幻小說出版商獎(jiǎng),并出版過許多雨果獎(jiǎng)、星云獎(jiǎng)的獲獎(jiǎng)作品,在英語世界有著廣泛的知名度和讀者群。“權(quán)威的出版社、有良好品牌的叢書等,也是圖書能贏得市場的一個(gè)重要因素(而能贏得市場,也就意味著譯介有可能取得成功)。”(謝天振,2003)讀者對作品的期待與出版社的權(quán)威性不無關(guān)聯(lián),優(yōu)質(zhì)出版社就是銷量的保證。《三體》就仰仗托爾出版社長期積累的社會(huì)資本和文化資本,順利地打入了歐美市場。
美籍華裔譯者劉宇昆自身的資本積累也是《三體》在英語世界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劉宇昆在雙語功底、跨文化意識(shí)以及翻譯實(shí)績上占據(jù)著獨(dú)特的優(yōu)勢,積累了雄厚的文化資本,為成功譯介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目前,翻譯界、文學(xué)界和文化界一致認(rèn)為中國文學(xué)想要“走出去”,理想的翻譯模式應(yīng)是由具有中國經(jīng)歷、中文天賦、中學(xué)底蘊(yùn)以及中國情誼的目標(biāo)語譯者進(jìn)行翻譯(劉云虹 等,2014)。而《三體》的譯者劉宇昆正是這樣的目標(biāo)語譯者,他出生于中國甘肅,少時(shí)隨父母移民美國,后考入哈佛大學(xué)攻讀英美文學(xué)專業(yè)。他本身是一位高產(chǎn)的科幻作家,創(chuàng)作的英語科幻文學(xué)作品常引入大量中國文化元素,輸出富有東方特色的文化符號,比如中國美食、清明節(jié)、折紙、中藥和圍棋等。值得一提的是,劉宇昆關(guān)注漢字結(jié)構(gòu),“引入漢字作為小說的有機(jī)構(gòu)成部分”(王侃瑜,2016),比如在MonoNoAware(《物哀》)中,甫一開篇敘述者就提到世界的結(jié)構(gòu)就像繁體字“傘”;ThePaperMenagerie(《手中紙,心中愛》)的故事結(jié)尾,主人公一遍遍模仿繁體字“愛”的寫法等。扎實(shí)的雙語功底、多元文化背景的成長體驗(yàn)和中西方文化的熏陶,為他創(chuàng)造了成為優(yōu)秀譯者的必備條件。同時(shí)劉宇昆也是一名譯者,自2011年就開始譯介中國科幻小說,助力中國本土科幻成功“出海”。除《三體》外,他還譯介了陳楸帆的短篇小說《麗江的魚兒們》,斬獲了由美國科幻奇幻翻譯杰出認(rèn)可協(xié)會(huì)授予的第二屆科幻奇幻翻譯獎(jiǎng)最佳短篇獎(jiǎng);編譯了英語世界的第一部中國科幻作品選InvisiblePlanet(《看不見的星球》)。華裔身份賦予他東方情懷,這種既能立足本土、又能胸懷國際的翻譯模式使劉宇昆往返于2種迥異的話語體系和文化思維之間游刃有余,也使他能夠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在譯本的目標(biāo)定位、擇取標(biāo)準(zhǔn)及翻譯策略等方面進(jìn)行明智的判斷。
社會(huì)資本通常以名氣積累的形式而被制度化,當(dāng)行動(dòng)者能夠合理運(yùn)用自己所占有的社會(huì)資本,其社會(huì)資本將實(shí)現(xiàn)高度的自我增值。投射在翻譯領(lǐng)域,所謂自我增值可以體現(xiàn)在譯者的社會(huì)資本積累對譯作在世界文學(xué)版圖中地位的鞏固和加強(qiáng)作用。譯者在文學(xué)場域獲得的社會(huì)資本與原作的文學(xué)資本、社會(huì)資本相互作用,促使譯作得到同行的廣泛認(rèn)可和讀者的更多關(guān)注。劉宇昆創(chuàng)作、翻譯的眾多中國科幻作品在主要英語國家都獲得了良好的反響,為其在西方科幻文學(xué)界積攢了矚目的社會(huì)資本。劉宇昆自2002年開始創(chuàng)作短篇科幻小說,已發(fā)表百余篇原創(chuàng)作品,數(shù)量驚人。其中,短篇小說《手中紙,心中愛》分別于2011年和2012年摘得世界幻想文學(xué)大獎(jiǎng)星云獎(jiǎng)、雨果獎(jiǎng)的最佳短篇小說獎(jiǎng),劉宇昆成為首位華裔世界科幻小說的雙料獎(jiǎng)得主。2013年,他又憑借《物哀》斬獲雨果獎(jiǎng)最佳短篇小說獎(jiǎng)。2015年,劉宇昆的首部長篇小說TheGraceofKings(《國王的恩典》)在美國出版,獲星云獎(jiǎng)和軌跡獎(jiǎng)最終提名。他在文學(xué)場域中獲得的聲名為自己在世界科幻文學(xué)版圖中謀得一席之地,也為自己在翻譯場域積累了豐富的社會(huì)資本,獲得了可利用的資源。盡管美國讀者對劉慈欣及其作品《三體》知之甚少,但譯者劉宇昆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為《三體》的出版增加了無形的資本,有譯者的名氣與榮譽(yù)加持,讀者難免會(huì)對劉宇昆的翻譯感到好奇,從而愿意進(jìn)一步了解這部科幻作品。《三體》的翻譯出版借譯者與權(quán)威出版社資本積累的東風(fēng)走上了西行之路,譯者、知名出版社自身的經(jīng)濟(jì)資本、文化資本、社會(huì)資本積累,以及二者間的良性互動(dòng)促使譯本在新的迥異的閱讀空間中得到西方主流社會(huì)的賞識(shí)與接受,為英語世界讀者打開了一扇了解中國科幻文學(xué)的窗口。
3. 譯本形態(tài):特定歷史語境下的“他者”敘述
“譯介方法的選擇與運(yùn)用直接影響譯作的風(fēng)格與品質(zhì),因而也對中國文學(xué)在海外的接受與傳播具有決定性意義。”(劉云虹,2019)成功的譯本應(yīng)該是在西方多元系統(tǒng)文化中心中延續(xù)原作的文學(xué)生命,而非原封不動(dòng)地移植原作內(nèi)容,因此,翻譯的忠實(shí)并非僅局限于文字層面,也關(guān)乎原作的語言風(fēng)格、文化精神、作家氣質(zhì)和民族內(nèi)涵等不同的層面與維度。有鑒于此,一名合格的譯者需要能夠充分地尊重原作中獨(dú)特的中國文化元素,不削足適履、曲意逢迎,同時(shí)也必須考量譯本的接受環(huán)境,增強(qiáng)可讀性,避免艱澀的譯文。在翻譯《三體》之前,劉宇昆已經(jīng)公開發(fā)表了大量譯作,成果斐然,從他的翻譯實(shí)踐中,可以窺見其翻譯策略的選擇:他十分注重保留原作文化中異質(zhì)性的“他者”,致力于講述原汁原味的中國故事。劉宇昆認(rèn)為,任何故事脫離本土文化進(jìn)入一個(gè)新的文化圈的時(shí)候,不能只關(guān)注于丟失的部分,而拒絕新納入的部分(林嘉燕,2014)。在《三體》的翻譯中,譯者選擇保留原作中“他者”的異質(zhì)性元素,同時(shí)又能適應(yīng)新的語境,從而實(shí)現(xiàn)保持作家的本意,服務(wù)于特定的文學(xué)效果。
《三體》植根于中國文化土壤,字里行間渲染出獨(dú)特的“中華形象”,講述了一則具有中國氣質(zhì)的人類科幻故事,如“紅岸基地”、“唐”號航母、秦始皇等中國文化元素和東方科技氛圍比比皆是。劉宇昆在翻譯這類話語時(shí)秉持忠實(shí)原文的原則,原文中絕大多數(shù)中國文化特色和特定歷史背景的文化印記都得到了較好的保留,使譯文并未過多雕琢,脫離原著的文化框架,保留他者的文化特色,使譯作在異質(zhì)文化土壤中獲得新的質(zhì)體。
例①
原文:大鳳披著棉襖,紅肚兜和一條圓潤的胳膊露出來。(劉慈欣,2008)66
譯文:Feng had her coat draped over her shoulders, exposing her red belly-band, and a strong, graceful arm. (Liu,2014)252
肚兜是中國傳統(tǒng)服飾中護(hù)胸腹的貼身內(nèi)衣,最早可追溯至《左傳》中“皆衷其衵服”的“衵服”。肚兜上紋樣一般為花卉草蟲,在中國民俗講究中寓意趨吉避兇。譯者在翻譯時(shí)沒有采用bra或bandeau來翻譯貼身衣物,而是逐字直譯為belly-band,表明該物品為中國傳統(tǒng)服飾,避免讀者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相似的例子還有粗俗無禮、不修邊幅的反恐隊(duì)隊(duì)長史強(qiáng)說英文“警察”一詞時(shí),源文本為“泡立死”(police的中文發(fā)音),譯者特意按照發(fā)音譯為Pao-Li-Si而非police,如同有些中國學(xué)生記背英文單詞時(shí)投機(jī)取巧,標(biāo)注漢語拼音,這體現(xiàn)出史強(qiáng)粗俗的人物性格,也展示了中國特有的文化背景;再如,翻譯中國俗語“肉包子打狗”時(shí),劉宇昆保留了“肉包子”這個(gè)中國美食的意象,譯為be a meat dumpling thrown to the dogs,給讀者帶來了新的閱讀體驗(yàn)。
劉宇昆以“異化”為主導(dǎo)的翻譯策略使譯文忠實(shí)而又傳神,但有時(shí)西方讀者理解小說的知識(shí)儲(chǔ)備欠缺,陌生的文化意象無法帶給讀者流暢的閱讀體驗(yàn)。因此,考慮到讀者的有效接受,譯者需要兼顧譯本可讀性。在《三體》的英譯本中,譯者適當(dāng)增補(bǔ)副文本,使譯文在盡量貼合中文的前提下,增強(qiáng)了文本在異質(zhì)文化語境中的可接受性。比如,《三體》英譯本在扉頁添加了人物關(guān)系表,在書舌新增內(nèi)容導(dǎo)讀,幫助讀者梳理人物關(guān)系,厘清故事脈絡(luò),同時(shí)極大地激發(fā)了讀者的好奇心和閱讀欲。此舉正是因?yàn)樽g者重視譯介活動(dòng)中讀者的可接受性,適度削弱作品中陌生化元素造成的閱讀障礙。為了增強(qiáng)譯本可讀性,譯者還采取了添加注釋這一重要手段。
例②
作為物理學(xué)家的女兒,葉文潔猜出了那就是從1964年開始震驚世界的中國兩彈工程。(劉慈欣,2008)15
譯文:As the daughter of a physicist, Ye guessed that it was a reference to the double-bomb project1that had shocked the world in 1964 and 1967.
譯文注釋:1 This is the Chinese term for the work behind “596” and “Test No.6”, the successful tests for China’s first fission and fusion nuclear bombs, respectively. (Liu,2014)26
20世紀(jì)50年代中期,中國曾做出研制“兩彈一星”的戰(zhàn)略決策,這一決策的成功實(shí)施增強(qiáng)了中國的國防實(shí)力,但英語世界的讀者對這一史實(shí)幾乎是陌生的。譯者在處理中國的歷史文化時(shí),努力向原作靠近,必要時(shí)適當(dāng)增補(bǔ)解釋和說明,盡力保留原作者的文學(xué)氣質(zhì),并傳遞相關(guān)歷史信息。劉慈欣在《三體》中,以核彈為基礎(chǔ),構(gòu)想出了精妙的階梯計(jì)劃,因此“兩彈工程”在整部作品中擁有特殊含義。鑒于其事件之復(fù)雜,背景之特殊,如若僅作直譯,目標(biāo)讀者必然難以理解該工程的重要意義。對此,譯者添加了注釋:“兩彈工程指‘596’工程和1967年第六次核試驗(yàn)中成功引爆原子彈和氫彈的工程”,這一做法使得原作中特定時(shí)代的社會(huì)面貌得以忠實(shí)地呈現(xiàn)在譯者筆下,又不至于冗雜,增強(qiáng)了譯作的可讀性。又如在翻譯原著中的“二鍋頭”一詞時(shí),譯者直接將其音譯為“er guo tou”,同時(shí)又在當(dāng)頁添加注釋“er guo tou is a distilled liquor made from sorghum, sometimes called ‘Chinese vodka’”(Liu,2014)107,說明“二鍋頭”是中國以高粱為原料的釀制白酒。劉宇昆在整體上采取異化策略,在此基礎(chǔ)上又采用腳注的形式輔以適當(dāng)?shù)脑鲅a(bǔ)。雖然腳注是較為侵入性的解釋工具,但譯者在翻譯時(shí)秉持“在故事上留下最小指紋”(林嘉燕,2014)的原則,僅展示出讀者需要理解故事的含量的信息,使譯文在陌生感與熟悉感中達(dá)到一種微妙的平衡,既完整地再現(xiàn)了原文所具有地歷史內(nèi)涵中國特定歷史語境時(shí)的社會(huì)風(fēng)貌,也不影響西方讀者的整體閱讀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三體》英譯本對原作的章節(jié)結(jié)構(gòu)進(jìn)行了重新編排、整合,恢復(fù)了作品的原貌。《三體》第一部于2006年5月起在《科幻世界》雜志上連載,但中文版出于話題敏感性的考慮,將位于開篇章節(jié)的相關(guān)故事背景介紹挪至全書中間部分。而《三體》英譯本調(diào)整了中文出版書的結(jié)構(gòu),按照最初的連載順序進(jìn)行編譯,即把原作章節(jié)的第七至九章重新放回小說開篇,在“Part I Silent Spring”中就交代了全書的相關(guān)故事背景。這一改動(dòng)讓“對中國歷史了解不多的讀者能理清思路”(Nusinovich,2015)。顯然,劉宇昆翻譯的《三體》英譯本通過“異化”翻譯策略保留了原語的文化意象,努力呈現(xiàn)出原語文化中異質(zhì)性的“他者”,讓譯作透射出原作的光芒和色彩,同時(shí)借助注釋等副文本手段,為讀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識(shí),將語言的異質(zhì)性控制在主流詩學(xué)規(guī)范可接受的范圍內(nèi),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英語讀者的閱讀障礙,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原作傳遞的異質(zhì)文化。
雖然中國文學(xué)作為被主導(dǎo)語言文本在英語世界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但在全球大融合背景下,譯入語讀者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力正在發(fā)生變化,因此翻譯方法也不應(yīng)一味固守歸化原則(劉云虹,2019),應(yīng)“積極引導(dǎo)海外讀者欣賞中國文學(xué)的審美”,考慮如何輸出中國文學(xué)特質(zhì)(錢好,2018)。劉宇昆刻意呈現(xiàn)出的具有鮮明異國特色的“他者”譯本,在英語世界獲得了文學(xué)聲望,為中國文學(xué)融入以西方為主導(dǎo)的世界文學(xué)體系提供了新的借鑒。
4. 海外傳播與譯本接受
自《三體》英譯本出版以來,不斷刷新我國當(dāng)代文學(xué)海外銷量最高紀(jì)錄,讓西方世界看到了中國人在漫長文明中的歷史想象力,中國科幻從世界文學(xué)版圖的舞臺(tái)邊緣進(jìn)入西方視野,這對處于弱勢地位的中國當(dāng)代科幻文學(xué)而言,意義非比尋常。
“一本圖書能夠被世界不同國家的圖書館收藏,是這本圖書思想價(jià)值、作者影響以及出版社品牌等綜合影響的結(jié)果。”(何明星,2019)目前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在世界各國圖書館的館藏?cái)?shù)據(jù),是反映其海外影響力的核心指標(biāo)之一,也是海外傳播范圍的客觀憑證。據(jù)全球聯(lián)機(jī)書目數(shù)據(jù)庫WorldCat的檢索統(tǒng)計(jì),截至2021年10月底,《三體》全球有1341家圖書館收藏,是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譯作有史以來的最高館藏紀(jì)錄。其館藏?cái)?shù)量之多遠(yuǎn)超2014年被收入進(jìn)“企鵝經(jīng)典”系列的中國文學(xué)作品《解密》,以及唯一入選2017年度亞馬遜Kindle First優(yōu)選閱讀項(xiàng)目的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高興》。收藏TheThree-BodyProblem的海外圖書館的地理分布數(shù)據(jù)如表1所示,TheThree-BodyProblem在美國的圖書館館藏量雄踞榜首,達(dá)1017家,其次是澳大利亞123家,英國96家,充分表明了該作品引起了以歐美為中心的西方英語世界的廣泛關(guān)注。

表1 收藏The Three-Body Problem的海外圖書館所在國家及數(shù)量(截至2021年10月30日)
中國文學(xué)的對外譯介與傳播一定程度上依賴于“是否能引起英語讀書界的關(guān)注并贏得其權(quán)威書評機(jī)構(gòu)及書評家的積極評價(jià)”(劉亞猛 等,2015),因此,主流媒體的曝光率也是評判一部作品是否有影響力的標(biāo)尺。歐美主流媒體一貫以“接受屏幕”,即所謂受傳地文化過濾系統(tǒng),來評價(jià)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譯作。而《三體》英譯本問世后,歐美主流媒體紛紛改弦易轍,對作品予以正面介紹和報(bào)道。2014年,《紐約時(shí)報(bào)》以“中國為美國科幻小說迷換口味”(“In a Topsy-Turvy World, China Warms to Sci-Fi”)為題刊發(fā)書評,稱“異于地球的三體人文明與地球人互動(dòng)的故事,這種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故事會(huì)更受到美國讀者的青睞”。此后,《華盛頓郵報(bào)》《紐約客》《華爾街日報(bào)》《洛杉磯時(shí)報(bào)》等美國主流媒體也紛紛發(fā)表書評與采訪報(bào)道。其他西方國家媒體,如澳大利亞的《悉尼先驅(qū)晨報(bào)》《澳大利亞人報(bào)》,英國《衛(wèi)報(bào)》《每日電訊》《海峽時(shí)報(bào)》及各國專業(yè)科幻媒體和科技媒體也給予高度贊揚(yáng)和正面評價(jià),開創(chuàng)了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譯作在西方媒體首次被大規(guī)模報(bào)道的先河。
此外,讀者閱讀體驗(yàn)也非常重要,一部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風(fēng)格特點(diǎn)獲得讀者接受的程度如何主要以讀者評價(jià)為判斷標(biāo)準(zhǔn),也直觀地反映了出版機(jī)構(gòu)在市場營銷、渠道推廣等方面的綜合效應(yīng)。Amazon、Goodreads、Google等網(wǎng)站上的普通讀者評價(jià)是閱讀體驗(yàn)反饋的主要來源之一。據(jù)統(tǒng)計(jì),截至2021年10月底,《三體》英譯本在全球最大的讀者評論網(wǎng)站Goodreads上有超過11000條評論,綜合評價(jià)4.1星(滿分為5星),世界最大的圖書銷售平臺(tái)之一——美國亞馬遜網(wǎng)站有超過3300條讀者評論,綜合評價(jià)4.2星(滿分為5星),均創(chuàng)下了中國當(dāng)代文獻(xiàn)譯作海外讀者反饋?zhàn)疃嗟臍v史記錄。著名科幻作家金·斯坦利·羅賓遜(Kim Stanley Robinson)評價(jià)道:“劉宇昆譯筆了得,全書流暢而明晰,讓我們始終窺見中國人的世界觀。他的翻譯讓作品更加有趣,不愧為一部頂級科幻作品,讓人覺得陌生而又熟悉。”2017年,《紐約時(shí)報(bào)》首席書評人采訪美國前總統(tǒng)奧巴馬時(shí),奧巴馬對《三體》予以 “故事背景宏大,讓我的日常工作顯得渺小”的極高評價(jià),并寫信催更后續(xù)作品。著名嚴(yán)肅奇幻小說《冰與火之歌》的作者喬治·R.R.馬丁(George R. R. Martin)在《紐約時(shí)報(bào)》《華盛頓郵報(bào)》等主流媒體上對《三體》推崇有加,認(rèn)為它“奇妙地混合了科學(xué)和哲學(xué)思辨、政治和歷史、陰謀論和宇宙學(xué)”,“值得被提名”(孫武,2015)。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由此可見,《三體》不僅贏得了英語世界大眾讀者的青睞,也獲得了精英人士的高度認(rèn)可,取得了亮眼的對外傳播實(shí)績。
5. 結(jié)論
《三體》的譯介概況揭示了翻譯文學(xué)作品的復(fù)雜過程,譯本的翻譯、傳播與接受離不開譯者、出版機(jī)構(gòu)、讀者群體、評論家等多體系的協(xié)調(diào)與努力。其中,譯者劉宇昆、中教圖和托爾出版社依托各自的資本,助力《三體》進(jìn)入西方科幻文學(xué)系統(tǒng),極大地促進(jìn)了中國科幻文學(xué)走近世界文學(xué)版圖中心;譯者有效地調(diào)節(jié)了譯介的各個(gè)要素,實(shí)現(xiàn)了整體意義上的忠實(shí),使譯本形態(tài)充分展現(xiàn)出原作的文學(xué)氣質(zhì),在西方世界建立了真實(shí)而又完整的文學(xué)形象;《三體》英譯策略總體呈現(xiàn)出“異化”傾向,“他者”在可控的情境下得以充分地顯化,同時(shí)譯者也借助副文本等手段兼顧到了譯本的可讀性和接受性,最終贏得了廣泛的受眾。雖然中國科幻文學(xué)在英語世界仍然和者甚寡,走進(jìn)西方多元文化系統(tǒng)中心前路漫漫,但《三體》的傳播經(jīng)驗(yàn)為中國科幻文學(xué)的海外傳播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借鑒,中國科幻文學(xué)在異域的傳播與接受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