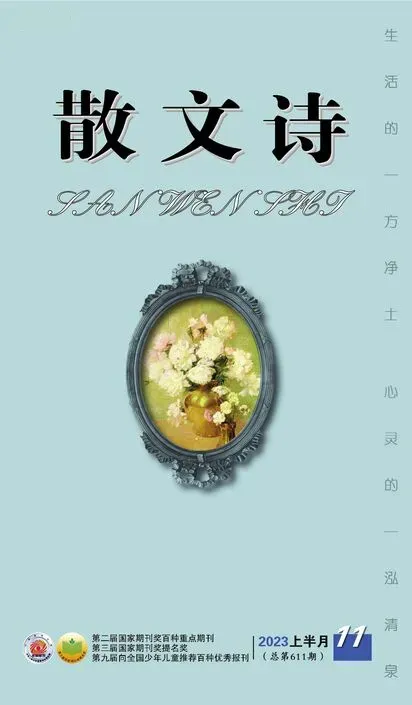大海邊的希緒弗斯與哈姆雷特
◎霍俊明
曉岸的散文詩(shī)組章《出海紀(jì)》(由21節(jié)組成)又一次面向了“大海”這樣一個(gè)恒久的空間,面對(duì)著一代又一代人的“復(fù)寫(xiě)”,這一精神類型的寫(xiě)作顯然充滿了危險(xiǎn)和歧路,稍有不慎,就會(huì)滑入經(jīng)驗(yàn)和套路化的慣性抒寫(xiě)之中,稍有不慎,脆弱的個(gè)體就會(huì)被黑沉的大海所吞噬掉。顯然,曉岸筆下的大海已經(jīng)成為精神場(chǎng)域和命運(yùn)坐標(biāo),個(gè)體不斷予以自我盤(pán)詰和調(diào)校。作者并未局限于此,而是由大海又輻射到周邊事物以及相應(yīng)的繁復(fù)經(jīng)驗(yàn),由此,我們看到的是經(jīng)由回溯、幻想和重構(gòu)所連綴、輻射開(kāi)來(lái)的網(wǎng)狀情志空間和難以言說(shuō)的焦灼的存在狀態(tài)。正如作者所慨嘆和詰問(wèn)的:“這是活著的意義嗎?在海水未冷卻前,不要讓肉體也嘗試著適應(yīng)腐爛的結(jié)局。”在此,我們聽(tīng)到了哈姆雷特的聲音回響。
“大海不適宜觸摸”作為抒寫(xiě)主調(diào)復(fù)現(xiàn)、穿插在文本之中。可見(jiàn)“大海”與抒寫(xiě)主體之間的關(guān)系或心理距離,它讓一代又一代的詩(shī)人為之抒寫(xiě),也讓一代又一代人在時(shí)間的浪花和漩渦中湮滅,“大海從未掩飾它的不屑。//它,一次一次用狂浪卷出水中沉浮的骨骸。它用恐嚇緊緊包藏它孤寂的情懷。它的不屑直接化成冰冷的海水灌進(jìn)你動(dòng)蕩不眠的夜晚。”由此可見(jiàn),大海既是永恒的召喚者和靈魂的撫慰者,又是神秘的存在主義者以及嚴(yán)酷的埋葬者和終結(jié)者。毋庸諱言,個(gè)體的存在(生老病死)之路在終極意義上都是超級(jí)一致的,即都是單向路上快速消耗、消殞的肉身,而困惑卻總是恒常如新的,“你用鐵鋸截?cái)嗌L(zhǎng)的記憶,用它濃稠的汁液涂滿天堂的鏡子。你的臉在鏡子背后扭轉(zhuǎn),一再拒絕,忍受著衰老的誘惑,忍受著那神秘吟唱的溶蝕。”與此同時(shí),生活的邊界和想象的邊界總是在大海這里得以拓展和更新。大海帶來(lái)的是時(shí)間之謎的永恒命題,是哈姆雷特式的糾結(jié)與困惑,也就更需要希緒弗斯式的永不疲倦、永不停歇地追問(wèn)與精神地搏斗。無(wú)疑,大海作為永不休止的時(shí)間動(dòng)作會(huì)激起每個(gè)人的恐懼、敬畏,激活每一個(gè)生命體的經(jīng)驗(yàn)和超驗(yàn)。
該散文詩(shī)的第2節(jié)是一個(gè)略顯“突兀”而又是時(shí)下諸多寫(xiě)作者都要面對(duì)的一個(gè)顯豁的精神背景或存在情勢(shì)。當(dāng)“油燈灰暗,火苗閃動(dòng)”這一相當(dāng)老舊而又溫暖場(chǎng)面出現(xiàn)的時(shí)候,回憶的火光中一個(gè)面孔斑駁“講故事的人”也就隨之登場(chǎng)了。接下來(lái),村莊、城鎮(zhèn)、流浪狗、鐵軌、火車(chē)、夢(mèng)、離鄉(xiāng)者、群山都成了倫理化的景觀,城市的現(xiàn)代化與鄉(xiāng)土的前現(xiàn)代性之間的齟齬猶如鋸齒在不斷加深。第4節(jié)出現(xiàn)了與之接續(xù)的類似場(chǎng)景和心境,“在陌生的城市之光下,打開(kāi)手掌的命運(yùn)之線,若有若無(wú)。用一把黑色的鹽粒將它填塞、阻截,你就真的會(huì)回到真正的生活?”第5節(jié)也是如此,城市(異地)與個(gè)體(故鄉(xiāng))之間齟齬的精神空間與失重的存在狀態(tài)再次得以復(fù)寫(xiě),“在別人的城市,出租房和公園的長(zhǎng)椅,甚至在圖書(shū)館旁紫色的竹林,那些你所說(shuō)的重與輕,都是別處的生活。就像群山中生銹的鐵軌,平行,筆直,卻又各自斑駁,失散。”在第10節(jié)中,這兩大生存空間的摩擦狀態(tài)再一次出現(xiàn),“他們一定經(jīng)過(guò)那里——沉寂的鐵軌和落寞的村莊。開(kāi)過(guò)花的道路上,雨水正消失。”對(duì)此,需要提醒寫(xiě)作者們(包括曉岸在內(nèi))注意的是要盡量避免倫理和道德的過(guò)多滲入,不能淪為簡(jiǎn)單的倒退式的自怨自艾的“鄉(xiāng)愁主義者”。顯然,曉岸已經(jīng)注意到了這一點(diǎn)。
寂靜、孤獨(dú)、焦慮、虛無(wú)以及死亡重新被大海與火山激活,它們一次次來(lái)到文本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而恒常如新的困窘與困惑猶如命運(yùn)所帶來(lái)的一個(gè)個(gè)悲欣交集的時(shí)刻。這是類似于“秋天的戲劇”的過(guò)渡與轉(zhuǎn)換時(shí)刻,所以,在曉岸的筆下,我們與群山、礁石、海岸線、灌木叢、秋風(fēng)、夕陽(yáng)、黃昏以及黑夜、星光迎面相撞,那些搖晃不已的風(fēng)中之樹(shù)以及游蕩者、夢(mèng)幻、沉默的思考者顯然是時(shí)間的寓言化對(duì)應(yīng),它們是命運(yùn)在四季輪回和時(shí)間更迭中不斷要面對(duì)的生命狀態(tài)。在第7節(jié)中,“自由”作為高頻詞附著在以大海為中心的場(chǎng)景中,它們出現(xiàn)的次數(shù)越多,與之對(duì)應(yīng)的個(gè)體的限囿和困惑就越是無(wú)法消解。
“星空”(“星光”“鏡子”“圓月”“航燈”“燈塔”“水手”)與“大海”作為垂直的精神維度構(gòu)成了一條永恒的時(shí)間之路,在既向上(回溯、記憶、幻象、矚望、黎明、遠(yuǎn)方)又向下(此刻、現(xiàn)世、命運(yùn)、黑夜)的路途中,那么多人在“蹈海”般的仰望、攀爬、探詢、抗辯、叩訪,那么多人試圖借助永恒的時(shí)間光梯或黑夜中的船帆把自己從人世的沉沉淵藪中拉拽和救贖上來(lái),“一個(gè)人躲在星光的后面,不停地擦拭著銅鏡,它帶來(lái)記憶的磨損抵消了你對(duì)大海的渴望。那些記憶順著大風(fēng)流淌的方向流失。而所有的帆,都在黑夜升起的地方靜默。//并不是每一種黑都來(lái)自于光,來(lái)自于困囿光的壁障。”然而,這一希緒弗斯和哈姆雷特式命運(yùn)獲啟的過(guò)程是如此之艱難,很多人在途中墜落到沉沉無(wú)邊的大海浪濤中去。于是,在“大海”的終極背景下一個(gè)“游蕩者”的形象出現(xiàn)了,“你似睡非睡,迎著暗光而去。迷離的光亮里,一只黑藍(lán)色的蝴蝶跟隨著你。它的翅膀扇動(dòng)著,極其細(xì)微的灰塵漂浮起來(lái)。仿佛有暗流召喚,那些閃著光的灰塵在你身體留下的影子中遁形。”
是的,在社會(huì)時(shí)間尤其是城市化、現(xiàn)代性時(shí)間的背景之下,我們目睹了越來(lái)越多的游離者、游蕩者,他們作為夜行者更多是在午夜或凌晨或夢(mèng)幻中出現(xiàn),往往面孔模糊、背影沉暗、語(yǔ)調(diào)駁雜。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大海與星空之下的“游蕩者”并不是自我放棄的精神孤兒,并不是沒(méi)有方向感的離群索居甚至自暴自棄,而恰恰是融合了哈姆雷特與希緒弗斯雙重性格的蹈海者、追問(wèn)者、探尋者以及精神自證者。
在靜寂和虛無(wú)中,他們胸腔中不斷發(fā)出號(hào)角般的聲響。他們?cè)诼o(wú)邊際的海岸線上向大海隨手扔出了漂流瓶,等待又一個(gè)命運(yùn)在萬(wàn)千偶然中將其撿拾、打開(kāi)。時(shí)間的秘密與存在的困惑已毋庸多言,這是被照徹又瞬間淹沒(méi)的時(shí)刻。瞧,那個(gè)精神游蕩者正在向我們?nèi)鐗?mèng)幻如迷霧般走來(lái),而我們可能正是這個(gè)游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