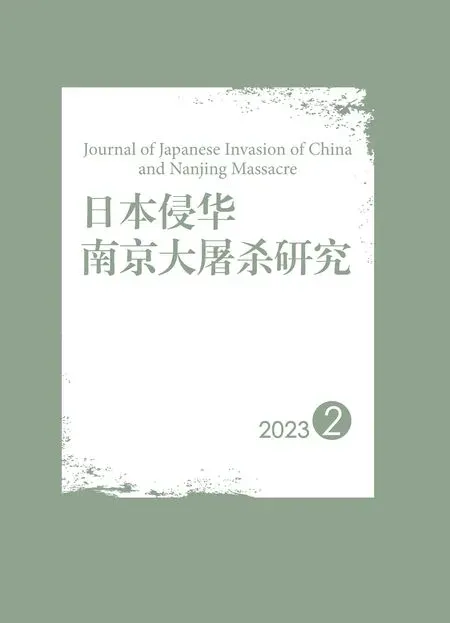華中日軍憲兵與南京大屠殺
王 萌
南京大屠殺是侵華日軍在華中淪陷區犯下的重大戰爭罪行。正如人們所理解的,憲兵的職責主要在于監察和維持軍紀,近代日本憲兵也不例外。南京大屠殺期間華中日軍軍風軍紀的極度紊亂,導致南京城內外無數慘案的發生,反映出日軍隨軍憲兵的嚴重失職。戰后,由原日軍憲兵組成的“憲友會”對此亦不得不承認,“南京事件對日軍而言,是作為一大污點而留在歷史上的,對于指揮官及憲兵而言,均為一大教訓”。(1)全國憲友會連合會編纂委員會『日本憲兵正史』、全國憲友會連合會本部、1976年、510頁。學界既往關于侵華戰爭時期日本在華憲兵的研究,主要在于揭露其對淪陷區民眾犯下的罪行,然而對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隨軍憲兵的動向及其失職問題卻鮮有關注。(2)中國學界對于近代以來日本在華憲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偽滿關東憲兵隊的組織、職能和暴行問題上,代表性成果如傅大中《關東憲兵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與霍燎原、潘啟貴主編《日偽憲兵與警察》(黑龍江出版社1996年版)等。程兆奇注意到淞滬會戰期間日軍第十軍配屬憲兵的失效與士兵軍紀紊亂之間的聯系,參見程兆奇《侵華日軍軍風紀研究——以第十軍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日本學界以大谷敬二郎、纐纈厚、荻野富士夫等學者的研究為代表,系統梳理了日本憲兵勢力在本國及臺灣、朝鮮等殖民地不斷擴展的歷史脈絡,具體參見大谷敬二郎『憲兵』(新人物往來社、1973年)、纐纈厚『憲兵政治:監視と恫喝の時代』(新日本出版社、2008年)與荻野富士夫『日本憲兵史 思想憲兵と野戦憲兵』(小樽商科大學出版會、2018年)等。其中,荻野較為詳細地考察了全面侵華戰爭時期日軍憲兵在華北、華中、華南淪陷區的組織網絡,然而未涉及日軍憲兵參與南京大屠殺等重大事件的情況。日軍隨軍憲兵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面對日軍官兵的暴行為何不能履行其職責?此后華中日軍憲兵的“權威”又是如何樹立的?本文希望結合如上問題,考察南京大屠殺期間隨軍憲兵的動向,以及大屠殺前后華中日軍憲兵在組織與職能上的變化,揭示其與華中日軍軍風軍紀之間的聯系。
一、日軍憲兵在淞滬及其周邊戰場上的失職
憲兵是近代日本政府模仿西方兵制的產物。1881年1月,日本政府在陸軍部內設立憲兵,不久頒布《憲兵條例》,其第一條規定:“憲兵位于陸軍兵科之一部,執掌巡按檢察之事。視察軍人之非行,兼有行政警察與司法警察之事。兼隸內務、海軍、司法三省,負責國內安寧。”(3)田崎治久『日本之憲兵』、軍事警察雑誌社、1913年、517頁。由此可見,日軍憲兵自設立之初即擁有對官兵的檢察權,兼掌行政、司法警察的職權。此后,憲兵的權限不斷擴大,從監察軍風軍紀,延伸至對民眾運動的鎮壓、對社會思潮的監控等,其職能“不如說,比之普通警察,乃掌握更廣泛警察業務的警察機關”。(4)憲兵司令部『日本憲兵昭和史』、巌南堂書店、1939年、6頁。
駐華憲兵伴隨日本軍隊對中國領土的侵略與駐屯而出現。日俄戰爭結束后不久,日本成立關東憲兵隊,是為日本對華派駐憲兵之始。日本學者將戰前日本憲兵分為兩類,即1920年代以來在日本國內實行恐怖統治的“思想憲兵”,與1930—1940年代在傀儡國家、日軍占領地實施殖民統治的“野戰憲兵”。(5)荻野富士夫『日本憲兵史 思想憲兵と野戦憲兵』、緒言9頁。事實上,偽滿洲國成立后,關東憲兵隊逐步形成較為嚴密的組織系統,在職能上兼具“思想憲兵”與“野戰憲兵”雙重角色。關東憲兵隊成為日本軍國主義鎮壓偽滿境內抗日力量的“利器”,其所推行的“思想對策”工作,乃“對于妨礙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并統治中國東北的一切思想和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采取的行動予以鎮壓、逮捕、殺害或投入監獄”(6)《關于思想對策的罪行》,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偽滿警察統治》,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57頁。,可謂臭名昭著。
除東北淪陷區之外,日本還在沿海沿江口岸日租界或勢力范圍內派駐憲兵。全面抗戰爆發后,駐華各地的日軍憲兵分隊迅速投入情報搜集等工作,為日本軍國主義進一步侵華而服務。在淞滬會戰前夜,日軍駐上海憲兵分隊即派出憲兵下士官大前旭及翻譯,前往上海北站附近偵察國民黨軍的運輸情況與保安隊的備戰狀況。從日方檔案可見,日軍駐上海憲兵分隊很早就在當地廣羅間諜,建立情報網絡。如大前旭于1936年秋抵達上海后,在南市中國人旅社中獨居的數月間“完成密探網絡之基礎,屢屢提供有力之情報等,一貫至誠熱心精勵于勤務”。(7)「在上海憲兵下士官及通訳生死不明ニ関スル件報告」(1937年8月23日)、『支受大日記(普)其1 2/2 第1號の2 12冊の內 昭和13年自1月11日至2月4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普大日記-S13-2-144。
淞滬會戰爆發后,日軍駐上海憲兵分隊的情報搜集活動極為猖獗,源源不斷為日本軍部與在華中作戰的日軍提供情報,但另一方面,僅30人的日軍駐上海憲兵分隊,基本未被投入治安維持方面的工作。(8)長期以來,日軍駐上海憲兵僅5人。1936年9月日本憲兵司令官中島朝今吾向陸軍大臣寺內壽一建議,增派駐上海憲兵至30人。這些憲兵“在并無遺憾地完成本來任務的同時,要充分協助陸戰隊的警備工作,且要抓緊搜集情報及從事對領事館警察、工部局公安局警察、在鄉軍人等的指導工作”,參見「上海憲兵増強に関する件」(1936年9月25日)、『昭和11年 「陸満密綴9.16—11.13」』、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満密大日記-S11-10-42。據日軍第十軍軍醫早尾虎雄觀察,11月下旬日軍占領地區內完全不見憲兵的蹤影,“每日每夜中國人的空屋處于被焚燒的狀態,甚至連撲火者都沒有。日人街區很多店鋪都未開張,也沒有所謂的慰安所,私設的賣淫屋不過在暗夜中私下交易”。(9)早尾乕雄「戦場心理の研究」、岡田靖夫解説『戦場心理の研究』第1冊、不二出版、2009年、227頁。當時日軍占領區內的治安,主要由日本海軍陸戰隊維持。因日本軍部已向上海派遣軍下達進攻南京的指令,故對士兵酗酒斗毆等違反軍紀的行為,海軍陸戰隊大多采取視而不見乃至縱容的態度。淞滬會戰后華中日軍官兵肆意違反軍紀的心態,正如時為第三師團士兵曾根一夫所解讀的:“上海激戰結束后,大家本以為可以好好歇一下的,沒想到又接著準備一場難以想象的大規模戰役,這對士兵打擊很大……大家想這次恐怕是活不了了。因此情緒變得自暴自棄。”在曾根看來,日軍官兵的放縱心理導致軍風軍紀的紊亂,“我認為‘南京屠殺’就是這時才開始萌芽的”。(10)曾根一夫:《我所記錄的南京屠殺》,王衛星編:《日軍官兵與隨軍記者回憶》,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10冊,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268頁。
另一方面,在淞滬周邊戰場,激烈戰斗與強行軍導致日軍后勤補給遲滯。因給養困難,日軍士兵四處搶掠,出現大量與之伴生的惡行。為了避免日后受到檢舉,日本士兵在作惡后往往殺人滅口,制造更大的慘案。第十軍憲兵隊長上砂勝七意識到隨軍憲兵人數過少的問題,“無奈相對于幾個師團20萬的大軍,只配備不足百人的憲兵,這無論如何是管制不了的”。盡管一些軍官呼吁增加憲兵或輔助憲兵以維持軍風軍紀,但在上砂看來,憲兵人數不足的問題在戰事激烈的狀態下難以解決,“在大敵當前的進攻推進中,各部隊都希望使用盡可能多的兵力,根本不會同意我們的要求。我們只能制止實在看不下去的現行犯”。(11)上砂勝七『憲兵三十一年』、東京ライフ社、1955年、176頁。在急行軍期間,隨軍憲兵在官兵眼中如同擺設。面對官兵的暴行,憲兵僅在被占領城市和村莊的主要場所張貼“預防火災、杜絕盜竊、愛護居民”等告示,“委婉”地加以提醒。即便如此,憲兵的勸阻仍會受到一些部隊軍官的質疑與斥責,“這次隨軍的憲兵到底是日本軍隊的憲兵,還是中國軍隊的憲兵?管的實在太寬了!”(12)上砂勝七『憲兵三十一年』、177頁。
淞滬會戰爆發以后,華中日軍憲兵主要由上海派遣軍、第十軍隨軍憲兵,以及原駐上海憲兵組成,有130余人。憲兵作為主掌監察軍風軍紀的軍事警察,其職責正如《憲兵服務規程》所規定的:“憲兵對于軍人軍屬違反(軍法軍紀)的行為或認為有違反之虞時,對于同級以下者直接糾正之;對于上級者,要使其注意。”(13)憲兵司令部『日本憲兵昭和史』、1035頁。不難看出,華中日軍憲兵在淞滬及周邊戰場未能履行這一職責,從開始便出現失職的問題。這一反常現象,固然與日軍占領區憲兵數量較少且主要從事情報工作有關,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一線部隊的指揮官為了達到盡快攻占南京、擴大戰果的目的,唯我獨尊,驕橫無忌,對于下屬官兵從事掠奪等違反軍法軍紀的行為采取漠視、袒護的態度,導致憲兵地位不彰、威信受損。
二、南京大屠殺期間隨軍憲兵的失職問題
當日軍士兵在淞滬及周邊地區肆意掠奪,最終上升至拒絕上級命令、無視日本國際形象的地步時,日本軍部并不會袖手旁觀。1937年11月,第十軍隨軍憲兵向該軍法務部報告了大量士兵從事掠奪暴行等軍紀廢弛的現象,法務部由此向該軍司令官提出整肅軍紀,避免引起國際問題的建議。(14)「第十軍(柳川兵団)法務部陣中日誌」、高橋正衛編『続·現代史資料6 軍事警察』、みすず書房、2004年、29頁。不久,日本軍部派出若干參謀,以指導作戰的名義前往前線,參謀們開始指揮隨軍憲兵,追查所謂的“現行犯”。
在攻占南京前夕,日軍參謀本部向上海派遣軍及第十軍下達指令,“若是中國軍隊并不接受投降勸告,12月10日下午即開始進攻。進入城內部隊的行動如上記同樣處理,特別要嚴肅軍風紀,盡快恢復城內治安”。參謀本部在傳達的注意事項中強調,“對于掠奪行為或雖因不注意而失火的行為,要加以嚴厲處罰。使多數的憲兵及輔助憲兵與軍隊同時入城,防止不法行為”。(15)全國憲友會連合會編纂委員會『日本憲兵正史』、505頁。然而,日本軍部的指令并未起到任何作用,華中日軍上層沒有派遣多數憲兵同時入城。淪陷后的南京,戰爭暴行無處不在,日軍官兵視軍風軍紀為無物,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對此感嘆,“今日我軍價值竟如此低落”。(16)「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會編『南京戦史資料集』、偕行社、1989年、229頁。
事實上,南京淪陷后日軍憲兵的情報工作并未間斷,如第十軍隨軍憲兵始終密切關注底層官兵的思想動向,在給該軍法務部的報告中記錄了一些底層士兵對長官辱罵、掌摑等“下克上”的現象。(17)「第十軍(柳川兵団)法務部陣中日誌」、參見高橋正衛編『続·現代史資料6 軍事警察』、60頁。正是通過隨軍憲兵的報告,華中日軍上層確切了解到大屠殺期間底層官兵違反軍紀的情況與嚴重程度,如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上村利道在日記中坦言:“根據憲兵報告,軍紀上的違反者相當多。而召集少尉、準尉級寡廉鮮恥的行為,實在令人遺憾至極”。(18)「上村利道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會編『南京戦史資料集』、275頁。但另一方面,面對日軍官兵大肆違反軍紀的行為,隨軍憲兵未能對之加以糾察與阻止,對于南京城內外無數慘案的發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戰后,“憲友會”以及不少原日軍憲兵,均述及南京大屠殺期間隨軍憲兵的失職問題。他們大多強調憲兵人數過少之說,如“憲友會”表示,“淪陷當初南京并無一名憲兵,12月17日與松井司令官同行入城的憲兵,憲兵長以下僅17名……在南京發生不幸事件,遺憾的是,12月13日至17日期間憲兵并不在南京”。(19)全國憲友會連合會編纂委員會『日本憲兵正史』、510頁。原華中派遣憲兵隊隊員志村毅在談及隨軍憲兵對于南京大屠殺的責任問題時,認為“無論如何,若為事實,作為沒能制止日軍殘暴行徑的憲兵之一員,應該深刻反省……憲兵在日本軍隊里一方面有擔負維持治安的任務,另一方面也有管制那些對中國平民施以非法殘暴行為的義務。這一說法或有狡辯嫌疑,但是,當時在約兩三萬人的師團中僅有約50名憲兵,可以說,要防范過激軍事行動以及暴力行為于未然,幾乎是并不可能的”。(20)志村毅「戦爭を知らない世代に語り継ぐ」、創価學會青年部反戦出版委員會『揚子江が哭いている——熊本第六師団大陸出兵の記録』、第三文明社、1979年、187頁。作為這一說的延伸,也有將憲兵失職問題歸因為戰事緊張者,“在中國大陸,正規憲兵主要在占領后的地域內才能夠實現任務……然而虐殺行為絕大多數發生在占領前的進攻中。第六師團絕大多數前線士兵的從軍記說明,他們大都置身于日夜行軍戰斗的‘進攻’階段。故而憲兵之手幾乎無法涉及,呈現出相當矛盾的狀態”。(21)「座談會 熊本編を終えて」、創価學會青年部反戦出版委員會『揚子江が哭いている——熊本第六師団大陸出兵の記録』、197頁。不難看出,這些說法基本處于為隨軍憲兵辯護的立場,強調其失職的客觀原因,并未觸及失職問題的本質。事實上,無論是留守南京的外僑,還是當時日軍其他官兵,對于隨軍憲兵的失職問題都有較為深刻的揭露。
在大屠殺初期,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即向日軍提出,希望在安全區入口設置崗哨阻止士兵進入,同時建議日軍立即派出憲兵維持治安。外僑拉貝等人期望日軍憲兵能夠切實履行其軍事警察的職責,即“晝夜在安全區巡邏,對于偷竊、搶劫、強奸或搶奪婦女的士兵,憲兵有權逮捕”。(22)[德]約翰·拉貝著,劉海寧等譯:《拉貝日記》,江蘇人民出版社、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頁。面對外僑的反復申訴,日本駐南京外交官員“僅限于作些有關憲兵的微不足道的許諾”。(23)《1937年12月16日至27日金陵大學與日本大使館通信副本及其按語》,陸束屏編譯:《歷史上的黑暗一頁——英國外交文件與英美海軍檔案中的南京大屠殺》,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頁。12月19日,日軍派出4名憲兵守衛金陵女子文理學院。(24)[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譯:《魏特琳日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3頁。這使外僑一度認為,“我們向日本大使館提出的抗議奏效了”。(25)[德]約翰·拉貝著,劉海寧等譯:《拉貝日記》,第166頁。
然而,外僑很快對日軍憲兵的表現感到失望,“我們知道有憲兵在,但是他們人數太少,也太文雅,不能維持軍紀”。(26)《南京美國財產與權益的狀況》(1938年2月28日),陸束屏編譯:《忍辱負重的使命——美國外交官記載的南京大屠殺與劫后的社會狀況》,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26頁。他們發現,盡管有若干憲兵在難民聚集的建筑門口站崗放哨,然而日本士兵到處爬墻越舍,毫無顧忌;盡管金陵大學圖書館等文教場所與難民營的門上貼有憲兵所書禁止入內的布告,然而日本士兵將之撕毀后,公然闖入掠奪財物或強奸婦女。當看到有士兵就在日本使館大門附近實施強奸時,金陵大學緊急委員會主席貝德士諷刺道:“這難道就是貴國的幾個憲兵重新恢復秩序的跡象嗎?”(27)[德]約翰·拉貝著,劉海寧等譯:《拉貝日記》,第199頁。當傳教士魏特琳看到上海路上小販兜售贓物時,她在日記中寫道:“很顯然,留下來的少數中國警察沒有相應的權力,而為數不多的日本憲兵連自己的士兵都管不住,更不要說管老百姓了。”(28)[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譯:《魏特琳日記》,第178頁。因與日軍憲兵經常打交道,拉貝在寫給日本使館的信中較為委婉地提到其失職問題,“如果執行上街巡邏命令的憲兵能增加雙崗,以便在個別的房子中搜尋并且逮捕士兵,那么總的局勢就會迅速改觀”。(29)[德]約翰·拉貝著,劉海寧等譯:《拉貝日記》,第208頁。魏特琳對于涉及日軍憲兵的申訴亦持謹慎態度,認為“要講策略,否則,可能引起這些士兵的仇恨。對我們來說,這可能比我們目前遇到的麻煩更糟”。(30)[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譯:《魏特琳日記》,第154頁。
日軍官兵的記述則較外僑更為直接。步兵少尉前田吉彥目睹士兵在南京城內肆意掠奪,他在日記中批評道:“憲兵正在干什么啊!要立即對他們加以管制,確立軍紀!”(31)「前田吉彥少尉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會編『南京戦史資料集』、467頁。日軍航空兵軍曹井手純二在回憶錄中寫下身處下關碼頭等大屠殺現場時的觀感:“日本軍的軍紀為什么會如此墮落呢?……且說在現場,哨兵和憲兵都不在,行動很自由,甚至拍照都是可能的。”(32)井手純二:《我所目睹的南京慘劇》,王衛星編,葉琳、李斌等譯:《日軍官兵日記與回憶》下,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61冊,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52頁。一些日軍官兵的日記中記載了憲兵失職的現象,如第十軍參謀山崎正男看到一個憲兵欲制止軍官酒后喧鬧卻反被其撲倒的窘狀,暗諷憲兵的軟弱。(33)「山崎正男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會編『南京戦史資料集』、409頁。1938年1月26日,美國駐南京領事館官員愛利生在前往日軍軍營調查一起強奸案時遭到日軍官兵毆打,是為“愛利生事件”。指揮毆打愛利生的軍官天野,還犯下強奸、傷害、掠奪等多種罪行,憲兵對其亦無可奈何,“可以理解,法學士、律師鉆了法網的空子。對于憲兵的調查答辯頗為巧妙。未必可見會受嚴重處分”。(34)「上村利道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會編『南京戦史資料集』、294—295頁。
南京淪陷之初,華中日軍中上層沉浸于“膺懲中國”、炫耀戰功的狂熱氣氛之中,并未對淞滬會戰以來軍風軍紀紊亂的問題加以重視,由此導致大屠殺期間隨軍憲兵在日軍中的“權威”進一步失墜。無論是留守外僑,還是現地日軍官兵,均認為憲兵對于底層官兵缺乏基本的約束力,面對暴行幾乎無所作為,其無能與怯弱助長日軍官兵的作惡氣焰,致使軍風軍紀更為敗壞。
三、南京淪陷后日軍憲兵參與暴行
盡管普通官兵對于隨軍憲兵的觀感不佳,一些原華中日軍上層軍官卻對其高度贊譽,如原華中方面軍發言人宇都宮直賢在戰后稱:“憲兵在南京城內的舉止的確優秀,他們軍紀嚴明,就連外國記者也很佩服。”(35)宇都宮直賢:《黃河、揚子江、珠江——回憶在中國的工作》,王衛星編:《日軍官兵與隨軍記者回憶》,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10冊,第13頁。為了維護日軍形象,隨軍憲兵在與外僑的接觸中往往表現出較為溫和、友善的一面,有時也會勸止士兵對外僑的騷擾,從而獲得一些外僑的好感。但是,大量史實表明,隨軍憲兵對待中國民眾表現出蠻橫、兇殘的另一面,其參與對中國民眾的諸種暴行,同樣為軍風軍紀的破壞者。
日軍憲兵以“檢舉”抗日力量為名義,肆意屠戮南京軍民。戰后,“憲友會”關于大屠殺期間日軍憲兵是否參與“檢舉”工作表述模糊,稱“日軍在檢索便衣士兵之際,若由憲兵為之則較為熟練,然而一般部隊官兵并無此經驗。故而對于一般民眾與便衣士兵的辨別就很困難,超過必要程度的嚴酷檢出與處置,由此留下了很大禍根”。(36)全國憲友會連合會編纂委員會『日本憲兵正史』、510頁。顯然,“憲友會”的說法,意圖通過否定隨軍憲兵參與“檢舉”工作而為其開脫罪責。大量資料表明,隨軍憲兵不僅參與“檢舉”或搜捕工作,而且大開殺戒,其兇殘與普通官兵無異。如12月15日步兵第七聯隊隊部命令全隊官兵次日向難民區出發,徹底搜捕殲滅國民黨殘余士兵,要求隨軍憲兵隊協助聯隊。(37)歩兵第七連隊「戦闘詳報」(1937年12月7日—12月24日)、南京戦史編集委員會編『南京戦史資料集』、622頁。值得注意的是,步兵第七聯隊的戰斗詳報說明當時南京城內并非沒有隨軍憲兵。顯然,憲友會的說法有誤。又如一些外僑所見聞的,在1938年元旦當日,“‘舉止似乎文明一些’的憲兵今天抓捕了一些普通士兵,理由是有嚴重的不軌行為。據說這些士兵被槍斃了”。(38)[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譯:《魏特琳日記》,第166頁。事實上,華中日軍上層并不否認憲兵參與搜捕工作,如飯沼守在日記中記載,南京淪陷后憲兵即開始在城內大肆搜捕“抗日力量”,“憲兵不斷逮捕潛伏于南京難民區域或外國大使館等地的不逞之徒,主要包括保安隊長、八十八師副師長等”。(39)「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會編『南京戦史資料集』、233頁。松井石根的副官岡田尚在證言中亦提到,“也有進入難民區對中國士兵的搜捕。搜捕由憲兵來執行,據說中國兵從帽子痕跡上就能被發現”。(40)「松井軍司令官付·岡田尚氏の証言」、阿羅健一『聞き書 南京事件』、図書出版社、1987年、28頁。另外,日軍憲兵不僅參與“檢舉”或搜捕工作,而且直接策劃慘案。據曾根一夫記載,因懷疑南京郊外某個村莊具有“很強的抗日情緒”,在隨軍憲兵的策劃下,日軍部隊趁村民午飯之際偷襲并屠戮了整個村莊。(41)曾根一夫:《我所記錄的南京屠殺》,王衛星編:《日軍官兵與隨軍記者回憶》,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10冊,第306頁。
日軍憲兵參與對“慰安婦”的暴行。憲兵強征中國婦女為“慰安婦”的行為,在第十軍參謀山崎正男的日記中有明確記述:“寺田中佐指導憲兵,在湖州設置娛樂機關。憲兵透露,要征集百人左右。”(42)「山崎正男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會編『南京戦史資料集』、411頁。山崎所述的強征之地雖非南京,然可證實憲兵強征中國婦女的暴行確實存在;憲兵維持慰安所“秩序”的場面,在第十六師團衛生兵上羽武一郎的日記中有詳實記述,“妓女也出來迎接了,但是70名妓女接待500名士兵不知要等到什么時候,我只好算了。士兵們排成兩隊哇哇亂叫,憲兵吃力地維持著秩序,面對這些女人誰不想大干一場呢!”(43)上羽武一郎:《上羽武一郎陣中日記》,王衛星編:《日軍官兵日記》,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8冊,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86頁。諸如此類憲兵維持慰安所“秩序”的場景,在東史郎日記中也有記載。(44)東史郎『我が南京プラトーン——一召集兵の體験した南京大虐殺』、青木書店、1987年、120頁。
大屠殺期間日軍憲兵從事強奸、掠奪的暴行,在外僑的記述中屢見不鮮。英國外交部駐華官員豪爾在報告中談及1938年初南京城內日軍憲兵參與搶掠的情況,“‘恢復軍紀’的確是極度漫不經心,甚至憲兵也強奸、搶劫,無視他們的職責……有好幾天,我們一個憲兵也沒有看到。最近,將特殊的袖章發給日本兵,稱他們為憲兵,這意味著他們對自己的不端行為擁有特殊的保護,并且不必履行某些日常的職責”。(45)《豪爾致外交部128號電報》(1938年1月10日),陸束屏編譯:《歷史上的黑暗一頁——英國外交文件與英美海軍檔案中的南京大屠殺》,第65、68頁。魏特琳觀察到,“今天(1938年1月13日),我發現一名日本憲兵和一個日本士兵在外國人的住宅里搶劫”。(46)[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譯:《魏特琳日記》,第178頁。中方人員也記載了日軍憲兵參與暴行的事實,如避難于難民區原美國大使館內的國民黨軍軍醫蔣公榖揭露,“使館自前幾天屢被敵人搶劫,經國際委員會及美僑向敵方提出抗議后,敵方派中島部隊憲兵四人來守衛,各房間都來看了一次,遇到有婦女的,就嬉皮笑臉地進去坐坐,還要討香煙吸。進出都被限制,反而不方便起來。一到晚上,他們還不是同樣的跑出去做那搶劫奸擄的勾當。嚇,倒算是憲兵呢!”(47)蔣公榖:《陷京三月記》,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頁。
日軍官兵在日記中同樣記載憲兵恣意戕害中國民眾的暴行。上村利道在日記中提到一起令人不明所以的“宮崎憲兵事件”,“宮崎憲兵大尉存在越權行為……宮崎憲兵的行動越聽越感到其非常識且違規行為很多。實在令人難辦”。(48)「上村利道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會編『南京戦史資料集』、290頁。若參看第十六師團參謀木佐木久的日記,大概可知這一事件的端倪,即憲兵宮崎為掩蓋自己的失職,惡意迫害兩名無辜的中國女子,木佐對此評價道:“我對于所謂的憲兵者,未嘗帶有惡感,然而就本次事件,感到極度憎惡。使我軍的名譽、南京的軍紀失墜的究竟是誰?甚而要剝奪這兩個可憐女子的生命。不得不感到強烈義憤。”(49)「木佐木久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會編『南京戦史資料集』、431頁。
大屠殺期間日軍憲兵對中國民眾濫施暴行的現象,成為此后日本統治南京的常態。這一期間隨軍憲兵所表現出的殘暴性,也為日后的南京憲兵隊所承繼。曾根一夫切身觀察到南京憲兵隊對當地民眾施暴的肆意性:
這兒所謂的“大掃除”,并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室內室外的清掃。憲兵隊的“大掃除”指的是把作為嫌疑犯抓進來的關押人員全部處死。
“這么隨隨便便就把人殺了,如果有冤枉的人怎么辦?”我這樣問道。對我的提問,成瀨(憲兵名——引者注)顯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傲慢地說道:“凡是被憲兵隊盯上抓捕來的人,不分有罪無罪,全部作有罪處理。就算你沒有罪,拷問之后就作有罪處理。頑固的家伙就嚴刑拷打。拷打致死的,就編造一份有利的調查記錄作為有罪處理,這樣案子就結了。關鍵是以什么方式處死他們,所以問題不在于他們是否有罪。”
這簡直是無法無天。之所以本國人和外國人都懼怕“東洋魔王”,就是因為日本憲兵隊就是這樣一個可怕的地方。以前我就聽說,只要被抓進憲兵隊,就不可能活著回來。現在看來的確如此。(50)曾根一夫:《我所記錄的南京屠殺》,王衛星編:《日軍官兵與隨軍記者回憶》,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10冊,第326頁。
從曾根的這段記述可見,南京憲兵隊專以拷掠為能事,毫無法紀觀念可言,其殘暴性、肆意性與大屠殺期間隨軍憲兵對暴行的參與可謂一脈相承。然而,與大屠殺期間隨軍憲兵分散化、小規模的作惡活動不同,南京憲兵隊對中國民眾的暴行更具組織化、常態化,刻意營造出憲兵政治的恐怖氣氛及其對淪陷區民眾的威懾力,由此成為淪陷時期南京民眾與外僑聞之色變的“魔窟”。事實上,南京憲兵隊的所作所為,可謂戰時日軍野戰憲兵對中國淪陷區實施恐怖統治的縮影。
四、華中派遣憲兵隊的編成與憲兵“權威”的樹立
南京淪陷后華中日軍制造各種慘案,嚴重破壞日本軍政當局歷來所宣傳的軍紀嚴明形象。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對此不無感嘆:“不料我軍南京入城之際,發生諸多暴行奪掠之事,乃至于我軍有不少損傷威德之處。”(51)松井大將「支那事変日誌抜粋」、南京戦史編集委員會編『南京戦史資料集』、48頁。在大屠殺經歷一個階段后,參謀長塚田攻在向各部隊的通牒中強調:“希望此際對軍風軍紀的維持振作投入最大努力……其中軍紀軍風方面,令人顧忌的事態近來漸漸頻繁發生。”(52)「軍紀風紀ニ関スル件」(1938年1月9日)、『支受大日記(密)其2 昭和13年自1月14日至1月26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3-1-110。鑒于“(南京)令人顧忌的事態業已發生”,在攻占杭州前夕,華中日軍上層要求隨軍憲兵入城后要切實履行職能,尤其當日軍官兵因戰斗需要而侵損到在杭外國人權益時,“要盡可能講求當地解決之手段,同時不失時機地向集團司令部及最近憲兵報告與通報”。華中日軍上層認識到增加憲兵數量的必要性,要求參與攻城的第十八、第一○一兩個師團各派出一個中隊作為補充憲兵,至日本駐杭州領事館附近加強巡視。(53)「杭州占領に伴う秩序維持及配宿等に関する件」(1937年12月20日)、『陸支密大日記 第49號 2/2 昭和15年』、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5-126-221。
1937年11月,華中方面軍成立。考慮到日軍將長期駐屯華中淪陷區,日本軍部在攻陷南京之前即仿效偽滿關東憲兵隊,籌備成立專門的華中日軍憲兵部隊。軍部將這支部隊命名為“華中派遣憲兵隊”,規定其在組織上隸屬華中方面軍司令官,設總部于上海,在職能上主掌華中方面軍行動區域內的治安工作及軍事警察業務。(54)「中支那派遣憲兵隊臨時動員要領、細則の件」(1937年12月9日)、『陸支機密大日記 第7冊 2/2 共7冊 第12號の2 昭和13年』、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機密大日記-S13-19-109。在編成規模上,軍部將原配屬于華中日軍的102名隨軍憲兵擴充至400名后就地編入華中派遣憲兵隊,并將該部隊司令官的階級定為與聯隊隊長同等的大佐級。按日本軍部的規劃,華中派遣憲兵隊下設上海、南京、杭州三個憲兵隊,其中南京憲兵隊設隊本部與三支分隊,含官兵共計119人。(55)「中支那派遣憲兵隊ノ編成配置及服務ニ関スル件報告」(1938年1月12日)、『支受大日記(密)其4 昭和13年自2月1日至2月2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3-2-111。1937年12月18日松井石根下達指令,上海派遣軍于南京憲兵隊管區內設軍律會議,處理由該管區內違反軍律者引起的案件。然而,直至1938年1月10日,華中派遣憲兵隊方告編成。
伴隨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中日戰事的失敗,日本陷入戰爭泥沼。如何動用一切軍政力量,形成對中國淪陷區的長效殖民統治,成為日本軍政當局開始思考的課題。伴隨華中派遣憲兵隊的正式編成,華中方面軍司令部隨即出臺《華中派遣憲兵隊服務規定》,進一步明確該部隊的職能細節與業務范圍,如第四條規定“憲兵要注意區域內諸情況,將必要事項不失時機地報告、通報華中方面軍司令官及各軍司令官”、第六條規定“憲兵協助治安及宣撫工作,使其目的易于達成”、第八條規定“憲兵要經常視察軍人軍屬之行為,警戒預防其非法行為”等。(56)「中支那派遣憲兵隊服務規定」(1938年1月10日)、『支受大日記(密)其4 昭和13年自2月1日至2月2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3-2-111。
松井石根還向華中派遣憲兵隊司令官大木繁作出訓示,強調這支部隊對于華中日軍維持占領區內社會治安以及下一步作戰的重要意義,“事變爆發以來已歷數月,我軍給予敵軍致命打擊,現已攻陷首都南京,如今我軍欲使行動區域安定,進而充實戰力,準備下一期作戰。此際迎來精強之華中派遣憲兵隊,可為我軍于實力上增添一大戰力”。或許松井已注意到南京淪陷后憲兵的失職問題,他特別強調“憲兵的行動必須作為一般軍隊及所在民眾的模范”,在業務方面要充分“自省自戒”,尤其要注意避免引起國際糾紛:
目前之狀況,要牢記保安及軍事警察之業務特別重要,對于所在民眾致力于警防綏服之同時,要無遺憾地使軍隊之統率及行動變得更為容易。為能以寡少兵力而盡其任,要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業務重點……對于如陷入職權濫用、受到軍民彈責等,不可馬虎對待。要嚴格自戒自律,且在我軍行動地域內國際關系十分復雜,列國的權益錯綜,鑒于此,要經常以公正妥當態度處理之,不可釀造事端。(57)「中支那派遣憲兵隊長に與ふる訓示の件」(1938年1月13日)、『支受大日記(密)其2 昭和13年自1月14日至1月26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3-1-110。
從如上《服務規定》與松井訓示中可見,華中派遣憲兵隊自成立之初,即被授予極大的權限,其職能并不僅限于約束軍風軍紀,而且涉及日本對淪陷區民政工作、特務工作等多方面;其業務范圍可視其活動區域的實際情況而變動,具有很大靈活性。以隸屬南京憲兵隊的常州憲兵分遣隊為例,在1938年1月下旬駐屯常州日軍的衛戍會報中,詳細記載該分遣隊要求當地官兵必須注意的事項,除“防止未發之犯罪”“嚴格管制非法行為,尤其是掠奪”“絕對不許進入禁止入內的房屋”“不得對婦女施暴”“嚴格要求外出者的服裝及敬禮姿態”“各部隊一般外出時要向憲兵分遣隊通報”等整肅軍風軍紀方面的事項之外,還包括“協商小賣部商品價格”“特別注意通信上的防諜”“對于身體檢查結果不合格的娼妓,不使之從事交易行為”等方面的內容。(58)「陣中日誌 自昭和13年1月1日至昭和13年1月31日 獨立攻城重砲兵第2大隊本部(4)」、『獨立攻城重砲兵第2大隊 陣中日誌 昭和12年12月1日—13年1月31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支那事変上海·南京-230。
日本軍部與華中日軍上層在華中派遣憲兵隊編成后,有意識地樹立其“權威”。華中方面軍參謀長塚田攻特別指派一批憲兵進駐南京、鎮江、上海等地船舶運輸機關,嚴格檢查歸國日軍官兵攜帶的物品,尤其禁止他們將從南京等地掠取的中國貨幣、有價證券、金銀器件、藥品、鴉片等攜帶回國。作為加強憲兵“權威”的重要措施,“各部隊長要講求萬全之處置方式,不得使部下回避以上檢查,私下將物品出售、隱匿、破壞等,若發現有如此情況則處以嚴懲”。(59)「鹵獲及押収品引継並內地攜行貨物に関する件」(1938年2月8日)、『支受大日記(密)其8 昭和13年自2月24日至2月27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3-5-114。憲兵嚴查歸國官兵攜帶的物品,使不少官兵在南京等地所犯的掠奪罪行暴露,由此引起他們的恐慌。當時日軍官兵對憲兵的恐懼心理,如早尾虎雄所分析的:
按當時戰士思考角度,認為如對敵地物品加以占據,即可隨意自由處置,此亦無可奈何之情況。金銀財寶、被服、絨毛類、中國衣服等,大量被作為私物寄回國內。故有回國之際私物檢查之流程。在中國所得之物、所購之物一概禁止帶回國內。此完全系憲兵之工作。因存此實情,士兵心中對于憲兵之恐懼超過想象。故其在病態中對于軍法會議、憲兵、處刑、死刑、自首等詞多有交織。此種情況在國內未嘗可見。(60)早尾乕雄「戦場心理の研究」、岡田靖夫解説『戦場心理の研究』第1冊、231頁。
此外,通過使憲兵嚴厲查處官兵酗酒、毆斗、失儀等違反軍紀的行為,進一步強化其“權威”。在上海方面,據早尾虎雄觀察,1938年1月初,日軍占領區內酒館徹夜狂歡,醉步蹣跚的士兵哼著小曲嬉笑逐鬧,毫無軍紀意識。盡管街頭有不少憲兵巡視,“然而眼中相當寬大不加咎責,只要深夜不喧鬧,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并不妨礙他們去享樂”。華中派遣憲兵隊成立后不久,華中方面軍司令部即向上海派遣軍下達《上海市內(不含南市)軍人軍屬管理規定》,要求當地巡察及憲兵要嚴格監視態度不良的軍人軍屬,對于過分者現場加以糾正,且要警視敬禮規范,將不良者通報所屬部隊。(61)「中支那方面軍軍法會議陣中日誌」、高橋正衛編『続·現代史資料6 軍事警察』、133頁。2月,上海憲兵隊加大整治官兵酗酒斗毆等行為的力度,對于尋釁滋事者,“結果必然毫不客氣對之檢舉”。(62)早尾乕雄「戦場心理の研究」、岡田靖夫解説『戦場心理の研究』第1冊、230頁。在南京方面,“愛利生事件”發生后,日本外務部門遭到美方嚴重抗議,南京憲兵隊隊長小山彌即向華中日軍上層提出增加輔助憲兵與增設城內憲兵派出所等建議。(63)「飯沼守日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會編『南京戦史資料集』、243—244頁。不久,南京日軍特務機關宣布設置打給憲兵隊的報警電話,并在主要馬路出入口安排憲兵監視士兵舉止等,以此加強對駐南京日軍部隊軍風軍紀的約束。(64)「被占領側から見た日本軍の南京占領」、南京戦史編集委員會編『南京戦史資料集』、776頁。據拉貝觀察,1938年1月末以后,南京主要街口已有憲兵把守,禁止日軍士兵隨意在街上游蕩。在某些案件中,一些日軍士兵被憲兵當場逮住并拘捕,“憲兵的數量正日益增加,治安狀況也將隨之好轉”。(65)[德]約翰·拉貝著,劉海寧等譯:《拉貝日記》,第448—449頁。
華中派遣憲兵隊對軍紀的整肅工作自2月“開始活躍起來”,至4月徐州會戰前后憲兵在華中日軍中的“權威”得以完全樹立,“全軍全面緊張,面目一新。所謂憲兵之觀念開始浸入士兵們的頭腦中,大概是從這一時刻開始的”。(66)早尾乕雄「戦場心理の研究」、岡田靖夫解説『戦場心理の研究』第1冊、227、229—230頁。然而,伴隨華中日軍憲兵“權威”的樹立與強化,底層官兵對憲兵的恐懼心理也在不斷渲染,曾根一夫注意到“當時日軍士兵普遍恐懼憲兵隊的介入”“憲兵隊成為士兵們最厭惡的地方,士兵們都畏懼、憎恨憲兵。即使沒做虧心事。見了憲兵都會避開”。(67)曾根一夫:《我所記錄的南京屠殺》,王衛星編:《日軍官兵與隨軍記者回憶》,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10冊,第301、326頁。
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華中日軍憲兵“權威”的樹立,特務工作逐步成為戰地憲兵的核心職能,監察軍風軍紀的本職反而日漸淡化。井上源吉作為原華中派遣憲兵隊隊員,曾經對戰時華中憲兵職能上的這一轉變有所說明:“說到其任務,在戰地憲兵本來任務管制軍紀之外,情報搜集、思想戰對策、中國民眾對策、宣撫宣傳、對第三國人的保護、對交戰國人的監視等,幾乎掌管所有部門。因此,除重大的掠奪暴行、強奸事件之外,必然處于馬馬虎虎應付原本任務的狀態”。井上還提到,作為華中日軍基層形態的野戰憲兵,在從事特務工作中獲得不受監督、獨斷專擅的執行權與處置權,“特別是對于被派遣到遠隔之地的派遣隊長、分遣隊長,因被授予法的范圍內的某種獨斷執行權,故而根據不同情況,甚而連作為特務機關的任務,或屬于軍政方面的施策,也通過憲兵之手來進行”。(68)井上源吉『戦地憲兵』、図書出版社、1980年、123頁。志村毅描述了野戰憲兵從事特務工作的場景,“在某個戰場上,憲兵只是乘坐著跨斗式摩托車或是騎馬來到駐扎地,聽取情況后又馬不停蹄地返回。而間諜則由憲兵拷問”。(69)志村毅「戦爭を知らない世代に語り継ぐ」、創価學會青年部反戦出版委員會『揚子江が哭いている——熊本第六師団大陸出兵の記録』、189頁。聯系上文所述南京憲兵隊對中國民眾“生殺予奪”的肆意性,就不難想見日軍野戰憲兵手握何等無羈的權力。
結 語
南京大屠殺期間諸多慘案的發生,與華中日軍憲兵存在密切關聯。淞滬會戰結束之后,華中日軍憲兵面對軍中滋生的酗酒斗毆等違紀行為采取漠視態度,對于官兵掠奪、強奸等戰爭暴行怯于阻止、揭露,從一開始就沒有在軍中樹立作為“軍事警察”的“權威”。南京淪陷后,僅有少量隨軍憲兵進入城內,他們對于日軍官兵制造的暴行,依舊采取熟視無睹甚而姑息縱容的態度,導致憲兵的“權威”進一步失墜。需要指出的是,大屠殺期間隨軍憲兵不僅未能成為維護軍風軍紀的表率,且與普通官兵同流合污,同樣扮演戰爭暴行制造者的角色。
全面侵華戰爭初期華中日軍憲兵“權威”的失墜,應被視為一種反常現象。淞滬會戰以來,華中日軍上層為盡快實現攻陷南京、迫使國民政府屈服的目標,利用各種手段強化部隊戰力,甚而通過犧牲軍風軍紀,以激發底層官兵的蠻勇。隨著戰事的平靖,樹立憲兵在軍中的“權威”,成為日本軍部與華中日軍上層加強其對部隊統制力、重塑日軍“軍紀嚴明”形象的重要舉措。南京大屠殺期間隨軍憲兵出現的失職問題,又促使日本軍部與華中日軍上層加快這一進程。
隨著華中派遣憲兵隊的編成,華中日軍憲兵在組織和職能上發生明顯變化。華中派遣憲兵隊一改原日軍隨軍憲兵臨時、松散的組織形態,逐步形成“華中方面軍—華中派遣憲兵隊—主要都市憲兵隊—基層地區憲兵分隊(派遣隊)”的垂直隸屬結構,其組織嚴密性大為提高。至1945年時,華中派遣憲兵隊下屬分隊數達35支,憲兵網絡基本涵蓋華中淪陷區內主要城鎮(70)參見荻野富士夫『日本憲兵史 思想憲兵と野戦憲兵』、255頁。,野戰憲兵成為戰時日本對華中淪陷區實施殖民統治的基干力量;在職能上,華中派遣憲兵隊被授予更為廣泛的權限,其業務逐步集中于特務工作,行政、司法警察的職能凸顯,軍事警察的職能弱化。
華中憲兵“權威”的樹立,是否改變了華中日軍軍風軍紀的面貌?南京大屠殺之后,華中派遣憲兵隊在一份關于南京治安狀況的調查報告中提到,“駐屯各地的日軍官兵仍沉浸于戰勝之勢頭,遂致軍風軍紀渙散,敢于從事各種犯罪活動,給居民生活帶來不安。因各上司、機關給予適當的指導和管理,目前軍風軍紀趨好”(71)《關于南京憲兵隊轄區治安恢復狀況的調查報告(通牒)》(1938年2月19日),莊嚴主編:《鐵證如山——吉林省新發掘日本侵華檔案研究》,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版,第62頁。,以此說明在短時期內憲兵的整肅工作取得良好的效果。1943年7月,華中派遣憲兵隊教習隊制定《軍事警察勤務教程》,其中較長時段地考察了華中日軍軍風軍紀的變化:
中國事變爆發之初,即南京陷落不久之際,華中軍人軍屬的惡行犯罪頗多,特別以對上官冒犯等惡性軍紀犯為首,辱職、掠奪、強奸等令人厭惡的犯罪頻發,其后因上司的指導得當與官兵的自覺而逐漸減少……雖然犯罪漸減的傾向如前所述,然而若觀察其惡質程度,則難稱良好。即逃亡、企圖免除兵役、自傷等戰爭倦怠厭惡乃至觀望凱旋等,志氣戰意消沉,或基于破壞軍紀軍秩以下犯上的思想意識,冒犯長官之類行為有所增加,尤其是出現內容惡質化的傾向。另外,對中國人的掠奪、強奸等相關犯罪不絕其跡。(72)「軍事警察勤務教程」、高橋正衛編『続·現代史資料6 軍事警察』、447—448頁。
從這段記錄可見,南京大屠殺之后憲兵突擊性的整肅工作,并未使日軍官兵形成對軍法軍紀敬畏的心理。雖然官兵的犯罪數量有所減少,然而其所犯罪行的性質更為“惡劣”。軍心渙散、“下克上”等問題在華中日軍中日益突出,底層官兵對中國民眾的掠奪、強奸等戰爭犯罪行為頻繁發生。這一報告揭示了南京大屠殺后華中日軍憲兵基于官兵恐懼心理所樹立的“權威”,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戰地日軍軍風頹廢、軍紀敗壞的實相。
然而另一方面,在日本軍部的扶持下,以野戰憲兵為形態的華中日軍憲兵卻掌握了不受監督、獨斷專擅的執行權與處置權,其在淪陷區基層肆意作惡、橫行無忌,通過制造各種慘案,營造恐怖氣氛,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威懾淪陷區普通民眾、鎮壓抗日力量的“爪牙”。戰爭時代,華中日軍憲兵聲名狼藉,不少人戰后成為國民政府指名的戰犯,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日軍憲兵作為法理上的軍風軍紀維護者,在現實中則是軍風軍紀的破壞者,這一矛盾性事實上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即已暴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