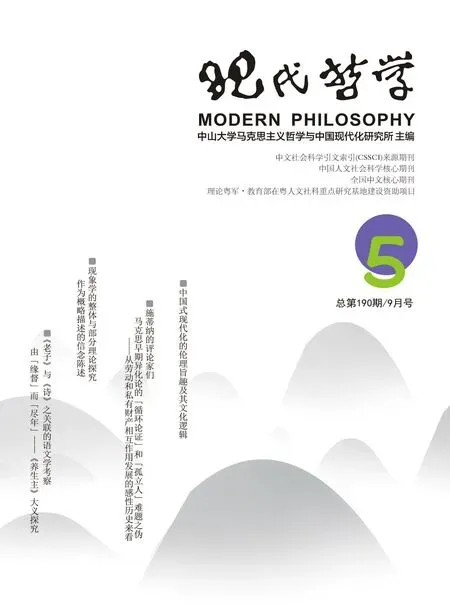《老子》與《詩》之關聯的語文學考察
鄧聯合
《詩經》之名確立于漢武帝時期,此前它被稱為《詩》或《詩三百》。作為早期經典,《詩》不僅是先秦諸子共享的思想資源,更是那個時代“士以上階層的最重要的通識教育科目”,習《詩》、誦《詩》則是貴族間“文化交往和語言交往的基本方式和手段”(1)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時代的宗教、倫理與社會思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66頁。,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關于《詩》對古代學者的深刻影響,清代學者劉開說:“夫古圣賢立言,未有不取資于是《詩》者也。道德之精微,天人之相與;彝倫之所以昭,性情之所以著;顯而為政事,幽而為鬼神,于《詩》無不可證。故論學論治,皆莫能外焉。”(2)劉開:《讀詩說》,轉引自張豐乾:《可與言〈詩〉--中國哲學的本根時代》,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第49頁。確如劉開所言,先秦諸子著述多引《詩》、論《詩》,其中尤以儒家為甚。從道家學派來看,即便是對推重《詩》的儒家多作激烈批評的《莊子》,也不僅數次明確提及《詩》,其思想和文本還與《詩》有著微妙的隱性關聯。(3)參見鄧聯合、趙佳佳:《〈莊子〉與〈詩〉的顯隱關聯發微》,《中國哲學史》2022年第4期。迥異于《莊子》,《老子》全書對《詩》卻只字未提(4)當然,《老子》全書也未明確引述或提及其他早期經典。,無論是以褒或貶的方式,但這并不意味著二者全無關聯。事實上,就老子本人而言,身為主藏書之事的“周守藏室之史”(《史記·老子列傳》)或所謂“征藏史”(《莊子·天道》),他必定熟知《詩》,并極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受到《詩》的影響。
先看一條春秋時期史官引《詩》論事的記載。據《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趙簡子問史墨:“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對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史墨所引《詩》句見小雅《十月之交》。從《左傳》的這條記載可以看出:首先,史官群體不僅熟悉《詩》,而且擅長發掘和運用某些詩句蘊涵的哲理,以“斷章取義”的方式推類論說現實政治問題;其次,史墨所引《詩》句“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近通于《老子》的相反相生思想,如第二章所說“高下相傾”。(5)若無特別標注,本文所引《老子》皆依王弼本。
此外,《莊子》外篇所載老子與孔子涉及《詩》的兩則對話也值得關注。其一,《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老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其二,《天道》篇:“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于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愿聞其要。’”這里所說的“十二經”雖所指不詳,且與《天運》篇提及的“六經”極可能都是晚出的儒家經典總名(6)參見張恒壽:《莊子新探》,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9-160、173頁。,但想必其中包括《詩》。這兩則對話雖皆為真假難定的寓言,但至少表明一點:在“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史記·莊子列傳》)的莊子學派看來,老子熟悉《詩》的內容和精神旨趣,故而貶其為“先王之陳跡”。
基于上述原因,筆者認為,雖然《老子》未曾提及《詩》,但鑒于《詩》對包括老子在內的先秦諸子以及它在漢代升格為“經”之后對學者所具有的廣泛、持久的影響,如果仔細考察《老子》從郭店本到王弼本的復雜演變歷程,將不同時期的《老子》傳本與《詩經》相對照,那么就會發現《老子》在成書之初就已受到《詩》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在此后的文本演變中還愈加深入。本文擬從語文學的進路探討《老子》與《詩》的關聯,二者的思想關聯暫存而不論。
一、文 體
關于《老子》的文體,學界曾有不同看法。在上世紀的老學論爭中,顧頡剛認為《老子》是賦體,而賦體乃戰國末期的新興文體,故《老子》應成書于《呂氏春秋》與《淮南子》之間;(7)顧頡剛:《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古史辨》第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81頁。馮友蘭認為《老子》應成于《論語》《孟子》后,非問答體,而是屬于戰國時期的“簡明之‘經’體”;(8)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210頁。錢穆認為詩、史、論是古代文體演進的三種先后形態,記言記事之“史體”必晚于詩,論又晚于史,而《老子》之文體乃“論之尤進”者,故應晚出于《孟子》《荀子》后。(9)錢穆:《莊老通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102-103頁。對于這些論斷的疏失處,詹劍鋒已作出有力辯駁(10)參見詹劍鋒:《老子其人其書及其道論》,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4頁。,茲不贅述。
檢討顧、馮、錢的上述觀點可見,三位學者都把《老子》的文體性質與其成書年代這兩個不同問題并合討論。他們之所以斷定《老子》成書較晚,且誤認其文體為賦、經或論,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他們未能得見戰國寫本的郭店《老子》(11)關于郭店本《老子》的成書時間,大致有戰國早期、戰國中期、春秋末期三種說法。(參見裘錫圭:《郭店〈老子〉簡初探》,《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29-30頁;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第9頁;許抗生:《初讀郭店竹簡〈老子〉》,姜廣輝主編:《郭店竹簡研究》(《中國哲學》第20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3頁;郭沂:《楚簡〈老子〉與老子公案》,《郭店竹簡研究》,第119頁。),其所依據的都是較晚的漢魏時期的王弼本。1990年代,郭店本的面世從根本上推翻了各種《老子》晚出說,同時為我們考察該書的本貌提供了直接的文本依據。老子為春秋晚期的史官,因此討論《老子》(尤其是早期傳本)的文體特點及其生成背景,較為切當的方法是把郭店本與春秋時期的史官言論相對照。
史官的一個重要職責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老子》第14章),或推“天道”以明人事,即通過援引過往的社會歷史經驗和政治教訓,或基于他們所洞見的“天道”--宇宙萬物的普遍法則,對統治者的行為提出解釋、批評或箴諫。從《左傳》《國語》所載史官言論可見,其所述多有較為抽象且高度凝練、蘊意精深的斷語或格言,這些斷語或格言往往是史官針對現實所作的政治和道德話語演繹的前提性法則。例如,《左傳》:“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僖公十五年)“(史墨)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昭公三十二年)《國語》:“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周語》)“史蘇朝,告大夫曰:‘……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晉語》)將史官的這類言論與郭店本乃至王弼本《老子》的大多數篇章相對照,可發現二者的言說風格非常相似,以至于如果把這類史官言論寫入《老子》,也不會顯得捍格不入。其不同在于,郭店本《老子》展開了形而上的深邃思考,并創造性地將“道”樹立為獨立自存的本體,提出了“有狀成,先天地生……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反也者,道動也”“道恒亡名”(《老子》甲組)(12)本文所引郭店本《老子》,參見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劉笑敢:《老子古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等重要思想,因此屬于哲學文本,而非史官話語的簡單匯編之作。
郭店本《老子》的文本形式雖然總體上可歸為與史官話語相類的格言體,但其中許多篇句已不同程度地表現出詩的特點。一般來說,詩區別于其他文體的特點是抒情化、形象化,且句式規整、注重韻律和修辭。以下首先從句式和韻律兩個方面分析《詩》對《老子》的影響。
(一)句式。據劉笑敢統計,在《詩經》的305篇詩中,有152篇是純粹的四言詩,140篇以四言為主,雜以三言、五言、六言或七言,只有13篇是其他形式的雜言詩。也就是說,《詩經》是以四字句為主,并輔以其他變化。(13)參見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5年,第14-15頁。依此來看郭店本《老子》,其句式雖長短錯雜不一,但三組簡文中像《詩經》那樣的整齊、連續的四字句也不可謂少。例如,甲組:“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亡有;絕偽棄詐,民復孝慈。”“果而弗伐,果而弗驕,果而弗矜。”乙組:“明道如昧,夷道如繢,□道若退。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建德如□,□真如愉。大方亡隅,大器曼成,大音祇聲,天象亡形。”“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盅,其用不窮。大巧若拙,大成若詘,大直若屈。”丙組:“故大道廢,安有仁義;六親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安有貞臣。”顯然,在后世的帛書本以至王弼本中,整齊、連續的四字句更多,限于篇幅,此不詳舉。
(二)韻律。古今多有學者發現,《老子》文本的一大特點是入韻。例如,清人呂履恒說:“上下五千言,固多韻語。”(14)轉引自李波:《“〈莊〉之妙,得于〈詩〉”--明清〈莊子〉散文評點的詩性審美》,《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第18頁。劉師培說:“周代之書,其純用韻文者,舍《易經》《離騷》而外,莫若《老子》。”(15)轉引自譚家健、鄭君華:《先秦散文綱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1頁。此外,顧頡剛、胡適、錢穆、陳榮捷等學者也認為《老子》是押韻的。(16)參見顧頡剛:《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古史辨》第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86頁;胡適:《與馮友蘭先生論〈老子〉問題書》,《古史辨》第4冊,第418頁;錢穆:《莊老通辨》,第103頁;陳榮捷:《中國哲學論集》,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年,第180頁。按孫雍長的統計,《老子》全書用韻共計426處,其用韻特點是自由寬緩。(17)孫雍長:《〈老子〉韻讀研究》,《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朱謙之在其著《老子校釋》中除了以附錄的形式詳列《老子》全書韻例外,還特別指出了《老子》用韻與《詩經》之相合者。(18)參見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13-332頁。更進一步,劉笑敢通過“窮盡性的統計比較”,發現《老子》的用韻方式更接近于《詩經》而不是《楚辭》,由此他推斷“《老子》顯然是在《詩經》的風格影響下的產物”(19)參見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第一章“從《詩經》《楚辭》看《老子》的年代”。。筆者大致贊同前輩學者的這些看法,但認為其中有一點明顯的不足:他們在探討《老子》的韻律特點乃至其與《詩經》的關系時,所考察的對象文本都是王弼本,而郭店本不在其研究視野內。劉笑敢雖然注意到不同時期《老子》傳本的語言差異,但受研究條件的限制,郭店本同樣未被納入其考察范圍,他在分析《老子》與《詩經》的關系時,也只是盡可能地引用相對古樸的帛書本,同時偶爾參照王弼本。
事實上,即便從郭店本這一迄今所見最早的《老子》文本看,其中許多篇句的韻式已有受到《詩》之影響的顯著痕跡。需要說明的是,劉笑敢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王力《詩經韻讀》、朱謙之《老子韻例》等前人成果,從句句入韻、疊句與疊韻、交韻、偶句韻、富韻、合韻等方面,詳細探討了《詩經》的韻式對《老子》的影響。筆者將借鑒這一研究進路,簡要分析郭店本《老子》的韻律特點。

除以上幾種句句韻,劉笑敢還特別指出,通行本《老子》第44章的韻式既可以說是句句韻,也可視為句中韻。值得注意的是,該章早已見于郭店本中,且兩個版本的文字幾乎完全相同:“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持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厚藏,必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甲組)依劉氏之說,其中的“身”“親”為真部,“貨”“多”為歌部,“亡”“病”“藏”為陽部,“愛”“費”為物部,“足”“辱”為屋部,“止”“殆”“久”為之部(20)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第36頁。,其韻式同時具有句句韻和句中韻的特點。
第二,疊句與疊韻。劉笑敢以通行本第59章為例,認為其中重復的“嗇”“早服”“重積德”“無不克”“莫知其極”都是帶著韻腳的疊句和疊韻,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該章同樣見于郭店本乙組,撇開簡文中的缺字,二者的文句和韻式幾乎完全一致,茲不詳引。此外,甲組:“未知牝牡之合朘怒,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咎莫憯乎欲得,禍莫大乎不知足,知足之為足,此恒足矣。”乙組:“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這三例顯然都是重復某個字或某幾個字的疊字為韻。
第三,偶句韻。劉笑敢指出,通行本第9章是典型的偶句韻,其中的“保”“守”“咎”“道”皆為幽部。(21)同上,第42頁。我們看到,該章也已見于郭店本甲組,且其采取的偶句韻式與通行本完全相同。此外,甲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圣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教不教,復眾之所過。”這兩段顯然也都是偶句韻。
第四,富韻。所謂富韻是指句末用同一個虛字(例如“之”“也”“乎”等),虛字前再加一個押韻的字,這樣就形成兩個字的韻腳。郭店本中的富韻之例,除劉笑敢提到的通行本第17章已見于丙組外(22)郭店本丙組:“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甲組還有幾例:“反也者,道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守中,篤也。萬物並作,居以須復也。”“金玉盈室,莫能守也;貴富驕,自遺咎也。”“有亡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萬物作而弗始也,為而弗恃也……夫唯弗居也,是以弗去也。”“其脆也,易判也;其幾也,易散也。”這幾例中的“動也”與“用也”、“篤也”與“復也”、“守也”與“咎也”、“生也”與“成也”“形也”“盈也”、“始也”與“恃也”、“居也”與“去也”、“判也”與“散也”,都分別構成富韻。
劉笑敢認為,《老子》中的句句韻、疊韻、偶句韻、富韻等韻式都明顯地同于《詩經》,而筆者的上述考察則表明,郭店本《老子》早已運用了這些同于《詩經》的韻式。除了以上幾種韻式,郭店本甲組:“豫乎□若冬涉川,猶乎其若畏四鄰,嚴乎其若客,渙乎其若釋,屯乎其如樸,坉乎其如濁。”筆者發現,這幾句都是以句中處于相同位置的虛字“乎”押韻。(23)如果按照劉笑敢的說法,王弼本第10章采取的就是以句末虛字“乎”押韻的方式:“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専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為乎?”這種句中用韻的方式在《詩經》中也有先例,如《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晚于郭店本的《老子》各本與《詩經》用韻方式的相同之處更多,鑒于古今學者對此已多有發明,故筆者不再展開討論。通過以上對郭店本《老子》與《詩經》在句式和韻律兩個方面之相同點的比較分析,可知《老子》在成書之初就已受到《詩》的影響,這種影響導致其中的某些文句已呈現出詩歌化的特點。
二、修 辭
正是因為《老子》許多篇句句式規整、講求韻律,所以任繼愈認為《老子》“是以詩的形式寫出的”(24)任繼愈:《老子新譯》(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9頁。,朱謙之則說“《老子》為哲學詩,其用韻較《詩經》為自由”(25)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32頁。。除了用韻,《老子》的許多篇句作為“詩”還運用了擬人、排比、對偶、對比、比喻、頂真、復沓等多種修辭手法,而這些手法早已常見于《詩經》中。這里僅以頂真和復沓為例,討論《詩》在修辭方面對《老子》的影響。之所以只選擇頂真和復沓,是因為在《詩》《書》《易》等早于《老子》的經典文本中,惟有《詩》運用了這兩種修辭手法,《書》《易》中皆不見。
(一)復沓。復沓又稱復唱、疊章、重章迭句等,是指一首詩由若干章組成,各章主題、結構乃至句法基本相同,只在相應的局部變換少數字詞,從而形成反復詠唱、跌宕回環的藝術效果。從《詩經》全書來看,復沓是其中最典型尤其是國風運用最普遍的表現手法。運用復沓的詩篇或抒情或敘事,或兼抒情與敘事,各章之間的關系大致有兩種--平行和漸進。前者如《草蟲》,該詩首章、次章、末章的末句分別為“我心則降”“我心則說”“我心則夷”,其辭雖異,其情則類,三章平行共鳴。后者如《晨風》,其首章、次章、末章的第四句分別為“憂心欽欽”“憂心靡樂”“憂心如醉”,其辭前后各異,其情隨之愈加強烈,一章甚于一章,正如朱熹所云:“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如醉,則憂又甚矣。”(26)[宋]朱熹撰、趙長征點校:《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00頁。
復沓不見于郭店本《老子》,王弼本卻有3章明顯運用了平行復沓的手法。第11章:“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這三段的思想主旨和理路完全一致,其句法也基本相同,差別僅在于各段的句首以及各段末句中的“車”“器”“室”三字。再看第28章:“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這三段話的思想主旨、理路和句法結構也完全相同,只有首段的“雄”“雌”“谿”“離”“嬰兒”在第二段的同樣位置分別換為“白”“黑”“式”“忒”“無極”,在末段則相應換為“榮”“辱”“谷”“足”“樸”。此外,第49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這段文字雖然簡短,復沓的特點卻是顯而易見的。
(二)頂真。頂真又稱頂針、蟬聯、連珠、聯語等,是指“用前一句的結尾來做后一句的起頭,使鄰接的句子頭尾蟬聯”(27)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0頁。,從而形成環環相扣、文氣貫通、上遞下接、逐層推進的修辭效果。運用頂真手法的文句,用符號表示便是“A→B,B→C……”,其中連接上下句的B可以是一個字、詞或句子。頂真修辭在《詩經》中的運用雖不像復沓那樣普遍,但亦多有其例。據筆者統計,國風《行露》《江有汜》《簡兮》《相鼠》《中谷有蓷》《葛藟》、大雅《文王》《大明》《緜》《皇矣》《下武》《行葦》《既醉》《假樂》《板》《崧高》、周頌《良耜》、魯頌《有駜》等,都運用了頂真修辭。具體來看,用一個字連接上下句的,如《既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用一個詞連接上下句的,如《緜》“乃立皋門,皋門有伉”;用一個句子連接上下句的,如《相鼠》“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在郭店本《老子》中,甲組、乙組、丙組都有運用頂真修辭的文句:

甲組……吾強為之名曰大。大曰羨,羨曰,曰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對應王弼本第25章)侯王能守之,而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夫亦將知足,知足以靜……(對應王弼本第37章)……成功而弗居。夫唯弗居也……(對應王弼本第2章)……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對應王弼本第32章)乙組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對應王弼本第59章)
在王弼本中,運用頂真手法的篇句更多,除與上表所列相對應的句例,還有:

第1章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第3章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第6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第8章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第16章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第21章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其中有精。其精甚真。第23章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故從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第28章……為天下谿;為天下谿……為天下式;為天下式……為天下谷;為天下谷……第29章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第37章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第38章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第40章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第4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第52章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第56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70章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第74章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第81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綜括以上兩表可見,受到《詩》的影響,《老子》中運用頂真手法的篇章既多有用一個字或一個詞連接上下句之例,也不乏用一個句子連接上下句之例。而頂真句例從郭店本到王弼本的愈益增多則表明,在《老子》文本的演變中,《詩》的修辭手法的影響呈現出愈加深入擴大之勢。當然,作為哲學著作,《老子》運用頂真手法,絕不只是為了達到某種文學性的修辭效果,更是為了彰明思想環節的上遞下接、內在邏輯的逐次推衍,以及理論觀念的依序轉換、精神主旨的最終凸顯。
三、語 匯
不同于敘事性的散文、說理性的論文以及訓誥政令等其他文本形式,詩歌常運用一些特殊的語匯,以抒發某種情感,并達到富于節奏、朗朗上口,從而便于隨口誦唱流傳的效果,《詩經》的那些具有情感色彩的語氣詞和修辭性的大量疊字詞即屬此類。在這個方面,《詩》對《老子》文本的演變和生成也有顯著影響。
(一)語氣詞。《詩經》運用最普遍的語氣詞是“兮”,共出現300多次,它相當于現代漢語的“啊”或“呀”。對看《老子》,郭店本中不見“兮”字,其中的語氣詞多用“乎”“也”等。《莊子》雖被司馬遷認為“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史記·老子列傳》),外篇更被王夫之指為“但為老子作訓詁”(《莊子解·外篇序》),但通觀《莊子》全書,“兮”僅于內篇2見--“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人間世》),且與《老子》無關,而外雜篇中那些所謂“為老子作訓詁”,因此極有可能援引或轉述《老子》文句的《胠篋》《在宥》《天道》《天運》《徐無鬼》等篇,“兮”字卻并未出現。受到《詩》的影響,《老子》文本用“兮”字當在《莊子》之后的戰國晚期,這一點可以從其時幾部受《老子》的影響或闡發其思想的著作所引用或化用的《老子》文句看出來。
具體來說,《韓非子》全書引《老》有2句出現了“兮”字,分別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解老》)。成書于戰國晚期的《文子》(28)關于《文子》成書時間,參見裴健智:《〈文子〉文本及其思想研究》,博士學位論文,中國人民大學,2021年,第73-85頁。,書中引用或化用《老子》的文句則多見“兮”:
忽兮怳兮,不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道原》)
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氾兮若浮云。(同上)
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微明》)
為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上仁》)
此外,漢初《淮南子》引《老》也多見“兮”,例如:
忽兮怳兮,不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原道訓》)
其全也,純兮若樸;其散也,混兮若濁……澹兮其若深淵,泛兮其若浮云。(同上)
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道應訓》)
《文子》《淮南子》引《老》的上述文句,大致對應王弼本第21、15、20等章。帛書本中,“兮”皆換為“呵”。北大漢簡本中,“兮”或作“旖”,如下經第48、62、74章(分別對應王弼本第4、21、34章);或換為“虖”(乎),如上經第58章、下經第60章(分別對應王弼本第15、17章);此外,下經第61章(對應王弼本第20章)并用“旖”“虖”:“芒虖,未央哉……我旖未佻……絫旖,臺無所歸……我愚人之心也,屯屯虖……沒旖,其如晦;芒旖,其無所止。”
在王弼本《老子》中,帛書本的“呵”、漢簡本的“旖”和“虖”全部統一為“兮”,“兮”由此成為全書運用最多的語氣詞,共出現25次之多,即“淵兮似萬物之宗……湛兮似或存”(第4章);“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第15章);“悠兮其貴言”(第17章);“荒兮,其未央哉……我獨泊兮,其未兆……儽儽兮,若無所歸……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第20章);“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第21章);“寂兮寥兮,獨立不改”(第25章);“大道氾兮,其可左右”(第34章);“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第58章)。在晚于漢簡本、早于王弼本的河上公本中,相關語例幾乎與王本完全相同,惟王本第4章“淵兮似萬物之宗”一句,河本作“淵乎似萬物之宗”。值得注意的是,被許多學者認為其時代應與帛書本大致相當的傅奕本,書中“兮”字出現的情況也與王弼本基本一致。
在王弼本的上述語例中,有兩種“兮”字的用法尤其能說明《詩》對王本的影響。其一是第20章的“儽儽兮”,同樣的疊字詞后加“兮”的用法在《詩經》中頗多見,如“詵詵兮”“振振兮”“薨薨兮”“繩繩兮”“揖揖兮”“蟄蟄兮”(《螽斯》)、“脫脫兮”(《野有死麕》)、“渙渙兮”(《溱洧》)、“閑閑兮”“泄泄兮”(《十畝之間》)、“欒欒兮”“慱慱兮”(《素冠》),等等。其二是第21章的“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窈兮冥兮”,以及第25章的“寂兮寥兮”,這種一個句子(四字句)中有兩個“兮”字的用法也多見于《詩經》中,如“綠兮衣兮”“絺兮绤兮”(《綠衣》)、“父兮母兮”(《日月》)、“叔兮伯兮”“瑣兮尾兮”(《旄丘》)、“瑟兮僴兮,赫兮咺兮”“寬兮綽兮,猗重較兮”(《淇奧》)、“容兮遂兮”(《芄蘭》)、“伯兮朅兮”(《伯兮》),等等。相較于《詩經》,《楚辭》用“兮”雖然更多更頻繁,甚至可謂每言必用“兮”,但一個句子中用兩個“兮”的情況卻從未出現。基于此,如果再考慮到《楚辭》較少四字句,且其韻律形式與《老子》迥不相類,(29)劉笑敢指出,《楚辭》以六言或七言句為主,在王力《楚辭韻讀》所收28首《楚辭》中只有4首四言詩,其句式和韻式與《老子》差別較大。(參見劉笑敢:《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第19-23頁。)那么我們便只能認為《老子》中“兮”的用例是《詩》影響的結果。
(二)疊字詞。《詩經》運用了大量疊字詞。僅以國風周南為例,計有“關關”(《關雎》)、“萋萋”“喈喈”“莫莫”(《葛覃》)、“詵詵”“振振”“薨薨”“繩繩”“揖揖”“蟄蟄”(《螽斯》)、“夭夭”“灼灼”“蓁蓁”(《桃夭》),等等。《詩》之所以頻繁使用疊字詞,是因為這樣可以使詩句節律鏗鏘明快、音調優美,從而便于賦誦傳唱。
對看《老子》,與“兮”的用例一樣,郭店本沒有出現疊字詞,《韓非子》引《老》亦如此。與此不同,《文子》引《老》則有“綿綿若存,是謂天地根”(《精誠》);“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符言》);“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上禮》)。其后的《淮南子》引《老》有“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道應訓》),這里出現了“綿綿”“碌碌”“落落”“悶悶”“純純”“缺缺”等疊字詞。在漢代的各種《老子》傳本中,疊字詞更為多見:

帛書本漢簡本河上公本王弼本甲:綿綿呵若存乙:綿綿呵其若存第50章:綿虖若存第6章:綿綿若存第6章:綿綿若存甲:尋尋呵不可名也乙:尋尋呵不可命也第57章:臺臺微微不可命第14章:繩繩不可名第14章:繩繩不可名甲:天物雲雲乙:天物第59章:天物云云第16章:夫物蕓蕓第16章:夫物蕓蕓甲:眾人巸巸……累呵……蠢蠢呵……鬻…呵。鬻人蔡蔡,我獨乙:眾人巸巸……纍呵,佁無所歸……湷湷呵。鬻人昭昭,我獨若呵。鬻人蔡蔡,我獨閩閩。第61章:眾人巸巸……絫旖,臺無所歸……屯屯虖!猷人昭昭,我蜀若昏;猷人計計,我獨昏昏。第20章:眾人熙熙……乘乘兮,若無所歸……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第20章:眾人熙熙……儽儽兮,若無所歸……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甲:不欲若玉,珞。乙:不欲祿祿如玉,硌硌如石。第2章:不欲祿祿如玉。第39章: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第39章: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甲:……之在天下乙:圣人之在天下也,欱欱焉。第12章:圣人之在天下也,匧匧然。第49章:圣人在天下怵怵。第49章:圣人在天下歙歙。甲:其正察察,其邦夬夬。乙:其正,其民屯屯;其正察察,其……第21章:其正昏昏,其民萅萅;其正計計,其國夬夬。第58章: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第58章: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甲:缺此句乙:天罔第37章:天罔怪怪第73章:天網恢恢第73章:天網恢恢甲:10 乙:15151718
在《老子》運用的眾多疊字詞中,“昭昭”“繩繩”“綿綿”皆出自《詩》:“昭昭”見魯頌《泮水》“其音昭昭”;“繩繩”見周南《螽斯》“宜爾子孫,繩繩兮”,大雅《抑》“子孫繩繩”;“綿綿”見王風《葛藟》“綿綿葛藟”,大雅《綿》“綿綿瓜瓞”,《常武》“綿綿翼翼”,周頌《載芟》“綿綿其麃”。毋庸置疑,《老子》中的這三個疊字詞是其襲取《詩》的語匯的明證。從上述詞例統計可以看出,至遲自戰國晚期疊字詞始見于《老子》始,《老子》文本在漢代的演變過程中越來越多地使用疊字詞,其結果是相關篇句越來越表現出顯著的詩歌化特點。
通過以上對不同時期《老子》傳本中“兮”和疊字詞的用例分析,筆者推測:在《老子》文本的演變過程中,后世的傳承者對其篇句進行了修飾和增益;為達到便于隨口吟誦甚或配樂歌唱、利于授受流傳之目的,修飾者和增益者有意識地運用了疊字詞和“兮”“呵”“旖”“虖”等語氣詞,這顯然是受到《詩》的影響;而在漢代,最終在王弼本形成的時代,疊字詞之所以出現更多,“兮”之所以取代“呵”“旖”“虖”,成為《老子》全書運用最多的語氣詞,當是因為《詩》早已被官方確立為“經”,所以對學者產生了長久且更深刻的影響,使其在修飾、增益《老子》文本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借鑒了《詩》的語匯特點。
除了“兮”和疊字詞,《老子》中還有一些語匯與《詩》有關系,甚或取自《詩》。略舉數例:(1)作為《老子》最重要的思想概念之一,“無為”已多次出現于郭店本中(30)“無為”在郭店本甲組和乙組都寫作“亡為”,如甲組“是以圣人亡為,故亡敗……道恒亡為也”,乙組“以至亡為也,亡為而亡不為”,丙組“圣人無為,故無敗也”。劉笑敢援引語言學者的觀點,認為甲骨文中已有“無”字,但早期表示“有無”之“無”的,主要是“亡”而不是“無”。(參見劉笑敢:《老子古今》,第618頁。),這個詞最早見于《詩經》,如“我生之初,尚無為”(《兔爰》)、“寤寐無為”(《澤陂》),其意雖異,其詞則一;(31)關于《老子》與《詩經》中“無為”含義的異同,參見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64-65頁。(2)第10章“載營魄抱一”,“載”是語助詞,這種用法在《詩經》中極為常見,如“載驅薄薄”(《載驅》)、“八月載績”(《七月》)、“載馳載驅”(《皇皇者華》),等等;(3)第23章“飄風不終朝”,“飄風”出自《詩經》,如“其為飄風”(《何人斯》)、“飄風發發”(《蓼莪》)、“飄風自南”(《卷阿》)。此外,第51章“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對看《詩經·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二者的用語乃至句法都頗為相似。可以說,這些都是《詩》的語匯在《老子》中留下的痕跡。
四、結 語
作為中國思想文化的基源性經典,《詩》在先秦時期并非儒家的獨享品,而是包括老子在內的諸子百家在進行學術撰作時皆可取鑒的公共資源,其差別只在各家所取各異。到了漢代,由于《詩》被官方確立為“經”,借助政治意識形態長期的籠罩性力量,其對學者的熏染得到進一步強化。從客觀效應來看,《詩》既為其時傳播最廣泛、影響最深遠的經典,所以無論在思想還是文辭方面,《詩》對于學者的著書立說都具有范文的意義。以上從文體、修辭、語匯三方面梳理的《詩》在《老子》不同時期傳本中留下的痕跡,即可視為其范文效應在道家經典中的具體顯現。而這些痕跡在從早期的郭店本到較晚的王弼本中越來越多的出現,則表明《詩》是《老子》文本歷史性生成不可或缺的背景性經典,它不僅影響了《老子》這一道家立宗之作的初貌,而且始終伴隨并以獨特的方式深度參與了其后不同傳本的演變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