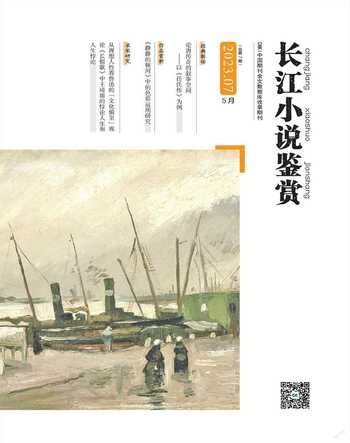石黑一雄《遠山淡影》中的女性創傷敘事
劉瑞鳳 齊雪艷
[摘? 要] 《遠山淡影》是石黑一雄創作最早的作品。這部作品以朦朧的筆觸展現了現代社會普通人遭受創傷的內心世界。主人公悅子在經歷戰爭后移居英國,又經歷喪女之痛。本文結合創傷理論和女性身份,分析《遠山淡影》中三位主要女性角色悅子、景子和藤原夫人的創傷原因以及創傷修復過程,這些女性在經歷創傷后或走向毀滅,或重拾信心,勇往直前。通過探討小說中女性經歷創傷后的成長軌跡,人們可以了解二戰后日本女性的生存狀況,她們不同程度的反抗也給予那些仍被邊緣化的女性鼓勵與力量。
[關鍵詞] 石黑一雄? 《遠山淡影》? 創傷? 女性
[中圖分類號] I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07-0089-04
日裔英籍小說家石黑一雄與奈保爾、拉什迪并稱為“英國移民文學三雄”。石黑一雄的移民身份,使他擅長于書寫戰爭文化與跨文化題材。不同于后兩位小說家鮮明的后殖民主義色彩,石黑一雄的作品,常以模糊的筆觸展現現代社會中普通人飽受創傷的內心世界,“創傷”是他作品中最鮮明的主題。關于《遠山淡影》這部作品,國內有賴艷、梅麗、楊芳、張勇等學者展開研究,重心放在戰爭記憶、自我欺騙、離散文學、身份焦慮等方面。然而,關于《遠山淡影》中女性創傷敘事的研究目前比較少,因此本文側重于從創傷理論和女性形象的角度出發,分析文中三位女性主人公的創傷經歷,并探究石黑一雄創傷書寫的意義。
一、創傷的表現
1.戰爭創傷
創傷源自古希臘文,原義是“受傷”,指的是加之于肉體的傷害,弗洛伊德認為創傷不止在肉體,更是加之于心靈的難以愈合的傷害。創傷的呈現方式有很多種,如回避、噩夢、閃回、驚恐、解離和麻木等。石黑一雄在《遠山淡影》中通過記憶閃回、主人公悅子與另一個自己“佐知子”內心對話的方式,塑造了這一歷經滄桑的女性形象,描寫女性成長的痛苦。
《遠山淡影》中人物經歷的實際時間是五天,而小說故事的時間跨度卻有十幾年,這主要來自悅子對戰爭的回憶。小說開頭,悅子回憶道:“那時最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這個日子指的就是美國向長崎投射原子彈,帶來災難性毀滅的一天。悅子在戰爭中失去了她的未婚夫。在續方先生后來的描述中,他收留了悅子,悅子當時的表現像個瘋子,甚至在半夜拉小提琴。這種類似“歇斯底里癥”的表現,正是悅子深受戰爭創傷的證明。戰爭對悅子的情緒、認知和記憶都產生嚴重而長期的改變,從而導致創傷后應激障礙,表現之一就是記憶閃回,即戰爭的傷痛始終揮之不去,即使早已時過境遷,受創者腦海里還是會不斷浮現當時的場景。因此,悅子想逃離日本,但移居英國后卻并未達到內心真正的平和,看似平靜的內心下仍是灰暗的戰爭陰霾。
如果說悅子作為成人尚且被戰爭傷害得如此之深,那么年幼的景子只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兒童是戰爭首當其沖的受害者,戰爭中兒童的利益往往最容易被犧牲。五六歲的景子在戰爭時目睹了一個發瘋的女人在水邊溺死自己的孩子,從此,這一幕成為她的童年陰影,景子常常抱著喜愛的貓咪自言自語,一次次說著“對岸有個女人”這樣令人毛骨悚然的話語。
因此,無論是悅子還是景子,她們都是戰爭這一集體創傷的受害者,都被這一集體創傷所裹挾。
2.家庭創傷
除了經歷戰爭帶來的創傷,《遠山淡影》中的女性還在無形中經歷了家庭創傷。悅子經歷的是男權社會的思想壓迫,特別是在恪守傳統文化的日本更是如此,女性的地位很低,只能順從丈夫的意志。悅子對丈夫二郎畢恭畢敬,即使懷孕也要事無巨細地侍奉丈夫和同事們吃晚飯。在探討夫妻雙方投票給不同政黨之時,續方先生說道:“現在的妻子都忘了對家庭的忠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選舉被看成是男性的特權,女性被剝奪了發表觀點的權利。這種要求女子全盤服從丈夫、服從家庭的觀念對女性的身心都產生了很大的壓抑,所以悅子第一段婚姻并不幸福。悅子的第二任丈夫也并未真正理解她,他和其他人一樣,認為日本這個民族好像無須多解釋,就是天生愛自殺。這種“不理解”甚至是詆毀的觀念體現了雙方地位的不對等。
法國作家露西·伊利格瑞認為女性在長期的父權制體系壓迫下會變得心理扭曲。二郎對悅子頤指氣使的態度足以印證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傷害——“我希望你別老亂動我的領帶。你在干什么呢?要知道我可沒有一早上的時間。”懷孕的悅子對丈夫的指示言聽計從,從未覺得有何不妥,甚至自我欺騙現在有了寶寶是最好的時機,丈夫有穩定的工作,自己很幸福。
不同于悅子的家庭創傷來自丈夫,景子的創傷主要來自父母的缺席。兒童時期遭遇的持續性創傷,會扭曲其尚未成型的性格,使其朝著不正常的方向發展[1]。危險發生時,兒童會向父母或兄弟姐妹尋求幫助。然而縱觀景子的一生,我們會發現景子從未和家人成功建立起親密關系。父親角色喪失,而母親一直熱衷于與新的男友弗蘭克交往,對小景子的內心世界缺乏關注。景子常常自言自語“河對面有個女人”,作為母親的悅子不僅沒有積極地幫助女兒擺脫陰影,反而把它看成景子發難時的小把戲。悅子甚至間接殺掉了景子最愛的小貓,只因為帶著它搬家是個累贅。她從未真正走進景子的內心,作為母親,她的角色實際上是缺位的。在悅子長時間的“放養”下,景子的內心創傷愈發嚴重,最后走上自殺的不歸路。
3.身份焦慮
作為移民作家,石黑一雄小說中的主人公或多或少都存在身份焦慮問題,身份焦慮帶來的孤獨感和疏離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物的創傷。“身份問題”這一概念始于埃里克森,埃里克森注意到:身份問題是個體的社會歸屬問題。當個人能夠取得所處社會的認同時,則可以建構身份,反之會產生身份焦慮。《遠山淡影》中悅子借助回憶得以重新思考自己與女兒的身份問題。
悅子經歷了兩次移民,第一次是從中川搬到長崎,之所以“國內移民”,是因為和表姐安子鬧了矛盾,她認為祖父家是一個有無數空房間的墳墓。悅子的“新家”是一所在戰爭炮火和政府推土機中幸存下來的小木屋,在這里悅子沒有身份認同感,周圍的女人對她議論紛紛。這種被孤立、被拋棄的感覺促成了悅子的身份焦慮。第二次移民是從日本到英國,與第一次移民不同,這一次體現的是東西兩種不同文化的矛盾沖突。由于文化隔膜與沖突,移民不同程度地體會到一種文化和心理層面的身份焦慮。悅子移居英國后寡居鄉村,過著一種“離群索居”的生活,悅子并未加入任何組織,唯一能成為她和日本文化紐帶的只有景子。景子的死切斷了悅子與日本的所有聯系,悅子回憶景子的過去也是對自己移民選擇的反思。
悅子從未真正融入這個國家,她寡居鄉村是因為她認為這是最像英國的地方,這個“像”證明悅子實際上并不理解英國文化,因此更談不上融入。因此,作為純日本血統的悅子,一方面經歷喪女之痛后失去了與母國的唯一紐帶,另一方面又無法完全融入當地文化。當初那個對異國滿懷期待,期盼在新的地方大展身手的悅子終究還是陷入了新的身份焦慮。
二、創傷的修復
1.重演創傷故事
創傷性事件發生后,該事件會持續在受創者的大腦中重復上演。因為創傷事件的發生,人腦的保護機制被全面摧毀,受創主體為了理解當時發生的事件,以及事件所引發的恐懼、憂慮等情緒,只能不斷在大腦中重復上演受創的瞬間,這種主觀意義上的不斷重演也被認為是創傷的一種形式。
《遠山淡影》中,敘述者悅子在回憶往昔和講述故事時,總能被讀者抓到把柄,她敘述的是一個當下的故事,即長女景子死后,自己在英國的生活。然而回憶的內容卻是“我”在日本期間和萬里子母女之間的交往,讀者讀到的故事是悅子把自己和景子的生活經歷轉嫁到虛構出來的萬里子母女身上。景子的死一直縈繞在悅子心中揮之不去,但是悅子在女兒妮基拜訪之后,提及秋千上的小女孩,才開始講述過去的故事。悅子的敘述一直在過去與現在之間跳躍。在回憶萬里子母女時,她的回憶是片段式的,悅子本人也無法確定記憶的真實性:“可能一個人都沒有,我不記得了。”悅子的回憶充滿矛盾和空白。這種不確定的回憶一方面是由于時間的流逝,另一方面是她的情感選擇,她不愿意承認內心真實的創傷,因此只能以含糊其詞的語言重建過去的創傷故事。石黑一雄說:“我喜歡回憶,是因為回憶是我們審視自己生活的過濾器。回憶模糊不清,就給自我欺騙提供了機會。”石黑一雄關注的不是創傷記憶真實與否,而是人們復雜的內心世界。
小說中作為旁觀者的悅子比母親佐知子更愛萬里子,佐知子是一個對女兒缺乏關愛的形象。當萬里子和佐知子因為移民問題爭吵時,佐知子對女兒說:“如果你不喜歡,我們會回來的。”這暗示了悅子對自己不計后果地把景子帶到英國而感到后悔,她是在和過去的自己對話:如果當初沒有離開,景子是不是就不會自殺了?景子在房間里上吊的畫面一直出現在悅子的腦海里——恐怖程度從未減弱,但是她早就不覺得這是什么病態的事了,就像人身上的傷口,久而久之就會熟悉最痛的部分。庫爾切寫道:“創傷記憶是毀滅性的經歷中無法被同化的碎片。”悅子對過往沉重事件的敘述是碎片化的,語氣是冷靜的,在回顧過去整理前因后果的過程中,從前的悲痛再度涌來,這有助于受創者宣泄壓抑已久的情緒,往事得以梳理,自我得到解脫。
2.重建聯系感
與外部世界建立聯系,是創傷修復的基礎,也是受創者必須經歷的過程。薩默菲爾德提出,受害者需要外界認可他們的創傷,因此關鍵不在于重返創傷記憶,而是在于重建文化身份。石黑一雄也提出當事者面對和接受創傷過去,是完成創傷修復的重要途徑。
《遠山淡影》中藤原夫人盡管和悅子一樣經歷了戰爭,失去了家人,但她積極地與周圍環境建立聯系,是唯一一個喚醒女性意識,實現經濟獨立的女性。通過做面館生意,藤原夫人慢慢走出創傷。她的丈夫曾經是長崎的重要人物。炸彈掉下來的時候,除了大兒子以外,其他家人都死了。經歷了如此之大的打擊,她還一直在堅持。面館生意使得她不再像戰前一樣,成為丈夫的附庸,而是勇敢地走出家庭,走向社會,與社會建立新的聯系。相似的創傷會產生群體認同。同樣經歷戰爭創傷的悅子在與藤原夫人的對話中汲取力量,獲得了繼續向前的勇氣,“每次我看見她,都對自己說:我應該像她那樣往前看。”藤原夫人幫助別人的過程,是她尋求和肯定自我的過程,也是她傳播獨立價值觀的過程。
創傷性事件破壞了個人與群體的關系,而群體團結則是減輕創傷傷害的最好方法。創傷的復原只可能發生在受創者與他人交流的情況下,不可能在隔絕中獨自完成。《遠山淡影》中悅子與大女兒景子并沒有建立親密的家庭關系,悅子對景子的心理需求常常放任不管,所以景子的自殺使得她明白自己作為母親是失敗和自私的。她開始對二女兒妮基溫和尊重,與二女兒溝通,理解她的生活方式,對女兒的需求盡量滿足,建立起一段正常的母女關系。
當受創主體在經歷敘述創傷、重建社會關系后,便實現與自己和解,在新世界中重生。悅子在小說結尾處坦然承認:“如今的我無限追悔以前對景子的態度。我一開始就知道她在這里不會幸福的。可我還是決定把她帶來。‘前些日子我突然想到,也許現在我該把房子賣了。”悅子不再選擇繼續住在這里,沉溺在景子死去的悲傷情緒中,而是坦然地面向新的生活。
三、創傷的價值與意義
1.撫慰創傷
20世紀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時代,戰爭、疾病等威脅著人類社會,創傷以前所未有的強度和廣度影響著人的生存。文學由于自身的再現功能,為創傷書寫提供了廣闊的土壤。作為移民作家的石黑一雄更加能體會現代化語境下的各種創傷,他和另外兩位移民作家奈保爾、拉什迪不同,他們的作品關注的重心是后殖民的種族創傷,而石黑一雄追求的是一種國際化寫作,他關注的是戰爭對全人類的傷害,是以人道主義的關懷視角無差別地再現戰爭給雙方帶來的傷害。即使是發動戰爭的日本,平民也經受摧殘,無論是婦女、兒童,還是成年男子,都或多或少地遭遇不幸。石黑一雄在撫慰創傷的同時也呈現了生命存在的意義。
對石黑一雄來說,創作從來都不是宣泄憤怒或狂躁的手段,而是用來紓解憂愁的,“現實世界并不完美,但作家能夠通過創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與現實抗衡,或者找到與之妥協的辦法”。生活中的每個人都會遭受創傷影響,我們要敢于直面傷痛,積極地尋找自我慰藉,從而找到生命的意義。
2.探索戰勝創傷新途徑
關于如何治愈創傷,一些學者已經給出了答案。朱迪斯·赫爾曼在《創傷與復原》中提出創傷的復原階段包括:恢復自主權、建立安全環境、回顧與哀悼、重建聯系感等。如果說朱迪斯·赫爾曼從理論角度指出了修復創傷的方法,那么作為小說家的石黑一雄則通過作品中主人公的具體事例,給予心靈受創者擺脫創傷記憶進而撫慰心靈的新渠道。
在石黑一雄的小說中,人物經過努力,幾乎都走出了創傷。治療創傷的第一種途徑就是幫助心靈受創者與外部世界積極地建立聯系,《遠山淡影》中,悅子通過與同樣經歷戰爭的藤原太太相處,被她積極樂觀的心態所打動,進而勇敢地走向新生活。藤原太太戰后重拾信心,以開小面館為生,實現了經濟獨立,與戰后社會重新建立聯系。打破自我隔離,重建人際關系是進行創傷復原的重要途徑,通過傾訴、交談,把內心的創傷情緒發泄出來,最后直面新的生活。石黑一雄小說中創傷書寫的意義,在于不僅表現了戰爭給人類帶來的無差別傷害,并且給予人類治療創傷的新途徑。
四、結語
《遠山淡影》是石黑一雄創作最早的一部小說。小說再現了悅子、藤原夫人、景子等女性經歷戰爭創傷、家庭創傷、身份焦慮后,或走向毀滅,或重拾信心的故事。悅子借“佐知子”的故事把自己的過去與現在相聯結,重建創傷故事,并與藤原太太積極交流,重新建立人際關系。悅子一改景子死后消極郁悶的情緒,轉為設身處地為二女兒妮基考慮,最終走出創傷,直面新的人生。石黑一雄的小說無差別地再現了戰爭給全人類帶來的傷害,撫慰創傷心靈,引導世人反思生命的意義,并給予世人走出創傷的新途徑,即直面創傷,積極地與他人建立聯系,實現經濟獨立。
參考文獻
[1]? ?赫爾曼.創傷與復原[M].楊大和,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
[2]? ?石黑一雄.遠山淡影[M].張曉意,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3]? ? 弗洛伊德.超越快樂原則[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
[4]? ?周穎.創傷視角下的石黑一雄小說研究[D].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2014.
[5]? ?王偉.論石黑一雄小說的創傷敘事[D].西安:西北大學,2017.
[6]? ?王飛.石黑一雄《遠山淡影》中的身份焦慮[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23(6).
[7]? ?陳瑩.戰爭創傷·帝國挽歌·記憶母題——論石黑一雄對戰后失序的道德思考[J].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18(1).
[8]? ?王婭姝.隱微、間性與世界主義——石黑一雄創作分析[J].文藝爭鳴,2020(2).
(責任編輯 夏? 波)
作者簡介:劉瑞鳳,伊犁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齊雪艷,文學博士,伊犁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