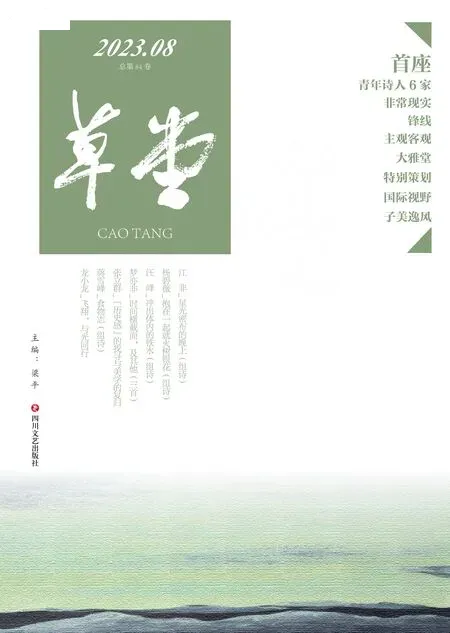僻 壤(組詩)
◎張二棍
[租房記]
小旅館,日租房,月租房……
無數(shù)個(gè)昏暗的房間里,盈蕩著種種
不可言說的氣息,等待著
下一個(gè)疲倦的人,來此酣然入夢
或輾轉(zhuǎn)反側(cè)。而墻角
一群窸窸窣窣的蟑螂,起身
向更加潮濕的地盤遷徙
它們不在意,房間里住著宿醉的
大盜,還是熬藥的小姐
仿佛它們才是這兒永恒的主人
一代代蟑螂們,在此無窮盡繁衍
虔誠又認(rèn)真。這浩瀚的房間
有它們的大道與歧途,也誕生了
它們的神跡、律法、恩典和罪過……
[重生記]
暮云低垂,地平線靜默如蒼生
我被幾聲似曾相識的鳥鳴,引誘至此
現(xiàn)在才懷疑,是幻聽
已太晚了。凝滯的空氣中,平日里
被遺忘的心跳,成了最大的動靜
仿佛一件剛剛出土的人形器皿
在無人處,漸漸復(fù)蘇。我終于
聽見了滴滴答答的血,在身體里
狼奔冢突。而我未曾目睹的
骨骼,也在皮囊之下,彼此
攙扶著,鼓舞著
撐起了我的每一寸肌膚
這妙不可言的時(shí)刻,萬物沉寂
我置身于黃昏的中央,獨(dú)自孕育
和撫養(yǎng)出,一個(gè)恍若隔世的新人
[易容術(shù)]
涂抹一點(diǎn)兒色彩,讓臉龐明亮
或暗淡。再準(zhǔn)備好一頂假發(fā)
灰白、漆黑、棕黃……都可以
把腰身束緊,成為羸弱的瘦子
也可以給寬松的衣衫中,塞入
一些棉花和報(bào)紙,變得臃腫而笨拙
努力像一條老狗,佝僂下來
或者一瘸一拐,蚯蚓般蠕動
然后,裝聾作啞,裝瘋賣傻……
似乎,世上所有的易容術(shù),都只會
讓一個(gè)人變老,變殘缺
變得呆滯、猙獰,百無一用。那么
有沒有一種易容術(shù),可以讓我們
變得矯健,從容,仿佛重生般
獲得生而為人的尊嚴(yán)……
有沒有一種易容術(shù),能夠
將那個(gè)伶仃的乞丐,幻化成
貴胄,將滿身腥味的屠夫
涂抹為慈眉善目的高僧。有沒有
一個(gè)易容高手,從廢墟中站了出來
笑中帶淚,說,我明明化成了灰
卻依然被你,以一滴眼淚,相認(rèn)
[湖水記]
禽鳴近耳,春枝垂肩
而無垠的湖水,恰是無邊的道場
旋渦為空,漣漪乃色
潛泳的人,遲遲沒有返回堤岸
像被派遣到幽靜的大水之中
去尋取無量教義。他的羽絨服
和褲子,疊放在一塊潔凈的石頭上
不動聲色,等候著主人
而陽光,燦爛跳躍在衣服的每一道
紋理之上,耐心等候著主人
從凜冽的水中,帶回一具
被春水滌蕩過的
嶄新肉身
[僻 壤]
依然有人自井取水,于爐火上
溫酒。不求甚解的讀書人
在白熾燈下,蹈手舞足
捧著粗瓷大碗的人,像捧起
一道圣旨。而黃昏中
砍柴歸來的人,仿佛背著
一座光芒四射的金山。原野里
四散著熱氣騰騰的騾馬,而庭院中
悠閑的雞犬,昂首挺胸
這是一方僻壤,假如你路過此地
討一碗水,就會得到一碗酒
你向誰,輕輕道一聲謝
他就會紅著臉
向你,深深鞠一個(gè)躬
[鳥鳴記]
有一次,窗外一嗓子接一嗓子
說不清也數(shù)不清的鳥鳴,紛至沓來
好像群鳥對一個(gè)凡人,獻(xiàn)上了無窮的祝福
還有一次,只聽得幾聲零落的鳥鳴
如同一只無助的鳥,對一個(gè)無能的人
發(fā)出了求救的哀音。這些年
不知是鳥鳴越來越稀罕,還是
我的聽覺越來越遲鈍,既沒有
收到過一只鳥的祝福,也沒有
一只鳥求助于我。仿佛,我落單在
這世上,早已百無一用。我深知
遲早會等來,形而上的一天
——那禿鷲,滾動著喉嚨
一聲不吭,俯身在我的床前
如探親,如滅親
[愧]
無休止的雨水,在窗外
急促落著,如獅吼
而手中香煙,無聲燃燒著
正由草木,化為灰燼。茫茫大霧
穿窗而來,淡淡煙氣
卻奪空而逃。我深知
來勢洶洶者,我無法阻擋
去者如斯,我亦無力挽留
在人間雖已多年,我依然
不如,面前這一扇窗戶通透
看上去,它單薄而脆弱
卻為我們收納,與阻擋了
這世上,如煙似塵的一切
[謝 絕]
那些名貴之物,與我保持著距離
甚至與我,永遠(yuǎn)隔著一道警戒線
一層玻璃,一個(gè)禮貌的手勢
那些名貴之物,謝絕了拍照與合影
甚至參觀。歷經(jīng)無數(shù)次的
謝絕過后,我再也無心攀附
和艷羨那些輝煌的成就,精美的手藝
我終于退守一隅
與一個(gè)個(gè)凡俗之物、糞土之輩
灰頭土臉的,廝混在一起
我終于活出了自知之明
在越來越平庸的日子里
供養(yǎng)出,一道道無法謝絕的皺紋
·創(chuàng)作談·
空想家或造夢師
據(jù)我所知,幾乎每一個(gè)詩人,都是歷經(jīng)無數(shù)次抓耳撓腮、捉襟見肘的思考,才寫下一些稱之為“詩”的雜念與臆想。為此,我曾一次次感慨,詩歌是猶疑者的事業(yè),而詩人,不妨稱之為世俗中的空想家,或白天里的造夢師。
我幻想過寺廟里,猛獸閉上血盆大口,練習(xí)抄經(jīng)念佛;深湖中,一具白骨追隨另一具白骨,在月夜遨游;我幻想過柴火堆里,一個(gè)灰撲撲的土地爺從噩夢中驚醒、啜泣。還有一次,在我想象里,街頭上涌動著無聲的螞蟻,商場里來往著貧窮的烏鴉,醫(yī)院里穿行著疼痛的白鼠……
你看,我這個(gè)不稱職的空想家,總喜歡借著無邊的虛構(gòu),把自己隱藏在一堆喋喋不休的想法之中,不能自拔。而在天馬行空的神思之外,我們的詩需要落地,需要及物,需要一個(gè)煙火人間的現(xiàn)場,來容納和演繹。
所以,一首好詩,可以沖破萬物間的隔閡,充當(dāng)來往于靜物、動物、人群之間的密探與信使。而一個(gè)詩人,并非單純意義上的風(fēng)光描摹者,世相說書人,還應(yīng)該是一個(gè)眼含熱淚的話事人,在屠刀與含冤者、炮火與玫瑰、銀行家與流浪漢之間,永不厭倦地周旋和商榷著,讓他們 (它們) 和解、體諒、互生情愫……當(dāng)我們愿意把單薄的肉身,放置在周遭這泱泱萬物當(dāng)中,來觀察、揣摩、思索,去做好一個(gè)話事人,那么,碎掉的杯子,被咀嚼過的果核,都將攜帶著它們的悲歡離合,它們的心跳、呼吸、血肉,出現(xiàn)在你我的身邊,榮辱同在……
所謂他者境況,亦即自身遭際。如此而來,詩歌的方寸之地,即為大千世界,而那分行的須彌瞬息,也是一個(gè)詩人的千古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