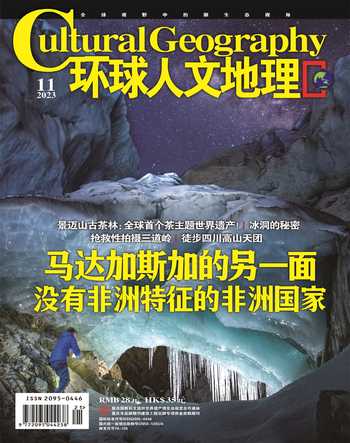戶外旅行的第一步
周影
下班后,我總會在編輯部待一會兒,翻看十年前,甚至更早的《環球人文地理》。
印象很深的一篇文章刊登于2016年12期(當時我尚在大學校園),標題是《等待郭川 那個在航海中永生的帆船第一人》。
老讀者與資深戶外玩家也許都知道郭川,他的新聞轟動一時。
郭川是位冒險家,也是位先行者。作為中國職業帆船第一人,他在國際上獲獎無數,曾勇闖“海上墳場”南美合恩角,也曾完成人類史上首次“無動力、不間斷、無補給”的北冰洋東北航線。
但在2016年10月25日,郭川在進行跨太平洋航行中失聯,衛星電話與互聯網通訊均無回應。最后地方派出了直升機,也只在海上找到了他的帆船,沒有找到他的身影……全網焦急地等待著他的消息,但同時,也有人對他不顧安危的冒險精神表示質疑。
不知道當時記者是懷著怎樣的心情采訪郭川團隊,寫下了這篇特稿。但我注意到一個細節,當期卷首語的署名并非任何一個編輯的名字,而是以筆名落款——“當歸”。
人文關懷與敬畏之心,我總在思考,在當今這個復雜的時代,該怎樣去表達與傳遞。是直截了當給出觀點,是藏于互文,還是見于每處細節——就如總編提醒的,不該寫山“被征服”。
最近,戶外運動再度流行。
已經不是那個互稱“驢友”的年代。現在入門戶外,興趣本身與體能基礎是其次,權威不斷被消解。社交媒體上,更多的是教你出發前事無巨細買齊裝備,登山鞋品牌存在怎樣的鄙視鏈,而穿什么顏色的沖鋒衣才能更“出片”。
“內卷”的戶外運動,某種程度上成了社交貨幣,中產的入場券,抑或證明自己不至于落伍的宣言。
應當如此嗎?
當我按照網上所說,帶齊所有裝備(包括頭燈、坐墊、醫療包、雨披等),認真搭配外套與鞋的互補色,拿上登山杖,加入當地一個戶外團隊時才發現,放下手機的世界,仿佛煞有介事的就我一人。不少人是隨性的,簡單的背包,非專業運動鞋,穿舊了的外套,甚至在前一天才臨時起意要出發——為什么就不可以參與進來呢?
說來也矛盾,被都市壓力、消費主義、身材焦慮等等挾持的年輕人,找到了“戶外”這個出口,沒想到精神內耗沒解決,反而又開始了新的攀比。
歸其原因,我們總是指望大自然,或另一個他者,例如書本、旅行目的地,充當救贖者的角色,卻忽略向內探索也要相輔相成。
多問問自己,為什么,為了什么。
當我們某天在閱讀與行走中獲得了接納、反思、共情的能力,也許就能很好地自洽:戶外運動也好,旅行也好,意義沒那么深奧,只兩個字——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