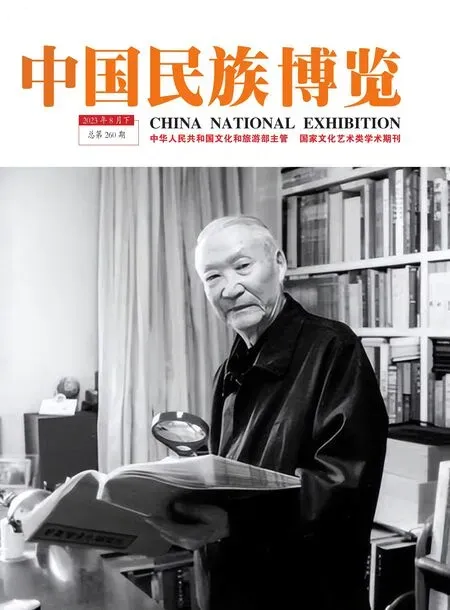跨越之后
——基于非遺舞蹈活態性質的數字化態勢思考
陳若楠
(華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一、基于“活態”性質的非遺舞蹈數字化
(一)非遺舞蹈與數字化
國家級名錄將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分為十大門類,題中“非遺舞蹈”指其中傳統舞蹈一類,專屬的項目編號是羅馬數字“Ⅲ”,包含儺舞、協榮仲孜、苗族古瓢舞、古藺花燈等[1]。隨著對民間舞蹈除民俗價值外的公共教育功用與文化生產經濟屬性的認識不斷深化,這種以人的身體為載體的藝術形式在今日跨越了現場表演,積極擁抱了數字化:數字化的備份與數據庫建立將非遺舞蹈轉化為一種可即時提取的電子資源,數字化傳播跨越了時空屏障給非遺舞蹈帶來走進大眾視線的良機,數字化活化利用與融合發展又促進了民間舞蹈藝術的生產性保護。數字化激發民間舞蹈數不盡的發展潛能,目前誠然需集百家之長,以大量學理性探討促進非遺舞蹈數字化事業進步。
(二)把握“活態”性質是非遺舞蹈保護與傳承的關鍵
非物質文化遺產相對物質文化遺產(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的數字化的復雜出于非遺“活態”性質所帶來的演變性與不確定性。空間概念上,非遺舞蹈更多作為意識形態而存在”[2],包括道具、服飾往往也是萌生于舞蹈知識的可復刻物件。時間維度上,民間舞蹈不像建筑、雕塑等可被判定屬為于“過去”的人類物質文化集合[3],它與農耕時代羈絆深遠,然更緊要的是它以流動變化的形態存在于現在、未來——它是活態的。因此,若將非遺的保護傳承工作當成對一客觀物件的保存與傳遞,則會因時空性質的修改而剝奪了其生命力。當然在備份保護上,可將民間舞蹈以進行固態存檔,但非遺舞蹈文化的踵事增華必須尊重并且圍繞“活態”這一性質展開。
二、非遺舞蹈數字化技術之外的
(一)技術硬傷
國內對非遺數字化尚未發展出貫穿全生命周期的技術體系[4],每一環節都有其要攻克的技術難關。以起始環節——信息采集為例。舞蹈的表現形式特殊,信息采集部分應拆解為四部分討論:一是對當地民俗文化、舞種描述、樂譜等的記錄,這部分以電子文本為載體或對紙質文獻使用圖像式掃描即可輕松滿足;二是民俗音樂伴奏的數字化,這部分有現場錄音以及音頻管理、剪輯等技術的牢靠支撐;三是道具、服飾等實物的數字化采集,可參考文物保護工程的經驗;四是對舞蹈肢體語言的數字化采集,在今非遺資源“活化性利用”的倡導下,單一或混合的文字、圖像與影像采集難以滿足保護轉型要求,3D 形式的舞蹈呈現受到學界近年來的關注。服務舞蹈的3D 技術可細分到動作捕捉、3D掃描、3D 建模等。以動作捕捉(Mocap)為例,它可以服務立體電子館藏、虛擬平臺、VR 教育設備、舞臺立體投影等項目的建設。常用的光學式動捕技術具有數據處理速率高、動作還原快等優點[5],但在具體作用時要盡量減少動作遮擋,舞蹈動作幅度大時標記點也容易丟失或不連貫。此外采集過程對傳承人的體力有一定要求,操作人員與負責壓縮轉換、附屬物件加工等的后期人員也相應承擔了大量工作。目前而言,傳統舞蹈三維模型資料的數據庫的規模成熟、舞蹈數據云庫的轉型升級任重道遠。除了信息采集,修復、數據整理與歸檔、平臺建設等非遺舞蹈數字化以及升級置換環節無一不存在著由于支撐技術不足而產生的遷就,新興技術在非遺舞蹈保護應用上的障礙為非遺保護機構與專業人員發出挑戰函。
另外發展技術所需的專業團隊聘請薪資、機器運輸與維護成本等配套資金問題也需納入考量范圍。高度依靠財政經費促進文物保護的資金格局促成數字化被動的局勢,以“高服務化”與“知識技術密集”為特征的消費結構升級尚在途中。此外,在初升文化創意行業競爭激烈情況下,非遺機構“自造血”的籌資方式——商業運作帶來的實際效益不足支持后顧無憂的技術擴張升級。可以說,技術硬傷并不是一元化的難題,需在物質基礎發展路上徐徐圖之。
(二)非遺舞蹈知識共享平臺建設乏力
知識共享平臺能為文化遺產愛好者、教師和研究人員、群眾對文化遺產材料的數字訪問提供統一的信息獲取渠道,是解決碎片知識分散成為“信息孤島”的有效途徑,建設非遺文化知識檢索平臺、經驗分享與交流討論平臺的任務往往由非遺保護中心以及博物館機構承擔,一些高志愿度的非政府組織(NGO)也參與其中。傳統舞蹈一類的數字平臺搭建并未成系統,主要是信息的公開程度有限,采風收集到的非遺舞蹈資源往往儲存在未對大眾開發的數據庫這一“象牙塔”中,供文化機構及高校學術部門取用,民眾從共享平臺所獲取的資料內容亦或形式上都并不豐富。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搜索引擎中輸入“舞蹈”,找到約2 條結果分別是“舞蹈陶俑”與“舞蹈紋彩陶盆”[6],“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博物館”網站中“傳統舞蹈”類目可獲取的資源局限于文本,僅個別有圖像資料[7]。考慮到客觀物質條件以及民眾興趣分散等許多制約因素,不期許知識共享平臺的搭建一蹴而就,但這是出于公益的必行之路。
(三)“宣傳”與“傳承”間的認知模糊
誠然在數字化非遺態勢下,非遺的申報、保護、研究、宣傳、傳承、開發等環節相輔相成,其中每一個環節都有其相對獨立的使命,但習見模糊化“非遺推廣”與“傳承”,將宣傳推廣混同傳承過程的認知誤區。
在今天,大眾娛樂形式的更迭使得民間舞蹈難以成為民眾充實生活與抒情達意的選擇,為避免非遺舞蹈的保護淪為淪為純學科責任,有關部門與社會力量不斷尋求方法突破純“公益性”“消耗性”的被動保護局限[8],使用信息媒體的宣傳推廣就是其中之一。然現代文明帶來的科技進步在拓展非遺舞蹈的傳播廣度時也沖擊到其所傳遞的知識深度,并且不少報道將橫向拓寬公眾認知的宣傳與縱向傳授知識的傳承搞混,將非遺舞蹈文化的社會推廣等同于傳承。實際上,傳承有其門檻,不是“固態知識普及”,提升對非遺舞蹈的社會關注度并不能直接實現非遺舞蹈活態傳承。可從知識內容與傳導環節上認識兩者的迥別。內容上,“傳承”要求不局限于“知道”,必須是全面、有深度的學習,尤其不能缺失對“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的學習,傳承人不僅要掌握技藝、套路、道具使用等,還需具備對具體民俗文化想法(如審美趨向)的共情,即非遺舞蹈的傳承必須包括真實的肢體參與與心理共情。這一層面上以碎片信息吸引群眾的“宣傳”完全無法相提并論。而從環節上看,人在媒體的視覺敘事中被動接受信息,是“觀看——接受”,而舞蹈套路學習的完整模式為“觀察——模仿——重復——記憶”,若缺乏了“模仿”“重復”與“記憶”,動作及意識就無法在“師”與“生”之間傳遞,更無談傳承。
誕生于農耕文明的非遺舞蹈以代際傳承的方式走到了今日,守護舞種存在、發展的傳承事業注定要嚴肅許多。不可因媒體報道中欣欣向榮的景象而自滿,勤勤懇懇搞好傳承人保護工作始終是保證非遺舞蹈可延續性的核心訴求。
三、以社群力量帶動活態保護與傳承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 年發布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提到“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9]現代文明與優秀傳統文化的并生成為一種共識,除避免割裂兩者之間的內蘊聯系外,要斟酌全球化之下的現代文明對民間本土意識多樣性的滲透度問題,以怎樣一個合適的速度、把控什么樣的方向促進非遺舞蹈的活態傳承與創新性轉化的問題亟待非遺傳承人與民俗學家、舞蹈家們找到平衡點。面對技術硬傷以及數字化態勢中的文明沖擊問題,可將目光由技術轉向“人”,基于非遺舞蹈的“活態”加強非遺舞蹈發展與城鄉發展規劃的結合,尤其要發揮農村社群對非遺傳承的作用緩解有關部門承擔的壓力,鼓勵非遺“原產地”社區的集中力量成為非遺舞蹈橫向推廣與縱向發展的主力軍。
社群(Community)除指地理意義上的特定社區,也可以是一個共享利益或價值觀的群體[10],一方水土一方人,長期居住者對所在地區孕育的精神文化產生的認同感與歸屬感他者無法比肩,而又因民間舞蹈這一藝術形式在空間利用與肢體參與上有其特殊性,所以應該提倡線下社區活動。以社區為單位的非遺文化浸潤在歐洲有優秀的實踐:集學習、工作或娛樂為一體的開放式文化遺產資料平臺Europeana 收集并公開展示了來自4000 多個不同機構的文化遺產資料[11],而項目WEAVE[12]通過講座、社會討論、數字展覽的方式,在文化遺產機構 (CHI)、少數民族文化社群和Europeana 三者間建立聯系。這一項以社區為中心、緊密結合數字知識共享平臺、吸收專業機構參與的項目值得國內非遺舞蹈文化事業借鑒,有目的性地扶助某一傳統舞蹈在原生地的深耕發展比泛推廣更符合其氣質與性格。此外,基于“社群中心”的非遺發展資源會集,旅游業發達的地區可將生態博物館(Ecological Museum)的建設提上文商旅創新議程,促進包含民間舞蹈元素的地域文化品牌建設。
加強非遺舞蹈發展與城鄉發展規劃的結合的另一目的是開拓農村就業新空間。對農村戶籍的蔑視是我國新時代城市就業歧視中特有的一類[13],妨礙著農村戶口勞動力的職業發展更有損和諧勞動關系構建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通過連結數字化工具,支持農村非遺舞蹈傳承點茁長,使當地農村人口尤其農村戶口大學生發揮身為“族內人(Insider)”對出生地文化熟諳的優勢。開展社討、展覽、演出等活動,廣泛吸納村民參與并提供相應就業崗位,促使農村勞力就近就業。建議將退休職工與中老齡村民納入非遺保護社區的力量隊伍,非但借助非遺文化保障老年人精神生活質量、降低老年群體孤獨率,亦通過提高老年人口勞動參與,為解決老齡人贍養問題提供新思路。
四、結語
數字化工具幫助非物質文化遺產實現從“遺產”到“資源”的跨越,然觸及資源約制、技術屏障等問題,我國依舊在非遺數字化轉型能力發展的起步路上,目前尚不具備大面積應用與推廣新型技術的能力。就現階段而言,以群眾力量重拾非遺舞蹈的人文溫度,讓非遺舞蹈資源“活起來”更有意義,未來的非遺保護與傳承必將是尊重民間文化活態發展規律的全民參與文化民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