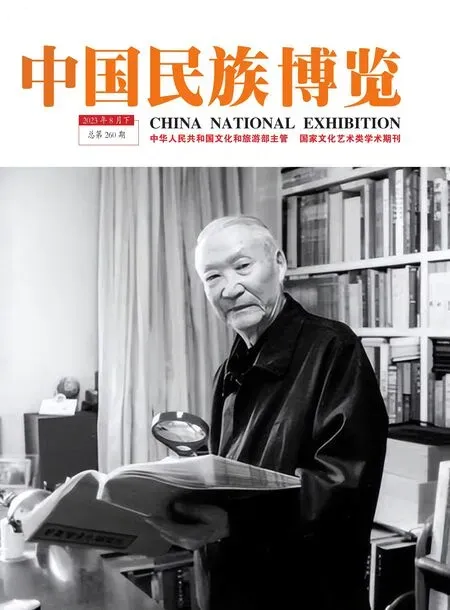論曹丕對文學(xué)發(fā)展的貢獻(xiàn)
高釋元
(洛陽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院,河南 洛陽 471934)
魏晉南北朝在文學(xué)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曹丕作為魏國的開國君主,扮演著重要角色。雖在政治上不如其父曹操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但在文學(xué)上卻有著多方面的建樹。曹丕作為文人集團(tuán)的實際領(lǐng)袖,與“建安七子”的關(guān)系尤為密切,并與“建安七子”共同完成詩文等方面的創(chuàng)作,形成了不同于當(dāng)時的文學(xué)風(fēng)格,對建安文學(xué)的繁榮發(fā)展起到關(guān)鍵性的作用。曹丕的詩歌除了內(nèi)容之外,在題材上的成果也不容忽視。在文學(xué)批評方面對后世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
一、曹丕對文人集團(tuán)的貢獻(xiàn)
(一)文人集團(tuán)的實際領(lǐng)袖
東漢末年,戰(zhàn)亂不斷,民不聊生。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使其在政治上有所建樹,統(tǒng)一之后北方的社會環(huán)境趨于安定。曹氏父子在當(dāng)時具有非凡的文學(xué)修養(yǎng),吸引大量文人聚集于北方,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的鄴下文人集團(tuán)。曹操作為當(dāng)時的政治領(lǐng)袖,無疑是鄴下文人集團(tuán)的開創(chuàng)者與締造者,而曹丕對鄴下文人集團(tuán)的發(fā)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曹操憑借自身的政治地位,網(wǎng)羅天下英才。以“七子”為代表,在曹植的《與楊德祖書》中有所體現(xiàn):“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yáng)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璉發(fā)跡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dāng)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包荊山之玉,吾王于是設(shè)天網(wǎng)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1]而“七子”中并不是每一位都奉行曹操的政治主張。陳琳曾為袁紹撰寫《為袁紹檄豫州》以討伐曹操,曹操在擊敗袁紹之后,因愛惜陳琳才華將其收為己用;阮瑀本持不合作之態(tài)度,卻也“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2]孔融甚至公然反對曹操,也被殺害。“七子”或因政權(quán)或因戰(zhàn)亂聚集于鄴下。而曹丕與其父戎馬一生所展現(xiàn)出的慷慨悲壯不同,便娟婉約更像是一個文人應(yīng)有的文學(xué)風(fēng)格。“曹殺文舉”中表現(xiàn)出曹操強(qiáng)烈的政治手段,給予“七子”強(qiáng)烈的施壓效果,而曹丕便娟婉約的詩風(fēng)具有文人之間的貼切,“以文會友”與曹操“嚴(yán)刑峻法”形成對比。正是由于曹丕對待文人態(tài)度之不同和與文人集團(tuán)的親近,使得彼此之間產(chǎn)生的情感非同尋常。“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3]不僅體現(xiàn)出領(lǐng)袖的態(tài)度,更是知音難尋、互敬互愛的情感體現(xiàn)。曹丕與文人的詩酒唱和,流露出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積極參與,進(jìn)一步推動文人集團(tuán)的發(fā)展。
(二)促進(jìn)建安文學(xué)的繁榮發(fā)展
身處建安文學(xué)中心的曹丕,在五官中郎將到太子期間,繼承了思想理論體系的新道路:擺脫經(jīng)學(xué)的束縛與古拙的寫法,不以儒學(xué)繁瑣的觀點延續(xù),從而轉(zhuǎn)向文人詩的華美,選用清詞麗句來表現(xiàn)語言的工麗,反映自己所看到的真實生活、抒發(fā)真實情感,使文學(xué)道路更加開闊。由于創(chuàng)作形式的改變,建安時期文人對于文學(xué)作品的地位和作用有著獨特的見解,對文章的特點、風(fēng)格都有著更深入的研究。曹丕開文學(xué)批評之先河,建安文學(xué)的興盛也與文學(xué)批評密不可分,文學(xué)的批評形成了思想的碰撞,對之后的“蓬萊文章建安骨”以及詩歌的發(fā)展與推進(jìn)起到了關(guān)鍵性作用。
二、曹丕在詩歌史上的貢獻(xiàn)
(一)開便娟婉約之風(fēng)
魏晉南北朝被稱為“文學(xué)自覺”的時期,而建安時期可以說是“文學(xué)自覺”的開端。以“三曹”為代表確立“建安風(fēng)骨”這一詩歌文學(xué)典范,為中國詩歌打開了新局面。曹操作為第一人,身處漢末動亂的時代加之特有的政治天賦,展現(xiàn)出同情民間疾苦的情懷和抒發(fā)自己能夠一統(tǒng)天下、建功立業(yè)的豪情與蒼涼之感。而政治的勝利者畢竟是少數(shù),多數(shù)人表現(xiàn)出的是對人生無常的感嘆和想要一展鴻圖的理想。因此這一時期多慷慨、悲涼之氣。曹丕的詩作主要是在擔(dān)任五官中郎將時產(chǎn)生,因隨曹操南征北戰(zhàn)看遍人間疾苦,便多了細(xì)膩、婉轉(zhuǎn)之情,與其父形成不同風(fēng)格。加之建安時期儒學(xué)傳統(tǒng)地位發(fā)生動搖,重情感、重個性發(fā)展以及對自我的肯定使得曹丕形成不同于時代的風(fēng)格:纖麗清新、深婉細(xì)膩,開便娟婉約之先河。內(nèi)容之豐富、形式的多樣使“建安風(fēng)骨”得以用另一種藝術(shù)特色呈現(xiàn),對豐富“建安文學(xué)”以及后來美學(xué)這一藝術(shù)范疇的發(fā)展提供條件。
(二)詩歌形式與內(nèi)容的多樣化
建安時期詩歌的特點與當(dāng)時時代的特點略有相似:意境開闊,自由灑脫。主要是按照漢樂府詩歌進(jìn)行發(fā)展,受漢樂府?dāng)⑹滦缘挠绊懀訌?qiáng)了抒情性。[4]七言詩起源于民間歌謠,從歌謠慢慢轉(zhuǎn)變成文人筆下的七言新詩體,最早在《詩經(jīng)》中有所體現(xiàn),但《詩經(jīng)》基本上是四言,七言甚少。《楚辭》多以七言為主,但大多數(shù)的句子中都有“兮”,相比七言詩還是有不同之處。七言詩產(chǎn)生于西漢時期,東方朔、劉向等都有作品傳承,對七言的發(fā)展也起到了推動作用。但七言在當(dāng)時并不算主體,流傳較廣的七言中,第一首是漢武帝時期的群臣聯(lián)句《柏梁臺詩》,第二首是東漢時期張衡的《四愁詩》。《四愁詩》全詩結(jié)構(gòu)整齊、韻律和諧,運(yùn)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對七言詩的發(fā)展有很大影響。但詩中每節(jié)的第一句仍有“兮”字,還未脫離《楚辭》的形式,直到曹丕的《燕歌行》才真正打破這一束縛。
曹丕的《燕歌行》其一最負(fù)盛名,全詩以第一人稱視角透露出女主人公對遠(yuǎn)方丈夫的無限思念。“秋風(fēng)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開篇以深秋為背景,以景襯情,為全詩渲染蕭瑟凄涼的氛圍,給人以空曠寂寞之感。同時以秋景抒發(fā)離別與思念之情,體現(xiàn)曹丕的獨特風(fēng)格。詩的中間部分以對話形式展現(xiàn),將女主人公的心理感情描繪得淋漓盡致,女主人公的急切、思念與悲傷之情躍然紙上。結(jié)尾一語雙關(guān)、升華情感,突出思念之切。作品把寫景抒情、寫人敘事以及女主人公的自言自語與思念之情巧妙地融為一體,構(gòu)成了一種思念至深、凄涼哀怨的風(fēng)格。細(xì)膩婉約、明媚清麗,呈現(xiàn)出一種陰柔之美,獨開建安時期另一詩風(fēng)。王夫之評價此詩“傾情、傾度、傾色、傾聲,古今無兩”[5]。明代鍾惺評曹丕“婉孌細(xì)秀,有公子氣,有文人氣”[6]。清代陳祚明評價曹丕詩篇“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動盻無非可憐之緒”[7],最能體現(xiàn)曹丕的藝術(shù)風(fēng)格。
曹丕在藝術(shù)上的創(chuàng)新,使得《燕歌行》在七言詩的發(fā)展上有著重要意義。《燕歌行》是中國文學(xué)史上現(xiàn)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詩,是“七言詩之祖”,七言詩從這里開始擺脫《楚辭》的形式,使七言獨立存在于文學(xué)史中。明代胡應(yīng)麟評“子桓《燕歌》二首,開千古妙境。”[8]我們可以看到曹丕在詩歌形式上敢于創(chuàng)新,開七言之先河。《燕歌行》中句句用韻,格調(diào)婉轉(zhuǎn),雖用韻單調(diào),但是在中國詩歌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為七言詩的發(fā)展做出了貢獻(xiàn)。經(jīng)過鮑照等人的努力,七言詩在南北朝文人的詩歌中日益繁榮,內(nèi)容方面更為豐富寬廣,藝術(shù)方面更為成熟精湛。曹丕的《燕歌行》二首在七言詩的發(fā)展上起到里程碑的作用。
曹丕不僅在詩歌的形式上進(jìn)行創(chuàng)新,而且在詩歌題材的創(chuàng)作上也極具特色。曹丕生活閱歷的豐富,加之受到不同程度的文化熏陶,使曹丕對所見所聞有多方面的感悟。題材的豐富反映出社會上的普遍現(xiàn)象,得以體會不同人物的思想感情,極具現(xiàn)實主義精神。
曹丕的詩現(xiàn)存四十余首,按題材劃分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宴游詩,如《芙蓉池作詩》,描寫細(xì)膩、文詞富麗,在我國山水詩的發(fā)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第二類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陽作詩》,通過對所見之物的感慨抒發(fā)個人志向。第三類是寫征人思婦的相思離別及思鄉(xiāng)之情,如《燕歌行》,最能體現(xiàn)曹丕詩歌的水平,對后代歌行體詩歌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詩歌題材的多樣化,為建安文學(xué)的發(fā)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曹丕在文藝?yán)碚撋系呢暙I(xiàn)
(一)開文學(xué)批評之先河
《典論·論文》是我國最早的一篇文學(xué)理論文章,是中國文學(xué)批評史上的第一部文學(xué)專論。它涵蓋了文學(xué)價值論、文學(xué)批評論及文體論等豐富的內(nèi)容,開啟了魏晉南北朝文學(xué)批評的先河,并提出個人的文學(xué)主張,開啟了文學(xué)自覺的時代。
《典論·論文》中提出“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論文。……常人貴遠(yuǎn)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于自見,謂己為賢。”[1]曹丕提出了自古以來文人互相輕視、崇尚名聲、不重實際,總是以自己所擅長的輕視別人所不擅長的,應(yīng)當(dāng)審察自己以衡量別人,能夠免于文人相輕這種通病來寫文章。[9]曹丕將這一現(xiàn)象首次拿到文章中,提出了適當(dāng)?shù)闹笇?dǎo),“審己以度人”及“貴遠(yuǎn)賤近”是對待文學(xué)應(yīng)有的態(tài)度,抨擊徒慕虛名的文學(xué)思想,推動詩文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七子”這一概念,確立“七子”的文學(xué)地位,在點評人物中形成獨特思想,對之后《文心雕龍》《詩品》等批評著作的產(chǎn)生提供了基礎(chǔ)。
(二)提出“文氣”論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qiáng)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jié)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1]文章以“氣”為主導(dǎo),氣又分為清氣和濁氣,不是可以出力就能容易取得的。即便是父親和兄長有很高超的個性與氣質(zhì),也不能完全轉(zhuǎn)移給與自己有血緣關(guān)系的人身上。在漢末盛行對人物進(jìn)行品評,“氣”是人物品評較為常見的概念,包涵了人物的個人修養(yǎng)、氣質(zhì)以及才能等多個方面。曹丕的“文氣”受到人物品評的影響,在文章的品評上也逐漸形成這一觀念,強(qiáng)調(diào)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個人氣質(zhì)是密切相關(guān)的,追求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個性。因此,“文氣”說標(biāo)志著“詩言志”向“詩緣情”思想上的轉(zhuǎn)變,標(biāo)志著文學(xué)自覺時代的到來,并把文學(xué)創(chuàng)作推向了美學(xué)的范疇。
《典論·論文》中的“文氣”從“才”和“性”兩方面論述個性和文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氣”是每個作家單獨具備的,是不同的,是由“性”的不同所導(dǎo)致的。例如建安七子中正是因為各自的“氣”有別,個性有別,而且是自然形成不易改變的,他們的創(chuàng)作才有著風(fēng)格的不同。曹丕正是用這個理論來分析“建安七子”的才性與“文氣”之間的關(guān)系。[4]
曹丕將“文氣”分為“清”與“濁”兩類,清為陽剛之氣,濁為陰柔之氣。曹丕在對“七子”的不同品評中也表現(xiàn)出他對建安時期雄渾剛強(qiáng)的文學(xué)風(fēng)格持贊賞和肯定態(tài)度,而這種肯定也與當(dāng)時時代所展現(xiàn)的豪邁自我密不可分,同時也對后世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影響,使得后世漸漸推崇這種剛強(qiáng)的文風(fēng)。“文氣”是文章的關(guān)鍵,曹丕提出的這一觀點賦予了文章以新的地位,成為文學(xué)發(fā)展的重要支撐,對后世文論有著深遠(yuǎn)的影響。
(三)肯定了文學(xué)的歷史地位
曹丕對文學(xué)給予極高的評價。他認(rèn)為“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曹丕提出文章的“不朽”,是比“立德”和“立言”還要重要的事情,在思想上提高文章的地位。儒家提出的“三不朽”中,以“立德”為首要,其次為“立功”,其次為“立言”。可見在當(dāng)時流傳的思想中,“立言”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立言”只是作為一種教化的工具,根本就是為“立德”所服務(wù)。而曹丕的《典論·論文》則是給予了“立言”空前的地位,將文學(xué)的價值提高。曹丕對文章進(jìn)行高度的評價,以一種全新的視角來看待文學(xué),對文學(xué)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起到促進(jìn)作用,是有利于文學(xué)發(fā)展的。曹丕所處的時代,是“文學(xué)自覺”的時代,也是文學(xué)史發(fā)展的重要時代,曹氏父子對文學(xué)的重視,促使當(dāng)時聚集了大量的文人作家,形成“文人集團(tuán)”,包括《典論·論文》中提到的“七子”。曹丕在繼承其父的政治成果之后,加強(qiáng)對文學(xué)的重視,促進(jìn)了當(dāng)時更多的文人進(jìn)行創(chuàng)作,領(lǐng)導(dǎo)建安文學(xué)的發(fā)展。
建安時代的詩歌發(fā)展迎來了高潮。身為文學(xué)家的曹丕,不僅激勵著建安文人們進(jìn)行創(chuàng)作,同時作為一個有獨立思想的個體,具有多方面的文學(xué)成就,創(chuàng)作了豐富的詩歌類型,形成對后世較大影響的理論體系,取得了輝煌成就。對于人物的理解與評價,應(yīng)當(dāng)先了解作者生活的時代,了解那個時代具有的社會風(fēng)氣,不能僅憑個人情感對作家下絕對的、片面的評價。曹丕以其獨特的地位及個性,在文學(xué)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曹丕不僅為建安文學(xué)的繁榮作出了貢獻(xiàn),而且在詩歌史留下壯麗篇章,在文學(xué)史上有著不可忽略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