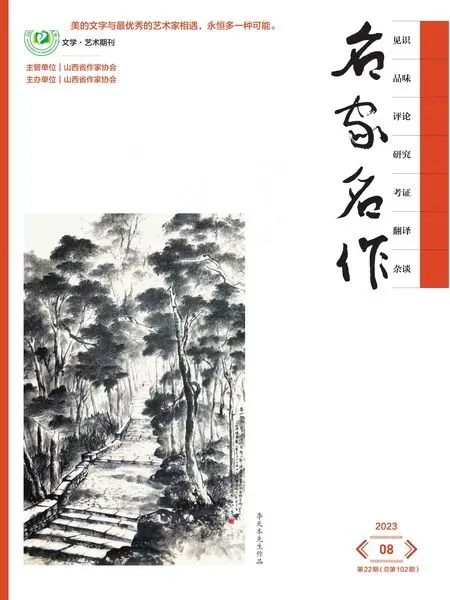淺析超越論現象學的心性論意義
呂 倩
胡塞爾從本質現象學轉向超越論現象學后,超越論還原是他現象學生涯的關鍵。胡塞爾自己認為他整個哲學的第一要務是超越論還原。如何理解超越論還原,通常我們是從理論哲學的層面來理解認識論和本體論的意義。僅從這里出發,胡塞爾的超越論還原和超越論現象學最根本的意義可能就喪失了,這將導致超越論現象學的狹隘和被輕視。因為按照胡塞爾自己對超越論還原或超越論現象學的理解,他的超越論還原是把“還原”帶入經驗,“在我的身體里,一種人格習慣在我的身體里形成”,并“超越了經驗的內在生命,把我們帶回它的終極生命之流”,最終指導我們生命的整體實踐。就此而言,超越論還原不僅具有認識論和本體論的意義,而且具有心性論的意義,它有助于心性實踐和心性修煉。
其實,把哲學理解為心性的訓練和修習,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是一種古已有之的傳統。對于中國古代哲學,儒釋道都在這方面有深入研究。道教和佛教作為宗教,必然以此為宗旨。對于儒家來說,這方面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談到西方傳統,皮埃爾·阿爾多認為“哲學學派特別符合某種生活方式的選擇和生存的選擇。它需要個人生活方式的徹底改變,需要每個人存在的改變,最終需要以某種方式存在和生活的欲望”。因此,“哲學,尤其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與哲學辯論密切相關的生活方式”。胡塞爾將現象學理解為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全面改變。
一般理解的超越論還原涉及“我”和“世界”兩個方面。在“我”方面,還原是一個關于“我”的自然態度的還原,是從自然態度到超越論態度的轉變。就“世界”而言,還原是將所謂現實世界視為現象,視為“我”眼中的世界、“我”意識中的世界。這種對超越論還原的理解當然沒有錯,但也不完全。因為完整執行的超越論還原不僅關系到自我主體和世界,也關系到作為交互主體的“我們”。胡塞爾在他后來的手稿中說:“通過現象學,我們明確了‘我’、‘我們’和世界的超越性的意義。”因此,超越論還原除了是對“我”和“世界”的還原,也是對“我們”的還原,是“我們”超越意義的彰顯。超越論還原的意義,即心性的修煉和生活方式的轉變,不僅涉及對“我”與“世界”的理解,還涉及對“我們”的理解。
自然的態度是對世界采取一種樸素的存在信念。這種態度主導的哲學認為世界是一個預先確定的客觀現實或實體。如果進行超越論還原,我們就從一種自然的態度轉變為一種現象學的態度,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也就進入了現象學的維度。從現象學的維度看世界,世界不再在自身之外,也不再是與人無關的客觀事實。
從現象學的態度和理解來說,“看山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因為當時的山川之“見”,已經不是簡單的以自然態度為主導的“見”,而是一種現象學的“見”。“樸素觀”一直得不到解決,所以我們用這個現象學的“眼”來“看山”。在現象學的視角中,世界依然展現在“我”眼前,但它不是與“我”無關的客觀世界,現在出現在“我”眼前的世界就是作為現象的世界。在胡塞爾的現象學中,世界向“我”的出現是通過“我”的意識出現的。世界是表象,但“我”的主觀意識是它出現的方式。它如何出現在“我”眼前,對“我”意味著什么,其實是由“我”的人生經歷、生活實踐以及生命體悟決定的。
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我”所看到的世界不再是客觀的實在世界,而是“我”主觀意向活動的結果。這正是胡塞爾超越論還原所要揭示的。他在《現象學心理學》中寫道:“自我不僅僅是被動地意識到給予者……他……構建客觀關系、事態、自然狀態和關系狀態;同樣有價值狀態,實踐狀態等。”即客體關系、事態、性質、關系狀態、價值狀態、實踐狀態都是由自我構造成的,或者說是與一個人的行動意圖有關的項目。從這個意義上說,自我生活在自己的意義場中是活躍的。接著他說:“客觀性也有其原始的給予方式……但是他們的獨創性……是來自自我活動的行動的獨創性。”這樣,“風景”的“原本給我的方法”,即原本呈現給我的方法,就來自“自我活動的行動”,即“對你自己來說,它來自你自己的行動,作為一個已經出生的人,你會在那里”。超越論還原后,你會發現對象周圍的世界是你自己的精神構成。
在超越論還原中,伴隨著世界意義的轉變,“我”和“世界”之間的聯系也發生了轉變。在自然態度中,在把世界理解為客觀真實時,“我”也把自己視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和片段,并受制于世界的變化。但是,通過超越論還原,世界被還原為“我”的意向性活動的建構性成就和意義的統一時,“我”就不再是世界的一部分和片段,而是成為世界的 “建造者”,成為意向性活動的發散者和意義的賦予者。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和世界之間存在著一種原始的“關聯”。這種關聯在自然態度中被掩蓋了,而一旦“我”打斷它并將自己從其中解放出來,世界和“我”的意識之間的這種“關聯”就變得明顯了。“在這種解放中,并通過這種解放發現了世界本身和世界的意識之間的普遍關聯,而世界的意識是絕對封閉的,是絕對獨立于自身的。這一點,從最廣泛的意義上理解,最終產生了一種絕對的相關性,一方面是所有性質的所有意義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絕對的主觀性,因為它構成了意義和存在在這種最廣泛的方式中的絕對相關性。”被這種關聯聯系起來的雙方永遠不可能被分開。并不是說主體和世界被捆綁在一起,而是主體的意識和作為其意向性成就的世界總是相互關聯、相互構成的,從一開始就是一體。“我”所處的世界從一開始就被建構為“我”有意的活動(后來被海德格爾激化為 “存在”)的結果。當然,這種 “構成 ”或 “建構 ”不能被理解為無中生有,仿佛有一個非世界性的主體,而這個主體創造了世界。胡塞爾在這里說的是,我們從一開始就有這種“相關”的結構,一方面是意識,另一方面是作為意向性相關物的世界。兩者從一開始就相互關聯,交織在一起,形成了意識生活整體。
在胡塞爾晚期的現象學中,超越論還原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在整個西方現象學中,它并沒有被強調,甚至幾乎被忽視。原因之一可能是超越論還原作為一種自愿的心性修煉的實踐,在西方哲學傳統中難以立足,因此在西方現象學中實際上被低估了,例如,當今著名的現象學家之一莫蘭認為,“我不認為《觀念I》的偉大之處在于它引入了超越論還原、擱置、意向性活動、意向性關聯等。而是認為它的關鍵突破是胡塞爾發現了自然態度及其關聯物——自然世界”。然而,這種實踐在東方佛教的心性傳統中是一個重要的基本課題,從這個角度來看,超越論還原的實踐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心性的實踐。
佛教瑜伽行派唯識宗的“三性說”和胡塞爾的還原思想不僅在基本思想上可以比較,甚至在其論證的基本結構上也可以比較。兩者之間有相似之處。在下文中,我們將對它們稍作比較,“三性說”的第一次出現是在印度瑜伽行派的早期經典《解深密經》中,它是瑜伽行派以空性為基本見解、通過改造中觀派二諦思想而形成的關于根本真實( 諸法實相) 的學說。用胡塞爾的術語來說,這兩個真理是在自然態度中和超越論態度中發現的真理。瑜伽行派繼承了中觀派緣起性空的二諦思想,但他特別解決了如何從世俗的業力現象來討論開悟的可能性的問題,并由此發展出“三性說”。三性指的是一切現象( 諸法) 的三種存在形態,它們分別是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
遍計所執性指具有分別功能的意識妄執各種事物為實在,它相當于胡塞爾自然態度中自我對事物的存在設定。依他起性是“三性說”的關鍵,首先,依他起性和遍計所執性有關聯,遍計所執性是在依他起性的基礎上把種種“依他而起”的現象執著為實在;其次,依他起性和圓成實性也有關聯,圓成實性即在依他起性的基礎上滅除遍計所執性。圓成實性不是遠離依他起性而從遍計所執性中通過跳躍達到的,而是在依他起性的基礎上徹底遠離遍計所執性的執著達到的。這樣講來,依他起性和圓成實性的關系是“非異非不異”。這里依他起性相當于胡塞爾通過心理學還原而得到的動機引發,而圓成實性相當于胡塞爾超越論態度中的超越論領域。他在《現象學的心理學》中就明確說過,經過現象學還原之后,世間我的心理內容仍然被“作為超越論的內容被保留住”,“那全部的本己本質性的心靈內容,也就是那個心理學的現象學還原所造就的而且是心理學的現象學所描述的心靈內容,將經由最高階而徹底化的懸置而作為超越論的內容被保留住”。
唯識宗的理論邏輯是一個轉識成智的心性修習過程,同樣,胡塞爾現象學以動機引發為中心,轉自然態度為超越論態度,這個過程作為超越論還原也是一個心性修習的過程。而且這里要特別指出,這個作為心性修習的超越論還原是在心理學道路( 而非生活世界道路) 中具體展開的。在心理學道路中,胡塞爾特別強調心理學還原對于從自然態度向超越論態度過渡的必要性,正如唯識“三性說”強調依他起性對于從遍計所執性向圓成實性過渡的必要性一樣。動機引發作為精神的因果性法則( 正如依他起性作為分別自性緣起的根本法則一樣) 已經可以被心理學還原所把握,但是這種動機引發的關系仍然隱含著存在設定( 正如依他起性中隱含著遍計所執性一樣) ,只需要在心理學還原下的動機引發的基礎上徹底去除存在設定( 正如在依他起性上遠離遍計所執性一樣) 。胡塞爾說:“假如整個自然都變成只是所思的現象,只要其真實的實在性被棄置不顧,那整個被還原到純粹心理存在和生命的自我便不再是那個自然客觀的經驗態度與說法中實在的世間人——自我。”
胡塞爾在《現象學的心理學》中說道:“那全部的本己本質性的心靈內容,就是那個心理學的現象學還原所造就的而且是心理學的現象學所描述的心靈內容,將經由最高階而徹底化的懸置而作為超越論的內容被保留住。”現象學心理學更接近自然態度,更容易接受。此外,激進超越論的境界一方面很難達到,因為它實際上只是一種理想,另一方面也很難獨立存在,因為它與心理學的境界是平行的。因此,現象學心理學不是一個單純的向導,不是爬上超越主義的頂峰后要拆除的梯子;相反,現象學心理學一方面與自然生活相聯系,另一方面與從非哲學的自然人開始的實際心性實踐相聯系。所謂的拓展“自我”意識其實就是指跳出、超越、拋棄主觀意識,主觀意識其實是和客觀世界對立的,二元論為基礎的,就因為修身其實可以拓展肉身賦能的意識所以此為破壁,破二元。自由意識拓展到最后可以和宇宙意識融為一體,無邊無盡的心性是也。這不是二元,但不排斥二元,包含了相對論,摒棄了一切主義,但又不是任何主義,它無所謂被定義,反正不懂得怎么形容描述也不會懂,這就是所謂的“自由”意識。“所有的物理學先驅都是神秘家,理由是他們想超越物理的局限,進入神秘的覺知,也就是要轉化這個世界的陰影現象,揭露更高、更永恒的實相。他們是神秘家并非因為他們研究物理,而是他們可以不顧物理。換句話說,他們希望神秘體驗論是形而上的,也就是‘超越物理’的。”按照史蒂芬·平克的說法,“也許我們追求的目標是,暫時跳出你自己的心智,將你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看作是自然界的宏偉設計,而不是看作事物存在的唯一方式”。歸命本覺心法身,常住妙法心蓮臺。如果說心性是法身,那么超越心智就是般若波羅蜜多,說來說去還是要將“我”去除才行。東方哲學的確為歸納性實踐的討論提供了更豐富的思想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