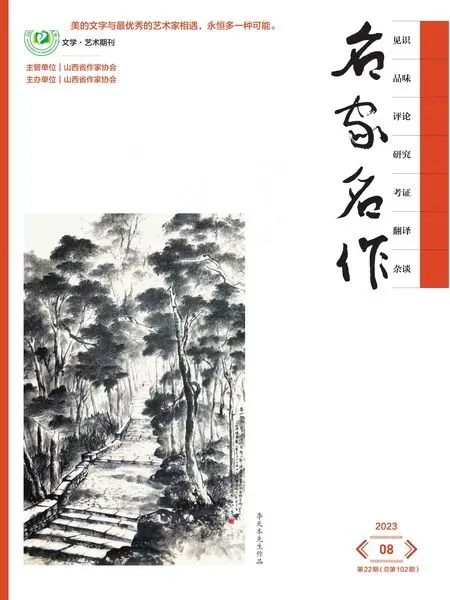海明威《雨中的貓》的女性意識解讀
沈津雯
一、引言
20世紀60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中提出了“女性意識覺醒”的口號,該覺醒被界定為女性通過教育,逐漸認識到自身權利被剝奪、遭受歧視的現實,并把日常生活中受壓迫的經驗轉化為批判的意識和反抗的行動。同一時期,美國婦女運動的領袖人物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奧秘》一書中解構了“快樂家庭主婦”的神話,喚醒了美國女性的主體意識。女性意識的內容也隨著歷史發展和社會變革而不斷變化與充實。隨著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興起,女性文學作品逐漸成為作者探索社會問題、傳遞思想意識的媒介,促進了社會對女性權益等相關話題的關注。21世紀初,丁藝茹將女性意識定義為在一定歷史時期,女性作為主體對自己在客觀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價值的自覺意識,其重要標志是爭取女性獨立的地位。同時,她指出女性意識是女性對自身存在的特殊性的探秘,它觀察到的不單是男性眼中的女性,還是女性眼中的自己,它既是女性對男性經驗積極有效的否定,也是女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尤其是對自身價值的體驗和醒悟[1]。《雨中的貓》是海明威早期少數以女性為主體、從女性視角來寫的作品。小說圍繞著一位美國妻子想救貓、尋找貓、想養貓和得到貓四個環節展開敘述,其中的女性意識具體體現在女性對傳統母親角色的渴望、對獲得尊重和獨立的渴望以及對情感的投射性認同三個方面。
自作品發表以來,國內外各大學者分別從語言特點、寫作技巧、人物塑造和女性主義等方面對其進行了分析和討論。國內學者賈艷萍和胡玲玲結合海明威的生活經歷和時代背景解讀《雨中的貓》的多重象征意義,指出小說通過象征手法反映兩性沖突;楊紅梅從人稱指示語的角度,深入分析小說主題意義的表現關系;而國外學者 John V. Hagopian則從小說的對稱性入手,探討文中語言和動作等細節描寫中呈現的精巧結構和意義表達。論及小說中所體現的女性意識,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肖佳樂對小說中的意象做系統分析并進行角色符號解讀,常榮則著重對小說中的兩性關系進行解讀,表達出女性試圖與男性處于平等地位的需求;而程穎將結合小說的故事情節發展,將其中的女性意識覺醒解構成四個階段;楚承華則從海明威“冰山原則”創作理論入手,表現了小說中女性在男性霸權下自我意識的覺醒和抗爭,《雨中的貓》也因此被譽為海明威著力表現女性意識的一部佳作。
而從前述學者的研究來看,討論較多的是小說的寫作手法和創作理論、兩性之間的矛盾沖突與女性意識的覺醒,忽視了女性在男權社會中面臨的生存困境,對于女性意識覺醒尚存的不足與失敗的討論較為欠缺。因此,本文較全面地對小說中的女性意識進行解讀,探討男權社會中男性對女性地位、作用和價值等方面的壓制,以及由此產生的女性對自由與獨立的渴望、掙脫社會成規和改善自我的進步意識,以期為小說的解讀和賞析提供新的視角。
二、《雨中的貓》中體現出的女性意識
(一)逐漸蘇醒的女性意識
海明威在《雨中的貓》中通過各類白描手法以及修辭手法,著重表現出女性在男權社會中開始勇于表達自己的訴求與欲望,并努力將其付諸行動。通過這種方式,海明威在小說中將女性意識與限制、壓抑和抗爭聯系在一起,揭示了女性對自身地位、作用和價值的追求,從而傳遞出一個重要的信號——女性意識的覺醒是一種自我解放的過程,是與社會期望和限制斗爭的開始。
首先,小貓是小說中女主人公情感空虛的替代品,在拯救雨中的貓失敗后圍繞貓編織的幻想更加表明了她對傳統女性和母親角色的渴望[2]。在希臘神話中,貓被認為是掌管生育的女神“芭斯特”的代表,象征著愛情與生命力。在小說中,女主人公不僅希望“小貓來坐在我膝頭上,我一撫摩它,它就嗚嗚叫”,還想要“把頭發往后梳得又緊又光滑,在后腦勺扎個大結,可以用手摸摸”[3]。這是女性天然具備的母性使然,雨中貓的出現使女性角色的主體意識逐漸復蘇,并在這個過程中變得更加勇敢與堅強,希望改善夫妻關系,展開對新生活的期待[4]。追根溯源,海明威在《雨中的貓》中對這一象征意義的關注來源于他的妻子哈德莉。海明威于1921年與哈德莉結婚后,因不愿承擔家庭的責任而迫使懷孕的哈德莉流產,直至哈德莉30余歲再次懷孕執意生子時,海明威才迎來他的第一個孩子。因此他將這一情形通過貓的意象投射于小說中。
其次,小說中,女性主義思想實際上一直蘊含于女主人公的潛意識中。例如,她喜歡旅館老板在路過時對她鞠躬施禮的莊重風度以及為她效勞的諸多服務禮節,她滿足于在旅館老板的行為中感受到的重視與尊重,女主人公被丈夫長期抑制的女性意識得以在此短暫地安放與回歸。而貓的意象只是導火索——貓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激發了女主人公自我想象與自我改變的生命潛能,貓的消失使她不再壓抑自己的情感需求與物質欲望,引發了她內心對美麗、浪漫、自由、尊嚴的渴求。在小說中,尋貓未果的女主人公在回房后與丈夫展開對話,前后一共提出了12次“想要”。從一開始“要是我把頭發留起來,你可認為是個好主意嗎”這一委婉無力的詢問語氣,逐漸變為以堅定的“我想要”口吻提出自己的需求。在拉康的想象中,他將幻想定義為主體呈現其欲望的場景,或者是主體維系自己欲望的手段。女主人公向丈夫表達訴求的行為生動地表現了她對新生活的向往,呈現出突破社會和文化條件限制的新女性意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大量采用第三人稱視角敘述,客觀真實地敘述女主人公的生存困境,但在她向丈夫訴說自己一系列渴求之時巧妙地轉化為第一人稱視角,用一連串“我要”的強烈祈使句宣泄自己的精神與物質需求。作者借助人稱轉變這一敘述技巧實現移情與離情的表達效果,將她從不健康不和諧的婚姻關系中暫時解脫出來,雖然小說中女主人公的訴求沒有得到滿足,但作者在對立的視角中含蓄地揭示了她為掙脫傳統社會角色束縛而做的努力與自我抗爭,呈現了其女性意識覺醒的信號。
誠然,海明威筆下的女性有著復雜的性格特征,這既反映出這些女性人物受所存在的時代影響,又表現了海明威在其作品中賦予男性更多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而將大部分情感因素和家庭責任賦予女性。因此,海明威在小說中所描繪的女性角色十分關注她們與男性之間建立的情感紐帶,她們的存在始終無法擺脫對男性的依賴。但難能可貴的是,在《雨中的貓》中,海明威所描寫的女主人公在思想層面上有所覺醒,也在行動上付出了努力,并實現了由此產生的情感投射性認同。
海明威筆下的女主人公經常扮演看護者的角色,這種角色在父權制社會中極為常見,而為了表現自己是不受父權制脅迫的女人,這類女性角色通常通過保護比她更弱小的事物來獲得他人的認可以及自我安慰,從精神層面分析,這是一種情感投射性認同[5],如同《雨中的貓》的女主人公渴望保護這只比她更加弱小的貓。在小說中,女主人公在想要去救貓時拒絕了丈夫的幫助,而是堅定地表示“不,我去”;并且在侍女詢問她在尋找何物時堅定地強調了兩遍“我很想要它,我很想要這只貓”。這種企圖扮演傳統的男性所擔任的“拯救者”的英雄角色也是典型的新女性作為,她在救貓時產生的想要去保護而非被保護的心態實際上便暗示了女性試圖反抗并掙脫傳統社會角色束縛的女性意識覺醒,作者借此凸顯出女性在抗爭性別成規與社會刻板定位過程中產生的英雄主義,并由此實現了情感自救。
由此可以看出,盡管海明威所描繪的女性角色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但他已經在別出心裁的人物塑造中超越了傳統男性作家的視野,能夠拋開男性的個人偏見,來表達她們的體驗與渴望——渴望改變自己被男性話語權壓迫與支配的處境,渴望掙脫傳統社會的角色束縛,渴望擺脫虛偽冷漠的婚姻桎梏,渴望擁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和價值追求。
(二)被壓抑的女性意識
在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之前,男人被普遍認為是比女人更高級的人類。隨著啟蒙運動中人人平等的理想的流行,這種觀點逐漸轉變為帶有刻板理念和期望的性別二元論——它規定男性遵循人性和理性,而女性則象征自然和感性。因此,在男權社會中,男性在男女的二元關系中長期掌握著極端權威。小說中,海明威同樣通過象征手法、對比手法等修辭手法凸顯出男性崇尚理性、壓制感性的典型價值觀,以及因此被長期壓抑的女性意識。
1.男性對女性意識的壓制
不難發現,在整個故事中丈夫從未放下手中的書本,對妻子的情感變化也始終持冷漠的態度。在這里,書成了這對夫妻之間情感障礙的象征。在物理層面,夫妻之間因為不同的行為與理念無法進行情感交流;在精神層面,當時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男性自恃掌握文明這一工具的傲慢或許是他抗拒與作為家庭主婦的妻子交流的深層原因。因此,在小說中,丈夫聽聞妻子執意冒雨尋貓時并未動身幫助,反而先用“我來做”在言語上剝奪了妻子的主觀能動性,而后對只身闖入雨中的妻子仍然不管不顧,只是繼續看書;當妻子因沒有找到貓而悵然而歸,并提起她想要恢復女性的魅力與吸引力、想要有穩定的家庭生活、想要突破婚姻圍墻鞏固夫妻關系,甚至想要改變她的社會地位時,丈夫也始終躺在床上看書,對妻子的一系列渴求置若罔聞,默認妻子需要生活在他的意愿下不得更改。無獨有偶,在海明威的另一部短篇小說《白象似的群山》中也有一位冷漠無情的美國男人,他對女朋友所說的話題同樣漠不關心,只是一味地希望她能夠墮胎,使其對婚姻陷入絕望之中。海明威通過描繪男性角色無法理解女性豐富細膩的內心世界,表明男性堅守崇尚理性的價值觀,并習慣性地用漠視和壓制女性意識的發展與表達的方式在男權社會中支配女性的言行、禁錮女性的思想。
相較于丈夫的無作為,旅館老板的有作為同樣凸顯出男性從根本上對女性意識的壓制以及對女性有所作為的否定。小說中,旅館老板作為情人或父親的替代形象體現了典型的男權社會價值觀:女性是弱者,需要男性來保護,同時反映了女主人公的存在沒有價值[6]。雖然旅館老板派侍女為女主人公送傘,但他并未親自出門幫助她一起尋找雨中的貓;他最后為女主人公送去玳瑁貓的行為,看似是出于對女性的尊重和體諒,實則如同溫柔刀,在無形中剝奪了女性的話語權,迫使女性接受男性的想法與安排。這種行為更深層次地壓抑了女性正向合理的情感需求,同時否認了女性作為獨立個體所能彰顯的價值、作用與地位,凸顯出在父權制頑固思想的主導下,女性的個體意識和個人情感始終取決于男性,女性僅靠意識覺醒而沖破社會成規束縛的困難仍舊很大。小說在此頗有深意地結尾,海明威并未寫明女主人公收到貓的心情與態度,他巧妙地使女性在這場自我意識覺醒的反抗中在最后被徹底剝奪了話語權,顯示出文明作為工具在男權社會中對女性意識更深層次的壓抑,這樣似有若無卻又不言而喻的懸念充分展現出海明威文學表達的高明之處。
正如英國女性主義者希拉·羅博瑟姆所指出的那樣,女性總是以各種方式被歷史隱藏。小說中還有多處細節體現出女性在男權社會中被輕視甚至漠視的境遇。例如,不同于男主人公有一個名字“喬治”,兩位女性角色始終無名無姓。因此,從小說中可以看出,海明威通過描寫女性處于傳統性別角色規定下的情感和感受,巧妙地暗示即便女性有意識地追求獨立人格與社會地位,最終也難逃被男性壓制的結局,表現出海明威于作品中蘊含的對女性的關注和同情。
2.女性意識覺醒的失敗
正如布盧姆在《現代批判觀點》中所指出的海明威敘事模式的特點:“通過對話和細節,用含蓄的、間接的、中性的手法暗示人物內心世界的變化。”[7]海明威在《雨中的貓》中同樣通過長段的對話展現了女主人公的女性主體意識受到社會傳統觀念的約束,女性意識的覺醒無法獲得實質性的勝利。
首先,小說中妻子對不幸和匱乏的表達,揭示了她婚姻中存在的問題[8],同時,她對自己愿望的讓步與放棄是女性受控于男性社會地位的體現。當她直率地向丈夫表達自己向往象征著女性柔美的長發;想要銀質的餐具和新衣服;期盼燭光晚餐與春天的到來時,卻遭到了丈夫的漠視。然而可悲的是,妻子在訴求無法得到滿足之后并沒有繼續努力抗爭,而是迅速做出了讓步:“反正我要一只貓,我現在就要一只貓。要是我不能留長頭發,也不能有樂子,那我總可以有只貓吧。”[9]她在潛意識中自然地放棄了一開始提出自己需求時的興奮與強烈的渴望,轉而低聲哀求丈夫給予自己些許尊重與關心,哀求無果后便接受了她在男權社會中的尷尬地位,最后無奈而凄涼地“望向窗外有燈的地方”。在海明威的另一部長篇小說《伊甸園》中,女主人公凱瑟琳則是剪了一頭男式短發,但她同樣是為了消弭兩性之間的隔閡。由此可見,雖然海明威筆下的女性角色所體現出的思想進步性不可忽視,她們出于女性本能的需求意識,對傳統的家庭婚姻制度、自己被賦予的依附性角色以及男權中心的意識形態感到不滿,并受此驅動去探索女性權利,但她們的女性意識并未完全覺醒,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女性對自己訴求的讓步與放棄暗示著其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終究在兩性和諧思想下寂滅,她們仍然無法改變并持續受制于丈夫的想法,她們的話語在男性的話語霸權下仍然顯得蒼白無力。
其次,“雨”是海明威小說中常用的意象之一,他曾表示“雨是空虛的代名詞”。在《雨中的貓》中,他通過描繪女主人公身處充滿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的異鄉,傳達了一種虛無主義的思想,即女主人公面對令人厭惡的環境時產生的孤獨與不安會迫使她躲進自己的內心世界,從而突出與激發個體的潛在情感,在小說中尤指夫妻之間的情感[10],而女主人公在枯燥無味的婚姻生活里無法被關愛呵護,更進一步放大了她內心的孤獨和荒蕪。在這種情況下,貓就是一種能引發情感波動的事物,促使女主人公超越她所處的那個封閉而壓抑的精神世界。因此,海明威通過描寫貓的意象來形象地影射女性的困境,使貓成為女主人公的化身,又通過貓的消失暗示女性意識覺醒的失敗結局。
貓作為一種寵物,通常只能依附于人類生存。同樣,女性在父權制霸權下難以擁有自己的地位、自由、尊嚴和權利。她們只能作為丈夫的“所有物”溫順乖巧地依附于男性生存,甚至被視為女性應有的“自然屬性”,難以實現自我價值。當雨強勢且難以逆轉地落下時,貓只能在桌子下面暫時躲避它被淋濕的遭遇,而女性同樣在男權社會中漂泊不定、孤苦無依、弱小無助,卻又難以改變現狀。貓在雨中的可憐境遇與女主人公如出一轍,于是她對貓的命運產生強烈的共鳴,對其產生惻隱之心。但貓的消失暗示著女主人公試圖反抗傳統男權社會的失敗,她終究屈服于與丈夫關系中潛藏的不適,并且無法擺脫不和諧的婚姻,難以保全自身的獨立人格。
另外,故事本可以在男女主人公的對話之后結束,但海明威在最后加了一個諷刺的結局,女主人公具有象征意義的愿望荒唐地實現了——她最后收到了旅館老板送來的“大玳瑁貓”,但從作者的描述中可以猜測,它并非她希望拯救的那只雨中的貓,且這種“得到”依然是男性給予的,更糟糕的是,通過得到她想要的東西,女主人公失去了隱喻她真實困境的手段以及真正擺脫的機會[11],丈夫對她的冷漠與壓制以及彼此婚姻關系中的交流障礙都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就被粉飾太平,女主人公憑借其意識覺醒而做出的努力至此意義全失。海明威成功地用小說所能達到的所有詩意,描繪了一種極其辛酸的人生體驗。
三、結語
《雨中的貓》沿襲了海明威簡練平實的寫作風格,運用象征手法、對比手法等修辭手法與不同的敘述視角巧妙地展現了女性在男權社會中面臨的困境與抗爭,以及兩性之間存在的思想對立與矛盾。盡管海明威在對女性角色的描寫方面還存在局限和不足,但他在小說中極力彰顯的女性意識覺醒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會性別問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并通過對角色匠心獨運的塑造展現了對女性充分的關切、理解與尊重;同時,他在小說中對兩性適當的社會角色、地位、價值、權力與相適性關系等方面做出的探索仍然具有前衛的思想意義與啟示作用。這部短篇小說就像一顆種子,種在了尚未覺醒的、將醒未醒的女性心里,同時也在潛意識中為已經覺醒的女性提供了指引,在不同時代持續觸及更廣大的受眾,賦予其不同時代意義的深思與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