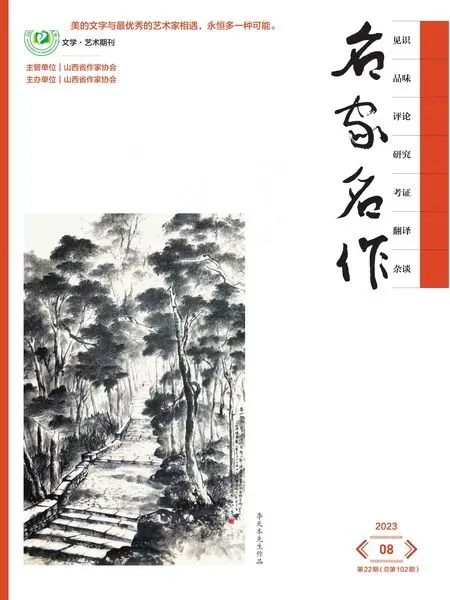費蘭特的文本執念與文學真實
謝雙超
意大利當代著名女作家埃萊娜·費蘭特(筆名)在當代西方女作家中已經成為一個“現象級”人物。在近30年的寫作中,她始終隱姓埋名,從未在公眾場所露面,堅持自己小說的“文本至上”,以至被人猜測為“一個寫作班子”,或一個男作家,或一個以故弄玄虛“吊胃口”來贏取關注的人等。但無論如何,她的作品已經被譯成數十種文字,并贏得廣泛好評,作品以獨特的視角、題材和對人性的深刻揭示,引發了人們的無盡慨嘆和日益深刻的思考。
到目前為止,作者相繼出版了長篇小說《煩人的愛》(1992)、《被遺棄的日子》(2002)、《暗處的女兒》(2006)、《成年人的謊言生活》(2019)和被稱之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離開的,留下的》《失蹤的孩子》。另外出版有通信訪談集《碎片》(2016)、隨筆集《偶然的創造》(2018)等。
其中《煩人的愛》和《被遺棄的日子》被改編成電影,引起了很大轟動,使作者獲得更多的關注。而“那不勒斯四部曲”也被改編成電視劇并連續播出。
一
文本就是出版發行的文學作品本身。費蘭特認為,一本小說出版后,就成為有獨立品格的存在,并以其作者所賦予的內涵特色走入社會。那些現實主義小說,因為抓住了時代熱點,觸碰到了人們敏感的關切點,反映了時代的重大主題,所以獲得人們對作品的高度關注。而深刻揭示人性、注視人類社會矛盾復雜性和個體、群體普遍糾結的永恒性問題,就決定了作品的價值。因此,在作者和讀者之間,文本才是最根本的。“書是一切,應該被放在首要位置。”①埃萊娜· 費蘭特:《碎片》,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第304頁。在近30年的寫作生涯中,幾乎所有的采訪者(都是文本問答,以信件和電子文本的方式)都會提出作者為什么“隱姓埋名”的問題,而費蘭特認為,作品出版而走向社會,正如一個長大成熟的孩子,再也不用依附于父母,人們關注、評價的只能是這個“新人”,而不應計較其父母是誰。
以作品為本,是作家對待作品應有的正確態度,但讀者或媒體對作家產生好奇也并不奇怪。僅僅是在文本封面上印刷一個化名,在當下社會難以算是很合理、正常的事。畢竟對作家成長背景和人生歷程的了解是理解作品的重要因素。費蘭特說:“我覺得讀者并不應該尋找作者的私人生活,而是要在他署名的書里尋找他。在文本之外,……我們要把書籍放在最中心的地方。”“一個作家比他的作品更出名,這是不應該的。”②埃萊娜· 費蘭特:《碎片》,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第340頁。她說,人們喜歡莎士比亞,絕對是喜歡那些偉大而杰出的作品。即使人們不知道阿可辛·貝爾(夏洛蒂·勃朗特作品上的化名)是誰,也照樣喜歡《簡·愛》。“文本包含的東西會超過我們的想象。文本已經飽含那個寫作的人,假如你要去找他,他就在那里,你會比真認識他的人了解到更多東西。當作家以簡單、純粹寫作——在文學中唯一重要的東西——的姿態出現在讀者眼前,他無法避免就成為敘事或者詩句的一部分,虛構的一部分。”③埃萊娜· 費蘭特:《碎片》,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第264頁。必須承認,費蘭特“文本執念”的價值毋庸置疑,但她堅持“隱姓埋名”,也許這并非唯一理由。
對于一個作家來說,通過自己的作品表達對人生命運的感悟與感受,絕對不是一種“自言自語”,正如費蘭特所說,雖然作品出版就成了“身外之物”,但那也是“我們積極生活的衍生物”,“一本書必須促使讀者去反思自身的處境,思考這個世界”。如果自己的作品確實幫助了困惑中的讀者,“我會很幸福,也會感到非常不安。……這也是文學一個沉重的責任”①埃萊娜· 費蘭特:《碎片》,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第314頁。。費蘭特多次談及拒絕公開露面的理由,說得最多的就是擔心公眾轉移對作品的關注,擔心由于媒體炒作,干擾自己內心和環境的安寧與自由,影響后來的寫作。自己既不想擴大“成功”和增加自己的光環,也不需要推銷作品,更不想效益最大化。甚至在作品改編成影視劇作品時,只是對改編劇本提出一些書面意見,并再三強調如果傷害“作品本意”,她寧可放棄改編拍攝。其實,后來她在悄悄看完電影后,感受到改編的不易和導演、演員的辛苦,也表達了尊重和感謝。然而,在“文本執念”意識下,她認為文學文本到底是原創,到底是內涵更為廣大和豐富的領域,那些影視改編也就是以文字故事為啟發進行的“再創作”。也正因為如此,所謂“忠實原著”和“超越原著”不僅不可能,甚至多數都是膚淺和簡化之作。由此看來,那些曝光度極高、聲名顯赫的大作家,確實往往就顯得“江郎才盡”“力不從心”。或許她隱姓埋名是一個優秀作家為文學理想而處心積慮的不得已而已。而無數的世界文學名著改編的影視劇作品盡管費盡心機、耗費巨大,擴大了原著的影響,卻并不能代替原著,得不到閱讀原著那樣的豐厚收獲。
由于費蘭特的作品深刻揭示了當下社會生活中人際關系的復雜性,如利益、友誼、情感、婚姻等諸多矛盾,她或許會顧忌現實生活中那些自己身邊人對那些“揭示”的感受。她在乎的不是能增加多少光環,而是擔心不要陷入無數怨恨的泥潭。她在多次采訪的回言中都說自己就是不想聲張,甚至不想讓身邊的人知道自己是什么“作家”。她愿意在一個“小小的角落和空間”寫作,面對突然的來訪,總是匆忙掩飾自己的寫作。正如她在回答記者詢問時所說:對于一個想投身于寫作的女人,“她需要對抗來自社會的各種各樣的壓力,不應該被自己的公眾形象所束縛,她需要全心全力投入寫作,無論是在表達還是在策略上,都要盡量自由,不受束縛”②埃萊娜· 費蘭特:《碎片》,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第351頁。。
或許這也與她的個性有關。“我屬于那種不喜歡照相也不喜歡錄像的人。我一旦注意到那些喜歡我的人用手機對準我,我就會轉過身,用手遮住臉。”她會明確地拒絕。從朋友對她相貌的稱贊可知,她并非自慚形穢或有什么相貌缺陷。“我口才不好,不擅長講話,不僅僅是在公共場合,私底下也是如此。”③埃萊娜·費蘭特:《偶然的創造》,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第99頁、71頁。至少這些都是她堅持“隱身”的各種因素。
無論是什么原因,費蘭特看重的就是自己的這支筆,自豪的就是自己的文本。
二
現在,埃萊娜·費蘭特已經是名滿天下了,其作品已經被翻譯成數十種文字。在中國,“那不勒斯四部曲”翻譯出版最早的是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從2017年開始,已經連續加印近30次。翻譯者四川外國語大學教授陳英博士說,每一次加印多時可達十萬冊。如今其所有作品幾乎都被讀者高度關注。2015年,費蘭特被《金融時報》評為“年度女性”。2016年,《時代》周刊將費蘭特選入“最具影響力的一百人”。《外交雜志》將其列入“影響世界的一百人”。美國讀者對作品的喜愛形成熱潮,被稱之為“費蘭特熱”。讀者認為其作品“寫出了真實而真誠的故事”。
很顯然,正如作者的自信,這些獨闖天下的“孩子”,已經走得越來越遠,影響越來越大,讓她感覺到了“文學的力量”。“至于我的書為什么成功,我并不知道原因,但我確信可以在講述的故事里還有寫作方式中找到答案。”④埃萊娜·費蘭特:《偶然的創造》,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第236頁。
費蘭特是寫女性故事的專業戶,如女性心理小說、女性教育小說、女性友誼小說……總之是以女人寫女性。這也是人們猜測她是女作家的根據,也是她承認自己性別特征的證據。她說:幾乎每一位現實主義作家在自己塑造的文學“主人公”中都無法隱藏作家的個性特征,當你充分閱讀一位作家的作品時,大致可以感受到作家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她辯稱自己并沒有“隱身”,甚至直接告訴大家,《煩人的愛》中的女主人公黛莉亞和《被遺棄的日子》中的女主人公奧爾加,兩個人成長的背景、經歷和性格等就有真實自己的影子。“我的寫作基于我內心的事實和情感。”⑤埃萊娜· 費蘭特:《碎片》,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第191頁。后來的作品仍然是作家本人對真實自我的演繹和補充。
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使費蘭特所有的小說都寫得那么“真實”,令人覺得書中人物血肉豐滿、性格鮮活,呼之欲出,似曾相識。甚至感覺那些故事就發生在身邊,那些看似意料之中或者意料之外的故事起伏,都讓人萬千慨嘆、百般低徊,從而沉思不已。尤其是“那不勒斯四部曲”,兩位女友六十多年的友誼,在作者筆下,那些日子和無數的故事中,甜蜜、糾結、怨懟、關心、痛苦都浸透著友誼和愛戀,“對愛的需求,是我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說起來好像是一件讓人難以置信的事……我們對愛的需求是最重要的,會排擠其他需求,支配著我們的行為”①埃萊娜· 費蘭特:《碎片》,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第72頁。。正是生活中的磕磕絆絆、恩恩怨怨、糾結痛苦,才使人們認清那些收獲、奮斗和滿足及幸福的可貴。人生是跌宕起伏、浪花四濺的小河,前面一定有平坦寬闊的去處。
讀者的激動與感動說明一切。“我們認為您的小說深入挖掘了女性的世界和情感,這是您創作的核心,已經遠遠超越了過去的作家對于這個主題的描寫。”您的“作品探討的問題很現實。我想象,您的作品也很可信、流暢而深刻。我很少看到這么深入挖掘女性內心生活和情感的作品。……我很確信您能幫助我們成長,讓我們獲得尊敬。我對您描述的東西特別有同感。”②埃萊娜· 費蘭特:《碎片》,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第199頁。
無數作家早已寫過無數關于女性的作品,如被視為神品的《簡·愛》《傲慢與偏見》《德伯家的苔絲》《安娜·卡列尼娜》等,除了文筆流暢、謀篇精當,都關注女性生活中最糾結的時代困惑,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尷尬的社會地位及復雜的情感世界。而費蘭特的作品恰恰具備這些特征:現代(后現代)西方社會中人的自由,個人主義,虛擬的(宗教)信仰,發展變化的代溝、矛盾摩擦和沖突,傳統的淡化以及自以為是,各行其是的社會情狀,人們如何“合理地”自處并與他人相處,其將這些全方位地展現在作品的故事中。人們理念的差異和變化,更加劇了語言和行為的費解。“我認為一個作家應該寫對他影響最大的事,但要在故事中找到一個能夠點燃讀者的溫度。一本書能成功,能流傳下去,那是因為它承載著那些最難醫治的傷口,能抓住一點兒之前人們浮夸地稱為‘時代的精神’的東西。”③埃萊娜· 費蘭特:《碎片》,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第203頁。毫無疑問,就是因為使讀者的感同身受和產生共情、共鳴,才使他們認可和接受了費蘭特對時代女性的精彩描摹與深沉期待。
是啊,這是個令人困惑無邊的時代!人們面對的是一個五花八門、光怪陸離、千變萬化、信息潮涌的時代!“碎片”?是碎片!不是整體、齊一、統合、一致,更非和諧、平順、曉暢、清晰。費蘭特說,當代感受多而深刻的可能是痛苦,“這個詞從我童年開始一直在陪伴著我”。而她母親常說的是,當一個人遭受各種矛盾情感的折磨時,感受到的東西是淤積在“內心的一團碎片”。這些碎片在心里東拉西扯,“腦子里有各種各樣的東西攪和在一起,就像漂浮在腦子上的殘渣”④埃萊娜· 費蘭特:《碎片》,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第89頁。。費蘭特肯定地認為,一個人如果很痛苦,遲早就會變得支離破碎。她的作品實在就是對社會病的一種深刻省視,立足心理分析基礎(她不喜歡大段文字分析)上的一種清晰展示,人物與故事雖然很瑣碎、似乎反常,但卻極其真實可信。她尤其在意“深深挖掘女性內心深處的疼痛”“女性生活中的缺陷”,“希望那些難以言說的東西能夠出現在小說的字里行間”。而所有的“挖掘”和“赤裸裸的揭示”,就是為了“令人正視和警醒”,“讓人反思一些深層的問題”。
費蘭特認為自己不是在寫歷史、寫自傳,實在不適合用“真實”來評價自己的作品。自己只是懷著一腔真誠,追求符合時代特征,因為文學就是立足于現實、超越現實的虛構。“從根本上來說,文學就是一種謊言,是大腦的神奇產物,是語言組成的一個獨立世界,對于寫作的人都是真相。” “讓一切變得精致而新穎的是文學的真實。”而文學真實就“意味著說出真相,文學的虛構讓你可以去說實話”,意味著“拋開所有技巧和效果,真實會推翻那些看起來真實、迷惑人的東西。我更喜歡一種真實的效果,而不是象征層面忽然涌出的真相”⑤埃萊娜· 費蘭特:《碎片》,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第112頁、198頁、238頁、261頁、289頁、296頁。。正如畢加索所謂的“藝術以謊言的形式向人們展現真實”⑥愛德華·威爾遜:《人類存在的意義》,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第41頁。。
埃萊娜·費蘭特堅持以寫作追求真相,揭示那些深埋人們心底、不想表露和難以啟齒的東西,以引起閱讀者警醒和捫心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