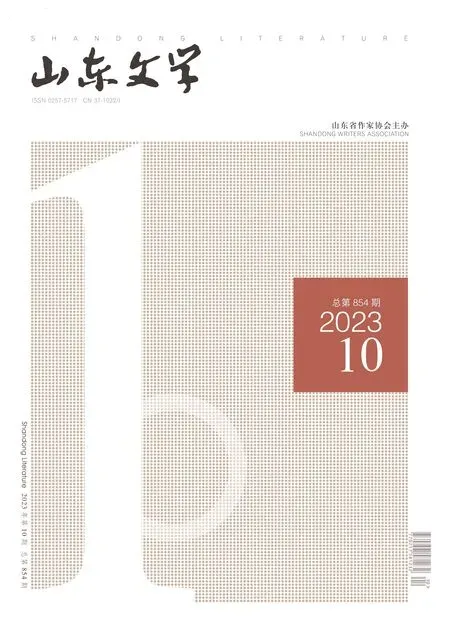靈魂手札
楊彩云
一
2015 年,我六十五歲,想寫一部拋卻所有虛偽和淺薄,真正屬于自己的書。這并不是說之前寫的書不誠實,只是出于各種客觀制約,許多時候敞不開心扉,而不得不將一些自認為非常重要的東西扣下來,造成部分的缺失和無奈的遺憾。而人到暮年,還有什么可顧忌的呢?什么也不怕了,不要糟蹋了最后的歲月和手中的這支筆。于是很快有了一個選題:我們這代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人,雖然晚年大都安樂幸福,但我們經歷的太多了,饑餓、迷惘、掙扎、沉淪、奮進……可以說,人間的苦難,除了戰爭其他都經歷了。
總結閱歷,世間的事啊,有著驚人的重復性,以為突圍了,卻還在里面,不知什么時候還會突然被撞一下,撞得頭破血流。就像遭受了邪惡的詛咒,怎么也不能徹底擺脫,于是還沒有動筆,書名便有了:《魔咒》。
說寫就寫,當年年底,《魔咒》便完成了一稿,電腦顯示五十七萬字。我打字飛快,但不是寫出來的,是“喊”出來的,那是一種純粹的發泄,有什么泄什么,黃河決口,滔滔不絕,怎么痛快怎么來。后來常有人奇怪地問:“你怎么寫得那么真實?”能不真實么?那是在地殼的高壓下擠出來的原油,是西瓜熟得自個兒落了地,又裂開淌出的紅瓤,能不真么?嚴格地說,最初的那一稿不是小說,而是個超大的日記,在肆無忌憚的叫喊。得到了某種程度的發泄之后,我的情緒有所緩解,不再是個發瘋的婆子,漸漸又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作家不能自說自話,應該為社會發聲,為大多數人起碼為一部分人發聲,個人情緒必須與大眾情緒保持一致,才有社會性和代表性,才能讓讀者產生共鳴,引起共思和共議,才可以成為送給別人觀瞧的文學作品。
于是開始了第二稿,這一稿就比之前內容豐富了,切入了時代背景,將故事進展、人物成長與時代擰在一起,我想起了許多熟悉的人和事,許多故去的和活著的朋友,許多印在腦子里永遠也洗不去的事件和場景,開始重新組合重要人物,重新確立主人公形象,重新洗牌,盡量將內容立體化具象化。我要盡其所能地為那代人呻吟、呼喊、流淚和歡笑。
當然,這并不太難,因為我對那些東西太熟了,無論人或事,都活了似的紛紛跑到我的筆下,擠著讓我安排,我就是起了個召集的作用,把他們盡量有序地放在合適的地方。什么時候出現什么人,什么時候發生什么事,這由不得我,而要由著歷史的推進和人物性格的發展。我就是個調度員和化妝師,負責每個人不要亂跑,負責他們的服裝頭飾,自然也負責道具和美工。
而我也必然是其中的一員,屬于自編自導自演,所以很投入。我回到了六十多年前朦朧記事的時期。還記得當時的民歌:老年賽黃忠,青年賽羅成,婦女賽過穆桂英。后來就記得提著小瓦罐去食堂領飯了,先是大個的紅薯,有一斤多重,稀溜溜的,小孩都拿不起來,大人們感嘆:得燒多少柴禾才能煮成這樣啊。后來紅薯沒有了,只提回來半罐清湯。有次路上被人伸腿絆了一跤,湯灑了,我哭了,一輩子不愛理那個人,至今想起心里還有點兒耿耿——那是饑腸轆轆中唯一可下肚的東西啊。
但那時,人們是多么地振奮啊,似乎共產主義真的明天就要到來了。我六歲上學,老師嫌小不要,但我已經認得一些字,數數也不差。那時收學生的標準是能不能正確地數夠十個數。我學會的第一支歌是少年先鋒隊隊歌,而讓我激動得熱淚盈眶的第一支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這些,對我的一生都產生了重要作用。每當聽到她們的時候,兩行熱淚滾滾而下,那種激動和當初的激動一樣,心弦隨著旋律一齊顫動。我愛我們的國家,我愛我們的人民,我也愛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就是從小印在心里的思想。所以,《生命深處》多次提到保爾·柯察金的那段名言——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由此可見,幼年的教育對一個人是多么重要。
我今年七十三歲了,身體不好,已是風燭殘年。但往事歷歷,依然如初。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可恨的好記憶,許多的事情放不下。愛的依然在愛,恨的依然在恨。不僅沒有削減,反而某些感覺還在加強。好壞的作用是長效的,就像往人體里打激素,打到一定程度就產生永遠也無法消除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越來越嚴重。但對搞寫作的也許是好事,它可以幫助人不太費勁地就找到感覺。于是,我從剛記事那時開始,一節一節地回憶起來,并一節一節地開始敘述。當然,《生命深處》的延伸期在一百多年前,那肯定是虛構,小說就是虛構嘛。只有思想內核是真實的,這種思想內核是作者的原動力,也是作品的內在支撐,是作品和作者的共同靈魂。我想干什么呢?我想讓尚有良知的人們知道,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希望許多的悲劇不要發生起碼少發生,讓善良的人得到安寧,讓邪惡的人感到羞恥,讓這個世界更加美好。而要達成這樣一個目的,必須對社會進行深刻的思考,對歷史進行認真的回顧,對人性進行CT 機式的切片掃描。
二
寫這部書真的需要一定的勇氣,這是自揭自家的瘡疤,而且沒有麻藥和消毒水,時時都是撕皮割肉火辣辣的痛感。
親戚中正式送書看的只有大姐。因為大姐問“又出書沒有?出了就寄給我。”我趁機趕緊寄了過去。我倆都是被上海拋出來的孩子,感情上比較接近。過了一陣子,做賊心虛似的打電話問看多少了?電話那頭大姐的聲音平靜中略帶激動:“看完了,惹得哭了好幾回。”我一下子放了心,謝天謝地,我的大姐沒惱。大姐問:“你怎么還記得三陽路?我都忘記三陽路了。”是的,我記得三陽路,盡管在我出生那年上海的三陽路就改成了中山北路,但我還是記得。并根據三歲之前少得可憐的幾個畫面還原了三陽路,也還原了上海解放初期的棚戶區。前幾年有部電視劇叫《國家的孩子》,講困難時期上海將一群孤兒送往草原,后來在那兒生活成長的故事,由傅程鵬主演。我看了好幾遍,是替我大姐看的,大姐十七歲離開上海去往戈壁灘,雖然不是孤兒,但也和孤兒差不多。至于我,曲里拐彎同樣存在著那種感覺。
大姐沒有惱,我很欣慰,這樣也算替大姐寫了一番文字。還有我那個可惡的記憶,抹上了就再摳不去,上海中山北路126 號就是我家的門牌號碼,直接就寫上去了,改一個數字都不痛快。是的,《生命深處》的不少地名和人名都是經過反復思量的,都和原型有著某種關連,甚至一字不改,直接實名制。只有這樣我的情感才通暢,筆下才有感覺。比如里面的馮氏,那是個量身打造的人物,活生生的就是那樣,幾乎一點兒都沒有走形。我也曾把她改為柳氏,但不行,感覺立刻不對,看著就別扭,就像鑰匙沒對準孔眼,咔啪咔啪亂響,只好又改回來。當然,主人公端木槿絕對是綜合了那代人基本特征寫出來的,她是那代人行為和思想的代表,是平民英雄。但她也不是完人,有馬失前蹄的時候,甚至關鍵時刻會有重大失誤。比如與馬向東的婚姻,自己給自己設下了個巨大的陷阱,深陷其中走了許多彎路,吃了許多苦。有讀者十分惋惜,問為什么要讓她嫁給各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的馬向東?但設身處地想想,她那個時候還有出路嗎?她也是個知冷知熱有血有肉的人呀,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情況下,她崩潰了,她完了,這就是人生悲劇。但端木槿之所以是端木槿,是她依然站起來了,并沖出來了,盡管傷痕累累,她還是鳳凰涅槃地踏入了社會,成就了自己。這就是那代人的情操和追求,那代人死而復生的鋼鐵意志。
端木槿的人設當然是很慎重的,因為她是主人公,整部書幾乎都是圍繞她來寫的。百萬字的長篇,第一章她出生,最后一章她去世,一生涵蓋了中國七十年的歷史。她如一只小船,在九曲十八彎的歷史河道里迂回前行,也有順風的時候,但順風遠沒有逆風多。所以,端木槿必然要用巨大的努力來換取最后的成功。但這種為了追求理想九死而不悔的精神不正是社會所需要的嗎?不正是許多人所缺失的嗎?所以,只能讓她受苦,不受苦沒有辦法,我救不了她。她出生的家庭、所處的年代加之她倔強不屈的性格,必然要發生那樣的事情。她一生沒有過真正的輕松和幸福,最后的結局,在定稿之前比這還要慘。于是有人說,你不能這樣殘忍,慘得看不下去了。中國戲劇往往以大團圓結局,所謂“不殺奸臣不煞戲”,那是人們美好的愿望。梁祝死后也得讓他們化為蝴蝶,然后一起翩翩起舞,那是浪浪主義。而我是現實主義。但在別人的提議下,也來了一點兒中和,于是最后一稿讓結尾有了一絲溫情,端木槿在沒有遺憾中比較安慰地死去。但書問世后立刻又有人尖銳地指出:她不應該這樣溫和地死去,這是一種人為的安排。建議如果將來改電視劇,一定要按原稿改過來,那才是真正的現實。真佩服這位先生的洞察力,一眼就看出了“作弊”。也就是說,我還沒有真正地正視現實,沒有將悲劇進行到底。沒有進行到底的原因是我的心軟了一下,但現實會軟嗎?現實是無情的,如果端木槿真有其人,她的最后肯定也是悲劇,她就是個悲劇性格。
但我讓她有了一段真正的愛情,甚至讓她與真愛發生了性。這在我四五十年的寫作生涯中是破天荒的唯一一次。我所有的作品與風月無關,從不寫情愛。有人當面開玩笑:你的作品不好看,連個接吻的場景都沒有。世間除了情愛就沒有其他了嗎?非得戲不夠愛情湊嗎?太可笑了。我對情愛沒有興趣,所以不寫情愛。但必須給端木槿一段情愛,還必須讓她與所愛的人發生性,哪怕只有一次,也能讓她的人生完整,不然那才叫殘忍。
《生命深處》中的秦月,是個比較受喜愛的人物,因為個性特別。這個人是有出處的,我說過幾乎所有人物的名字都與原型有關,此人名叫孫月霞,是我的一位初中同學,著名劇作家,曾憑歷史劇本《畫龍點睛》名噪一時,可惜去世了。秦月便是為了紀念她而設的,而秦月從形象到特征則完全是小說版的孫月霞。我們倆在互不通氣的情況下,竟同年一個開始寫小說,一個開始寫劇本,并都獲得了成功。當時有人撰文寫了篇“宋江河畔三女杰”的文章,挺有影響,那就是她和我,另一位是歌唱家。她的去世,讓我難過和沉默了許多時日,人生無常啊。作為懷念,我讓秦月成為三劍客中人生最完美的一個。她還好好地活著,活在我的心間。至于王鳳華,則集中了農村基層婦女干部的所有正面形象,可以說她是張英,也可以說她是李華,她是優秀婦女干部的代表。在長期的工作中,我和許多這樣的女同志成為朋友,她們會把自己的故事講給我聽,我也會在有意無意間觀察她們,當然那時不是為了寫《生命深處》,而是一種職業的本能。
三
為什么要寫悲劇?因為我寫的是端木槿。端木槿是行走在懸崖上的人,懸崖很高,路很窄,雨天路滑,不掉下來都困難。而當她墜落的時候,眼看著也沒有辦法。夠不著,夠著了僅憑人的雙臂也托不住,她帶有高空沖擊力。在我走向文學創作之路的時候,最初動筆寫的就是一部長篇悲劇。也許因為其中的人物和情節有些感人,被推薦參加山東省作協中長篇小說座談會。著名作家劉知俠、林雨和王希堅親自審閱,并在字里行間密密麻麻寫了修改意見,可見其重視程度。可是傷痕文學瞬間過去,有人提出了質疑:新社會有悲劇嗎?我那時只有二十幾歲,是個初學者,連標點符號都點不太準。但我很不理解這種提問,你沒活在天底下嗎?有些悲劇的發生是不講時代的,辟如車禍,辟如天災,太平間里哪天沒有冷凍著的人!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悲劇,就像有空氣的地方就會有生物。只是要看這個悲劇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說明問題的可能性。悲劇是最彰顯人性的事件,人在它面前無所遁形。現在回想起來,為什么《生命深處》想動手了就可以即刻動手,連腹稿都不打,那是因為我已經為它做了一輩子的準備,決非一時興起。我絕非多愁善感之人,喜歡交友,喜歡大笑,還能豪飲。以往文章中也常帶有一種豪氣,誰又知我能寫這種以淚洗面苦不堪言的悲劇,不可思議的矛盾現象。這是真覺得苦了,不吐出來不行了。也許水火交融,才能產生更狀觀的景象。更重要的,我的職業是作家,老牛自知黃昏晚,還能再寫多少東西呢?一生都沒有怎么追求榮華富貴,到了這個時候,更應該放下一切的虛偽和怯懦,去表達心中最想表達的東西,寫出一部有分量的真正屬于自己的作品來,相當于阿Q 畫他的圓圈。最初的時候,我想大概能寫五十萬字,但第一稿就是五十七萬,接下來這里補上一個情節,那里再添加一個人物,添去補來,最后達到了一百萬。我要的不是數字,數字說明不了根本問題,我要的是質量。一小塊黃金頂過一大車石頭,但如果真有一大車黃金那不更好嗎?質量的問題在于深度和厚度,在于駕馭文字的能力,在于所要表達的東西有多少價值。我真的是個很不聰明的人,空有一身膽,卻很難看透事物的本質。所以只好拼命地想,想破腦殼地想,分析社會,回顧歷史,拆解所有可能觸及到的現象,當然更要分析人。世界上最復雜的是人心,人說人心有六個棱,而我說不知道有多少個棱,連每個人自身都不會真正清楚自己。因為會變,萬花筒般動一動就變。而活人又是在不停的運動之中,那么就要去捕捉瞬間的變化和形態,來完成自己的作品。我讀過兩年中文,記得最結實的兩句話就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和“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生命深處》的最難點,就是事件發生時的社會性和歷史性,雖然作品中沒有幾個直接關于這種問題的字眼,但它無處不在,是情節推進最根本的掌控點。情節不會自個兒產生,人物也不會自兒長成,都需要時代和社會做他們的根基和鋪墊,或者說是一切人物運行的底色和軌道。
我有一個長處,就是會看人,知道人在什么時候想什么做什么,什么時候有一個什么樣的笑臉或哭相,也就是說,文字語言還算過關。我時常坐那兒冥思苦想,怎么樣才能讓作品更厚重一些?讓人物更豐滿一些?讓語言更精彩一些?沒有捷徑可走,只有苦思苦索,誠實地去反復回憶和思索所寫時代的外在和內涵,尋找人物命運和它們的重要關連,掘寶一般去努力地深掘一點,再深掘一點。哪怕掘出一絲絲新的光亮,也欣喜若狂。因為我知道這是作品厚度和深度的根本所在,更知道這可能是我最后一部作品了,必須把它寫好,必須把圓圈畫圓,不讓此生留下遺憾。
人物也不是那么容易寫的,端木槿這個醫生身份就讓我費了老鼻子勁兒。我對醫學一竅不通,又必須寫得像個醫生,還是個中西醫結合,會針灸,會開方,會急救治療。我去鄆城縣中醫院學習,實習生一樣跟在醫生屁股后面從病房走到藥房,從辦公室走到ICU,裝模作樣地摸摸病人的頭,詢問病人的情況,看人家的病歷,要人家的處方。鄆城中醫院十分配合,第一天為了等我,晚了半小時才開始查房。之后,只要需要,就打電話詢問,再加上我自己生病和看病的經歷,好歹湊成了端木槿。這個人物不是醫生的時候,我幾乎游刃有余,而當是醫生的時候,不敢多寫一個字,不敢有半點兒發揮,一個詞也要在百度上查找,唯恐露出馬腳。以至后來有人問:你當過醫生?我笑著搖頭。甚至有位先生打電話咨詢精神病患者怎么治療,因為端木槿用針灸治好了病人。當然,也有真正的醫生提出了一些問題,說有些兒不太像。這是肯定的,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在真人面前糊得再好的紙人也糊弄不過去。如果我把端木槿的身份改為民辦教師,那就無論如何也不會露蹄爪了,因為我有著十三年的教齡啊。但不能把她弄成教師,弄成教師就更成了我了。為了避這個嫌,可累死我了。
許多人屬純虛構,比如李玉全,比如曲峰,比如端木友和董先生,還有馬任遠等等。端木槿需要有這些人,這些人能幫著完成端木槿形象的塑造。但假人得當成真人寫,他們真的活動在我的眼前,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都生動鮮活,我也就用語言把他們生動鮮活地搬了下來。曲峰死了,我哭得很傷心,心痛曲峰心疼端木槿,那么悲壯,那么凄慘,我自始至終陪著端木槿在追悼會上痛哭。寫到曲峰給端木槿的幾封信的時候,又嗚嗚咽咽地哭起來,寫一遍哭一遍,似乎真的看到了曲峰在雪山之上寒夜之中披著毛氈給愛人寫信,一封一封又一封,充滿愛之激情地寫,卻不知這是絕筆。許多的時候就是這樣,一邊寫一邊哭,一邊寫一邊笑,只是笑的時候沒有哭的時候多,也就造成讀者哭比笑多。有讀者在網上說,看這部書要先準備好擦淚的紙。可他們不知道,最早哭的是我,哭得最多的也是我,許多時候,我伏案大哭,而且是寫一遍哭一遍。就像那些地方有淚泉,一到地兒淚就控制不住地流下來。我是個多么硬氣的人啊,幾次生病開膛破肚都沒皺過眉頭,可是我為我的人物哭,我深愛他們,就像母親愛孩子。我希望他們好,可是我沒有辦法拯救他們,我只能把他們的事情寫下來,以敘衷腸。于是,我的筆下便出現了一幕幕悲催,希望這些悲催能引起人們的思索,能化解些人世間的戾氣和邪風,讓生活變得更美好。
四
我的重點在于寫人,社會歷史只是背景,人物投在這些背景上,折射出時代和歷史的色標。我只是在充當一個端木槿式的醫生,大聲說出自己對病情的分折。而人,都會生病,社會也會有病,沒有病就不需要前進了。可怕的不是病,而是諱病忌醫。雖然我不會鬼門十三針,去扎回一個人的記憶,但我希望用我的文字去喚醒一些稀里糊涂生活和在錯誤的路上不肯回頭的人,我希望我能像蠟燭一樣點燃起青年的希望,給他們一點向上的勇氣和力量,我在拿端木槿為他們做榜樣。所以,盡管我寫的是悲劇,但風格卻絕對悲而不哀,苦而雄壯,滿滿都是正能量!我極不喜歡負能量太多的人,讓人喪氣,讓人提不起精神,讓人活著也像死了。為什么不精神地活著呢?生命只有一次啊,所以我們要振奮,要努力,要像保爾那樣把自己煉成鋼鐵。當然,我們離鋼鐵都還很遠,這就需要繼續努力。《生命深處》要實現的是一種價值,追求的也是一種價值,人的價值,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一步步走向的是生命的高峰。當然,價值最終水平會因人而異,但一個人只要盡到他最大的努力,他就達到了自我價值的頂峰。
《生命深處》第八稿完成了,是該送給某些朋友看看了,提些修改意見。這也是寫作生涯中從沒有的事情。我是個獨行者,從不請人看稿提意見,也從不請人寫序,似乎那是狗尾續貂,有蹭別人熱度之嫌。2018 年4 月,我乘車去菏澤,參加市文學創作突出貢獻獎頒獎儀式,路上接到一位朋友電話,和我談修改意見。他是一位資深編輯,對于小說創作有著獨特的見解,他提了四條誠懇且中肯的意見,我一一記在心間。頒獎完畢,順道回了鄆城,與朋友相聚,同時也去醫院做了一下體檢。影像報告單上顯示“腎積水”。何為腎積水?不懂,其實上一年就說腎積水,但忙于寫作,沒當回事,連找人看報告都沒有。這回找人看看吧。醫生是我的一個學生,學生皺著眉嚴肅地望著我:“楊老師,你回濟南以后要馬上去大醫院做進一步檢查,不然,你的腎可能要保不住了。”我有些吃驚,沒太大感覺啊,有這么嚴重嗎?但也不敢再大意,回來后就去了醫院,醫生讓住院,這才覺得可能是有些問題。但向來獨立獨站,自己的事情自己承擔,雖然和女兒同住一個城市,但沒有住在一起,住院也沒有告訴她。一個人捏著單子,樓前樓后樓上樓下,每天反反復復做各種檢查。怎么這么煩人呢,比我寫文章還復雜。第七天午睡醒來,一睜眼女兒在床前站著,我奇怪地問,“你怎么來了?”女兒一臉委屈:“你住院了也不告訴我。”我笑了笑,告訴她干什么,她又不是醫生,我又不需要照顧。半月后我被從內科轉到了外科,醫生問:“你有孩子嗎?”我回答:“有。”“明天讓你孩子過來。”我感到有些不妙,但醫生的樣子根本不想對我說什么,只好給孩子打了電話。第二天,女兒女婿都來了,首先去了醫生辦公室,出來后臉色不太好,但也沒多說什么,只是說:“需要手術。”我說,“手術就手術唄,要做趕快做。”趕快做趕快好,我還急著去改稿呢。那會兒還想起趙麗蓉侯耀文演的相聲《英雄母親的一天》,記者反反復復教給她如何說話如何走路,她卻“司馬光砸光”一個勁兒地說不對,急得最后裝病,然后端著盆急急買豆腐去了。我也很急啊,卻在醫院里沒完沒了地耗著。我所知道的就是個瘤子,需要切掉一個腎,切掉就切掉,反正還有一個。于是若無其事地進了手術室,出手術室以后,人是不能動了,還高燒不退,好容易退下去就該出院了。可病理報告卻遲遲不拿給我看,催了幾遍,女兒哭了,我一下明白了怎么回事,但訓斥她“你哭什么?我還沒哭呢。”是惡性,而且屬高密度。唉,看樣子一時半會好不了,既來之則安之吧,接下來化療,計劃六期,每期比同病房的室友多用一倍的藥,重藥治大病,看樣子是不輕。各種難以忍受的不適很快到來,頭發很快脫落。但我極不喜歡住院,病房太吵,夜里無法睡覺。只要有一點兒可能,我走幾步歇一歇,一個人走到公交站牌,傍晚再一個人走回來。女兒太忙太累,我知道人在崗位上的不易,不能長期請假,盡量少影響她工作。第四期剛開始,血鈣突然成百倍地升高,立刻轉往內分泌科,是甲狀腺旁瘤,一個從來沒聽說過的病。但這個病十分可惡,會迅速地把骨中的鈣吸出來,然后積存到腎里。我只有一個腎了,可不敢讓鈣占地了。于是立刻手術。這個手術在脖子上,醫生給我拍了照,看上去血乎乎一片慘不忍睹。原以為是小手術,結果失音了,一年多不能發聲,指手劃腳冒充啞巴。喉嚨里那個負責開關的物件失了靈,吃飯喝水都往氣嗓里跑,整天弄得狼狽不堪。化療還得接著進行,這下好,一刀沒過癮,再來一刀,化療也值得了。
我不能說話,也不能平躺,好在有個躺椅,日夜在躺椅上躺著,直到現在五年了都沒有上床。人不能動,可腦子能動,我在思索我的稿子,思索怎么才能讓它更厚重一些,更藝術一些,哪些地方需要怎么改,哪些地方需要再添些東西。畢竟八遍了啊,所有的文字幾乎全都打印在了心上,哪兒有什么問題全知道。還有題目,原來不是叫《魔咒》嗎,三稿的時候有天看電視,突然在屏幕上出現“風雨晚來秋”,呀,這個名字好啊,那時正在寫端木槿凄涼的晚年,與我的心境十分吻合,且十分文學。于是改為《風雨晚來秋》。但八稿之后躺在那里再次認真考量的時候,感到風雨晚來秋調子太低沉,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那么叫什么呢?要找一個通透全文綱舉目張的名字,但想啊想啊想不出來。急得無數遍抓著自己的頭發喊著自己的名字在心中高叫:“楊彩云,你到底在寫什么?你到底要表現什么?” 突然,一個名字出現了:生命深處。雖然這不像文學名字,而更像個哲學名字,但寫的就是這個!
于是最終定名:《生命深處》。
我在叩問生命的意義:在生命的深處,我們能留下什么?能找到什么?同時,也是一種人生的嘆息。
大半年后坐得起來了,我立刻走到了電腦前,打開電腦的那一刻十分激動,我終于回來了!但手指僵硬,敲打不起來。我打字多快啊,還是四通打字機的時候,所有報刊和出版社都不再接受手寫體,需要先送到打字部去打印。可是打字員們從來沒打過文學作品,許多地方根本不懂,弄得錯別字滿篇一塌糊涂,氣得我大光其火。隨后說:“你們別氣我了,我也不罵你們了,我自己去學。”社會上剛有電腦,極貴,還需托關系才買得到,但也有了電腦培訓班。我去了,問什么輸入法最快,人家說“五筆輸入法”。那我就學五筆。整整兩個月,天天坐在電腦前,只練習指法,聽著啪啪啪啪清脆而有節奏的鍵盤聲,像聽歌似的享受。之后便會用了,盲打。二十多年練習下來,如果失了業完全可以去干替人打字的活兒。可是,我的十指不聽話了,一天下來,不過改了百十個字,所有的指關節疼得像斷了一樣,全扎煞著彎曲不得。我暗驚,壞了,不能打字了。第二天,還是試著打,慢慢的,能動了,啪啪啪啪有節奏的聲音又響起來了,我放心了,沒事了。
如此又過了一年,改到了十一稿,為什么改那么多遍,因為像打發心愛的女兒出嫁一樣,總想再好一點,再完美一點,哪怕一根頭發絲也不要亂。2020 年初,與作家出版社達成了出書意向,讓把稿子快點發過去。但我還是沒發,還要再檢查一遍,就是這一遍,把結尾改了。那是即將年關的時候,累得站都站不住,因為我的病始終沒有好,而這種病又極怕累,但病痛和勞累對于那時的我已不是事兒,我只要完美的作品,起碼保證自己滿意。還要盡快把稿發給人家,作者對出版社都是懷揣敬畏的。身體不好以后可以慢慢地養,文字變成印刷體就一個也改不了了。我依然坐在那里,啪啪地敲打著鍵盤,感覺就是個上了戰場的戰士,在端著刺刀渾身是血地拼殺。終于把稿子發出去后,我虛弱地對編輯說“從此我再不看一個字,最后校對定稿也不看,拜托了。”
是的,我可以說自己是個戰士,從小就是。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各種艱難困苦只能自己解決,無依無傍。從而養成了獨立獨站不依賴任何人的性格。但我也是幸運的,我人生的最大幸運就是從事了寫作這項事業。前幾天身體特別差勁,因為已經進入了生命倒計時,說話都快沒聲了。女兒擔憂地問還有什么事能讓我快樂一點?我想了想說:“還是寫作。”只要一坐到電腦跟前,一進入寫作狀態,就會精神大變,迅速振作起來。到了這個時候還能忘記所有,思維敏捷手指飛快,大概我就是個為寫作而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