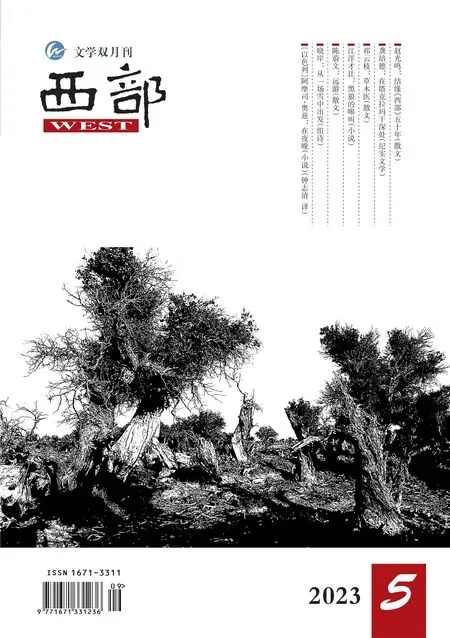錫婚宴
丁奇高
一
宴會設在一個免門票的景區里。景區很大,掛著“AAA”級的牌子。周邊廣袤的荒灘地里種滿了常青樹,郁郁蔥蔥的。
我進去以后,跟著指示牌,繞了一大圈才找到地兒。
一座農家飯店掩映在茂密的小樹林里,像是擴大版的“四合院”。一身喜慶的迎賓小姐領我到達宴會廳。她精致的高跟鞋在我前面發出“嗒嗒嗒”的響聲。我突然有點兒后悔來這里了。
宴會廳的背景屏幕上是一家三口的巨幅合影,照片像是在某個公園的草地上拍的,上面的一行大字寫著:愛在你的左右。我雖近視,卻一眼就看懂了這行字的寓意。三個男人從我身邊經過,他們邊走邊談,中間那個就是今天的男主人向左。他居然假裝沒有看見我。
白色衣裙搭配平底編織涼鞋。我從來沒有這么穿過。也難怪。
真是不該來這里見證別人的錫婚。
前面的幾排椅子上人已經坐滿了。過道上幾個小孩子拿著氣球,舉著扎了羽毛的魔法棒四處亂跑。一個小姑娘嘴里喊著:“別過來,黑暗女巫。”只見她東跑西跑,最后躲在了一張椅子后面。我悄悄走過去坐下,對她眨了眨眼睛。她蹲到地上,一只手抓住我裙子的一角,另一只手捂著嘴笑。
我的腦海里出現了小時候偷吃甜果子,而媽媽卻毫無察覺,仍舊拎著果子盒帶我去串親戚的畫面。
“陳旭,你早來了呀。”是呂麗,是個上身異常豐滿的大美女。
“我也是剛到,不過你小聲點兒,我正在掩護在逃公主呢。”
小姑娘見有人來了,嘴里叫著“奶奶,奶奶”跑開了。她是向左哥哥的小女兒。
呂麗是我的高中同學,那時我們住一個宿舍,像是影子一樣整天黏在一起。近一年不見,她消瘦了許多,下巴上冒出一堆奇怪的小痘痘。
“瘦了啊,只是你這臉?莫非是迎來了第二春嗎?”
“哎,一言難盡,怎么說,算是辣椒吃多了吧。”
“你們都來了呀。”向左朝我們走了過來。他那張臉白凈、帥氣。看得出來他今天精心收拾過。“呂麗可是出過國的女人,見多識廣,不好伺候。”
“我哪兒不好伺候了?”呂麗撇撇嘴,“你這是推卸責任,想輕易就把我打發了?今天你這錫婚宴的酒必須給我備足了,姐姐我不醉不歸。”
“管夠,晚上你們睡我家里。”向左笑嘻嘻的。他看了我一眼,馬上扭過頭去。前面有人叫他,我和呂麗示意他快去。
舞臺上主持人開始講話,賓客們漸漸安靜下來。
呂麗湊到我的耳邊說:“向左的媳婦看起來不像有那種病的人呀!”
“那是一種慢性病,照顧得好,十年八年死不了人。”
“她挺可憐的。”
我拍了一下呂麗的屁股,發現她的皮膚異常松弛。
主持人請今天的女主人談談感受,女主人聲音很小顯得有氣無力,說了沒幾句,眼淚便“滴滴答答”落了起來。
二
向左的媳婦家有姐妹三個,她在家排行老三,小名三兒。我跟前夫沒離婚時,她跟著向左來過我家,那時她還沒有得病,看起來楚楚動人,我揶揄向左撿了個大便宜。
她婚后患上了紅斑狼瘡,致使五個月大的嬰兒胎死腹中。
我的第一段婚姻維持了不到七年,離婚的主要原因是前夫看不慣我的生活方式。他訓斥我都結婚生孩子了怎么還整天做著文學夢。我們離婚的導火索是一套《博爾赫斯全集》,當時花了三百多塊錢,差不多是我半個月的工資了。前夫為此氣惱不已,伸手打了我。
“陳旭,你看,”她嘴里不知什么時候含著一顆糖,我聞到了是薄荷味的,“向左怎么還跟棵楊樹似的戳在那兒,三十七歲了也不發福。”
的確,臺上站了十幾個人,都是他們一大家子的。向左的媳婦三兒個子不高,穿了高跟鞋勉強一米六,向左媽更低,向左的哥哥矮胖。三兒身邊的小男孩大約五六歲,是向左的兒子向右。還有剛才那個小姑娘,一直被她奶奶扯著小手。
“時間過得真快,那時候向左還是個小不點。”我感嘆。
“可不是嗎,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呂麗掏出手機拍照留念。
我和向左高二坐過一年同桌。那個時候他身高不足一米五,長著一頭細軟發黃的頭發,小臉蛋,深眼窩,說話奶聲奶氣的,跟個洋娃娃似的。
我在家挨揍,向左在家挨過的揍不比我少。扇臉、罰跪、擰大腿,即便挨了揍,他哭也是錯不哭也是錯。我們的友誼就是在互相傾訴自己受過的疼痛中建立起來的。
但僅僅過了一個并不漫長的暑假,高三開學時再見到向左,他竟然長成了一根旗桿,身高足有一米九,那張拉長的絲瓜臉扭曲得讓人不忍心看。
三
呂麗給我看她發的朋友圈,配的文字是:別人的錫婚,有白金鉆戒,我的呢?
我笑她真是個愛慕虛榮的家伙。
“這點虛的都不敢,還活個什么勁兒,可活到今天什么都變了。”
這女人今天怎么多愁善感起來了。
向左的兒子向右兩歲大的時候,三兒的系統性紅斑狼瘡引發股骨頭病變住了院,向左的母親不愿意照看孫子,向右在醫院里哭鬧個不停,情急之下向左給我打電話求救。我撂了電話,拿了個毛絨玩具塞進包里就往醫院趕。
我到了醫院大吃一驚。三兒很年輕,卻因為長期服用激素,面部嚴重浮腫,眼睛幾乎睜不開了。她躺在病床上,見到我只說了一句“陳旭來了”,就不再開口。我知道她很痛苦。
我蹲下來跟向右打招呼,掏出毛絨玩具。他一下子撲到了我懷里。
那天我深深感受到,這樣的一個男人負擔其實挺沉重的。
那時我的第一段婚姻剛剛結束。我以凈身出戶的形式換得前夫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了字,盡管辦離婚證的幾塊錢也是我出的,但三十一歲的自己終于重獲自由。我對著藍天深吸了一口氣。
我從小恨我的父親。他為了讓母親生兒子不惜毀了她的身體。
當初我和前夫結婚只是想從家里逃出來而已。前夫比我大十四歲,我不顧家人反對嫁給了他。
婚后我有三年沒有回過娘家。
四
“儀式結束了,咱們去趟洗手間,回來就該吃飯了。”呂麗撩了撩頭發,枯黃的臉上展露出一絲笑容。
“看不出來向左挺浪漫的,給媳婦辦錫婚宴,還送白金鉆戒,真讓人羨慕。”我說。
“的確,這樣的老公,全國也找不出來幾個。就是這家伙一見面就夸人家胸大,我總以為他是想揩我油呢。”呂麗挺了挺她的F 杯。
“現在又想被人家揩油了?”
“去,你個女流氓。”
我在洗手間門口等呂麗。洗手臺很干燥,鏡子上看不到水珠。我注視著鏡子里的自己。今天化的淡妝,耳邊垂下來一縷頭發。
我和向左一起考上了本地的大專——言午學院。當年言午市的文化宮影院名字聽起來很官方,卻是南方來的一個私人老板運營的,過了十二點后,影院就會播放一些外國影片來吸引觀眾。向左帶我去看過。我不敢睜眼,只聽聲音,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向左坐在旁邊,不停地開導我,說我早晚要長大的。然后,我就看了一點,再然后周末沒事他就約我去看夜場電影。
事實證明性啟蒙是有必要的,這讓我對男朋友這一物種有了更多的認識。很快,我就和一個長得很帥的男生好上了,向左則如同消失了一般。
“一個人在這兒干啥呢。”
我扭頭一看,是向左。
他一邊洗手,一邊盯著鏡子,他說:“在鏡子里,你也能看見我的臉。”
“鏡子里的有什么用?”我笑著問。
“你還是不戴首飾?都快奔四了,也該戴了。”他沒有搭我的話茬,而是談起了世俗的東西。
有幾滴水從他手里甩出來濺到了鏡子上。
“我不稀罕那些東西。”我回答。
“三兒喜歡那些東西,今兒又送給她一枚白金鉆戒,”他低著頭,像是自言自語,“今天你很不一樣。”
“哪兒不一樣?”我問。
“是太迷人了吧!”呂麗出來了。我往后退了退,騰地兒讓她洗手。“不但迷人,俺們陳旭還有才,從高中起就是個才女,還嫁了個作家。”
“就你話多。”我有些生氣,空氣一時變得有些凝滯。
呂麗低頭擺弄手上的甲片,向左趁機摸了我的脖頸。
“走吧,吃酒去,豬場的左經理。”呂麗說。
“不敢當不敢當,我膽子小,兩位美女先走。”
呂麗當然知道我和向左的一些關系,但她的理解存在偏頗。第一段婚姻破裂以后,我過了三年多的單身生活,向左曾不止一次發出暗示,只要我“需要”,他可以隨叫隨到,但我拒絕了。
有一次我夢見了一個死人,我趴在那人身邊痛哭,死人的床板太低,后來我想挪一下身子,一瞬間來了一個男人,他說著話,但他說的是什么,我卻完全聽不見。他是向左。
前夫的母親找人帶話,讓我和她兒子復婚,她說離婚的女人就是一張破報紙賣不上好價錢,她兒子有房有車隨時可以再找一個,到時候我后悔都來不及了。我沒有理睬她。前夫是個媽寶男。
起床后我渾身酸痛,精神不振,就去了出租屋門口的美容店推背。
“波顏國際”美容店的女老板很會聊天,一頓東拉西扯后,結論只有一個,就是女人得學會花錢。
離過婚的女人應該讓自己更美,這是她的原話。我接受了她虛偽里掩蓋著的真誠。我讓她把我的雜眉修掉,她說我這野生眉太粗獷,一點兒不精致,這次她要免費帶給我美。我一咬牙一狠心在她那里充了一萬塊錢的卡。
五
向左大學宿舍的舍友只有老七來了,他是最不愛說話的一個。我離異后,有人給我介紹對象,沒想到見面時居然是老七,我們不由得感慨言午市真是小啊。
大家聊的大都是和向左有關的事,他的牌技,他如日中天的養豬生意。
“向左你快過來,我非要問問你高二那一年暑假,你到底吃了什么好東西,怎么突然就長那么高了?你今天必須給大家解釋一下。”呂麗發問。
“肯定是吃了‘壯壯精’(一種速成豬飼料的名稱)。”有個滿面紅光的中年男人接話。
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的。
做怪夢后的一天下午我和向左見了一面。他把我拉到他廂式貨車的駕駛室,問我:“快說說,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哪有,是人家非要娶我。”
他搖下車窗玻璃,掏出一支香煙塞到嘴里,手里握著火機,卻沒有點燃。
“可以啊,陳旭。”他語氣里有些不屑。
“志趣相投,不分年齡,再說我只比他大六歲,我愛讀書,他喜歡寫小說!說真的,我本來以為我這一生再也不會結婚了。”
“快給我講講。”
“我倒是希望收到像沈從文寫給三三那樣的情書,但他至今沒給我寫過呢,也許以后會寫的,不急。”聽到三三,他愣了一下。我說:“那個三三可不是你的寶貝三兒。”
他沒有聽懂,但把兩條腿朝我靠了靠,想拉我的手,我用力甩開了他,然后我指了指自己凸出來的肚子。
“你又懷孕了?”他吃驚地問。
“是啊,四個月了,胎兒很穩定了,前幾天在醫院做了四維彩超,是個可愛的小男孩。”
他又想摸一下我的頭,我下意識地躲開了。我從車上下來了,我的身子尚不到笨重的時候。
我們簡單地聊了以前、現在和將來,情緒都有些傷感,交流變得索然無味了。我和他仿佛一直都沒有長大。我該走了。
我對向左說:“今天見到你,很想告訴你,要好好照顧你媳婦,不可以再對不起她。”
“就告訴我這個?”他反問。
“是啊,你以為是來聞豬肉味的?”
“我這輩子都不會和三兒離婚的,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六
“不好意思啊大家,如有招待不周,請多多包涵。來,三兒,給哥哥姐姐們倒酒。”向左領著媳婦過來了,三兒剛剛哭紅了眼,妝都花了。
“你們能來是我們的榮幸,我不敢喝酒,以茶代酒敬大家了。再次感謝大家照顧俺家向左的生意。”
向左的一只胳膊始終貼在她的后背上,顯得十分親昵。
老七掏出一個大紅包塞到三兒手里。他說這是宿舍七位兄弟們的心意。向左在三兒耳朵邊小聲嘀咕了幾句,三兒收下紅包,走過去和老七抱了抱,老七的臉頓時臊得跟紅蓋頭一樣。老七三十八了,離我們上次“相親”過去三年多了,仍舊沒有找到對象。
輪到我和呂麗時,向左接電話去了,三兒過來敬酒,我表示酒量不行,呂麗也說不會喝,我們倆本想和三兒以茶代酒,不料坐在呂麗旁邊的啤酒肚男起身慷慨相助,他舔舔嘴唇替我們喝了,說好東西不能浪費,喝完還不忘加了呂麗的微信。
幾個大男人拿起話筒:“我對你愛愛愛不完,昨日像那東流水……”一聽就是暴露年紀的老歌。一直熱鬧到下午四點多,宴會才陸續散場。
我問呂麗能不能多玩一會兒,我和她雖然都住在言午市,可一個住大南邊,一個住大北邊,見一面其實挺不容易的。
“我們去劃船吧?”我提議。
“就咱倆?”呂麗問。
“你還想要誰去?那個啤酒肚男?”
“NO,他不行,噸位太大,不安全。可以喊上你的大作家,讓我深度了解一下。”呂麗一臉狡黠。也許是她聞酒氣多有點上頭了。
“他在家看書,不愛湊這些熱鬧,我喊不出來的。”我說。
“是喜歡和你單獨相處吧!不見了,不見了,真是的,你跟我還藏著掖著。你可真不夠意思了。”
“怕你有非分之想唄。再說一見你,萬一他忍不住誘惑呢?”我笑嘻嘻地回答。
我拉著她向碼頭走去。她一看見船,像個小姑娘似的,歡呼雀躍起來。
坐船的人還挺多。我們排了一會兒隊,才等上了一條綠色的四人座腳蹬船。
雙洎河的一截河水被一座水泥大壩攔起來,匯聚成了一個豬耳朵形狀的水庫。有本地人依托水庫修了個景區,發展起了旅游業。景區里建設了水上高爾夫、跑馬場、游泳池、游船、釣場等設施,又引進了民俗園、紅色教育展館、兒童樂園、網紅秋千、鄉村食堂等特色項目,吸引了周邊很多人前來游玩。
我們脫了鞋把腳伸進河水里。小船隨著水流任意東西。
“我想我還是告訴你吧。”呂麗一臉鄭重,令人不太適應。我沉默不語,等她說下去。
“我決定去做手術了。”
“手術?什么手術?”我好奇地問。
“左胸全切,乳腺癌中晚期。我本來下不了決心,我怕就算切了也活不了多久。可現在不切的話,怕癌細胞擴散,我會很快死掉。我舍不得女兒,她那么可愛。活著多美好呀,陳旭。”
呂麗看著水面上的夕陽,面容生動。
我在她的臉頰上親了一口,小船短暫失去平衡產生一陣晃動。
“切,明天就切。你那大圓球,太氣人了。等一下,我能再摸摸吧,以后就摸不到了。”
“都什么時候了,還想著占便宜。”
“割一個,我就不嫉妒你了,呂麗,我想要你活。”
我們一定是笑得太大聲了,驚動得水面起了風,浪頭多了起來。
呂麗高中落榜后,身為包工頭的父親花大價錢讓她上了四年的外語學院學習商務英語,她畢業后去了上海,在一家外貿公司上班,認識了馬來西亞商人拉吉。拉吉十四歲就出來闖蕩世界,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英文和泰文,呂麗經不住他的愛情攻勢,很快就和他同居了。他們辦理了旅游簽證,四五年間,她跟著拉吉輾轉去過澳大利亞、泰國和美國。他們在塔斯馬尼亞州摘過蘋果,在曼谷當過導游,在紐約的一家孔子學院代過漢語課,后來他們又在吉隆坡生活了三年多。兩人一度走到談婚論嫁的地步。拉吉曾在一個夏天跟著呂麗回農村老家商量婚事,拉吉害怕蹲坑里蠕動的白蟲子,呂麗的父親特意在自家的樓上為拉吉修了個廁所,嶄新的抽水馬桶專門供他使用。兩人最終沒有結婚。
分手后,呂麗從馬來西亞回來了。已經三十一歲的呂麗成了村子里的大齡剩女,她不得不面對迫在眉睫的婚姻問題。家里人比她還要著急,由于十里八鄉都知道她過去的事情,沒有一個媒人愿意上門提親。一年后,她倉促地嫁給了初中同學宋倫,當時她的父母沒有要一分錢的彩禮。
宋倫曾經追求過呂麗,那時候的呂麗家庭條件好,穿著又時尚,吸引了一眾男生的目光,甚至有不少校外的青年等在學校門口看她,那會兒她根本看不上宋倫,沒想到宋倫竟然在她寢室樓下用削筆刀割腕了。
盡管口子不深,只流了一點兒血,卻在學校里產生了不少議論,宋倫后來患了抑郁癥。他初中沒上完就去讀了技校,畢業后在外地的一家水力發電站維修發電機。
同學聚會上,呂麗見到了仍舊單身的宋倫,兩人閃婚。
婚后,呂麗跟著宋倫在發電站的職工宿舍里住過一段時間,她懷孕后回到了家里。隨著女兒的出生,她沒有再出去工作,成了全職家庭主婦。宋倫在外上班,一兩個月才回來一次,兩人聚少離多,他經常連句話都不和呂麗說。
五六年下來,呂麗過得并不快樂。
她不止一次對我說,她偷偷想念過拉吉。我自然明白,女人類似“喪偶式婚姻”的日子當然是不好受的。所以,我才勸她多帶著女兒出來走走,只當是散散心,但她已經習慣宅在家里了。這次她能來向左的錫婚宴倒是個意外。
我們剛上岸,就看見向左朝我們走來。呂麗說她得趕緊走了,回去通知家人今天晚上就去省城住院。她走得太急,差點兒撞到河邊的一棵柳樹上。
“她怎么了?”向左問我。
我不說話,一個勁兒地流眼淚。
呂麗的背影很快消失了,我怕她再也不會出現了。
西邊的太陽正在一點點墜落,陣陣的晚風裹著濃稠的魚腥味。
“呂麗得了乳腺癌,必須盡早切掉一個,只有切了才有可能活。”我的大腦不自覺地在回放著……
那不是夢境,而是真實存在著的。
“要相信奇跡,乳腺癌中晚期存活率挺高的,切了就好了。”向左惋惜地說。
“呂麗,求你不要離開我。”我哽咽著,試圖把聲音吞沒在自己的喉嚨里。向左不知何時淺淺地抱住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