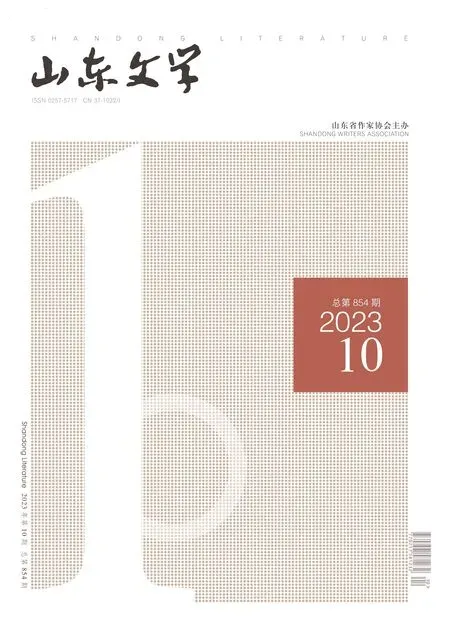訴說曠古的酩酊與澄明
——《芝鎮說》的醉話、鳥語和鬼話
趙月斌
現代小說家擁有訴說一切的權利。他可以化身為葛里高里寫出《變形記》,可以假手迫害狂寫出《狂人日記》,可以顛覆“齊東野語”寫出《九月寓言》,可以召集亡魂寫出《生死疲勞》《第七天》,也可以模仿偵探小說寫出《玫瑰的名字》,可以用學術評注的方式寫出《微暗的火》,甚至以無人稱敘述寫出《悠悠歲月》,以反小說的姿態寫出《橡皮》《形同陌路的時刻》……總之,一個無畏的小說家可以窮盡一切手段,寫出任何不像小說的小說。就此而言,逄春階的《芝鎮說》似乎沖出了傳統小說的窠臼,寫成了一部小說之外的小說。
《芝鎮說》本身就是“現代”的產物,它以連載的方式在傳統報紙和網絡平臺同步推出,讀者的即時互動或多或少會影響作品的敘事進程,使之成為一種時刻與受眾連線的“云創作”。無數隱形的圍觀者,不僅隨時反饋點贊,還會提出意見要求,他們的看法、建議乃至媒體的審查機制,都會借助作者之手,化為《芝鎮說》的一部分。所以這部作品的真實作者,除了直接現身的作家逄春階,應該還包括隱匿在“云”后的悠悠眾口,包括最終掌控此“云”何去何從的“上帝之手”。正是這種開放的“云同步”的寫作方式,把《芝鎮說》變成了一部眾聲喧嘩的多聲部小說:它面朝故鄉,立足于芝鎮,廣納家國傳奇、時議流言,雜取種種“說”合為一說,總成欲說還休的自圓其說。故而,《芝鎮說》的開放式寫作使其具備了一種“著‘說’立書”的文體形式,它當然是逄春階寫出來的作品,但從文本上看,更像一部“說”出來的話本。在這里,小說家化身為說書人,他訴說一切,亦將一切訴諸于“說”。正因此,這部小說的結構盡管近乎散漫,但是說書人的三寸不爛之舌總能將其說得端緒分明頭頭是道,既說得開,又收得回,一切盡在事關“芝鎮”的言說中。
芝鎮——脫胎于作者的家鄉景芝鎮——盛產美酒,鄉人皆好酒擅飲,故常因喝酒留佳話,亦因喝酒鬧笑話。所謂“芝鎮狗四兩酒”“芝鎮豬,排山倒海酒呼嚕”,芝鎮的萬物生靈似乎無不帶有酒意。沒有酒,恐怕也就沒有了芝鎮;沒有酒香,也就沒有了芝鎮人一身的膽氣和神魂。本書作者和小說的敘述者公冶德鴻也不例外,他們自幼喝著芝酒長大,當數酒的傳人。出乎酒徒之口《芝鎮說》,自是三句話不離其酒,講出的盡是酒故事,說出的盡是酒話。所以你會看到,在芝鎮不光婚喪嫁娶節慶祭祀等重要場面要喝酒,而且產婦難產會以酒催生,大夫開藥方會以酒糟作引,寫毛筆字也以酒研墨蘸酒揮毫,老人臨終時也要喝一盅酒,甚至會在提前打好的墳壙里埋一壇酒,死不瞑目的人嘴里滴上幾滴酒才安然離世……酒,簡直就是芝鎮的提神至物、續命瓊漿,要是沒有一口酒“頂著”,沒有那“喝酒望醉”的蓄意,即便巧舌如簧的說書人,恐怕也說不出這酣暢淋漓的荒腔走板,我們也看不到這如醉如癡的酒后“真言”。
于是,《芝鎮說》即如濟南道人袖中的酒壺,雖只一壺,卻是飲之不盡的“家傳良醞”——身為“喉舌”的逄春階顯然自帶酒意,將一部小說寫成了“大話”,把上百年的家事國事釀成了絮叨不盡的萬千啁哳。《芝鎮說》借酒說話,借酒話敷衍不可說不忍說不易說之話,所以這部書并非飲酒作樂借酒消愁,而是借酒療病借酒去病——診療一個家庭乃至整個民族的“沒有疤的內傷”。故而,與酒相對的另一重要線索便是藥:作為中醫世家的公冶家族,源溯孔子的女婿公冶長為祖先。這位通鳥語的奇人曾因烏鴉的報復而身陷縲紲,其子孫亦近乎生而有罪,尤其是“庶出”的公冶祥仁一系,雖是世代行醫,亦難免背負深重的“內傷”。另外,哪怕像陳珂、王辮、弋恕、牛二秀才那樣的烈士英雄,雷以鬯、芝里老人那樣的地方名士,也都受過不同程度的“內傷”。至于族長“六爺爺”、暗娼“黑母雞”、匪類張平青、神婆藐姑爺這類各有一套處世哲學而自行其是的人,更有可能病在骨髓,疾在心靈。作者將“內傷”作為小說副題,其用意不言自明:“內傷”簡直就是一種代代相傳的無癥之病,人們或者渾然不察,或者消極回避,或者以酒“擔事”——靠著一種虛浮的快意活出點兒人樣。因此《芝鎮說》又多講醫道,多見藥方,多寫藥與酒的相生相克,多寫醫者于飲者奇妙關聯。比如“我大爺”公冶令樞,就是一個藥酒不分家無酒不歡的人。他聲稱“酒是百藥之首”,聽來像是反科學的詭辯,卻是見于《漢書·食貨志》的一句老話。《說文解字》也認為,“醫(醫)”“得酒而使”“酒所以治病也”,所以從“酉”(酒)。可見“醫酒同源”甚至“醫源于酒”的說法并非無稽之談,《芝鎮說》一再寫到藥酒不分的情節更是佐證了藥與酒的親密關系。像公冶令樞,沒有酒腦子就不好使,喝了酒之后才會“思路清晰,兩眼放光,眉飛色舞”。有一次受傷住院,竟在嘴里大嚼酒精棉以解饞,后來偷偷喝上高度芝酒,方才過了酒癮。如此嗜酒之人,年近百歲“依然酒盅不離手,越喝眼越亮”,似乎又反證了酒勝于藥——那無藥可治的“內傷”實為心病、癔病,這根深蒂固的隱疾大概只能靠酒來療救了。
針對這一似有還無似病非病之病,《芝鎮說》有如經年累積的醫案卷宗,記錄了芝鎮人的集體癥候,更記錄了公冶家族及其鄉里鄉親的個人行狀,試圖“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故而作為記者的公冶德鴻充當了主訴一切的代言人,由他穿針引線、內引外聯,和盤托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和不知道的一切。何以道出“不知道的一切”?不只因為這位記者可以“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更因為作者讓他具備了“聽懂一切”的特異功能:既聽得上達天聽的高頭講章,也聽得不上臺面的土話、瞎話,甚至鳥語、鬼話。所以這部書的主訴人表面上是記者公冶德鴻,實際還有醉話連篇的公冶令樞,公冶家族的不死鳥弗尼思,以及“我親老嫲嫲”(曾祖母)、“我爺爺”的亡靈。他們發出的聲音不見容于世,非但難得聽聞,而且殊為禁忌,誰會拿醉話當真?又有誰能聽取鳥語、鬼話呢?但是“訴說一切”的小說家盡可以“聽見一切”,讓那些從無機會面世的寂靜之聲化作了傾動人心的神啟之聲。
借助“我大爺”公冶令樞的醉話,公冶家族的“往事”“糗事”乃至國仇家恨得以全面呈現,作為“庶出”的長孫,他深受“內傷”的戕害,故帶有強烈的個人恩怨,至于“家丑”實情如何,權且姑妄聽之。整部小說的重心則是“我親老嫲嫲”“我爺爺”,作者并未充當全知全能的上帝去主宰他們的故事,而是讓他們的亡靈直接出場,主動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由當事人主訴其本事,自然最為直觀地增強了小說的感染力。由是,丫鬟、小妾出身的“我親老嫲嫲”重回人間,與從未謀面的重孫子隔代對話,講述了她作為舊時代低人一等的“媽”(正室為娘,庶室為媽)一生的遭際:先是被賭鬼父親賣身為奴,后被“我老爺爺”納為小妾。在家她是不受待見的“賤骨頭”,在外是手上“不干凈”的“穩婆(接生婆)”。即使她照顧哺育了公冶家上下三代人,還是常遭歧視甚至欺侮,直到六十多歲還被正出的兒子(六爺爺)“待打就打,待罵就罵”,死后進祖墳、入族譜仍然備受損抑。雖其苦了一輩子,她卻“不感覺苦”,被人叫作“笑佛”,成了芝鎮十里八鄉有口皆碑的“媽”。因此,當她化為魂靈追今撫昔,仍舊坦然無怨,并未像后輩子孫那樣背負沉重的“內傷”而耿耿于懷。這個景姓女子原本沒有名字,因為她的夢兆讓“我老爺爺”公冶繁翥挖到了一朵《抱樸子》記載的仙藥靈芝,故得名景苬(xiú)。苬與芝異名互訓,景苬即“景芝”之謂,所以“我親老嫲嫲”亦可視作芝鎮的化身。公冶繁翥將靈芝供奉于祠堂,責打不敬靈芝的兒子,又似乎將景苬視同靈芝一樣的祥瑞,并給予虛空的慰藉。景苬或許也因此得到了一種精神上的補償。
另一個“飄然而至”的亡靈是“我爺爺”公冶祥仁。他推崇“聽天命,盡人事”的處世之道,懸壺濟世,誓為良醫,“不游離于社會,也不游離于老百姓”。英雄烈士死難,他敢雪夜酹祭;土匪孬種得病,他也出診開藥方。終其一生,是明大義、知進退的一方賢達。但是這位公冶繁翥的長子,景苬的親生兒子,只因庶出的身份,至死“內傷”未愈。盡管生母生他愛他,不惜斷指教子,可在這位“大少爺”眼里卻“只是個媽”“永遠是下人”,即使后來他也知禮行孝,很少惹親娘生氣,但是他們的母子關系始終隔著一道坎兒,至死不曾跨過。所以當其彌留之際仍未釋懷,只是重復著母親的姓氏撒手而去。可見所謂“內傷”在他遠離人世后仍不得化解,只能借孫子之口表達枉為人子的反思和愧疚。春秋時期的宋莊公曾發狠,不到黃泉不見其母,終究還是忍不住相見于大隧之中,母子和好如初。可是兩千七百年后,公冶長的子孫哪怕下赴黃泉,還是不能摒除人間的流毒,成為“其樂也融融”的鬼魂。
母親生為“笑佛”,死而無憾。兒子生前“也不一定”,死后仍然糾結無緒。他們在陽間的“鬼名字”(外號)竟也宿命般適用于陰間。從小說行文來看,這對母子不只在世有隔,不只陰陽兩隔,到了地下仍然不在一個維度,否則何必要找公冶德鴻在中間傳話呢?回頭再看“也不一定”公冶祥仁生前的自救之策:生母下葬之后,留下一包從娘家帶回的“老娘土”,他以酒沖土,像吃中藥一樣,把“老娘土”喝得干干凈凈。孫子出生過滿月那天,他騎驢六十里,趕到公冶長的墓地祭拜祖先:“把額頭貼近那堆黃土,會產生一處特別的安全感,一種與天地神靈達成默契的欣慰從土里涌向心里,再升騰起來滲透全身。”這種敬土情結或也源于一種原始的土地/女性崇拜。《釋名》曰:“地,底也,言其底下載萬物也。土,吐也,土生萬物。”從女媧到后土娘娘,作為傳統農業社會的神圣象征,我們的“土地母親”和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地母神一樣,“生出萬物,撫育人類,并再次地接納它們回到子宮之中。”([古希臘]埃斯庫羅斯:《祭酒人》)公冶祥仁吃“老娘土”,大概可以身心慰藉;拜“海大海高”的祖墳,或也可以安撫靈魂。他似乎本能地找到了父母兩系共同的根源,把那堆黃土當成了母親的懷抱,把天地神靈(地母)當成了最后的救贖。只可惜,食土、拜墳并未令其安然終老,甚至未讓他入土為安,反而讓他懸置在無盡的羞愧中。
最后來說公冶祠堂供奉的神鳥弗尼思。它就像無所不知的萬事通,公冶一族的家史逸事,世間的名物掌故,一概張口就來;還像深諳世道人情的老祖宗,不時臧否人物,醍醐灌頂。此鳥非凡鳥,是小說中的智者、精靈,它所講出的“鳥語”,便是多少凡人也難抵及的。誰能像它一般心口如一了無掛礙呢?比之芝鎮的蕓蕓眾生,大概它才是唯獨沒有“內傷”的一個。芝鎮地處東夷,其先民向以鳥為圖騰,認為自己的始祖是鳥卵所生。公冶家人懂鳥語,供奉不死鳥,或即鳥族后裔。那么弗尼思是什么鳥?單看字面,曾揣度它暗諧“匪夷所思”“非你所思”之意,因那鳥語確實不可思議,超乎想象,它能思你所思,亦可思你所未思,簡直就是會通世俗與神圣的屬靈之物。后經作者明示,弗尼思便是鳳凰,更證實了它是東夷的瑞鳥。
傳說東夷部落的伏羲氏、女媧氏皆以風為姓,風通鳳,風姓即鳳姓,所以東夷尊崇鳳鳥,以鳳為圖騰。小說里寫到再造《尚書》的伏生及其女兒羲娥,即伏羲氏后裔。另據《左傳》記載,少昊之時曾有鳳鳥至,遂以鳥名官,有鳳鳥氏、玄鳥氏等諸多官職名號,少昊名鷙,堪稱“百鳥之王”。弗尼思即鳳鳥無疑,其名字卻是地地道道的外來語,最早見于明代“西來孔子”艾儒略(1582—1649)編譯的《職方外紀》:“傳聞有鳥,名弗尼思,其壽四五百歲,自覺將終,則聚干香木一堆,立其上。待天甚熱,揺尾燃火自焚矣。骨肉遺灰,變成一蟲,蟲又變為鳥。故天下止有一鳥而已。”可見,弗尼思就是燒不死的火鳳凰。方以智(1611—1671)的《物理小識》又稱弗尼思為“度爾格國鳥”,度爾格即土耳其。根據詞源,弗尼思(phoenix)來自古拉丁語。這樣說來,弗尼思竟是一只不死的洋鳥。不過,鳳凰涅槃的說法并非純屬泊來品,元代詩人楊維楨就寫過鳳凰浴火歷五千劫而重生的詩。小說中的弗尼思本是紫檀木雕成,確也經歷過一場大火,要不是公冶德鴻的祖母從火堆里搶出來的,恐怕早已燒成了灰。如此說來,弗尼思便是名副其實的不死鳥。可這古老鳳鳥為的洋名何來?大概正是西風東漸帶來的一線靈光。我們看到芝鎮有祠堂,有廟堂,還有教堂,一百多年前就有不少洋牧師和時髦的外國女子,公冶祥仁便曾跪求圣母瑪麗亞保佑自己賭場贏大錢,弗尼思之名大概就來自民間不自覺的文化交匯。所以,供奉在公冶祠堂的弗尼思又不盡是被本地香火熏暈的土鳥,還是一只中西合璧的不死之鳥,那么,它的“匪夷所思”確乎其來有自,它的“鳥語”當然可以超乎小說之上,甚至超乎一切之上,成為比一切醉話、鬼話都要浩茫無邊的神話。
“禮失而求諸野”——《芝鎮說》引孔子的話作為題記,或正暗示了一種信而好古的返祖沖動。“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說文解字》)——“禮”本來就是敬奉神明的產物,小說以此開篇,即便僅指某種世俗的行為規范,也表明“禮”早已成為壓倒一切的集體無意識:哪怕我們都是滿腦子科學理性的現代人,仍不可避免地重復著永恒回歸的神話。我們看到,雖然作者也在家族史、芝鎮故事之上架構了格局宏大的英雄敘事,但他顯然無意將其寫成某種氣象森然的民族寓言,而是著意寫出了那宏大格局中的“物相雜”、那森然氣象中的“也不一定”,寫出了世俗與神圣合而為一、經驗和超驗互滲的世界。所以他才會把芝鎮變得醉意朦朧,如有神在。于是六界通融,人神互見,萬類更生,失語者開口說話,亡靈不請自來:天子夫子、烈士先驅、報人記者、儒醫賢達、僧尼教士、神婆卦師、梟雄奸佞、老爺太太、仆從婢妾、拳師娼優、醉漢賭徒、浪人覓漢、漢奸土匪、兵痞無賴王八蛋,以及不死之鳥、玉皇遺蝗、仙家月精、毛驢黑馬、藥酒靈芝、皂角牡丹、馉馇家寧、九龍桃木劍……這一切召喚著失去的一切,小說家則以他的“齊東野語”訴說一切。
《芝鎮說》說什么?小說結尾“我爺爺”公冶祥仁的亡靈有句引述《易經》的話:“天地之大德曰生。”大概可以為全書收總。自從公冶長非罪成囚,那條傳衍至今的“縲紲”早已深深勒進了后世子孫的骨肉,以至于在地上畫個圈兒就能讓你不敢妄動。那些無影無形而又如影隨形的“規矩”“禮數”似乎就潛伏在每個人的血液中,成為無法療救的“內傷”。李澤厚說過,“禮”的神圣性決定了它既是人間的規范,又是上天的律條。這人間的禮儀也是神明的旨意,于是人和神同在一個世界的“禮教”就成了中國特有的“宗教”。可是這個“宗教”只有無法超越的現世,沒有明確的另一個世界,人們只能在“禮制”的鵝籠里自求多福。(參見李澤厚:《由巫到禮》)千百年來,“禮教”非但沒有齊人以禮,反倒成了吃人的東西。然而所謂“吃人”的禮教,吃人的未必就是事神致福之“禮”,而是上施下效之“教”,是造成內傷、吞噬靈魂的種種“縲紲”和教條。“我親老嫲嫲”——景氏“媽”之所以生不能當“娘”,死不能入祖塋,不就是因為那“幾百上千年的規矩”嗎?雖生如靈芝,卻身為下賤,一個“撈”回了無數生命的接生婆,自己擁有的卻是被輕慢和被踐踏的一生。孔子說“禮失而求諸野”——彼時的鄉野之“禮”,恐怕更接近它的本義,尚且具有超道德的神圣性,而非只是親親尊尊的繁文縟節。“天地之大德”只會活人,怎么會吃人呢?所以小說里不乏有人“活出了各自的樣子”。他們之所以沒被“內傷”反噬,原因就是“有口芝鎮酒頂著”,在這里“酒”才是活命的法寶。酒本始于祭祀,可以接引神明。地處東夷的芝鎮,未必講究“酒以成禮”,卻可以靠酒超越世俗世界。所謂“醉者神全”,大概也算一種重獲自由的超越狀態。
維特根斯坦說,對于不可言說之物,我們應該保持沉默。《芝鎮說》卻借滿紙酒話說出了“子不語”的眾多怪力亂神。孔夫子要“敬鬼神而遠之”,又要“敬神如神在”,關鍵問題不是神在不在,而是有沒有敬畏之心。假如我們能夠重返芝鎮,或許也能飲酒以樂,訴說曠古的酩酊與澄明:同人于野,利涉大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