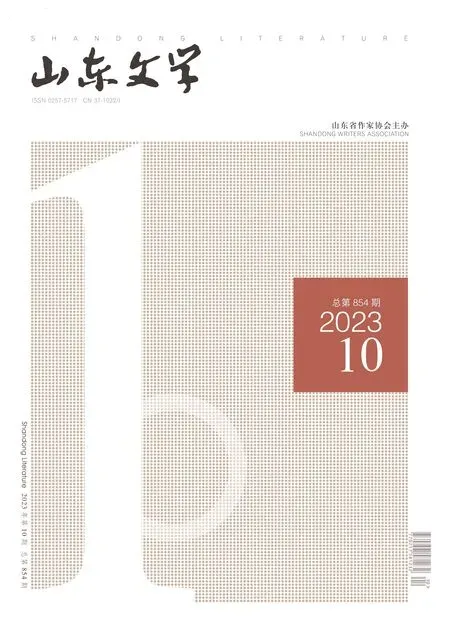七彩水晶
徐 源
在我九歲時,我們家生活在大山里,家里馴養著野鹿、錦雞、松鼠,我與父親到菜園鋤草,它們就會趴在柵欄上圍觀,喇叭花一朵一朵順著荊竹條爬行,爬到它們身上,就盛開了。那時,我的小動物們,都是父親從森林里撿回的,父親不是獵人,但他經常到黑漆漆的森林里去,回來時身上總濕漉漉的,還散發著一股木葉般腐蝕的清晰味兒,我知道,這就是森林的味道。我的小動物們說,這片無盡的森林,是蘑菇仙子的,每當月光皎潔之時,森林里的動物們、植物們,就會換上銀色的衣裳,參加蘑菇仙子舉辦的音樂舞會。
父親會不會是去參加音樂舞會?
父親身體不好,經常咳嗽,三十八歲的他,面容枯瘦,人們預測,他活不了多久。我們家曾賣掉一頭母牛,把他送出山外就醫,他從山外回來后,咳得更加厲害,有幾次還咳出了血。我的母親是一位裁縫,她在另一塊土里,種了許多麻,根據不同的季節,為我們織麻縫衣,有時,她也把山里的花草和云朵采來,在衣裳上染成精致的圖案,被時間磨得破損的田園,在母親純熟的手藝下,也會用炊煙把它縫補得貼貼實實。
有一天,父親與母親商量,決定帶我到森林里走走。這是我多年的愿望,一想到要見到蘑菇仙子了,我的心就激動得怦怦跳。
那天,父親刮掉了他蓄留已久的胡茬兒,在梳子上沾了些清水,把頭發梳得整潔、光亮,他穿著一件青色的中山裝、一雙反光皮鞋,從母親手里接過沉甸甸的行李,與母親對視三秒后,牽著我的手,對母親說:
“我走了。”
母親咬著嘴皮,眼里閃著淚花。我不知道,那天母親為什么悲傷,父親要領著他的兒子到森林里參觀,這是一件多榮耀的事,我不知道,那天母親為什么會穿一件白色的衣服,白得像午后的云一樣,刺著我的眼睛。可現在是黎明,薄霧籠罩著我們,我們撥開它,走了十幾米,母親在后面喚我的名字,我回過頭,看見她微笑著向我揮了揮手,薄霧像蠶絲一樣把她束住,她像一只白色的蝴蝶,欲掙扎著飛舞起來,她努力了那么幾次,始終站在原地,我看見,她伸手抹了抹眼淚,可她還是微笑著向我揮了揮手。父親呢?父親沒有回頭,他牽著我的手,義無反顧地向前走。
我和父親踩著曙光走了一里路,太陽才從森林里升起來,我們的褲腿已被露水打濕,沿路上生長著比人還高的苞谷稈,修長、寬大的葉片伸到路上,割著我們的臉。這一片莊稼地是爺爺交給父親的,父親已耕種了二十年,這些苞谷是父親親手種下的,它們生長得茂盛,到了秋天,準會有一個好收成。但是,現在,父親卻沒心情關心它們,他正牽著他的兒子,一心往森林里走,金色的陽光灑在大地上,他也無心拾起一縷,他正牽著他的兒子,去會見蘑菇仙子。他兒子的心,正激動得怦怦跳,這是一個多美好的清晨啊!
我和父親來到森林邊緣,黑乎乎的森林透出一股陰冷的風,它像一頭心無旁騖的野獸,在陽光的撫摸下溫和地喘著氣。父親上前向它問好,它動了一下身子,風從遠處滑來,吹動了我們的衣衫,它豎起耷拉著的耳朵,就這樣,我和父親鉆進它的耳朵里,沿著它陡峭的耳壁,我走進向往已久的黑森林。
我們踩著一條鋪滿落葉的小徑往前走,叢林深處突然跳出一只貍子,皮毛黑白相間,眼睛圓得像兩顆珠子,它擋在我們面前,我以為它會攻擊我們,它站立起來,向我們敬了一個禮,父親給它招了招手,它興奮地跑到父親跟前,不斷用前爪子撓著脖子,父親蹲下身子,從行李里取出一些食物,它捧著我們的食物,一溜煙就消失了。
這條小徑很長很長,也不知走了多久,我走累了,父親就把我扛在肩上。我騎著父親的脖子,像騎著一匹青色的馬駒在森林里暢行,陽光透進森林,小徑兩旁的草木伸展著身子,抖落一些鳥語,我聞到一股草莓的香味,持久而誘人,父親說:“這就是鳥語的味道。在這片森林之外,是沒有人能聞到它的。”父親讓我用心去感受,我微閉上眼睛,任草莓的香味浸濕我的臉龐,這草莓的香味,有偏向于巧克力味的、有偏向于牛奶味的,有偏向于檸檬味的、還有偏向于櫻桃味的,想不到,森林里的鳥語是如此的誘人。
我們正說著話,一只藍色的鳥飛停在我的手臂上,它向我點了點頭,開始梳理自己的羽毛,它的羽毛藍得發亮,好像無數藍色的天空疊加在一起,才能調出這種充滿魔力的藍。我屏住呼吸,生怕打擾它,父親察覺到了我的心思,從口中吹出一聲明亮的口哨,藍色的鳥并沒有飛走,相反,它跟著父親的口哨,唱起了歌。
不知不覺,我們走到一座小木屋前,父親把我從肩上放下,他熟悉地推開了門,我以為里面會有一些讓我驚奇的東西,比如會住著一位老婆婆或者小鹿,也比如會堆滿閃閃發光的果實,但除了幾張凳子,什么也沒有,我與父親坐下來休息,我問父親:
“爸爸!我們什么時候才能見到蘑菇仙子?”
父親說:“快了。”
這時,我發現,自從我們進入森林后,父親沒有咳嗽過一聲,他的臉色也有了紅光,整個人看上去無比精神。我們在小木屋里簡單吃過一些干糧后,父親對我說:
“路還很長,我們需要在小木屋睡一個午覺再啟程。”
我急于會見蘑菇仙子,對父親的安排表示不滿,我噘起嘴,坐在一旁默默生氣。父親走進叢林,沒幾分鐘,摘來了一張寬大的樹葉,這樹葉足有一米多寬,上面鋪滿絨絨的毛,摸上去很柔和,父親把它蓋在我身上,撫摸著我的頭,說:
“睡吧!睡吧!我會守護在你身邊的。”
下午,我們在森林里遇見了母親,她依舊穿著那件白色的衣服,手腕上挎著一個籃子。她扇動著翅膀,飛舞到我身邊,她真的變成了一只蝴蝶,優雅美麗。我非常驚訝,母親為什么會在這兒,我問母親:
“媽媽!你不是在家里嗎?為什么會在這兒啊?”
母親笑了笑,說:“傻孩子!我來森林里采點野果,給你們準備晚餐啊。”
母親給父親理了理散亂的衣領,與父親對視了三秒后,對他說:“放心去吧!去吧!”
父親緊握著母親的手,久久不愿松開,母親解開他干枯的手指,突然變得憂傷起來:
“去吧!別讓孩子失望。”
母親籃子里的野果,正在發光,它那件白色的衣服,在黑森林里顯得耀眼。三十八歲的父親再次牽著我,告別母親,向著森林更深處走去。我們走了十多米,我回過頭看母親,發現她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衰老。父親呢?父親依然沒有回頭,他牽著我的手,義無反顧地向前走。
我們經過一個湖泊,湖泊周邊開滿鮮花,湖水綠綠的,散發著乳香。我想在這兒玩一會兒,父親便停了下來,他坐在一塊巖石上,看著我跑進了花叢中。這些花,與我在森林外見到的不一樣,沒有根,沒有葉,懸在空中,花瓣呈不同的幾何圖形,有三角形、長方形、扇形、圓形,五光十色,花瓣碩大,花瓣中心不是花蕊,而是糖果。
我捧著一朵花的臉龐,問它:“您好!您叫什么名字呀?”
它搖晃著腦袋,從花瓣間發出了細微的聲音。我興奮地向父親招了招手,此時,我看見,父親已脫光衣服,一頭扎進湖里,他像一條魚,在湖里自如地游著,我也脫掉衣服,跳進湖里,跟在父親的后面游了起來。我們游累了,就坐回湖邊休息,我看見,父親的身子瘦得皮包骨,沒有一點肌肉,我伸手去撫摸他的背脊,冰涼涼的,沒有一點溫度。我的鼻子酸酸的,忍不住抽泣起來,父親一把把我摟在懷里,陽光從樹枝間透下來,照射在我們赤裸的身上。
黃昏,我們終于在一個寬大的樹洞里見到了蘑菇仙子,她穿著一件彩色花斑的裙子、一雙水晶鞋,頭上戴著一頂花冠,說話帶著回音。蘑菇仙子招呼我們坐下,幾朵小蘑菇隨即給我們端來牛奶和點心。蘑菇仙子說:
“吃吧,吃吧!你們父子倆是森林尊貴的客人,只有你們才能走進它,也只有你們才能見到我。”
蘑菇仙子輕輕揮了一下手,灰暗的樹洞立刻變得富麗堂皇,此刻,月光也從窗外透了進來,蘑菇仙子領著我們走出樹洞,先讓我們參觀森林里的月光,然后再回洞里參加音樂舞會。
森林里四處閃著銀光,仿佛黎明的雪景。月光在空中飛旋,一片一片,輕盈、柔和,月光堆積在樹枝上,又從樹枝上悄無聲息滑下,月光包裹著我和父親,我看見父親笑了,笑得那么幸福。森林里的石頭像一顆顆星辰,不斷眨著眼睛,鳥兒們唱出的歌聲,也是銀色的,野獸們的腳步聲,也是銀色的。動物、植物,從四面八方起來,蘑菇仙子舉辦的每一場音樂舞會,它們都不會缺席。
音樂舞會上,蘑菇仙子作了簡短的致辭,并向所有動物、植物們介紹了我和父親,它們紛紛給我們分享了自己的禮物,我和父親被一群小蘑菇拉著到了舞池中央,大家圍著我們唱起了歌,跳起了舞:
尊貴的人類朋友,歡迎您來到黑森林
黑森林是我們的家園,也是你們的家園
如果哪天您丟失了它
請在月光中呼喚它的名字,它就會歸來
歌聲好像不是從它們口中發出,而是從樹洞的每一個細胞里發出,立體、悅耳。它們跳著跳著,就在空中飛舞起來,我和父親也跟著失去重心飄到了空中,這么奇妙啊,任憑我怎樣蹲腳,身子都不會往下墜。我們在空中飛舞了一會兒,蘑菇仙子就站在舞臺上唱起了歌,一時間,她的歌唱把所有事物凝固住了,時間仿佛停了下來,只有那聲音,悠揚、縹緲,好像來自遙遠的未知地,干凈而透徹,我和父親,動物、植物們的心靈受到了一場洗禮。
舞會結束后,動物、植物們紛紛散去,但月光仍舊灑在森林里,它會為它們照亮每一條晚歸的路。我和父親向蘑菇仙子告別,她攔住了我們,盛情地說:
“樹洞的深處,就是這片森林的心臟,我想邀請你們前去參觀。”
我和父親欣然點了點頭,蘑菇仙子領著我們,在樹洞里打開一扇隱蔽的門,沿著一條窄小的、幽深的小道往里走,我們走著走著,看見前面閃著光亮,再往前走,才發現這條小道由白色的水晶鋪就,小道兩旁,生長著的是粉色的、藍色的、紫色的水晶,我伸手撫摸著它們,它們冰涼中帶著濕潤,沁人心脾,蘑菇仙子告訴我們:“這些水晶,都是森林的精氣。”
小道盡頭,是一個寬敞的大廳,大廳里也全是水晶,比小道兩旁生長的水晶更巨大、通透,我們仿佛來到了一個透明的世界,感覺身子也如水晶一樣,是那樣透明、干凈。透明的父親牽著透明的我,在蘑菇仙子的指引下,沿著幾級水晶臺階,走向大廳中央的平臺上,那里矗立著一塊白色的水晶,光照進它里面,立刻變成了紅、橙、黃、綠、藍、靛、紫七種顏色,迷幻動人,蘑菇仙子介紹說:“這塊水晶,是眾晶之首,森林之魂。你們可走進它里面,也可從它里面走出來。”
我看了一下父親,他對我點了點頭,默許我的沖動,我走進那塊水晶,一開始,一股冰涼之氣透進我身子里,讓我難受,我往里走,逐漸適應它的氣息,心境變得平靜、遼闊,后來,我感覺自己的每一個細胞里,都閃耀著水晶之光。這無疑是一次愉悅的旅行,我從水晶里走出來后,把這微妙的感覺告訴父親,在蘑菇仙子的鼓勵下,父親也決定試一試。我站在水晶前,看見三十八歲的父親走進水晶,他走進水晶后,立刻變成了紅、橙、黃、綠、藍、靛、紫七種顏色,一分鐘時間,色譜消失,父親仿佛被水晶融化了一樣,我只看到無邊的透明,看不見父親的身影。
我在水晶前,等了許久,也沒有等到父親歸來,我無比悲傷,蘑菇仙子告訴我,父親去了他想去的世界,她撫摸著我的頭,慈祥地說:“孩子!你該回去了。”
我在小木屋里醒來后,身邊空無一人,月光給森林鍍上了一層輕緲的銀,我喊了幾聲“爸爸”,沒有應答,方知是夢一場。我的悲傷,像樹葉腐蝕的氣息一樣,在森林里漂浮著。我準備沿父親領我走過的路返回家里,我走啊走啊,也不知這條路有多長,我的腳掌磨起了血泡,我的衣衫被荊棘扯得襤褸,我的下巴被風吹出了胡須,我帶著孤獨勇敢地走著,當我走出森林,映入我眼簾的不再是那個偏僻、寂寥的深山,也不再是那個炊煙裊裊、牛歡狗吠的人間。
這是一個民房雜亂、街道堆滿垃圾的小鎮,窗口里透出的燈火,想努力把它擦亮,可它卻陷進了廢墟一樣黑夜,無法自拔。這一條回家之路,我走了二十九年,現在,三十八歲的我,弄丟了三十八歲的父親,我不知該以怎樣的身份,去面對這個居心叵測的世界。
這些年,我沒找到一條與世界對話的途徑。
人往往就是這樣,如果這世界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樣子,我們寧愿把自己封閉起來,拒絕與它交流、融合。顯然,我的這種推理,是不適合用在孩子身上的。我的孩子叫小寶,六歲了,他在三歲的時候,某一天突然變得沉默起來,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不愿與人交流,語言表達能力出現退化現象,后來,他干脆不說話了。三年來,他沒喊過我一聲爸爸,偶爾從他的嘴里冒出幾句含混不清的詞,很難猜測出他想表達什么,他的性格越來越孤僻,拒絕與小朋友們玩,見到陌生人瞳孔放大、表情恐慌,他總一個人呆呆地躲在角落里,一待就是大半天。醫生說,他患上了自閉癥。
自閉癥,又稱孤獨癥或孤獨性障礙,是廣泛性發育障礙的代表性疾病。全國有近一千萬自閉癥患者,他們僅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個人發著暗淡的光,被稱為來自星星的孩子。
我不知道小寶來自哪一顆星辰。
現在,小寶就躺在我懷里,他睡著了,發出輕微的鼾聲,我伸手關掉空調,拉上車窗簾子,以免陽光照射著他,汽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它有著節制的時速和清晰的目標,而我身心疲憊、目光漂浮,車廂里陌生的人們,微閉著眼,佯裝小睡,他們各懷心事,難以與外人訴說心中悲喜,而那些一閃而過的青山或白云,與車窗對立,不知與我們多少逝去的日子有關。
這是我第五次帶小寶來重慶,從我居住的小鎮到重慶,要坐六個小時的大巴車,車到沙坪壩長途汽車站,已是下午兩點,我搖醒了小寶,他面無表情地睜開眼睛,不哭不鬧,表現得順從,我背上行李,牽著他的手,走下了車。夏日的重慶,悶熱得像一個大蒸籠,沒有一絲涼風。我牽著小寶,沿一條寬闊的大街向前行走,流水般的車輛在熱氣里穿梭,流水般的車輛,更像一群螞蟻在熱鍋上爬行,忙碌而急躁,根本不理會路邊一位三十八歲父親的酸甜苦辣,也不理會一位六歲孩童的孤獨。我買了一瓶冰凍的礦泉水,給小寶喝了一點,我們走到了一家小旅館——賓歸旅社,前四次,就住在這里,老板還記得我,簡單問候了一聲,付了八十元,辦理了入住手續。
房間窄小而潮濕,散發著一股霉味,小寶坐在床上,呆呆地望著泛黃的天花板,我打了一盆清水,從行李包里取出毛巾,給他擦拭身子,我說:
“小寶好乖,左洗洗,右洗洗,上洗洗,下洗洗,涼快好休息。”
小寶對我的話充耳不聞,他還在看天花板,對我來說,那塊天花板枯燥無奇,也許,小寶從中看到了一個五彩紛呈的世界,所以,他看得那樣入迷。我試圖從小寶的視覺,去觀察那塊陳舊的天花板,那些泛黃的斑痕,是歲月留下的印跡,有幾處,由于受潮,瓷粉已剝落了些許。這塊天花板,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懸浮在這座城市的某個角落,它忍受了繁華,更忍受了孤寂,難道,它不厭倦自己的使命嗎,也許,它本身就沒有使命,只有狀態,那就是懸浮。
我艱難地從這塊天花板幻生的景象,進入小寶的心境。小寶啊,你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洗漱完畢,我掏出手機,打開APP,再次檢查所掛的西南醫院兒童精神科陳醫生的專家號,這是明天上午的號,一個星期前預約的,自從三年前采用陳醫生的治療方案后,每半年,小寶都要來復查一次。這三年,為了小寶,我拒絕了所有飯局,放棄了熱愛的寫作,把時間和精力都放在他身上,作為父親,哪怕前方荊棘遍布,如果沒有工具,我也要用身子為他開辟一條行走的小路,我希望我的孩子沿著這條小路走下去,抵達的不是懸崖,而是花園。
我希望小寶內心里的那顆星辰,是有溫度的。
晚餐時,我帶小寶到旅館隔壁的餐館里吃小籠包,他對食物從不挑剔,給什么他就吃什么,他對我表達意見時,會用手作簡單的比畫,三年時間,我已適應了他自創的手語,這是父親與兒子之間唯一的溝通渠道。晚上睡覺,小寶有自己專用的小毛毯,這條小毛毯用了多年,已經很陳舊了,但他只需要它,沒有它,晚上他就拒絕睡覺,一個人站到墻壁前賭氣,重新換一條一模一樣的也不行,好像這條小毛毯會散發出獨特的氣息,這氣息讓他無比信任。
第二天早晨,我帶著小寶到醫院排隊,在上衛生間時,我讓他站在門邊,不準亂動,當然,不用叮囑,在陌生的環境中,他也不會亂跑,我以為只要他在我的視線內就沒有問題,只是一眨眼的工夫,當我推開衛生間的門時,已看不到他,我急得四處尋找,呼喊著他的名字。我大腦中的第一個反應是,他被人販子抱走了,我尋求到醫院保安的幫助,他們熱心地參與了搜尋。最后,還是保潔阿姨在打掃衛生間時,在衛生間的另一個隔間里,發現了呆呆站著的小寶,這一場虛驚差點奪走了我的魂,我緊緊摟著他,五味雜陳,眼眶里溢出了一個三十八歲男人堅強的淚水。
陳醫生對小寶的狀態很樂觀,對自閉癥的治療,除按療程進行藥物治療外,行為心理治療及特殊教育也很重要,陳醫生建議我加入了語言訓練、游戲訓練及增強物的使用。行為心理治療及特殊教育主要靠父母平時潛移默化的植入,對于自閉癥,一百個好醫生不如一個好家長,陳醫生說:
“再堅持三年,我相信他會有很大的改觀,繼續努力。”
我說:“只要孩子有希望,別說三年,三十年我也堅持。”
陳醫生給小寶開了處方單,我接過單子后,向他深深鞠了一個躬,他站了起來,拍了拍我的肩膀,投出信任的目光。
醫院里,人潮涌動,人們進進出出,悲欣交集,人間太苦,但從沒有一個人會因為這種苦而放棄它,他們還是那樣熱愛它。就像我愛著我的小寶,這種愛來源于生命——卑微而堅定。
小鎮后面的林場,是我們縣最大的國有林場,栽種的多是杉樹。十年前,林場發生了一次特大火災,連燒了七天七夜,幾乎燒掉了它的三分之二,在這場火災中,犧牲了三名消防人員和兩名當地群眾。林場邊上有一片墳地,父親就葬在那兒,火災原因是那年清明,一戶人家在墳地里放火炮引發了山火,那次火災,徹底燒毀了我童年時漫長而溫馨的夢。
火災過后,山坡一片漆黑,東倒西歪的樹干,像一截截未完全火化的骨頭,它們卑微地呈現在風雨下,任人們說三道四。我所夢到過的蘑菇仙子,我所夢到過的音樂舞會,我所夢到過的七彩水晶,我所夢到過的父親,是時間與意念所生出的幻境嗎?當森林被擄走后,剩下的只是一片殘酷的廢墟及平凡的現實。那是一片可通往過去的森林,當它被燒毀后,我的記憶開始變得混亂,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我美好的童年,我消失在水晶里的父親的愛。
當我向往的美好的世界,如森林一樣灰飛煙滅,我們——也許會關掉身上的每一個窗口,拒絕世界這突如其來的另一張面孔。我們也會變得孤獨,變得自閉,并以曠日持久的姿勢,去對峙、對抗無所適從的一切。只有感同身受,才能與小寶站在同一條線上,讓他放棄戒備,帶領著他,沿一條鋪滿落葉的小徑,走向我所憧憬的黑森林,尋找那遺失的快樂和透明的水晶。
從重慶回來后,我給小寶擬訂了訓練計劃,每天晚上進行十分鐘聲音訓練、半個小時游戲訓練、十分鐘增強物訓練,每個星期,帶他去一次兒童樂園。
為培養小寶的注意力,我以他喜愛的玩具木槌作為增強物,不同方向、不同速度移動木槌,吸引他的目光,然后,讓他對視我的眼睛,我才把木槌給他玩。接下來進行單音和單詞的訓練,為了讓他注意我的發音特征,我每發一個音,都盡量做到表情豐富,嘴型夸張,我們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他就會跟著我正確發出“a”“o”兩個單音了。每一段時間的游戲訓練,我變化著花樣與他一起玩,我們玩挑豆子游戲時,我在盤中倒滿黃豆,加入少許花豆,我和小寶從黃豆里把花豆一粒一粒找出來;我們玩五官游戲時,我面對小寶,一邊說“眼睛”“鼻子”“嘴巴”“耳朵”,一邊觸摸自己五官相應部位,讓小寶模仿著做,比一比誰正確、速度快。有時,我還給小寶讀故事書,雖然他不感興趣,但我也堅持讀,一個故事,讀十遍,讀一百遍,讀得多了,這個故事就潛意識地成了他內心世界所知曉的一部分。
每個星期去一次兒童樂園,主要是想讓他多與同齡小朋友接觸,學習與人交往。有一次,在兒童樂園,他正在玩皮球,一位調皮的小朋友跑過來搶了他的皮球,還打了他一巴掌,他呆呆站著,我看到了他的無助與麻木,心里很痛。小孩子間打鬧,本是尋常之事,但對我來說,事態非常嚴重,他自我的保護意識,會因為這次經歷讓他把剛打開一個縫的心扉重新關閉。我只得找到那位小朋友的母親,苦口婆心向她說明情況,并請求她幫忙,讓小朋友給小寶道歉。
每一步,我都走得很小心;每一步,我都走得很辛苦。
我對父親的記憶其實很少,只記得他是林場里的工人,常拿著一只煙斗,吧嗒吧嗒地抽個不停。我九歲的時候,發了一次高燒,燒到四十度,持續不退,他背著我穿過那片林場,走了兩小時山路,到縣城去看病。我患的是腦膜炎,醫生說,要是再晚半天,我連小命也保不住,醫好了,也會留下后遺癥。
那時,我的父親背著我,走一步咳三聲,他的肺癆已到了晚期,醫生勸他住院,他自感時日不多,背著病愈的我悄悄溜了。父親以為我長大后會變成一個傻子,但他沒有機會看到我長大,就在那年冬天,當他從喉頭里咳出最后一口血時,他的生命定格在了三十八歲。
我想,我應該帶著小寶,去拜訪一下父親。
秋陽高照,我牽著小寶的手,走過金黃的田野,向著那片黑漆漆的廢墟走去。年邁的母親拄著一根木棍子,跟在我們身后,我時常回頭看看她,怕她跌倒,她總微笑著向我們揮揮手,示意我們先走,她會慢慢趕上。
十年時間,林場也沒把燒焦的山野復綠,每年都補種樹苗,種一年死一年,種得人絕望。我們走到廢墟邊緣,遠遠就看見了父親的墳頭,上面生長的茅草在風中搖曳著,好像在向我們招手。
我和小寶給父親打理了雜草,擺上供品,磕了三個頭,我不知道父親看見了嗎,他曾經九歲的兒子和他兒子六歲的兒子。
“爸爸!爸爸!爸爸!”我對著墳頭喊了三聲,我的聲音空蕩蕩的,心也空蕩蕩的。
母親坐在墳場邊的石頭上,舉起木棍子,敲了敲父親墳頭上的泥土,喘著氣,說:
“出來曬太陽啰!”
我又想起了黑森林里的母親,她是有機會變成蝴蝶的,但她選擇了放棄。這么多年,她一直陪在我身邊,以驚人的速度衰老。
哦!我失去的美麗的黑森林。在我九歲時,父親常摸著我的頭,一言不發,陽光噙在他的眼眶里,他抱緊一團團野草,若有所思、行動緩慢,這無盡的野草啊,多像他的愁緒,年復一年生長。父親是一片黑森林嗎?父愛是那一股木葉般腐蝕的清晰味兒嗎?
陽光涂抹在廢墟上,陽光也想把它還原成昔日繁茂的模樣,陽光的努力是徒勞的,它越涂抹,廢墟越蒼涼。我多想牽著小寶,走進這片廢墟,一直走啊走啊,走進童年的夢里,走到這片大地的心臟,那里有一塊七彩水晶,人們可以自由地走進去、走出來,人們可以像水晶一樣,唱著透明的歌。
一只松鼠從草叢中跑出來,躍到一塊高聳的石頭上,它回頭調皮地看著我們,用前爪撓著自己的臉,得意洋洋的樣子。小寶最先看見了它,他用手指向松鼠,嘴里發出了一句含混不清的話:
“爸爸!那——那——”
松鼠受驚,一溜煙逃走了。我緊緊摟著小寶,一粒淚水滴在了手背上,秋日的陽光走進淚水里,折射出紅、橙、黃、綠、藍、靛、紫,我的心突然被這久違的溫暖觸著,啊!水晶,七彩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