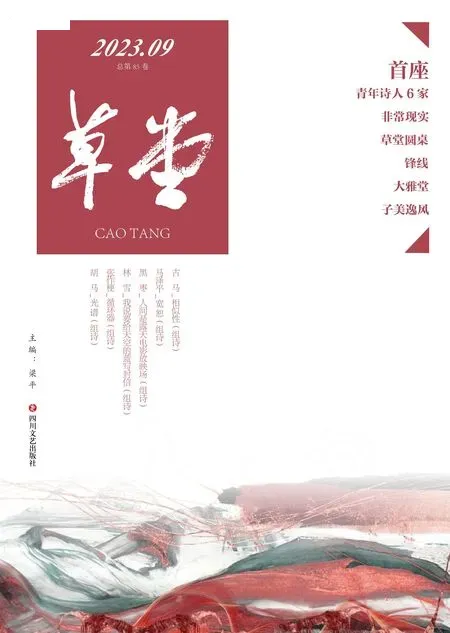鄉(xiāng)土意識(shí)的覺(jué)醒與詩(shī)意的演進(jìn)
◎袁錦鈺

袁錦鈺
伴隨著鄉(xiāng)土作家的散失與鄉(xiāng)土文學(xué)的日漸凋零,文學(xué)和鄉(xiāng)土的距離越來(lái)越遠(yuǎn)。我們不得不面對(duì)的現(xiàn)實(shí)是——鄉(xiāng)土文學(xué)已經(jīng)面臨拐點(diǎn)。詩(shī)人作家們和鄉(xiāng)土的血緣紐帶日漸疏離。曾出身農(nóng)民的作家們多年難回故土,關(guān)于鄉(xiāng)土創(chuàng)作的激情也日益減退,難以寫(xiě)出真正反映鄉(xiāng)土命運(yùn)、鄉(xiāng)土倫理、鄉(xiāng)土情結(jié)的作品。
詩(shī)人林雪的作品給人以最直接印象與沖擊的莫過(guò)于——“鄉(xiāng)土”。從早期的“朦朧詩(shī)”到如今深入生活的鄉(xiāng)土關(guān)懷,林雪的轉(zhuǎn)變是飛躍式的,是一種誕生去舊存新式的“蛻變”。拋棄細(xì)碎繾綣的閨閣情愫,詩(shī)人將更多的關(guān)注投注于更加深沉遼闊的鄉(xiāng)土大地。
鄉(xiāng)土詩(shī)意中的詩(shī)人主體性確立
當(dāng)我們談?wù)撈鹪?shī)歌與詩(shī)歌文本,詩(shī)人主體性是我們無(wú)法回避的一點(diǎn)。詩(shī)人作為詩(shī)歌的主宰者,以一己之力構(gòu)建一個(gè)精神的王國(guó)、一個(gè)思想的烏托邦。因此,在很多詩(shī)人的詩(shī)歌之中,詩(shī)人主體性是外顯且無(wú)法撼動(dòng)的。在詩(shī)人主體性的具體表現(xiàn)上,除了對(duì)于歷史和文化的批判,詩(shī)人們還在更多追求著詩(shī)歌的更高境界——對(duì)于人類(lèi)生存境況的揭示以及對(duì)于人類(lèi)命運(yùn)的關(guān)懷與救贖。當(dāng)我們談到林雪的詩(shī)歌:“我要在石頭里坐好/成為石膏洞里/一簇氣泡”(《我的馬車(chē)帶走了哪些詞?》),“那些我們看不見(jiàn)的人/我們/把握不住的事物/在對(duì)我們的/回憶中撤離”(《詩(shī)意秧苗》)。在《大地葵花》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林雪的詩(shī)歌中運(yùn)用了大量“我”“我們”等第一人稱(chēng)代詞,以第一人稱(chēng)對(duì)所見(jiàn)之人事物進(jìn)行敘述,對(duì)個(gè)人情感也是直接地進(jìn)行抒發(fā),詩(shī)人主體外顯并在詩(shī)歌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得以不斷強(qiáng)化。同時(shí),林雪也善于從旁觀者的角度、以第三人稱(chēng)視角觀察生活,“村莊睡在自己的經(jīng)驗(yàn)里/河流向右轉(zhuǎn)身/那些避難的人還未返回/被死亡截留的人/還沒(méi)入睡”(《睡吧,木底》),看似是在講述他人的事件與故事,但在細(xì)致敘述中流露出的上帝視角則從另一個(gè)角度加強(qiáng)了敘述者的存在感,并沒(méi)有刻意地規(guī)避與隱藏,使得進(jìn)行敘述的詩(shī)人雖未以第一人稱(chēng)視角直接亮相,詩(shī)人主體性卻在詩(shī)行敘述之中自然得以展露,不斷鞏固加深,可謂“未謀其面已知其人”。
除此之外,林雪詩(shī)歌中的詩(shī)人主體性有著與其鄉(xiāng)土情結(jié)相適應(yīng)的獨(dú)特特征。廣泛來(lái)說(shuō),在文本中進(jìn)行自我形象的塑造使得詩(shī)歌主體成為主宰,這是詩(shī)人們建構(gòu)詩(shī)人主體性的常用手法。該手法的特征便是以強(qiáng)烈道德感、崇高感凸顯存在和自我矛盾斗爭(zhēng),并且使詩(shī)人主體符號(hào)化。而在林雪的詩(shī)歌中,詩(shī)人主體性并非通過(guò)拔高自身而突兀顯現(xiàn),究其原因便是因?yàn)樵?shī)人獨(dú)特的鄉(xiāng)土意識(shí)為其提供了有力支撐,使其詩(shī)人主體性與鄉(xiāng)土意識(shí)緊密融合,于鄉(xiāng)土意識(shí)之中顯現(xiàn)。林雪在創(chuàng)作中以“赫?qǐng)D阿拉”這一鄉(xiāng)土意識(shí)的精神標(biāo)桿作為關(guān)切人類(lèi)命運(yùn)的根本出發(fā)點(diǎn)和落腳點(diǎn),實(shí)現(xiàn)詩(shī)人主體與鄉(xiāng)土情結(jié)自然融合,從而使得自身的創(chuàng)作既具有崇高普世情懷,同時(shí)又以扎根大地的鄉(xiāng)土意識(shí)持續(xù)為這種“悲憫”與“救贖”輸送精神給養(yǎng),使得詩(shī)人無(wú)論是抒懷或悲嘆都顯得豐滿踏實(shí)而不輕飄。詩(shī)人主體性也就以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得以建構(gòu),同時(shí)也成為詩(shī)人的鄉(xiāng)土意識(shí)向著更深遠(yuǎn)層次進(jìn)化的途徑之一。
鄉(xiāng)土詩(shī)歌中女性詩(shī)格的轉(zhuǎn)變
當(dāng)我們談及林雪,“詩(shī)人”是她的第一標(biāo)簽,但在此基礎(chǔ)上另外一個(gè)重要標(biāo)簽也不容忽視——“女性”,這是無(wú)論談及其本人或其作品時(shí)都無(wú)法規(guī)避的一點(diǎn)。在這里“女性”不僅僅是指其生理屬性,在涉及其作品時(shí)則指向“女性主義”。而林雪在其至今為止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經(jīng)歷了兩次轉(zhuǎn)型與蛻變,其中女性詩(shī)格的轉(zhuǎn)變則貫穿了整個(gè)過(guò)程。
在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初期,詩(shī)人林雪就以《夜步三首》入選了當(dāng)時(shí)轟動(dòng)一時(shí)的選本《朦朧詩(shī)選》,這本詩(shī)選在當(dāng)時(shí)的地位是歷史性的。可以說(shuō),林雪在當(dāng)時(shí)以一種使人驚艷的詩(shī)人身份于中國(guó)文壇隆重登場(chǎng)。盡管林雪在極其年輕的年紀(jì)迅速取得了文壇承認(rèn),但是在當(dāng)時(shí)百花齊放的“朦朧詩(shī)”流派中,相比舒婷、北島等已被廣泛接受和認(rèn)可的詩(shī)人,林雪所處的位置仍相對(duì)邊緣。不可否認(rèn),受年齡所限,林雪當(dāng)時(shí)的閱歷與技巧還帶有青年詩(shī)人身上常見(jiàn)的對(duì)于自我的過(guò)度關(guān)注和視野上的狹窄。但這時(shí)其作品中特有的女性的細(xì)膩與敏感已經(jīng)成為林雪重要個(gè)人特色,同時(shí)也為其之后女性主義覺(jué)醒做好了鋪墊。
經(jīng)過(guò)一段時(shí)間的沉淀與自我精神的深度探索,林雪創(chuàng)作中的女性詩(shī)格已然萌發(fā)。正如其自述一般:“到了20 世紀(jì)90 年代,我覺(jué)得我自己尋找到了一種寫(xiě)詩(shī)的語(yǔ)言和語(yǔ)氣:即女性經(jīng)驗(yàn)、意識(shí)與角色,女性在社會(huì)分工中的理想、心靈、命運(yùn)和情感。比如我在那個(gè)時(shí)代的工作、愛(ài)情或閱讀,一次輕易的離別帶來(lái)的永訣,在無(wú)數(shù)夜晚寫(xiě)下的詩(shī)篇,忍受過(guò)同樣的孤獨(dú)悲傷。這一切都曾經(jīng)是我心中的詩(shī)歌素材,像《微火》《紫色》等參加詩(shī)刊社青春詩(shī)會(huì)時(shí)寫(xiě)出,并被稱(chēng)為是女性主義寫(xiě)作代表詩(shī)人的代表作。”(林雪、許維萍:《詩(shī)歌:對(duì)大地和人民的熱愛(ài)與低吟》)此時(shí)的詩(shī)人經(jīng)歷了情感的洗禮進(jìn)而蛻變,與自己的內(nèi)心在某種程度上達(dá)成了和解。在這一階段,詩(shī)人對(duì)待生活的態(tài)度已經(jīng)有所調(diào)整,并且開(kāi)始將目光轉(zhuǎn)向了觸手可及的日常生活,詩(shī)歌中描寫(xiě)的對(duì)象也開(kāi)始有了平凡的人和事。如果說(shuō)前一個(gè)階段詩(shī)人仍飄浮于朦朧詩(shī)意的“虛化的”詩(shī)情之中,到了這一階段,詩(shī)人因內(nèi)心精神的擴(kuò)充與豐滿開(kāi)始向下沉,逐漸開(kāi)始生長(zhǎng)出向大地扎根的根須,女性主義不斷成長(zhǎng)和完善,同時(shí)鄉(xiāng)土意識(shí)開(kāi)始覺(jué)醒并且日益占據(jù)重要的篇幅與位置。
終于,沉浸于“淡藍(lán)色的星”的詩(shī)人終于找到了通向詩(shī)歌更深處的道路,沉潛多年,詩(shī)人林雪迎來(lái)了又一次轉(zhuǎn)型,而此次轉(zhuǎn)型也可以看作林雪詩(shī)人品格的一次質(zhì)變。2006 年,《大地葵花》集結(jié)出版,第二年便獲得了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一個(gè)尋找詞語(yǔ)/并被詩(shī)歌尋找的女人/正在接近/她生命中最后的時(shí)光”(《有生之日》)。《大地葵花》中這些超越了純粹個(gè)人情感經(jīng)驗(yàn)的詩(shī)篇,強(qiáng)有力地證明了詩(shī)人林雪已經(jīng)完成了生命與哲學(xué)的偉大相遇,實(shí)現(xiàn)了從小我走向大我甚至無(wú)我的精神轉(zhuǎn)變。
通過(guò)對(duì)其女性主義覺(jué)醒與女性詩(shī)格轉(zhuǎn)變過(guò)程的梳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林雪因生命體驗(yàn)的豐富使得女性主義覺(jué)醒的程度不斷加深,而豐富的生命體驗(yàn)與不斷覺(jué)醒的女性主義共同作用,促使林雪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核心日益下沉,最終觸及深層的鄉(xiāng)土意識(shí)內(nèi)核——詩(shī)人的鄉(xiāng)土情結(jié)。在詩(shī)人的鄉(xiāng)土情結(jié)被觸發(fā)之后,又反過(guò)來(lái)與已趨向成熟的女性主義相互融合進(jìn)行補(bǔ)完,而二者補(bǔ)完的成果便是林雪女性詩(shī)格的轉(zhuǎn)變。這一轉(zhuǎn)變是以其獨(dú)有的生命體驗(yàn)對(duì)女性主義的多元性、復(fù)雜性進(jìn)行探索與思考,而這一生命體驗(yàn)的精神內(nèi)核便是詩(shī)人的鄉(xiāng)土情結(jié)。以女性的主體意識(shí)融入鄉(xiāng)土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最終實(shí)現(xiàn)個(gè)人女性主義的真正成熟,同時(shí)也從另一角度對(duì)詩(shī)人鄉(xiāng)土意識(shí)進(jìn)行補(bǔ)充與支撐,是對(duì)于原本女性詩(shī)格的系統(tǒng)升級(jí)。在這次轉(zhuǎn)變之后,林雪開(kāi)始以細(xì)膩獨(dú)特的女性視角講述廣博的鄉(xiāng)土故事,實(shí)現(xiàn)了女性主義與鄉(xiāng)土詩(shī)意的完美融合。
“鄉(xiāng)村客車(chē)”與博爾赫斯式的“小說(shuō)”圖式
博爾赫斯,其存在與作品是公認(rèn)的20世紀(jì)現(xiàn)代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分水嶺。其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與影響力自不必贅述,且博爾赫斯的作品在中國(guó)一經(jīng)登陸,就立刻在文壇上散播開(kāi)來(lái),掀起一股巨大的博爾赫斯潮流,引得無(wú)數(shù)中國(guó)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學(xué)習(xí)與模仿,對(duì)中國(guó)文學(xué)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博爾赫斯的出現(xiàn)使得傳統(tǒng)文學(xué)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很大的變化,值得一提的是博爾赫斯從一個(gè)全新角度打破了文學(xué)種類(lèi)的界限,其短篇小說(shuō)總是帶有詩(shī)化傾向與詩(shī)意色彩。這已成為博爾赫斯極具辨識(shí)度的個(gè)人標(biāo)簽。而作為在其影響下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之一,詩(shī)人林雪在精神原鄉(xiāng)和偉大思想的影響下,孕育出了與博爾赫斯的小說(shuō)詩(shī)化相對(duì)應(yīng)的具有鄉(xiāng)土意識(shí)的詩(shī)歌的小說(shuō)化。
“東州街到五龍30 公里/出城的路啊越走越搖晃/生活啊越來(lái)越荒涼” (《鄉(xiāng)村客車(chē)》),這首詩(shī)里僅通過(guò)不長(zhǎng)的篇幅就生動(dòng)描繪了擠坐在鄉(xiāng)村客車(chē)?yán)锏娜藗儯?shī)人基于乘客們的身形與裝扮,對(duì)他們?nèi)粘5泥l(xiāng)村生活進(jìn)行了想象性描寫(xiě)。生銹的車(chē)體、原鄉(xiāng)人的喉音、荊條葉子、曬干的氈靴和烏拉草……幾乎沒(méi)有絲毫多余筆墨,僅通過(guò)渾北大地上原生的些許意象,就使得鄉(xiāng)村大地上人們生活的煙火氣升騰于讀者眼前心間,并且在最終呈現(xiàn)出的效果上更勝于冗長(zhǎng)小說(shuō)的鋪排敘述,點(diǎn)線成面,于詩(shī)行中呈現(xiàn)出博爾赫斯式的精致的小說(shuō)化。
“詩(shī)歌的小說(shuō)化是一個(gè)概括性定義,總體來(lái)說(shuō),是詩(shī)歌從普遍抒情轉(zhuǎn)向后現(xiàn)代普遍敘事的過(guò)程”(劉成康《論博爾赫斯小說(shuō)中的“嵌套”藝術(shù)》)。在博爾赫斯小說(shuō)哲學(xué)的影響下,林雪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中也蘊(yùn)含著鄉(xiāng)土化了的博爾赫斯式的“小說(shuō)”圖式。首先從林雪詩(shī)歌的語(yǔ)言上來(lái)看,詩(shī)歌語(yǔ)言的小說(shuō)化通常被認(rèn)為是詩(shī)歌的禁忌,但詩(shī)人卻能用其卓越技巧和細(xì)膩感知,敏銳地尋找到二者之間的臨界點(diǎn),使其詩(shī)歌語(yǔ)言在詩(shī)與小說(shuō)之間達(dá)到一種微妙的平衡,自然流露出“博爾赫斯傾向”。其次,林雪善于在詩(shī)歌中構(gòu)建一個(gè)沉浸式“小說(shuō)場(chǎng)”,而這個(gè)“小說(shuō)場(chǎng)”又通常以鄉(xiāng)村為背景,這就要求詩(shī)人在詩(shī)歌語(yǔ)言的組織上擺脫小說(shuō)的松散敘述,使得詩(shī)歌結(jié)構(gòu)更為緊密和富有“原鄉(xiāng)”質(zhì)感。同時(shí),在有限詩(shī)句中承載豐富內(nèi)容,也要求詩(shī)人必須從遣詞造句上精心雕琢,使得每一行詩(shī)句都蘊(yùn)藏著巨大信息量,為詩(shī)歌在意義上擴(kuò)容。可以說(shuō),林雪的詩(shī)歌以赫?qǐng)D阿拉為精神原鄉(xiāng)的大地為創(chuàng)作的根基與背景,融合博爾赫斯式的創(chuàng)作手法,共同構(gòu)建出一幅“鄉(xiāng)土小說(shuō)式”的詩(shī)歌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