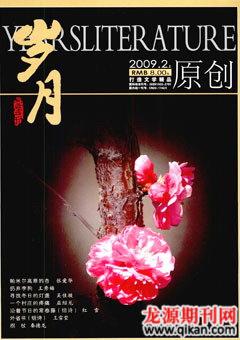尋找冬日的燈盞
吳佳駿
時令漸入冬季,該靜的,都安靜下來了。
每年的這個時節,我的心,都有種被靜謐撫慰過后的透徹。盡管,寒冷會使我的生活秩序,或多或少遭受一些影響。
城市鈍化了人對自然變化的敏感。
無論是走在喧鬧、擁擠的大街上,還是站在家中孤懸的陽臺上,我的目光都是那樣驚悚不安。我看到很多的老人,呆在屋子里。偎著個電火爐,和一只貓說話,和一只狗談心。我看到更多的年輕人,坐在街邊的餐館里,談工作,談愛情。每個人都有自己過冬的方式,都有獨自抵御寒冷的辦法。
季節的冬天來臨了,一些人的冬天,也在來臨。
入冬那天,我回了一趟老家。臨走前,我在城里買了兩件毛衣,兩瓶燒酒。毛衣,是買給母親的。在我的記憶里,母親很少穿毛衣。我五歲那年,父親從遠方回來,買了一件黃色毛衣,作為禮物,送給母親。可母親一次也沒穿過,她將那件毛衣拆成線團,改織成了一條圍巾,和一件小毛衣。后來,那件小毛衣,穿在了我的身上,而那條圍巾,套在了父親的脖子上。
再后來,那件小毛衣被我穿舊了,母親又將之改織成一條毛褲,或者一件毛背心,陪伴我度過了無數個寒冷的冬天。暖絨絨的毛衣穿在我瘦弱的身上,不僅溫暖了我的身體,也溫暖了母親的心。
我的整個童年時光,都升騰著一團由一件毛衣幻化而成的黃色火焰,飄蕩在我記憶的天空,明亮、吉祥。
一件毛衣,呵護著一顆稚嫩的心,平安過冬。
時間是流動的。我在一個比一個寒冷的季節中,慢慢長大。而母親卻在一天天老去,衰老的跡象,就像她每個冬天都穿在身上的那件破棉襖。綴滿的補丁,是她臉上被嚴寒凍傷的皮肉。每一個補丁,都深藏著母親一個苦澀的秘密。母親為了掩飾自己內心的疼痛,總是將那件破棉襖洗得干干凈凈。倘遇冬陽天氣,她也一定不忘將棉襖放到太陽底下,反復翻曬,將堆積在棉襖里的寒氣和霉菌,驅殺干凈。這樣,即使在那些苦難的歲月里,母親也讓我們這個家,充滿了陽光的味道。
一件破棉襖,加深了我對母親的理解和認知。
燒酒,自然是給父親準備的,父親嗜酒,以致于,他的脾氣,都沽上了酒的性格——火暴,剛烈。凡遇到不順心的事,他就愛發脾氣。而母親,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父親的“出氣筒”。父親每次咒罵母親,母親都低埋著頭,沉默得像一只可憐的羔羊,對父親百般忍讓、遷就。直至父親最終在她的隱忍下,無計可施,而走向了平和和中庸。
我的母親,這個普通農村婦女。簡直是一個鄉村哲學家和悟道者。她很早就領悟到“天下至柔者至剛”這個道理。她以女性特有的寬容和善良,消融了父親的強硬和倔強。
不再發脾氣的父親,從此只與酒為伴。酒,是父親精神上的一盞燈。沒了酒,他會很寂寞。母親對父親的嗜酒,是有看法的。她說:酒會要了一個人的命的。
父親是母親心里的一盞燈,也是我們這個家的一盞燈。為了這盞燈不過早地變得暗淡,母親曾想借助茶來勸父親戒酒。然而,幾經周折,母親還是輸給了父親,輸給了點燃和照亮父親這盞燈的另一盞燈——酒。
酒,是支撐父親過冬的良藥。惟有酒,才能使父親的人生明亮,骨骼溫暖。
鄉村的冬天,多了些宿命的意味。
落光了葉子的樹枝上,掛著的兩個空鳥巢,像兩頂鄉村老人廢棄的舊氈帽。村頭的那條河流,變得比以前淺了,瘦了,沉靜中透著憂傷。野地里,薄靄朦朧,白色的霧狀顆粒,灑滿了田間堆積的草垛。寒氣上升,滲透在身體周圍,濡濕了我的視線,也濡濕了我的記憶。
小時侯,我和姐姐常在黃昏時分,走向冬日的山坡。姐姐肩背背篼,手握割草刀,寒冷將她的一雙小手,凍得通紅。五根指頭,像五根細小的紅蘿卜。姐姐每天都必須趕在天黑前,割滿一背篼野草。圈里的那頭老牛,還在盼著她帶回的晚餐呢。我則牽著家里的唯一一只羊,跟在姐姐身后,鼻涕掛在嘴角,像剛剛凝結的冰凌。我怕寒冷凍壞我的雙手,而生出一個又一個凍瘡,只好將手插在褲袋里,把栓羊的繩索套在腰桿上。喂飽羊,是我每天的責任。
姐姐每割一會兒草,就要抬頭看我一眼,也看我身邊的羊一眼。她在看我們的時候,內心是充滿恐懼的,她那驚懼的眼神里,總是閃動著一絲不確定的信息。我知道,姐姐是怕我,或者羊,會被寒冷凍死。而無論是哪一種結果,她最終都沒法回家向父母交差。羊的生命和我的生命,同等重要。但姐姐知道,每年,都會有一些人,或者一些牲畜,在冬天死去。
我們深刻記得爺爺臨終時的樣子。那個冬天,村莊迎來了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雪。雪花紛紛揚揚,飄灑在故鄉的大地上。地面上積滿厚厚一層雪,雪覆蓋了地上的荒草,也覆蓋了平時熟悉的道路。爺爺嘴叼大煙袋,抬頭望望天,半響才說了句:“狗日的雪,下了四天四夜了,啥時才有個完!”說完,他就牽著圈里那頭跟他一樣老的牛,慢慢地向遠處走去。那頭牛,跟了爺爺一輩子。無數個冬天,他們都是在相互依偎中走過來的。
那天,直到天黑盡,也不見爺爺和他的那頭牛回家。而雪花還在繼續飄灑,絲毫沒有要停止的意思。當我們打著火把,在田野里找到爺爺時,他已經伏在牛背上,四肢僵硬,永遠地睡著了。牛的背上搭著爺爺身上穿的棉大衣,而爺爺的整個身體,早已被雪花覆蓋,像一尊凝固的雕塑,定格在一片冰雪世界里,也定格在我們的記憶中。
活下來的老牛,很孤單,衰老得也很快,每天都淚花閃閃。
做一頭牛,或一只羊,也是不容易的。
爺爺走后,父親將飼養老牛的任務,交給姐姐去完成。他說:“老牛在,你爺爺就在。”
從此,姐姐和我,心里都充滿懼怕。我們擔心,在某一天,老牛也會像爺爺一樣,安靜地死去。這是我們無法掌控的結局。
誰能真正熬過冬天呢?
父親掄著臂膀,在院子里劈木柴。母親將劈開的木柴,摟到墻角,壘出碉堡的模樣。他們在替自己積累生活的資源和能量。他們的心里,需要旺盛的火焰和光源。
母親知道我要回來,停止了去野外的一切勞動,特意取下灶梁上掛了一個周年的臘肉,為我做了一桌豐盛的晚餐。劈完木柴的父親,冒著寒冷,在村頭徘徊,坐立不安。一雙昏花的眼睛,直愣愣盯著回村的山路。他渴望在那條路上,看到我歸來的身影。就像曾經,他望著我離村時的背影,以及那一個個滯重、堅定的腳印。
入夜,四周都安靜下來。干澀的冷風,在屋子外面鉆來竄去。父親、母親和我,圍桌而坐,熱氣騰騰的飯菜,擺了一大桌。這種暌違已久的親情氛圍,讓我感到一種踏實而寧靜的幸福。父親和母親,爭著為我夾菜。我的回家,成了他們最為隆重的節日。
但在父母高興的背后,我還是隱隱感覺到一絲不安。透過十五瓦電燈泡暗黃的光線,我看到了父母身體上,那被歲月的利斧斫傷的痕跡。母親臉上滄桑的皺紋,已經不能再掩飾她經受風霜雨雪后的平靜。父親彎弓的脊背,掉光的門牙,以及他那條患風濕病的“老寒腿”,都在時間的監視下,證明著他的苦難人生,離最終的大地,越來越近
凝視父母,我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
他們都生活在寒冷里太久了,以致于,他們的生命里住進了一片雪原。那片雪原,不是火能夠烤得化的。父母所需的溫暖,也絕不是一件毛衣,或一瓶酒的事情。
那么,冬天所呈現的色彩,就只能籠罩上一層惆悵和悲涼嗎?
我時常想,爺爺在多年前那個冬天的辭世,絕不是因為那場持久飄飛的大雪,也不是由于下雪所帶來的更大的寒冷。而是源于嵌入他骨子里的巨大孤寂和絕望。這種生命的感受,是生活饋贈給他的,只有他自己能夠體會。如果,我那曾經深愛著他的奶奶,不曾先他而去。也許,爺爺的孤寂,就會分出一份,讓他生命中的另一半去承擔和消磨。如果,我的父親,曾經能把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抽出一小半,投入到爺爺的晚境上去,爺爺的孤絕至少也不會那樣強烈。
可我父親,當時都在干什么呢?
有些事情永遠無法說清,回憶總是布滿傷痕。現在想來,我是理解父親的,父親也有他的苦衷。在一次醉酒后,父親拉著我的手說:“孩子,在過去的那些日子里,要不是我和你母親,你和你姐姐,甚至連我們這個家,恐怕都難平安過冬。”
爺爺把人生最后的信任和安慰,留給了陪伴他大半生的那頭老牛。他相信,老牛是理解他的心靈秘語的。只是不知道,老牛的內心世界,爺爺能否看透?
有四季,就一定有冬天。有年輕,就一定有暮年。
暮年,也應該有美麗和浪漫的一瞬吧。就像雪花的墜落,不止代表寒冷,也昭示春訊。
母親還是穿上了我為她買的毛衣,雖然,她的表情告訴我,這件毛衣并不合她的身。母親是屬于鄉村的,她已經習慣了穿棉襖,也練就了抵抗寒冷的方法。這種扎根泥土的生存,曾使母親嘗試過各種各樣的活法,有時像莊稼一樣活著,有時像野草一樣活著,有時像樹一樣活著……
活下來的母親,走過了一個又一個漫長的冬天。
母親反復撫摸著身上的毛衣,臉上浮現出了她一生中少有的榮耀。我不知道,這種虛幻的榮耀,能否最后支撐她平安地走過比寒冬更難熬的暮年。
我從母親身旁立起身,推開房門。看見父親躺在床上,鞋也忘了脫。如雷的鼾聲,打破了冬夜的寧靜。吃飯時,父親看見我為他買的酒,有些興奮,忍不住多喝了幾口。酒再一次讓他找到了作為父親的尊嚴。
我幫父親脫掉鞋子,掀開棉被,將他的身子蓋嚴實。我不敢想象,衰老的父親,還能把酒當作他生命中最強有力的支撐。
除了酒,誰還能將父親的晚境照亮?
在父母心中,我是他們共同的燈盞。但我能成為他們心中一盞永不熄滅的燈嗎?
有燈照耀的冬天,肯定是溫暖的。心溫暖了,生命才有亮色。
在城市里待久了的人,都應該去鄉下走一走。最好是在冬天,要不然,你就永遠不知道生命的耐寒性,也不會真正理解溫暖的含義,更不會知道季節對人生的暗示。
城市不像鄉村,季節都被欲望和污染吞噬、破壞了,看不真切,看不究竟。甚至連太陽和月亮,也很難用視覺進行區分。但在鄉下,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每一個季節的嬗變,都是時間的一次轉身和敘事。它見證了生命的衰老和輪回,又催使萬物在輪回中復蘇和生長。
誰要是站在冬天的邊沿,能看到春天的陽光,誰就是幸福的。我看到了——盡管,我是代替母親看到的。
母親,是沒有春天的。
沒有春天的母親,用自己寒微的一生,千百次,將春天喚醒,像喚醒另一個人提前到來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