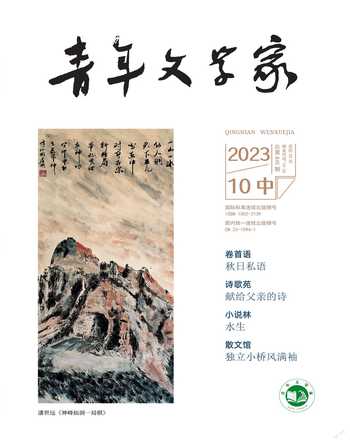試論唐詩的時間意象
王一寧
茫茫往代,時間以起興、作比等形式出現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它作為哀嘆自身、國家命運的載體,是千余年來詩人的詠嘆對象。而在詩歌發展過程中,詩人對時間意象的描寫方式和視角有所變化。本文將從功能角度導入,著重研究唐詩在視角、寫作方式、情感表達相較于前人領先的方面,并結合歷史、思想等多方面振葉尋根,淺析唐朝詩歌視野擴大的背后因素。
曹葦舫在《詩歌意象功能論》中把意象的功能分為表述功能、建構功能、美感功能。表述功能,具有描述、擬情和象征作用;建構功能,指多個意象組合起來構成完整的內涵;美感功能,指意象不僅有外在之美,更有內蘊之美。
一、先秦兩漢(表述功能和建構功能)
中國的文學發展有很明顯的直覺體悟的思維方式,就像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所說的“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人與自然在詩中和諧共處。鐘嶸在《詩品序》中提到詩歌的寫作是“即目直尋”的,“高臺多悲風”“明月照積雪”,不過多雕飾,詩歌便“自然英旨”,外樸內秀。因此,在感慨時光流逝時,詩人能把抓不住的、抽象的時間以描寫自然意象的形式訴諸揮毫落紙的文字中。
先秦時期,詩人就常以自然景物作為起興,感嘆時光流逝,如《詩經·采薇》從“柔”到“弱”,再到“剛”,表示戰爭不斷;《詩經·氓》從“桑葉沃若”到“其黃而隕”,表示女子年華逝去;《詩經·蜉蝣》從羽翼“楚楚”到“麻衣如雪”,表示時光短暫。以此觀之,此時意象就具有建構功能,意象不再是單獨的、靜止的,而是組合起來流動成具有復雜意義的時間概念,傳達相對完整的意思。《楚辭》描寫時間節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草木之間傾注了屈原對國家凋敝、君王昏庸的悲慟感傷之情。此時意象已具備表述功能的擬情性、描述性。
二、唐(美感功能)
先秦兩漢描述時間的意象業已具備表述和建構功能,但唐詩的時間描寫在廣度和視角上遠遠領先前人,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將自我融入整體。前人的意象還局限于自身生命的短暫,但是唐詩已經從群體角度出發,以生生不息的生命延續來抗衡時間的無窮無盡。被聞一多先生譽為“頂峰上的頂峰”的《春江花月夜》中,張若虛因月而多情,以月代表無窮時間,“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這突破了自我相對于綿延時間的渺小之感、無力之情的局限性,把視角轉換至人類整體的延續,時間意識和宇宙觀的擴張,體現了唐詩的開闊視角和廣闊眼界的同時,也蘊含著朝氣蓬勃、蒸蒸日上的盛唐氣象。再如,劉希夷《待悲白頭翁》中的“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和賀知章《回鄉偶書》中的“惟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二人把視角擴展到人群整體,不再局限于自身個體意識,超越了東漢末《古詩十九首》中的“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以己為憂的視角,開拓了更高的視野。
二是把時間注入非時間的事物,使意象連接古今未來,包羅萬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唐人七絕的壓卷之作—王昌齡的《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詩人身處正北邊塞,仿佛看到了百年前的明月和邊關,雄偉滄桑,而在這百年間,邊關和明月又見證了多少戰士血灑疆場,目睹了多少男兒馬革裹尸,歷史好像在這一刻被凝固住了。詩人寫詩時望見了秦漢,后人讀詩時看到了盛唐,詩歌像一條長線貫穿秦漢、盛唐,以及現在。時間在詩中被打通,其帶來的震撼和情感沖擊不言而喻,雖無任何解說,但讀者已然心領神會。又如,在《將進酒》中,李白飲酒高歌“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酒中蘊藏著時間的概念,以時間的無限來襯托自己的郁郁不得志,暗含無限感傷。再如,李賀的《金銅仙人辭漢》,“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天如果也有情感的話,天也會老啊!寥寥幾句,永恒的、廣袤的、無窮的天被賦予了詩人的情感,以“衰老”這一時間之意寫出李賀在仕途不順的困境下,哀郁敗落的悲痛欲絕躍然紙上,即使是天也盛不下、端不住,叫人潸然淚下。
三是以意象寄托情感,不再述說抱負志意,即陳子昂在《修竹篇序》所總結的“興寄都絕”。先以劉禹錫的懷古詩《烏衣巷》為例,“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連接了過去和現在,表達了詩人對六朝衰落凋零的無限惋惜,對王謝家族繁盛與沒落的感慨;《石頭城》一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月”和“潮”兩個意象都聯通了六朝與中唐,潮水被詩人賦予了時間的概念,它見證過舊朝的繁華,現如今看到此時的空城也只能寂寞地回去,金陵蕭瑟,王氣黯然,物是人非;《西塞山懷古》中“山形依舊枕寒流”一句,詩人借“山形”“寒流”來表示時光的流逝,今非昔比,表達其對人事消磨的感慨。又如,李商隱登樂游原時懷念漢朝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登樂游原》)和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江南春》),分別抒發了詩人對晚唐最后的無奈頹然之情和對南朝梁遺留景觀的慨嘆憂思之情。對于這樣的詩句,其雖沒有描寫自己的感情,但通過時間注入意象傳達給讀者歷史的滄桑巨變,讓讀者感同身受。這是簡單意象背后無窮的內涵之美。意象不僅是單位,更是交織在一起的生命力和情感。這種美是模糊的、無法言喻的,卻又能震撼心靈的,即言外之意,這便是意象的美感功能。
四是對于自然的觀察更加細致,詩人全身心地體會自然,達到“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李清照《念奴嬌·春情》)的入微境界。“詩家天子”王昌齡運用意象出神入化,其所作“紅旗半卷出轅門”(《從軍行七首》其五)一句,巧妙地抓住紅旗被風吹至一半卷起的形態,點明此時從轅門出,通過對意象的準確把握及時間的精確性,繪制出前軍捷報頻頻出入轅門的情景,使戰爭勝利的喜悅和豪邁之情躍然紙上。杜牧見到少女貌美,所作“娉娉裊裊十三余,豆蔻梢頭二月初”(《贈別二首》其一)二句,用二月初的豆蔻梢頭作比,跟以往單純把少女比作花不同的是,“二月初”點明了是花骨朵兒,盡寫十三歲少女的含苞待放,青澀稚嫩,風情初現,更加撩人心弦,極具畫面感的同時,又使得意象更空靈、更耐咀嚼。溫庭筠在寫閨怨詩時,形容女子悲傷輾轉的內心,“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更漏子·柳絲長》),通過描寫整晚雨水滴落在葉子上接連不斷的聲音,運用通感的形式,調動我們的聽覺、視覺,寫出了深閨女子的悲切難耐、無法入睡的焦灼無助。
小小的意象,迸發出無可言說的豐富情感,讓讀者感同身受。后世,蘇東坡的“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惠崇春江晚景》),零星綻放的桃花便可預見春天悄然而至,僅僅看到鴨子浮游,便能體會到水的漸暖、春的到來,這便是對自然細致入微的觀察和全身心的體會。小的意象孕育著無窮的內在美,具有豐富的美感功能。
三、魏晉南北朝
唐詩的意象如此空靈縹緲,如此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觀瀾索源,筆者認為主要歸功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發展。下面將從幾個方面來闡釋唐詩意象開闊明亮的原因:
從寫作手法上,詩人用對仗解決合掌,使得意象間大開大合。南朝宋時,鮑照意識到合掌的不足,在《發后渚》中用對仗拉開相鄰詩句的空間,容納更多內容,“途隨前峰遠,意逐后云結”。到了南朝梁時,庾信開創了大開大合的寫作方法,“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寄王琳》),在短小的詩句中囊括更多的內容,豐富了整體內容的表現力。到了唐代,這一手法得到發展,如“分野中峰變,陰晴眾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終南山》),王維描寫山峰陰陽兩面的不同,由廣闊宏偉的開闊視角到落在一樵夫上。到了杜甫,意象進行無限擴張,“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登高》),用“不盡”“萬里”“無邊”來展現范圍之廣、時間之長,宏大的意象先打開后收攏,最后停在小小的酒杯上,“潦倒新停濁酒杯”,不讓人覺得突兀,反而有種囊括宇宙之意。
因此,在描寫時間的唐詩中,視角多樣開闊,可運用的意象無窮無盡,且具有跳躍性。如上文提到的“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便是大開大合寫法的極致突破,從明月、邊關到遙想戰士戰死沙場,描寫跨越時空,視角轉換頻繁,意象無限擴張。《春望》一詩并沒有中心意象,但意象跳躍性極強,被注入了時間與空間,是杜甫詩歌風格沉郁頓挫的原因之一。“悠悠一千年,陳跡唯高臺”(《宋中十首》),高適描寫時間意象時用“千年”,時間被無限擴張,盡寫歷史的滄桑之變和對梁孝王不再現世的無限惋惜。“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早發白帝城》),李白此時剛被赦免,用“千里”和“一日”作對比,寫出自己放蕩不羈、心情舒暢的快意,僅僅一葉輕舟便駛過了千里水、穿過了萬重山,意象大開大合,包羅萬象。
從思想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玄學不斷發展。曹魏末期,阮籍的政治抒情組詩《詠懷八十二首》已經表現出道家思想的滲透,但還停留在《古詩十九首》的思想層面,沒有為“竹林七賢”提供出路。西晉時,經過不斷探討,向秀和郭象提出“名教即自然”(《難嵇叔夜養生論》)的理論,即自性論,核心思想為:想出世便隱居,想入仕便做官。經過情緒上、理論上的準備,東晉道家繼西漢初期后重新進入統治階層的視野,并成為世家門閥的主流思想。隨著時間推移以及社會變革,道家人格漸次成為中國人格的一部分。這使得中國文學有以下幾方面的轉變,為唐詩提供了思想基礎:
一是更加深刻的生命意識。楊景龍在《試論中國詩歌的時間生命主題》中提到,“有沒有時間意識標志著人的生命是否走出蒙昧狀態”,“時間意識的強弱標志著人的生命意識的覺醒程度”。魏晉以來,社會動亂,政權更迭,人的個體生命意識及自我思想開始覺醒,使得文學具有典型的亂世特點。錢穆先生在《國學概論》評價道:“魏晉南朝三百年學術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個人自我覺醒是已。”因此,詩歌中體現出自我憂患意識。
在此說明時,筆者借《古詩十九首》與兩晉的具有生命意識的時間意象來對比。東漢末年,朝政混亂,宦官與外戚交替干政,士族發起的兩次黨錮之禍皆以失敗告終。此時,詩人沒有道家核心的思維邏輯,徒有浩然正氣,因此詩歌中充斥著絕望之情,遂多以及時行樂為主題,如《驅車上東門》中的“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而在魏晉時期,隨著玄學的發展,隱逸之路的大門打開,詩人得以在文學創作中表達了曠達的心態。最為代表性的是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雖仍是及時行樂的思想內核,但在時間的描述上體現了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以滿足感官為目的的消磨時間,非東漢士族仕途失意的無可奈何,體現了魏晉時期儒道互補的思想形態。在唐詩中,李白被貶時高吟“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將進酒》),雖也是困境之嘆,卻在描述時光流逝時展現著磅礴氣勢,水天相接,一氣呵成,體現了詩人在困境時的豁達,仍然向上的積極,具有濃烈的自我生命意識。
二是以欣賞的眼光看待自然。《詩經》里的自然只是作為起興,重點還是抱負和理想,漢末的自然描寫死氣沉沉,沒有生機。隨著玄學發展,人們發現山川草木的蔥郁茂盛,逐漸意識到這并非是人力所能為的,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由此,詩人從自然中發現了一些人生意義。因此,宗白華評價“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世說新語〉與晉人之美》)。
以上玄學對文學產生的兩方面影響,使得唐人心態健康,富有彈性,詩的意象描寫更加清新可愛、自然流暢,有著鮮明的生命意識。崔顥登上黃鶴樓題下“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樓》),以想象中的黃鶴意象連接古今,朗朗上口的詩句,更耐后人咀嚼。白居易游覽石門澗感嘆“自從東晉后,無復人游歷。獨有秋澗聲,潺湲空旦夕”(《游石門澗》),時過境遷,只有秋日里山間的流水在不停息地緩慢流淌,詩句描寫如初生芙蓉,意象空靈純凈,讓人反復琢磨。
從描寫對象上,因為對自然的深刻體會,以及對語言局限性的認識,東晉時陶淵明詩歌的所詠之辭開始淡化,“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至南北朝才正式完成轉變。這是中國古詩的偉大革新,“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含蓄》)。在唐詩中,情感融入意象,詩以意象為中心,不再述說個體意志。因此,唐詩的意象細膩多情,以小見大。王昌齡表達對洛陽親人的思念,“一片冰心在玉壺”(《芙蓉樓送辛漸》),晶瑩剔透,感情豐沛細膩。王維進入深林,觀察到光斑“復照青苔上”(《鹿柴》),意象清新可愛,言外之意透出了高處枝繁葉茂,抒發了詩人的閑情逸致。在描寫時間時,“月落潮平是去時”(元稹《重贈》),“月落潮平”代表著時間周而復始,抒發詩人想象友人離去后的思念悲傷。李商隱在無題詩中表達對妻子的無限思念,“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無題》),自己的思念像春蠶吐絲一樣至死方休,像蠟燭一樣燃燒成灰才能止住眼淚。詩人通過春蠶和蠟燭這兩個意象來表達時間的難熬,以及自己不渝的真心,盡寫無限思念之情,叫人感同身受。
大開大合的寫作手法為唐人提供了開闊的視野,玄學的發展讓唐人重視自我生命和山川草木,言不盡意的發展讓唐人在意象上寄托情感。這使得唐詩在擁有宏大景象的同時,又兼具對自然細致的觀察,抒發了郁郁不得志的情感。視角開闊,意象飽滿,字里行間流露著蓬勃的朝氣、灑脫的氣象,這便是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所說的“盛唐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