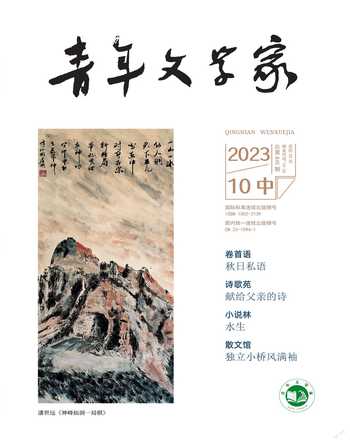約翰·福爾斯小說的敘事藝術研究
吳強
約翰·福爾斯的小說具有顯在的現代主義特征,因其敘事上超前的先鋒性而被稱為“動態的藝術家”。約翰·福爾斯對傳統現實主義技法的革新使其文學創作既具有高度的藝術性又具備暢銷的市場價值。約翰·福爾斯以敘事形式的變形和轉化為文本的敘事內容找尋到了恰切的形式,使小說的外部結構與內在肌理形成圓融的美學狀態,以自由的敘事狀態實現了對現實的觀照和對時空的哲性反思。
一、自由變換的敘事視角
盧伯克的敘事學理論揭示了視角在文本中的重要敘事功能,敘事視角的擇取,表征著隱含作者的內在情感立場,決定著讀者以怎樣的眼光和道德標準審視作品中的人物,如何獲取以及獲得怎樣的文本信息,因而敘事視角的擇取對文本的敘事效果具有巨大的影響作用。約翰·福爾斯小說中的敘事視角呈現出自由變換的特質,根據敘事內容的展示需要靈活地變換視角,使不同視角下的講述形成復調式的敘述,從而使文本產生多義性的特征。
約翰·福爾斯擅長以視角的切換揭示同個事物的不同面目,視角的轉化如同棱鏡般折射出不同的光線,揭示著真實本身所具有的豐富性。例如,在《收藏家》中,約翰·福爾斯的視角擇取就別有意味,小說共分為四個區間由交織穿插的雙重視角進行講述,不同敘事者的視角交替出現并操持著各自的敘事立場,使線性發展的故事情節衍生出多變的面貌和質地。小說先是以克雷戈的內聚焦第一人稱敘述講述了其對米蘭達的熾熱感情,這份熊熊燃燒的情感使他不自覺地向米蘭達的所在之處靠攏,并期望能將其永遠留在身邊。而第二部分的敘事則采取了米蘭達的內聚焦第一人稱敘事,以日記為載體向讀者毫無保留地敞開了人物的主觀心理空間,讓讀者了解到同克雷戈視角下的講述迥然不同的事實:克雷戈熱切的迷戀并未打動米蘭達的心,反而使她感到身陷囹圄。雙重視角下的講述呈現出各異甚至矛盾的面目,從而在文本中形成了富有張力的復調,多重視角下的敘事聲音在文本中回蕩,相互補充、相互質詢并形成互照,使讀者不得不依靠自己的道德判斷與信息分析來判斷事情的真相。而后,敘事視角又重歸克雷戈的掌控之下,他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痛訴米蘭達染上肺病后凄美死去的經過,將自己渲染成為失去愛人后“痛不欲生的失落者”,失掉所愛的苦楚甚至令他喪失了生存的意志。正當讀者為他的深情所打動,并將兩人的愛情悲劇視為命運的陰錯陽差時,結尾部分中的克雷戈卻重新發現了可供他投射深情的對象—美麗活潑的商品銷售員瑪麗安。至此,讀者才在復調的矛盾敘事中發現事情的真相,克雷戈所謂的“愛情”不過是為了遮蔽自己收藏癖的托詞,他對瑪麗安的執著僅是物化他者以實現自我滿足的外在表現。約翰·福爾斯有意地以多重視角完成故事的講述,同時在文本中懸置道德評判或價值標準,使小說具有開放性的廣場特征,使讀者能切身地參與進文本意義建構的審美過程。
而在《法國中尉的女人》中,約翰·福爾斯對視角切換的使用則更為純熟和圓潤,敘事者“我”在全知視角和限知視角之間不斷切換,有選擇地向讀者敞開或遮蔽信息,從而使小說中薩拉的形象變得撲朔迷離。在文本的敘述中,第三人稱的敘事者“我”以全知視角出現并統攝著文本,從各形各色人物的家世出身、人際往來到他們隱秘的情感關系、性格特征,似乎是無所不知的全能敘述者。在敘述故事的同時,“我”還大段地插入自己的議論與評說,在文本中表現出巨大的話語權力。然而,當涉及薩拉時,“我”的全知視角卻瞬間轉變為限制性的敘事視角,變得吞吞吐吐、語焉不詳,使讀者和主人公查爾斯一樣被濃重的謎團所吸引。全知視角與限知視角的互照使薩拉毫無疑問地成了小說中最獨特的存在,使薩拉不需要經過任何詞語的渲染即成為文本敘事聚焦的所在。敘事視角的轉換構成了奇特的迷宮,使讀者同主人公查爾斯般著迷地追尋著薩拉,試圖了解她復雜的身世、揭開她身份的謎底,在虛構與真實之間不斷地涉渡,只為了在文本的細枝末節中拼湊出完整的真相,從而在審美接受的過程中保持著高度的集中狀態。
敘事視角的自由變換使約翰·福爾斯的小說呈現出現代主義小說的多義性特征,不同視角下的講述形成了別有意義的互文,使文本本身具有敞開性與開放性,使文本意義的最終實現成為創作主體與接受客體在互動中完成的動態過程。視角的變換凸顯了約翰·福爾斯對敘事形式的駕馭能力,以其具有先鋒意義的敘事形式表現了作家出眾的創作才賦。
二、形式復雜的敘事結構
約翰·福爾斯的小說通常具有復雜的結構形式,作者善于通過編織復雜的敘事結構為小說制造出人意料的反轉,從而產生戲劇化的審美效果。約翰·福爾斯的小說因對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線性敘事結構的顛覆而充滿現代主義的先鋒性,由結構的繁復變形而制造的敘事迷宮,使讀者在對小說進行審美接受的過程中,不得不通過對結構形式的拆解來實現對文本的解讀,從而使他們的接受過程產生了有意味的延宕,造成了其審美接受過程的時延。
約翰·福爾斯擅于在小說中織構層層嵌套的套盒結構,不同的敘事層級相互疊加并套合,使小說形成了層次豐富的“劇中劇”式的結構形態。例如,《巫術師》所采取的是“故事套故事”的結構方式,表層敘事講述了出身于中產階級的青年尼古拉斯困惑于身份所帶來的安逸生活,及其隨之而來的巨大空虛感,在雙親因意外而離世之后前往希臘尋找內心真正的自我的經歷。約翰·福爾斯在尼古拉斯的自我尋找之旅中,嵌套了神秘富豪康奇斯的自敘傳式的講述,分段性地敷陳了其如何從逃離戰火的普通士兵搖身變為德康伯爵的承襲人,再到北極進行鳥類考察的傳奇經歷。此時,表層敘事中的主人公尼古拉斯隱秘地實現了聚焦的轉移,從敘事聚焦的客體變為了聚焦他者的主體,成為讀者實現視角代入的被動聆聽者。而后,文本實現了從表層敘事到深層故事的過渡,康奇斯以排演戲劇的形式幫助尼古拉斯實現對“自我”的確證,全景式的沉浸戲劇漸漸使尼古拉斯失去了對現實和虛幻的辨別能力,他愛上了戲劇中的演員霍爾慕斯小姐,卻無法辨別她的愛來源于自身真實的情感,還是角色在服從劇本情節的發展理路。康奇斯所排演的戲劇作為文本的深層故事,同表層敘事之間構成了奇異的“劇中劇”的關系,他的本意并非擾亂尼古拉斯對真實的感知,而是為了使其理解“存在所具有的可靠性”,從而實現對真正自我的清晰認知。尼古拉斯從戲劇所制造的迷宮中的覺醒表征著其自我認知的明晰,人物對于“存在”合理性的認同也標識其思想演化進程終于抵達了可以自洽的終點。嵌套式的敘事結構使尼古拉斯的自我尋找之旅充滿了奇幻色彩,背離了傳統現實主義的敘事常規,從而使文本產生了強烈的存在主義哲學底色。
而在《法國中尉的女人》中,這種嵌套式的復合結構被運用得更為純熟。文本的表層故事講述了倫敦紳士查爾斯對薩拉的尋找過程,充滿了傳統騎士文學的理想主義氣息,當讀者將文本“誤讀”為現代騎士對淪落在萊姆鎮的流言蜚語中的少女進行拯救時,約翰·福爾斯卻又引入了小說的深層敘事,揭示了“被拯救”的薩拉實則并不需要被拯救的事實,她主動地選擇了讓自己成為法國中尉的女人并通過這個虛假身份獲得了真正的自由,這種“消極優勢”的獲得使薩拉得以有意識地操縱并誤導整個小鎮的居民,以便讓自己從維多利亞時期的傳統道德秩序中脫身,成為真正意義的現代自由女性。深層敘事對表層故事的顛覆令讀者的審美驚異得到了放大,戲劇化的情節陡轉使小說取得了波瀾起伏的敘事效果。同時,約翰·福爾斯有意在嵌套式的結構中增加結構形式的變體。在小說的結尾處,故事的外部結構衍生出了新的“枝節”,多元開放結局的呈現使小說在收束階段形成了橘瓣式的并置結構。與薩拉短暫地交契,隨后又與之分離的查爾斯,同歐內斯蒂娜成婚,并獲得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隨后即被隱含作者指出,這只不過是查爾斯的一段空中樓閣般的想象。接著,隱含作者講述了屬于兩人的另一重結局,薩拉離去后查爾斯也因毀壞婚約而離開英國謀生,在美國同薩拉重逢后,才得知他們已經育有一個可愛的女兒。然而,當故事的畫面定格在幸福的時刻后,原本重新隱沒在文本中的隱含作者卻再次登場,并“將手表倒撥了15分鐘”,主人公們幸福的場景隨即破裂,薩拉依然不愿重蹈維多利亞時期傳統女性的既定命運軌跡,查爾斯在失望中頹然離去,卻感受到自己已經煥然一新,重獲新生。多元結局的同時敞開予以文本以開放式的結構特征,不同的可能性被統攝在同個主題下相互并列,使時空的復雜性得以具象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使文本因敘事結構的復雜而形成了無窮的魅力。
敘事結構的復雜形式使約翰·福爾斯的文學創作具有現代性的先鋒特征,它所指向的是與傳統現實主義文學迥然不同的審美范式,成為把握繁雜的現實的有效方式。小說中敘事結構的多變形態與豐富的敘事層級在文本中形成了余韻悠長的復調,時刻拓展著讀者想象力的邊界。
三、寓意豐富的互文手法
互文是約翰·福爾斯小說中常見的敘事技法,通過吸收和轉化其他文本并對其進行重述和再創作并由此形成新的文本,使兩個故事之間生成豐富的指涉關系,向讀者展示了文本建構的想象過程。不同文本之間的交匯產生了豐富的對話性,通過引用、戲擬、模仿,以及暗示等手法,在本無關聯性的文本之間建立聯結,使小說的闡釋空間得到了充分的拓延。
戲擬是約翰·福爾斯小說中經典的互文手法,《收藏家》同莎士比亞的戲劇《暴風雨》之間具有鮮明的模仿和轉換關系,兩個文本的女主人公共享著“米蘭達”的命名,她們同樣美麗而頑強,以頑強的意志力守衛著自己的靈魂的純潔。而《收藏家》中的米蘭達自述的日記中始終以《暴風雨》中的人物“凱列班”作為克雷戈的代稱,這個粗野而可怕的形象正隱喻著克雷戈真情流露的外衣下蠻橫自私的靈魂。同時,克雷戈對米蘭達非理性的愛情也在文本中構成了“暴風雨”式的情緒氛圍,文本之間的互文關系使“暴風雨”成為《收藏家》中人物之間深沉而暴烈的情感涌動的外在表征,成為讀者理解小說敘事的一條通幽曲徑。故事結構模式與人物形象的高度相似使小說《收藏家》可以被視為劇作《暴風雨》的現代轉化,兩重文本之間相互指涉的關系使《收藏家》不再僅被理解為“愛而不得”的俗套故事,而是通過對古典戲劇的再創作和再演繹獲得了浪漫的詩性,得以被置放在更嚴肅的語境中加以探討,并從中發掘出文本對人性的深邃探問。
而在《法國中尉的女人》中,約翰·福爾斯則通過引用不同文體的作品的言語片段來為小說與其他文本建立互文關系。與情節無關的語段的插入和拼貼,既造成了讀者審美閱讀過程的延宕,也使他們在引用的文段中獲得有關情節發展的暗示。例如,小說的首個章節便引入了哈代詩作中的名篇《謎》:“煢煢孤影,日馳天遙。”在海邊遠眺的神秘女人薩拉正是這樣一個煢煢孑立的孤獨者形象,而她謎一樣的氣質和神態不僅深深地吸引了主人公查爾斯關注的視線,也在讀者心中投下了巨大的疑影。整部小說正是縈繞著薩拉這個美麗而神秘的“謎”團開始織構文本,對薩拉真實身份的找尋構成了文本的經緯和線索。詩歌同小說之間因相互指涉和隱喻形成了奇妙的互文關系。隨著讀者對文本的深入越深,對開篇這首“平平無奇的小詩”的敘事功能及其隱喻作用就會越感心驚。而第30章中,約翰·福爾斯則別有用意地引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大段論述,以此來暗示波爾塔尼太太對待薩拉的方式。她虛偽的本性和溫情背后的冷漠使薩拉感到鄙夷和恐怖,并最終以反抗的形式重新獲取了自我的主導權,重獲了自由。這些引文同小說的章節所具有的隱喻關系,使它們彼此之間形成了有意味的互文,使多重文本在小說中自由地交匯,形成了極為寬廣的意義闡釋空間。互文手法的應用使約翰·福爾斯的小說敞開了更寬廣的闡釋可能,令其可以通過對其他文本的調用實現自身的敘事目的,在文本空間的互通間實現敘述的自由。
約翰·福爾斯小說的敘事形式具有鮮明的實驗特征,他打破了傳統現實主義小說封閉的審美范式,使現代主義的美學原則逐漸崛起,揭示了文本形式所具有的獨立的審美意義與敘事功能。約翰·福爾斯小說中自由變換的敘事視角、復雜多變的形式結構和具有豐富寓意的互文手法,從敘事的層面深刻地啟迪了當代文學的創作,產生了難以忽視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