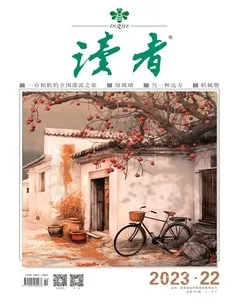黃順安
☉周志文
黃順安的母親在我家附近的菜市場里賣水果,她與我認識是因為妻子偶爾到她那里買水果。十年前,黃順安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由母親牽著來到我家,他母親十分懇摯地請求我協助黃順安。
我陪妻子買菜時,會經過她的攤子,但我不曾和她交談過,她帶著孩子來尋求一個陌生人的協助,自然不會是小事,我心里想。
我原先以為是多么困難的事。但一交談,我才知道不是多么困難,原來她帶孩子來,是想讓我“教”孩子扎一個燈籠。因為小學老師規定,每個人要交一個自己做的燈籠,作品將算作勞作課的成績。我小時候生長在鄉村,雖然不能像孔子所說的“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但是手工之類的事,大致上還難不倒我。我問黃順安:“老師要你們做哪一種燈籠?是不是有規定的式樣?”但無論我怎么問,都得不到答案,他的母親看著他,直叫他“說呀、說呀”,但黃順安不敢開口,她其實也不怎么敢直接跟我說話。她看著妻子說:“黃順安的老師說,做得越漂亮分數越高。”
我答應他們母子,教黃順安做一個漂亮的燈籠。我們約好,第二天晚上黃順安把學校發的材料帶來我家,我們視材料而定,“設計”一個燈籠,務必出奇制勝。母子歡喜離去。
第二天晚上,黃順安準時來按我家門鈴,他母親也跟在后面。我看到黃順安帶來的如竹簽般細的竹條和玻璃紙,知道根本無法扎一個難度較高的如兔子、金魚之類的燈籠,只能做一個簡單的小燈籠。我告訴黃順安,把六根等長的竹條,扎成兩個等邊三角形,兩個三角形底和頂相疊,就成了一個六角星,我們就來做一個六角星的燈籠吧,黃順安說好,于是我們就開始工作。但黃順安一點都不懂如何把竹條扎成三角形,更不用說扎成六角星了。這個燈籠從裁截竹條、捆扎直至貼上玻璃紙,完全是我一個人在做。黃順安坐在我旁邊,看一下我,看一下別的地方;他的母親,則是一徑無言而有些羞赧地笑著。

黃順安提著新做好的燈籠,他母親則是千恩萬謝。他們離開后,我問妻子,他們怎么知道我會做燈籠?妻子也不明所以。第二天,妻子從菜市場回來告訴我,黃順安的母親告訴她,黃順安的老師讓黃順安做燈籠,黃順安不會做。既然是老師讓學生做燈籠,那么老師一定會做。黃順安的母親對妻子說:“你先生不是做老師的嗎?”于是,她就來拜托我,多么理直氣壯的理由呀!
隔了約莫一個月,我路過她攤子的時候問她,黃順安的燈籠得了幾分?她說分數她不知道,但燈籠被學校留下來展覽還沒發下來,證明成績尚且不壞。她說黃順安對“他”的作品并不滿意,據黃順安說他的幾個同學做了裝有輪子的燈籠,還可以推著在路上走。“我看老師你替他做的已經不錯了,”她笑著對我說,“我們家黃順安,真是歪嘴雞還圖整粒米吃呢!”
我和妻子買菜的時候,盡量避免走過她的攤子。如果經過就不好意思不向她買些水果,而她總在稱好算好價錢之后,又塞進一些水果,這樣的人情,在我身上已形成一些壓力。后來我們才知道她丈夫在做鋪柏油的工作,個子矮胖,面色黧黑,偶爾下雨天不外出工作的時候,會幫她賣水果。他總在旁邊幫著裝袋,嘴里嚼著東西,似乎從來沒說過一句話。
就這樣,十年過去了。菜市場依舊是菜市場,嘈雜混亂,每天充滿新鮮,又堆積著同樣的污垢。黃順安上初中的時候,我見過他一面,那時他穿著藏青色的夾克制服,站在水果攤邊上,已經比母親高了。我和他們母子寒暄了幾句,沒說什么具體的話,這是我最后一次見到黃順安。
那天,我到郵局寄掛號信,回來的時候經過菜市場。中午時分,陽光從雜亂的布棚之間垂直射下,和四周黑沉沉的背景相對照,形成一種詭異而特殊的氣氛。菜市場已經沒什么人了,黃順安的母親在收拾攤子,笑著說好久沒見我了,我也說是,隨即問她黃順安現在在哪里上學。“他啊,已經不讀了,”她說,“去年高職畢業,現在在一家冷凍食品廠當工人。”
“那很好呀,可以賺錢孝敬你啦。”我說。
“有什么好?他自己花都不夠呢。”她沉吟了一下說,“還是你們做老師的好,賺得比他多,又有寒暑假。”
我想起十年前,她牽著黃順安的手,羞赧地按我家門鈴的樣子。在她心中,老師這個職業,包含了多少我們身為老師的人所不了解的意義啊。可能有一段時間,她曾期望黃順安做一個既賺錢、又有寒暑假,還有許多人所沒有的才能的老師吧,這些才能,甚至包括會扎紙燈籠。
“你沒有怎么樣吧?”
我一定站在那里太久。我跟她說沒有怎么樣,然后走回家去。我,不只是我,還有世界都沒有怎么樣。十年已過,如果沒有過去相對照,整個世界的一切,都好像靜止著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