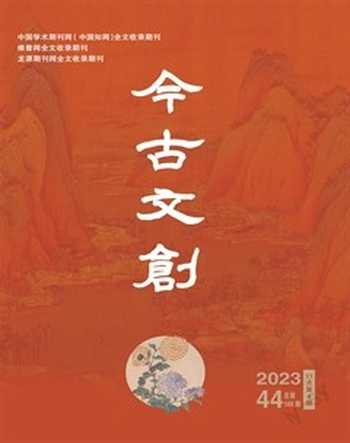塵埃中綻放的花
【摘要】汪曾祺在《大淖記事》中創造了一個理想化的大淖世界。在這里,小人物雖然面對著沉重的生活壓力,但依然追求著自由,展現出生生不息、堅韌不拔的生命力。從結構到審美內涵,小說浸透著濃厚的生命美學意蘊,又包含了作者對文明與生命關系的反思。
【關鍵詞】汪曾祺;《大淖記事》 ;生命美學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標號】2096-8264(2023)44-005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4.017
《大淖記事》創作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正值中國新時期文學起步之際,發表之初就以獨樹一幟的風格吸引了眾多關注。作品描述了大淖優美的自然環境,講述了錫匠十一子與巧云的愛情故事,刻畫了一批生動鮮活的大淖居民形象,歌頌了健康向上的人性之美。從結構設計到審美內涵,它以詩意的語言創造了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民間世界,處處浸透著濃厚的生命美學意蘊,又暗含著對文明發展的反思。
一、美的“留白”:環境塑造
汪曾祺說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 [1] 《大淖記事》可謂這種思想的集中體現。
《大淖記事》全篇分為六節,開篇便花費筆墨交代“大淖”之名的由來,接下來的三節全部用來描繪大淖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直到第四節主要人物才正式出場。
自由和自然是大淖之美的核心。大淖是“一片大水。說是湖泊,似還不夠”[2],春天“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紅色的蘆芽和灰綠色的蔞蒿”;夏天“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紅色的蘆芽和灰綠色的蔞蒿”;秋天,人們把茅草“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頂上”;“冬天,下雪,這里總比別處先白”。“大淖指的是這片水,也指水邊的陸地”。除了湖中諸景,生活在這里的人們也像大淖的四季一樣自然地生活著,這些形形色色的居民組成了大淖的人文景觀:賣紫蘿卜的、賣風菱的、賣山里紅的、賣熟藕的,“像一些候鳥,來去都有定時”,過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還有挑著錫匠擔子,走街串巷的錫匠們,“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靠肩膀吃飯”的挑夫。這是一個充滿詩意的世界,一切都在按自然的方式自由生長。
雖然文字間充滿了對自然之美的向往,但作品并沒有走向脫離現實的境地,相反,大淖的人文環境塑造帶著濃厚的生活氣息。小販們“大都不是本地人”,他們每天早出晚歸,點著“半干不濕”的柴草,還要隨著季節的變換遷移,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錫匠們恪守著嚴格的紀律,甚至需要習武防身。挑夫吃著粗糙的飯菜:“青菜小魚、臭豆腐、腌辣椒”;而他們淘氣的孩子們則收集蘆柴,“從鄉下人的草擔上猛力拽出一把,拔腿就溜”,這是多么有童趣的場景,但看似輕松愉快的他們也早早走出了童年:“十三四歲的孩子就開始挑了”;女人們“像男人一樣的掙錢,走相、坐相也像男人”,甚至“也用男人罵人的話罵人”。大淖居民做著繁重的體力勞動,可以說生活在社會邊緣,如詩的風景也并不能減輕他們沉重的生活。倘若用文明的眼光去審視這里的生活,甚至能夠看到野蠻和粗俗的影子。作品并沒有因為對和諧的追求而淡化這份真實的沉重,也沒有美化普通勞動者的卑微生活;相反,他細致入微地刻畫出這些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唯恐讀者不能形成一個明白的印象。
美的塑造正是在真實的生活背景之下展開的:這里的女人“發髻的一側總要插一點什么東西”,或者是“清明插一個柳球”,或者是“端午插一叢艾葉”“一朵梔子”“一朵夾竹桃”,沒有鮮花時插“一朵大紅剪絨花”;她們“挑著一擔擔紫紅的荸薺、碧綠的菱角、雪白的連枝藕,走成一長串,風擺柳搖似的嚓嚓地走過,好看的很”。在生活的壓力之下,處在社會下層的大淖人每日為生計奔波,但在這樣的生活中,他們也沒忘記追求美好。他們對生活抱持著本能的熱愛,充滿了健康的活力,在生活的塵土中處處顯露出高貴的人性之美。
海德格爾說過:“我們是植物,不管我們愿意承認與否,我們這種植物必須連根從大地中成長起來,方能在天穹中開花結果。”[3]大淖居民身處卑微卻不忘美好,在生活的重擔下仍保持著熱愛,時時刻刻以微小的“美”追求著一種無意的詩意。小說的自然環境正是在“自然——生活——美(自然)”的往而復返中塑造完成的:真實生活的沉重不會消解生命之美。
這一部分在全文之中作為主要情節的“留白”存在著。宗白華認為美的塑造“在于能空,對物象造成距離,使自己不沾不滯,物象得以孤立絕緣,自成境界。”在這部作品中,環境描寫所占篇幅與主要情節所占的篇幅幾乎一致。在某種意義上說,大量的環境描寫正是主要情節部分的“留白”。作者所要建構的,與其說是一個限定在開端、發展、高潮、結局框架中的傳統故事,毋寧說是一個富有生命力的“世界”。結構上的松散恰恰保證了審美所需的距離感。
在閱讀過程中,大家也能清楚地感受到這樣的設計帶來的結果:故事和人物似乎都是由層層遞進的環境描寫所推演出來的。在這里,環境塑造不再是隸屬于人物和情節的棋子,二者成了相互滲透,不可分離的整體;結構換句話說,人物是扎根在世界之中的。對于這樣的設計,作者在《〈大淖記事〉是怎樣寫出來的》一文中提到:“我這樣寫,自己是意識到的。所以一開頭著重寫環境,是因為‘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樣’,‘這里的人也不一樣,他們的生活,他們的風俗,他們的是非標準、倫理道德觀念和街里的穿長衣念過“子曰”的人完全不同’”。從這里可以看出,松散的結構正是作者是有意識安排的結果,其目的正是為了構建一個獨特的“世界”,無所謂失衡。人物是活動在世界中的,情節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為這一切賦予合理性,讀者在閱讀中隨時可以意識到這樣一點:“大淖”這個虛構的世界活生生地存在著,包容著一切,在人物和情節的面前也并不處于從屬地位。這就是如前所說的“留白”的效果,它使小說別有一種空靈之美,在主要情節之外仿佛還有無限的空間、無限的故事。正是“留白”讓這個世界擁有了無限豐富的生命力,這種豐富性在主要情節展開后依然作為一種情節外的“空白”持續在場。“‘空’可以使對象呈現為孤立絕緣的‘美’的對象,而且能顯現對象的本來面目。”在背景的無限空間和真實生命力之中,主要情節作為這個世界中的一件事發生了,這樣的安排在一開始便具有賦予真實性和吸引讀者審美注意的雙重意義。
二、美的追求:自由解放
十一子與巧云的愛情構成了小說的主要情節,其審美的核心正是美的終極理想:自由解放。
大淖人的愛情觀是自由的。作者在第三節結尾處特地拿出一整段來描寫大淖人對待男女愛情的態度:婚嫁“極少明媒正娶”,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而“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還是惱,只有一個標準:情愿”。
婚嫁“極少明媒正娶”,愛情似乎只有一個標準:“情愿”。對于禮法教條來說,這是背離,難怪街里的人要說這里“風氣不好”了。不過作者還不滿足于此,他立刻反問一句:“到底是哪里的風氣更好一些呢?難說”。大淖就是這樣一個不為世俗所容的地方,它因為自然而“原始”,因為自由而“野蠻”,又因為自然和自由而富有生命力。
這種自由寄托在兩位主人公身上,可以說,他們是審美理想的化身。十一子長得“挺拔廝稱,肩寬腰細,唇紅齒白,濃眉大眼,頭戴這遮陽草帽,青鞋凈襪,全身衣服整齊合體”,“天熱的時候,敞開衣扣,露出扇面也似的胸膛,五寸寬的雪白的板帶煞得很緊”,“走起路來,高臺腳,輕著地,麻溜利索”,不愧為一表人才。每逢十一子唱戲,“附近的姑娘媳婦都擠過來看——聽”。巧云則是“瓜子臉,一邊有個很深的酒窩”,“眉毛黑如鴉翅,長入鬢角”,“眼睛有點吊,是一雙鳳眼”。每逢她去看戲,人們都“不是在看戲,是看她”。
十一子與巧云可謂是天作地設的一對。巧云落水,十一子救了她。接著,沒有海誓山盟,也沒有物質考量,甚至沒有一個明確的開始信號,兩人的愛情就這樣自然而然地萌發了,真誠又樸素。彼時,封建禮教依然控制著人們的日常生活,自由的愛情難能可貴。追求自由的人不是付出生命的代價,就是曲終人散,空留一場遺憾。但在大淖,十一子和巧云的愛情卻生長開來。究其根本,這里的人們認為你情我愿的愛是理所應當的。
審美理想正是借由十一子和巧云的愛情故事集中展現的。擺脫束縛、追求自由的情結貫穿了巧云和十一子愛情的全程。他們一個是錫匠里的“金鳳凰”,另一個是挑夫黃海蛟家的一朵花,兩人情投意合,后來遭到保安隊劉號長的阻撓:十一子被打成重傷。在這樣一個悲劇里,小說歌頌的人性的光輝得到了升華。巧云沒有拋棄十一子,而是“沒有經過太多考慮”,拿起扁擔“就去挑擔掙‘活錢’去了”。在巧云看來,這是無須多慮的選擇,而我們卻能夠從巧云的堅守上看到一種光輝的生命力,那是一種未經雕琢的,甚至近乎原始的健康與活力。作者以這個遠離禮教束縛的純凈鄉野,向我們展示了自然人性那自由自在又無比堅強的本色。
愛情是人類最美好的情感,是生命中的自由和解放的集中展現。只有大淖能孕生出這樣的愛情,雖然結局并不美滿:十一子重傷,巧云的父親臥病在床,巧云不得不去當挑夫,扛起整個家。這是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結局,但作者卻留下了這樣的結尾為整個故事收尾:
十一子的傷會好嗎?
會。
也許是覺得一個“會”不足以承擔他心中對于人性之美的贊嘆,作者又以極為肯定的語氣強調道:“當然會”。
在主要情節中,除了十一子和巧云兩位主人公,作者還塑造了一批自覺幫助主人公的平凡居民。悲劇發生后,他們迫使縣政府懲罰了造成悲劇的劉號長。可以說,居民的存在正是對自由追求的側面肯定:他們團結起來保衛十一子和巧云,保衛大淖的生活。不過,真的是悲劇喚醒了大淖居民嗎?通讀全篇后,不難發現,也許悲劇只是給他們提供了機會,而真正驅動這一切的是他們身上與主人公一樣的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生命活力。這種生命力沒受道德律令的教化,沒有子曰詩云的支撐,大淖人只是覺得應該伸出援手,只是覺得人與人之間應該有同情和關心,只是覺得追求自由的十一子和巧云理應追求,就像他們認為愛情該以“情愿”為標準,是不需要解釋的。追求自由、捍衛自由的崇高斗爭只是在作者淡淡的文字中自然而然地進行著,卻展現了生命不竭,追求不止的美的理想。宗白華認為,中國傳統美學不同于西方美學之處就在于其“往復、來回、周而復始、無往不復”[4]的觀念,生命的推移隨著宇宙的律動展現不竭的美。小說從大淖出發,經過主要情節的渲染,又回到大淖的居民、回到大淖的生活之中,在結尾處完成了整篇小說的生命之美的升華。
在大淖,苦難沒有扭曲人性,因此也沒有塑造人性,它更像一面鏡子,把平日埋藏在平凡生活中的美好人性照了出來。這種獨特的表現方式,也許正是作者“恬靜、淡泊”的美學追求在小說細節上的展現。不在平凡中泯滅,也不畏懼苦難的威嚇,始終保有健康、健全的、活力四射的人性,這樣的大淖住民,也許正是作者理想人性的例子。究其根本,健康人性的本質正是追求自由,不受約束,熱愛美好,人與人之間保持真誠和善良。
“《大淖記事》寫的是一個愛情故事。但它不是一般的愛情悲劇,沒有一把淚,一滴血。”[5]大淖的生活是殘酷的,作者不否定,但有意不去寫它的血和淚,而是在悲劇的泥沼中留下了一個肯定的呼喚作為結尾,這正是對生生不息的自由的強調:雖然身處塵埃依然追求著開出美麗的花。
三、美的內涵:生生不息
作者曾說:“《大淖記事》等幾篇東西就是擺脫長期捆綁的情況下寫出來的,從這幾篇小說里可以感覺出我鳶飛魚躍似的快樂”[6]。鳶飛魚躍的快樂是一種沒有外在的壓抑、自由隨意的快樂。大淖正是這種 “快樂”的結晶,一個理想化的世界。
生活在大淖的人們是平凡的:挑夫、錫匠、小販……但這些卑微的人卻以他們普通的日子進行著一場純凈的遠征,在無意中展現著不屈的生命活力。小說以舒緩優美的文字點染出明麗的人情:這里沒有苦大仇深的斗爭,也沒有海誓山盟的愛情,一切都在平白如水的文字中前進。擺脫拘束,崇尚自然,追求自由,這些巨大的主題在小說中并沒有伴隨著刻骨銘心的戰斗和流血,而是以某種自然而然的狀態融入了大淖人的生活中。自由是本應如此的,愛情是應該追求的,個性就是自然,是從來如此的。作者曾說過:“我們當然是需要有戰斗性的……引起療救的注意的悲壯宏偉的作品”,但“我的作品不是”,“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7]。
這種“健康的人性”體現在貫穿整部小說的生命力中。大淖的居民不是哲學家,不是知識分子,他們只是普通的下層人物,他們追求自由與解放也不是經受扭曲、壓迫后的覺醒,而是一種自然狀態的保持。他們的生活與作為自然環境的大淖緊密相連,富有天人合一的活力與生命力。誠然,大淖并非沒有斗爭和壓迫,只是那種生生不息的東西并不是歷經磨難的靈魂,而是一個個平凡的人;他們也不是為了明確的目標和未曾擁有的東西而戰,只是在保衛自然而然的生活狀態。比起崇高的話題,這種斗爭也許只能說是一種不自覺的追求,卻在不經意間展現出不屈的生命力。大淖人沒有血海深仇,生生不息的意志與自由的追求早已是自然狀態,是不需要特意提及的。“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風俗, 他們的是非標準、倫理道德觀念和街里的穿長衣念過‘子曰’的人完全不同。”他們也許說不出道理,但已深得精髓。
不息的生命力又表現在大淖居民的生活狀態里。宗白華提到生命觀念時說過:“中國人……對生命的態度卻不是正視的抗衡,緊張的對立,而是縱身大化,與物推移”[4]。大淖居民的生活態度可以概括為平淡。他們順應自然變遷的節奏,沒有過多的欲望。但這并非麻木,恰如小說給出的解釋:這只能歸結于“他們的生活,他們的風俗,他們的是非標準、倫理道德觀念和街里的穿長衣念過‘子曰’的人完全不同”。而在這種自然的生活狀態之下的正是堅韌不屈的生命力:他們尊重自由愛情,不看重制度化的倫理道德,為了保衛自己的生活能趕走保安隊,甚至能迫使縣政府講和。斗爭是突發的,不會扼殺生命的力量,平淡才會。斗爭能激發人們追求美好的決心,塑造出崇高和偉大;平淡是長久的,會逐漸消磨人性,讓旺盛的活力變成冷漠。大淖人的生活恰恰是平淡的,連沉重也是,但他們以他們的行動證明,平淡從來沒有消磨掉他們的力量。在瑣碎和卑微中保持著樂觀純真的活力,又能迸發出追求美好的堅韌力量,這正是不息的生命之美的內涵。
四、文明與生命的反思
作品以其詩意的語言和巧妙的結構塑造了富有生命力的大淖。大淖的居民尊重大淖,遠離“文明”的他們過著幾乎自在自為的生活,展現著生生不息,堅韌頑強,純真樸素的生命之美。但大淖也是原始而粗糙的,在這里,無論人們的生活態度還是生活方式都透露出一種難為世俗所容的色彩。顯然,作者塑造出這樣一個理想的世界或多或少是為了與所謂“文明”世界相對照的。雖然作品平淡如水,但它背后所體現的問題卻值得深思:文明是否該引起更多的懷疑和反思,生命在文明之前究竟應該局于何處?
文明是以“人”為基礎的,盡管它的前進伴隨著人的扭曲;文明還是一種約束,但這種約束是不為人所控制的:它可以既阻擋愚昧的利劍,又捆綁人性的高貴。
通讀作品不難看出,作者所說的健康人性可以等同于某種理想的人性,或者說純粹的人性,它沒有被文明戴上猶豫的枷鎖,是自由而美好的。大淖居民,他們沒有對于自由的深入思考,甚至沒有這種能力,也不覺得有必要;他們的真純和善良不是源自修養,而是一種天生攜帶的“照例”的想法。追求自由,追求美,追求善良已經融化到了他們的生活中,變成了無須多慮的行動。就像這篇小說,人物與背景有機地融合在一起,無法分離。
作品成功地塑造出十一子、巧云和一大批普通人的形象,在他們的一舉一動中展現出對自由健康的人性的追求,同時隱含著一種若有若無的反思:文明在遮蓋所謂的“野蠻”的同時,是否也遮蓋了“人” ?面對大淖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態度,初看之下有些難以理解,甚至有些厭惡:這不是赤裸裸的原始嗎,這不是純粹的落后嗎?但細讀起來,它卻引人反思,到底什么是文明,文明又是為了什么?為什么沒有文明的地方卻保留了更加純粹的人性,為什么大淖人在枯淡的生活中卻活力十足?是否過快的前進扭曲了人本來擁有的東西,而那種東西本來是“文明”應該帶來的?
這樣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要帶上某種“反文明”的色彩,或者全盤反對文明進步,神化古代生活,或者不假思索地歌頌文明,接受文明所帶來的一切:這兩種傾向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片面性的危害。文明的前進保障了人類生命的延續,同時又扭曲自然的人,迫使個體的人喪失生命活力。
作品在那個時代給了跑步前進的人們一記柔軟的針刺,它所提出的問題現在看來猶有余威:生命與文明的關系究竟是什么?大淖具有“街里”所沒有的生命力,這里的一切都是自然的,是美的,是自由蓬勃的。孰優孰劣,至少作者的觀點不言而喻。如今,在現代化進程快速推進,數字技術日新月異,以人為本、為了人民的觀念也在不斷健全,重新思考上世紀末所提出的這一問題,對深刻認識發展與人的關系,乃至對社會未來的走向似乎依然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汪曾祺.汪曾祺自選集[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2]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說選[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2.
[3](德)海德格爾.海德格爾文集·講話與生平證詞(1910—1976)[M].孫周興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4]宗白華.宗白華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5]凌宇.是詩?是畫?——讀汪曾祺的《大淖記事》[J]. 讀書,1981,(11).
[6]汪曾祺.汪曾祺小品[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2.
[7]汪曾祺.晚翠文談新編[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 1988.
作者簡介:
孫小凡,男,山東濟南人,山東師范大學2021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