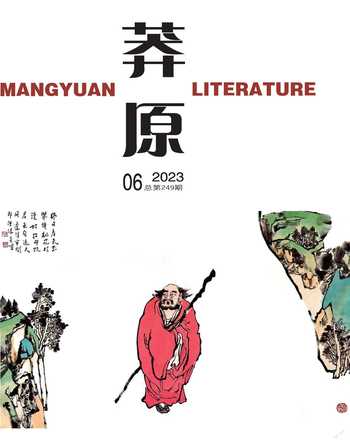召喚存在 守望鄉(xiāng)愁
楊文臣
劉慶邦的《響器》《遍地白花》兩部短篇,是小說,也是詩——不是體裁意義上的詩,而是海德格爾意義上的詩,是對存在的召喚和對鄉(xiāng)愁的守望。
藝術:存在的敞開與召喚
劉慶邦對《響器》《遍地白花》非常珍愛,說他自己也經(jīng)常讀,而且讀的時候還很感動。[1]兩部作品講述的都是藝術的故事——不是圍繞藝術發(fā)生的故事,那個并不重要,而是關于藝術本身的故事,是對藝術之為藝術的言說。劉慶邦談到《響器》時曾說,“這里面,故事可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味道,是音樂的自然性。看這個小說,好比你看到一棵樹,你只看到滿樹繁花,而不在意枝干。”[2]
藝術的本質(zhì)是什么?海德格爾告訴我們,藝術是藝術家和藝術作品的本源,它使藝術家成為藝術家,使藝術作品成為藝術作品。藝術不是某個存在者,諸如某種屬性、某種制度,而是存在之真理的自行置入,是存在者之存在的敞開,“(藝術)在存在者之間打開了一方敞開之地,在此敞開之地的敞開性中,一切存在遂有迥然不同之儀態(tài)。”[3]凡·高的《農(nóng)鞋》之所以是藝術,在于它敞開了農(nóng)婦的世界,將農(nóng)婦置于大地無聲的召喚之中:勞作的艱辛、收獲的喜悅、四季的輪轉(zhuǎn)、人世的榮枯、生之歡欣與死之戰(zhàn)栗……
《響器》中的音樂就是這樣的藝術,是可以發(fā)出召喚的大地之聲。海德格爾把人喚作“終有一死者”,響器就是給死者送行的音樂。在樂聲中,有漫天紅霞,有皚皚白雪,有狂風呼嘯,有暴雨如傾,有紛至沓來的天災人禍,有撲之不滅的生命之火,有相逢把酒且高歌,有訣別無語話凄涼……人類的苦難、憂傷、企望和生生死死,都被召喚而來,存在入于本質(zhì),一個純一的、親密無間的世界展開,逝者安然回歸大地的懷抱。
《遍地白花》中女畫家的畫,也是這樣的藝術。那座古舊的門樓子,那棵老鬼柳子樹,那臺廢棄的碾盤,還有那輛快要散架的太平車,如同凡·高的 《農(nóng)鞋》一樣,原來只是純?nèi)灰晃铮谧骷液团嫾业墓P下,它們打開了一段段塵封的歲月,敞開了一個個起滅無常的世界。這樣的藝術,會召喚我們進入其中,“就像是一個神話般的世界,讓人一看就不知不覺走進去了。”
藝術敞開的那個世界,就是終有一死者的存在,那是一種“共在”,是天地神人四方游戲,是一切存在物的相互允諾和守護,是蕓蕓眾生此呼彼應的圓舞之境。在響器的統(tǒng)攝下,悲痛不再只是屬于逝者一家,而是“成為全人類共享的幸福的悲痛”,人們此刻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寄身天地間,同悲萬古塵。畫上的老人,也不再只是房東的公公,他也是小扣子的祖父,是所有人的祖父,深深的皺紋鐫刻了世間所有的艱辛與滄桑,平靜的目光含蘊了世間所有的良善與悲憫。
在日常狀態(tài)下,存在自行隱匿,唯有追問和運思,才能將其帶入一種無蔽狀態(tài)。也就是說,存在永遠不屬于日常狀態(tài),所以,那些如草木般生長在大地上的村民,并不置身于存在的光亮之中,他們也需要被召喚。高妮和小扣子,都在藝術中接受了召喚,他們因而變得柔軟和慈悲,有了神性的光輝。后期的海德格爾把存在喚作“故鄉(xiāng)”,它并不就是我們的出生之地,不是我們曾在的某個物理時空,它只在追問和運思時才會進入我們的視野。所以,海德格爾稱人類為“異鄉(xiāng)人”,即便你從未遠行。女畫家是異鄉(xiāng)人,一次次在追憶中回歸那個遍地白花的夢中故鄉(xiāng);小扣子也是異鄉(xiāng)人,因為女畫家的引領,他才開始緬懷祖父,才開始感應草木之魂,那片遍地白花的土地才終成故鄉(xiāng),“把小扣子感動得都快要哭了”。
按照海德格爾的理論,藝術是藝術家的本源,不是藝術家占有藝術,而是藝術居有藝術家,借藝術家開顯存在。“一首詩的偉大正在于:它能夠掩蓋詩人這個人和詩人的名字。”[4]那張“有點可惜”的照片,其實準確地抓住了響器藝術的本質(zhì):它不是個體的聲音,而是整個族類的聲音,是生命的吶喊,是大地的悲鳴。作為存在的真理,藝術是非個人化的,既召喚觀者也召喚藝術家。這就可以解釋,何以劉慶邦一次次閱讀這兩部作品,入于其中且感動不已。
詩:藝術的本質(zhì)與先導
在農(nóng)村老家生活的時候,我經(jīng)常聽到響器的吹奏聲,那是一個曾有兩千多人居住的大莊子,老人去世是常有的事。坦白說,并不喜歡,覺得太吵鬧,尤其是大學畢業(yè)后那幾年,我不想安心在農(nóng)村教書,有空就窩在家里啃考研資料,響器高亢的聲音對心煩意亂的我簡直就是一種折磨。后來考研上岸,讀了幾年書,進入城市,再也沒有聽到過響器的聲音。
直到有一天,因為工作上的一個機緣,我系統(tǒng)研讀了墨白的作品,開始懷念起那種聲音。《愛神與顱骨》中的響器,《民間使者》中的塤,都促使我在《墨白小說關鍵詞》一書中寫下一些文字。(巧合的是,墨白是劉慶邦的周口老鄉(xiāng))此后,我還特地上網(wǎng)觀看了關于響器的電影《百鳥朝鳳》,與響器有關的一切總能引起我的興趣。讀劉慶邦的《響器》,之于我對響器的理解,無疑又是一次升華。
也就是說,我被響器所打動,是源于文學的引領。海德格爾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宣稱,詩在一切藝術領域中具有優(yōu)先性,一切藝術本質(zhì)上都是詩,“建筑和繪畫總是已經(jīng)、而且始終僅止發(fā)生在道說和命名的敞開領域之中。它們?yōu)檫@種敞開所貫穿和引導……它們是存在者之澄明范圍內(nèi)的各有特色的詩意創(chuàng)作,而存在者之澄明早已不知不覺地在語言中發(fā)生了。”[5]語言是存在的家,沒有語言的命名和道說,沒有語言對存在者的澄明,藝術是不可能的。
海德格爾盛贊的語言,不是我們?nèi)粘J褂玫牧魉渍Z言,這種語言在他眼中是一種用濫了的語言,發(fā)不出任何召喚。為藝術發(fā)生提供“敞開領域”的語言是本質(zhì)的語言,是純粹所說,“純粹所說乃是詩歌”。[6]顯然,這種“詩歌”不是一種文學體裁,而是一種語言的樣式,一種作為純粹所說、能夠澄明存在的語言。我們基于體裁特征加以認定的詩,很多不能納入海德格爾的范疇;而海德格爾意義上的詩,也并不受體裁的限制。
在海德格爾的意義上,《響器》和《遍地白花》是詩,是澄明之詩,也是返鄉(xiāng)之詩。
詩在,故鄉(xiāng)就在,鄉(xiāng)愁就在
今年春節(jié),我回到了闊別八年的故鄉(xiāng),發(fā)現(xiàn)鄉(xiāng)親們大都進城買了房子,土地由幾個承包者進行機械化、規(guī)模化經(jīng)營,現(xiàn)在村子里常住人口也就三五十個老人。過年的時候也很冷清,有些人回村放掛鞭炮便匆匆回城,有些人干脆不再回來。我不知道故鄉(xiāng)現(xiàn)在是否還有響器班子,不知道老人們?nèi)ナ罆r是否還有響器相送,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有,也不會有多少圍觀者了,崔豁子們的風光一去不返了!劉慶邦應該也想不到,《響器》問世才短短二十來個春秋,農(nóng)村就已有滄海桑田之變遷。再過一些年,等這些老人離開,村子將是如何光景,我不敢想象!
像從前那樣再聽一次響器,已然成了難以實現(xiàn)的奢望。鄉(xiāng)愁無處安放!
更讓人憂心的是,不遠的將來,我們是否還有故鄉(xiāng)可以回返?是否還有鄉(xiāng)愁可以縈系?
海德格爾給了我們慰藉。他說,“故鄉(xiāng)”并不是一個空間概念,并不必然屬于從未離開的人。面朝黃土背朝天、如牛馬般勞作的鄉(xiāng)民們沒有故鄉(xiāng),被利欲驅(qū)迫而整日心神不寧、東奔西走的現(xiàn)代人沒有故鄉(xiāng),那些衣錦晝游、圈山占水的輕薄之輩也沒有故鄉(xiāng)。故鄉(xiāng)只屬于精神上的返鄉(xiāng)者,只在你眼含熱淚地追問和呼喚時才到場,與你空間上的位置無關。
進而言之,故鄉(xiāng)只在詩的話語中到場,“返”不是時間或空間上的折返,而是當下的進入,是與故鄉(xiāng)在詩中相遇。海德格爾這樣闡釋荷爾德林的詩:“哀歌《返鄉(xiāng)》并不是一首關于返鄉(xiāng)的詩歌,相反,作為它所是的詩,這首哀歌就是返鄉(xiāng);只消這首哀歌的話語作為鐘聲回響在德國人的語言中,那么,這種返鄉(xiāng)就還將發(fā)生。”[7]是的,響器班子沒有了,但回蕩在《響器》之中的樂聲,會永遠對讀者發(fā)出召喚。劉慶邦的每次閱讀,都是一次返鄉(xiāng);我們的這次重溫,也是一次返鄉(xiāng);而且,如海德格爾所說,這種返鄉(xiāng)未來還將發(fā)生。
詩在,故鄉(xiāng)就在,鄉(xiāng)愁就在!
注釋:
[1]《何子英、劉慶邦:兩副筆墨寫盡生活的堅硬與柔美》,騰訊網(wǎng)—長江文藝雜志社2020年7月21日,https://new.qq.com/rain/a/20200721A0J9Q500.
[2]《劉慶邦:我的作品就是我的響器》,搜狐網(wǎng)—新京報2006年03月17日,http://news.sohu.com/20060317/n242338029.shtml.
[3][德]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孫周興選編,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版,第293頁.
[4][德]海德格爾: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8頁.
[5][德]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孫周興選編,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版,第295頁.
[6][德]海德格爾: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7頁.
[7][德]馬丁·海德格爾:《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27頁.
責任編輯 申廣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