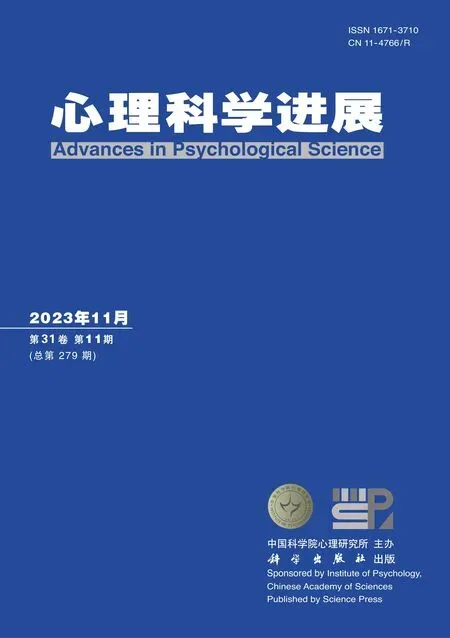社會網絡視角下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對團隊合作的影響*
曹 曼 趙曙明 張秋萍 呂鴻江
·研究構想(Conceptual Framework)·
社會網絡視角下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對團隊合作的影響*
曹 曼1趙曙明2張秋萍1呂鴻江1
(1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南京 211189) (2南京大學商學院, 南京 210093)
團隊內子群體可能引發分化、沖突, 甚至導致團隊分崩離析。以往研究忽視了團隊領導這一關鍵個體, 未能充分揭示其在子群體間的直接協調過程, 更缺乏對領導?子群體?團隊三方關系的深度解析。鑒于此, 本文擬基于社會網絡視角, 引入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這一概念(即團隊領導作為兩個或多個子群體之間的中介人), 探討團隊領導對子群體沖突的調和從而實現團隊合作的過程機制。本文擴展了子群體領域研究, 也為提升團隊管理及團隊領導效能提供了理論借鑒和實踐指導。
團隊領導, 齊美爾網絡中介, 子群體, 團隊合作
1 問題提出
當前全球經濟格局持續調整, 各國政治格局錯綜復雜, 加之新冠疫情的強勢來襲, 組織所面臨的外部環境挑戰不斷加劇。隨著團隊成為組織解決復雜任務的關鍵形式, 如何促進各團隊內部的有效協同和合作成為了組織有效應對外部環境挑戰的關鍵。然而, 團隊內子群體(子團隊)的不斷涌現(謝小云等, 2012), 可能引發分化、沖突, 甚至導致團隊分崩離析(倪旭東, 季百樂, 2019), 因而成為組織成功應對環境、獲取競爭優勢的重要障礙。例如, 快手資深員工在公司內網發布長文控訴部門內部存在大量暗中較勁, 這種現象廣泛存在于公司各級部門, 導致部門任務推進困難重重; 而作為全球最大家電零售巨頭的百思買關閉中國所有門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組織內部“蓮花派”、“沃爾瑪派”等紛爭明顯, 管理混亂。因此, 如何緩解子群體間沖突, 從而有效實現團隊合作, 成為組織當前亟需解決的現實問題。
現有研究表明, 子群體或子團隊可能會對團隊運作產生不利影響(Thatcher et al., 2003; Li & Hambrick, 2005; Rico et al., 2007; Chiu & Staples, 2013; Ellis et al., 2013; Hutzschenreuter & Horstkotte, 2013; Heidl et al., 2014; 謝小云等, 2012; 陳帥, 2016; 倪旭東, 季百樂, 2019; 孫玥璠等, 2021)。例如, 子群體的形成可能導致個體將自身歸類于不同的特定群體, 加劇了子群體之間的交流障礙, 進而阻礙團隊有效合作(O’Leary & Mortensen, 2010; Ndofor et al., 2015; 周建等, 2015; Meyer et al., 2016)。若子群體內部具備較高的凝聚力, 子群體成員可能會出于維護子群體利益的群體目標而損害團隊的整體利益(Bezrukova et al., 2009; 謝小云等, 2012)。中國情境下的管理者常常將其“親信”列入主要統治群體, 這些“親信”經常為謀取本派私利而引發公司或團隊內部派系之間沖突不斷(Chi, 1996; 羅家德, 鄭孟育, 2009)。因此, 探究子群體消極影響的緩解機制也成為了理論研究的重要議題。
針對如何有效整合與協調團隊內子群體這一問題,已有研究從團隊結構和情境特征等方面探討了子群體消極作用的調節機制(Carton & Cummings, 2013; Homan et al., 2007; Bezrukova et al., 2009; Bezrukova et al., 2012; 潘清泉等, 2015; 倪旭東, 季百樂, 2019)。例如, 通過干預子群體的數量、平衡性和子群體強度來減少子群體的消極作用(Gibson & Vermeulen, 2003; Cronin et al., 2011; Meyer et al., 2015; 陳慧等, 2019)。近年來, 僅有零星研究開始探討特定領導風格對子群體消極影響的緩解作用(Chen et al., 2023), 例如包容性領導(Du et al., 2021; Qi et al., 2022)、謙卑型領導(Yao et al., 2021)和關系型領導(陳偉等, 2015)等。
然而, 現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 以往關于如何緩解子群體負面影響的研究更多停留在對于調節變量的探索(陳慧等, 2019; Qi et al., 2022), 缺乏對于如何直接減少或規避其負面影響的具體過程的探討。在組織實踐中, 子群體負面影響緩解是非常重要的實踐議題。缺乏對于其過程的系統研究嚴重阻礙組織管理者深刻理解對于這一問題的自主干預。其二, 已有子群體研究大多將屬性特征作為研究其社會過程的立足點(Bezrukova et al., 2009; 倪旭東, 季百樂, 2019), 少有研究根據關系網絡來考察個體?子群體?團隊之間的互動結構(Homan et al., 2020)。然而, 個體、子群體、團隊并非簡單的屬性特征集合, 而是嵌套且相互依存的多層關系結構(Thatcher & Patel, 2012)。在這種關系結構中, 不同行動者的行為和決策都可能對其他行動者產生影響。目前研究焦點過度聚焦于屬性分析, 缺乏對關系模式的探討, 忽略了各行動者之間的關系網絡的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缺口, 本研究擬根據社會網絡領域中“其他參與者關系干預”理論框架(The Changing Others’ Relationships Framework) (Halevy et al., 2019), 探討團隊領導作為團隊內重要行動者如何利用自身獨特的關系模式來進行子群體沖突的調諧并對團隊結果產生影響的具體過程。“其他參與者關系干預”理論框架的核心觀點是作為第三方的網絡中間人能夠建立和加強其他參與者之間的關系。通過聚焦二元互動關系, 第三方可以利用信息(如建議和反饋等)或激勵手段等中介行為來塑造參與者之間關系, 包括創建或終止參與者之間的關系、改變其他參與者之間關系符號(從積極到消極或者相反) (Halevy et al., 2019)。因此, 當團隊領導作為子群體之間的中介, 即齊美爾網絡中介(Krackhardt, 1999), 則有可能通過自身的中介行為協調并緩解子群體之間的沖突。此外, 齊美爾網絡中介其第三方嵌入的特性也表明, 即使并非有意協調雙方的沖突, 也可能通過多種非語言形式來緩解沖突和矛盾, 從而有利于絕對沖突的過渡和調解(Simmel, 1950)。基于此, 探討團隊領導作為齊美爾網絡中介對子群體沖突的協調則正好解決了上述理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該研究不僅有利于明晰團隊領導如何利用其位置或機會直接影響子群體間關系, 而且有助于全面揭示團隊領導?子群體?團隊三方調諧過程。
鑒于此, 本文擬基于社會網絡視角, 引入團隊領導的齊美爾網絡中介這一概念, 即團隊領導作為兩個或多個子群體之間的中介, 探討其對子群體沖突的調和從而實現團隊合作的過程機制, 以構建團隊領導?子群體?團隊三方關系的理論框架。為了深入剖析這一過程, 具體解決方案是:第一, 借鑒社會網絡視角, 根據團隊內不同網絡內容的分類, 界定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的內涵。第二, 基于“其他參與者關系干預”理論框架, 解析不同網絡的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對子群體之間沖突及團隊合作的影響機制。第三, 考察不同網絡的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與子群體之間沖突及團隊合作之間關系的重要邊界條件。
2 國內外研究現狀及發展動態
2.1 子群體負面影響緩解研究
子群體是基于某種特定關系屬性, 團隊成員之間自發形成的小群體, 其中成員之間具有相對直接且緊密的關系(Wasserman & Faust, 1994)。團隊內子群體的存在可能會帶來多種負面影響, 例如社會分類理論指出, 團隊內子群體的存在會引發群際偏見及相應的負面認知, 進而阻礙團隊進程(Tajfel et al., 1971)。與社會分類理論類似, 距離理論(Brewer, 1991)認為子群體成員與其他子群體成員存在心理距離, 因此合作意愿降低。具體而言, 相比不同的個體, 人們更喜歡與自己相似的個體親近, 因此在整個團隊中, 團隊成員因其相似性而更加喜愛和信任子群體內部成員, 而對子群體外部成員不信任(Carton & Cummings, 2012; Bezrukova et al., 2009), 尤其是在強子群體中的成員更能夠看到他們與子群體內部成員的高度相似性以及與子群體外部成員的高度差異性(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4)。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不同子群體及其成員之間可能出現沖突。
現有關于如何緩解子群體負面影響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調節機制, 鮮有針對如何直接減少或規避其負面影響的探討。目前有關調節機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子團隊結構屬性、團隊成員個體屬性和團隊情境因素三個方面。在子團隊結構屬性方面, 子團隊數量、平衡性、均勻度能夠對子群體的影響起到調節作用(Carton & Cummings, 2013; Antino et al., 2019; 倪旭東等, 2016; 倪旭東, 賀爽爽, 2018; 田莉等, 2021; 張新星, 劉新梅, 2021)。在團隊成員個體屬性方面, 平等的團隊成員地位(Ely & Thomas, 2001)、多樣化的信念(Meyer & Schermuly, 2012)、團隊子成員交換(倪旭東, 季百樂, 2019)等因素是不同子團隊和成員間進行溝通交流和學習的必要保證。團隊成員在平等的情境下會更好地理解互依的任務及存在的差異, 提高彼此學習的主動性。在團隊情境方面, 一些特定的領導風格能夠削弱團隊多樣性或子群體存在的負面影響。變革型領導可能促進整個團隊成員對目標的清晰度和共享度, 從而減少子群體負面影響(Shipilov et al., 2008)。包容性領導能夠抑制子群體的負面影響, 并促進員工的敬業度(Du et al., 2021; Qi et al., 2022)。此外, 良好的團隊氛圍(Gilson & Shalley, 2004)、團隊任務特征(Xie et al., 2020)、團隊的集體主義(Ma et al., 2022)、團隊認同(孫玥璠等, 2021)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不同子群體間的互動, 引導他們朝著共同的目標努力。
以往研究為子群體負面影響的緩和提供了良好借鑒, 但忽略了團隊領導這一關鍵個體如何直接對團體內子群體進行整合及協調, 更缺乏對團隊領導與子群體之間多方調諧過程的深度探討。實際上, 團隊領導作為團隊內的關鍵個體, 是團隊目標主要負責人, 其行動無疑能夠對子群體以及團隊產生重要影響。遺憾的是, 現有文獻中對于團隊領導直接協調的研究非常匱乏, 使得我們未能全面揭示團隊領導與子群體之間的作用過程。因此, 本文擬借鑒社會網絡領域內齊美爾網絡中介, 探討團隊領導對子群體影響的作用機制。
2.2 齊美爾網絡中介對子群體負面影響緩解研究的突破
齊美爾網絡中介(Simmelian brokerage)是指社會網絡意義上派系(cliques)之間的中介(Krackhardt, 1999) (如圖1所示中A)。其中派系(cliques)是指三個或以上節點之間直接連接的圖, 且所有成員之間都是互惠的。值得注意的是, 此處派系即為社會網絡意義上基于圖論所形成的小群體。

圖1 齊美爾網絡中介
資料來源:作者繪制
齊美爾網絡中介的概念最早起源于Krackhardt (1999)對齊美爾三方關系闡述(Simmel, 1950)的擴展和延伸。齊美爾(Simmel, 1950)提出在社會過程中加入中介的三元關系在關系的質量、動態及穩定性上與二元關系有著本質的不同。相對于二元關系, 三元關系減弱了個體性, 降低了個體的議價能力, 增強了沖突的解決。一方面, 第三方的存在表明絕對沖突的過渡和調解(Simmel, 1950)。另外一方面, 即使第三方并非有意協調雙方的沖突, 也能夠通過非語言形式來緩解沖突和異議。基于齊美爾對三方關系的闡述(Simmel, 1950), Krackhardt (1999)進一步提出齊美爾網絡中介的概念即社會網絡意義上內部緊密聯系的小群體之間的中介。作為多個小群體的成員, 齊美爾網絡中介者與組內的其他成員構成了非常具有凝聚性的結構, 如圖1中, A和B、C從屬于小群體1, 則三者之間是緊密聯系的。A和D、E從屬于小群體2, 則三者之間也是緊密聯系的。A則是齊美爾網絡中介, 連接了小群體1和小群體2。
基于社會資本的構成觀點, Latora等(2013)認為齊美爾網絡中介可以被看作是閉合網絡和開放網絡的結合, 一方面, 齊美爾網絡中介是相互不連接的團隊之間的唯一連接, 另外一方面, 在每個團隊內部, 齊美爾網絡中介又與組內的其他成員構成了非常具有凝聚性、閉合性的網絡。在以往社會資本的相關研究中, 一直存在著關于何種網絡結構能夠成為社會資本的爭議。一些學者認為, 閉合結構有利于提升信任和歸屬感, 增強合作行為和社會規范, 形成共享的文化。另外一些學者認為, 開放結構能夠從網絡中介或結構洞之間獲得非冗余的信息。為解決這種爭議, Latora等(2013)的研究指出, 個體不僅能夠從單一的閉合結構或開放結構獲得收益, 而且能夠從兩者的整合中汲取優勢。因此, 齊美爾網絡中介, 作為個體在封閉結構和開放結構之間界面上的結構位置, 成為了協調這種爭議的重要著力點(孫笑明等, 2018)。
為進一步明晰齊美爾網絡中介的概念內涵, 有必要將其與子群體研究中已被廣泛應用的交叉分類模型(Chen et al., 2017)進行概念比較。通過概念對比發現, 齊美爾網絡中介在指代對象、內涵范圍和動態視角等方面均不同于交叉分類模型, 具有其獨特的概念內涵和應用情境。具體差異如下:
(1)在指代對象上, 齊美爾網絡中介是指同一網絡中子群體之間的中介, 而交叉分類模型中則是指因不同屬性類別而形成子群體之間的重疊。從社會網絡視角出發, 子群體(或派系)是基于某種特定關系網絡基礎上, 團隊成員之間自發形成的小群體(Wasserman & Faust, 1994)。例如在團隊朋友網絡中, 可能存在多個基于朋友網絡的子群體。齊美爾網絡中介則是這種子群體之間的中介。交叉分類模型則是社會分類的多個維度或屬性同時用于影響個體的判斷(Crisp et al., 2003)。例如, 在性別和種族兩種屬性的交叉中, 對于黑人女性感知者來說, 其他黑人女性是雙重群體內成員(在兩個分類維度上重合), 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是混合群體成員(僅在兩個類別維度中的一個維度上與感知者重合), 而白人男性是雙重群體外成員。因此, 齊美爾網絡中介和交叉分類模型在指代對象上具有很大的差異。
(2)在內涵范圍上, 齊美爾網絡中介同時包含網絡中介的結構和中介行為, 而交叉分類模型則僅僅從配置的角度考察了結構。齊美爾網絡中介是一種類型的網絡中介, 相比于網絡中介的位置和結構, 近年來一些研究認為網絡中介是一種行為, 即中介相關的行動(Boari & Riboldazzi, 2014; Quintane & Carnabuci, 2016; Halevy et al., 2019)。與以往的結構主義相對應地, 這種概念化定義更聚焦于作為中介的中間人在實際情況下做了什么, 而不是假設占據中介的位置就能自動做出中介相關行為。因此, 齊美爾網絡中介并非僅限于結構, 而是涉及作為齊美爾網絡中介行動者的具體行為。而交叉分類模型中重疊的成員關系則僅是從子群體配置視角考察了結構。當各子群體之間存在跨組的相似性時, 交叉分類產生, 重疊的成員關系存在(Bezrukova et al., 2009; Chen et al., 2017)。
(3)在動態性視角上, 齊美爾網絡中介能夠帶來動態的結構變化, 而交叉分類模型則側重于從靜態視角考察子群體之間重疊的配置。無論從行為視角, 還是從社會網絡研究中“其他參與者關系干預”框架來看, 作為網絡中介的第三方有可能通過中介行動來改變其他參與者的關系, 從而實現網絡的動態結構變化。Halevy等(2019)認為, 中介的行為是第三方利用信息(如建議和反饋等)或激勵手段來塑造參與者之間二元關系的影響過程, 其中包括為第三方創造或終止參與者之間關系的能力, 以及第三方改變其他參與者之間關系符號的能力(例如從積極到消極)。然而, 交叉分類模型則僅靜態地分析了重疊的成員關系對子群體內成員社會評價的影響(Grigoryan, 2020; Prati et al., 2021)。例如, 不同的交叉重疊配置會導致不同的評價(Crisp et al., 2003)。
鑒于齊美爾網絡中介涉及三方關系(即中介者和不同小群體內的其他行動者), 本研究提出, 齊美爾網絡中介可能觸發更高一層的社會整合過程, 從而對所在集體產生綜合影響。在齊美爾網絡中介的情境下, 團隊領導作為不同網絡的齊美爾網絡中介, 有可能通過自身的中介行為, 緩解并改變兩個或多個子群體之間的摩擦和矛盾, 從而提升團隊合作和團隊效能。因此, 結合上述子群體負面影響緩解研究, 引入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這一概念, 進而探討其對子群體沖突的調和從而促進團隊合作的過程機制, 對于最終構建團隊領導?子群體?團隊三方的關系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3 研究構想
本文擬整合社會網絡視角, 探究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對子群體沖突的調和從而實現團隊合作的過程機制, 包括在理論上重點提煉不同的網絡內容下齊美爾網絡中介的內涵, 在實證研究上考察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與團隊合作的中介機制及調節機制。本文主要由以下三部分構成:研究1基于網絡內容分類(工具型網絡和表達型網絡)對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內涵進行界定; 研究2考察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類型(工具型和表達型)如何分別影響子群體之間沖突以及最終的團隊合作; 研究3探討團隊領導不同齊美爾網絡中介影響的重要邊界條件?團隊領導作為中介的合作傾向及團隊領導的政治技能。這三個部分共同構建了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影響過程的理論框架。研究框架如圖2所示。
3.1 基于網絡內容的齊美爾網絡中介內涵界定
本研究旨在根據特定網絡內容分類, 對齊美爾網絡中介內涵進行再界定及再劃分, 從而為后續研究進一步明晰不同網絡內容的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如何促進團隊合作提供更為詳盡的理論基礎。具體而言:首先明確社會網絡內容分類; 其次, 針對不同的網絡內容對齊美爾網絡中介進行劃分, 分別確定其內涵; 最后, 對不同網絡內容的齊美爾網絡中介與其他類似的概念進行對比分析, 歸納出基于網絡內容的齊美爾網絡中介的獨特之處。
根據社會網絡的內容, 社會網絡分為工具型網絡和表達型網絡。其中工具型網絡通常出現在工作角色的履行過程中, 涉及工作相關資源的交換, 包括信息、專業知識、建議甚至是物質資源(Fombrun, 1982; Lincoln & Miller, 1979)。表達型網絡則主要涉及友誼和社會支持等情感性交流, 是指通過社會情感支持和規范期望影響個體/組織身份的非正式聯系。從理論上來看, 網絡關系的內容定義了交換的主要資源, 而社會網絡的各種性質如何發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于網絡關系當中存在的特定資源。從實證檢驗上來看, 不同類型網絡內容發揮作用的過程具有顯著差異。基于此, 本研究擬整合齊美爾網絡中介和網絡內容分類, 將齊美爾網絡中介劃分為工具型齊美爾網絡中介及表達型的齊美爾網絡中介, 并將其與相關的概念進行對比分析, 以明晰其概念及基本特征。
3.2 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與團隊合作的中介機制
基于在齊美爾網絡中介情境下高度適用的“其他參與者關系干預”框架, 擬進一步探討不同的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工具型網絡中的工作網絡和表達型網絡中的朋友網絡)對團隊合作的影響過程。“其他參與者關系干預”框架是由Halevy等(2019)提出, 用以描述第三方如何通過中介行動來改變其他參與者的關系。Halevy等(2019)認為, 中介的行為是第三方利用信息(如建議和反饋等)或激勵手段來塑造參與者之間的二元關系的影響過程。中介活動包括兩個基本方面:其一, 第三方創造或終止參與者之間關系; 其二, 第三方改變其他參與者之間關系的符號 (例如從積極到消極)。
在齊美爾網絡中介的情境下, 團隊領導作為不同網絡齊美爾網絡中介的作用及影響過程遵循“其他參與者關系干預”框架。團隊領導作為整個團隊的關鍵個體, 其職位權威賦予的特殊威信能夠為其改變子群體之間的關系或程度提供支持。因此, 團隊領導作為第三方, 有可能通過自身的中介行為, 緩解并改變兩個或多個子群體之間的摩擦和矛盾, 從而促進團隊合作。
3.2.1 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工作網絡)、團隊內子群體之間任務沖突與團隊合作
當作為工作網絡的齊美爾網絡中介時, 團隊領導在獲取工作信息的數量和質量上均具有較大優勢。當擁有這種信息和資源優勢后, 團隊領導為實現整個團隊的目標, 更愿意從整體上協同多個子群體之間的任務內容及問題解決途徑, 從而減少子群體之間的任務沖突。此外, 團隊領導可以利用其跨子群體的優勢, 將一個子群體的行為和觀點轉換成適合其他子群體的理解方式, 從而協同兩方甚至是多方的努力, 調解工作過程中的諸多不適及分歧, 減少過于激烈的任務沖突。然而, 當團隊領導所占據的齊美爾網絡中介(工作網絡)超過了一定程度, 團隊領導面臨協調多方的壓力(Mehra & Schenkel, 2008), 協調任務分歧的負擔過重(Long Lingo & O’Mahony, 2010), 從而可能無法順利地緩解并改變兩個或多個子群體之間工作上的摩擦和矛盾。

圖2 總體研究框架
命題1: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工作網絡)與團隊內子群體之間任務沖突成U型關系。
在齊美爾網絡中介的情境下, 團隊的任務沖突不僅是個體之間, 還涉及到不同子群體之間。單純個體之間的任務沖突可能促使團隊成員交換不同的信息和知識, 從而促進彼此對互依任務的了解, 增進集體學習。然而, 不同子群體之間的任務沖突更易引發雙方形成對抗, 不利于子群體之間的信息交互和思維碰撞, 也就更談不上對任務的及時識別和深刻理解, 最終導致較低的團隊合作。
命題2:團隊內子群體之間任務沖突與團隊合作為負相關關系。
命題3:團隊內子群體之間任務沖突在團隊領導的齊美爾網絡中介(工作網絡)與團隊合作之間關系起到中介作用。
3.2.2 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朋友網絡)、團隊內子群體之間關系沖突與團隊合作
朋友關系是一種有明確義務的角色(Henderson & Argyle, 1986), 涉及提供幫助、完全公開和誠實、分享秘密、不向他人透露信息等(Bridge & Baxter, 1992)。當作為朋友網絡的齊美爾網絡中介時, 團隊領導能夠通過非正式關系來緩解各子群體之間的情感矛盾, 從而對團隊合作產生積極影響。團隊領導作為不同子群體之間的聯結, 為了雙方或多方的團結, 能夠采取多種措施減少負面情感信息在子群體之間的傳遞和傳染。此外, 基于齊美爾網絡中介的位置, 團隊領導能夠敏銳地觀察到沖突點, 并予以及時地協調或調解, 從而避免更大的沖突。然而, 當團隊領導所占據的齊美爾網絡中介(朋友網絡)過高時, 團隊領導所具備的關系沖突緩沖器的作用可能會失效。建立和維持友誼通常需要大量的支持和關注, 這可能會導致疲勞(Methot et al., 2016)。更為重要的是, 團隊領導作為朋友網絡的齊美爾網絡中介越多, 需要維持不同友誼關系的程度越高, 可能會不斷加劇關系沖突的協調期望及隨之而來的能量消耗(Methot et al., 2016)。
命題4: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朋友網絡)與團隊內子群體之間關系沖突成U型關系。
關系沖突一方面能夠導致團隊成員之間的信任降低和對抗加強(陶愛華等, 2018), 進而降低其共同解決問題的意愿和能力, 最終影響團隊合作(De Dreu, 2006)。另一方面, 關系沖突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耗散了團隊成員的資源, 使其不得不抽出時間和精力來應對, 最終導致團隊合作的進一步惡化(De Wit et al., 2012)。
命題5:團隊內子群體之間關系沖突與團隊合作為負相關關系。
命題6:團隊內子群體之間關系沖突在團隊領導的齊美爾網絡中介(朋友網絡)與團隊合作之間關系起到中介作用。
3.3 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與團隊合作的調節機制
根據“其他參與者關系干預”框架, 網絡中介是一個社會影響過程。當中介者占據齊美爾中介的位置之后, 個體可能會被不同的動機、信念及價值觀所驅使, 從而轉化為截然不同的行為傾向。這種不同行為傾向隨后能夠影響齊美爾網絡中介的結果。此外, 除了行為傾向的影響, 個體是否能夠利用齊美爾網絡中介所蘊含的機會還受到個體能力因素的影響。因此, 本研究擬考察個體的行為傾向和個體能力的影響, 并將重點考察團隊領導的合作傾向和政治技能的作用。
合作傾向是指中介者嘗試將其他參與者聯系在一起, 從而彌合他們之間的信息鴻溝, 并整合各種貢獻的傾向(Stovel & Shaw, 2012)。這種傾向的中介者不會利用網絡中的信息差距和不對稱為自己謀利, 而是努力將其他參與者聯系起來, 以促進他們之間的合作和相互調整。當團隊領導作為齊美爾網絡中介的合作傾向更高時, 團隊領導更愿意為了整個團隊的目標, 采取多種方式促進兩方或多方子群體的信息交流和情感交流, 例如將一種情境中具有特定價值的信息和價值轉變為對另外一種情境的信息。隨后, 幫助團隊緩解各子群體之間的任務沖突和關系沖突, 從而促進團隊合作的達成。
政治技能是指在工作中能夠有效地理解他人, 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影響他人最終達到個人或組織目標的能力(Ferris et al., 2005, p. 127)。高政治技能的領導能夠并且愿意利用自身網絡能力及影響力, 增強自身信任度和聲譽(Ferris et al., 2005), 最終增強領導有效性(Snell et al., 2014; Brouer et al., 2013)。擁有高政治技能的領導在人際互動中表現出的真誠性, 有利于幫助其建立與他人的信任和支持關系, 而減少其被視為操縱或公開施加影響的嫌疑(Douglas & Ammeter, 2004)。這些擁有高政治技能的團隊領導, 有能力利用齊美爾網絡中介的位置和機會, 幫助團隊緩解各子群體之間的任務沖突和關系沖突, 從而促進團隊合作的達成。
命題7:團隊領導作為中介的合作傾向調節了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工作網絡)與團隊內子群體之間任務沖突之間的關系。
命題8:團隊領導作為中介的合作傾向調節了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朋友網絡)與團隊內子群體之間關系沖突之間的關系。
命題9:團隊領導的政治技能調節了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工作網絡)與團隊內子群體之間任務沖突之間的關系。
命題10:團隊領導的政治技能調節了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朋友網絡)與團隊內子群體之間關系沖突之間的關系。
4 理論建構與創新
團隊內子群體可能引起的分化、沖突, 甚至使得整個團隊分崩離析, 日益成為組織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挑戰。但在此過程中, 團隊領導如何直接對子群體進行協調整合, 采用何種干預方式, 作用效果及作用機制是什么, 現有文獻尚缺乏全面揭示和考察。本研究則引入齊美爾網絡中介這一概念, 探討團隊領導對子群體沖突的調和從而實現團隊合作的過程機制。本研究不僅擴展了子群體領域研究, 而且也為提升團隊管理及團隊領導效能提供了理論借鑒和實踐指導。具體貢獻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本文通過引入團隊領導的齊美爾網絡中介這一全新概念, 考察了其對子群體沖突及團隊合作的作用過程, 不僅從理論上推動了現有子群體領域的研究進程, 也為企業在實踐中有效解決子群體協調整合的問題提供了全新思路。子群體負面影響緩解問題已成為業界和學界共同關注的重要議題。雖然以往子群體研究考察了子群體的結構特征(如Carton & Cummings, 2013; Cronin et al., 2011)、特定領導風格(如Du et al., 2021; Qi et al., 2022)等對子群體消極影響的調節作用, 但是鮮有研究基于團隊領導視角對子群體間直接協調的過程進行探討, 更是缺乏依托關系網絡方法來考察個體?子群體?團隊之間的互動結構(Homan et al., 2020)。本文則根據“其他參與者關系干預”框架(Halevy et al., 2019), 指出團隊領導作為不同網絡的齊美爾網絡中介, 有可能通過自身的中介行為, 緩解并改變兩個或多個子群體之間的摩擦和矛盾, 從而促進團隊合作。具體而言, 當團隊領導作為工作網絡的齊美爾網絡中介時, 在獲取工作信息的數量和質量上具有顯著優勢。當擁有這種信息和資源優勢之后, 團隊領導為了整個團隊的目標, 更能從整體上協同多個子群體之間的任務, 從而減少子群體之間的任務沖突, 最終實現團隊合作。當團隊領導作為朋友網絡的齊美爾網絡中介時, 能夠通過非正式關系來緩解各子群體之間的情感矛盾, 采取多種措施減少負面情感信息在子群體之間的傳遞和傳染, 并敏銳地觀察到沖突點予以及時的協調或調解, 從而對團隊合作產生積極的影響。本研究通過借鑒社會網絡視角, 構建團隊領導?子群體?團隊三方關系的理論框架, 更為精細深入探討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子群體沖突和團隊合作的作用過程, 擴展了現有子群體研究。此外, 本研究也為企業實踐中有效協調子群體之間的矛盾沖突提供具體指導。相對于特定領導風格的甄選和培育效果均需要較長時期才能得到檢驗, 團隊領導在子群體之間的中介作用, 對于緩解子群體之間沖突更為及時、更具有針對性。在谷歌開發Google+的過程中, 項目團隊領導拉斯洛·布克就曾利用自身在各子項目中的資深專家角色來處理團隊內部的派系沖突。他身為各子項目的連接者, 在項目內部組織不同子項目的核心成員進行一系列的會議和討論, 以促進過程信息的開放和工作需求的透明, 最終歷時短短一年該項目團隊就成功將Google+這一預計可以與Facebook抗衡的產品推出了市場。
第二, 本文根據網絡關系的內容, 對團隊領導齊美爾網絡中介的內涵進行重新界定。已有研究大多關注齊美爾網絡中介的結構化內涵(Krackhardt, 1999; Latora et al., 2013), 缺乏對其網絡內容的系統考察。基于對網絡結構而非網絡內容的關注, 以往網絡研究更多地將不同種類的網絡關系看作是等價的。這就導致研究中經常會出現將不同類型的關系混雜在一起的現象, 其潛在假設為同一組參與者表現出的不同結構模式僅僅是真實結構的變體。然而, 不同類型的網絡關系可能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從理論上來看, 網絡關系的內容定義了交換的主要資源(Aral & Van Alstyne, 2011;Kwon et al., 2020)。社會網絡的各種性質如何影響重要結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于網絡中存在的資源。從實證檢驗來看, 不同類型的網絡內容對重要結果的影響過程及機制具有顯著差異。例如, Porter等(2019)通過元分析發現, 雖然工具型網絡和表達型網絡的中心性都與員工離職相關, 但是中介過程不同。工具型網絡的中心性通過工作績效和組織承諾降低離職, 然而表達型網絡的中心性則通過工作滿意度和組織承諾降低離職。因此, 本文整合齊美爾網絡中介和網絡內容分類研究, 進一步將齊美爾網絡中介劃分為工具型齊美爾網絡中介及表達型齊美爾網絡中介。其中, 工具型的齊美爾網絡中介是指在工具型網絡內不同派系之間的中介。這種工具型齊美爾網絡中介更多地是基于工作或任務相關網絡, 例如, 工作流網絡或咨詢網絡。而表達型的齊美爾網絡中介則是指在表達型網絡內不同派系之間的中介。這種表達型齊美爾網絡中介更多地是基于朋友或者支持相關網絡。因此, 本文研究結論能夠為團隊管理者整合團隊內不同內容的社會網絡(工具型網絡和表達型網絡), 并主動利用、占據其關鍵位置(如子群體間的中介人)來對子群體甚至團隊進行有效管理提供有益啟示。
最后, 本文考察了齊美爾網絡中介對團隊合作這一團隊結果的影響機制及邊界條件。現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探索齊美爾網絡中介者自身的影響(Ashforth et al., 2008;Tasselli & Kilduff, 2018), 而缺乏對其他參與者及整個集體影響的系統探討。然而, 網絡中介本身就涉及三方關系(Kwon et al., 2020), 即中介者和其他行動者, 甚至是所在團隊。社會網絡內的機會也是由自身和其他參與者的行為共同決定的。此外, 個體對網絡中介利益的追尋可能促進或背離集體利益, 中介的策略也可能觸發更高一層的社會整合過程, 從而對所在集體產生影響。例如, Bizzi (2013)發現, 當將員工視為獨立個體時, 占據中介者位置的員工所實施的競爭和權力導向的行為可能是有利的, 而當涉及群體效能和群體氛圍時, 則會產生摩擦和矛盾。鑒于此, 本研究旨在基于社會網絡視角考察組織或團隊內的社會關系模式、結構、資源和認知, 明晰團隊領導的齊美爾網絡中介對團隊合作的影響機制和邊界條件。研究結論不僅能夠從多理論視角擴展齊美爾網絡中介的研究框架, 也能夠在實踐中為管理者有效化解組織或團隊內的網絡生態危機提供有益啟示。例如, 團隊領導者通過占據團隊內不同網絡的重要位置如齊美爾網絡中介, 并實施相應的行為, 能夠更為順利地實現有效團隊合作。
陳慧, 梁巧轉, 張悅. (2019). 基于Meta分析的團隊斷裂研究: 分類, 效果與情境.,(3), 116–130.
陳帥. (2016). 團隊斷裂帶對團隊績效的影響: 團隊交互記憶系統的作用.,(1), 84–94.
陳偉, 楊早立, 朗益夫. (2015). 團隊斷裂帶對團隊效能影響的實證研究——關系型領導行為的調節與交互記憶系統的中介.,(4), 99–110.
羅家德, 鄭孟育. (2009). 派系對組織內一般信任的負面影響., (3), 3–13+76.
倪旭東, 賀爽爽. (2018). 子團隊利弊作用的調節機制.,(5), 910–921.
倪旭東, 季百樂. (2019). 如何消除子團隊的消極作用——子團隊成員交換的作用.,(2), 259–268.
倪旭東, 項小霞, 姚春序. (2016). 團隊異質性的平衡性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5), 556–565.
潘清泉, 唐劉釗, 韋慧民. (2015). 高管團隊斷裂帶、創新能力與國際化戰略——基于上市公司數據的實證研究.,(10), 111–122.
孫笑明, 崔文田, 王巍, 劉斌, 裴云龍. (2018). 中間人及其聯系人特征對結構洞填充的影響研究.,(2), 59–66.
孫玥璠, 張琦, 張永冀. (2021). 高管團隊斷裂帶對企業實質性創新的“雙刃劍”作用:業務多元化視角.,(8), 141–149.
陶愛華, 劉雍鶴, & 王沛. (2018). 人際沖突中失望的個人效應及沖突類型的調節作用.,(2), 235–242.
田莉, 張劼浩, 袁國真. (2021). 創業團隊身份異質性對團隊沖突過程與結果的影響——基于團隊斷裂帶的多案例研究.,(12), 324–338.
謝小云, 張政曉, 王唯梁. (2012). 團隊背景下的子群體關系研究進展評析.,(10), 22–29.
張新星, 劉新梅. (2021). 均衡還是失衡?信息型子團隊均衡對團隊創造力的作用機理研究——親社會動機的調節作用.,(7), 157–172.
周建, 李小青, 楊帥. (2015). 任務導向董事會群體斷裂帶、努力程度與企業價值.,(1), 44–52.
Antino, M., Rico, R., & Thatcher, S. M. (2019). Structuring reality through the faultlines lens: The effects of structure, fairness, and status conflict on the activated faultlines–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5), 1444–1470.
Aral, S., & Van Alstyne, M. (2011). The diversity-bandwidth trade-off.,(1), 90–171.
Ashforth, B. E., Harrison, S. H., & Corley, K. G. (2008). Identification in organizations: An examination of four fundamental questions.,(3), 325–374.
Bezrukova, K., Jehn, K. A., Zanutto, E. L., & Thatcher, S. M. B. (2009). Do workgroup faultlines help or hurt? A moderated model of faultlines, team identification, and group performance.,(1), 35–50.
Bezrukova, K., Thatcher, S. M., Jehn, K. A., & Spell, C. S. (2012). The effects of alignments: Examining group faultlines, organizational cultures, and performance.,(1), 77–92.
Bizzi, L. (2013). The dark side of structural holes: A multilevel investigation.,(6), 1554–1578.
Boari, C., & Riboldazzi, F. (2014). How knowledge brokers emerge and evolve: The role of actors’ behaviour.,(4), 683–695.
Brewer, M. B. (1991). The social self: On being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5), 475–482.
Bridge, K., & Baxter, L. A. (1992). Blended relationships: Friends as work associates.,(3), 200–225.
Brouer, R. L., Douglas, C., Treadway, D. C., & Ferris, G. R. (2013). Leader political skill,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A two-study model test and constructive replication.,(2), 185–198.
Carton, A. M., & Cummings, J. N. (2012). A theory of subgroups in work teams.,(3), 441–470.
Carton, A. M., & Cummings, J. N. (2013). The impact of subgroup type and subgroup configurational properties on work team performance.,(5), 732–758.
Chen, S., Wang, D., Zhou, Y., Chen, Z., & Wu, D. (2017). When too little or too much hurts: Evidence for a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faultlines and performance.,, 931–950.
Chen, X., Zhu, L., Liu, C., Chen, C., Liu, J., & Huo, D. (2023). Workplace divers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1021–1045.
Chi, S. C. (1996). Exploring confidant relationships of business managers.,, 1–15.
Chiu, Y-T., & Staples, D. S. (2013). Reducing faultlines in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 teams self-disclosure and task elaboration.,(5), 498–531.
Crisp, R., Ensari, N., Hewstone, M., & Miller, N. (2003). A dual-route model of crossed categorisation effects.,(1), 35–73.
Cronin, M. A., Bezrukova, K., Weingart, L. R., & Tinsley, C. H. (2011). Subgroups within a team: The rol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integration.,(6), 831–849.
De Dreu, C. K. (2006). When too little or too much hurts: Evidence for a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ask conflict and innovation in teams.,(1), 83–107.
De Wit, F. R., Greer, L. L., & Jehn, K. A. (2012). The paradox of intragroup conflict: A meta-analysis.,(2), 360–390.
Douglas, C., & Ammeter, A. P. (2004). An examination of leader political skill and its effect on ratings of leader effectiveness.,(4), 537–550.
Du, J., Ma, E., & Lin, X. (2021). When diversity leads to divided teams: A multi-level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team faultlines and employee engagement.,, 102818.
Ellis, A. P., Mai, K. M., & Christian, J. S. (2013). Examining the asymmetrical effects of goal faultlines in groups: A categorization-elaboration approach.,(6), 948–961.
Ely, R. J., & Thomas, D. A. (2001). Cultural diversity at work: The effects of diversity perspectives on work group processes and outcomes.,(2), 229–273.
Ferris, G. R., Treadway, D. C., Kolodinsky, R. W., Hochwarter, W. A., Kacmar, C. J., Douglas, C., & Frink, D. D. (2005).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political skill inventory.,(1), 126–152.
Fombrun, C. J. (1982). Strategies for network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s.,(2), 280– 291.
Gibson, C., & Vermeulen, F. (2003). A healthy divide: Subgroups as a stimulus for team learning behavior.,(2), 202–239.
Gilson, L. L., & Shalley, C. E. (2004). A little creativity goes a long way: An examination of teams’ engagement in creative processes.,(4), 453–470.
Grigoryan, L. (2020). Perceived similarity in multiple categorisation.,(4), 1122–1144.
Halevy, N., Halali, E., & Zlatev, J. J. (2019). Brokerage and brokering: 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organizing framework for third party influence.,(1), 215–239.
Heidl, R. A., Steensma, H. K., & Phelps, C. (2014). Divisive faultlines and the unplanned dissolutions of multipartner alliances.,(5), 1351–1371.
Henderson, M., & Argyle, M. (1986). The informal rules of working relationships.,(4), 259–275.
Homan, A. C., Gündemir, S., Buengeler, C., & van Kleef, G. A. (2020). Leading diversity: Towards a theory of functional leadership in diverse teams.,(10), 1101–1128.
Homan, A. C., van Knippenberg, D., van Kleef, G. A., & De Dreu, C. K. W. (2007). Bridging faultlines by valuing diversity: Diversity beliefs,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diverse work groups.,(5), 1189–1199.
Hutzschenreuter, T., & Horstkotte, J. (2013). Performance effects of top management team demographic faultlines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 diversification.,(6), 704–726.
Krackhardt, D. (1999). The ties that torture: Simmelian tie analysis in organizations. In S. B. Bacharach, S. B.Andrews, & D. Knoke (Eds.),ns (Vol. 16, pp. 183–210). Stamford, CT: JAI Press.
Kwon, S. W., Rondi, E., Levin, D. Z., De Massis, A., & Brass, D. J. (2020). Network brokerage: 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6), 1092–1120.
Latora, V., Nicosia, V., & Panzarasa, P. (2013). Social cohesion, structural holes, and a tale of two measures.,(3), 745–764.
Li, J., & Hambrick, D. C. (2005). Factional groups: A new vantage on demographic faultlines, conflict, and disintegration in work teams.,(5), 794–813.
Lincoln, J. R., & Miller, J. (1979). Work and friendship ties in organiza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lational networks.,(2), 181–199.
Lingo, E. L., & O'Mahony, S. (2010). Nexus work: Brokerage on creative projects.,(1), 47–81.
Ma, H., Xiao, B., Guo, H., Tang, S., & Singh, D. (2022). Modeling entrepreneurial team faultlines: Collectivism, knowledge hiding, and team stability.,, 726–736.
Mehra, A., & Schenkel, M. T. (2008). The price chameleons pay: Self‐monitoring, boundary spanning and role conflict in the workplace.,(2), 138–144.
Methot, J. R., Lepine, J. A., Podsakoff, N. P., & Christian, J. S. (2016). Are workplace friendships a mixed blessing? Exploring tradeoffs of multiplex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job performance.,(2), 311–355.
Meyer, B., & Schermuly, C. C. (2012). When beliefs are not enough: 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 of diversity faultlines, task motivation, and diversity beliefs on team performance.,(3), 456–487.
Meyer, B., Schermuly, C. C., & Kauffeld, S. (2016). That’s not my place: The interacting effects of faultlines, subgroup size, and social competence on social loafing behaviour in work groups.,(1), 31–49.
Meyer, B., Shemla, M., Li, J., & Wegge, J. (2015). On the same side of the faultline: Inclusion in the leader's subgroup and employee performance.,(3), 354–380.
Ndofor, H. A., Sirmon, D. G., & He, X. (2015). Utilizing the firm's resources: How TMT heterogeneity and resulting faultlines affect TMT tasks.,(11), 1656–1674.
O'Leary, M. B., & Mortensen, M. (2010). Go (Con)figure: Subgroups, imbalance, and isolates in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 teams.,(1), 115–131.
Porter, C. M., Woo, S. E., Allen, D. G., & Keith, M. G. (2019). How do instrumental and expressive network positions relate to turnover?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4), 511–536.
Prati, F., Crisp, R. J., & Rubini, M. (2021). 40 years of multiple social categorization: A tool for social inclusivity.,(1), 47–87.
Qi, M., Liu, Z., Kong, Y., & Yang, Z. (2022).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 faultlines on employees’ team commitmen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and team identification.,(6), 1299–1311.
Quintane, E., & Carnabuci, G. (2016). How do brokers broker? Tertius gaudens, tertius iungens, and the temporality of structural holes.,(6), 1043– 1573.
Rico, R., Molleman, E., Sánchez-Manzanares, M., & van der Vegt, G. S. (2007). The effects of diversity faultlines and team task autonomy on decision quality and social integration.,(1), 111–132.
Shipilov, A. V., & Li, S. X. (2008). Can you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 Structural holes’ influence on status accumulation and market performance in collaborative networks.,, 73–108.
Simmel, G. (1950).. New York: Free Press.
Snell, S. J., Tonidandel, S., Braddy, P. W., & Fleenor, J. W. (2014).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skill dimensions for predicting managerial effectiveness.,(6), 915–929.
Stovel, K., & Shaw, L. (2012). Brokerage.,, 139–158.
Tajfel, H., Billig, M. G., Bundy, R. P., & Flament, C. (1971).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intergroup behaviour.,(2), 149–178.
Tasselli, S., & Kilduff, M. (2018). When brokerage between friendship cliques endangers trust: A personality–network fit perspective., 61(3), 802–825.
Thatcher, S. M., & Patel, P. C. (2012). Group faultlines: A review, integration, and guide to future research.,(4), 969–1009.
Thatcher, S., Jehn, K. A., & Zanutto, E. (2003). Cracks in diversity research: The effects of diversity faultlines on conflict and performance.,(3), 217–241.
Van Knippenberg, D., De Dreu, C. K., & Homan, A. C. (2004). Work group diversity and group performance: An integrative model and research agenda.,(6), 1008–1022.
Wasserman, S., & Faust, K. (1994).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Xie, L., Zhou, J., Zong, Q., & Lu, Q. (2020). Gender diversity in R&D teams and innovation efficiency: Role of the innovation context.,(1), 103885.
Yao, J., Liu, X., & He, W. (2021). The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informational faultlines and creativity: Moderating role of team humble leadership..(12), 2793–2808.
The effect of team leaders’ Simmelian brokerage on team cooperation from the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CAO Man1, ZHAO Shuming2, ZHANG Qiuping1, Lü Hongjiang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2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Subgroups within a team can result in differentiation, discord, and eve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team. However, previous research has neglected to acknowledge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team leader in directly coordinating activities among subgroups and has failed to conduct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tripartite relationship involving the team leader, subgroups, and the entire team. The study tends to integrate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to introduce a novel concept, team leaders’ simmelian brokerage, that is, team leaders acting as brokers between two or more subgroups, and explore its reconciliation of subgroups' conflicts and subsequent facilitations of team cooperation. This study not only advances the literature on subgroups,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subgroup management.
team leader, Simmelian brokerage, subgroup, team cooperation
2023-03-07
*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2202032, 71832007, 72272032, 71972139, 72262010 ), 江蘇省博士后科研資助計劃項目(2021K609C)。
呂鴻江, E-mail: Lvhongjiang@seu.edu.cn
B849: C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