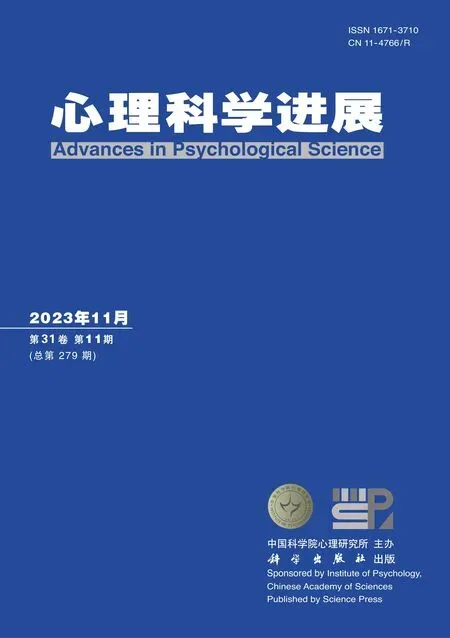敬畏的親社會效應:小我與真我的作用*
趙 越 胡小勇 馬佳馨
敬畏的親社會效應:小我與真我的作用*
趙 越 胡小勇 馬佳馨
(西南大學心理學部, 西南大學人格與認知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重慶 400715)
敬畏是一種對浩瀚的刺激以及現有心理結構無法適應的刺激的情感反應。大量實證證據顯示, 敬畏可以促進各種形式的親社會行為。至于其中的心理機制, 小我假說認為, 誘發敬畏體驗的浩瀚刺激會導致自我的渺小感, 推動個體的注意力從自我轉移至他人, 進而促進了親社會行為; 真我假說則認為, 敬畏有助于促進個體的注意力從日常的世俗關注向更大的精神存在轉移, 激發了個體對其真實自我的追求, 進而促進了親社會行為。小我與真我假說可以在“大二”框架下進行整合, 即敬畏在自我的能動維度(真我)和共生維度(小我)上通過兩條平行的路徑促進親社會行為的產生。未來研究需要更深入地探討敬畏的親社會效應的心理機制, 并在此基礎上開發出促進捐贈等親社會行為的干預措施, 以期為第三次分配戰略的有效實施提供心理學方案。
敬畏, 親社會性, 小我, 真我
從山頂上看風景, 盯著被星星點綴的黑暗天空, 聽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想法被表達出來……所有這些情境都能誘發一種特殊的情感:敬畏。在社會學、哲學和宗教等領域中, 人們對敬畏的興趣始終如一, 認為這種情感與審美反應、政治變化和宗教轉變密切相關(Burke, 1990; Keltner & Haidt, 2003; Weber, 1978)。但在心理學研究中, 敬畏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幾乎沒有受到重視。它能被作為當代心理學研究的重要主題主要得益于Keltner和Haidt (2003)的開創性工作。建立在Maslow (1964)和McDougall (1910)等少數先驅者的研究基礎之上, Keltner和Haidt (2003)首次提出了敬畏的原型模型, 對敬畏進行了系統的概念化; 指出敬畏可以重新定位人們的生活、目標和價值觀; 并認為令人敬畏的事件是使個人成長和改變的最快、最有力的方法之一。最近的研究發現, 敬畏會產生深遠的社會影響。敬畏可以讓人們感覺到與他人聯系在一起(Bai et al., 2017; 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 認同更寬泛的群體類別, 如“人類”或“地球居民” (Shiota et al., 2007; 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 產生親社會行為(Piff et al., 2015; Prade & Saroglou, 2016; Stellar et al., 2017)。這種通常由非社會性刺激引發的情感為什么會導致親社會的結果?基于小我假說與真我假說, 本文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回答, 系統地探討了自我不同方面在敬畏的親社會效應中發揮的作用。就現實意義而言, 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將有助于推進第三次分配戰略的實施。第三次分配指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 通過個人收入轉移、個人自愿繳納和捐獻等非強制方式進行的再一次分配(厲以寧, 1993)。作為一種典型的親社會行為, 慈善捐贈被認為是第三次分配的基礎及主要載體(鄧國勝, 2021)。在探明機制的基礎上開發出有效的干預策略, 充分發揮敬畏的積極作用, 將有望為推進以慈善捐贈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戰略提供科學的心理學方案。
1 敬畏
敬畏(awe)是一種對寬廣、浩大的刺激(例如, 高大的樹木、日落), 以及現有心理結構無法適應的刺激產生的情緒反應(Perlin & Li, 2020)。它是一種邊界模糊但具有核心特征的情緒, 即浩瀚感和順應的需要(Keltner & Haidt, 2003)。浩瀚感(perceived vastness)是指對刺激物的感知, 認為它在知覺上和/或概念上是巨大的。例如, 觀看宏偉的大峽谷和理解復雜的相對論都可以算作敬畏的潛在誘因。更關鍵的是, 這種刺激極大地擴展了觀察者在某些維度或領域的通常參照系, 產生了順應的需要。順應的需要(need for accommodation)來源于皮亞杰的認知理論, 指的是當所面臨的刺激和現存的認知圖式不符時, 個體根據新輸入的刺激來改變原有認知圖式的需要。例如, 在理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時, 人們必須改變他們原有的對時間和空間的理解。簡而言之, 敬畏產生于一種由比自我或自我的已有認知參照框架大得多的刺激所引起的感覺, 即浩瀚感; 而這種感覺需要新的心理表征來理解, 即順應的需要(趙小紅等, 2021; Keltner & Haidt, 2003; Monroy & Keltner, 2022; Weger & Wagemann, 2021)。
敬畏的核心特征決定了某種情緒能否被歸類于敬畏家族, 所有涉及到以上兩個特征的情緒體驗都可以被認為是敬畏家族中的一員(Keltner & Haidt, 2003)。此外, Keltner和Haidt (2003)還確定了敬畏的五大邊緣特征, 邊緣特征則解釋了不同敬畏狀態之間的差異, 這些特征通常與敬畏的誘發因素有關, 可以對敬畏體驗進行調節, 從而引起不同種類的敬畏, 導致了這種體驗的多樣性, 包括美的敬畏、能力的敬畏、美德的敬畏、超自然的敬畏與威脅的敬畏(周凌霄等, 2022; Chirico & Yaden, 2018; Keltner & Haidt, 2003)。具體來說, 基于美的敬畏指的是觀看具有美感的事物時所引發的敬畏體驗, 這些體驗帶有審美愉悅的味道, 例如觀看兵馬俑、金字塔時的體驗(Schindler et al., 2017)。基于能力的敬畏指的是個體被具有卓越能力、天賦和技能的人引發的伴隨欽佩感的敬畏體驗, 例如觀看一個優秀運動員比賽時的體驗(Onu et al., 2016)。基于美德的敬畏指的是個體被表現出美德或品格力量的人所引發的帶有提升感的敬畏體驗(Haidt, 2003), 例如對于每一個中國人來說讀到袁隆平的生平時產生的體驗。基于超自然的敬畏則指個體所具有的帶有宗教或精神成分的敬畏體驗, 常出現在個體感知到上帝或其他超自然實體的時候并伴隨著不可思議的感覺(Bussing, 2021)。基于威脅的敬畏指的是個體面對威脅和危險時產生的帶有恐懼感的敬畏, 例如面對具有威脅性的自然景象(暴風雨)時產生的體驗(Gordon et al., 2017)。所有這些不同類型的敬畏體驗, 只有在敬畏的核心特征(浩瀚感與順應的需要)被確立后才會出現。
2 敬畏的親社會效應
盡管敬畏常常由非社會性的刺激所引發, 它卻具有深刻的社會效應。典型的敬畏被歸類為積極情緒中的一員, 因為它最經常被體驗為積極的價值(董蕊等, 2013; Shiota et al., 2007)。作為一種積極的情緒, 敬畏對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有好處。敬畏可以減弱個體的自我意識(Piff et al., 2015), 使人們感到與他人或集體緊密相連(Bai et al., 2017), 并增強生命意義感(Dai et al., 2022)、幸福感(Sturm et al., 2022)和謙遜感(Stellar et al., 2018)。此外, 經歷過敬畏的個體表現出了較高的合作性(Joye & Bolderdijk, 2015)、較低的攻擊傾向(Yang et al., 2016)和對金錢的欲望(Jiang et al., 2018), 并更少地采取道德冒險行為(李明等, 2019)。更重要的是, 敬畏似乎對個體的親社會性產生了廣泛的促進作用。在多項相關研究中, 研究者發現特質敬畏與被試在親社會傾向測量上的得分呈正相關(Fu et al., 2022; Jiao & Luo, 2022; Li et al., 2019; Lin et al., 2020)。
無論是在以幫助為主還是以分享為主的親社會行為中, 敬畏的親社會效應都得到了實驗證據的支持。通常, 研究者認為以幫助為主和以分享為主的親社會行為分別反映了人們對工具需求和未滿足的物質欲望的反應(Dunfield, 2014)。許多實驗研究都支持了敬畏對幫助行為的促進作用(Guan et al., 2019; Piff et al., 2015; Rudd et al., 2012)。例如, 在自然情景中, Piff等人(2015)通過讓被試沉浸在一片高聳的桉樹林中來誘導敬畏狀態, 并與注視高大建筑物的條件進行了對比。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 敬畏條件下的被試向實驗者提供了更多的幫助, 表現為幫助假裝無意掉落11根鉛筆的實驗者撿回了更多的筆。此外, 敬畏同樣促進了人們付出更多時間來幫助他人(Guan et al., 2019)或慈善機構(Rudd et al., 2012)的傾向。一項在組織背景下展開的研究同樣發現, 對在工作場所中經歷的敬畏的回憶, 其中包括了對組織或同事能力的敬畏, 增加了被試以較低報酬幫助研究人員進行另一項研究的意向, 以及后續的真實幫助行為(Meng & Wang, 2022)。對于分享行為, 大部分研究得到了一致的結論(Guan et al., 2019; Luo et al., 2022; Piff et al., 2015)。例如, 在COVID-19大流行的背景下, Luo等人(2022)引導被試回憶并沉浸于某個在疫情期間讓他感到敬畏的時刻, 結果發現, 回憶醫務工作者不顧自己的健康, 堅持在艱難的環境中戰斗等敬畏時刻的實驗組被試比娛樂組和中性組, 捐贈物資的意愿更強、捐贈金錢的數量更多。這一結果支持了基于美德的敬畏對分享行為的促進作用。然而, 也有少數研究得到了不一致的結論(Joye & Bolderdijk, 2015; Rudd et al., 2012)。例如, Joye和Bolderdijk (2015)發現由自然景觀誘發的敬畏雖然強化了親社會價值觀, 但沒有提高人們向受災者分享金錢或物品的意愿。但他們認為這一結果很可能受到了額外變量的干擾而不反映真實的效應。此外, 一些研究者認為在上述的研究中, 外顯的親社會性測量可能會夸大人們在敬畏誘導后表現出的善良傾向, 因此他們進一步采取了一種內隱的方法測量親社會傾向, 結果發現對敬畏的誘導會增加自發的慷慨和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幫助的親社會意圖, 這些幫助情境被隱藏在一些看似與親社會無關的情景中以掩蓋真實的實驗目的(Prade & Saroglou, 2016)。總之, 上述發現為不同類型敬畏的親社會效應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包括對自然之美、對他人的美德和能力的敬畏。這些敬畏都不涉及到威脅、恐懼或害怕的感覺, 被研究者們認為具有積極的情感基調(Gordon et al., 2017; Keltner & Haidt, 2003)。這支持了積極敬畏對親社會行為的促進作用。
綜上可知, 先前的多數研究都認為敬畏是一種積極的情緒狀態(Cao et al., 2020; Piff et al., 2015)。然而, 在近期開展的部分研究關注了敬畏的消極方面——基于威脅的敬畏。這是一種帶有恐懼色彩的敬畏, 通常由破壞性的自然災害(如海嘯和龍卷風)或專制的獨裁者所誘發(Gordon et al., 2017)。基于威脅的敬畏是否能增加親社會性?一些研究者認為基于威脅的敬畏同樣可以促進親社會性(Guan et al., 2019; Piff et al., 2015; Seo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2)。例如, Piff等人(2015)探討了消極的和非自然的敬畏體驗對親社會傾向的作用。研究過程中, 使用威脅性的自然刺激(龍卷風、火山)和非自然的刺激(彩色水滴與一碗牛奶的碰撞)誘發被試的敬畏狀態。結果表明, 消極的敬畏和非自然的敬畏均可以顯著地增加被試的親社會傾向。后續研究者將消極形式和積極形式的敬畏加以對比。被試觀看誘發積極敬畏的自然全景、誘發消極敬畏的自然災害視頻或中性對照視頻。誘發消極敬畏的視頻來自BBC的《地球星球》, 由在火山、龍卷風和海嘯等自然災害中拍攝的片段組成(Gordon et al., 2017; Jiang et al., 2018; Piff et al., 2015)。情緒評估表明, 積極和消極的視頻能夠成功地喚起不同類型的敬畏, 在消極敬畏下被試感受到了更強烈的威脅水平。隨后完成親社會傾向測量。結果表明, 在積極和消極敬畏條件下的被試均比在中性條件下的被試傾向于向失業的陌生人捐出更多的金錢, 并且兩種條件之間沒有顯著的差異(Guan et al., 2019)。上述研究為威脅敬畏的親社會效應提供了直接的實證證據。而另一些研究者則認為威脅敬畏與恐懼、較低的自我控制和較高的情境控制有關, 這將導致較低的親社會性(Gordon et al., 2017; 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例如, Septianto, Nasution等人(2022)使用慈善廣告操縱基于威脅的敬畏, 通過在廣告中加入(或不加入)洪水的圖像來激發高水平(或低水平)的威脅性敬畏, 并通過在廣告中強調“為什么”或“如何”的信息操縱建構水平。盡管威脅敬畏的主效應不顯著, 但在低建構水平的條件下, 研究者發現經歷了高水平威脅敬畏的被試會做出更少的慈善捐贈。總之, 基于威脅的敬畏會對親社會行為產生兩種相反的效應, 在這背后可能存在著不同的心理機制。
3 敬畏影響親社會行為的心理機制
依據情緒的社會功能取向可知, 情緒會影響與自我相關的認知, 從而使個體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Bai et al., 2017)。研究顯示, 短暫的情緒狀態可以以系統的方式對自我概念產生影響(Oveis et al., 2010; Tracy et al., 2014)。也就是說, 情緒可以通過影響自我這一核心中介促進人類在群體中生活的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Bai et al., 2017)。那么, 敬畏的親社會效應是否是通過自我這一核心機制起作用的?研究者們給出了肯定的回答(Jiang & Sedikides, 2022; Piff et al., 2015; Shiota et al., 2007; Stellar, 2021)。
3.1 小我假說
通過將注意力集中在誘發敬畏體驗的浩瀚刺激物上, 敬畏將促進個體產生一種“小我” (small self)的感覺, 這是一種感到自我渺小、減弱并感到無足輕重的感覺(Tyson et al., 2022)。小我假說提出“小我”是敬畏體驗促進親社會反應的核心機制(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根據這一立場, 敬畏將通過減少自我導向的關注來促進親社會性, 這反過來使更多的注意力可以用于他人導向的關注(Perlin & Li, 2020)。盡管不同的研究者對于小我的概念進行了不同的操作(即相對于自我的浩瀚感、自我減弱感和感知的自我大小), 但小我的中介作用仍得到了大量實證證據的支持。例如, 研究發現觀看令人嘆為觀止的風景圖或視頻、站在自然中注視高聳的樹木以及每天進行敬畏之行都有助于產生自我渺小感, 并促進個體的親社會性(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 Sturm et al., 2022)。具體而言, Piff等人(2015)使用視頻法來誘導敬畏感, 被試被隨機分配到敬畏、娛樂或中性條件中的一個, 敬畏條件下, 向被試呈現來自BBC地球系列的自然片段, 該片段由風景優美的遠景、山脈、平原、森林和宏大的峽谷所組成。而后, 被試完成了對小我的測量, 如“我覺得自己很渺小或無足輕重”或“我覺得有比自己更偉大的東西存在”, 這些項目反映了相對于自我的浩瀚感(對比自己更偉大的事物的感知)和隨之而來的自我減弱感(自己的存在和目標相對來說是無足輕重的)。最后, 通過獨裁者游戲考察被試的親社會水平。結果發現, 與娛樂和中性條件的被試相比, 觀看敬畏視頻的被試表現得更加慷慨。更重要的是, 中介分析表明上述效應是通過小我來中介的。后續的研究進一步采用了非言語方法來測量小我的構念, 被稱之為感知到的自我大小(perceived self-size), 他們發現經歷過敬畏的被試會使用更小的圓圈、畫出更小的圖形或簽署更小的“我”來代表自己, 進而促進積極的社會效應, 并且這些起源于個人主義文化的發現同樣也適用于集體主義文化(Bai et al., 2017)。總之, 像上述研究(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所表明的那樣, 小我是一種由對比自我更浩瀚的刺激物的感知所導致的自我渺小、減弱且無足輕重的感覺(Tyson et al., 2022)。實證證據也初步證實了小我感在敬畏的親社會效應中起到了中介的作用。
然而, 隨著研究深入, 研究者發現在回答一些問題時“小我”的解釋力存在不足。問題之一在于, 敬畏具有變革性(transformative)能力, 它讓人經歷了人生中的一個關鍵時刻, 啟動了一個改變的過程(Chirico & Yaden, 2018; Keltner & Haidt, 2003; Maslow, 1962; Stellar et al., 2017)。Keltner和Haidt (2003)指出, 敬畏可以改變人, 重新定位人們的目標和價值觀, 引發敬畏的事件可能是個人成長和改變最迅速、最有力方法之一。其他定性和理論工作也支持了這一觀點, 他們認為敬畏為個體提供了反思自己人生并重新評估自我價值的機會(Bonner & Friedman, 2011)。總之, 敬畏的體驗可能會促使人們開放地探索外部世界并思考更深層次的問題(Danvers & Shiota, 2017; Nelson- Coffey et al., 2019)。簡而言之, 就是成長。但這些成長和改變的過程實際上如何展開, 又將怎樣影響敬畏的親社會效應?這些問題不能被小我機制強調的注意力轉移所解釋(Perlin & Li, 2020)。換言之, 如果自我減弱并感到無足輕重, 是什么驅使個體進行反思并發起變革追求呢?對此, 小我的中介作用不能給出滿意的回答。更廣泛地說, 敬畏的自我渺小效應在三個方面受到了批評(Perlin & Li, 2020)。首先, 自我導向和他人導向的關注并不是互斥的。將注意力從自己身上轉移開并不需要將注意力集中在他人身上, 反之亦然。其次, 關注他人不一定會增加有利于他人的動機。第三, 與以上的論點類似, 小我不能解釋敬畏的變革能力。如果可以的話, 正如Tyson等人(2022)得出的結論, 小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我的心理擴張, 而非縮小”。
3.2 真我假說
針對“小我”的不足, 研究者們提出了真我假說, 他們認為由敬畏引發的真實自我可能是實現自我轉變、個人成長和心理成熟的關鍵(Jiang & Sedikides, 2022)。真實自我(authentic self)被定義為一個人與真實或真正的自我相一致的感知, 即一個人的自我是真實的或不加修飾的感覺(Sedikides et al., 2019)。該假說指出, 敬畏激發了個體對真實自我的追求, 真我會提醒個體他們的關鍵價值得到了維護, 并激勵他們采取相應的行為, 如關注他人利益的行為(Schmader & Sedikides, 2018; Sedikides et al., 2019)。具體而言, 敬畏體驗有助于促進自我超越, 將個體的注意力從日常平凡瑣事轉向更大的精神存在(Chirico & Yaden, 2018; Jiang et al., 2018; Yaden et al., 2017); 這提供了一種自我疏離或角色疏離的機會, 使個體得以與自己保持心理距離, 從而為反思留下空間, 最終促進了對真我的追求(Emmerich & Rigotti, 2017; Kross & Ayduk, 2017)。對真實自我的追求可能通過自我反思和自我探索的過程體現成長。一些研究者推測敬畏會激勵人們對生命意義的尋求, 其中包括了對真實自我的尋求(Danvers et al., 2016)。Perlin和Li (2020)認為這種對意義和真實自我的尋求實際反映了一種深入的自我探索和改變的過程, 并進一步認為當人們進行自我反思和探索時, 注意力被引向自我的更深層、更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說, 對個人感到有價值和重要的東西進行探索。因此, 由敬畏激發的真實自我追求可能迫使我們重新探索和評估最深切的個人目標與關鍵價值, 讓我們意識到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 由此實現自我成長與轉變。通過強調個人的關鍵價值并激勵人們采取相應的行為(Erickson, 1995; Schmader & Sedikides, 2018; Sedikides et al., 2019), 對真實自我的追求繼而影響了兩種親社會行為:一方面, 促進了一般的親社會性, 即旨在造福他人或集體的行為。因為, 這被認為與人們的真實自我和關鍵價值有廣泛的聯系。事實上, 真實性被發現與關心他人利益正面相關(Koltko- Rivera, 2006; Lenton et al., 2013)。而另一方面, 阻礙了不真實的親社會性, 即有利于他人或集體但違背真實自我的行為, 例如寫一封違背自己對候選者真實看法的推薦信(Schmader & Sedikides, 2018; Sedikides et al., 2019)。這是因為, 提醒個體其真實自我就會讓他們不愿意以與之抵觸的方式行動。
真我假說的基本觀點得到了初步的實證支持。在相關研究中, Jiang和Sedikides (2022, study14)檢驗了真我在敬畏和兩類親社會行為之間起到的作用, 發現在兩種親社會行為中, 真實自我追求的中介效應均是顯著的, 由敬畏引發的真實自我追求導致了一般親社會性的增加和不真實親社會性的減少。上述發現也在實驗室環境中得到了進一步驗證, 研究者使用回憶任務來操縱敬畏, 結果發現真我追求中介了敬畏對一般親社會性的影響(Jiang & Sedikides, 2022, study11)。此外, 由敬畏操縱引發的真實自我追求還可以削弱不真實的親社會性。在后續研究中, 研究者繼續采用相同的方法操縱敬畏感并測量真實自我追求。他們還測量了不真實的親社會性, 向被試展示了一個兩難故事, 并要求他們盡可能生動地想象自己是主角。在故事中, 陳某的主管向他求助, 以獲得區域經理晉升評估中其他候選人的材料。在這里, 幫助行為違反了陳某內心深處所看重的公正原則, 但拒絕幫助則會對他在公司中的職業發展造成傷害。隨后, 測量被試的幫助傾向以得到一個不真實的親社會指數。結果發現, 由敬畏引發的真實自我追求減少了不真實的親社會性(Jiang & Sedikides, 2022, study12)。
3.3 “大二”視角下的小我與真我整合機制
小我假說和真我假說分別從注意和成長的角度對敬畏促進親社會行為的心理機制給出了不同的答案。那么, 在敬畏促進親社會性的過程中二者究竟是怎樣的關系?當前研究假說似乎可以在“大二”框架下進行完善與整合, 基于“大二”框架, 敬畏將通過小我與真我的平行中介同時在自我的不同維度上促進親社會行為的產生。
“大二”, 即能動(agency)與共生(communion), 有助于整合小我與真我在敬畏的親社會效應中起到的作用。能動意為個體通過權力、控制等方式追求自身的獨立; 共生意為個體通過關愛、交流等方式融入社會和群體(Abele et al., 2016)。基于進化的視角, 能動和共生抓住了人類生活中所面臨的兩個核心挑戰:追求個人目標和屬于社會群體(Azoulay et al., 2022; Hogan, 1982)。能動與共生維度已被證實可以為分析人格、社會認知、價值觀和動機等領域提供一個有效的框架(Abele & Wojciszke, 2014; Fiske et al., 2007; Paulhus & John, 1998)。重要的是, 作為人類行為的基本模式, 能動與共生已經被證明可以映射到自我之上。對自我描述進行的內容分析發現, 它們可以被可靠地歸類于能動與共生這兩個維度之上(Abele & Bruckmüller, 2013; Diehl et al., 2004; Uchronski, 2008)。這表明能動和共生是自我的基本維度, 并可以在個體的自我表征中被有意識地使用(Diehl et al., 2004)。理論及實證研究指出, 小我屬于共生維度, 它反映了人類面臨著的第一個挑戰(屬于社會群體)在自我中的解決; 真我則是一種自主的、自我決定的自我, 屬于能動維度, 它反映了人類面臨著的第二個挑戰(追求個人目標)在自我中的解決(Diehl et al., 2004; Stell, 2018)。
小我通常被表征為一種親和性、順從性的自我, 屬于自我概念的共生維度(Diehl et al., 2004; Stell, 2018)。從理論起源上看, 小我的提出基于敬畏的適應性與功能性取向(Bai et al., 2017; Keltner & Haidt, 2003)。該取向認為敬畏最初可能是作為一種對強大的、高地位的他人的尊敬性反應而出現的, 而后逐漸拓展到其他具有浩瀚性特點的刺激上(Keltner & Haidt, 2003)。在這種反應中涉及到將自己的利益和目標服從于強大的領導者的傾向, 這具有適應性的意義, 因為它通過非暴力手段構建了一種集體等級制度, 對人類的生存很重要(Fiske, 1991; Keltner & Haidt, 1999)。小我研究認為上述理論特征的核心在于由敬畏誘發的小我感(Bai et al., 2017)。在敬畏體驗中, 與浩瀚性的刺激物的接觸伴隨著一種自我在比較中被減弱的感知, 使體驗者覺得自己擁有一個“小我”, 促進個體面向他人并融入集體(Stellar et al., 2017)。根據其理論提出, 這種自我表征被認為是一種親和性、順從性的自我, 因而屬于自我概念的共生維度。一些其他證據也支持小我可以被歸類為敬畏對自我共生維度的作用(Bai et al., 2017; Diehl et al., 2004; Perlin & Li, 2020)。例如, Diehl等(2004)根據以往測量能動與共生維度的量表總結出一份可用于編碼自我特征的詞匯清單, 在該清單中反映小我的“服從的”“謙遜的”等形容詞被認為是共生維度的典型代表。可見, 小我是一種共生性的自我表征。
真我通常被認為是獨特的、自我決定的, 因此屬于自我的能動維度(Maslow, 1962)。從理論起源上看, 真我假說的提出試圖解釋一個小我假說難以解釋的問題, 即敬畏具有的變革能力(Jiang & Sedikides, 2022)。真我假說認為, 通過激勵真實自我, 敬畏可以影響人們的關鍵目標和價值, 并由此促進自我的成長和改變(Danvers & Shiota, 2017; Nelson-Coffey et al., 2019)。成長和改變被視為自我能動維度的重要方面(Bakan, 1966)。此外, 當個體得以成為他真正的自我, 感到自己是活動和感知的創造性中心, 就更有自我決定權、更具能動性并比其他時候更具有“自由意志” (Maslow, 1962)。該觀點強調了由敬畏激發的真實自我具有的獨特性和自我決定性, 表明真我應當被歸類為一種能動的自我表征。實證研究發現, 特質敬畏與能動呈正相關, 并與個體的從眾傾向呈負相關(Stell, 2018)。對外部壓力的遵從往往被認為與真實性相反(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可見, 真我是一種能動性的自我表征。
能動與共生屬于自我的兩個不同維度, 二者以一種互動的、相互平衡的、相互促進的方式發展; 那些平衡地整合了能動和共生的個體往往表現出深刻的親社會動機(Frimer et al., 2011; Mansfield & McAdams, 1996)。這意味著, 積極敬畏將在自我的兩個基本維度上通過兩條平行的路徑共同促進親社會性:在共生維度上, 敬畏促進了小我的產生, 進而導致親社會行為; 在能動維度上, 敬畏促進了真我的產生, 進而導致親社會行為。初步的實證證據間接支持了這一觀點, 發現小我無法中介敬畏對真實自我追求的影響(Jiang & Sedikides, 2022)。這一結果表明小我無法解釋真我所發揮的作用, 真我的作用在小我的效應之外也能得到很好的證實。這從實證上驗證了真我假說的確指出了敬畏通向親社會性的另一條路徑, 即能動的路徑。能動路徑將有助于解釋敬畏對一般親社會性和不真實親社會性的不同效應, 特別是對不真實的親社會性。具體而言, 敬畏對不真實親社會性的阻礙作用表明, 如果某種行為違背了一個人的真實自我和關鍵價值, 盡管這種行為有利于他人或集體, 個體也不會選擇去做。這反映了由真實自我激發的親社會行為是一種自主的、自我決定的而非受控的行為(van den Bosch & Taris, 2018)。那么敬畏的親社會效應一定不是僅僅基于自我渺小感和對他人的注意力轉移; 相反, 通過誘發真實自我, 這些親社會效應可能同時基于一個人對他真正的自己和自己的核心動機的深化理解(Perlin & Li, 2020)。這同樣證明了真我將通過一條能動的路徑將敬畏與親社會行為相聯系。因此, 積極敬畏將在自我的能動維度(通過真我的中介)和共生維度(通過小我的中介)上通過兩條平行的路徑共同促進親社會行為的產生。
為什么基于威脅的敬畏會對親社會性產生兩種截然相反的效應?“大二”框架同樣有助于理解背后的機制。與積極的敬畏類似, 在共生維度上, 消極敬畏將通過小我促進親社會行為的增加(Piff et al., 2015)。具體來說, 威脅的敬畏同樣由一個被評價為巨大的刺激物誘發(Shiota et al., 2007), 它被認為可以促進小我感, 提高對他人的關注(Piff et al., 2015), 這將導致更高的親社會性。然而, 與積極敬畏的不同之處在于, 在能動維度上, 基于威脅的敬畏將導致無力感的增加或效能感的降低(能動的反面), 并因此導致親社會行為的減少(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具體而言, 當試圖適應一個巨大的、有威脅的刺激時, 基于威脅的敬畏會伴隨著恐懼感(Chaudhury et al., 2022; Gordon et al., 2017)。恐懼與較低的控制感有關(Keltner et al., 2003), 這種感覺導致了無力感的增強(Gordon et al., 2017), 降低了個人對其行動效能的感知(Bri?ol et al., 2007)。如果人們覺得他們缺乏足夠的效能來改變現狀(即不相信他們采取的措施可以有效地促進幫助), 他們可能不會追求親社會行為(Jin & He, 2018; 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因此, 高水平的威脅敬畏導致個體產生無力感, 進而減少親社會行為。
在能動維度上, 消極敬畏表現出與積極敬畏不同的功能, 其核心原因在于:這種消極的敬畏體驗以威脅性為主要特征, 會導致控制感和確定性的減少、恐懼和焦慮的感覺增加和交感神經系統的喚醒(Gordon et al., 2017)。那么在威脅的背景下, 敬畏對自我的影響是更消極和基于恐懼的, 自我控制感和確定性的降低最終引發個體的無能為力感(Gordon et al., 2017), 即降低了個體的能動取向(Bri?ol et al., 2007)。因此, 不同于積極敬畏領域中得到的一致結論, 基于威脅的敬畏對親社會行為產生了不同的效應:一方面, 通過在共生維度上促進小我感, 人們希望做出親社會的行為; 另一方面, 由于威脅的存在, 行動者同時在能動取向上體驗到無力感, 覺得缺乏足夠的效力來做出改變, 進而抑制了親社會行為的產生(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鑒于這種矛盾性的存在, 消極敬畏的親社會效應可能取決于個體對威脅性的感受和應對。例如, 持有增長論的個體認為威脅和挑戰代表著成長的機會, 在對威脅和挑戰的反應中, 他們對自己完成特定任務時的行動效能表現出更積極的判斷(Martocchio, 1994)。因此, 當遇到誘發威脅敬畏的刺激物時, 持有增長論(相對于實體論)的行動者更有可能期望他們的親社會行為具有更高的效能, 這增加了他們在經歷威脅敬畏時的親社會行為(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
4 小結與展望
敬畏感是一種復雜的、與自我相關的情緒。大量實證證據顯示, 積極敬畏可以促進各種形式的親社會行為。至于其中的心理機制, 小我假說認為, 誘發敬畏體驗的浩瀚刺激會導致自我的渺小感, 推動個體的注意力從自我轉移至他人, 進而促進了親社會行為; 而真我假說則認為, 敬畏激發了個體對真實自我的追求, 真我會提醒個體, 他們的關鍵價值得到了維護, 并激勵他們采取關注他人利益的行為。小我與真我假說可以在“大二”框架下整合, 即敬畏在自我的能動維度(真我)和共生維度(小我)上通過兩條平行的路徑促進親社會行為的產生。該領域的研究有助于探明情感對人類社會性的核心作用, 并對開發出促進捐贈等親社會行為的有效干預方案具有啟發性意義, 對于第三次分配戰略的有效實施具有參考價值。然而, 本領域的研究還存在如下不足, 需要未來予以深入考察。
首先, 未來研究需要進一步考察敬畏對親社會行為的影響是否具有普遍性。雖然大多數研究都證實了積極敬畏對親社會性的促進作用, 初步的證據顯示, 在外顯和內隱的親社會測量中都可靠地發現敬畏的親社會效應(Lin et al., 2020; Prade & Saroglou, 2016)。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得到了不一致的發現(Joye & Bolderdijk, 2015; Luo et al., 2022; Meng & Wang, 2022)。例如, Joye和Bolderdijk (2015)發現敬畏沒有提高人們幫助受災者、捐錢、捐物和獻血的意愿。盡管研究者們認為這很可能是由于受到了實驗中采用的特殊測量方法的干擾。但除此之外, 還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敬畏的親社會效應, 未來需要更多研究加以檢驗。值得注意的是, 隨著研究的深入, 敬畏的親社會研究由傳統的積極敬畏領域拓展到帶有恐懼色彩的威脅敬畏。當前, 基于威脅的敬畏與親社會行為之間的關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發現, 一種認為與積極敬畏一樣, 基于威脅的敬畏也能帶來更多的親社會行為, 然而另一些研究則發現它導致了更少的親社會行為。初步證據發現內隱理論等因素在其中起到調節作用(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 未來研究應更加深入地探索其邊界條件, 發揮威脅敬畏對親社會行為的促進作用。
第二, 對于小我與真我在敬畏與親社會行為之間的作用, 需要未來研究在理論和實證層面進一步豐富與完善。小我研究強調敬畏會減少自我導向的關注, 進而增加他人導向的關注, 這種注意轉移將自我導向的關注與他人導向的關注對立了起來(Perlin & Li, 2020)。然而, 人類是在合作的、相互依賴的環境中進化的, 在這種環境中, 關注自我和關注他人是無法分離的, 它們密切地交織在一起(Over, 2016)。人類的關注點不僅包括“我?關注” (對自我福祉的自私關注)和“你?關注” (對他人的親社會關注), 還包括“我們?關注”, 即對相互依賴的、與我們的利益有關的集體關注(Tomasello, 2016, 2019)。因此, 敬畏可能通過將“我?關注”轉移至“我們?關注”促進親社會行為。那么, 這一觀點是否成立, 需要未來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予以進一步考察。對于真我研究需要關注的是, 真實自我往往包含著許多相互矛盾的成分, 有好的、社會期望的部分和壞的、違背社會期望的部分(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 那么敬畏如何通過真我來促進親社會行為呢?從動機轉變的角度來理解真實自我將有助于回答這一問題。敬畏可能會引起一系列的動機轉變, 研究發現敬畏促進了對個體目標層級中的高層次動機的關注, 并減弱了對低層次動機的關注(Bai et al., 2021; Shiota et al., 2007;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因為人們的社會理想動機往往比不理想動機在目標層級中更重要、更優先, 所以通過促進目標層級中的高層次動機, 敬畏激勵了對真實自我中好的、社會期待的部分的追求, 最終導致了親社會行為。該觀點在動機的層面上細化了真我在敬畏的親社會效應中發揮的作用, 但還需要未來實證研究予以深入考察。更值得關注的是, “大二”框架下的理論認為, 平衡地整合了能動和共生的個體往往表現出深刻的親社會動機; 敬畏在自我的共生維度和能動維度上通過小我與真我的平行中介促進親社會行為的產生, 這一觀點能否經得起檢驗, 需要未來研究予以充分考察。
第三, 該領域研究對未來開發出更多促進捐贈等親社會行為的有效干預方案具有啟發意義。目前, 已有學者開發出了一種被稱為“敬畏之行”的干預(Sturm et al., 2022)。該干預為期8周, 每周進行15分鐘的戶外散步, 通過引導被試努力挖掘出在散步中體驗到的驚奇感受, 并盡量每周更換一個新地點來培養敬畏感。研究顯示, “敬畏之行”有助于“小我”的體驗, 并促進了更多的親社會積極情緒。更為重要的是, 除了在散步過程中產生瞬間的情緒體驗變化之外, 這種干預措施的效果甚至拓展到了干預的背景之外, 鼓勵了日常生活中的共情等親社會情感。這一發現對于塑造日常生活中的親社會行為也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此外, 虛擬現實技術(Chirico & Gaggioli, 2019)也被證明是促進敬畏的一種手段。該技術能夠在虛擬的環境中產生存在感, 這種特殊體驗能夠增加敬畏的強度, 進而促進親社會行為。其他的證據顯示, 正念訓練或每日日記可能是有效的干預措施。例如, Waller等人(2021)發現, 進行正念呼吸練習可以增加敬畏的感覺。每日日記法可能也是一個簡單有效的干預方式, 該方法有望通過向被試介紹敬畏的定義并指導其完成每日敬畏日記描述當天經歷的敬畏體驗來增加敬畏情緒(Bai et al., 2017)。除了對敬畏本身進行干預外, 針對敬畏引發小我與真我的轉變進而促進親社會性的核心機制, 開發出以自我轉變為核心的干預方案應該是未來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真我的心理機制表明, 如果想要使親社會行為得到最有效的實施, 它需要符合一個人的真實自我(Schmader & Sedikides, 2018)。因此, 慈善組織可能需要分析其潛在捐贈者的真實自我追求并據此定制他們的慈善活動, 使其與潛在捐贈者的真實自我追求相交, 或部分滿足其追求(Jiang & Sedikides, 2022)。此外, 自然災害是威脅敬畏的重要誘因, 在這些災害中產生了巨大的受助需求, 一個有效的干預措施是定制高建構水平的慈善廣告。研究發現向被試呈現強調“為什么”的廣告時, 經歷威脅敬畏的被試將報告出更高的捐贈意向(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總之, 該領域干預方案的開發將有助于充分利用敬畏對捐贈等親社會行為的積極作用, 從而為推進以慈善捐贈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戰略提供科學的心理學方案。
鄧國勝. (2021). 第三次分配的價值與政策選擇.(24), 42?45.
董蕊, 彭凱平, 喻豐. (2013). 積極情緒之敬畏.(11), 1996?2005.
李明, 李敏維, 李文俏, 高定國. (2019). 敬畏對道德冒險行為的影響.(1), 48?58.
厲以寧. (1993). 發展市場經濟與為人民服務.(10), 6.
趙小紅, 童薇, 陳桃林, 吳冬梅, 張蕾, 陳正舉, … 唐小蓉. (2021). 敬畏的心理模型及其認知神經機制.(3), 520?530.
周凌霄, 李姍殷, 彭凱平, 王陽, 管芳. (2022). 敬畏體驗量表的中文版修訂.(5), 1138?1142.
Abele, A. E., & Bruckmüller, S. (2013). The big two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i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In J. Forgas & J. Laszlo (Eds.),(pp. 173?184). Psychology Press.
Abele, A. E., Hauke, N., Peters, K., Louvet, E., Szymkow, A., & Duan, Y. (2016). Facets of the fundamental content dimensions: Agency with competence and assertiveness- communion with warmth and morality., Article 1810. https://doi.org/10.3389/fpsyg. 2016.01810
Abele, A. E., & Wojciszke, B. (2014). Communal and agentic content in social cognition: A dual perspective model., 195?255. https://doi.org/10.1016/B978-0-12-800284- 1.00004-7
Azoulay, R., Wilner-Sakal, M., Tzabag, R., & Gilboa- Schechtman, E. (2022).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self-concept: The effects of interpersonal motivations and inclusionary status on spontaneous self-descriptions of communion and agency.(3), 1?9. https://doi.org/10.1177/14747049221120095
Bai, Y., Maruskin, L. A., Chen, S., Gordon, A. M., Stelar, J. E., McNeil, G. D., … Keltner, D. (2017). Awe, the diminished self, and collective engagement: Universals and cultural variations in the small self.(2), 185?209. https://doi.org/10.1037/pspa0000087
Bai, Y., Ocampo, J., Jin, G., Chen, S., Benet-Martinez, V., Monroy, M., … Keltner, D. (2021). Awe, daily stress, and elevated life satisfaction.(4), 837?860. https://doi.org/10. 1037/pspa0000267
Bakan, D. (1966).Chicago: Rand McNally.
Bonner, E. T., & Friedman, H. L. (2011). A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awe: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3), 222?235. https://doi.org/10.1080/08873267.2011. 593372
Bri?ol, P., Petty, R. E., Valle, C., Rucker, D. D., & Becerra, A. (2007). The effects of message recipients' power before and after persuasion: A self-validation analysis.(6), 1040?105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3.6.1040
Burke, E. (199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ssing, A. (2021). Wondering awe as a perceptive aspect of spirituality and its relation to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Frequency of perception and underlying triggers., Article 738770. https://doi.org/10.3389/ fpsyg.2021.738770
Cao, F., Wang, X., & Wang, Z. (2020). Effects of awe on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healthy versus unhealthy food products.(3), 264?276. https://doi.org/10.1002/cb.1815
Chaudhury, S. H., Garg, N., & Jiang, Z. X. (2022). The curious case of threat-awe: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conceptualization.(7), 1653?1669. https:// doi.org/10.1037/emo0000984
Chirico, A., & Gaggioli, A. (2019). When virtual feels real: Comparing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presence in virtu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s(3), 220?226. https://doi.org/10. 1089/cyber.2018.0393
Chirico, A., & Yaden, D. B. (2018). Awe: A self-transcendent and sometimes transformative emotion. In H. C. Lench (Ed.),(pp. 221?233).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007/978-3- 319-77619-4_11
Dai, Y. W., Jiang, T. L., & Miao, M. (2022). Uncovering the effects of awe on meaning in life.(7), 3517?3529. https://doi.org/10.1007/ s10902-022-00559-6
Danvers, A. F., O’Neil, M. J., & Shiota, M. N. (2016). The mind of the "happy warrior": Eudaimonia, awe, and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In J. Vitters? (Ed.),(pp. 323?335).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007/978-3- 319-42445-3_21
Danvers, A. F., & Shiota, M. N. (2017). Going off script: Effects of awe on memory for script-typical and -irrelevant narrative detail.(6), 938?952. https://doi.org/10.1037/emo0000277
Diehl, M., Owen, S., & Youngblade, L. (2004). Agency and communion attributes in adults' spontaneous self- representations.(1), 1?15. https://doi.org/10.1080/ 01650250344000226
Dunfield, K. A. (2014). A construct divided: Prosocial behavior as helping, sharing, and comforting subtypes., Article 5. https://doi.org/ 10.3389/fpsyg.2014.00958
Emmerich, A. I., & Rigotti, T. (2017). Reciprocal relations between work-related authenticity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work ability and depressivity: A two-wave study.Article 307. https://doi.org/10.3389/ fpsyg.2017.00307
Erickson, R. J. (1995). The importance of authenticity for self and society.(2), 121?144. https://doi.org/10.1525/si.1995.18.2.121
Fiske, A. P. (1991).New York: Free Press.
Fiske, S. T., Cuddy, A. J. C., & Glick, P. (2007).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social cognition: Warmth and competence.(2), 77?83. https://doi.org/ 10.1016/j.tics.2006.11.005
Frimer, J. A., Walker, L. J., Dunlop, W. L., Lee, B. H., & Riches, A. (2011). The integration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in moral personality: Evidence of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1), 149?163. https://doi.org/10.1037/ a0023780
Fu, Y. N., Feng, R. D., Liu, Q., He, Y. M., Turel, O., Zhang, S. Y., & He, Q. H. (2022). Aw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11), Article 6466.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9116466
Gordon, A. M., Stellar, J. E., Anderson, C. L., McNeil, G. D., Loew, D., & Keltner, D. (2017). The dark side of the sublime: Distinguishing a threat-based variant of awe.(2), 310?328. https://doi.org/10.1037/pspp0000120
Guan, F., Chen, J., Chen, O., Liu, L., & Zha, Y. (2019). Awe and prosocial tendency.(4), 1033?1041.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9-00244-7
Haidt, J. (2003). Elevation and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of morality. In C. L. Keyes & J. Haidt (Eds.),(pp. 275?289).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s://doi.org/ 10.1037/10594-012
Hogan, R. (1982). A socioanalytic theory of personality. In M. Page (Ed.),(pp. 336?355).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Jiang, L., Yin, J., Mei, D., Zhu, H., & Zhou, X. (2018). Awe weakens the desire for money., Article e4. https://doi.org/10.1017/prp. 2017.27
Jiang, T., & Sedikides, C. (2022). Awe motivates authentic-self pursuit via self-transcendence: Implications for prosociality.(3), 576?596. https://doi.org/10.1037/ pspi0000381
Jiao, L. M., & Luo, L. (2022). Dispositional awe positively predicts prosocial tendencies: The multiple mediation effects of connectedness and empathy.(24), Article 16605. https://doi.org/10.3390/ ijerph192416605
Jin, L. Y., & He, Y. Q. (2018). How the frequency and amount of corporate donations affect consumer perception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6), 1072?1088. https://doi.org/ 10.1007/s11747-018-0584-7
Jongman-Sereno, K. P., & Leary, M. R. (2019). The enigma of being yourself: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uthenticity.(1), 133?142. https://doi.org/10.1037/gpr0000157
Joye, Y., & Bolderdijk, J. (2015). An exploratory study into the effects of extraordinary nature on emotions, mood, and prosociality., Article 1577.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4.01577
Keltner, D., Gruenfeld, D. H., & Anderson, C. (2003).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2), 265?284.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10.2.265
Keltner, D., & Haidt, J. (1999). Social functions of emotions at four levels of analysis.(5), 505?521.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99379168
Keltner, D., & Haidt, J. (2003). Approaching awe, a moral,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emotion.(2), 297?314.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0302297
Koltko-Rivera, M. E. (2006). Rediscovering the later version of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Self-transcendence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unification.(4), 302?317.https://doi.org/ 10.1037/1089-2680.10.4.302
Kross, E., & Ayduk, O. (2017). Self-distancing: Theory, research, and current directions., 81?136. https://doi.org/10.1016/ bs.aesp.2016.10.002
Lenton, A. P., Bruder, M., Slabu, L., & Sedikides, C. (2013). How does “being real” feel? The experience of state authenticity.(3), 276?289.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2012.00805.x
Li, J., Dou, K., Wang, Y., & Nie, Y. (2019). Why awe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self-transcendence meaning of life.Article 1140.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9.01140
Lin, R., Hong, Y., Xiao, H., & Lian, R. (2020). Dispositional awe and prosocial tendency: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elf-transcendent meaning in life and spiritual self-transcendence.(12), Article e9665. https://doi.org/10.2224/sbp.9665
Luo, L., Zou, R., Yang, D., & Yuan, J. (2022). Awe experience triggered by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promotes prosociality through increased feeling of connectedness and empathy.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 10.1080/17439760.2022.2131607
Mansfield, E. D., & McAdams, D. P. (1996). Generativity and themes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in adult autobiography.(7), 721?731.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6227006
Martocchio, J. J. (1994). Effects of conceptions of ability on anxiety, self-efficacy, and learning in training.(6), 819?825. https://doi.org/ 10.1037/0021-9010.79.6.819
Maslow, A. H. (1962).Princeton: Van Nostrand.
Maslow, A. H. (1964).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McDougall, W. (1910).(3rd ed.). Boston: John W. Luce.
Meng, L., & Wang, X. (2022). Awe in the workplace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1), 44?53. https://doi.org/10.1002/pchj.593
Monroy, M., & Keltner, D. (2022). Awe as a pathway to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2), 309?320. https://doi.org/10.1177/ 17456916221094856
Nelson-Coffey, S. K., Ruberton, P. M., Chancellor, J., Cornick, J. E., Blascovich, J., & Lyubomirsky, S. (2019). The proximal experience of awe.(5), Article e0216780.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6780
Onu, D., Kessler, T., & Smith, J. R. (2016). Admiration: A conceptual review.(3), 218?230. https://doi.org/10.1177/1754073915610438
Oveis, C., Horberg, E. J., & Keltner, D. (2010). Compassion, pride, and social intuitions of self-other similarity.(4), 618?630. https://doi.org/10.1037/a0017628
Over, H. (2016). The origins of belonging: Social motivation in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1686), Article 20150072. https://doi.org/10.1098/rstb.2015.0072
Paulhus, D. L., & John, O. P. (1998). Egoistic and moralistic biases in self-perception: The interplay of self-deceptive styles with basic traits and motives.(6), 1025?1060. https://doi.org/10.1111/1467-6494. 00041
Perlin, J. D., & Li, L. (2020). Why does awe have prosocial effects? New perspectives on awe and the small self.(2), 291?308. https://doi.org/10.1177/1745691619886006
Piff, P. K., Dietze, P., Feinberg, M., Stancato, D. M., & Keltner, D. (2015). Awe, the small self, and prosocial behavior.(6), 883?899.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018
Prade, C., & Saroglou, V. (2016). Awe’s effects on generosity and helping.(5), 522?530. https://doi.org/10.1080/17439760.2015.1127992
Rudd, M., Vohs, K. D., & Aaker, J. (2012). Awe expands people’s perception of time, alters decision making, and enhances well-being.(10), 1130?1136.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2438731
Schindler, I., Hosoya, G., Menninghaus, W., Beermann, U., Wagner, V., Eid, M., & Scherer, K. R. (2017). Measuring aesthetic emotion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a new assessment tool.(6), Article e0178899.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78899
Schmader, T., & Sedikides, C. (2018). State authenticity as fit to environment: The implications of social identity for fit, authenticity, and self-segregation.(3), 228?259. https://doi.org/ 10.1177/1088868317734080
Sedikides, C., Lenton, A. P., Slabu, L., & Thomaes, S. (2019). Sketching the contours of state authenticity.(1), 73?88. https://doi.org/ 10.1037/gpr0000156
Seo, M. J., Yang, S. Y., & Laurent, S. M. (2022). No one is an island: Awe encourages global citizenship identification.,(3), 601?612. https://doi.org/10.1037/ emo0001160
Septianto, F., Nasution, R. A., Arnita, D., & Seo, Y. (2022). The role of threat-based awe and construal level in charitable advertising.(5), 1532?1555. https://doi.org/10.1108/EJM-06-2021- 0403
Septianto, F., Seo, Y., & Paramita, W. (2022). The role of implicit theories in motivating donations in response to threat-based awe.(1), 72?88. https://doi.org/10.1177/07439156211042281
Shiota, M. N., Keltner, D., & Mossman, A. (2007). The nature of awe: Elicitors, appraisals, and effects on self-concept.(5), 944?963.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0600923668
Stell, A. J. (2018).(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ussex.
Stellar, J. E. (2021). Awe helps us remember why it is important to forget the self.(1), 81?84. https://doi.org/ 10.1111/nyas.14577
Stellar, J. E., Gordon, A., Anderson, C. L., Piff, P. K., McNeil, G. D., & Keltner, D. (2018). Awe and humility.(2), 258?269.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109
Stellar, J. E., Gordon, A. M., Piff, P. K., Cordaro, D., Anderson, C. L., Bai, Y., … Keltner, D. (2017). Self-transcendent emotions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s: Compassion, gratitude, and awe bind us to others through prosociality.(3), 200?207. https://doi.org/10.1177/1754073916684557
Sturm, V. E., Datta, S., Roy, A. R. K., Sible, I. J., Kosik, E. L., Veziris, C. R., … Keltner, D. (2022). Big smile, small self: Awe walks promote prosocial positive emotions in older adults.(5), 1044?1058. https://doi.org/ 10.1037/emo0000876
Tomasello, M. (2016).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omasello, M. (2019).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racy, J. L., Weidman, A. C., Cheng, J. T., & Martens, J. P. (2014). Pride: The fundamental emotion of success, power, and status. In M. M. Tugade, M. N. Shiot, & L. D. Kirby (Eds.),(pp. 294?310). The Guilford Press.
Tyson, C., Hornsey, M. J., & Barlow, F. K. (2022). What does it mean to feel small?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small self.(4), 387?405. https://doi.org/ 10.1080/15298868.2021.1921018
Uchronski, M. (2008). Agency and communion in spontaneous self-descriptions: Occurrence and situational malleability.(7), 1093?1102. https://doi.org/10.1002/ejsp.563
van Cappellen, P., & Saroglou, V. (2012). Awe activates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feeling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3), 223?236. https://doi.org/10.1037/a0025986
van den Bosch, R., & Taris, T. (2018). Authenticity at work: Its relations with worker motivation and well-being., Article 21. https://doi.org/ 10.3389/fcomm.2018.00021
Waller, M., Mistry, D., Jetly, R., & Frewen, P. (2021). Meditating in virtual reality 3: 360° video of perceptual presence of instructor.(6), 1424?1437. https://doi.org/10.1007/s12671-021-01612-w
Wang, M., Qu, X., Guo, C., & Wang, J. (2022). Awe elicited by natural disasters and willingness to help people in afflicted areas: A meditational model.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07/ s12144-022-03227-3
Weber, M. (197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ger, U., & Wagemann, J. (2021). Towards a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awe and wonder: A first person phenomenological enquiry.(3), 1386?1401.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8-0057-7
Yaden, D. B., Haidt, J., Hood, R. W., Vago, D. R., & Newberg, A. B. (2017). The varieties of self-transcendent experience.(2), 143?160. https://doi.org/10.1037/gpr0000102
Yang, Y., Yang, Z., Bao, T., Liu, Y., & Passmore, H. A. (2016). Elicited awe decreases aggression., Article e11. https://doi.org/ 10.1017/prp.2016.8
Awe’s prosocial effect: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small self and the authentic self
ZHAO Yue, HU Xiaoyong, MA Jiaxin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we is an emotional response to vast stimuli that challenge the current frames of reference and require a new schema to accommodate. A large body of empirical studies have highlighted that awe engenders various forms of prosocial behavior. Regarding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implicated, the small-self hypothesis posits that the vastness of stimuli that evokes awe elicits feelings of self-smallness, which diverts the individual's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self and towards others, thus promoting prosocial behavior; the authentic-self hypothesis suggests that awe helps to facilitate a shift in the individual's attention from regular mundane concerns to a larger spiritual presence, which stimulates the individual's pursuit of his or her authentic self, thus promoting prosocial behavior. These research hypotheses can be integrated within the “Big Two” framework, which suggests that awe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through two parallel paths in the dimension of agency (authentic self) and communion (small self).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prosocial effects of awe and, on this basis, develop efficacious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prosocial behavior, such as don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psychological strategies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strategy.
awe, prosociality, small self, authentic self
B848
2022-11-26
*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22YJA190003)、重慶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項目(2021NDYB089)、2020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重點(招標)項目(SWU2009206)資助。
胡小勇, E-mail: huxiaoyong@sw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