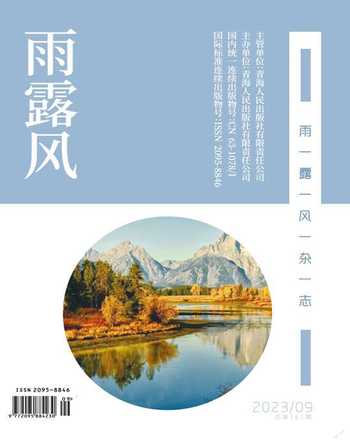勒內·基拉爾“摹仿欲望”視域下的《鹿》
薩博·瑪格達(Magda Szabó,1917—2007)是匈牙利當代文學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作為她文學生涯轉型時期推出的第二部小說,出版于1959年的《鹿》以其新銳的風格獲得一致好評,是匈牙利文學界十年“冷凍期”后“西方派”作家重返大眾視野的標志性作品。作品通過主人公艾絲特的自述,瑪格達剖析了她悲劇性的生活,讀者于其中也不難發覺“嫉妒”這一心理狀態對人物性格及情節的特殊意義,它既促成了艾絲特的成功,也是摧毀一切的導火索。匈牙利文學評論家扎裴·拉斯洛指出,“《鹿》講述了一種濃縮了的、升級了的、發展到極致了的嫉妒”。[1]5本文運用勒內·基拉爾(Rene Girard)“摹仿欲望”及其相關理論,分析薩博·瑪格達如何以嫉妒構建起《鹿》的整體世界,并最終實現對欲望的超越。
一、欲望書寫與超越欲望:《鹿》的欲望模式
《鹿》以恩契·艾絲特的自述講述了她獨特的經歷與命運。艾絲特的少女時代充滿貧窮與屈辱,她的父親是一個沒落且古板的貴族,因為家道中落,艾絲特時刻面臨著缺衣少食的困境,她母親不得不通過教授鋼琴課來補貼家用。安吉拉是她媽媽的一位鋼琴學生,她美麗善良且家境優渥,貧窮導致的自卑及強烈的自尊所磨礪出的爭強好勝,讓艾絲特對安吉拉抱有一種復雜的態度:一方面,安吉拉優渥的家境和外向的性格,使艾絲特在最初就出于本能地厭惡她;另一方面,艾絲特實則也將安吉拉視為自己的朋友,因為安吉拉不僅對她十分友善,更對她有種異常的迷戀。但是,二人的友誼最終因艾絲特的嫉妒而崩塌。小說中,安吉拉家的小鹿讓艾絲特魂牽夢縈,她計劃將小鹿偷走并放生,然而當成功帶走小鹿后,小鹿卻意外沖向鐵軌而亡。不難看出,艾絲特、安吉拉和鹿形成了一個特殊的三角結構,這一結構由艾絲特對安吉拉的嫉妒所驅動,并由她對自身的厭棄為內在動力。在勒內·基拉爾“摹仿欲望”的理論透鏡下就能明晰這三者如何相互影響,更能深入剖析艾絲特嫉妒的內涵。
首先,艾絲特對安吉拉的嫉妒源于她對安吉拉無意識的仿效。勒內·基拉爾在其理論中提出,許多情況下主體對客體強烈的追求實則只是摹仿了介體對同一客體的欲望,此處介體便成為被摹仿的“他者”,而這一非自發的、從他者那里摹仿來的欲望即“摹仿欲望”。在艾絲特、安吉拉與小鹿構成的欲望關系中,安吉拉作為欲望中介引導著艾絲特欲望的指向,而艾絲特也在不斷地摹仿安吉拉的行為和喜好:想變得更漂亮,想變得慷慨大方,甚至因為安吉拉覺得家里紫色的窗簾很漂亮,紫色也在后來成了她最喜歡的顏色等等。因此艾絲特對鹿的渴望和嫉妒,實則也是對安吉拉喜愛小鹿這一行為的摹仿,而在鹿這一虛幻的客體背后,她內心真正的欲望是成為像安吉拉那樣擁有富足悠然的生活的人。
其次,艾絲特對安吉拉的嫉妒也源自她長久以來的缺失感和匱乏感。除了物質上的匱乏,艾絲特還需要面對父母對自己的漠視。安吉拉的父母縱然貌合神離卻依然能夠時時給予安吉拉呵護和關愛,“總是有人愛撫著她,給她指出更平坦的路”。[1]11可艾絲特的境況則是“在我們家里沒有人會考慮到我的感受,誰也不會因為我而做什么或不做什么”。[1]68基拉爾認為,嫉妒不由自主地證明了嫉妒者的存在缺失和羞恥感,而在這一層面上,嫉妒他人則更意味著“對自身本質有一種不可遏制的厭惡”。[2]19對自身的厭棄和對安吉拉的摹仿暴露了她對被愛、被關懷的渴望,在這一基礎上二人與鹿之間構建起的“欲望三角”模型也得以進一步明確:作為客體的鹿,不僅是艾絲特達到“成為安吉拉”的手段,而且逐漸使其混淆了自己真實的欲望指向,這也最終導致了小鹿的死亡。
對欲望與嫉妒的書寫是瑪格達創作《鹿》的核心部分,艾絲特的“摹仿欲望”并未因為小鹿的死亡而終結,通過勒內·基拉爾“摹仿欲望”的相關理論,可以發現艾絲特經歷了嫉妒的生成、欲望變形和欲望三角崩塌并最終完成了對欲望的超越,而在復雜的時代背景影響下,她的行為實則也成為特殊年代欲望模式發展變形的例證。
二、欲望的變形與消解:《鹿》中的雙重危機
在20世紀50年代這一極為龐雜喧囂的政治語境中,薩博·瑪格達卻將小說的敘述重點置于艾絲特的心理世界與欲望模式上,塑造了一個倔強孤僻卻又惹人憐愛的女性形象。恩契·艾絲特的身上隱含著同“摹仿欲望”息息相關的雙重危機:主體危機與時代危機,這兩種危機共同寫就了艾絲特悲劇性的命運。
艾絲特的第一重危機是“摹仿欲望”造成的主體危機。一方面,長期將自身的欲望與生存價值依附于安吉拉,使艾絲特徹底失去了對自我欲望的構建能力,而只能在他者身上尋覓、借鑒自己的人生追求。即便已經成為足以名留青史的女演員,她也常發覺自身精神上的空虛,“我早上一副樣子,中午一副樣子,晚上則是另一副樣子”。[1]15在不斷摹仿他者的過程中艾絲特逐漸變成一個空心人:沒有任何原發欲望,只能在不斷地摹仿中繼續將自我掏空并以此維持自己岌岌可危的主體性,而和安吉拉的重逢不過是又一次經由介體確定自身的欲望的過程。另一方面,二人的地位的平等化進一步加劇了競爭。“平等非但不能讓最渴望平等的人得到滿足,反而只會刺激他們的欲望。”[2]150相似的地位是競爭激化的直接推手,成年后的艾絲特即使擁有了同安吉拉相似的社會地位與物質財富,也未能完成對欲望的消解反而變得更尖銳,而當曾作為欲望中介的安吉拉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生活理想之后,艾絲特同安吉拉的競爭也就落到了更為真實的客體,即安吉拉的丈夫久拉。
對他人的摹仿除了出自艾絲特自身的主體危機,也同小說的歷史背景息息相關,而她所面臨的第二重危機正是其時代危機。隨著二戰和蘇聯入侵,20世紀50年代匈牙利傳統的階級與社會秩序被戰爭沖垮,可傳統等級的崩潰非但不能消解“摹仿欲望”,反而使“大量的摹仿性競爭涌入”。[2]240這是因為在時代的劇變中,舊的規則與統一性的喪失使人人都只能經由摹仿他人獲得短暫的統一性,因此當主體危機向艾絲特發出無力繼續構建自身身份的警報時,這個充斥著“摹仿欲望”的社會便成為她重新依附于對安吉拉的摹仿的推手。
那么小鹿和久拉的死亡是否意味著《鹿》是以慘淡的前景否定了消解“摹仿欲望”的可能呢?事實上瑪格達對此并非持悲觀態度,而是在揭示欲望本質的基礎上做出了消解欲望的嘗試。
一方面,替罪羊的獻祭和犧牲是終結摹仿欲望的手段之一。除了真實出現的鹿,薩博以“鹿”為題目并將其作為小說的關鍵意象顯然還另有深意。艾絲特在回憶起自己扮演圣誕老人的經歷時,她認為“由于圣誕老人,我后來才能成為伊菲革涅亞”。[1]65在這里,伊菲革涅亞指的是古希臘神話中阿伽門農和克呂泰涅絲特拉的長女。特洛伊戰爭期間,阿伽門農為了得到神助獻祭長女,被光明女神阿爾忒彌絲用一只母鹿換下。安吉拉的小鹿和久拉代替艾絲特接受了欲望的懲罰,因此也同神話中的母鹿般具有替罪羊的意義。在“摹仿欲望”理論中,替罪羊有凈化暴力、消解欲望的意義,而這兩次獻祭也最終使艾絲特發覺自身欲望的真相,完成了對“摹仿欲望”的超越并重新開始認識自己。另一方面,回憶可以厘清欲望的根源從而擺脫欲望中介的影響。艾絲特的本體病在于她以摹仿他人而非自我的經驗來建構自我主體,在阿甘本看來,“經驗的缺失讓語言失去權威性,因為沒有人有足夠的權威來確保經驗的真實”。[3]3因此,在自述中對過往的回溯同時也是經由回憶確認自身經驗真實性的過程,這不僅重構著艾絲特的主體性,而且消解著對安吉拉和其他中介欲望的依附。
值得注意的是,“摹仿欲望”實際上也深入參與了小說形式和風格的塑形,這使《鹿》除了具有揭露“摹仿欲望”真相的意義之外,也開創了一種新的欲望書寫模式。
三、“心理現實主義”:“摹仿欲望”與《鹿》的書寫策略
作為一位“心理現實主義”小說家,一些學者將薩博·瑪格達的文學成就歸功于她完成了“在小說中再現私人歷史與國家命運”。[4]此外,也有學者認為其特殊性在于通過獨白的形式表達了對女性命運與女性成長的關懷。[5]從整體上看,《鹿》以人物的內心獨白將個體命運同國家歷史關聯起來,而這種特殊的“心理現實主義”是同匈牙利的文學傳統分不開的,匈牙利文學大師馬洛伊·山多爾就曾在創作中以多個人物的內心獨白反映人物命運在歷史中的浮沉,見證并記錄市民階層的興衰史,同時,雖然被冠之以“現實主義”,瑪格達實則并不追求全景式的歷史再現或是對歷史進行評價,她的目的在于寫出艾絲特強烈的內心情感之源以及其在不同階段的變遷。那么,“心理現實主義”對于揭示“摹仿欲望”又有何助力?
首先,“嫉妒”這一情緒對艾絲特真實欲望的掩飾,使作者必須深入人物內心來拆解其偽裝。在“摹仿欲望”的法則中“要想得到客體,非掩飾自己的欲望不可”。[6]167這種對欲望的掩飾在小說中具體表現為艾絲特的謊言,可以說,“摹仿欲望”使艾絲特在成長的過程中對他人封閉了內心,甚至逐漸失去了自我,因此唯有修復其真實的過去才可以完成對人物欲望根源的發掘。
其次,特殊的時間維也為解讀“摹仿欲望”模式的變遷提供了基礎。小說雖然打破了線性敘事,卻又同純粹的意識流手法不同,其遵循著一種內在邏輯,即過去與現在的交疊和對比。此外在兩個不同的生命階段中,安吉拉都是艾絲特“摹仿欲望”的中介,然而隨著安吉拉與艾絲特所處環境和地位的變化,艾絲特的“摹仿欲望”也隨之變形,由前述可以發現,當作為中介的安吉拉由曾經觸不可及的“外中介”向觸之可及的“內中介”轉變時,她對于艾絲特的阻礙意義也就逐漸取代了曾經的可仿效性,小說中前后躍遷的時間維便從對立中揭示了欲望模式的形式變化,且展示了其同社會環境的復雜聯系。
最后,以內心獨白來統攝小說,也拓展了心理可能性的探索和敘述空間。縱覽小說不難發現,瑪格達并不在意以心理描寫再現人物性格或是推動故事情節,而是在對艾絲特心理不間斷地展示中繪制著其嫉妒的動態圖景,這種既具有戲劇獨白性又兼具意識流小說特征的“潛對話”,使讀者也可以深入艾絲特的嫉妒之源。無獨有偶的是,作為“心理寫實主義”開創者之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樣認為現實主義的本質在于“書寫精神的可能性”[7],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犯罪和極端的精神狀態為切入點探究精神的可能性,那么在《鹿》中瑪格達則是通過嫉妒描繪深陷“摹仿欲望”的個體的墮落與救贖。與此同時,人物命運同歷史發展的關系給予了小說一種不同于宏觀敘事的私人記憶,在這個基礎上,對生活細節的刻畫則為其增添了更多真實性,瑪格達將虛構情節同真實歷史緊密相關,消解了獨白這一形式所帶來的隔閡感,使得讀者能夠真正同人物共情。
四、結語
現代社會對欲望的書寫和崇敬已經屢見不鮮,基拉爾從“摹仿”的角度,分析了自浪漫主義時期始摹仿欲望隱秘的拓張和逐漸增強的影響力。《鹿》的重要性正在于其對于“摹仿欲望”的揭示和超越。瑪格達通過描寫艾絲特同安吉拉的關系,探究了特殊歷史時期欲望模式的變換,而這也直接影響并決定了小說的技巧手法。經由內心獨白這一獨特的心理描寫方式,《鹿》成為匈牙利特殊歷史階段中欲望模式變化發展的寫照。不過薩博·瑪格達也并未放棄尋找出口的可能,并以兩次獻祭和回憶促使主人公完成最終的蛻變。
作者簡介:劉雪陽(1998—),女,長春理工大學漢語言文學方向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注釋:
〔1〕[匈牙利]薩博·瑪格達著,余澤民譯.鹿[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8.
〔2〕[法]勒內·基拉爾.浪漫的謊言與小說的真實[M].羅芃,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
〔3〕[意]吉奧喬·阿甘本.幼年與歷史:經驗的毀滅[M].尹星,譯.陳永國,校.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
〔4〕舒蓀樂.薩博·瑪格達的心理現實主義[N].文藝報,2012-12-10.
〔5〕Louise Pstermann Twardowski.Magda Szabo:Female Destinies in the turmoil of Hungarian history[J]Art,Literature,and Culture,2004.117-220.
〔6〕[法]勒內·基拉爾.莎士比亞:欲望之火[M].唐建清,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
〔7〕張磊.再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高意義的現實主義”[J].俄羅斯文藝,2022(4):8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