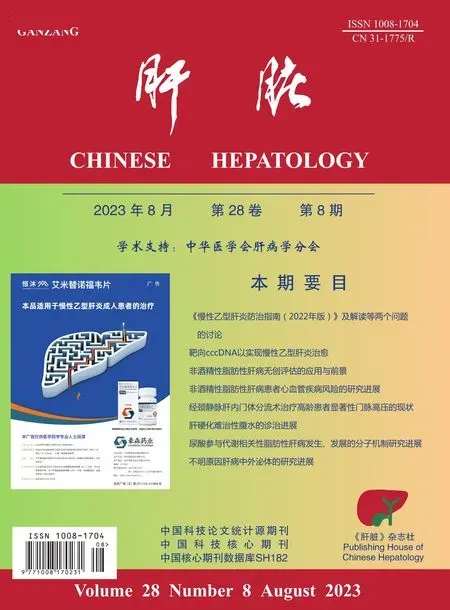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心血管疾病風險的研究進展
管炬博 范建高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現已成為全球最常見的慢性肝臟疾病,患病率高達25%~30%[1]。雖然NAFLD很常見,但肝臟并發癥的發生率相對較低,且主要發生在肝硬化患者[2],而心血管疾病(CVD)和非肝臟惡性腫瘤為無進展期肝纖維化患者的主要死因[3]。因此,對于負責NAFLD患者診療和管理的臨床醫生而言,與代謝心血管疾病相關合并癥的防治必須放在首要地位。評估NAFLD患者心血管疾病(CVD)和肝外惡性腫瘤等最常見并發癥的發病風險,是實現及時有針對性的篩查和初級預防策略的關鍵目標[4]。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CVD和NAFLD之間存在聯系,CVD是NAFLD患者最常見死亡原因的認知促進了相關防治對策的出臺[5]。心血管風險的預測是基于識別關鍵的疾病驅動因素,如糖尿病和高血壓,并根據CVD風險和治療閾值權衡是否降血脂治療。不同于其他傳統的CVD風險因素,NAFLD作為CVD風險評估的作用一直被低估。然而,在NAFLD與CVD風險的相關研究中,主要缺失的部分是專門針對NAFLD在CVD風險預測中的附加值的研究。假若CVD的預后和風險預測因NAFLD的診斷而不同,在初級保健中推動NAFLD的診斷不僅是為了肝病本身,而且有助于CVD風險預測,而治療NAFLD則更有望降低CVD風險。
一、NAFLD與CVD風險相關
NAFLD本身與肥胖、2型糖尿病(T2DM)、血脂紊亂等心血管危險因素密切相關。來自美國第三次全國健康和營養調查(NHANES III)的7 761例參與者的數據顯示,NAFLD患者比沒有NAFLD的群體CVD發病風險高出近25%[6]。另外,最近的流行病學研究表明,與無NAFLD患者相比,NAFLD患者致死性和非致死性CVD事件發生率均顯著增高。
肝纖維化作為慢性肝病進展的重要預測因素,對NAFLD患者的預后和CVD風險評估都有重要影響。一項使用8 511例醫務人員健康數據的隊列報道顯示,在調整社會人口統計學變量、歐洲冠狀動脈風險評估(SCORE)評分、他汀或阿司匹林的使用等因素后,合并進展期肝纖維化(FIB-4指數≥2.67)的NAFLD患者CVD事件發生風險高于無進展期肝纖維化者[7]。事實上,NAFLD患者肝纖維化的進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長期暴露于常見代謝心血管危險因素(如T2DM、肥胖、高血壓)的后果。代謝心血管風險因素與全身胰島素抵抗、系統性炎癥和氧化應激的增加密切相關,這些因素可加劇肝細胞損傷并導致庫普弗細胞和肝星狀細胞活化,從而導致脂肪性肝炎和肝纖維化的發生。然而,在CVD的風險評估中,肝纖維化的作用常被低估。CVD的風險評估應考慮納入FIB-4等廣泛使用的非侵入性肝纖維化生物標志物。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肝臟脂肪變性也與CVD風險增加有關。例如,一項對來自美國3 756例接受冠狀動脈計算機斷層造影的患者進行的嵌套隊列研究發現,無論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風險評分、嚴重的冠狀動脈狹窄和代謝綜合征的特征如何,超聲檢查診斷的肝脂肪變性與主要CVD事件的發生風險有著更高的相關性[8]。
二、NAFLD對CVD風險的預測作用
鑒于NAFLD的發生和發展特別是肝纖維化與CVD風險密切相關,NAFLD與CVD風險之間的聯系一直是近10年的研究熱點。證實NAFLD和CVD發病之間的關聯將是對該領域的重要貢獻。許多研究在探討NAFLD是否可能是CVD風險預測中有意義的附加因素。根據描述NAFLD與CVD之間獨立關聯的研究、薈萃分析的結果顯示,NAFLD與CVD風險之間存在相關性[4, 6-8]。與之相矛盾的是這些文獻未能確定此類關聯[9]。在單變量分析中,相關研究證實了肝臟脂肪含量與CVD發病率之間的關系[10]。然而,這些關系在使用包含所有傳統心血管疾病風險因素以及通過CT測量肝臟脂肪含量等基線數據或時間相關模型的多變量分析中,并未得到進一步證實[10]。為此,至今尚無足夠證據表明NAFLD患者CVD風險高于其他代謝心血管危險因素。
有系統綜述和薈萃分析描述了500多萬患有和不患有NAFLD群體CVD的發生率和死亡率[11]。 僅考慮對傳統心血管危險因素進行完全校正的研究,NAFLD與CVD發生率和心血管相關死亡率之間仍存在獨立聯系。但不可避免的是,這些研究并未考慮所有危險因素[10, 11]。例如,已知腰圍與CVD和NAFLD有關聯,但多數研究并未測量腰圍。混雜因素對NAFLD增加CVD風險的評估仍是有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現有的流行病學方法(例如E值)能估計未測量的混雜因素影響力,這些混雜因素若存在,將否定所觀察到的研究結果[12]。以NAFLD和非致命CVD事件之間的關聯(HR值為1.31)為例[11],E值是1.95。提示如果NAFLD與非致命性CVD事件的HR高達1.95,則未測量的混雜因素可以解釋所觀察到的關聯。為了進一步判斷這一發現的相關性,可以使用偏倚因素法來比較已知的混雜因素[4]。在這個案例中,可以使用T2DM,因為這與NAFLD(校正體質指數后HR=2)和CVD發生率(HR=1.5)有關。從現有的大型研究中整理數據,偏倚因子為1.4,這比整合的薈萃分析中觀察到的NAFLD與非致命性CVD事件之間的關聯更大[4]。總之,剩余的未測量的混雜因素仍然可能影響現有研究所描述的NAFLD與CVD風險之間研究結果。
然而,只有當NAFLD的診斷能有意義地增加CVD風險預測,或針對NAFLD的治療方法在CVD的初級預防中起作用時,這種臨床相關性才會具有實質價值。最重要的是,雖然納入腰圍和腰臀比等內臟型肥胖指標的大樣本研究確實發現兩者之間的相關性,但NAFLD并不能提高CVD風險預測的準確性[13]。綜合NAFLD與CVD事件關聯的薈萃分析結果、持續存在的未測量的混雜因素以及相關研究[10],NAFLD似乎不太可能成為CVD風險計算中的重要預測因素。雖然NAFLD的診斷會促使臨床醫生對患者進行CVD風險評估,但這些患者最終仍以與無NAFLD患者相同的方式進行管理[4]。然而,NAFLD對這些結果的影響并非無效。基于人群的研究顯示,NAFLD的存在會使T2DM和高血壓病等合并癥風險增加2倍以上[14]。而這些代謝相關合并癥是CVD風險增加的獨立危險因素,為此NAFLD的診斷和治療對CVD的預防仍然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對NAFLD死亡率估計的研究顯示,在NAFLD各種結局的時間-事件分析中,代謝合并癥的后續發展應被視為時間相關共變量,否則將與NAFLD本身的影響混為一談[10]。
三、NAFLD患者的管理和治療有助于降低CVD風險
治療NAFLD患者肝病的目的通常是預防肝纖維化進展和降低肝硬化和肝細胞癌的發生風險。即使是在那些有進展期肝纖維化和代償期肝硬化的NAFLD患者中,最常發生并最終導致死亡的原因仍然是全身代謝功能障礙的并發癥[4]。這對肝病專科醫生、藥物開發人員以及監管機構和投資方提出了挑戰。從目前NASH藥物開發的方向來看,治療相關代謝障礙的有利影響可能不僅僅是在肝臟,甚至惠及全身。作為管理NAFLD患者的肝病科醫生,更應該靶向超重/肥胖、糖尿病、高血壓、血脂紊亂等心血管風險因素,將對這些危險因素有潛在益處的行為干預、藥物干預等措施納入到綜合性治療方案中。生活方式干預在CVD的一級和二級預防以及NAFLD的防治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15]。例如,運動可以通過調控胰島素通路,發揮除了減輕體質量之外的降低CVD發生率以及減輕肝臟脂肪變性程度的作用。同樣,一定程度的減輕體質量可以改善肝臟組織學、全身胰島素抵抗和系統性低度炎癥[5]。
索瑪魯肽在T2DM、肥胖癥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藥物研發中的平行發展可能是其全身額外治療益處的最好例證。索瑪魯肽降低T2DM患者的CVD風險現已得到證明[16]。其對肥胖患者的益處目前正在進行試驗。考慮到先前NASH 3期臨床試驗中肝臟臨床事件的發生率較低,在目前進行的3期試驗中索瑪魯肽可能會治療和預防比肝臟事件更多的CVD事件。雖然這是試驗中的一個次要終點,但無論其對肝病的影響如何,這對NASH患者至關重要[4]。然而,現在沒有研究表明胰高血糖素樣肽-1(GLP-1)受體激動劑可以治療NASH及其相關纖維化[5]。因此,GLP-1受體激動劑對NAFLD患者的肝臟組織學獲益仍需進一步研究證實[17]。
四、總結與應對策略
綜上,NAFLD與CVD是全球普遍流行的公共衛生挑戰。肝脂肪變性可能不是CVD事件的獨立預測因素,但卻是導致T2DM、高血壓、血脂紊亂從而引起NAFLD患者CVD風險增加的條件。當前研究重點需要從描述性流行病學研究轉移到與患者直接相關的臨床研究上,包括NAFLD的診斷如何影響CVD風險預測以及兼顧防治CVD的NAFLD治療策略的最佳實施辦法。我國是全球NAFLD和CVD流行的高發地區,NAFLD患者的CVD負擔沉重。對NAFLD患者根據肝臟損傷纖維化和動脈硬化性CVD風險進行分層分級的多學科團隊參與的規范化管理是預防NAFLD患者發生CVD、肝硬化和肝癌,以及降低患者全因死亡率、CVD相關死亡率和肝病相關死亡率的重要措施[18]。動員基層醫生、全科醫生、臨床營養師、運動康復師、體質量管理師、心血管醫師參與到以肝臟專科醫生和代謝內分泌科醫生為首的脂肪肝防治工作中,關注脂肪肝患者的體質量和腰圍,系統篩查和監測代謝綜合征,及時通過飲食調整、運動、行為修正以及藥物干預等方式,可望降低我國NAFLD及其相關CVD發病和進展風險,從而改善患者生活質量并延長壽命。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