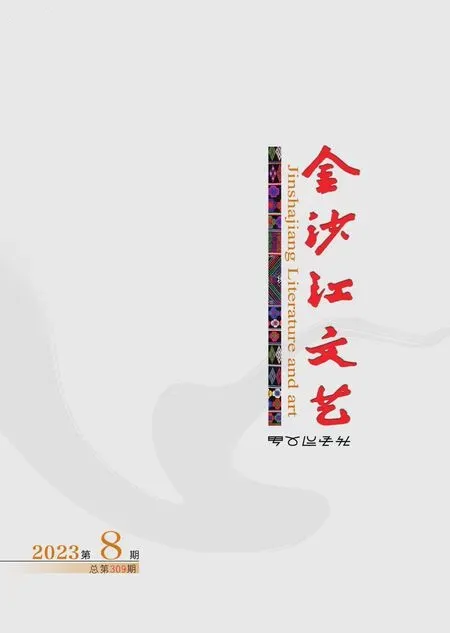艾蕪與楚雄
◎ 普顯宏 (彝族)
艾蕪是云南人民的老朋友,艾蕪愛云南,云南愛艾蕪;艾蕪既是四川人民的驕傲,也是我們云南人民的驕傲。我參加成都艾蕪研究學會三年多來,梳理出了兩篇艾蕪第二次南行的長文和繪制了一張艾蕪南行的路線圖,知道艾蕪三次南行的詳情經過,更加懂得中國文壇上不朽的艾蕪精神。
艾蕪一生三次南行,第一次是1925年,從成都流浪到滇西德宏,后來又漂泊到緬甸、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地,歷時7年,有小說集 《南行記》問世。第二次南行是在1961年9月,也就是在第一次 “南行”后的34年,同行的有老作家沙丁、劉真、林斤瀾等,歷時6個月,出版了 《南行記續篇》。第三次南行是在1981年2月下旬,在第二次南行20年后,77歲高齡的艾蕪應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邀請。這一次與他同行的有老作家高纓、馮永祺等人,又寫了 《南行記新篇》。
艾蕪第一次南行時徒步經過了楚雄州的祿豐、楚雄、鎮南三縣;第二次南行時艾蕪因患肺結核不能顛簸來回都是坐飛機,從昆明直飛滇西保山,從地理上沒有經過我們楚雄州。第三次南行艾蕪從昆明坐汽車沿320國道途經祿豐縣在楚雄住宿、講課、開座談會,到牟定縣鳳屯公社秧田沖生產隊訪問。從滇西返回時在南華縣吃飯,住宿于楚雄。
艾蕪第一次南行時沒有寫日記,第二次南行留下了部分日記,第三次南行有完整的日記。我從出版的19卷《艾蕪全集》中查找,得到艾蕪第一次南行時與楚雄州有關的三個細節。
在艾蕪散文集 《漂泊雜記》(1935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出版)中,有一篇紀實散文——《舍資一夜》,千余字。寫1927年仲春,艾蕪從昆明流浪到祿豐一平浪舍資驛時,天黑找住宿無著,在點著松明火的街道小酒館喝酒時遇到一彝族中年男子 (其實是個酒罐)。男子夸下海口 “包住”,艾蕪因此還幫男子付了酒錢。結果深夜男子領艾蕪回家住宿時,因酒醉連連敲錯門,自然鬧出了些笑話。最后待男子找到了自己的家時,敲門后老婆也是嫌棄他酗酒臭罵一頓后自然也沒有給他開門,結果艾蕪和喝醉酒的祿豐彝族男子,就只好無奈在屋檐下睡了一夜。
也是在艾蕪散文集 《漂泊雜記》中,艾蕪寫了一個唱著鎮南州 (今南華縣)歌謠的中年男人,這篇 《走夷方》的紀實散文,最初發表于1934年1月16日上海 《申報》 “自由談”欄目上。文章開頭作家這樣寫道:
“男走夷方,女則居孀;生還發疫,死棄道旁。聽著暫時聚會的旅伴,拖起漫長的聲音,在唱鎮南州人唱的歌謠時,輕煙也似的憂郁,便悄悄地繞在我的心上了。跟著他拐下山坡的那一陣,簡直是缺乏了走路人應有的力氣。”
艾蕪在滇緬邊境八慕遇到 “走夷方”的鎮南州人的時候,年僅23歲,帶著好奇心和這個年齡特有的叛逆性格,與鎮南人有過一段精彩的對白。
我的旅伴 (一個中年人)說,在清明以前直至去年的九月,這個期間,這里是不缺少晴天的,每天都是好太陽,雨嘛,一滴也瞧不見。現在呢,可就倒霉了,每天總得淋幾場雨的。這里的雨,不像漢人地方的雨哪,又毒又可怕 (很容易生病)的。還有那瘴氣呵,瘴氣!菩薩保佑!
他說到這里,他的周身像突遭襲擊一般,簡直戰栗起來。隨即好意地責備我,說是年輕人怎不在臘月間出來,現在來送死么?
我一面聽著他的話,一面真見了路上的傣族婦女,多是眉清目秀的,而且有的農家姑娘,竟比漢族女子反要美麗些。便說道,這里的人,不是活得很好么?
這是夷人呀!他大聲地駁斥我,隨即舉出許多漢人在這里中了瘴毒的可怕情形來。我無話可說了,只有用一句話來抵他,即是說,那么,你現在又來夷方做什么呢?
“天哪,這是為了要吃飯,為了要養家哪。”他愁苦地呻吟著。
我因要在言語上戰勝他,就微笑地答道: “我不是也同你一樣的嗎?”
其實,那時我沒有家,也不只是為了一己的生活,多半的原因,是由于討厭現實的環境,才像吉卜賽人似的,到處漂泊去。然而,為了要看看新奇的景物,便來到這么令人喪氣的地方,自然心里也不免有些憂郁了。
“那么,你也做我一樣的生意嗎?”他閃著狡猾的眼睛。
“什么?你做什么生意?”我倒問起他來。
“呃呃?”他不答復了,只是哼著他的鎮南州人的歌謠。
后來走到八募原野,經緬甸的便衣巡警搜查時,才曉得他,我的老好的旅伴,是私販鴉片煙的。倘如早知道,我便要裝成他那么一副老成的面容,學他責備我一樣,來貢獻我的忠告的。但他卻由那一次,連同禁物帶到牢中去了,以后一直沒有見過面。
讀著 《走夷方》,我讀出了鎮南人民在舊社會的心酸和苦難;也讀出了鎮南人淳樸誠實、吃苦耐勞的性格。
據艾蕪第三次南行去牟定訪問彝族村寨路過呂合鎮時的日記 (1981年2月18日)記載:1927年春天,艾蕪流浪到此時曾在呂合街上住過一夜。當時正遇到街上有一家人的女兒結婚辦喜事,艾蕪懷著好奇的心情參加了這場鄉村婚禮,他送給新娘的禮物是一支圓珠筆。我衛校畢業后曾在呂合煤礦職工醫院工作28年,經常去趕呂合街,對呂合街的情況非常熟悉。艾蕪送新娘圓珠筆,當時應該是非常時尚,算得上是高科技產品。
艾蕪第三次南行,于1981年2月17日與高纓、馮永祺同車抵達楚雄,住楚雄州招待所。艾蕪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到街上走走。1927年春天曾在此住過一夜,今天已大變了。楚雄現有人口二百五十萬,出蠶絲、絲綢緞,出烤煙、香煙,還出鹽。”
2月18日一早,艾蕪一行到牟定縣鳳屯公社秧田沖生產隊,即現在的鳳屯鎮颯馬場村委會秧田沖彝族村寨訪問,彝族是艾蕪第三次南行中計劃采訪的五個少數民族之一,但最后沒有寫出文學作品。這個秧田沖彝村就靠公路邊上,是我當年回牟定老家時的必經之路。前不久我向在牟定鳳屯鎮工作的文友李登科打探過,艾蕪30多年前訪問過的彝村秧田沖,至今仍保留著許多彝族古老民風遺跡。
艾蕪第三次南行在楚雄文壇上算得上是大事件,18日下午,楚雄州文聯組織城區文藝工作者聆聽艾蕪和高纓的文學創作講座。我專門到楚雄州圖書館文獻資料室查找過,艾蕪和高纓的這次講課,經整理后發表在1981年的第2期 《金沙江文藝》上,艾蕪的約一萬八千多字,高纓的一萬多字,題目可能是編者加的,艾蕪的是《我是怎樣走上文學的道路的》,高纓的是 《從艾蕪同志的講話所想到的》,題目的左下方分別印有艾蕪和高纓講課時的照片,但當時的照片印刷質量不好,紙質粗糙,不甚清晰。
18日晚上,據艾蕪日記載,州長(應該是我的老鄉、已故老州長普聯和)和副州長來訪,又召開座談會。艾蕪第三次南行有個特點:自稱 “威風八面,心情愉悅。”
艾蕪第三次南行從滇西返回時,于3月30日一早從大理出發,來到南華縣吃午飯。但無從考證在沙橋吃還是在縣城吃。按當時習慣,從大理出發到昆明的班車,到南華沙橋剛好是中午12點前后,那時的司機都習慣在沙橋停車吃飯,從昆明到大理的班車也是如此。加之沙橋有享譽滇西的美食 “沙橋三絕”:臭豆腐、酸菜魚、千張肉,號稱小香港。晚上艾蕪住楚雄,于3月31日返回到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