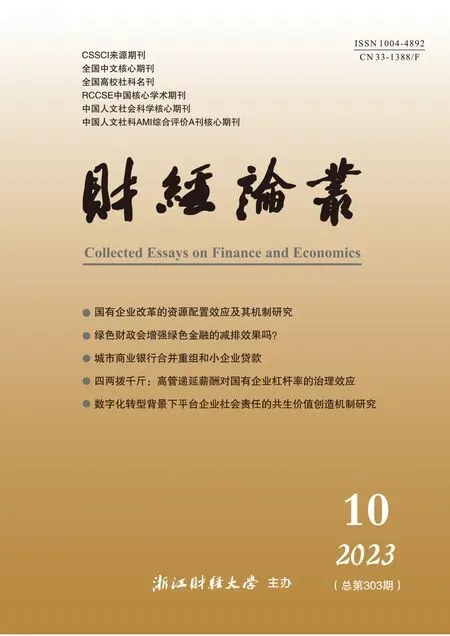四兩撥千斤:高管遞延薪酬對國有企業杠桿率的治理效應
張興亮
(南京審計大學會計學院,江蘇 南京 211815)
一、引 言
為了控制杠桿率高企的問題,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去杠桿”政策。去杠桿政策實施后,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逐步企穩,并在2017年有所回落[1],高杠桿企業的杠桿率有所降低[2]。但也不排除一些企業為了滿足監管機構對杠桿率的相關要求進行杠桿操縱的可能性[3]。特別是國有企業,在去杠桿政策壓力下,出現了隱藏債務的現象[2]。這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說明,一刀切的去杠桿政策會產生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一刀切的去杠桿政策可能對經濟有所“誤傷”。但高杠桿企業、“僵尸”企業等仍需去杠桿,因此,如何設計精準機制讓必須降杠桿的企業主動降杠桿還需要進一步探索。
近年來一些研究發現,高管遞延薪酬(1)Jensen和 Meckling(1976)[26]提出“內部債務”(Inside Debt)的概念,其中包括遞延薪酬(Deferred Compensation)和養老金計劃(Benefit Pensions)。由于中國企業沒有普遍執行養老金激勵[12][13],因此,既有中文文獻中所指的內部債權[13]、內部債務[15]或延付薪酬[12][14]均是指遞延薪酬。能使高管更謹慎地經營企業[4],采取更加保守的財務政策[5][6],企業的財務杠桿更低[7][8]。既有研究還探討了高管遞延薪酬對債務期限結構[9]、可轉換債券[10]、內部資本市場的效率[11]的影響。可以說,高管遞延薪酬是影響企業杠桿率或債務的一個重要因素。但目前國內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銀行高管遞延薪酬制度的效果或影響[12][13][14][15][16],對于非金融企業高管遞延薪酬制度現狀如何,以及有何治理作用,一直鮮有研究。事實上,我國部分非金融國有企業一直存在對高管部分薪酬進行遞延支付的做法。早在2003年,《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國資委令第2號)規定,對于中央企業負責人,“績效年薪的60%在年度考核結束后當期兌現,其余40%根據任期考核結果等因素延期到連任或離任的下一年兌現”。此后,國資委令第17號、22號、30號、33號、40號逐步對第2號令進行了修訂,但央企負責人部分績效年薪延期支付的規定一直被保留下來。除了中央企業之外,部分地方國有企業也設有高管遞延薪酬制度。那么,這種在部分非金融國有企業中應用的高管遞延薪酬制度能否對杠桿率形成治理效應?本文針對這一問題開展研究。
本文認為,高管遞延薪酬使高管與債權人的利益捆綁在一起,是一種高管的自我約束機制,高管為了確保獲得遞延薪酬,會采取更加保守的財務政策,主動承擔既有債務的應有義務,從而能有效抑制因預算軟約束和所有制紅利導致的國有企業杠桿率高企問題。以中國A股國有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本文發現,高管遞延薪酬能顯著降低國有企業杠桿率,有直接治理效應。進一步的機制檢驗表明,高管遞延薪酬通過降低國有企業借新還舊、過度負債從而降低杠桿率,從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比較視角、抑制高風險投資視角的檢驗也驗證了其中的影響機制。本文最后的進一步分析表明,與去杠桿前或未采用高管遞延薪酬制度的國有企業相比,去杠桿后那些采用高管遞延薪酬制度的國有企業的杠桿率顯著更低,這說明高管遞延薪酬制度能與去杠桿政策協同,對國有企業杠桿率產生了協同治理效應。
本文可能的主要貢獻在于:首先,本文提供了高管遞延薪酬有“四兩撥千斤”治理效果的支持證據,這對現有經濟背景下如何設計國有企業杠桿率的精準治理機制有一定啟示意義,有助于減少“一刀切”政策所引發的杠桿率操縱以及對經濟“誤傷”所導致的高昂制度性交易成本。其次,既有關于非金融國有企業杠桿率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業外部治理機制,如減稅降費[17]、利率市場化[18][19]、金融科技[20][21]、控制政府財政赤字與財政支出[22]、理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關系[23]等,本文從企業內部治理視角探討國有企業杠桿率的治理問題,是對既有從企業外部治理視角文獻的重要補充。最后,目前國內關于高管遞延薪酬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行業,本文針對非金融國有企業高管遞延薪酬的研究也是對既有針對金融業高管遞延薪酬研究的有效補充。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眾所周知,國有企業一直是中國經濟的主要組織形式,其不僅承擔著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提高利潤等經濟目標,也承擔著兜底就業、提供公共產品和實現國家戰略任務等非經濟目標。這些政策性的非經濟目標給國有企業帶來了比較大的政策性負擔,這是導致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的根源[24]。預算軟約束具體表現為,政府通常對國有企業提供更多的財政補貼、稅收優惠,以及支持銀行等金融機構向國有企業貸款,同時,國有企業因承擔非經濟目標、出現政策性虧損而經常向政府要資源、要政策,還可能將經營性虧損上報為政策性虧損,以獲得政府的支持。就政府支持銀行向國有企業貸款而言,國有企業通常比民營企業以更低的成本獲得更多、更長期限的借款,還可能出現持續虧損的國有企業能從銀行持續獲得貸款的現象,導致僵尸貸款和僵尸企業層出不窮。可以說,預算軟約束是導致國有企業杠桿率高企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國有企業由于其國有身份,有政府背書,且一般規模比較大,有更多的抵押物,處于國家支持或重點發展的行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更愿意向國有企業貸款,這種所有制紅利也是國有企業杠桿率高企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除了預算約束、所有制紅利等制度原因之外,國有企業杠桿率高企還可能歸因于企業內部治理機制出了問題。根據自由現金流假說,負債會減少可由企業高管自主支配的自由現金流,從而能夠抑制高管的自利行為[25],如此,則擁有剩余控制權的企業高管會盡量減少負債融資。但國有企業的杠桿率表現卻與自由現金流假說相反,其原因在于負債并不能對國有企業高管形成很強的約束,沒有對高管的行為產生治理效應。負債對國有企業高管沒能形成強有力的約束可以說是預算軟約束在國有企業內的具體表現。換言之,國有企業之所以預算軟約束,根本原因在于國有企業高管沒有承擔起負債帶來的約束責任。如果能讓國有企業高管承擔起負債的相應責任,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則變為預算硬約束,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則會迎刃而解。具體可采用兩種機制讓國有企業高管承擔起負債的相應責任。一是硬性約束機制,即通過設計相關政策,規定國有企業高管在債務融資、債務履約、違約后果等方面應承擔的義務和責任;二是高管自我約束機制,即將國有企業高管的個人利益與債權人的利益協調一致,讓國有企業高管不愿意過度負債,更愿意積極主動履行已有的債務合約。就以上兩種機制的實施成本而言,硬性約束機制可能會導致國有企業高管的規避行為,如盈余管理、杠桿率操縱等,會產生較高的實施成本;而高管的自我約束機制能讓高管積極主動承擔由債務引起的責任和義務,實施成本較低。
事實上,Jensen和Meckling(1976)[26]就曾提出讓高管以一個與公司資本結構相同的比率持有公司的債務和股權,以降低債務和股權代理成本。高管持有的公司債務通常有養老金和遞延薪酬,Jensen和Meckling(1976)[26]稱其為內部債務(Inside Debt),相當于一種高管的自我約束機制,能激勵高管與外部債權人的利益一致,減少外部債務的代理成本。遺憾的是,在Jensen和Meckling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內部債務并沒能引起學者們的關注,但事實上其在公司治理實踐中一直被應用[4]。內部債務能使高管采取更穩健的財務政策,使企業的杠桿率更低[8]。在中國,部分國有企業一直存在對高管部分薪酬進行遞延支付的做法,一些地方國有企業也有類似將高管部分薪酬遞延支付的制度。
本文認為,國有企業高管的遞延薪酬制度能成為高管的自我約束機制,能對因預算軟約束、所有制紅利而導致的國有企業杠桿率高企問題產生治理作用。原因在于,實施高管遞延薪酬制度是將高管的部分薪酬延期到以后期間再支付,高管能否在到期時順利拿到薪酬取決于企業的經營狀況。對于國有企業而言,高管能否獲得遞延薪酬,不僅取決于國有企業在高管遞延薪酬到期時的業績,還包括國有企業當時是否穩定,有沒有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鑒于此,依據管理層防御理論,有遞延薪酬的國有企業高管,為了能夠獲得到期的薪酬,會有很強的防御動機,他們會采取有利于自己能夠獲得到期遞延薪酬的防御行為,即不愿過多負債以便國有企業能夠到期償還遞延薪酬這種“內部債務”。而且,高管遞延薪酬實質上是把高管的利益與債權人的利益捆綁在一起[27],能夠使高管主動承擔起企業債務所帶來的義務和責任,以避免企業無法償還到期債務這種不利因素限制其獲得到期的遞延薪酬,從而能夠最終化解國有企業因預算軟約束而導致的杠桿率高企問題。概言之,國有企業高管遞延薪酬會硬化國有企業預算約束,最終降低國有企業杠桿率。對于所有制紅利,國有企業高管遞延薪酬制度也能抑制因所有制紅利給國有企業帶來更多的債務問題。因為高管能否獲得遞延薪酬與其任期內的經營業績掛鉤,經營業績指標包括凈利潤和經濟增值加等,如果國有企業負債過多,則會導致利息費用過高,從而導致凈利潤降低。更重要的是,對國有企業高管的經濟增加值考核會考慮債務資金成本,負債越高、債務資金成本越大,企業的經濟增加值越小,有強烈防御動機的高管會在負債帶來的收益與成本之間進行權衡,遞延薪酬越多的高管越不會過度負債融資。同時,負債經營會使企業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在有遞延薪酬制度的國有企業中,防御的高管為了確保能夠獲得遞延薪酬,會減少債務融資。
綜上,遞延薪酬能夠引起國有企業高管強烈的防御動機,產生不愿意過多負債以及更愿意履行既有債務的義務以確保獲得遞延薪酬的防御行為,并且高管遞延薪酬的比重越多,高管去杠桿就越積極,因而能對因預算軟約束、所有制紅利導致的國有企業杠桿率高企問題產生治理作用。根據以上分析,提出本文具體研究假設:
H1:與未采用高管遞延薪酬制度的國有企業相比,采用高管遞延薪酬制度的國有企業杠桿率更低,且高管遞延薪酬越多,國有企業杠桿率越低。
三、實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滬、深股市A股國有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由于在研究中需要使用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而中國上市公司自2007年采用新企業會計準則,為了避免企業會計準則變更而導致的財務數據不可比,本文使用2007—2020年數據為研究樣本。同時,在研究中剔除了金融業上市公司,同時剔除被ST、*ST或PT的上市公司,也剔除了所有者權益為負的國有上市公司。研究中所使用的上市公司高管遞延薪酬數據來自于萬德數據庫(Wind),企業產權性質數據來自于色諾芬數據庫(CCERDATA),其他財務數據均來自于國泰安數據庫(CSMAR)。研究中使用的數據處理和計量分析軟件為Stata16.1。
(二)變量定義及衡量
1.企業杠桿率的衡量。既有文獻比較常用的做法是以“資產負債率”衡量企業杠桿率。本文認為,直接采用資產負債率衡量企業杠桿率有很大“噪音”。因為企業總負債中既包括金融性負債也包括經營性負債,其中金融性負債是指短期借款、長期借款、應付債券、分期付款業務產生的長期應付款、以及上述將在一年內到期的負債等有息負債,其典型特征是使用這些負債是有成本的。而經營性負債是指應付賬款、應付票據、預收賬款、其他應付款等經營過程中產生的、一般情況下無利息的負債。雖然企業在會計處理上把經營性負債作為負債進行處理,但經營性負債與金融性負債有本質區別。一個經營性負債占比較大的企業,恰恰說明這個企業有競爭力,其在行業中或供應鏈中處于強勢地位。因此,將經營性負債作為企業杠桿的組成部分顯然不合適,或者說資產負債率并不能反映出企業真實的杠桿水平。所以,去杠桿主要是指降低金融性負債的比重。鑒于此,本文以金融性負債衡量企業杠桿,以“金融性負債÷總資產”衡量企業杠桿率,具體地,根據金融性負債包括的不同內容,本文設計了兩個衡量杠桿率的指標:
Flev1=(短期借款+長期借款)÷總資產,該變量衡量的是因銀行借款等間接融資方式形成的企業杠桿率。
Flev2=(短期借款+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長期借款+應付債券+長期應付款)÷總資產,該變量衡量的是由全部金融性負債形成的企業杠桿率。
2.高管遞延薪酬的衡量。國內關于高管遞延薪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金融業上市公司,而非金融業上市公司對高管遞延薪酬相關信息披露較少,但事實上的確有企業實施了高管遞延薪酬制度。萬德(Wind)數據庫提供的上市公司資產負債表數據中有“長期應付職工薪酬”項目(不包括股票期權等股權激勵),該項目主要反映不是由當期發放的,而是應于以后期間發放的薪酬,包括工資、福利費等,這比較符合遞延薪酬的定義。基于此,本文將“長期應付職工薪酬×(董監高年薪總額÷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的計算結果作為高管遞延薪酬,以此為基礎設計了兩個變量:一是連續變量ConDefer,用“高管遞延薪酬+1”的自然對數衡量;二是啞變量DumDefer,當國有企業存在高管遞延薪酬制度時取值為1,否則為0。
3.控制變量的選擇及衡量。參考陸正飛等(2015)[28]、鐘寧樺等(2016)[29]對企業債務研究,本文選擇企業規模(Size)、可抵押資產(Colla)、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CF)、資產凈利率(ROA)、總資產增長率(Growth)、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FShare)、賬面市值比(MB)、管理費用率(Expense)、非債務稅盾(NDts)、所得稅率(ITR)、高管持股比例(MShare)作為控制變量。所有變量的定義及衡量方法見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及衡量方法
(三)實證研究模型
為了檢驗假設1,本文設計了回歸模型(1):
Flev=α0+α1Defer+α2Size+α3Colla+α4CF+α5ROA+α6Growth+α7FShare+α8MB
+α9Expense+α10NDts+α11ITR+α12MShare+∑Industry+∑Year+ε
(1)
在模型(1)中,Flev為杠桿率,共有兩種衡量方法,分別為Flev1、Flev2;Defer為高管遞延薪酬,共有兩種衡量方法,分別為ConDefer和DumDefer;Industry和Year分別表示行業和年度啞變量。若假設1成立,則模型(1)中Defer的回歸系數α1應當顯著小于0。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本文刪除變量Flev2之外各變量的缺失值,共得到10497個觀測值。由于衡量變量Flev2需要用到應付債券、長期應付款等數據,而這些數據缺失較多,為了防止觀測值太少,因此,本文并沒有基于變量Flev2刪除缺失值。為了消除變量異常值的影響,本文在1%和99%分位數上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了Winsorize處理。從Flev1、Flev2樣本量的比較來看,國有企業采用發行債券或分期付款等方式比較少或缺失值較多。ConDefer的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19.454,說明樣本中企業之間高管遞延薪酬數額差異較大。DumDefer的均值為0.138,說明樣本中大約有13.8%的國有企業采用了高管遞延薪酬制度。
(二)多元回歸結果
表3報告了模型(1)的OLS估計結果。當因變量為Flev1時,無論是連續變量ConDefer還是啞變量DumDefer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高管遞延薪酬顯著降低了國有企業由銀行借款構成的間接融資杠桿率。當因變量為Flev2時,連續變量ConDefer和啞變量DumDefer的回歸系數也顯著為負,說明考慮國有企業所有金融性負債后,高管遞延薪酬能夠顯著降低國有企業杠桿率。以上結果表明,高管遞延薪酬制度的確能對國有企業杠桿率高企問題產生直接治理效應,假設1得到驗證。

表3 高管遞延薪酬與國有企業杠桿率
(三)穩健性檢驗(2) 限于篇幅,穩健性檢驗結果略,作者備索。
1.內生性問題。模型(1)中的考察變量ConDefer或DumDefer與因變量可能相互影響,即可能是杠桿率較低的國有企業才選擇高管遞延薪酬制度。當內生變量是ConDefer時,本文采用兩階段估計方法(2SLS)進行重新估計,以解決上述內生性問題。參考黃秀路和葛鵬飛(2018)[13]的研究,選擇同行業高管遞延薪酬的均值作為ConDefer的工具變量,然后采用2SLS估計方法,結果顯示,無論因變量是Flev1還是Flev2,ConDefer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考慮內生性后,假設1依然得到驗證。當內生變量是啞變量DumDefer時,若是杠桿率較低的國有企業才選擇高管遞延薪酬制度,這屬于典型的樣本自選擇問題,本文采用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進行穩健性檢驗。具體地,按照最近鄰匹配的方法在對照組(未采用高管遞延薪酬制度的國有企業)中獲得與實驗組(采用高管遞延薪酬制度的國有企業)傾向值得分匹配的樣本,然后將這些樣本與采用高管遞延薪酬制度的國有企業樣本形成PSM樣本,并將模型(1)在該PSM樣本中進行OLS估計。結果顯示,考察變量DumDefer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假設1再次得到驗證。
2.重新衡量杠桿率。王竹泉等(2019)[30]認為,準確的資本杠桿是指以自有資本撬動總資金的倍數,如果以資產負債率衡量杠桿率,應當稱為資本結構杠桿率,其中負債是指金融性負債,但總資產應當修正為總資金,即總資產扣除經營性負債后的余額。為此,本文將計算Flev1、Flev2的分母替換為“總資產-經營性負債”,重新衡量間接融資杠桿率和總杠桿率,并分別用OFlev1、OFlev2表示,然后再對模型(1)進行OLS估計,其中經營性負債包括應付賬款、應付票據、預收賬款、其他應付款、應付職工薪酬、應交稅費等,ConDefer和DumDefer的回歸系數仍然顯著為負,結果再次支持假設1。
五、機制檢驗
在提出假設時,本文認為,高管遞延薪酬能成為高管的自我約束機制,從而能抑制因預算軟約束和所有制紅利導致的杠桿率高企問題,以下分別從借新還舊、過度負債、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對比、抑制高風險投資等視角對上述影響機制進行檢驗。
(一)借新還舊視角
如果國有企業能夠采用借新債還舊債方式償還到期債務,說明預算軟約束非常嚴重,若高管遞延薪酬顯著降低了國有企業借新還舊現象,則說明高管遞延薪酬能夠抑制預算軟約束。參考張興亮和夏成才(2015)[31]的研究,本文以當年應還銀行借款由借入資金償還的比例衡量借新還舊,并用符號BNPO表示,即BNPO=(當年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當年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上年末短期借款余額+上年末一年內到期非流動負債余額),該值越大,表示借新還舊的比例越高。將模型(1)中的因變量替換為BNPO后的OLS估計結果見表4所示。考察變量ConDefer和DumDefer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高管遞延薪酬顯著降低了國有企業借新還舊的比例,抑制了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問題。進一步地,本文采用溫忠麟等(2004)[32]的中介效應檢驗方法,將BNPO和ConDefer或者BNPO和DumDefer同時放入模型(1),結果見表4所示。當因變量為Flev1時,BNPO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即借新還舊比例越多,國有企業杠桿率越高,ConDefer或DumDefer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以上結果表明,借新還舊在高管遞延薪酬與國有企業間接融資杠桿率之間起到顯著的中介效應,即高管遞延薪酬因為降低了國有企業借新還舊的比例從而降低了國有企業間接融資杠桿率。當因變量為Flev2時,結論不變。

表4 高管遞延薪酬、借新還舊與國有企業杠桿率
(二)過度負債視角
由于所有制紅利更可能導致國有企業過度負債,因此本文以下檢驗高管遞延薪酬是否能夠顯著降低國有企業過度負債,從而抑制因所有制紅利導致的國有企業杠桿率高企問題。參考陸正飛等(2015)[28]的研究,計算得到Flev1、Fleve2的過度負債指標ExFlev1、ExFlev2。然后,分別將ExFlev1、ExFlev2作為模型(1)的因變量,執行OLS估計,結果見表5所示。A組報告了高管遞延薪酬對過度負債ExFlev1的影響,ConDefer或DumDefer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高管遞延薪酬顯著降低了國有企業間接融資過度負債率。此外,參考溫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應研究方法[32],將ExFlev1和ConDefer或者ExFlev1和DumDefer同時放入模型(1)進行OLS估計,結果顯示,ExFlev1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而ConDefer和DumDefer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負,以上結果表明,高管遞延薪酬能降低間接融資過度負債率,從而降低國有企業間接融資杠桿率。B組報告了高管遞延薪酬對過度負債ExFlev2的影響以及ExFlev2的中介效應,結果與A組基本一致。綜上,高管遞延薪酬能通過降低過度負債率從而降低杠桿率。

表5 高管遞延薪酬、過度負債與國有企業杠桿率
(三)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比較視角
如果說高管遞延薪酬能夠抑制因預算軟約束、所有制紅利導致的國有企業杠桿率高企問題,那么,高管遞延薪酬對國有企業杠桿率的治理效應應當比對民營企業杠桿率的治理效應更顯著,因為預算軟約束、所有制紅利主要是國有企業的問題而非民營企業的問題。為此,以下本文從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比較的視角驗證高管遞延薪酬對國有企業杠桿率的影響機制。具體地將企業產權性質變量SOE(國有企業取值為1,民營企業取值為0)分別與ConDefer和DumDefer形成交乘項:ConDefer×SOE和DumDefer×SOE,將交乘項與SOE加入模型(1),結果見表6所示。當因變量為Flev1時,ConDefer、DumDefer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但不顯著,說明高管遞延薪酬制度對民營企業杠桿率的治理效應并不顯著,而交乘項ConDefer×SOE和DumDefer×SOE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相對于民營企業,高管遞延薪酬對國有企業杠桿率的治理效應更顯著,更能顯著降低國有企業的間接融資杠桿率。當因變量為Flev2時,結論不變。綜上,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比較的結果說明,高管遞延薪酬能抑制預算軟束和所有制紅利導致的國有企業杠桿率高企問題。

表6 高管遞延薪酬、產權性質與企業杠桿率
(四)抑制高風險投資視角
高管遞延薪酬會使高管更謹慎地經營企業,更不愿意進行高風險的投資,因而不會導致企業杠桿率高企,本文對這一影響機制進行檢驗。企業購買股票或投資于房地產的風險較高,因此以交易性金融資產和投資性房地產衡量高風險投資,具體地,高風險投資Vin=(投資性房地產+交易性金融資產)/總資產,檢驗結果見表7所示。當因變量為Vin時,ConDefer和DumDefer的回歸系數雖不顯著,但均為負。將Vin放入模型(1)后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變量Vin的回歸系數均為正,當因變量是Flev2時,Vin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有證據表明高風險投資會導致高杠桿。變量ConDefer或DumDefer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負。以上結果基本驗證了高管遞延薪酬通過抑制高風險投資從而對國有企業杠桿率有顯著治理效應這一影響機制。

表7 高管遞延薪酬、高風險投資與國有企業杠桿率
六、進一步研究:高管遞延薪酬對去杠桿政策的協同效應
高管遞延薪酬對國有企業杠桿率有直接治理效應,那么,高管遞延薪酬制度作為杠桿率的內部治理機制,其能否與去杠桿政策相協同,對國有企業的杠桿率產生協同治理效應?從協同理論的視角來看,國有企業杠桿率治理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去杠桿政策、高管遞延薪酬制度實質是這個系統中的兩個子系統。去杠桿政策需要國有企業高管去落實,如果去杠桿符合高管的利益,則高管有動力積極落實去杠桿政策。當國有企業存在高管遞延薪酬制度時,去杠桿符合高管的利益,因為杠桿率的降低會使企業未來還本付息壓力小,企業有足夠的現金支付到期的遞延薪酬,高管的利益更能得到保障。概言之,高管遞延薪酬子系統可能會對去杠桿政策子系統形成很好的協同,從而對國有企業杠桿率形成協同治理效應。對于以上分析,本文設計以下模型(2)進行驗證。
Flev=β0+β1DL+β2(DL×DumDefer)+β3DumDefer+β4Size+β5Colla+β6CF+β7ROA
+β8Growth+β9FShare+β10MB+β11Expense+β12NDts+β13ITR+β14MShare+∑Industry+∑Year+ω
(2)
與模型(1)一致,模型(2)中的Flev是杠桿率,共有兩種衡量方法,分別為Flev1、Flev2。DL為去杠桿政策變量,由于去杠桿政策實施于2015年底,因此,本文將年度是2016年及以后年度,DL賦值為1,年度是2015年及以前年度,DL賦值為0。模型(2)中的其他變量與模型(1)一致。如果高管遞延薪酬能與去杠桿政策協同并對國有企業杠桿率形成協同治理效應,則模型(2)中的β2應顯著小于0,表明與去杠桿前或未采用高管遞延薪酬制度的國有企業相比,去杠桿后采用高管遞延薪酬制度的國有企業的杠桿率顯著更低。表8報告了模型(2)的OLS估計結果。DL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在2015年去杠桿政策之后,那些未采用高管遞延薪酬制度(DumDefer=0)的國有企業的杠桿率顯著降低,即去杠桿政策確實發揮了作用。交乘項DL×DumDefer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去杠桿后那些采用高管遞延薪酬制度的國有企業的杠桿率顯著更低,即高管遞延薪酬能與去杠桿政策協同從而對杠桿率形成協同治理效應。

表8 高管遞延薪酬對去杠桿政策的協同效應
七、結論與啟示
本文探討高管遞延薪酬這種企業內部治理機制對國有企業杠桿率的治理效應,并得出以下研究結論:第一,高管遞延薪酬會使高管傾向采取更加保守的財務政策,更不愿意過度負債,更愿意積極承擔現有債務的義務和責任,對國有企業杠桿率能產生直接治理效應,顯著降低國有企業的杠桿率。第二,高管遞延薪酬能夠通過抑制借新還舊水平從而降低國有企業杠桿率,說明高管遞延薪酬能夠治理因預算軟約束導致的國有企業杠桿率高企問題。第三,高管遞延薪酬能通過抑制過度負債從而降低國有企業杠桿率,說明高管遞延薪酬能夠治理因所有制紅利導致的國有企業杠桿率高企問題。第四,高管遞延薪酬能與去杠桿政策有效協同,對國有企業杠桿率產生了顯著的協同治理效應。
本文的研究結果能帶來以下啟示:其一,當前國際經濟環境具有極大不確定性,目前保市場主體、保就業的壓力巨大,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能給予市場更好的預期,有助于提振經濟,有的企業應當加杠桿,但也有的企業應當降杠桿,因此需要更加精準的杠桿率調節或治理機制。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高管遞延薪酬制度是一種具有較大靈活性、交易成本較低的機制,可以根據企業的狀況,通過調節高管遞延薪酬的比重達到調節杠桿率的目的,在國有企業中應當進一步推廣,并結合相關戰略目標進行調整和優化。其二,預算軟約束和所有制紅利引起的系列問題是國有企業治理中的關鍵問題,也一直是國有企業治理的難點。本文研究結果所帶來的啟示是,全面推行或設計類似于高管遞延薪酬制度是抑制預算軟約束和所有制紅利等問題的有效做法,能夠避免外部硬性約束機制所導致的企業規避或操縱問題。其三,本文高管遞延薪酬制度能與去杠桿政策有效協同的研究結果表明,企業外部治理機制在內部治理機制的協同配合下能發揮更好的作用,因此,在建立企業治理體系時,有必要在企業內部構建諸如高管遞延薪酬制度的內部治理機制,使其能與企業外部治理機制有效協同,從而實現企業外部治理機制與內部治理機制的激勵相容,達到更好的企業治理效果。
值得說明的是,本文沒有采用文本分析等方法通過分析企業年度報告來識別企業是否采用高管遞延薪酬制度,若如此,則對高管遞薪酬的衡量更準確,這是本文的一個局限,也是未來一個有價值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