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潮快閃”在海外:一種國際傳播的“藝術地理”范式
■ 楊光影
近年來,展示漢服、民樂、中國舞的“國潮快閃”成了海外華人青年和留學生熱衷的一種公共藝術活動。(1)高娓娓:《美國華人華僑發起街頭快閃,祝大家新春快樂,北京冬奧圓滿成功》,“新浪網”,2022年2月5日,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635106672/6175bf7002700wl7m,訪問日期:2022年8月18日。此類活動通過挪用在西方青年中流行的“快閃”形式,不僅在海外諸多城市的公共空間內傳播開來,更在“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國際社交平臺上引發了熱議。可以說,“國潮快閃”通過藝術地理的創造性實踐來展示國家形象、講好中國故事,已經形成了獨特而醒目的藝術傳播現象,由此也會成為我們研究國際傳播特別是對外傳播的一種新維度。據筆者所見,國內學界當前對相關問題的關注尚不夠多,系統性的研究也比較缺乏。筆者認為,在相關研究普遍關注國際傳播中國家政策的正面宣傳(2)比如姜飛、張楠:《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2021年研究綜述》,《全球傳媒學刊》2022年第1期;文春英、吳瑩瑩:《國家形象的維度及其互向異構性》,《現代傳播》2021年第1期;胡正榮、田曉:《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話語體系的構建:分層、分類與分群》,《中國出版》2021年第16期。、領導人訪問等重要時政新聞的外媒報道與國際輿論偏向(3)比如劉娜、田輝:《國事訪問的國際媒體可見性及其影響因素——以1978—2018年我國領導人出訪的報道為例》,《新聞記者》2019年第4期;胡鈺:《當代國際政治傳播的新趨勢》,《人民論壇》2022年第13期。的同時,我們也不妨深入觀察和思考這些“快閃”活動中的藝術行動形式與策略,關注其效果轉化和在國際互聯網社交平臺上的傳播。
鑒于海外的“國潮快閃”與公共空間及其數字化的密切關聯,本文擬借用哈里特·霍金斯(Harriet Hawkins)的“創造型藝術地理”(Creative Art Geography)理論,探討這些活動在“創造”文化地理空間過程中建構出的國際傳播新范式,即一種“藝術地理”實踐范式。霍金斯的這一理論將藝術理論家羅莎琳德·克勞斯(Rosalind Krauss)的“擴展領域”與人文地理學中的“創造轉向”理論結合,論述了在從景觀建構到參與實踐的公共藝術實踐范式變革中,藝術化的創造性行動形成新的公共空間與新的文化地理形態的潛能。(4)Harriet Hawkins,“Geography’s Creative (Re)turn:Toward a Critical Framework,”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3,no.6(2018):1-22.鑒于“國潮快閃”牽涉到藝術化的參與行動以及文化藝術空間的建構,“創造型藝術地理”對國潮快閃的國際傳播研究當具有一定的闡釋力。
一、藝術塑造新文化空間:藝術地理的“創造型”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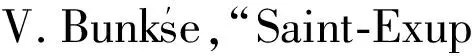
在對“創造型藝術地理”的論述中,霍金斯還提到克萊爾·畢曉普(Claire Bishop)的“參與式藝術”、權美媛(Kwon Miwon)的“特定場域藝術”(Site-specific Art)理論,并從地理學的角度重新審視了社會空間的參與機制。藝術理論家通常以“關系美學”作為理論支撐,闡述參與式藝術如何打破公共空間中既有的社會關系,以及如何建立新的關系。(11)參見Miwon Kwon,One Place after Another:Site Specific Art and Locational Identit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2);Claire Bishop,Participation(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6).相比這種“關系美學”的思路,霍金斯更注重藝術在重建社會關系之后生成了(或會生成)何種文化地理生態。在此,連接藝術與生活的藝術形式尤其是參與式藝術被霍金斯所重視。參與式藝術的空間實踐力及其“藝術行動主義”(Artivism),強調參與者對空間進行形態和意義的再創造,以及重構空間地緣、空間政治、地方想象、身份認同的可能性。(12)參見Harriet Hawkins,Geography,Art,Resrarch:Artistic Research in the GeoHumanities(New York:Rouledge,2021),pp.83-85;Dagmar Danko,“Artivism and the Spirit of Avant-Garde Art,”Art and the Challenge of Markets 2(2018):235-261.類似的話題同樣被西方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所談及,當然,以戴維·哈維(David Harvey)、多琳·馬西(Doreen Massey)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人文地理學家的理論底層邏輯是:政治經濟制度和結構的變革引發空間經驗和藝術美學形態的變遷(如哈維認為后福特主義制度是后現代美學的緣起);(13)David Harvey,“Monument and Myth,”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9(1979):362-381.而與之相比,霍金斯更關注藝術本體所包含的活態的空間創造力,并聚焦于這種創造力的激活方式。她認為,藝術所創造的文化地理生態不一定是固定的、持久的,這是一種生成式的、有兼容性甚至臨時性的創造性空間,它有別于資本的規劃空間。霍金斯希望此類空間能夠生成打破地緣區隔的文化生態。(14)Harriet Hawkins,“Geography’s Creative (Re)turn:Toward a Critical Framework,”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3,no.6(2018):2.
二、在藝術行動中創造“認同空間”:海外國潮快閃的藝術地理生態
通常認為,“快閃”活動由美國時尚雜志《哈珀》(Harper’sMagazine)的主編比爾·瓦西克(Bill Wasik)發起。當時,他通過電子郵件招募了數名參與者,臨時集合到紐約的梅西百貨店。這群參與者不斷詢問售貨員有沒有“愛情地毯”(實際并無此物)出售,而10分鐘后又立刻離開。“快閃”(flash mob)這個稱呼則是瓦西克事后定的。(15)Bill Wasik,“My Crowd or,phase 5:A Report from the Inventor of the Flash Mob,”Harper’s Magazine(March,2006):56-66.“快閃”強調匿名參與、突發介入和即興表演,組織者基于電子郵件或網上社交平臺發出行動號召和主張,將彼此匿名的參與者集結到公共空間,進而把預先的行動主張表演出來,然后快速散去。顯然,這種活動因其參與性和空間創造性,可歸入霍金斯“藝術行動主義”的范疇。(16)參見Paulina Bronfman,“‘A Rapist in Your Path’:Flash Mob as a Form of Artivism in the 2019 Chilean Social Outbreak,”Connessioni Remote 2,no.2(2021):210-225.進一步而言,我們可以從“創造型藝術地理”的角度解讀“快閃”。與西方的“快閃”活動相似,海外的“國潮快閃”同樣在參與中創造著新的文化空間,而且這里更有學術意味的是:這種在異國他鄉的城市中創造出的文化地理生態,包含著霍金斯所說的“臨時”“包容”與“活態”。但同時,海外的“國潮快閃”又有與西方“快閃”的明顯不同之處,其進行的傳統藝術展演不會像詢問所謂“愛情地毯”那樣擾動公共空間。因此,我們可以發問:西方式“快閃”如何創造新的文化空間?海外的“國潮快閃”如何重構西方“快閃”?這種重構創造出了怎樣的文化地理生態?
(一)空間的創造性破壞:西方快閃的“藝術行動主義”
維拉格·莫爾納(Virág Molnár)從藝術史角度出發,同樣將西方的快閃活動溯源到達達主義的“藝術行動主義”(17)Virág Molnár,“Reframing Public Space through Digital Mobilization:Flash Mobs and the Futility of Contemporary Urban Youth Culture,”Space and Culture 17,no.1(2014):46-47.。從先鋒藝術的脈絡來講,“藝術行動主義”一開始就是文化抵抗的實踐路徑與藝術形式之一,當今的西方快閃則是網絡社會中“藝術行動主義”的延伸。“藝術行動主義”基于藝術介入公眾與社會的主張,意在讓藝術家走出畫廊與美術館,通過藝術化的行動引發公眾關注、制造文化話題,以此表達觀念。這與達達主義藝術家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況與人道危機,對資產階級啟蒙運動所建構的理性、科學精神產生懷疑,從而通過“反理性行動”傳播抵抗立場是有一定的相似之處的。
在霍金斯看來,先鋒藝術是集表演、實物、參與和組織于一身的綜合體,可以通過某種意義上的“沒有預設”的創造性行動去建構鮮活的文化地理生態。不過,在說到創造的方法與路徑時,霍金斯對“創造性”的解釋依舊滑動于“參與”“組織”等描述性語匯中間,沒能提煉出一個富有理論穿透力的概念。對此,筆者擬借用戴維·哈維提出的“創造性破壞”加以彌補。哈維將先鋒藝術歸入后現代藝術美學的范疇,把它與現代藝術作對比。他結合利奧塔、詹姆遜等后現代哲學家的論述,將后現代美學的特質總結為“為破壞而破壞”的“創造性破壞”(18)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2),p.44.。對先鋒藝術而言,“創造性破壞”不僅呈現于挑戰資本主義制度及其藝術體制的努力,更表征于介入與擾動公共空間的創造性實踐。無論是博伊斯(Joseph Beuys)的參與式藝術,還是紐約的涂鴉藝術,起初都帶有藝術家和參與者群體的擾動甚至破壞傾向,但需要強調的是,藝術行動主義對空間的“攪動”并不是物質層面的,而是對空間中既有的社會關系的革新。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社會空間通常被視為社會實踐的物質基礎,其中也包含社會關系的組織結構。因此,“情境主義國際”等左翼的先鋒藝術流派力圖通過行動和表演制造暫時的感性連接和情境,以此喚起人們對資本主義那種已經讓他們習以為常的操控的反思與抵抗。(19)J.Brien Houston,H.SeoandL.A.T.Knight,“Urban Youth’s Perspectives on Flash Mobs,”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no.3(2013):236-237.
在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后,擾動式的藝術行動開始延拓其數字化維度,快閃活動也成了其代表之一,在網絡社會語境中延續突發介入、“越軌”表演等形式的“創造性破壞”。具體來說,首先是利用社交媒體組織參與者突然介入公共空間。在介入梅西百貨店的活動引發關注后,快閃活動逐漸流行,德國慕尼黑火車站的“吹泡泡”快閃、英國泰特美術館的“無聲迪斯科”快閃等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20)同上。而這些活動的共同之處就在于前期通過電子郵件或社交媒體聯絡。其次,快閃繼承了達達主義、“情境主義國際”對“越軌”的偏好。并不存在的“愛情地毯”打破了日常化的消費行動;而在泰特美術館,本應觀看藝術作品的觀眾卻成了帶著耳機跳舞的“迪斯科舞者”。這些無傷大雅的“越軌表演”打破了公共空間中既有的關系結構,在攪動空間秩序的同時創造出了新的社會關系與空間形態。
在快閃的“創造性破壞”中,行動者共同建構出一個異質集合的、感知互相激發的、情境激烈生長的抵抗空間。快閃的組織往往沒有特別精確的計劃,組織者僅僅通過一個號召,將對此感興趣的各色陌生人聚集起來,每個參與者基本都是根據自己對號召的理解展開行動的。如此一來,各人的行動方式會存在一些差異,卻又能暗合成一種相關性的聯結。在此,行動者實際創造出了一種德勒茲所說的“集合”空間。所謂“集合”,恰是指異質的物互相聯結并不斷產生新意義的“生成狀態”;(21)Martin Müller,“Assemblages and Actor-networks:Rethinking Socio-material Power,Politics and Space,”Geography Compass 9,no.1(2015):29;另參見Deleuze and C.Parnet,Dialogu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69.而異質的參與者在相關行動中的聯結,就組成了“異質集合”(assemblage)的空間文化生態。在“集合式”的連接中,參與者之間、參與者與好奇的觀看者之間的感知是相互激發的。由于行動的突然性與創意性,參與者共同打破了既有的空間關系,而且在各自打破的過程中相互啟發,從而拓展新的可能性。如慕尼黑火車站的“吹泡泡”快閃,在參與者吹泡泡的同時,候車的乘客也可能加入其中進行觸碰泡泡的游戲。在行動者的相互激發中,原本繁忙且頗有焦慮氣息的火車站短暫地變成了歡樂的嬉戲場。此外,異質集合還會有其數字化的生長。打破空間既有關系的行動意味著空間認知邊界的拓展,這種拓展會因為臨時性和偶發性而呈現動態擴張的趨勢,并在相互激發中呈現出激烈生長的擴張狀態,這樣的生長狀態通過數字媒體的傳感,可能引發更多人的模仿。
(二)破壞性創造:海外國潮快閃對西方快閃的機制轉化
如上所述,西方式快閃對公共空間的“創造性破壞”主要以群體的突發介入為起點。海外的國潮快閃也挪用了這種包含臨時性、隨機性、偶發感和意外感的介入形式,攪動異國城市的公共空間。譬如2018年華人青年和留學生在英國曼徹斯特街頭開展的漢服快閃,在曼徹斯特多個街區的英倫風格景致中展現了獨特的差異化美學;又如2018年新春,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巴西圣保羅、美國舊金山等地的華人華僑以快閃的形式歡度春節、唱響“中國”,也暫時打破了公共空間慣常的社會關系——像金門大橋這樣的地方原本是橫跨舊金山的通道,當國潮快閃以古琴的表演介入該場所時,它臨時變成了演出的場所,其間出現了展演和觀看的關系。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挪用形式的背后,國潮快閃的參與者以組織化連接將西方快閃的“破壞性”轉化了。所謂“連接”,是存在于數字互聯時代的人、數字平臺與社會空間構成的社會關系網絡中的,而西方的快閃攪動社會空間的那種“破壞性”來自于一種異質性的連接。西方快閃因發起者更加個人化、計劃性更弱,其連接方式屬于數字平臺上的陌生化社交,由此形成的快閃社群基本也是一種高度異質的集合體。在西方快閃中,“破壞性”來自于現場行動的在場性和不確定性,也正是這種非固定的行動形態才能破壞既有的社會空間關系。而要實現這樣的不確定性,也離不開多樣化、臨時性的參與者群體。可以說,連接的異質性越強,其所涉群體的多樣性就越豐富,快閃的“破壞力”也就越大。與之相比,國潮快閃將異質性連接轉化成了同質性連接,大大降低了“破壞力”。國潮快閃往往通過官方的社團組織發起,這等于將其數字連接的核心變成了數字媒體上的熟人社交,陌生化社交則成為其外圍延展,由此形成的快閃群體是同質聚集的網絡共同體,如留學生群體的國潮快閃背后是成員相互熟悉的校內社團、校友會、同鄉會等。這一變化讓快閃群體更加可控,減弱了快閃對空間的“破壞性”。
我國的納稅人身份有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兩種。因為不同的納稅人身份所納稅的方式和稅額有較大的區別,享受的優惠政策或者待遇方面也不同,所以納稅人事先要對自己的納稅人身份有一個充分的考慮,到底選擇哪個身份最有利于自身的稅負。新出臺的的政策明確表示,在2018年12月31日前,一般納稅人如果滿足相關政策條件就可以從一般納稅人轉回小規模納稅人,在此之前沒能抵扣完的進項稅額作轉出處理。所以,這就讓很多企業都心動了,導致一些企業盲目的想要轉回小規模納稅人,以便給自己減稅,卻忘了結合自身企業的實際情況全盤考慮,這將會帶來物極必反的后果。
另外,從“在場”的連接來看,西方快閃活動的連接隨機性、隨意性和偶發性也很強,在臨時“游戲”中顯現了對空間的較強“破壞性”;華人在海外進行的國潮快閃則將之轉化為計劃性連接,在精心設置的“程式”中削弱了這種“破壞性”。我們知道,西方快閃的社群連接邏輯依然是“情境主義國際”的行動方式的延續,講求以臨時集體創造出“情境”,進行一種游戲化的“破壞”,以連接藝術、日常與空間,只不過“情境主義國際”帶有更講求政治美學的抵抗性,以此反思資本主義的空間規劃和日常而已。相比之下,海外的國潮快閃的連接大多出于自上而下的計劃,參與者在正式開展活動之前,是在社團的組織下精心排演過的。在排演的基礎上,程式化在參與者的表演中替代掉了不少隨機性。但應該注意的是,這并不意味著空間創造力的消解。相反,國潮快閃通過喚起文化記憶的表演策略,實現了從“創造性破壞”到“破壞性創造”的轉變。在海外的國潮快閃中,漢服、古琴、傳統戲曲等成為主要的內容,這些集體表演創造出傳統文化的“情境”,在臨時解構既有的社會空間關系的同時,制造出新型的跨文化交際空間。如果從符號學角度來看,這些表演可被視為傳統文化符號的一種活化。
進一步以文化符號的視角來看,亞文化研究者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將西方的青年亞文化視為一種“風格抵抗”(22)[美]迪克·赫伯迪格:《亞文化:風格的意義》,陸道夫、胡疆鋒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頁。,比如嬉皮士、酷兒等青年亞文化群體以制造抵抗性文化符號去對抗主流文化和父權文化,而西方的快閃同樣包含亞文化的維度,其偶發的表演形態同樣可視為一種“風格的抵抗”,只不過抵抗的焦點已由物質符號的制造轉向了非物質的行動生成。與之不同,國潮快閃的表演在突然介入特定空間后,創造出一種以傳統文化符號為紐帶的“風格協商”。這體現在三方面:其一是快閃社群內部互為觀眾的相互確證;其二是快閃社群與國外觀眾之間的美學溝通——這種溝通并不是符號意指層面的,而是基于對符號能指如漢服的色彩、古琴的音色、戲劇的唱腔的感知,這樣的在場感知無疑能喚起國外觀眾對中國文化的想象;其三是傳統文化情境與異國公共空間的協調關系。所以,國潮快閃中的文化展演并未擾亂公共空間,相反,其文化情境通過文化符號的活化滲入了異國的公共空間,形成了一種“東方情境”與當地地方性的對話關系。
(三)青年亞文化、傳統藝術和民族與國家意識的共構:海外國潮快閃創造的認同空間
西方的快閃活動作為青年亞文化的一種形態,以“創造性破壞”去生成一種帶有反叛色彩的“抵抗性認同”。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將網絡社會中的“認同”分為三類:其一是認同國家、民族和主流文化的“合法性認同”,其二是反叛主流文化的“抵抗性認同”,其三是社區通過組織和參與而自發生成的新的社群認同,即“計劃性認同”。(23)[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夏鑄九、黃麗玲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顯然,無論是在梅西百貨問詢“愛情地毯”還是在慕尼黑火車站吹泡泡,快閃都具有“非主流”的意味,通過對公共空間中既有關系的“創造性破壞”,生成并不一定是激烈反對,而是帶著戲謔性質打破陳規的“抵抗性認同”。這種戲謔無疑繼承了先鋒派否定藝術自律、輕視藝術體制、講究藝術介入生活的傳統。
與之相比,海外的國潮快閃通過程式化參與、展演互見、跨域連接,形成了基于社群計劃的“合法性認同”。卡斯特認為,網絡社區與社群是個人在網絡社會實踐中形成的組織群體,而社區的組織實踐會形成“計劃性認同”,它區別于“合法性認同”和“抵抗性認同”,是一種新的認同類型。在海外的國潮快閃中,我們也確實看到體現著同質化連接和計劃性連接的群體性組織實踐,這樣的實踐并不意味著參加國潮快閃的社群認同取代了“合法性認同”,相反,他們建構出的是一種青年亞文化、傳統文化、民族與國家意識三者“共構”的認同空間。
對此我們稍作展開。從活動過程來看,這種共構包含“社群認同—身份認同—民族與國家認同”的漸進。盡管組織方式已經轉化,但海外的國潮快閃依然包含青年亞文化的形態。這類快閃的參與主體是青年,且以留學生、“二代移民”等華人青年為主,他們的聚集有利于產生社群認同。同時,他們將傳統文化植入活動之中,既以青年亞文化的形式呈現傳統文化,也以傳統文化的風格呈現青年亞文化,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傳統文化與青年文化的共構。這種共構的連接點就在于身份認同,特別是華人身份的確證與展現。最終,隨著《我和我的祖國》等主旋律歌曲的演唱,華人的身份認同又轉化為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
而從組織機制來看,前述的三者共構是在程式化參與、展演互見、跨域連接中得以“落地”的。此類國潮快閃多是經過精心排演的,這種程式化的參與強化了其活動的計劃性,消解了參與者的獵奇心態,計劃中出現的傳統文化符號則可以不斷催化“合法性認同”的生成。而“合法性認同”的生成過程也是展演互見的過程,參與者既作為表演者開展活動,也能成為喚起圍觀者“合法性認同”的“觸媒”。例如2019年9月在澳大利亞悉尼歌劇院、唐人街和海港大橋出現的漢服快閃,迅速引發了路人圍觀,特別是當地華人。在圍觀中,觀看者的民族與國家認同會被傳統文化符號的活化表演所喚起,與表演者形成關于認同的相互確證。另外,“合法性認同”的形成還可以通過一種異質文化的跨域連接來實現。國潮快閃制造了臨時的傳統文化情境,這就與異國的文化語境形成了跨地域的連接,而該連接中的語境反差可以激發參與者的身份認同,由此強化其“合法性認同”。用具體例子來說,澳大利亞的漢服快閃在悉尼歌劇院旁邊舉行,該建筑作為整個澳大利亞的標志性建筑,與由漢服指代的中國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除了異域空間與傳統符號的反差之外,國外圍觀者的認可也是跨域連接中激發“合法性認同”的一個面向。在澳大利亞的漢服快閃中,不少當地本土人士也積極圍觀,他們的“打卡”正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好奇乃至初步認同的反映,而這種來自異域族群的認同也從側面激發了華人參與者的“合法性認同”。
概言之,國潮快閃將藝術行動主義的“創造性破壞”轉化為“破壞性創造”,在組織化連接中創造出生成“合法性認同”的文化空間。這種生成是通過程式化參與、展演互見、跨域連接而實現的。
三、基于“圖景族”的空間認同:從藝術地理到藝術數字地理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海外的國潮快閃的國際傳播不僅在異國物理空間中的藝術地理創造之中展開,還延伸到了數字空間中的國際社交媒體平臺上。快閃的誕生本身即始于電子郵件往來形式的組織,而當移動互聯技術普及之后,社交平臺不僅可以集結快閃活動,還可以將快閃的狀況“再平臺化”。快閃所創造的藝術地理圖景會被轉化為社交平臺的“共情酶”,由此形成包含空間化認同的數字傳播——這里的“共情酶”是受到“討論酶”(discussion catalysts)的啟發而衍生的概念。伊泰·西美爾博伊姆(Itai Himelboim)等人以“討論酶”描述社交平臺中催生受眾參與討論的中介,(24)Itai Himelboim,Eric Gleave and Marc Smith,“Discussion Catalysts in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s:Content Importers and Conversation Starter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no.4(2009):771-789.然而能驅動網絡受眾參與的不僅有話題討論,還包括共感共情、共趣激活、文化想象。因此,本文擬以“共情酶”一語來指稱國潮快閃在社交平臺上催生情感認同的要素。
(一)快閃空間數字化:藝術的“數字地理圖景族”
在自媒體發布和大數據推介的支撐下,國潮快閃在社交平臺上的傳播會將物理空間中的地理生態數字化與圖像化,進而使之變為呈“圖景族”樣態的藝術數字地理生態。“圖景族”的說法受到媒介理論家列夫·曼諾維奇(Lev Manovich)的啟發:曼諾維奇提出,社交平臺的視覺文化不再是單一作品的觀看,而是相關作品的“族類”聚集。他對海外社交平臺“圖享”(Instagram)上的“自拍”圖像展開研究,通過分析對同一城市標志物的自拍,揭示這數以億計的圖片為受眾建構出來的對城市空間的重新認知。(25)N.Hochman and L.Manovich,“Zooming into an Instagram City:Reading the Local through Social Media,”First Monday 18,no.7(2013),accessed August 9,2022,https://firstmonday.org/ojs/index.php/fm/article/view/4711/3698.而在海外社交平臺上發布國潮快閃內容的自媒體,除了有活動的直接參與者外,還包括其圍觀者,這些“共趣”粉絲的轉發增加了國潮快閃消息擴散的速度和廣度。在民間化、多樣化與微觀化的傳播過程中,同一地點的國潮快閃即構成一個“圖景族”。由此,當國潮快閃成為熱點議題之后,不同地點的國潮快閃還可以形成有共通議題的相關性聯結,由此構成更大范圍內的“圖景族”。“圖景族”會在議題保持足夠熱度的時間段內動態生長,不斷強化相關行動的空間轉向與正向傳導。
同時,在平臺的受眾端,對此類快閃感興趣的西方受眾同樣會在大數據推介中接收到相關的藝術地理圖景,從而在內心建構出國潮快閃的地理“圖景族”。這樣的接受機制近乎一種視覺化的“網絡議程設置”。議程設置是傳播學的經典概念,主要是指媒介精英對公眾輿論議題的引導;網絡議程設置則是議程設置概念在網絡空間中的延續。研究者郭蕾分析道,傳統媒體議程設置的焦點在于內容生產,而網絡議程設置的焦點在于關系建構。若借鑒心理學的“認知架構”觀念,可將網絡議程設置視為網絡傳媒對受眾進行的一種相關內容的“認知架構”建設,而這樣的架構依賴于網上的社交關系。(26)Guo Lei,“A Theoretical Explication of the Network Agenda Setting Model: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in Guo Lei and M.E.McCombs(ed.),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Networks:New Directions for Agenda Setting(London:Routledge,2015),p.16.在基于大數據的類型化推介之下,國潮快閃實際上已成為網絡議程設置的一個議題,而由此形成的“藝術地理圖景族”則是平臺試圖給予受眾的一種視覺化的“認知架構”,能夠引導更多的西方受眾去理解中國的風貌與思維。
(二)破除歧見:“共情酶”的空間化認同
海外社交平臺的受眾主體自然是西方民眾,其中不乏大量青年。對西方青年而言,海外華人青年的展演具有一種青年亞文化的親緣性。參與這些快閃的海外華人青年長期在當地學習、生活,更熟悉當地的青年文化及亞文化,擁有鮮活的文化體驗。于此而言,相比國內的快閃參與者通過社交平臺和網絡圖像去模仿,海外華人青年更能接觸快閃的原生形態,其介入公共空間的行動狀態也更接近于西方的快閃,也讓西方青年更容易形成對國潮快閃的“數字共情”。
除了青年亞文化層面的共情之外,漢服、古箏等元素的出現亦帶動了西方青年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想象。西方人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原本具有一種地理向往與地緣想象,這種想象以陶瓷、絲綢等作為“物媒”。在國潮快閃中,以絲綢為材料的漢服會以其東方風格重新喚起西方青年的這種想象,兼以民族音樂實施聽覺維度的感知操練,在彰顯文化魅力的同時引導文化認同。當然,不可否認的是,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社會)長期存在針對華人的族裔歧見,好萊塢電影中以“傅滿洲”為代表的反派華人形象亦深入許多民眾的心里。所以,海外的國潮快閃在社交平臺中所傳播的傳統文化,其首要作用目前尚不全在于展示文化魅力,而是讓“數字共情”通過平臺用戶的轉發和評論得以擴散,從情感維度通過共情想象去減弱和消除偏見。
綜合來看,西方青年基于亞文化的青年共趣與傳統文化的想象共情,可以進一步理解中國的民族與國家認同。目前,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西方主流媒體尤其是美國媒體往往重點報道中國社會的負面消息,將中國塑造為未來的“敵人”,以期引起西方民眾的敵意和恐懼;而對參與社交平臺的多數西方青年來說,對中國的認知同樣主要依靠社交平臺上有關中國的新聞來建立。萊巴茨(Claire Laybats)和特雷丁尼克(Luke Tre-dinnick)認為,傳媒場域沒有所謂的“事實”,只有“競爭式真相”(competitive truth)(27)Claire Laybats and Luke Tredinnick,“Post Truth,Information,and Emotion:View All Authors and Affiliations,”Business Information Review 33,no.4(2016):204-263.。因此,比起國事訪問報道等時政新聞的傳播,國潮快閃可用生動活潑的形式呈現民族與國家認同,從某種意義上說更有利于西方青年形成對中國的正面認知,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西方主流媒體的負面議程設置的效果。
(三)認同的空間轉向:中國國家形象的藝術數字地理
我們已經看到海外的國潮快閃可以創造出青年亞文化、傳統文化和民族與國家共構的“合法性認同”。這樣的認同在國際社交平臺上以破除歧見為基礎,力圖有效引導西方青年轉變對中國形象的看法;而這種轉變無疑基于國潮快閃在物理空間創造的“認同空間”之藝術地理生態。在數字空間中,藝術地理生態可以通過社交平臺中的自媒體賬號擴散,助推中國國家形象數字傳播的“空間轉向”,落實其民間性、社群性和微觀化。下面稍作展開。
首先是民間性傳播。國潮快閃的性質為非官方活動,其參與者也并非官方正式派遣,這讓它區別于宣傳國家形象的正式儀式。比如,早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中國政府就曾在紐約時代廣場的大屏幕發布國家形象宣傳片,其內容和傳播機制分別以宏大敘事和國際辨識度為重點,既展示了中國的標志性成就,也有國際影視明星和國際體育明星加盟。相比之下,無論從機制上說還是從內容上說,國潮快閃在國際網絡社交平臺上的傳播都帶有民間性:其發布機制是偏向隨意性、個人化的,其內容是“素人化”的和“接地氣”的,也正是這樣的民間性收獲了西方民眾特別是其中的青年人的額外認同。
其次是社群性傳播。快閃活動的每個參與者都可以是聚合“粉絲”的“個人社區”(personal communities)(28)Vincent Chua,Julia Madej and Barry Wellman,“Personal Communities:The World according to Me,”in John Scott and Peter J.Carringto(ed.),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Los-Angeles,London:SAGE,2011),pp.1-29.,所以整個活動可以成為“個人社區”吸納“共趣粉絲”的“共情酶”。由此,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正面認同會在“個人社區”中展開,實現一種基于“共趣粉絲”的社群性的擴散。“粉絲”的轉發和評論會加劇這樣的擴散,而國際網絡社交平臺用戶以西方民眾為主體,更不乏西方青年,所以他們的關注、轉發與評論也會對中國形象的正面傳播有不少助益。
最后是傳播的微觀化。參與者通過自己的賬號發布的活動圖像與視頻,其記錄現場的視角、剪輯方式多有不同,屬于個人化、多樣性的呈現。這種多樣性可以給平臺受眾以足夠強的趣味性,不容易使之產生刻板的、類型化的印象。
國潮快閃在正面傳導中國形象的同時,還形成了傳播中國主張的藝術地理范式。比如在意大利、哈薩克斯坦等國進行的國潮快閃中,“‘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主題之一。當然,這種主題并不會在活動過程中刻意提出,而是在社交平臺的后期傳播過程中加以標注或提示的。社交平臺以喜好、標注等作為連接參與者關系網絡和內容傳播網絡的節點,通過對主題的標注,“‘一帶一路’倡議”即可成為國潮快閃的重要主題,構成新的“共情酶”。即便西方青年用戶對“一帶一路”的具體內涵不甚了解,也能通過國潮快閃的數字傳播“感知”該倡議所展示的開放態度、溝通立場和合作訴求。
小 結
綜上所述,以霍金斯的“創造型藝術地理”理論為視角,可以確認海外的國潮快閃活動實際上建構出了一種國際傳播的“藝術地理”新范式。霍金斯聚焦于藝術如何創造藝術空間與文化地理,將理論視野聚集到先鋒藝術等行動主義的藝術流派對空間的意義與文化地理生態的再創造上。快閃活動作為對藝術行動主義的一種繼承,以講求突發介入、偶發連接的“創造性破壞”打破既有的空間關系,解構既有的公共空間形態。而海外的國潮快閃活動又將“創造性破壞”轉化為“破壞性創造”,通過對突發形式的挪用以及將偶發連接轉化為組織邏輯,建構出了青年亞文化、傳統文化、民族與國家意識三者共構的“合法性認同”的空間。國潮快閃不僅創造了物理空間中的藝術地理生態,還能在國際社交媒體平臺上形成“數字地理圖景族”。在從物理空間的單一圖景到網上社交平臺“圖景族”的聚合中,平臺的西方受眾尤其是青年受眾易于通過亞文化的“共趣”和傳統文化的想象,破除其族裔偏見和政治歧見,轉向對中國國家形象及主張的空間化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