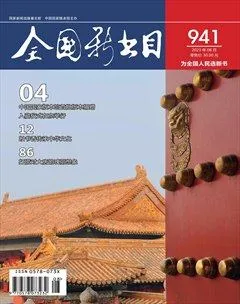《一路風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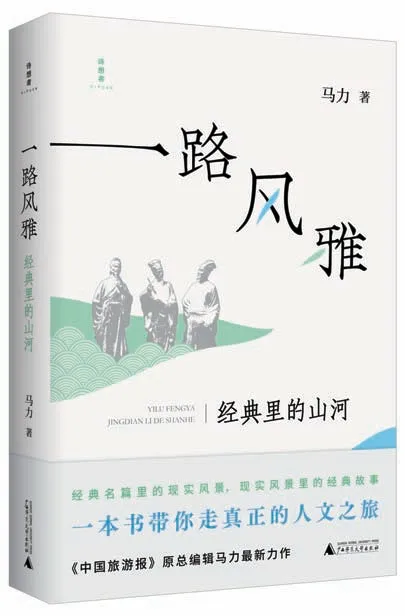
馬力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3.5/76.00 元
馬力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高級編輯,曾任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中國旅游報》總編輯。著有散文集《鴻影雪痕》《走遍名山》《風雅樓庭》等,文學評論集《山水文心》,專著《中國現代風景散文史》等。曾獲冰心散文獎、中國報紙副刊作品獎等獎項。
本書主要抒寫和文學藝術經典相關的著名風物,突顯自然、人文景觀和經典詩文及其歷史背景之間的聯系,從中讀者既能領略華夏勝概之美,又能深品古今詩人作家描摹景物的筆墨,更可體味他們放曠林泉、寄興煙霞的詩意情懷,在閱讀中與作者一同游望南北形勝之地,在今日情境中重游,尋找歷史的痕跡。
大風起兮云飛揚——歌風臺和《大風歌》
我昔年過秦川五陵原時,眼掃長陵,深驚其高大,漢世樓臺多求此樣氣象。
在中國古代的宮室中,秦漢時期的幾無一存。《古詩十九首》有云:“西北有高樓,上與浮云齊。”縱使夸張,仍可知漢人筑樓是不怕與云比高的。我在西安時沒有見到漢家宮闕,故對上林苑、未央宮那樣的勝跡無從想象,但沛縣享帝鄉之名久矣,今人興造漢城,以意為之,略求同舊時相似。我入內一看,深沉雄大,漢世之風近身可感。
漢城建在湯沐湖上,實際是一座浮在水上的宮苑,廣造殿堂,高筑帝闕,舉目一望,檐牙似無盡端,令我有些眼花繚亂。司馬相如《上林賦》云:“于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土木之工仿佛照此而來。漢承秦制,我想,躲開修齊治平不談,至少在建筑的氣派上,秦漢無別。唐杜牧描寫的秦宮的雄麗,和司馬相如真是同等筆墨。而阿房宮即上林苑前殿,漢唐賦家身入黃門之內,只好盡心鋪張辭藻。
高祖好楚聲,他的《大風歌》極短,僅三句:“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班師過家門的劉邦在父老子弟面前顧盼自雄,酒酣而歌,何等意氣揚揚!蕭統把此首樂府歌辭輯入《文選》雜歌類,天下傳誦。
《大風歌》和項羽的《垓下歌》一抒定鼎還鄉之喜,一遣失鹿絕命之悲,同為楚騷的名作。劉項二人都不是搖筆桿子的文士,談不上什么學問藝術,但武功之外的這幾行詩,后人講秦漢文學時卻躲不開。語曰:“固天縱之將圣,又多能也。”劉勰即持此論,云:“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這像是一段諛辭,完全沒有說出個所以然。司馬遷謂高祖歌此詩后,“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他記項王垓下悲歌,也用了“泣數行下”四字。劉項爭鋒,得失殊異,吟詩寄志是本紀中最動人心魄處,太史公在這里不易一字,什么意思呢?我還沒能想透。
劉邦置酒沛宮,擊筑觴詠,是應該有一座高臺的。而沛縣果然就有歌風臺,壁高,殿闊,同《大風歌》的豪氣配得上,說它是一座晝錦堂也無不可。唐伯虎的《沛臺實景圖》不知道是照著什么畫出來的,瘦石古柳掩著一角瓦脊,靠右題了數行字,看上去有些清曠,就意境論,和今日的歌風臺很不一樣。
我所見的《大風歌》碑是一件殘物,只存上一半,余下的像是補接的。通篇用大篆,年代頗難斷定,或曰為蔡邕書,實在也不好確說。假定是真,放入西安碑林也足以有它的高位。伯喈每臨池,“如對至尊”,此塊詩碑大概也是這樣寫出來的。

太史公謂:“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后人繪高祖像,大約本此。袁子才《隨園詩話》:“古無小照,起于漢武梁祠畫古賢烈女之像。”照此看,漢代即有劉邦繪像也是可能的。
歌風臺上塑有高祖像,只看臉的話,真是“隆準而龍顏,美須髯”,有狂霸之氣,在一旁還可以配上李白的詩:“按劍清八極,歸酣歌大風。”這比把他供在神龕般的御座上要好。
沛縣是靠微山湖的,云水蒼茫,恰是出《大風歌》的地方。項羽家在宿遷,去沛縣未遠,那里也有湖——駱馬湖。湖邊會有一座西楚霸王的造像嗎?可惜我沒有去過,無以言,只是覺得項羽總該是魂返江東的吧!他嘗言:“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壯志未酬,項王及死才三十出頭,千載之下仍惹人為其功罪扼腕,但正統的漢史官卻并不怎么尊重這位拔山扛鼎的英雄。司馬遷說他“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真是嚴于斧鉞。
我好像望見沛公站在歌風臺上冷笑。在知堂老人看來:“項氏世世為楚將,劉氏則是吏胥流氓,成敗不同,這大概亦是世家破落后的自然趨勢吧。”話雖未可上比史家之言,卻實在是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年紀大起來了,思及劉、項,尤感前引的幾句比起我少時單純從說書唱戲上得來的皮毛深透得多。
東海之處聳崇巔——花果山和《西游記》
花果山的竹節嶺下有一尊吳承恩像,連云港的同志說是贛榆工匠刻的。石像臥于花樹叢中,我端詳片時,如對一山之主。
半山筑有吳承恩紀念館,一帶粉墻,瓦屋芳池,不知道是不是他寫《西游記》時住過的吳庵別墅。射陽先生為淮安人,坐船北行,經灌河口來訪花果山,路很近。館中有一幅乾隆時繪的《東海云臺勝境圖》,花果山自波濤中聳出,真是海上的仙山,鼓棹而往固屬意中事了。
山中多花,秋天未到,金黃的菊花就在山徑兩旁吐艷了。鳥鳴與蟬噪互答,有一種天然的和諧,林谷被襯得極清幽。吳承恩寫神話小說的時候,過眼景象大略相近吧,靈思馳騖,所以文字特別浪漫。

“花果山”這名字大約是從《西游記》里借用過來的。花果山是云臺山的主峰,而云臺山古稱蒼梧山,讓人想到舜帝死于蒼梧之野的傳說。直到今天,一些連云港人還是常把云臺、蒼梧掛在嘴邊。“蒼梧云起至今愁”是頗牽幽思的舊句,但花果山不會使人憂郁。王維有云:“花迎喜氣皆知笑,鳥識歡心亦解歌。”我踏入一山翠蔭中,懷的就是這種心情。
層階盤折,遙入縹緲云氣間。這一段山路也叫十八盤,只是同泰山那里的一比,具體而微,足見中國風景在名稱上的趨近。登花果山的盤道要省一些力,因為路短,坡又不甚陡峻,盡可放緩步子,意態悠閑地去走。“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看花聽鳥的妙處無妨在此間領受。為游山饒添趣味的則是沿途所遇的耍猴人,猴子伏在這些壯漢的肩上,對山外來的男女全無畏色。
風門口是要過的頭一道“天門”,風勢果然很大,炎夏往這里一站,很涼快。此處砌了一座山門,有幾個賣西瓜的漢子吆喝生意,瓜已熟透,剖開就露出多汁的紅瓤,山行的旅人看了會甜到心里去。四圍緊臨生涼的深峽,不然吹不來這樣大的風。從這里回望來路,一片蒼郁,亂峰缺處,閃出嶺底的大村水庫,太陽下的波光映著岸邊的阿育王塔(本地人呼為大村塔)。
從風門口轉過一道彎,躍上臥在琵琶嶺下的九龍橋。溪水順著九條大澗瀉下,在橋底匯流,于深谷間激起喧響。橋于明萬歷十五年(1587 年)建起,旁植的千年銀杏仍舊極茂綠,舊籍中發黃的歷史附著在這些古物上,反而會勃發鮮活的生機。由這座磚構拱橋過到對岸,就到了鎖澗去水簾洞的路上。北面忽然撲來一座高峰,多佛寶塔和海寧禪寺的檐脊仰翹于一山竹樹深處,真有不凡的氣象,通上去的索道則教人不禁吟出“云棧縈紆登劍閣”這句唐詩,題勒“花果山”三字的巨巖也一眼可以望到。入寺,從大雄寶殿的三尊佛的面目上,我悟到的只是一個“靜”字。院中的兩棵銀杏越千載仍頗頑健,人之百年猶如一瞬,真是不堪一想。
寺后石徑是折往水簾洞的。洞不深,微有曲折,壁濕,水珠泠泠下滴。洞口垂落一掛帷幔似的瀑布,其勢狂驟,這就是齊天大圣的水簾洞呀!此等地方少不了古刻,一望,果然。明海州知州王同留下的“高山流水”題鐫略能應景,卻稍嫌俗氣。清道光帝的“印心石屋”是題賜在淮北鹽政改革中建功的重臣陶澍的,這四個字我在蘇州滄浪亭見過,用于館苑小筑尚能相宜,放在此處格局較隘。被考古界尊為山斗的董作賓亦曾留有行跡,曰:“因為看《淮安府志》的時候,偶然見到《藝文》里有《朱世臣題云臺山水簾洞》的標題,想到水簾洞是美猴王的發祥地,也算是這部《西游記》的出發點,不無研究價值。于是就加意探訪,果然尋到了水簾洞的出處。”我仰觀飛流,想到彥堂先生履跡曾至,差可把“道夫先路”四字追贈于他。我呢,繼以考史嗎?自知無可為力。
在玉皇閣上憑眺片刻,我向著玉女峰登去,路畔是紫紅的雞冠花和艷黃的金鑲玉竹。隨著山勢漸高,鳥音漸漸稀疏,云霧卻一縷縷飄得緊了。在這樣的地方悠悠地走,仿若放步于寬閑之野,我頗有“天游”的感覺,可說“不亦快哉”了。至額題“迎曙”的石亭時,放出目光,才看出一點花果山的雄峻。流煙、青靄、云光、隱約的遠峰逸勢俱足,千崖萬壑覆綠,樹茂葉潤,浮嵐間的云山只有在遙瞻中才顯盡它的美。所可惜者是霧氣過濃,遮去山邊碧色的大海。
此處為江淮崇巔,斷崖上深鐫榜書:“遙鎮洪流”。字是康熙帝揮寫的,放在這里,勢穩。臨危巖而歇坐,我很想喝一碗山中的云霧茶,且盼能夠遠趨趙明誠、李清照夫婦的芳躅,去郁林觀殘墟賞看峭崖上的唐隸宋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