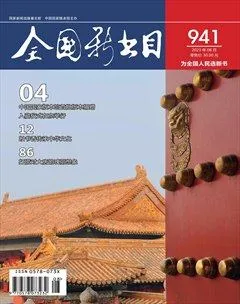詩文之辨
——酒飯妙喻
孫紹振
詩歌評論家。曾任中國文藝理論學(xué)會副會長,現(xiàn)為福建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dǎo)師。主要著作有《文學(xué)創(chuàng)作論》《文學(xué)的堅守與理論的突圍》等20 余部,散文集《愧對書齋》《靈魂的喜劇》等。2006年出版《孫紹振文集》8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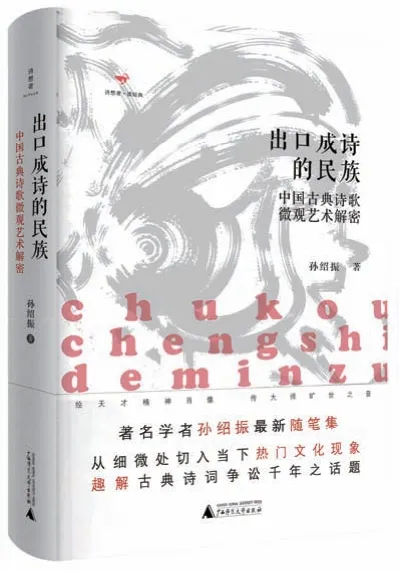
《出口成詩的民族:中國古典詩歌微觀藝術(shù)解密》孫紹振 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2.4/88.00元
詩與文的區(qū)別或者說分工,在中國文學(xué)理論史上相當受重視,在古典詩話詞話中也長期眾訴紛紜,但在西方文論史上卻不像這樣受到關(guān)注。在古希臘羅馬的修辭學(xué)經(jīng)典中,這個問題似乎很少論及,這跟他們沒有我們這樣的散文觀念有關(guān)。他們的散文在古希臘羅馬時期是演講和對話,后來則是隨筆,大體都是主智的,和我們今天心目中的審美抒情散文不盡相同。在英語國家的百科全書中,有詩的條目,卻沒有單獨的散文(prose)條目,只有和prose 有關(guān)的文體,例如:alliterative prose(押頭韻的散文)、prose poem(散文詩)、nonfictional prose(非小說類/非虛構(gòu)寫實散文)、heroic prose(史詩散文)、polyphonic prose(自由韻律散文)。在他們心目中,散文并不是一種特殊的文體,而是一種表達的手段,在許多文體中都可以使用。就像亞里士多德的《詩學(xué)》關(guān)注的不是詩與散文的關(guān)系,而是詩與哲學(xué)、歷史的關(guān)系:歷史是個別的事,而詩是普遍的、概括的,從這一點來說,詩和哲學(xué)更接近。他們的思路和我們的不同之處還在于方法上,他們是三分法,而我們是詩與散文的二分法。
在我們早期的觀念中詩言志、文載道,是把詩與散文對舉的。我們的二分法一直延續(xù)到清代,甚至當代。雖然形式上二分,但是在內(nèi)容上許多論者都強調(diào)其統(tǒng)一。司馬光在《趙朝議文稿序》中,把《詩大序》的“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稍稍改動了一下,變成“在心為志,發(fā)口為言。言之美者為文,文之美者為詩”。元好問則說:“詩與文,特言語之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詠情性之謂詩,其為言語則一也。”(《元好問詩話·輯錄》)以上都是把詩與文對舉,承認詩與文有區(qū)別,但強調(diào)詩與文的主要方面是統(tǒng)一的。司馬光說的是二者均美,只是程度不同;元好問說的是表現(xiàn)方法有異,一為記事,一為吟詠而已。宋濂則更加直率:“詩文本出于一原,詩則領(lǐng)在樂官,故必定之以五聲,若其辭則未始有異也。如《易》《書》之協(xié)韻者,非文之詩乎?《詩》之《周頌》,多無韻者,非詩之文乎?何嘗歧而二之!”(《宋濂詩話》)這種掩蓋矛盾的說法頗為牽強,擋不住詩與文的差異成為詩詞理論家們長期爭論不休的課題。不管怎么說,誰也不能否認二者的區(qū)別,至少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徐一夔詩話》說:“夫語言精者為文,詩之于文,又其精者也。”把二者的區(qū)別定位在“精”的程度上,立論亦甚為軟弱。
詩與散文的區(qū)別不是量的,而是質(zhì)的,這是明擺著的事實,可許多詩話和詞話家寧愿模棱兩可。當然,這也許和詩話、詞話的體制偏小,很難以理論形態(tài)正面展開有關(guān),結(jié)合具體作家和作品進行評判要方便得多。黃庭堅說:“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爾。”(轉(zhuǎn)引自宋陳師道《后山詩話》)在理論上從正面把詩文根本的差異提出來是需要時間和勇氣的。說得最為堅決的是明代的江盈科:“詩有詩體,文有文體,兩不相入。”“宋人無詩,非無詩也,蓋彼不以詩為詩,而以議論為詩,故為非詩。”“以文為詩,非詩也。”(《雪濤小書·詩評》)
承認區(qū)別是容易的,但闡明區(qū)別則是艱難的。對于詩與文的區(qū)別,人們一直爭論不休,甚至到二十一世紀,這仍然是一個嚴峻的課題。古人在這方面不乏某些天才般的直覺,然而,即使對起碼的直覺加以表達,也是要有一點才力的。明莊元臣值得稱道之處就是他把自己的直覺表述得很清晰:“詩主自適,文主喻人。詩言憂愁媮侈,以舒己拂郁之懷;文言是非得失,以覺人迷惑之志。”(《莊元臣詩話》)這實際上就是在說詩是抒情的(不過偏重于憂郁),文是“言是非得失”的,也就是說理的。這種用說理和抒情對詩、文進行區(qū)分的方式,至少在明代以前,應(yīng)該是有相當?shù)母鶕?jù),可惜把話說絕了,因而還不夠深刻,不夠嚴密。清鄒只謨在《與陸藎思》中則有所補正:“作詩之法,情勝于理;作文之法,理勝于情。乃詩未嘗不本理以緯夫情,文未嘗不因情以宣乎理,情理并至,此蓋詩與文所不能外也。”應(yīng)該說,“情理并至”至少在方法論上帶著哲學(xué)性的突破,不管是在詩中還是文中,情與理并不是絕對分裂的,而是互相依存,如經(jīng)緯之交織,詩情中往往有理,文理中也不乏情致,情理互滲,互為底蘊。只是在文中,理為主導(dǎo);在詩中,情為主導(dǎo)。這樣的說法比較全面,比較深刻。在情理的對立中,因主導(dǎo)性的不同而產(chǎn)生了不同的性質(zhì),這樣精致的哲學(xué)思辨方法竟然出自這個不太知名的鄒只謨的筆下,是有點令人驚異的。當然,他也有局限,畢竟僅僅是推理,還缺乏文本的實感。真正取得理論意義上的突破的,則是吳喬。他在《圍爐詩話》中這樣寫道:“問曰:‘詩文之界如何?’答曰:‘意豈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詩文體制有異耳。文之詞達,詩之詞婉。書以道政事,故宜詞達;詩以道性情,故宜詞婉。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文之措詞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啖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文為人事之實用,詔敕、書疏、案牘、記載、辨解,皆實用也。實用則安可措詞不達,如飯之實用以養(yǎng)生盡年,不可矯揉而為糟也。詩為人事之虛用,永言、播樂,皆虛用也。……詩若直陳,《凱風(fēng)》《小弁》大詬父母矣。’”
這可以說是真正深入到文體的核心了。鄒只謨探索詩與文的區(qū)別仍拘于內(nèi)涵(情與理),吳喬則把內(nèi)涵與形式結(jié)合起來進行考慮。雖然一開頭他認定詩文“意豈有二?”,但他并沒有把二者的內(nèi)涵完全混同,接下來馬上聲明文的內(nèi)涵是“道政事”,而詩歌的內(nèi)涵是“道性情”;形式上則是一個說理,一個抒情。他的可貴之處在于指出了由于內(nèi)涵的不同,導(dǎo)致了形式上的巨大差異:“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文之措詞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啖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把詩與文的關(guān)系比喻為米(原料)、飯和酒的關(guān)系。散文由于是說理的,如米煮成飯,不改變原生的材料(米)的形狀;而詩是抒情的,感情使原生材料(米)“變盡米形”成了酒。在《答萬季野詩問》中,他說得更為徹底,不但形態(tài)變了,性質(zhì)也變了(“酒形質(zhì)盡變”),這個說法對千年的詩文之辨是一大突破。
生活感受在感情的沖擊下發(fā)生種種變幻是相當普遍的規(guī)律,所謂情人眼里出西施,抒情的詩歌形象正是從這變異的規(guī)律出發(fā),進入了想象的假定的境界。例如“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誰謂荼苦,其甘如薺”“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xiāng)明”“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都是以感知強化的結(jié)果提示著情感上的強烈的原因。創(chuàng)作實踐是走在理論的前面的,而理論的落伍使得我國古典詩論往往拘泥于《詩大序》的“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的陳說,仿佛情感直接等于語言,有感情的語言就一定是詩,情感和語言、語言和詩之間沒有任何矛盾似的。其實,從情感到語言之間橫著一條相當復(fù)雜的迷途。語言符號并不直接指稱事物,而是喚醒有關(guān)事物的感知經(jīng)驗。而情感沖擊感知發(fā)生變異,語言符號的有限性以及詩歌傳統(tǒng)的遮蔽性都可能使得情志為現(xiàn)成的、權(quán)威的、流行的語言所遮蔽。心中所有往往筆下所無,言不稱意,筆不稱言,手中之竹背叛胸中之竹,是普遍規(guī)律。正是因為這樣,詩歌創(chuàng)作才需要才華。司空圖似乎意識到了“離形得似”的現(xiàn)象,但這只是天才的猜測,限于簡單論斷,未有必要的闡釋。
吳喬明確地把詩歌形象的變異作為一種普遍規(guī)律提上了鑒賞論和創(chuàng)作論的理論前沿,在中國詩歌史上可謂空前。它突破了中國古典文論中形與神對立統(tǒng)一的思路,提出了形與形、形與質(zhì)對立統(tǒng)一的范疇,觸動了詩歌形象的假定性。很可惜的是,這個觀點在他的《圍爐詩話》中沒有得到更系統(tǒng)的論證,但在當時已經(jīng)受到了重視,比如《四庫全書總目》,還有紀昀在《紀文達公評本蘇文忠公詩集》中、延君壽在《老生常談》中都曾加以發(fā)揮。當然,這些發(fā)揮今天看來還嫌不足,主要是大都抓住了變形變質(zhì)之說,卻忽略了在變形變質(zhì)的基礎(chǔ)上,還有詩文價值上的分化。吳喬強調(diào)讀文如吃飯,可以果腹,因為“文為人事之實用”,也就是“實用”價值;而讀詩如飲酒,可醉人而不能解決饑寒之困,旨在享受精神的解放,因為“詩為人事之虛用”。吳喬的理論意義不僅在變形變質(zhì),還在功利價值上的“實用”和“虛用”。這在中國文藝理論史上應(yīng)該是超前的,他意識到詩的審美價值是不實用的,還為之命名曰“虛用”,這和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所言審美的“非實用”異曲同工。當然,吳喬沒有康德那樣的思辨能力,也沒有建構(gòu)宏大體系的演繹能力,他的見解只是吉光片羽。這不僅僅是吳喬的局限,也是詩話詞話體裁的局限,但這并不妨礙他的理論具有超前的性質(zhì)。
吳喬之所以能揭示出詩與文之間的重大矛盾,一方面在于他的才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他心目中的散文,主要是他所說的“詔敕、書疏、案牘、記載、辨解”等,其實用性質(zhì)是很明顯的。按照姚鼐《古文辭類纂》中的界定,散文是相對于詞賦類的,形式很豐富:論辯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志類、雜記類、箴銘類,基本上是實用類的文體。在這樣的背景下觀察詩詞并進行邏輯劃分有顯而易見的方便之處,審美與實用方面的差異也可以說是昭然若揭。這一點和西方有些相似,西方也沒有我們今天這種抒情審美散文的獨立文體,他們的散文大體是以議論為主、展示智慧的隨筆(essay)。從這個意義上說,吳喬的發(fā)現(xiàn)仍屬難能可貴,畢竟西方直到差不多一個世紀以后才有雪萊的總結(jié):“詩使它觸及的一切變形”。在這方面,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理論家赫士列特說得相當勇敢,他在《泛論詩歌》中說:“想象是這樣一種機能,它不按事物的本相表現(xiàn)事物,而是按照其他的思想情緒把事物揉成無窮的不同形態(tài)和力量的綜合來表現(xiàn)它們。這種語言不因為與事實有出入而不忠于自然;如果它能傳達出事物在激情的影響下在心靈中產(chǎn)生的印象,則是更為忠實和自然的語言了。比如,在激動或恐怖的心境中,感官察覺到了事物——想象就會歪曲或夸大這些事物,使之成為最能助長恐怖的形狀,‘我們的眼睛’被其他的官能‘所愚弄’。這是想象的普遍規(guī)律……”其實這個觀念并非赫氏的原創(chuàng),很明顯,感官想象歪曲事物來自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第五幕第一場中希波呂忒與忒修斯的臺詞:“忒修斯,這些戀人們所說的事真是稀奇。”“情人們和瘋子們都有發(fā)熱的頭腦和有聲有色的幻想,瘋子、情人和詩人,都是幻想的產(chǎn)兒……詩人的眼睛在神奇狂放的一轉(zhuǎn)中,便能從天上看到地下,從地下看到天上。想象會把虛無的東西用一種形式呈現(xiàn)出來,詩人的妙筆再使它們具有如實的形象,虛無縹緲也會有了住處和名字。強烈的想象往往具有這種本領(lǐng),只要一領(lǐng)略到一些快樂,就會相信那種快樂的背后有一個賜予的人;夜間一轉(zhuǎn)到恐懼的念頭,一株灌木一下子便會變成一頭狗熊。”西歐浪漫主義詩歌衰亡之后,馬拉美又提出了“詩是舞蹈,散文是散步”的說法,與吳喬的詩酒文飯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可惜的是,吳喬的天才的直覺在后來的詩詞賞析中沒能得到充分的運用。如果把他的理論貫徹到底,認真地以作品來檢驗的話,對權(quán)威的經(jīng)典詩論可能會有所顛覆。詩人就算如《詩大序》所說的那樣心里有了志,口中就有了相應(yīng)的言,然而口中之言是不足的,因而還不是詩,即使長言之,也還不是轉(zhuǎn)化的充分條件。至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對于作詩來說,不管如何手舞足蹈都是白費勁,如果不加變形變質(zhì),寫出的作品肯定不是詩。從語言到詩歌并不簡單,也不像西方當代文論中所說的那樣,僅僅是一種語言的“書寫”。這種說法不如二十世紀早期俄國形式主義者說的“陌生化”到位,當然俄國形式主義者并未意識到詩的變形變質(zhì)不但是感知的變異,而且也屬于語義的變異(與日常、學(xué)理語言、散文語言拉開語義的“錯位”距離)。語義不但受到語境的制約,還能從詩歌形式規(guī)范的預(yù)期中獲得自由,因而它不但是詩歌風(fēng)格的創(chuàng)造,也是人格從實用向?qū)徝栏叨鹊纳A。正是在這升華過程中的突破,更主要的是突破原生狀態(tài)的實用性的人,讓人格和詩格同步向?qū)徝谰辰缟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