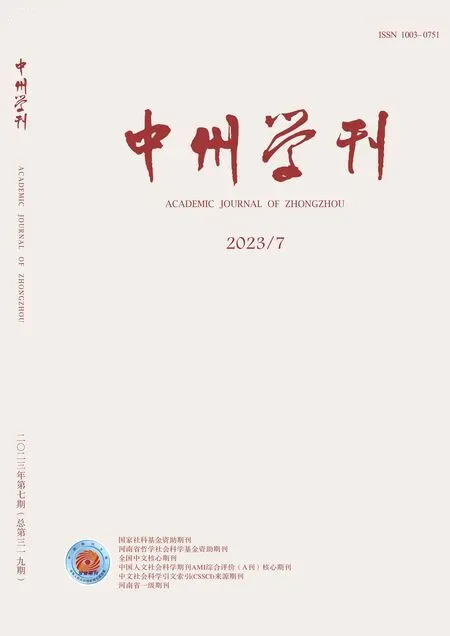自我的“解離”:殘雪文學(xué)創(chuàng)作精神密碼新解
姚曉雷 陳 瑩
20世紀(jì)80年代,殘雪作為“先鋒派”的代表性作家載入文學(xué)史。但是,不同于“先鋒派”以形式為審美對(duì)象,殘雪關(guān)注的是精神本身的過(guò)程性。在先鋒作家轉(zhuǎn)型的新世紀(jì),她堅(jiān)持文學(xué)實(shí)驗(yàn),將自己的創(chuàng)作命名為“新實(shí)驗(yàn)”文學(xué)。她的實(shí)驗(yàn)是一種靈魂內(nèi)部的實(shí)驗(yàn),她拿自己做實(shí)驗(yàn),讓生命力爆發(fā),將提升人性、拯救自身當(dāng)作最高的目標(biāo),其難度在于主動(dòng)發(fā)起“靈魂分裂”,作家必須在世俗世界“心死”,長(zhǎng)年累月囚禁自己,確保精神不會(huì)迸散才能創(chuàng)作[1]128。殘雪坦言:“自從我開(kāi)始正式表演之后,我對(duì)生活的愛(ài)愈發(fā)加深了。我的日常生活獲得了完美的節(jié)奏,我的身心充滿了活力。”[2]4“新實(shí)驗(yàn)”文學(xué)已經(jīng)成為殘雪超越日常的靈魂生活方式。
20世紀(jì)80年代至今的殘雪研究一直繞不開(kāi)其作品中那些令人費(fèi)解的精神現(xiàn)象,早期的研究將其概括為“夢(mèng)囈”“夢(mèng)魘敘事”“靈魂分裂”等,如程德培《折磨著殘雪的夢(mèng)》、王緋《在夢(mèng)的妊娠中痛苦痙攣——?dú)堁┬≌f(shuō)啟悟》、吳亮《一個(gè)臆想世界的誕生——評(píng)殘雪的小說(shuō)》等。這些說(shuō)法不斷地被沿用、重復(fù),導(dǎo)致殘雪作品中某些模糊、復(fù)雜的感受,至今沒(méi)有被厘清,“殘雪之謎”長(zhǎng)期存在。理論方法的濫用也導(dǎo)致一些結(jié)論下得比較模糊、粗暴,如“迷宮內(nèi)涵”“反懂”“巫性寫(xiě)作”等,并被廣為因襲。多數(shù)的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敘事學(xué)和語(yǔ)言學(xué)方面,關(guān)注文本的實(shí)驗(yàn)性特征、敘事體驗(yàn)、語(yǔ)言特色和意象分析等,忽略了殘雪文本中最關(guān)鍵的心理活動(dòng)性。事實(shí)上,殘雪作品中存在著明顯的“解離”現(xiàn)象,主人公常常有一種恍惚、漂泊的心靈感受,他們看似平靜,實(shí)則承受著復(fù)雜的內(nèi)心沖突。心理學(xué)上的“解離”是一種自我防御機(jī)制,其基本特征為意識(shí)、記憶、對(duì)環(huán)境的識(shí)別和感知的整合功能瓦解,主觀上感到麻木、不真實(shí)和抽離。殘雪描述她的“自動(dòng)寫(xiě)作”是這樣一個(gè)過(guò)程:腦中一片空白,以巫性的神秘力量,發(fā)起“靈魂內(nèi)部努斯和邏各斯的糾纏扭斗”。這個(gè)看似神秘的過(guò)程就是借助“解離”有保護(hù)地接近潛意識(shí),并釋放內(nèi)心沖突的過(guò)程。筆者認(rèn)為,借用現(xiàn)代心理學(xué)上的“解離”概念,能夠較好地解釋殘雪“自動(dòng)寫(xiě)作”的生成機(jī)制,拂去長(zhǎng)久以來(lái)籠罩在殘雪作品上的巫性迷霧,對(duì)“高難度的實(shí)驗(yàn)文學(xué)之謎”進(jìn)行一場(chǎng)祛魅式的還原。
一、靈魂深淵中的“解離”者
在既往研究中,“靈魂分裂”這一說(shuō)法已經(jīng)被大多數(shù)研究者認(rèn)同,但它始終不能較好地解釋殘雪創(chuàng)作中的某些現(xiàn)象。迄今為止,“迷宮內(nèi)涵”“殘雪之謎”的說(shuō)法仍在不斷沿用。本文之所以以“解離”作為研究的切入點(diǎn),是因?yàn)橄啾扔诩韧芯窟_(dá)成共識(shí)的“靈魂分裂”,“解離”涵蓋的現(xiàn)象更為豐富,既囊括了“分裂”所指的意涵,又能更合理地解釋殘雪創(chuàng)作中無(wú)法解釋的現(xiàn)象。在心理學(xué)中,“人格分裂”被列入“解離障礙”譜系,又被稱為“解離性身份識(shí)別障礙”。“人格分裂”者在自我內(nèi)部建立虛假的關(guān)系,分裂出不同的自體和客體狀態(tài),形成相互矛盾、沖突不斷的不完整體。“解離”涵蓋了比“人格分裂”更廣譜的內(nèi)容。因此,在創(chuàng)傷的視野上,“解離”被更多地使用。
殘雪對(duì)寫(xiě)作方法的巫性描述,以及“自動(dòng)寫(xiě)作”的巫性語(yǔ)言,實(shí)質(zhì)上都是“解離”狀態(tài)下的思維特征。巫文化的“出神”“附體”等“非我”的神秘境界,在本質(zhì)上都屬于“解離”現(xiàn)象。此外,殘雪筆下的主人公,經(jīng)常出現(xiàn)出神、游離、恍惚、失憶等“解離”性體驗(yàn),從文本內(nèi)部反映出作家“解離”的心理體驗(yàn)。
1.“解離”:一種心理防御機(jī)制
“解離”既是一種心理防御機(jī)制,也是一種韌性的心智品質(zhì)。心理學(xué)意義上的“解離”涵蓋一種或多種正常、主觀的完整心理生物功能的瓦解及中斷,包括記憶、身份、意識(shí)、知覺(jué)和運(yùn)動(dòng)控制等[3],一般是不請(qǐng)自來(lái)、令人不悅地侵?jǐn)_到覺(jué)知及行為,伴隨主觀經(jīng)驗(yàn)連續(xù)性的中斷、健忘、自我感喪失等。“解離”者通常早年遭遇創(chuàng)傷,并習(xí)得了強(qiáng)大的自我催眠天賦。他們可以自我誘導(dǎo)進(jìn)入恍惚狀態(tài),讓催眠和現(xiàn)實(shí)交替進(jìn)行。通過(guò)這種方式平息痛苦,重新掌控情感。“當(dāng)人因創(chuàng)傷或童年的受虐經(jīng)驗(yàn)而引發(fā)太強(qiáng)烈的恐懼與焦慮,調(diào)適的方法可能就是對(duì)周遭世界失去熟悉的知覺(jué),遁入無(wú)實(shí)感的內(nèi)心世界里”,“對(duì)世界的感知或體驗(yàn)發(fā)生改變以至于感覺(jué)世界變得不真實(shí)”[4]。
“解離”者通常心靈敏感、想象力豐富,擅于營(yíng)造虛構(gòu)的世界。正如殘雪在《有邏輯的夢(mèng)》中所說(shuō):“灰色而壓抑的童年和青少年是老天給予我的饋贈(zèng),外界的現(xiàn)實(shí)越絕望,深淵里的王國(guó)越燦爛輝煌。只不過(guò),那個(gè)王國(guó)我當(dāng)時(shí)沒(méi)法目睹,要等待好多年以后,它才會(huì)輪廓初現(xiàn)。”[5]108“我在敵人快要臨近之際用力閉上眼,于一瞬間變出一間地下室,將自己關(guān)在里頭。睜大的眼睛在多數(shù)時(shí)候是迷惘而緊張的,看不完的風(fēng)景探不完的險(xiǎn),只有在絕境赫然出現(xiàn)之際,眼睛才會(huì)緊緊閉上,同虛構(gòu)的身體一道策劃致命的場(chǎng)景轉(zhuǎn)換。”[2]62“解離”固然可以令心靈在創(chuàng)傷的壓迫中得到緩沖,卻不免導(dǎo)致自我內(nèi)部的沖突。一旦類(lèi)似的創(chuàng)傷事件再次出現(xiàn),個(gè)體就不得不尋求進(jìn)一步“解離”來(lái)應(yīng)對(duì),從而越來(lái)越輕易地喚起“解離”。
2.殘雪“解離”之門(mén)的開(kāi)啟
“解離”的誘因,既有瞬間的壓力,也有久遠(yuǎn)的慢性創(chuàng)傷。我們可以從殘雪的成長(zhǎng)經(jīng)歷,清晰地看出“解離”形成的軌跡。殘雪在特殊時(shí)代長(zhǎng)大,幼年家庭遭遇變故。1957年,她的父母被下放勞教,房子被沒(méi)收,全家搬到岳麓山下兩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里,經(jīng)常挨餓。殘雪在外遭受歧視,在學(xué)校被孤立,她的周?chē)涑庵悩拥难酃?她“最大的恐懼和尷尬就是同人接觸”。她自言:“在學(xué)校,在大院里,我都是越來(lái)越孤立了。他們?cè)谀抢锿?但他們并不叫我,因?yàn)橛X(jué)得我怪,我也不好意思過(guò)去。我成了寂寞的游魂。寂寞啊,寂寞啊。整整十多年我的大部分時(shí)間就在這樣的氛圍里度過(guò)。”[5]42她除了偶然同兩三個(gè)女孩有來(lái)往,大部分時(shí)間都待在家里,最大的樂(lè)趣就是一個(gè)人“表演”:“我從三歲的時(shí)候起就熱衷于表演。但是在我小的時(shí)候,那種表演是很特別的——我在腦海里進(jìn)行表演。因此沒(méi)有任何人知道我所上演的戲劇。”“當(dāng)我大起來(lái)時(shí),那些表演就持續(xù)得更久,情節(jié)更復(fù)雜了。”[2]2她可以在理性控制下發(fā)起和結(jié)束“表演”,甚至可以在清醒的狀態(tài)下發(fā)起它。她設(shè)想自己走進(jìn)一個(gè)又黑又深的隧道,走了又走,直到掉進(jìn)某個(gè)深淵,然后再一次走進(jìn)去,走了又走……有時(shí)她滯留在某一個(gè)層面,眼看就要滑下去了,但總有什么發(fā)亮的東西將她喚回來(lái)。她迷上了這樣的世界。她還常有奇異的夢(mèng)——總是夢(mèng)到位于走廊盡頭的三間空房子,房子里的人影影綽綽,如鬼魅一般充滿不祥之兆[2]48。
13歲時(shí),殘雪因遭遇歧視而輟學(xué)。此時(shí),外婆已經(jīng)去世,父母和哥哥、姐姐都不在身邊,殘雪一個(gè)人在黑暗的工具房里讀書(shū)自學(xué),幽閉讓她的內(nèi)心更加敏感。她可以沉浸在文學(xué)中許多天:“一連好多天,我心神恍惚,不斷回想著《孤魂鬼影》里頭的情節(jié)。我已經(jīng)知道了結(jié)局,結(jié)局很沒(méi)意思。可是那些情節(jié),實(shí)在給我太強(qiáng)烈的印象……當(dāng)我沉浸在恐怖情節(jié)中時(shí),我身上的瘋狂就被激發(fā)出來(lái)了……”[2]53在小黑屋的好幾個(gè)月里,她就著不太亮的燈光讀完了好多部文學(xué)書(shū),并萌生了進(jìn)行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想法。可以說(shuō),她的藝術(shù)靈感的萌芽與“解離”有關(guān)。
殘雪曾在《我是怎么搞起創(chuàng)作來(lái)的》中寫(xiě)道:“一個(gè)人,生性懦弱乖張,不討人喜歡,時(shí)時(shí)處在被他人侵犯的恐懼中,而信念偏偏又一貫用著一種別人看來(lái)是奇詭的、刻薄的眼光看這世界,暗藏著比一般人遠(yuǎn)為囂張的要顯示自身的野心。”[6]因?yàn)楠?dú)處,她習(xí)慣于站在一個(gè)有距離的地方看世界。那些被壓抑的個(gè)性,成為變形的意念深埋在心底。她只要讓自己“腦海空空”,就會(huì)感到一股陌生的情緒從內(nèi)部噴涌而出。她將這股力量稱為“冥想”。她說(shuō):“冥想賦予了我整體把握事物的能力。邏輯性并沒(méi)有喪失,反而在‘去偽存真’的觀察中成為了更高級(jí)的東西。是的,我終于能夠輕易地‘發(fā)現(xiàn)’本質(zhì)了——那種深層的邏輯,遠(yuǎn)遠(yuǎn)高于表面的邏輯,因?yàn)樗橇Ⅲw的,向著未來(lái)無(wú)限延伸的。”[2]79她時(shí)常感到“當(dāng)我放松警惕時(shí)候,那種地方就會(huì)有繩套拋出,套在我的脖子上”,“我感到滅頂之災(zāi)正在臨近,可又并沒(méi)有什么滅頂之災(zāi)”[7]。當(dāng)外界的危機(jī)降臨時(shí),她總能沉入混沌黑暗的內(nèi)心深處,靠著那黑暗中的一點(diǎn)點(diǎn)光亮,一直行走下去。
殘雪長(zhǎng)期一個(gè)人獨(dú)處,在人際關(guān)系的各個(gè)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缺失。由于無(wú)法真正脫離現(xiàn)實(shí),只能依靠“解離”來(lái)遁出現(xiàn)實(shí),她與外界的隔閡越來(lái)越復(fù)雜、強(qiáng)烈、持久。她用“解離”來(lái)防御外界,卻不免落入自我的深淵。一旦面對(duì)外界,她就充滿抗拒;想要突圍自我,卻被自我所吞噬;維持“解離”,反而招致更多的誤解。殘雪曾表示,自己永遠(yuǎn)不愿與現(xiàn)實(shí)和解,永遠(yuǎn)處在緊張、對(duì)抗的關(guān)系里,總是用一種異樣的眼光審視周遭的人與事,不想也不愿與之同流合污。“我的作品為何會(huì)成為今天的這個(gè)樣子,大概與我個(gè)人的性格有關(guān)。我從小就對(duì)世界處于敵對(duì)狀態(tài)。大人說(shuō)‘東’我偏要說(shuō)‘西’,我無(wú)論如何也不理解周?chē)娜藶槭裁磿?huì)那樣,更不會(huì)贊同他們的所有做法。于是,我只能采取自我封閉的方法,一直至今。”[5]160在殘雪的筆下,環(huán)境總是危機(jī)四伏,人與人的關(guān)系也總是劍拔弩張,這種不和諧的緊張感最初就源自成長(zhǎng)時(shí)期對(duì)外部世界的難以融入。
二、作為藝術(shù)方法的“解離”
人與他人的關(guān)系若是長(zhǎng)期失調(diào),就會(huì)產(chǎn)生基本壓抑和基本焦慮,產(chǎn)生虛假的人際關(guān)系,人就會(huì)意識(shí)到個(gè)體的孤獨(dú)和危險(xiǎn)。一個(gè)人越是孤僻,內(nèi)心世界就會(huì)越發(fā)敏感,越容易產(chǎn)生負(fù)面情緒,走向極端或虛無(wú)。殘雪用“解離”排解了孤僻的負(fù)面效應(yīng),并啟發(fā)了藝術(shù)靈感。眾所周知,殘雪小說(shuō)充滿反常的囈語(yǔ)和神秘的“自動(dòng)寫(xiě)作”體驗(yàn),獨(dú)特的思維在她成長(zhǎng)時(shí)期就已經(jīng)形成。
1.“解離”狀態(tài)下的寫(xiě)作
殘雪作品中那些有頭無(wú)尾的對(duì)話、突然中斷的時(shí)間和場(chǎng)景、不了了之的事件,向來(lái)被稱為“夢(mèng)魘敘事”,甚至有評(píng)論稱為“瘋子式的幻像思維及藝術(shù)語(yǔ)言”“似是而非暖昧不明的精神病”[8]。殘雪則將這些現(xiàn)象稱之為“自動(dòng)寫(xiě)作”:“我在實(shí)際創(chuàng)作時(shí),頭腦里一片空白,幾乎在無(wú)意識(shí)的狀態(tài)中,將涌現(xiàn)出來(lái)的語(yǔ)言不加改變地進(jìn)行排列。所以為讀者而寫(xiě)的問(wèn)題一點(diǎn)也沒(méi)有考慮。”[1]48“我完全不拘泥于一個(gè)個(gè)的詞匯……總之,使頭腦一片空白,隨筆寫(xiě)下去,才能感到無(wú)限的自由和痛快。”[1]104“寫(xiě)出上一句,還不知下一句在哪兒。完全沒(méi)有構(gòu)思,也沒(méi)有提綱。”[9]58她在頭腦空白狀態(tài)下,“讓潛伏在最底層的無(wú)意識(shí)直接展露”[9]49。她憑借巫性的神秘力量,發(fā)動(dòng)靈魂內(nèi)部努斯和邏各斯的糾纏扭斗,將潛意識(shí)內(nèi)容一氣呵成地列于紙上,在回歸理性狀態(tài)后,才逐漸發(fā)現(xiàn)其內(nèi)涵。她自言:“我寫(xiě)完的時(shí)候也不明白自己寫(xiě)的是什么。過(guò)了一段時(shí)間,有時(shí)過(guò)了半年后,才明白的。”[9]64這類(lèi)似柏拉圖所描述的神靈附體式的“說(shuō)話”。復(fù)雜的潛意識(shí)內(nèi)容集中涌現(xiàn),使她以為得到了巫性的神秘力量。事實(shí)上,她并不像自己說(shuō)的那樣“沒(méi)有明確的意圖”,而是有理智、故意的成分在。與其說(shuō)這是一種新的文學(xué)實(shí)驗(yàn),不如說(shuō)這是她的一種自我療愈。
殘雪通過(guò)“解離”開(kāi)啟“自動(dòng)寫(xiě)作”,將痛苦化成鏡中之像,用碎片化的講述瓦解創(chuàng)傷,在釋放內(nèi)心沖突的同時(shí)保護(hù)內(nèi)心。“通過(guò)迂回、間接和轉(zhuǎn)指或碎片化和變形來(lái)指稱不可言說(shuō)之物,動(dòng)用一系列修辭手法將隱藏與顯示融合起來(lái)。通過(guò)幻影效果來(lái)承擔(dān)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創(chuàng)傷經(jīng)驗(yàn),進(jìn)行創(chuàng)傷置換,從自身抽離并消耗了創(chuàng)傷,緩解無(wú)意識(shí)的壓力。”[10]人們讀殘雪的作品,普遍有一種陰郁、壓抑、受折磨之感,這是殘雪“內(nèi)在真實(shí)”的投射。“自動(dòng)寫(xiě)作”其實(shí)是在她還無(wú)力看清內(nèi)心時(shí),先原本地呈現(xiàn)它,在表現(xiàn)的過(guò)程中獲得對(duì)被表現(xiàn)物的認(rèn)識(shí)。從殘雪目前對(duì)巫性的自我理解中,可以判斷她的自我覺(jué)察較為混沌——“我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種說(shuō)不清道不明的、有點(diǎn)奇怪的時(shí)間與空間里頭,讓筆先行,讓自己所不知道的主題自行展開(kāi),讓自己控制不了的結(jié)構(gòu)自動(dòng)形成,讓每一個(gè)詞攜帶另一個(gè)世界的神秘氣味”,“將自己的理性思維融入這個(gè)感覺(jué),以此來(lái)發(fā)動(dòng)屬于自我的這個(gè)語(yǔ)言機(jī)制,從而達(dá)到自身語(yǔ)言體系的創(chuàng)造性生長(zhǎng)”[11]。她認(rèn)為自己能夠以感應(yīng)的方式,創(chuàng)造出獨(dú)特的語(yǔ)言,這種語(yǔ)言具有“人神溝通”的原始巫術(shù)特性。“神靈附體”“代神說(shuō)話”般的神秘體驗(yàn),正是對(duì)“解離”現(xiàn)象的巫性附會(huì)。殘雪對(duì)巫性的自我理解,無(wú)疑是她的一種自戀想象。
2.巫性的自戀解說(shuō)
巫術(shù)作為一種虛假的想象手段,具有使用心念力量控制環(huán)境、改造世界的特點(diǎn),這與殘雪過(guò)大的自我意識(shí)不謀而合。“巫術(shù)是由于原始人類(lèi)聯(lián)想的誤用,而幻想有一種不變的或同一的事物,依附于各種有潛勢(shì)力的物品和動(dòng)作,通過(guò)某種儀式冀能達(dá)到施術(shù)者目的的一種偽科學(xué)的行為或技藝。”[12]殘雪從小深受巫楚文化浸染,外婆驅(qū)鬼的身影作為長(zhǎng)時(shí)情境記憶進(jìn)入了潛意識(shí),她自然地將“解離”歸結(jié)為巫的神秘力量。對(duì)“解離”的巫性理解使她更深地陷入自我,她用自我來(lái)詮釋自我,以自我來(lái)佐證自我,看似在進(jìn)行“靈魂探險(xiǎn)”,其實(shí)已進(jìn)入一個(gè)思維閉環(huán)。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shuō),殘雪的自我有多大,她的文學(xué)世界就有多大。它是一個(gè)自給自足的圓圈,一個(gè)畫(huà)地為牢的孤島。她指出:“我所認(rèn)同的開(kāi)端是卡爾維諾多次描述過(guò)的那種開(kāi)端,即自給自足,用自己內(nèi)部的矛盾作為自身發(fā)展的動(dòng)力、營(yíng)養(yǎng),從歷史的沉渣里掙扎出來(lái),打出一片新天地。這種開(kāi)端,只有那些穩(wěn)穩(wěn)地站立在大地之上,內(nèi)部形成了精神生長(zhǎng)機(jī)制的個(gè)人才能達(dá)到。”[13]殘雪的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來(lái)自自我身心內(nèi)部“致命的危機(jī)”,正如她自己所說(shuō)的那樣:“純文學(xué)作者一生中大部分時(shí)間都處于致命危機(jī)中,創(chuàng)作可以說(shuō)是為了擺脫危機(jī)而有意制造危機(jī)。”[14]136“人為什么要進(jìn)行這樣一種古怪的緊張游戲呢?為了榨取生命,為了使精神長(zhǎng)存。”[14]138“通過(guò)寫(xiě)作,我創(chuàng)造了另外一種生活,也拯救了自己那墮落的靈魂。”“我的身體屬于寫(xiě)作,而我的寫(xiě)作,是我活的方式。至少目前,我一刻也不能停止。”[15]寫(xiě)作已經(jīng)成為殘雪生命的一部分,讓她在自戀中達(dá)到了片面的深刻和深刻的片面。對(duì)于她來(lái)說(shuō),只有自己的思想和感覺(jué)才是重要的。她精神上的被動(dòng)是顯而易見(jiàn)的,只有不停地依賴“解離”,精神才有安全感。由于她陶醉在自我內(nèi)部的閉環(huán)中無(wú)力自拔,其心理符碼又無(wú)法轉(zhuǎn)譯成現(xiàn)實(shí),因此其“靈魂探險(xiǎn)”的實(shí)際意義已經(jīng)被自我消解——最大的自我危機(jī)來(lái)自自我本身。
盡管殘雪用“巫言巫語(yǔ)”解說(shuō)自己,但實(shí)際上,其小說(shuō)的全部特點(diǎn)都源于那單一、極端、覆蓋全局的自我意識(shí)。她是飼養(yǎng)毒蛇的小孩,是“貼著墻根飛竄逃走的老鼠”,在自我的深淵中掙扎。她反復(fù)地囈語(yǔ),正如一個(gè)被嚇壞的孩子,非要把內(nèi)心的恐怖講給旁人聽(tīng)。細(xì)究下來(lái),殘雪的“靈魂探險(xiǎn)”背后,分明是一種被密不透風(fēng)的環(huán)境惡意擠壓出來(lái)的過(guò)剩、變形的自我意識(shí)。
三、作品人物的“解離”
殘雪作品中人物的某些令人費(fèi)解的特質(zhì),也并非無(wú)跡可尋,而是源于“解離”。他們通常是家庭、小社會(huì)中的困獸,在封閉的小環(huán)境中人格受到抑制。在變態(tài)的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中,“靈魂的出走”由個(gè)體上演到家庭,最終整個(gè)環(huán)境表現(xiàn)出形形色色的“解離”征候。
1.“解離”者的群像
像許多女作家一樣,殘雪的關(guān)注點(diǎn)常在小的人情社會(huì)范疇。她擅長(zhǎng)在微小的社會(huì)單位中,揭示最為險(xiǎn)惡的人際真相。她最?lèi)?ài)表現(xiàn)的,是人在家庭或小社會(huì)中封閉自己、人格衰竭、精神毀滅的悲劇。如《蒼老的浮云》中虛汝華在施虐狂母親和控制狂婆婆的打壓下,精神虛弱,神思恍惚。她的丈夫老況則被控制狂婆婆養(yǎng)成了一個(gè)“巨嬰”,人格孱弱,無(wú)力處理生活問(wèn)題。鄰居慕蘭是充滿敵意的窺視狂,通過(guò)隱性攻擊獲得滿足。虛汝華遭受四面八方的人際攻擊,不得不把臥室四面釘上鐵條,變得虛妄恍惚。她對(duì)老況說(shuō):“時(shí)常你在院子里講話,我就以為是婆婆來(lái)了。我的耳朵恐怕要出毛病了。比如今天,我就一點(diǎn)沒(méi)想到你在屋里,我以為婆婆一個(gè)人在那邊提高了聲音自言自語(yǔ)呢。”[16]6從慕蘭的視角看,虛汝華則是這個(gè)樣子:“那女的特別陰險(xiǎn),每次她從我們窗前走過(guò),總是一副恍恍惚惚的樣子,連腳步聲也沒(méi)有!怎么能沒(méi)有腳步聲呢?既是一個(gè)人,就該有一定的重量,不然算是怎么回事?”[16]18靈魂沒(méi)有重量,虛汝華終日恍惚地活著,遭受越來(lái)越多的誤解和非議,直至精神衰竭。篇名《蒼老的浮云》便是虛汝華生存樣態(tài)的具象化。
《霧》中的“解離”者是位母親。一場(chǎng)大霧后,全家人忽然都變成了影子,唯有母親出走了。母親只記得自己追著兩只四處下野蛋的白母雞迷失在林子里。“在崖洞邊上,我找到一個(gè)蛋,你看。我追著那些一閃一閃的白影子,累的胸膛都破碎了。”“早上一醒來(lái),我就發(fā)現(xiàn)那個(gè)蛋不見(jiàn)了,就是我拿給你看的那個(gè)。那是真的,是不是?”[16]196母親不斷找蛋,卻無(wú)法確認(rèn)蛋是真實(shí)存在的。她是一個(gè)迷失在自我內(nèi)部靜態(tài)而封閉的空間的人,意識(shí)停滯不前,一生都在茫然地“找一個(gè)蛋”。父親則是“一件外套”,外套里什么都沒(méi)有。“你的父親,是一件外套。那個(gè)時(shí)候,他穿著外套來(lái)到我們家,就是睡覺(jué)也不脫下。一天夜里,我鼓足勇氣在那件外套上一摸,發(fā)現(xiàn)里面什么也沒(méi)有。直到多年之后我才弄清事情的真相。”[16]198父親是一個(gè)只有外殼的空心人,一個(gè)存在卻“不在場(chǎng)”的人。一場(chǎng)大霧還原了真相。母親的離場(chǎng)和父親的不在場(chǎng),意味著“解離”者之間互相演化,把問(wèn)題帶到家庭中。父母不是靈魂出走,就是人格不全,家庭紐帶名存實(shí)亡。
在殘雪的作品中,從個(gè)人、家庭到環(huán)境,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解離”現(xiàn)象。《袁氏大娘》中袁氏大娘和她的兄弟姐妹們長(zhǎng)出吸盤(pán)和腳蹼,可以在夾墻、地道、陰溝、井底里來(lái)回穿梭。人們因其怪異而排斥他們。“我”則發(fā)現(xiàn)那些夾墻、地道在本質(zhì)上是這類(lèi)人躲避世俗、進(jìn)入夢(mèng)境的通道。他們?cè)趬?mèng)里將身體任意伸縮變形,穿行于各類(lèi)犄角旮旯,沒(méi)有任何空間能夠困住他們。“它們?cè)诎档乩锓趸?繁殖著,越來(lái)越多,占的空間越來(lái)越大,于是就破土而出,混跡于人群之中,使得很多人都對(duì)它們司空見(jiàn)慣了。”[17]最后“解離”擴(kuò)散為群體性現(xiàn)象。這也隱喻著“解離”現(xiàn)象是多么隱蔽、常見(jiàn),令人習(xí)焉不察。
2.“解離”者的覺(jué)醒
“解離”者異乎尋常地沉溺于另一個(gè)世界,卻會(huì)在長(zhǎng)久的平靜中爆發(fā)不可理喻的激情。如《表姐》里的表姐本是一個(gè)深居簡(jiǎn)出,沉溺幻想,不關(guān)心外界的淑女。某一年春節(jié)表姐去海邊的漁村過(guò)年,在火車(chē)上突然露出神經(jīng)質(zhì)的兇狠面目。到達(dá)漁村后,表姐開(kāi)始和粗鄙的廚師、門(mén)房等聚眾淫亂,甚至引誘表弟和父母加入。表姐壓抑已久的神經(jīng)質(zhì)行為似乎可以從她出生時(shí)的啼哭中找到端倪——她落地之際兇猛的哭聲甚至壓倒了窗外的雷鳴。表姐一旦回歸自我,便爆發(fā)出令人始料不及的瘋狂。《污水上的肥皂泡》中的“我”在長(zhǎng)久忍受折磨后“殺死”了母親。她有臥室不睡,卻故意睡在冰冷的廚房里,并大罵“我”虐待老母。“她時(shí)不時(shí)對(duì)我抱怨屋里冷得像個(gè)冰窖,一抱怨,就流鼻涕、流口水、罵我‘忤逆子’,居然如此虐待老母,最后總以嚎啕大哭來(lái)收?qǐng)觥!薄拔摇敝灰?tīng)到母親的聲音,“太陽(yáng)穴就一炸一炸地痛”[18]5。母親弄得我神經(jīng)崩潰,我忍無(wú)可忍,最終采取了瘋狂行動(dòng),將母親“化”在了肥皂水里。“我凝視著木盆里的水,那是一盆發(fā)黑的臟的肥皂水,水上浮著一串亮晶晶的泡泡,還散發(fā)出一股爛木頭的氣味。”[18]9母親在“我”的設(shè)計(jì)下化作一盆烏黑的、骯臟的肥皂水,這隱喻著母親是“我”心中難以磨滅的陰影。
殘雪筆下也有一部分“解離”者主動(dòng)作繭自縛,不想也不愿走出。如《阿娥》里的阿娥被長(zhǎng)年封閉在玻璃罐里。雖然她曾成功逃去舅舅家,卻自行捆住手腳鉆入床下,對(duì)解救她的阿林又踢又咬,蠻不講理地毆打阿林:“你這蠢貨,柜子里才有意思呢。我只要一出來(lái)就難受,你沒(méi)看到嗎?陽(yáng)光使我的血變黑,花粉使我的氣管粘膜腫脹,最糟糕的是,我在外面無(wú)法想事情了。我想出來(lái)的那些個(gè)事,你永遠(yuǎn)想不出。”[16]38阿娥只想活在“真空世界”的心態(tài),說(shuō)明她是自己鉆進(jìn)玻璃罐的。有人要拉她出來(lái),她也要千方百計(jì)回去。一旦“回不去”,她就會(huì)崩潰。與此類(lèi)似的,還有馬戲團(tuán)搬運(yùn)工長(zhǎng)發(fā)。《長(zhǎng)發(fā)的夢(mèng)想》中的長(zhǎng)發(fā)不敢接受新的工作,退縮在虛妄的世界里;《長(zhǎng)發(fā)的遭遇》中的長(zhǎng)發(fā)不僅自我放棄,甚至連家庭也要放棄。對(duì)于這些人物而言,不論是長(zhǎng)久平靜后突然爆發(fā)的瘋狂,還是在沉淪中的自我放棄,都是一種本能的、徒勞無(wú)益的突圍。但這種突圍不僅無(wú)法自救,還會(huì)在自我的閉環(huán)中陷得更深。
“解離”者的真正覺(jué)醒,在于正視自己的陰影。如《暗夜》里敏菊的猴山之旅,其實(shí)是她邁向自己的旅程。路上不斷出現(xiàn)一個(gè)要爬到猴山的單腿少年永植。敏菊時(shí)而變成永植,時(shí)而尋找永植。與永植的不斷相遇,是她與自己內(nèi)心世界的磨合、交鋒。最終她與永植合一,勇闖猴山。《家庭秘密》里,云香、阿芹發(fā)現(xiàn)自己有肢體再生功能。肢體象征自我的一部分,對(duì)肢體的切割、收藏、認(rèn)真觀察意味著認(rèn)識(shí)自我、剖析自我,肢體的再生則意味著重建自我。姐妹倆兒為了解“謎”而出走,最終卻發(fā)現(xiàn),謎底正是她們自己。《邊疆》中,女孩六瑾被父母遺忘在舉目無(wú)親的邊疆,卻意外找到了進(jìn)入自我世界的入口——小石城。在這里她聽(tīng)到了地下的水聲,蟲(chóng)子與風(fēng)的和聲……被遺棄的孩子象征著被放棄的自我,空靈的聲音則是靈魂深處的呼喚。“每當(dāng)我處在人生的轉(zhuǎn)折點(diǎn)上,從另一世界里就會(huì)傳出那種聲音來(lái),我的那些主人公就會(huì)開(kāi)口說(shuō)話……我一直在傾聽(tīng),至今仍然如此。”[5]320邊疆是“解離”者們找回自我的精神圣地,而那空靈的聲音,是引導(dǎo)靈魂回歸的歌聲。
結(jié) 語(yǔ)
“解離”對(duì)人、對(duì)己都是一種困擾。“解離”者試圖將自己放在真空環(huán)境中自我催眠、屏蔽痛苦,這使他們與他人、自我、真實(shí)的世界距離都很遙遠(yuǎn)。他們?nèi)粽娴南牖貧w自我,必須先看清自我。這樣的思考,離不開(kāi)超脫個(gè)人局限的眼光,殘雪卻在自我內(nèi)部越陷越深。
殘雪獨(dú)特的寫(xiě)作方式不是巫性的神啟,而是“解離”的迷思。對(duì)“解離”的巫性理解使她深陷內(nèi)部世界,精神的閉環(huán)實(shí)質(zhì)上消解了“靈魂探險(xiǎn)”的意義。相比于“靈魂分裂”,“解離”更恰當(dāng)?shù)亟忉屃藲堁┲爸i”,并為她的創(chuàng)作增添了一種社會(huì)觀察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