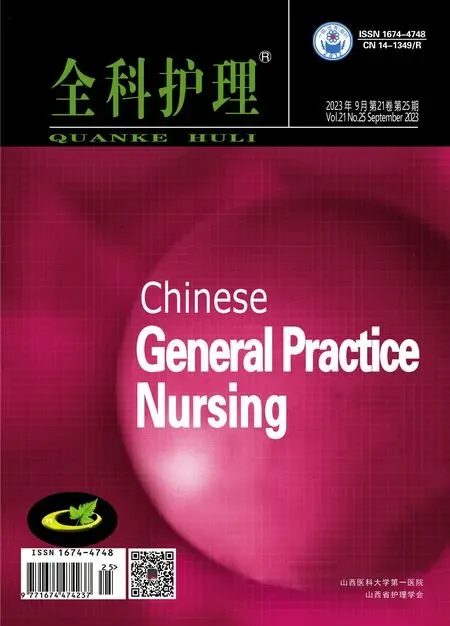癌癥病人疼痛災難化的研究進展
王汝霞,李福霞,李雪穎,楊麗娟,祝曉涵,孫 錚
疼痛是癌癥病人普遍存在的癥狀,由腫瘤本身或腫瘤治療引起。據調查,接受抗癌治療的癌癥病人疼痛發生率為24%~60%,晚期癌癥病人疼痛發生率為62%~86%,并且有超過1/3的病人疼痛分級可達中、重度[1]。癌癥病人疼痛災難化是指病人在接受癌癥疾病狀態前提下,依據自身及外部環境等因素對疼痛事件進行負向夸大的認知傾向[2]。研究表明,疼痛刺激過程中的“災難化”傾向會引發更強烈的疼痛體驗和更嚴重的情緒困擾,甚至可能會把急性疼痛轉變為慢性疼痛,最終導致殘疾[3-4]。疼痛災難化可以提前預警疼痛的發生,極大地影響干預時機,因此對于護理實踐來說至關重要。目前國內對于疼痛災難化的研究多集中在非癌性慢性疼痛,針對癌性疼痛的研究較少。本研究對癌癥病人疼痛災難化的影響因素和干預措施進行梳理,可為醫護人員今后制定更有效的干預方案提供依據,從而更好地預防和控制疼痛在風險人群中的發展。
1 疼痛災難化概述
疼痛災難化(pain catastrophizing,PC)這一概念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早期被定義為在痛苦經歷中產生的一種夸張的負面心理狀態[3-4]。后期其概念被進一步完善,指在實際或預期的疼痛體驗中產生的一種夸張的消極心理定勢,由反芻、夸大、無助3個維度構成[5]。反芻是指由于對疼痛的高度警惕與注意,導致大腦不受控制地經常性想象,是造成另外2個維度的根源[6-7]。夸大是指放大對事物的負面后果,無助是指個體對控制病情的信心嚴重喪失。在Lazarus和Folkman的壓力與應對模型中,反芻和夸大被視為疼痛應激源的初級評價,無助被視為次級評價[3,7]。證據表明,災難性思維可能是疼痛相關恐懼的前兆。Crombez等[8]認為高頻率災難性思考者比低頻率思考者在受到劇烈疼痛的威脅時更加恐懼。Lethem等在1983年提出了夸大疼痛感知的恐懼-回避模型[6],該模型的核心概念是對疼痛的恐懼,其中“對抗”和“回避”是對恐懼的2種極端反應,前者導致恐懼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少,后者導致恐懼維持或加劇。疼痛災難化是一種適應不良的應對策略,可促進癥狀的過度警覺和活動回避,而疼痛恐懼-回避信念的產生和強化,又會促使病人產生疼痛災難化的心理。最終,這種循環會導致病人身心健康和生活質量日益下降[9]。因此,造成殘疾的不僅是疼痛本身,還有心理和行為過程。
2 疼痛災難化評估工具
2.1 疼痛災難化量表
疼痛災難化量表(Pain Catastrophizing Scale,PCS)由Sullivan等[10]在1995年編制,用來評估個體疼痛時災難化思維強度,目前已經歐洲地區廣泛應用。該量表由反芻(4個條目)、夸大(3個條目)、無助(6個條目)3個維度,共13個條目組成。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每個條目采用0~4分計分,0分表示“完全沒有”,4分表示“所有時間”,總分為0~52分,得分≥38分說明達到疼痛災難化水平,得分越高表示災難化程度越高。我國學者Yap等[11]在2008年將該量表漢化,漢化后的量表各維度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39,0.768,0.809,信效度良好。
2.2 應對策略問卷
應對策略問卷(Coping Strategies Questionnaire,CSQ)由Rosenstiel等[12]于1983年編制,由忽視疼痛、疼痛的重新解釋、轉移注意力、自我應對、災難化、祈禱/希望、提高活動水平、增加疼痛行為8個維度,共50個條目組成。采用Likert 7級評分法,分數與疼痛災難化程度成正比。其中災難化維度共8個條目,Cronbach′s α系數為0.78~0.84,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該量表可靠性良好,評估內容全面,但是未多維度測量疼痛災難化程度,因此與PCS的評分結果存在差異[13]。
2.3 其他量表
除上述評估工具外,還有認知應對策略量表(Cognitive Coping Strategies Inventory,CCSI)、疼痛認知清單(Pain Cognition List,PCL)、疼痛相關自我陳述量表(Pain Related Self-statements Scale,PRSS)等測量工具,但是由于沒有深入研究災難性思維的具體維度,也沒有研究單獨針對其中災難化維度的信效度進行檢驗,因此并未獨立用于疼痛災難化的評估[14]。
3 癌癥病人疼痛災難化的影響因素
3.1 人口社會學因素
性別是影響癌癥病人疼痛災難化水平的關鍵因素之一。Cederberg等[15]在一項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癌癥病人的研究中指出,女孩的疼痛災難化程度要比男孩高,與此同時,女孩比男孩更容易通過哭泣、尖叫或表現出憤怒等方式來對疼痛做出反應[4]。對于年齡與癌癥病人疼痛災難化水平的關系尚存在爭議。Poulin等[9]對76例平均年齡為57歲的癌癥幸存者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年齡與疼痛災難化水平呈負相關,年輕病人比年老病人更容易報告疼痛,與Jacobsen等[16]的研究結果一致。但是Patton等[17]在對140例8~25歲癌癥幸存者的研究中指出,年齡越大,疼痛發生率越高,疼痛災難化程度越高。而Cederberg等[15]對61例7~18歲兒童和青少年癌癥病人的研究顯示,年齡對病人疼痛災難化水平的影響不明顯。這些研究結果的差別可能與被調查者的年齡段、癌癥類型以及疼痛程度不同有關。病人的婚姻狀況也與疼痛災難化水平相關。向微等[18]對81例乳腺癌骨轉移病人的橫斷面研究顯示,子女、配偶等家庭成員的支持對降低病人疼痛災難化水平有積極意義。
3.2 疾病相關因素
疼痛災難化水平與不同強度的疼痛體驗相關。Habib等[19-20]在研究中提到,疼痛災難化得分與癌癥病人疼痛強度增加有關,與Tait等[21]的研究結果一致。Keefe等[22]在對胃腸道癌癥病人的研究中指出,疼痛災難化水平與病人前1周的平均疼痛程度顯著相關。疼痛持續時間也是疼痛災難化的重要影響因素。Terkawi等[23]對頭頸癌病人的調查中顯示,慢性疼痛病人比急性疼痛病人疼痛災難化水平高。Bovbjerg等[24-25]在研究中也發現,經歷持續癌性疼痛的病人往往會表現出更高水平的疼痛災難化狀態。除此之外,Baets等[26]在探討有關乳腺癌術后婦女認知影響因素的研究中表明,疼痛災難化程度與機體功能失調程度密切相關。Schreiber等[25]在研究中提及疼痛災難化與個體疼痛敏感度增強密切相關,并且對個體標準化疼痛刺激的反應進行定量感覺測試,可以預測術后急性疼痛的嚴重程度。另外,頻繁、持續的就診或住院可能會促使衛生專業人員采取更密集、更具有侵入性的治療方法,這也會使癌癥病人產生疼痛的夸張表現[4]。
3.3 心理因素
疼痛不僅會使病人產生心理困擾,而且心理困擾實際上也會增強疼痛沖動的神經傳遞。研究表明,積極情緒會削弱疼痛沖動的傳導,而消極情緒則會增強疼痛沖動傳導[15]。
3.3.1 正性情緒
疼痛意愿指的是在不控制疼痛的情況下體驗疼痛的意愿,它是衡量病人對疼痛接受程度的指標之一。Gauthier等[27]在探討晚期癌癥病人疼痛接受度的相關研究中指出,疼痛意愿與疼痛災難化水平呈負相關。疼痛自我效能感是指人們利用自身內部資源控制疼痛的自信程度。Fisher等[28]在對乳腺癌病人的調查研究中發現,疼痛自我效能感得分越高,疼痛災難化得分越低。除此之外,Prasertsri等[29]在關于肺癌病人應對方式的研究中指出,傾向于壓抑性應對方式的病人疼痛災難化發生率明顯降低,原因可能在于壓抑性應對方式與更高的疼痛耐受性相關。Poulin等[9]對經歷過慢性神經病理性疼痛的癌癥幸存者進行橫斷面調查,結果顯示正念可以抵消高水平疼痛導致災難的趨勢,并且能夠顯著調節疼痛強度和疼痛災難之間的關系。這些研究說明正性情緒對降低疼痛災難化水平有積極意義。
3.3.2 負性情緒
情感表達的矛盾心理(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AEE),指的是想要表達自己的情感但又擔心表達后果的心理沖突。Porter等[30]在對胃腸道癌癥病人及其護理者的研究中指出,情感表達方面過多的心理沖突和困惑可能使癌癥病人轉向關注身體癥狀,容易導致疼痛災難化現象發生,并且疼痛災難化也介導了病人和護理者AEE對癌癥病人某些結局的影響。依戀風格可能會影響疼痛災難化水平。Gauthier等[31]在探索晚期癌癥病人疼痛災難化水平與依戀風格關系的研究中指出,疼痛災難化與焦慮型依戀呈正相關,與回避型依戀無關。除此之外,Fisher等[28]在研究中發現,疼痛災難化水平與病人抑郁水平呈顯著正相關,并且在抑郁癥狀和疼痛程度之間起中介作用。Sullivan等[4]的研究結果則顯示,焦慮與疼痛災難化存在顯著關聯。以上研究表明,負性情緒可以促進病人疼痛災難化思維的發展。
3.4 社會支持
Keefe等[22]以70例胃腸道癌癥病人及其照顧者為樣本,研究疼痛災難化與社會支持的關系時指出,疼痛災難化的發生與病人對工具支持的感知顯著相關,但與病人對情感支持的感知無關。例如胃腸癌和睪丸癌病人在日常活動時需要工具協助,但是護理人員提供的工具性支持可能有助于加強和維持高水平的疼痛災難化行為,從而加劇疼痛災難化對病人和照顧者的負面影響。并且當照顧者的壓力增加時,病人可能難以應對照顧者承受的高壓,轉向加重疼痛災難化水平。向微等[18]對乳腺癌骨轉移病人的橫斷面研究顯示,社會支持的增強以及人際關系的改善均與疼痛災難化各維度之間呈顯著負相關,這意味著社會支持對改善災難化水平有積極意義。
4 癌癥病人疼痛災難化的干預措施
4.1 疼痛教育
Pas等[32]在研究中對30例癌癥幸存者進行一對一疼痛神經科學教育(pain neuroscience education,PNE),主題包括急慢性疼痛的特征、急性疼痛起源、疼痛的演變以及持續性疼痛的潛在維持因素等。除此之外,研究人員還向病人發放了有關神經疼痛生理學的信息宣傳單以便病人閱讀。結果顯示,2周后病人疼痛災難化的反芻與無助維度得分顯著降低,與Manfuku等[33]的研究結果一致,說明PNE可有效降低癌癥病人的疼痛災難化水平。Lai等[34]針對36例中、重度癌癥病人設計了一項隨機對照試驗,來評估結構化疼痛教育計劃對住院癌癥病人疼痛體驗的影響。結果顯示接受結構化疼痛教育的病人疼痛災難化程度顯著降低,說明結構化疼痛教育可以有效改善住院癌癥病人的疼痛體驗。
4.2 多模式身心療法
Cyr等[35]對31例具有性交障礙的婦科癌癥幸存者設計了一項干預研究,即對參與者每周進行12次、每次60 min的多模式物理治療。具體內容包括知識教育、盆底肌肉鍛煉、使用小型陰道內探頭的肌電圖生物反饋、手動治療和家庭鍛煉計劃。結果顯示,經物理治療后病人自我效能感增強,疼痛災難化水平顯著下降。氣功身心鍛煉(Qigong Mind-Body Exercise,QMBE)是基于緩慢、有意識的呼吸運動和各種認知技能,放松機體精神、改善健康狀態的訓練方式。Osypiuk等[36]對術后患有持續性疼痛的42例乳腺癌幸存者實施為期12周、每周80 min的QMBE干預,內容包括上肢伸展、膈膜呼吸和集中注意力等認知技能鍛煉。結果顯示,癌癥幸存者經氣功身心鍛煉后,疼痛災難化現象得到改善。
4.3 認知行為療法
認知行為療法是改善慢性疼痛病人認知和行為的一種心理治療方法。Lukas等[37]在一項試驗中將138例疼痛災難化得分高的乳腺癌病人隨機分配到在線認知-行為訓練組或在線教育組(進行生活方式指導),對得分相對較低的322例病人進行常規治療。其中在線認知-行為訓練(online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e-CBT)課程要素包括認知重建、放松練習、應對焦慮、活動-休息平衡等,結果顯示圍術期進行e-CBT可有效降低病人的疼痛災難化水平。疼痛應對技能培訓(pain coping skills training,PCST)屬于疼痛管理認知行為療法的一種。Somers等[38]在試驗中對各類癌癥病人應用移動健康技術(移動設備上的視頻會議)提供短暫的PCST,解決可能影響病人的社會認知因素,增強他們管理疼痛的信心。結果顯示干預后病人的疼痛災難化現象明顯好轉,說明疼痛應對技能培訓在管理病人疼痛方面是一項可行的選擇。
4.4 正念減壓療法
正念減壓療法是通過正念冥想訓練減輕個體壓力、加強情緒管理的心理治療方法,包括正念瑜伽、靜坐冥想、轉移注意力等形式。Johannsen等[39]對129例接受原發性乳腺癌治療的女性設計了一項隨機對照試驗,結果顯示,正念認知療法可以改善病人的疼痛認知和反應,緩解病人的負性情緒,從而間接降低疼痛災難化水平,與侯云霞等[40]的說法一致。另外,此研究還顯示疼痛災難化介導了正念認知療法對乳腺癌病人持續性疼痛的影響。
5 思考與展望
疼痛災難化是癌性疼痛病人主要的負面心理情緒之一,受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目前,國外對癌癥病人疼痛災難化的研究已較為成熟,但是國內對此類人群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后續研究可以深入探索疼痛災難化的影響因素在癌癥種類與分型方面的差異,以及不同的干預措施對疼痛災難化各維度間的不同影響。同時,在臨床實踐中可以將疼痛災難化作為病人術后疼痛程度的預測指標,將其列為住院癌癥病人的常規評估內容,以便醫護人員提前干預,改善病人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