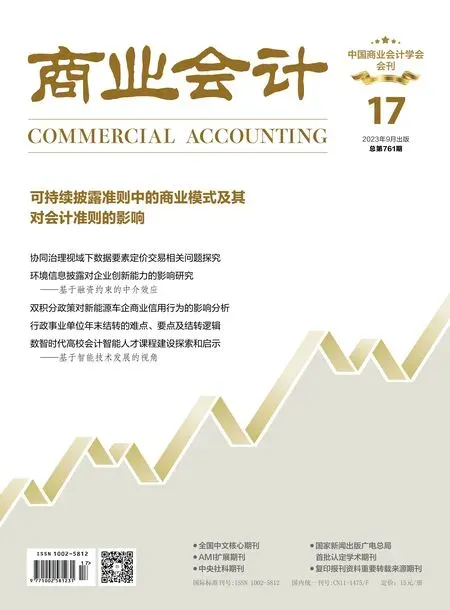環境信息披露對企業創新能力的影響研究
——基于融資約束的中介效應
遲錚(副教授/博士)
(大連外國語大學商學院 遼寧 大連 116044)
一、引言
當前,創新不僅是企業獲取和維持競爭優勢的必然選擇,也是推動國家技術進步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源泉動力。重大科技創新成果是關系到國家經濟、國防等方面安全的國之重器,一定要依靠自主研發使之牢牢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單位,同時也是國家的創新主體,企業層面創新成果的匯聚影響著國家整體的創新水平。因此,在新時代,如何進一步完善企業的制度環境以提升企業創新能力,已成為我國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進程中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近年來,隨著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關注企業創新的動因。研究的結果表明,影響企業創新的因素來自于諸多方面,如宏觀產業政策(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環境規制(齊紹洲等,2018;羅斌等,2020;王珍愚等,2021;李依等,2021)、政府補助(楊芷晴等,2019;鄭飛等,2021)、融資約束(董有德和陳蓓,2021;錢雪松等,2021),以及企業信息披露(徐輝等,2020;張哲和葛順奇,2021)等。已有研究在為促進企業創新建言獻策的同時,也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理論和方法。但經文獻梳理不難發現,已有研究中很少基于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視角來探索污染類企業創新能力的影響因素,而這一問題正是本文研究的核心。
不同于一般企業,污染類企業的創新活動具有更加顯著的正外部性特征(原毅軍和謝榮輝,2015),其披露的履行環境保護責任的信息也是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關注的信息。在當前“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可持續發展理念下,污染類企業能否通過技術研發來改變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生產方式和經營模式,能否在環境表現和履行環境保護責任方面交出一份讓社會各界普遍滿意的“答卷”,這不僅關系到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也會對我國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雙贏的戰略目標產生重要的影響。基于此,本文擬就污染類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對企業創新能力的影響展開研究,即試圖回答以下問題:第一,污染類企業提高環境信息披露質量是否對企業創新能力產生影響?第二,污染類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是通過何種路徑影響企業的創新能力?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環境信息披露與企業創新能力
創造性破壞理論(Schumpeter,1942)認為,企業為獲取超額利潤并保持競爭力需淘汰落后的技術及生產體系,并通過自身不斷的創新來實現企業的發展。創新能力是企業持續經營及保持競爭力的決定性要素。然而,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現代企業中,經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會損害股東的利益,從而產生代理問題(Jensen 和Meckling,1976)。也就是說,企業實際管理者會出于自利動機而瞞報企業的負面信息,從而使得企業風險無法及時地被企業的所有者感知,造成所有者的經濟利益受損。尤其是創新產出的收益具有跨期性,企業也不便對外披露創新項目的關鍵信息,所披露的也僅僅是非關鍵的信息,這都會產生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及代理問題,從而為管理者操縱研發活動以追求私利提供便利條件(徐輝等,2020)。內部控制雖然可以防范“內部人控制”下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但內部控制自身存在重大缺陷,也不利于企業持續的增加創新投入。企業的創新行為與社會信任有密切關系,社會信任會幫助企業獲取銀行等金融機構所發放的商業信用貸款,解決企業在研發及創新活動中所需要的資金問題,從而幫助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產生更多的發明專利(李雙建等,2020)。而社會公眾利益受損是源于社會公眾環境知情權的缺失和企業的環境失信行為,從而導致失信于銀行、投資者等利益相關者,企業的研發創新因為缺乏資金而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張哲和葛順奇,2021)。可見,由于現代企業兩權分離的特征,以及企業創新行為對社會資源的高度依賴性,亟需有效的信息披露機制來緩解企業與股東等外部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代理沖突和信息不對稱問題,進而推動企業的創新活動。
環境信息披露作為一種有效的企業信息披露機制,可以增強企業環境信息的透明度,以及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溝通(Inoue,2016),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楊張萌和彭效冉,2023),不僅有助于潛在的投資者了解企業環境責任受托履行情況及未來發展規劃,形成對企業價值的合理評估并做出有效的決策(Hamilton,1995),還可以產生對信息披露方的潛在監督作用,迫使企業的實際管理者收斂其用占據信息資源優勢而攫取外部投資者利益的行為,進而緩解利益沖突、降低代理成本和提高盈余質量。由于社會公眾評估與判斷企業環境風險的主要信息來源是環境信息,所以高質量的環境信息披露也是企業獲得外部利益相關者認可的重要途徑。例如,環境績效良好的企業往往會通過環境信息“告白”行為來獲得投資者的認可(沈洪濤等,2014);為了獲得、維持或修復合法性地位并爭取獲得利益相關者的理解、支持和信任,企業大都會通過披露對自身有利的環境信息來塑造良好形象和釋放“利好”信號,從而為企業創新戰略的順利實施創造條件(趙晶和孟維烜,2016)。此外,企業環境信息披露還具有信息增量效應,高質量的環境信息既可以改善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整體評價,使企業獲得利益相關者的支持,又有助于銀行等利益相關者督促企業制定合理的研發方案,規范研發行為,提高研發資金利用效率,降低研發失敗風險,進而提升企業創新能力(Ball et al,2018;徐輝等,2020)。綜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設1:
H1:環境信息披露有助于污染類企業提升創新能力。
(二)環境信息披露、融資約束與企業創新能力
企業開展創新活動,離不開研發資金的投入(Aghion和Howitt,1992)。資金是企業的“血液”,也是支撐企業研發創新的物資基礎。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是企業所需資金的主要來源。根據優序融資理論(Myers 和Majluf,1984),我國污染類企業在面臨融資選擇時,進行外源融資的首選是債務性融資而非股權融資,從而避免向外界傳遞出企業經營情況不甚理想的信號。當“融資難”和“融資貴”已成為污染類企業普遍存在的“老大難”問題時,能否緩解債務融資約束顯然是影響企業尤其是污染類企業研發和創新活動的關鍵(錢雪松等,2021)。
污染類企業面臨較大的債務融資約束可能源于以下兩個原因:一是污染類企業所面臨的綠色信貸政策的融資懲罰效應。我國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全面打響標志著對污染類企業的管控變得更加嚴格。國家出臺的綠色信貸政策更是要求金融機構嚴格控制向重污染企業發放貸款,信貸投放的對象應優先保證符合環保法律法規和政策的企業。綠色信貸政策意味著屬于綠色信貸政策“融資懲罰”對象的污染類企業,會較難獲得信貸資金的支持。二是行業特質給金融機構等債權人所帶來的高風險感知。行業特質是影響債權人風險感知的重要因素,若債權人的風險感知較高,則債務人不易獲得信貸資金,其融資能力也會隨之大大降低。由于污染類企業固有的環境問題往往會引發業績下滑風險、壞賬風險和環境訴訟風險,而債權人出于對這些潛在風險的擔憂,在與污染類企業簽訂的信貸合同中會加入更多限制性條款或提高對方債務成本從而保護自身利益。因此,環境信息披露能否幫助污染類企業提高聲譽度,并降低債權人的風險感知來緩解融資約束,無疑是影響企業創新成敗的重中之重。
污染類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不但傳遞了企業環境管理的成效和不足等實際情況,也展示了企業敢于承擔自身應承擔的環境保護責任的態度和實力,更是直接體現了污染類企業對利益相關者所擁有的環境知情權和參與權的充分尊重。污染類企業讓公眾最擔憂的是環境風險,而通過環境信息披露,可以讓公眾了解節能減排、污染防治和環保投資等信息,可以大大緩解企業與信貸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El Ghoul et al,2011;黃蓉和何宇婷,2020),有助于有社會責任感的債權人對債務人的風險水平和償債能力做出合理的判定,從而有利于進一步降低債權人對債務人的風險感知,以及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Zhao et al,2014)。而且企業積極的“綠色善意”表現也有利于維護其聲譽,改善投資者對企業的認知,從而降低企業的股權融資成本(Botosan,1997),使企業也更容易在資本市場獲得融資(Clarkson et al,2004;許罡,2020),進而有充足的資金用于研發與創新(部莉珺等,2023;張允萌,2021)。可見,污染類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可以通過緩解融資約束來提升企業創新能力。綜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設2:
H2:污染類企業可通過提高環境信息披露質量來緩解融資約束進而促進創新,即融資約束在環境信息披露對污染類企業創新能力的影響中具有部分中介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選取與模型設定
1.變量選取。
(1)企業創新能力(INNO)。本文參考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的研究,選用污染類企業當年的專利申請數量來衡量企業創新能力。這是因為企業當年的專利申請數量不易受其他因素干擾,可以較好地反映企業的創新產出能力。
(2)環境信息披露(EID)。本文參考畢茜等(2012)的研究,根據生態環境部、上海證券交易所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形式和內容要求,從披露載體、環境管理、環境成本、環境負債、環境投資、環境業績與環境治理、政府監管與機構認證等方面構建污染類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指數來測度與評價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
(3)融資約束(FC)。本文借鑒Kaplan 和Zingales(1997)的研究來計算KZ指數,并以該指數衡量污染類企業所面臨的融資約束。KZ 指數構建步驟如下:第一,按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與期初的總資產之比(CFi,t∕At-1)、現金股利與期初的總資產之比(DIVi,t∕At-1)、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與期初的總資產之比(CASHi,t∕At-1)、資產負債率(DTAi,t)、托賓Q值(TQi,t)等五個指標對樣本進行分類。如某一樣本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與期初的總資產之比(CFi,t∕At-1)小于全樣本的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與期初的總資產之比(CFi,t∕At-1)中位數,則kz1 取值1,否則為0;同理,如某一樣本企業的現金股利與期初的總資產之比(DIVi,t∕At-1)、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與期初的總資產之比(CASHi,t∕At-1)均小于全樣本現金股利與期初的總資產之比(DIVi,t∕At-1)、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與期初的總資產之比(CASHi,t∕At-1)中位數,則kz2、kz3 均為1,否則取0;如某一樣本企業的資產負債率(DTAi,t)大于全樣本資產負債率(DTAi,t)的中位數,則kz4 取值1,否則取0;如某一樣本企業的托賓Q值(TQi,t)大于全樣本托賓Q值(TQi,t)中位數,則kz5取值1,否則為0。第二,令KZ=kz1+kz2+kz3+kz4+kz5來計算KZ指數。第三,將KZ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與期初的總資產之比(CFi,t∕At-1)、現金股利與期初的總資產之比(DIVi,t∕At-1)、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與期初的總資產之比(CASHi,t∕At-1)、資產負債率(DTAi,t)、托賓Q 值(TQi,t)等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從而得出各變量的回歸系數,并將回歸系數作為每個樣本企業計算其某一年KZ指數的依據。
(4)控制變量(CONTROL)。本文控制了產權性質(STATE)等變量。控制變量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及其定義表
2.模型設定。為檢驗環境信息披露(EID)對污染類企業創新能力(INNO)的影響,以及融資約束(FC)在兩者關系中所發揮的中介效應,本文借鑒Baron和Kenny(1986)的研究分別構建模型如下:
其中,EIDi,t代表企業i在第t年的環境信息披露水平;FCi,t代表企業i 在第t 年的融資約束;INNOi,t代表企業i 在第t 年的創新能力;模型(1)用以檢驗環境信息披露(EID)對污染類企業創新能力(INNO)的影響,即檢驗假設1是否成立;模型(2)用以檢驗環境信息披露(EID)對融資約束(FC)的影響;模型(3)用以檢驗環境信息披露(EID)、融資約束(FC)對污染類企業創新能力(INNO)的影響,并根據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回歸結果來檢驗假設2 是否成立。
(二)樣本與數據來源
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與調整后的《上市環保核查制度》均在2014 年發布,所以本文選取2014—2021年滬深A 股污染類企業作為研究樣本,這樣做既與新時代的制度特點相契合,也可以避免外生的政策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沖擊影響。本文以證監會2012年修訂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來界定污染類企業的范圍。主要變量中的企業創新能力(INNO)數據,主要來源于污染類企業上市公司年度報告的財務報表附注中企業當年所申請的專利數量,即將企業當年專利申請數量作為企業當年的創新能力度量指標。主要變量中的環境信息披露(EID)數據,主要以披露載體、環境管理、環境成本、環境負債、環境投資、環境業績與環境治理、政府監管與機構認證等有關內容為依據,通過手工統計而獲得的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指數。融資約束(FC)是通過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與期初的總資產之比、現金股利與期初的總資產之比、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與期初的總資產之比、資產負債率、托賓Q值等來計算從而獲得KZ指數。本文在污染類企業原始樣本的基礎上剔除屬于ST、*ST的樣本企業,以及變量數據缺失的樣本企業,共計獲得3 432個年度觀測值,以此來保證研究結論的可靠性。企業當年所申請的專利數量、企業第一大股東的性質、企業期末總資產額(At)、企業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企業前三位高管人員薪酬總數額、企業獨立董事人數、企業董事會人數、凈資產收益率(ROE)、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CFi,t)、公司期初總資產額(At-1)、現金股利(DIVi,t)、現金及現金等價物(CASHi,t)、資產負債率(DTAi,t)、托賓Q 值(TQi,t)等數據均從國泰安CSMAR數據庫采集。披露載體、環境管理、環境成本、環境負債、環境投資、環境業績與環境治理、政府監管與機構認證等內容取自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環境報告和可持續發展報告。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本文的變量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表
從表2可以看出,在主要變量當中,企業創新能力(INNO)的最大值為7.2528,最小值為0,均值為2.4944,表明樣本中各企業每年申請專利的數量差距較大,各企業創新能力參差不齊;環境信息披露(EID)的最大值為0.9231,最小值為0,均值為0.4262,標準差為0.1915,表明大部分樣本公司都能積極進行披露與本企業有關的環境信息;融資約束(FC)的最大值為7.2970,最小值為0.0001,均值為0.6822,表明各企業在融資方面受到約束的情況不盡相同,多數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較弱。
(二)主檢驗的回歸分析
為驗證假設1 和假設2,本文分別通過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來檢驗環境信息披露(EID)與企業創新能力(INNO)、環境信息披露(EID)與融資約束(FC)、環境信息披露(EID)及融資約束(FC)與企業創新能力(INNO)的關系。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主檢驗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主檢驗回歸結果表
表3 報告了主檢驗的回歸結果。模型(1)的被解釋變量是企業創新能力(INNO),解釋變量是環境信息披露(EID);模型(2)是以融資約束(FC)作為被解釋變量,環境信息披露(EID)作為解釋變量來檢驗環境信息披露(EID)對融資約束(FC)的影響;模型(3)是以企業創新能力(INNO)作為被解釋變量,環境信息披露(EID)、融資約束(FC)作為解釋變量來檢驗環境信息披露(EID)、融資約束(FC)對污染類企業創新能力(INNO)的影響。模型(1)的回歸結果顯示,環境信息披露(EID)與企業創新能力(INNO)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359,即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水平(EID)越高,企業創新能力(INNO)會越強,假設1 得到驗證。這表明,污染類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對提升企業創新能力有著正向的推動作用。模型(2)的回歸結果顯示,環境信息披露(EID)與融資約束(FC)在10%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063,這表明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EID)越高,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FC)會越弱,即污染類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情況越好,越有利于緩解融資約束,使得企業較易獲得資金支持。模型(3)的回歸結果顯示,環境信息披露(EID)與企業創新能力(INNO)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354;融資約束(FC)與企業創新能力(INNO)在5%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077,這表明融資約束(FC)越弱,越有利于提升污染類企業創新能力(INNO)。通過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回歸結果可知,在模型(3)中的環境信息披露(EID)的系數0.354 小于在模型(1)中的環境信息披露(EID)的系數0.359,且環境信息披露(EID)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均顯著,顯然,融資約束(FC)在環境信息披露(EID)與企業創新能力(INNO)之間的關系中發揮了部分中介效應,即假設2得到驗證。這表明,污染類企業可以通過提升環境信息披露水平來緩解融資約束,進而為企業創新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分別使用工具變量法和替換被解釋變量法兩種方法,對經過驗證的假設1和假設2來進行檢驗并以此來克服模型的內生性問題。
1.工具變量法。本文首先將樣本公司的社會責任指數(CSR)作為工具變量,加入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隨后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歸,以此來驗證本文的實證結果。這樣做的理由是,當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情況較好時,會傾向于多披露諸如環境表現等信息,但這不會輕易改變其創新能力,即企業的社會責任指數(CSR)會影響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EID),但不會直接影響企業的創新(INNO),因此,樣本公司的社會責任指數(CSR)可以作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工具變量。企業的社會責任指數(CSR)取自潤靈環球社會責任報告。加入工具變量的回歸分析如表4所示。

表4 加入工具變量的回歸分析表
由表4可知,環境信息披露(EID)在模型(1)和模型(3)中均顯著為正,在模型(2)中的系數為-0.211,顯著為負,融資約束(FC)在模型(3)中的系數為-0.07,顯著為負,且模型(3)中的環境信息披露(EID)的系數2.910 小于模型(1)中的環境信息披露(EID)的系數2.924。顯然,本文的假設1和假設2得到進一步的驗證。
2.替換被解釋變量法。為驗證實證結果的可靠性,本文借鑒齊紹洲等(2018)的研究,采用企業被授權專利數作為企業創新的替代變量,并將模型(1)、模型(2)和模型(3)重新進行回歸。表5 是替換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分析表。環境信息披露(EID)的系數在模型(1)和模型(3)中均顯著為正,在模型(2)中的系數為-0.117,顯著為負,融資約束(FC)在模型(3)中的系數為-0.054,顯著為負,且模型(3)中的環境信息披露(EID)的系數(0.351)小于在模型(1)中的環境信息披露(EID)系數(0.354)。本文的假設再次得到印證。

表5 替代被解釋變量的回歸分析表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1)環境信息披露與污染類企業創新能力呈顯著正相關關系,換言之,污染類企業提高環境信息披露質量有助于提升污染類企業創新能力;(2)融資約束在污染類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對企業創新能力的影響關系中發揮部分中介效應,即污染類企業可通過提高環境信息披露質量來緩解融資約束進而促進創新。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1)環境屬于公共產品,應充分發揮政府“有形之手”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監管職能,這既是進一步完善環境信息披露制度,督促污染類企業履行環境責任、提高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需要,也是推動企業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舉措。同時,污染類企業應格外重視輿論動態和公眾環保訴求,要及時回應利益相關者關切的污染物和碳排放問題,并通過企業官方網站、微博、微信公眾號等媒介來積極披露自愿履行環境保護責任的信息。該信息既應通過企業財務報表附注的形式加以體現,也應通過單獨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或企業環境責任報告來進行披露。這不僅表明企業對利益相關者環保知情權的尊重,也能充分展示企業踐行綠色低碳發展理念、努力承擔社會責任的信心。(2)銀行等金融機構應踐行綠色金融理念,將綠色信貸支持范圍涵蓋污染類企業的研發項目,進而為企業的創新活動提供物質基礎。相關部門也應出臺相關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評價指標體系,以便于商業銀行等機構來進行信貸審批決策。對于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較低的企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應減少對其信貸支持力度,進而將信貸資金優先用于支持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較高的企業,給予這類企業以優惠待遇,以此來發揮綠色信貸對于企業創新的激勵作用并助力企業走綠色發展之路。(3)由于環境信息披露對污染類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效應在不同類型的企業間具有較明顯的異質性特征,故應摒棄現行的企業環境信息披露“一刀切”做法,對于不同產權性質及類型的企業所承擔的強制性披露環境信息的義務應加以區分。(4)“有為才能有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能否得到利益相關者的認可,關鍵在于企業在環保投資、污染防治方面的表現。因而,污染類企業發展中的當務之急是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大力實施綠色轉型戰略,塑造良好的公眾形象,這是企業獲得社會資源以及創新發展不可或缺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