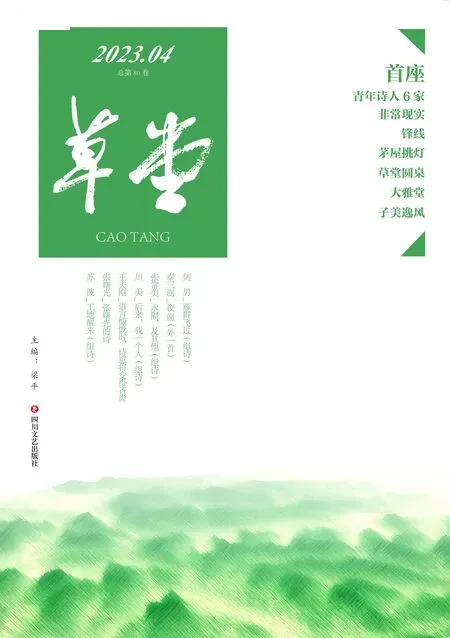非知的夜(組詩)
◎孔令劍
[緩慢之夜]
一個比喻。讀扎加耶夫斯基像
吃魚,代縣熬魚,慢火,久時
秋冬之夜,公路邊。飯館冷清
但燈光明亮,孤獨的吃魚人
漸漸品嘗出孤獨的美味——
窗外的生活繼續,重型貨車
不時疾馳而過,嘶吼著
掀起陣陣塵煙,仿佛目的地
就在道路的某個端點,充滿耐心
——詩歌,找到并把尖銳的魚刺
一根根挑出去的耐心,不是
鮮美的魚肉,一塊塊送到嘴邊
它的企圖,也不是扎你的喉嚨
而是讓余味持續得更久——
正如生活本身,遭遇和意義
緩慢地,扎加耶夫斯基寫下詩的整體
像一座大廈。我們要更加緩慢
沿著樓梯一步一步,走進某種幽暗
然后等待,眼睛,明亮而無所不見
仿如站在更高處的天臺,看人間
古往今來。吃魚的人還在細細品味
愜意似一種自我治愈,心底仿佛在說:
孤獨來的時候,孤獨的人
要把自己交出去,就像交出一張白卷
問題已列出,而答案,只是問題本身
[敞開之夜]
讀《空虛時代》,想到曾經的青春
是多么正確,花朵凋落,果實抵達
讀《家國天下》,知道如今的每個人
都已走過了幾千年,血液里,穩固的過去
和未來。讀《內在經驗》,懂得將自己
像房門一樣關閉,轉身走進夜的靜默
可能性的深淵才會敞開。讀《壇經》
仿佛看到自己曾經盲目信任的內心
善與忘我,仍是要竭力行進的彼岸
——心的世界,觸動我們之物終要歸來
2021 和2022 交接的冬季,夜晚,總是
從哪里吹來冷風的窗邊,墨綠色簾布
《中國大歷史》以及和長城有關的書籍
壘成臨時防風墻,我躺在下面,反復
閱讀著它們:《無形之手》《永恒的敵人》
《壇子軼事》《沉石與火舌》《水的空白》
《長長的錨鏈》……它們的名字聽起來
像一首首靜謐的元詩,目光輕踩詩行
仿佛要一直穿過地心,然后散開,并消失
在另一個世界的空氣——它們的創造者
也是自我的創造者,借助它們我要建造
自己的玻璃工廠,來到這里的人坦白一切
即使再小的光,也會被折射,無止境
而黑暗從不傳播。人們牢記,石頭和火焰
像曾經的少年,從淘洗后晾曬著的麥粒中
挑出細碎的雜石,一顆一顆,因丟棄而可貴
因丟棄而保持純粹,洗凈的麥粒,新磨的
面粉,自我的清香……整個過程寂靜而充滿
生機,仿佛詩人們的言語里,呼吸的影子
在跳舞,一片光的空無里,耳朵聽見誰的召喚
[詩思之夜]
沒有什么能夠逃離,生活的空氣
污濁,清新,總會有詩歌的呼吸
沒有哪一位詩人,不曾
在生活的河道漂游,從古至今
越是偉大的人,吃大海的鹽,越多
詩歌的質地就在入海口
咸淡之水,陸地與海洋,交鋒
混合,多樣,但不夠。生活持續
接到命令,奔赴他人的戰場
喘息中,聽見空曠的嗓音,從大地
濕熱的深處,加劇開采的礦井
負重的人,一只腳踏在地面
堅實的信任中,另一只,才有
邁出的可能,詩歌,是那只試圖
抬起的腳……還不夠。詩歌
應是一雙翅膀的抽象。助跑,側身
起跳,騰空,落地……賽場上
跳高選手全過程,揮舞的兩只手
持續釋放純正的詩歌:不是力
是一種隱秘,為越過一根
細細的橫桿,在生活和夢想之間
更多,在街道無人的夜,詩歌
是影子的全部事業。有誰
比自己的影子更疲累,更渴望
有誰,更堅定更迷狂,比自己
更孤單更靜默的原始的影子
一次次,走向下一盞街燈,沿著
某種不可計量的軌跡,影子從身前
越過頭頂,移到身后,越來越長
越來越細……詩歌,是影子
放飛的整個夜空:巨大,無聲
將被你所知,昏暗又明亮:某顆星
已為你,綴上永不熄滅的金色紐扣
[續夢之夜]
拿在枕邊的《科學與詩》還未翻動
微醺,昏昏欲睡,大腦被乳白色
空氣籠罩,窗邊的寒風輕柔了許多
燈光遲鈍,像承諾前無頭緒的思量
事物們連成一體,鏡頭慢移,夢
自然來臨并展開,多么順暢啊好像
發生在明天的事,又像一路走來
不息的河流,渾濁之水泛著光亮
隱約聽見自己的呼嚕聲,激烈
發自肺腑,醒來口舌干苦,嗓音
被再一次修正,仿佛關于時代之詩
詩人們各說各話,爭論到半夜
現在他們停下來,品嘗著黑色啤酒
凌晨一點,頭腦異常,干凈得像個新房
往里面搬什么都利落。夢中的“聲音
已停止,但影像還在轉啊轉”,卻不前進
漆黑的房間再次被臺燈的沉默點亮
繼續讀希尼《消失的島嶼》,1966 至1987
多么好的半部詩集,那個時期我醞釀
并來到這個世界,初入學校,還未熟悉
緊閉的鐵門,上課鈴聲,緊張混合著興奮
礦石人生的良好開端。而先前堅持
讀完的1988 至2013 卷,此刻才被告知:
自此往后,全靠熱愛和耐心。他人的
人生和詩,尤其后半部分,近于實驗
和嚴肅游戲,沒有提前死去的人
禁止模仿,而我在夢里又多活了一次
那里沒有否認秘史和欲望,沒有使過去
和未來貶值,一切的一切,仿佛存在于
詩意的瞬間,此刻,合起書頁拿起筆
記下非詩的詞句,返回夢中還不算太遲
——再次醒來,生活和夢將同樣讓人流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