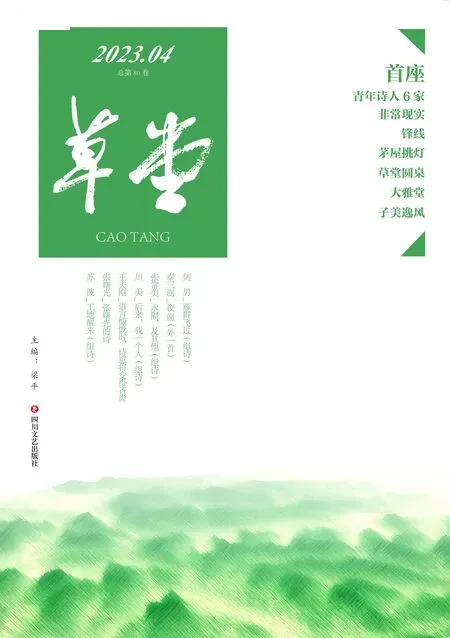夜 愿(外一首)
◎秦三澍
夜很勻。地再潮也要俯下去。
嗅覺承認它是失效的。
街角通電的柿子摘除了焦味兒,
等距地,陪我騎完與乞丐相逆的半程路。
他問,手慢慢攤開像清白的信:
“先生,最小的硬幣也行……”
腋下夾紙盒的男學生(他偷竊?)
從鏡片射出對警察的審查;
抱歉,你的疾行無法在罰款單上變現。
小獵犬狂吠。女主人道歉。
有密碼藏于記憶的醉少,手電光
揉著下一場烏云靦腆的肚子。
但手術刀銀亮的女聲在同幢樓的三層
激怒了陣雨。驚掉腋下的紙盒,
叫停清白的手勢,后者轉而舔
月暈圈住又搖勻的一層墨。
飄窗垂簾梯子,邀我們這免費的聽眾
一睹半裸的歌聲在浪尖停擺,
上揚,像沉到海底的座鐘
被魚鉤嶄新地輕輕撓著,不情愿
將身體一絲絲與青銅分離。
但她的嗓音讓我聽出一副精鋼刀叉
摔在地上前,已裹滿了油。
樓下頓足的醉少何不憤而爬梯,電光
魚叉般質疑她的瞳孔?
他錯誤的手將聲浪的齒輪摸壞。
一個新人,他,瘟疫中被劇院驅趕的
健康的小丑,把人心的弧度
當吊床無休止地擺著,直到警笛
軋住聲帶的半衰期。
變淺的蜜悠然呻吟著“父親”。
[L’Art de perdre 遺失之道]
I
針對你的植物性,你想用一些舊辦法。
憑信譽,能解釋得通嗎?
磨破的蜂群在另一簇花錐等著你模仿。
被削尖的芳香上,一個替你巡游的賭徒
贏得過一些被咬嚙的痕跡,
但不是替你。
你繞過他的夢。你能計算出的夢的軟邊
錯誤地塌陷到他該負責的區域。
手套偷走了你的手——似乎是幸運的?
風中露出一截侍者的白色。
像吃著印刷品的影子轉而被印刷。
他用步速在測試你
變成合格的新侍者之前,能否
像我建議的,這般想一個風餐的人。
II
他的聽眾在聽診器里。現場呢?一個對等物:
她的耳廓搖擺出女電報員的狡黠。
一把像樣的椅子承受著他樹脂般的聰明。他愿
意拿手中的信息交換到更少,卻不想稱之為舍
棄。植物性,這一秒與下一秒在毗鄰中添加過
它;它果真成了寡言的鄰居,像小銀扣扭著兩
個二分之一的手。這意味著更少。無論飾演過
多少次,她都反復說“真的與合拍無關”,她
知道看護著氣候對一個職業性的植物來說并不
算繁重。
但私募的激情何以替那不朽的男人
隱瞞?盲點在受罰,
像一個繞著配給制盤旋的節日
用爪子撥弄她的驕傲。
“你的缺席在朝他呼喊。”*
——“還在嗎?”醫生,最容易被清理的部分像
一份錄影更新著他自己。他發現的驚怖:一個有
待分析的記憶形成了微縮版本,跨越了性別看著
他。
III
他為他的苦惱重塑過牙齒。
坐姿,靠仰頭才能看清沒發育完成的希望,像絨
毛呈環狀附著在花粉細微的牙上。熱衷于采摘的
視線在觸摸到某種頑皮后被退回,超過一切迅疾
的東西,但它自信能找到屬于它的效率。
你能為你的捕獵換一批工具?
像一樁慈善事業:
在陷阱周圍,你寧愿你種植過的鏡子
依然遠播警示性的浪,
攀住嗅覺,它不斷被空氣的漏洞搶修著。
為此,蜂群發展出的歉意有一種晚期風味。
被排空后,一張信任票抵達。
所剩的嫣紅像鉛筆滑脫既有的軌道,
畫下微型橢圓:不完美的句號,完美的驟然。
上翹的姿勢不會沒有準備。
*: 引自Juliette Brevilliero 的“Le Chant du signe”詩。